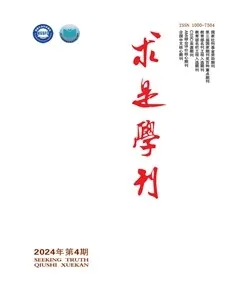中國傳統“道-藝”觀論要
摘 要:中國傳統“道-藝”觀對中國藝術創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道-藝”二元結構中去認識和處理藝術問題,充分彰顯出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民族性。中國傳統“道-藝”觀既豐富又立體,其中,“道器”論是對本體(本原之道)與實在(藝術之象)之隱顯關系的總體歸納;“道貫”論是對藝術創造中“一”與“多”關系的辯證提攝;“載道”論確立了中國古代藝術社會學“道主而藝從”的文藝認知格局;“同道”論主要涉及文化原型和藝術同構內秘之詮解;“樂道”論表征著中國古代藝術對審美境界與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全面了解中國傳統“道-藝”觀,對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藝術的生命意識、宇宙意識和超越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古代;藝術;“道-藝”觀;民族性
作者簡介:韓文革,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編輯部副編審(武漢 430063)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4.013
“道”“藝”關系是中國古代藝術理論探討中的一個核心論域。可以說,從“道-藝”二元結構中去認識和處理藝術問題,充分彰顯出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民族性,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豐富復雜的“道-藝”觀。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大多仍然停留在體用論層面的“道”本“器”(“藝”)用論以及工具論層面的“文以載道”論上,對中國傳統“道-藝”觀之豐富性的認識尚不夠深入。中國傳統“道-藝”觀既豐富又立體,涉及文藝領域及文藝活動諸多方面,除了體用論層面和工具論層面的探討之外,還有審美創造論層面的“道貫”論、文化原型論層面的“同道”論以及審美體驗論層面的倡導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合一的“樂道”論。只有對中國古代“道-藝”觀作不同理論層面的條分縷析的區分與總結,才能從慣常的認識中獲得對古代中國藝術處理“道”“藝”關系的新知,也才能充分了解中國文藝理論在理解世界本原同文藝創造及其特征之關系方面所顯示出來的民族性、獨特性。
一、“道器”論:本體(本原之道)與實在(藝術之象)之隱顯關系的總體歸納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道”是作為世界之本體而存在的,是指自然、社會運行的規律、原理,是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本質、本體、本原、本根性概念。如《易傳·系辭上》曰:“形而上者謂之道。”①王夫之也說:“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①這些對“道”的理解都是從形而上意義上展開或進行的。“器”則指體現道的實體、運載道的工具。《易傳·系辭上》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形乃謂之器。”韓康伯注曰:“成形曰器。”②孔穎達對無“形”之“道”與有“形”之“器”的這種形上與形下之別有非常詳細的闡述,其在《周易正義》中疏曰:“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無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也。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也。”③不難看出,老莊哲學中的有無論、《易經》中的道器論以及后世學者對道的理解都有其共同點,即強調有生于無,道統馭器,有形之器運載著無形之道,而無形之道又通過有形之器得以顯現,亦即道于無中生有,器于有中寓無。道所具有的超形而不離形的特點在中國哲學中也被反復論說。如老子認為,“道”先天地而生,“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且“不知其名”④,故而“道”具有超越普通形器的形而上特征;同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⑤,亦即“道”又具體落實到形而下的普通“物”“象”中。莊子也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信,可得而不可見。……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⑥《管子·內業》對道的描述也是:“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⑦不難看出,老莊及管子等人都充分注意到道與器、物、形、象之間不可分離的關系。
中國哲學中的“道器”論落實到藝術活動層面,其核心理念是將道與藝看作是隱與顯的關系。那么“藝”以什么來顯現“道”呢?中國傳統藝術哲學有著驚人一致的回答,即文(象)以明道,文以載道。“文”本義指線條或色彩交錯,引申為凡物之美麗而有文采謂之文。在古人看來,天文、地文、人文俱是道的顯現。如漢代陸賈即云:“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⑧明代宋濂也說:“人文之顯,始于何時?實肇于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⑨道以文(象)顯的思想在《周易》《禮記》等中國古代元典中隨處可見。劉師培曾總結說:
昔《大易》有言:“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考工》亦有言:“青與白謂之文,白與黑謂之章。”蓋伏羲畫卦,即判陰陽;隸首作數,始分奇偶。一陰一陽謂之道,一奇一偶謂之文。故剛柔交錯,文之垂于天者也;經緯天地,文之列于謚者也。三代之時,一字數用,凡禮樂法制,威儀言辭,古籍所載,咸謂之文。是則文也者,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也。由古迄今,文不一體,然循名責實,則經史諸子,體與文殊;惟偶語韻詞,體與文合。⑩
如果說《周易》《考工記》等元典中的顯“道”之“文”還主要指的是事物的形式美,而尚未專門言及具體的藝術及其創造問題,那么,東晉葛洪即已明確指出文藝形式美的重要性:“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因為道是隱匿難見、難尋的,所以作為傳道、達道、體道之重要載體的文、文章、文藝就不能視為“小道”或“余事”,因而他進一步斷言:“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余事也。”①相比于葛洪從現實生活經驗的直覺中認識到文章作為“道”(與“德”)之“弟”而不能“呼為余事”,劉勰顯然對此有著更高的理論綜合,其在《文心雕龍·原道》中明確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②即“道”是“文”之本,“文”乃“道”之顯,顯道之文由圣人出,故“文”因“圣”人而有明“道”之大用。劉勰首開的“文以明道”論,借助圣人這一中介把文藝與道的二元對立關系加以彌合起來,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真正建立起“道-藝”二元結構論,嗣后的中國文藝在討論世界本體與文藝之間的隱顯關系時,均不出此樊籬。湯用彤曾就“道”與“文”的關系作過如下精辟的概括:
萬物萬形皆有本源(本體),而本源不可言,文乃此本源之表現,而文且各有所偏。文人如何用語言表現其本源?陸機《文賦》謂當“佇中區以玄覽”。蓋文非易事,須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與之接,“籠天地(形外)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文當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蓋文并為虛無、寂寞(宇宙本體)之表現,而人善為文(善用此媒介),則方可成就籠天地之至文。至文不能限于“有”(萬有),不可囿于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方可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之最上乘,乃“虛無之有”、“寂寞之聲”,非能此則無以為至文。③
可以說,在中國傳統文藝理論中,這種道隱藝顯的觀點無處不在。如唐代徐寅即認為“勢”乃“詩之力”,“如物有勢,即無往不克”,這是因為“道隱其間”。④清代布顏圖在回答弟子何以“常論畫山水必得隱顯之勢方見趣深”這一問題時,認為“所謂隱顯者,非獨為山水而言也,大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隱顯,顯者陽也,隱者陰也,顯者外案也,隱者內象也”。在他看來,畫潛蛟之騰空、風雨之施行、才士之意趣、美人之豐姿等,均不出“隱顯叵測”四字至理和“筆墨濃淡虛實”之法。⑤不難看出,“隱之為體”是古人的基本看法,亦即道因其隱而不可言說,因為“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⑥。這種觀念反映到對“道”“藝”二者關系的看法上,就是強調在藝術創作中要以“神遇”“頓悟”等方式把握那難以言說的創作之道。這在古代藝術理論中可以說是俯拾即是,自莊子之以“庖丁解牛”喻道技關系后,代不乏人。如南宋嚴羽論“詩之極致”之其一,謂之“入神”,元代陶明濬曾對此解釋說:“入神二字之義,心通其道,口不能言。己所專有,他人不得襲取。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⑦對“入神”的解釋說明詩藝達到最高境界絕非言語所能傳達。類似的表述還有很多,如清代劉大櫆說:“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則死法而已。”⑧章學誠也說:“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
綜上,在中國古代豐富的“道-藝”觀中,道器論是至為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這是因為它從體用論層面對“道”的形而上本性與“藝”的形而下特征作了哲學上的闡明,并將之落實到道與藝的隱與顯之關系的提攝上。圍繞“道”之“隱”與“藝”之“顯”,中國藝術理論還延展出“道”之“常”與“藝”之“變”、“道”之“無形”與“藝”之“有跡”等諸多相關命題。可以說,“道器”論從本體與實在之總體關系上探討了藝術同世界本原及其內在規律之間的關系,因而尤其重要。這也是為什么在中國古代藝術理論中往往首重“道器”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道器”論為古人看待“道-藝”關系問題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論視域,即古人在處理“道-藝”關系時,往往會將之放到形上-形下、無形-有形、不在場-在場、體-用、常-變等二元對立結構中去理解。換言之,“藝”作為萬有之顯現與“道”作為無形無名的萬物所宗之隱匿,二者的關系在“道器”論中得到了全面的理論提攝。有學者對藝術創造中道器關系問題作過這樣精辟的理論概括:“綜是殊名,以生多故,賦之為物,陳之為彩,情因事以糾紛,事因物而結構,凡言舊事,必識故物。一時之制,百思攸托,一器一道,哲人謹焉。”①可以說,在中國傳統文藝理論中,以藝術實在之“象”(形、器、顯、用、有等為之異名)去呈現(或描摹、形構、體證)作為世界本體或本原之“道”(隱、體、無等為之異名),是中國傳統文藝理論最重要也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理念之一,這一理念不僅具有藝術發生學的本源開示意義,還從本體論角度確立了古人思考“藝術為何”與“藝術何為”兩大文藝核心問題的基本路徑。
二、“道貫”論:藝術創造中“一”與“多”關系的辯證提攝
在《老子》《易經》《莊子》等中國元典中,“道”常與“行”“達”“通”“貫”等事物的運動特征及其規律相關聯,因而道具有周行暢達、完整圓滿之特征。換言之,世界萬有之起源、本質、德性、原理乃至對其之言說,必以“道”一而貫之。正是由于“道”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且“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②等特征,所以在古人看來,它是萬物的唯一原理或形現萬有的整體性提攝,因而也必將貫穿事物及其發展的全過程。老子將這種“貫”稱之為“一”。《道德經》第三十九章即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③《淮南子·原道訓》亦云:“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④莊子將老子的“道貫”論拓展為“道通為一”:“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⑤意即細小草棍與粗大柱子,丑人與美女,或者寬大的、畸變的、詭詐的、怪異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種事態,從道的意義上講都是相互貫通而且渾一的。這其中的“一”,許慎《說文解字》解釋曰:“惟初大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⑥也就是說,“一”就是整體,它與“多”(部分或具體)共同辯證地構成了大千世界的基本圖景。“道”之貫通可以顯現為事物的同類相召。董仲舒說:“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⑦這也可以顯現為事物之間相反相成的轉化。如王弼在剖析“睽”卦時承接并發展了莊子的“道通為一”論:“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詭譎怪,道將為一。”⑧這便涉及事物(包括藝術中的美丑)互滲和相互轉化的問題。古人在討論藝術創造時亦將“道貫”論應用于其中。如就散文而言,劉大櫆認為“行文之道”在于“神為主,氣輔之”,因為“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⑨這就是說,優秀散文的“行文之道”在于“神”與“氣”始終貫穿于創作的各個環節直到作品的最終完成。就詩歌而言,陸時雍認為“詩道”歸納起來不外乎遵循“情真”和“韻長”兩個基本準則:“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夫獻笑而悅,獻涕而悲者,情也;聞金鼓而壯,聞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韻欲其長也,二言足以盡詩道矣。”①亦即貫穿詩歌創作之始終的是“情真”和“韻長”這兩個基本準則(即作詩之道)。就戲曲而言,王驥德主張“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②因此戲曲創作之全過程始終要考慮或處理好藝術創作如何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進行想象和虛構這一核心問題。
這種道貫論也滲透到繪畫中,古人往往認為繪畫藝術的最高境界在于求道、悟道、證道。清代石濤的“一畫”論便是其中的典型:
夫畫者,從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蒙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終于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下,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發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樸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③
在這段著名的“一畫”論中,“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俱各有道,然而畫家只有用心靈去透悟“一畫之洪規”,由纖微入廣大,洞悉萬事萬物的方圓、曲直、大小以及事物隱顯之至理、至態、至勢,方能將“太樸”那似散而實為“整一”的宇宙圖景呈現出來,而那能讓“此一畫,收盡鴻蒙之外”,使“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終于此”的,正是“道”之貫通使之然。質言之,石濤所謂的“一畫”,既是繪畫之始,亦是繪畫之終,這“一畫”既充分展示出“道成肉身”的過程,更將“道”的那種完滿性包含在筆墨的一切可能性的變化與展開中。
值得注意的是,“道貫”論的思想還滲透到小說創作及其批評中。如清人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便以《易》理闡釋《紅樓夢》,認為一部《石頭記》無非《易》道,并體現在諸多方面。其一,《紅樓夢》按照《易》的規律發展著故事情節。張新之評論說:“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書無非《易》道也。”④其二,人物的命運也同《易》道相通。比如關于林黛玉的命運,張新之又評論說:“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是極不善處世、極不自愛之一人,致蹈殺機而不覺。”⑤其三,關于人物的關系,張新之認為是《易》道中的陰陽對立統一的觀念直接影響著《紅樓夢》中人物關系的處理:“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石?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故《易》道貴陽而賤陰,圣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生于海,海處東南,陽也;金出于薛,薛猶云雪,錮冷積寒,陰也。此為林為薛、為木為金之所由取義也。”⑥其四,關于全書的結構,張新之則以“復卦”和“漸卦”的觀念來闡述《紅樓夢》,認為《紅樓夢》有貫穿的結構:“一部紅樓演一‘漸’字。”
總之,“道貫”論是從創造論層面就“道”對藝術創造全過程的貫通出發去探討藝術問題的。就藝術創造而言,無論是繪畫的“經營位置”,詩文的“起承轉合”“置陳布勢”與“脈相灌輸”,藝術創造中的取舍、聚散、主賓、整亂、開合、動靜、呼應、簡繁、空白、疏密、穿插、虛實諸多表現方式與手段,無不以道貫之。總之,大道有理法,小道有技能,藝術之妙,全在于“道”之貫通,這是中國古代藝術創造理論反復申說并加以強調的。
三、“載道”論:道主而藝從之文藝認知格局的確立
將藝術視為天道、倫理之載體并由此主張道主而藝從,是中國古代藝術社會學的重要理論特征。中國傳統思想認為,人的命運是由上天安排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①,在天(命)的絕對統治力面前,人只有“知命”“安天命”“順應天命”,因而作為人們活動與生存之依據的天命、天道也成為傳統哲學反復宣揚的觀念,如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②,孟子的“修身立命”③,莊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④,董仲舒為闡發君權神授而宣揚的“天人感應”⑤論,朱熹理學所宣揚的“存天理,滅人欲”⑥等。它反映到藝術領域中,便是將藝術看作天命或天道的載體,由此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載道”論。比如,在樂論中,《樂記·樂本篇》云:“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聲音之道,與政通矣。”⑦這種聲→音→樂→政→道的邏輯思考理路,實際上就是音樂理論中較早的“載道”論。在畫論中,張彥遠將繪畫看作是名教樂事和“載道”極品:“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⑧清代畫論家華琳甚至直接將這種“載道”論極端化到包括藝術創造的萬事萬物,他說:“天上浮云如白衣,須臾變化成蒼狗,蒼狗萬變圖,固宇宙間第一大奇觀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程子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則又通于道矣。道既變動不居,則天下無一物一事不載乎道,何獨至于畫而不然?”⑨中國傳統建筑同樣是天道的體現或象征。比如明堂或朝堂,被看作王權或天道的象征。《禮記·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⑩《白虎通》卷四“辟雍”還對之解釋說:“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都隱含著君權神授的法統永恒觀念或等級秩序觀念。在文學領域中,荀子的“明道、宗經、征圣”論直接啟發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明確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在他看來,“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因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這一主張也開啟了后世散文創作中關于文道關系的爭論并形成影響深遠的散文理論,如韓愈的“明道”論與“貫道”論、周敦頤的“載道”論和朱熹的“害道”論等。
這種道主而藝從的認知方式也直接形成了中國文藝崇“大道”而鄙“小言”的理論傳統。比如,中國傳統小說之所以后起且一直未能受到重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們認為它是“小言”而不能傳“大道”。如《莊子·外物篇》云:“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莊子·列御寇》云:“彼所小言,盡人毒也。”①這都是將小說視為閑言碎語或小言。《荀子·正名》中“小家珍說”的說法與莊子所言大意相同:“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愿皆衰矣。”②楊倞對這一句作注說:“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③在古人看來,言不入道,故曰小言。這實際都是將那些喋喋不休、辭費而無當的言論看作是“小言”,即不載大道、不中義理、不合王制或禮義的淺薄言論。從先秦到兩漢,人們對于不合大道的言論幾乎都以“小”稱之,如小言、小道、小知、小辯等,“小說家”即使被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錄入,得到的評價也不過是“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因為在班固看來,這些都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即使在孔子看來“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但因其“致遠恐泥”,所以“君子弗為也”。④小說被看作是只能以春秋筆法進行褒貶善惡而并不能載道的這種觀念延續到晚清。如西泠散人便痛批晚清以來的小說創作“非淫詞艷說蕩人心志,即剿襲雷同厭人聽睹”,而“欲求其自抒心裁,有關風化者”⑤,則少得可憐。
四、“同道”論:文化原型和藝術同構內秘之詮解
在中國文化哲學中有一種特殊的理解“道-藝”關系問題的致思路徑,即將《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均視為道之一體的不同顯現,并在此基礎上建構出中國古代的藝術同構論。
首先,“六藝”名異而道同。在古人看來,道同體而異名,如王夫之所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名者,言道者分析而名;言之各有所指,故一理而多為之名,其實一也。”⑥也就是說,道雖然在名稱上有異同之分,但指的都是宇宙世界的本質或基本規律,因而,無論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動”⑦,還是儒家所提倡“中庸之道”⑧,甚或禪理所倡導的心性之道,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是對道的共同體察。古人在闡釋具體的兵、農、醫、藝諸事(實踐活動)時,也多秉持此“同道”論。如《易》之闡釋天下之“道”,便“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⑨。這種“同道”論更深入到對中國傳統文化原型的理解中。比如,《淮南子》就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根基提出了“六藝同道”論,其《泰族訓》即云:“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⑩新儒家馬一浮繼承、發揮了這種“同道AIfaL56fYNES6AY2r5eIiQ==”論,并主張結合現代人對真、善、美的追求來弘揚“六藝”之道。他認為:“《詩》教主仁,《書》教主智,合仁與智,豈不是至善么?《禮》是大序,《樂》是大和,合序與和,豈不是至美么?《易》窮神知化,顯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撥亂,示人道之正,合正與常,豈不是至真么?”這實際是將“六藝”視為中國文化原型的基本象征,又從“六藝”兼具真善美并構成完整之價值體系的角度出發,闡述了“六藝”對“道”的參與與顯現。
其次,“同道”論構成了中國傳統藝術同構論的理論基礎。在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中,諸如“詩畫一體”“書中有畫”“書畫同道”等主張打破或融通藝術門類界限的理論表述貫穿了中國藝術史的發展過程,這些表述在理論內涵上的共同點就是將各藝術門類之間看成能相互融通的或可以異質同構的關系。如唐代張彥遠早有“書畫異名而同體”①的說法;蘇軾提出了“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②的見解。類似的看法還有“文者無形之畫,畫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跡而同趣”“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③等。清人馮應榴引用蘇軾詩夸獎老杜作詩和韓干畫馬為“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干丹青不語詩”④。對于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古代藝術理論家大多是從“同道”的角度進行解釋。如明人宋濂云:“倉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⑤清人華琳《南宗抉秘》亦云:“書成而學畫,則變其體不易其法,蓋畫即是書之理,書即是畫之法。如懸針、垂露、奔雷、墜石、鴻飛、獸駭、鸞舞、蛇驚、絕岸、頹峰、臨危、據槁,種種奇異不測之法,書家無所不有,畫家亦無所不有。然則畫道得而可通于書,書道得而可適于畫,殊途同歸,書畫無二。”⑥關于詩與畫的關系,清人葉燮亦說,“詩與畫,初無二道也”,原因就在于,畫是“遇于目,感于心,傳之于手而為象”,詩是“觸于目,入于耳,會于心,宣之于口而為言”。由此,“乃知畫者,形也,形依情則深;詩者,情也,情附形則顯”。⑦從這些論述不難看出,中國古代藝術理論認為,各種藝術門類雖然在傳達媒介或者表現的側重點上有所不同,但在藝術創造的深層道理上都是相通的,即都是以“形”或“象”去傳“情”、達“意”或悟“道”。這就是藝術傳達過程中的“圖文間性”⑧,藝術之所以能相通、相融,其根本就在于“藝術形式與我們的感覺、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動態形式是同構的形式”⑨,而“道”就蘊含在這種動態形式中,也蘊含在那些存在著普遍聯系與和諧統一的媒介交互性中。
如果我們深入追尋“同道”論何以構成中國傳統藝術同構論之理論基礎將會發現,這與中國古代間性哲學對藝術結構創造理念的浸潤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古代間性哲學強調以辯證視域處理天人、心物、陰陽、道器、形神、虛實、體用、動靜、內外、有無、濃淡、隱顯、繁簡、方圓、巧拙、疏密、真幻、藏露、未發與已發等諸多關系,主張藝術創造要順應藝術時空的變化,去捕捉藝術作品將成未成、將變未變之際的形式變化,去生成活化的藝術形式或者保持藝術形式的活化,也更推崇從“勢”的角度去判斷或考察事物的運動方式、軌跡和發展前景,并以此去處理藝術結構的創造問題,因而,山水布勢或人物位置的隱顯、映帶、奇正、斷續、疏密等結構關系成為畫家與觀者關注的中心;倡導“化空為時”(化人物活動空間為時間進程的結構模式)成為戲曲結構創造的基本理念;在書法創作中強調氣脈連通,于提頓、離合、收放之間出境界、顯性情;在文章結構布局上講究變化波瀾之妙、正側穿插之奇、短長高下之度、輕重隱顯之限、回互激射之勢。凡此種種,均是間性理念在古代藝術結構創造中的顯現,也是藝術同構、“同道”的結構內秘。
五、“樂道”論:對審美境界與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
古人常將藝術創造視為體貼和妙悟神秘之世界本原的重要方法或途徑。比如,關于書法,古人有“書之微妙,道合自然”“書肇于自然”“書之氣,必達乎道”①等說法;關于繪畫,有“圣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②,“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③,“筆墨之道,通乎造化”以及畫之奧妙“乃在濃淡明晦之間能得其道”④等各種大致相似的理解等。朱庭珍在《筱園詩話》中曾以山水詩為例,精辟闡述了山水詩創造本身就是一個悟道、體道且最終合道的過程:。
作山水詩者,以人所心得,與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證,而潛會默悟,凝神于無朕之宇,研慮于非想之天,以心體天地之心,以變窮造化之變。揚其異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獨,造其奧以泄其秘,披其根以證其理,深入顯出以盡其神,肖陰相陽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繪聲繪色而曲得其真,務期天巧地靈,借人工人籟而畢傳其妙,則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與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靈思,結為純意,撰為名理,發為精詞,自然異香繽紛,奇彩光艷,雖寫景而情生于文,理溢成趣也。使讀者因吾詩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勝畫真形之圖,直可移情臥游,若目睹焉。造詣至此,是為人與天合,技也進于道矣。此之謂詩有內心也。
從這段精彩的論述不難看出,古人往往將人生境界或精神境界的證得視為最高的價值目標。我們常常看到,藝術內在規律的探尋與把握固然也是古人所悉心追求的,但心性的證語、生命的安頓、胸次的陶洗才是其終極目的,即通過藝境的感悟與揭示去協和宇宙,參贊化育,深體天人合一之道才是他們真正的旨趣之所在,崇遠(傾向于向“遠”中求其韻味和意境)、尚空(推崇于“空”白處出大境界)和倡微(追求“物性的敞亮”)等才是中國文人審美追求的極致。
之所以將體道、悟道視為藝術的頭等大事,這同古人對藝術之特殊功用的全面認識有密切關系。在畫道中,由于“山水秉五行之精,合兩儀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結構之理,與山水所得于天,以獨成其奇勝者,則絕無相同重復之處”⑦,因此,水墨能“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⑧。在書道中,“書之為征,期合乎道”,書法的妙用在于它“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⑨在曲道中,那“度曲未終,云起雪飛”⑩的抑揚之道則又通乎人情事理,正如湯顯祖所描述的那樣:“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慉結。過當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沖孔動楗而有厲風,破隘蹈決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極所致,可以事道,可以忘言。”總之,在古人看來,藝術是體道、傳道、達道而最終趨于“樂道”的絕好載體。
“樂道”論主要從審美體驗與人生境界合一的角度去探討藝術的功能與效用。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強調,中國之學問在于人之相處、心之相通,其精髓當為一“樂”字,“樂”乃人生之本體或人生最高境界。①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儒道釋各家均以得道、悟道、體道為樂事,并對之反復加以宣揚。儒家之樂道志在養成人格,去體驗一種人格或人生境界之提升的快樂。如孔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曾點的“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孟子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②荀子的“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③,邵雍的“已把樂為心事業,更將安作道樞機”④等。道家之樂道在于以自然無為為法,在“虛靜”與“心齋”中觀照與體會宇宙的勃發生機,從而獲得精神的“逍遙游”與大解放,如莊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⑤,又如陶淵明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⑥。佛禪之樂道在于于頓悟中親證佛性的自在與“般若智慧”的敞現,如南禪宗慧能法師所說:“何名清凈法身佛?……世人性本自凈,萬法在身性。……自性常清凈。”⑦可以說,儒家的“人格之樂”、道家的“無為至樂”以及佛禪的“頓悟之樂”,皆在體道、悟道中得到完成。
正是這種“樂道”論使中國古代藝術創造始終將道與藝看作是生活實踐與藝術實踐合二為一的關系,主張道藝相統一。《論語·述而》中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⑧,將目標(道)、根據(德)、依靠(仁)和歸宿(藝)聯系起來進行闡發,奠定了中國古代思想中有關“志道”與“游藝”之關系的基本理路——“道寓于藝”“道外無藝”。后世以之作為理論依據加以闡發的不計其數。其中又以明代方以智《東西均》之“道藝”篇論述最為精彩:“知道寓于藝者,藝外之無道,猶道外之無藝也。”又云:“心有天游,乘物以游心,志道而終游藝者,天載于地,火麗于薪,以物觀物,即以道觀道也。”更云:“易一藝也,禪一藝也。七曜、四時,天之藝也。成能皆藝,而所以能者道也。”⑨從這些論述不難看出,方以智不僅從心—物—藝—道的內在邏輯聯系上闡述了道藝相統一的關系,而且還從“能-道”關系的角度將宇宙萬物的運行變化(如七曜、四時)、人對宇宙社會與人生的體察與洞悟(如易與禪)都視為廣義的藝術化展開,大大拓展了藝術活動的范圍。
質言之,“樂道”論蘊含著古人深刻的哲學追求,亦即對“通”的境界的追求。這種天人合一、從心所欲、逍遙圓通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中國美學所推崇的,它在中國美學中常常以達、敞、和、順、澈、明、亨、化、宜、泰、融、透、游、合、交等語詞表達或標示。這些既是審美活動的理論總結,更是古人對一種藝術化人生及其境界的倡導,其中所蘊藏的中國智慧在當代審美實踐和理論建構中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結語
總的來說,中國人之析物、窮理、盡心、驗行都以體道為旨歸,而中國藝術對詩情、文理、詞脈、書勢、畫韻、曲趣、園境等的追求或呈現也始終同對“道”的超越性的體悟密切相關。在形、文、法、技、言、筆、墨、勢等形而下的以形象為主的藝術范疇群外,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對諸如“大象無形”“立象盡意”“離形得似”“應目會心”“妙造自然”“化工”“入神”這類理論命題的提倡。所有這些,實際上都說明中國藝術哲學的開啟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對“道-藝”觀及其不同理論側面的闡解上,也集中揭示出中國藝術精神的精要:中國古代審美意識充盈著天地之大無出吾心,造物之妙盡入我意,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的宇宙意識;流動著自然—藝術—人必須在生命本體意義的高度上相通并得到統一的生命意識;高標著在審美體驗中去實現對物理時空或心理時空的大超越,去尋求精神的“逍遙游”或大解放的超越意識。它與視輪廓、比例、模式、尺度、外觀或結構為藝術創作與追求之核心的西方文藝創作理念有著很大的差異,只有深刻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把握中國藝術理論的民族性或民族特色。
[責任編輯 馬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