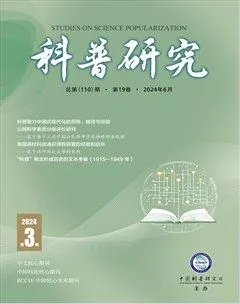國際科學教師培訓的內容、模式與啟示
[摘 要] 加強科學教師培訓是新時代黨和國家對科學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推進科學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本研究通過對56篇研究在職科學教師培訓項目的SSCI文章進行分析,發現國際科學教師培訓的內容聚焦綜合性與前沿性的科學知識、包含多種模型與變式的科學探究、不同角度切入的學科教學知識、數字化背景下增強科學教學的信息技術等主題;凝練出體驗—實踐—反思、示范—模仿、基于課程材料的嵌入式學習、以課例為核心的個性化指導、真實參與科學實踐、協同教學6種典型的培訓模式;基于研究發現的規律,得出我國科學教師培訓的3點啟示,將科學知識學習與教學法相結合、關注科學教師的實踐轉化、開展對培訓項目的追蹤性評價。
[關鍵詞]科學教師 科學知識 科學探究 學科教學知識 培訓模式 培訓效果
[中圖分類號] G53/57 [文獻標識碼]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3.007
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中小學科學教師是落實“雙減”政策、實施科學教育的主體。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在教育‘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1] 。做好科學教育加法需要抓住科學教師這一“關鍵少數”因素,直面新時代黨和國家對科學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師培訓對于提高教師專業素養、教學實踐的有效性[2]以及提升學生成績至關重要。因此,加強科學教師培訓是推進科學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但當前我國的教師培訓存在內容以理論知識為主、內容更新不及時、培訓形式單一、培訓學習效果不佳等問題[3]。國際上,如美國、英國等國家非常重視科學教師培訓,開展了系統化、多樣化的培訓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5]。對國外科學教師培訓進行研究,系統總結國外科學教師培訓的經驗,或可為我國科學教師培訓的困境提供解決思路。國內外學者已圍繞科學教師培訓項目的內容、模式開展了豐富的研究。然而這些研究或是以某個項目為研究對象,對其培訓課程、模式、策略進行個案分析,或是幾個項目的比較分析,鮮有研究對國外整體的科學教師培訓項目狀況進行系統總結。因此,本研究擬基于針對國際科學教師培訓項目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運用文獻分析法,梳理總結這些項目聚焦的內容主題,并基于對課程模塊架構的深入詮釋,凝練典型的培訓模式,從而為我國科學教師培訓提供有益借鑒。
本研究首先以“scien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ience teacher training”為關
鍵詞,對ERIC數據庫在2000年至2023年時間范圍內的論文進行檢索,從全球范圍內選取了4種SSCI英文期刊,即《科學教學研究雜志》(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國際科學教育雜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科學教育研究》(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科學教育》(Science Education) ①,共得到168篇文章。之后,本研究剔除了評論以及綜述類文章,針對職前教師和直接研究學生的文章,以及關注多元群體(如母語非英語、少數族裔、特殊教育)科學學習的文章,最終以56篇研究在職科學教師培訓項目的文章為樣本,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1國際科學教師培訓項目聚焦的內容主題
1.1綜合性與前沿性的科學知識
研究顯示,教師的科學知識(Science Content Knowledge)是教師層面對學生科學學習成績最大的預測因子[6]。學科知識不足將無法幫助學生掌握和推理更具挑戰性的科學內容,因此,很多國際科學教師培訓項目都致力于改善教師的科學知識,從而提高學生的科學學習成就。當前的國際培訓特別重視綜合性、前沿性的科學知識。綜合性體現在內容主題是跨學科的或者涵蓋多個內容領域的,前沿性指將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納入教師培訓中。
一方面,水科學、氣候變化、工程設計、環境科學、癌癥研究等跨學科主題都是教師培訓課程的重要內容[7]。例如,夏威夷的學者基于當地的海洋和島嶼環境,以水科學為培訓主題,幫助教師將學生的學校學習與日常生活聯系起來。同時,水科學本身是跨學科的,適合不同年級和學科領域的教師,從物理角度研究密度、風、波浪、潮汐和海底地形對全球海洋環流的影響;從化學角度了解水分子及其獨特的化學性質,這些性質對物理和生物領域具有重要意義;從生物視角探索水生生物多樣性,重點關注生物體的結構、功能和進化聯系;從生態學角度,運用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原理研究水環境[8]。
除跨學科培訓主題外,綜合性還表現為科學知識涵蓋多個內容領域,如生命科學(生命周期、遺傳特征與后天習得特征、適應性、食物網等)、地球科學(天氣和大氣、地球循環、土壤特征、自然資源、地表變化、太陽系等)、物質科學(物質的性質、混合物和溶液、沸點和熔點、能量和光、電和聲音、力和運動等)等領域[9-10],這些內容與當地的課程標準緊密相關。
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是日新月異的,中小學科學課程在改革和修訂中也會不斷納入新的科技成果。而很多在職科學教師,特別是教齡比較長的教師對這些新的科技成果并不熟悉,因為他們自己在上學的時候還沒有這些新知識和新技術,更不用說作為學校課程進行學習。因此,需要更新科學教師的知識以滿足當前科學教學的需要。克隆人、轉基因、設計嬰兒等新興生物技術被媒體廣泛關注,高中生物學和生物技術課程明確要求教師和學生討論新興生物技術應用所引發的社會和倫理問題[11],但一線教師對于如何在忙碌的教學中做到這一點感到困難。蘇格蘭的生物教師參加了愛丁堡大學組織的暑期學校,課程包含以下兩大模塊:(1)更新生物技術、遺傳學及其相關新技術的科學知識;(2)對這些技術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的認識[12]。納米技術是結合化學、生物學、物理學、材料科學、醫學和工程學等方面的跨學科領域[13],影響了很多現代與傳統產業,但在高中教授納米技術對于很多教師來說極具挑戰。因此,納米技術也是重要主題之一[14]。
1.2包含多種模型與變式的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是科學教育中最核心的話題,得到了全球范圍內科學教育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教師培訓往往伴隨著國家的科學課程教學改革,很多國家的科學課程標準中都強調學生要以探究的方式學科學。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教師對探究缺乏理解,而有些是教師對于探究存在誤區(比如以食譜式的方式強調技能發展)。因此,提升教師對科學探究的理解[15],以及開展科學探究教學的能力[16]是國際科學教師培訓的目標和方向。
當前教師培訓中最為廣泛使用的模型是5E學習環,其包括參與(Engage)、探索(Explore)、解釋(Explain)、遷移(Elaborate)和評價(Evaluate)5個環節[17],較好地平衡了教師指導與學生探索的關系,要求學生積極參與觀察、形成假設、測試想法、得出結論和推論[18]。與我國所強調的跨學科學習較為一致,國際范圍內的科學教育也強調將科學學習與閱讀進行整合,特別是針對母語非英語的學生。有培訓項目開發了整合閱讀的5E學習環,具體包括:(1)參與活動(5~10分鐘),視覺呈現或教師演示科學概念,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并建立過去和當前學習之間的聯系;(2)探索活動(10~20分鐘),學生通過小組合作操作科學材料或探索環境來學習科學概念;(3)解釋活動(15~30分鐘),通過直接教授科學詞匯、學生與同伴閱讀說明性文本以及與解釋科學概念的科學軟件(通過動畫和模擬)互動來更深入地理解科學概念;
(4)評價活動(10~20分鐘),學生在科學日記中展示他們對科學概念的理解;(5)擴展活動,如果時間允許,學生通過額外的活動進一步應用他們的理解。每天的課程都以總結問題來復習與目標相關的科學概念[19]。
針對食譜式探究的問題,有培訓者開發了強調流動性與多向指導的TSI(Teaching Science as Inquiry)模型。TSI模型的5個探究階段是啟動(Initiation)、發明(Invention)、調查(Investigation)、解釋(Interpretation)、指導(Instruction)。啟動階段激發興趣或聚焦探究問題;發明階段需要解決問題和收集信息,例如創建一個可測試的假設或解決程序步驟中的故障;在參與調查階段,學生通過測試或分析數據來收集新知識;在解釋階段,學生通過內部和外部的反思來提取信息;而指導存在于每個階段,包括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以及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交流。TSI模型是非線性的,強調教師和學生在整個探究過程中在各個階段之間來回移動,具有流動性和多向性的特點[8]。以啟動為例,教師可以在課堂開始時,使用啟發導入,也可以在整節課中不斷使用提問策略來重復啟發和吸引學生思考。這與現實中科學家的做法非常相似,TSI模型能夠幫助教師指導學生以真實的方式學習和從事科學。
1.3不同角度切入的學科教學知識
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是區分教師與學科專家的關鍵,發展科學教師的PCK是教師培訓的重要目標。關于PCK的結構內涵有很多理論,馬格努森(S. Magnusson)提出了有關科學教學領域的PCK構成,認為科學教學領域的PCK 包含以下5 個組成成分[20]:(1)科學教學定位,指符合特定年級水平的科學教學目標相關的知識和觀點;(2)科學課程知識,指教師必須理解學生在前幾年已經學到什么、接下來希望學生學習什么,以及教師教授與某個科學領域特定主題相關的材料或方案的知識[21-22];(3)學生科學學習的知識,即學習特定科學知識的先前必備知識或技能以及典型的學生前概念、迷思概念和思維方式等有關學生困難的知識[23];(4)科學評價的知識,包括指向科學素質的評價目標與內容,以及針對具體教學主題的合適的評價方法[24];(5)教學策略的相關知識,包括特定學科的教學策略[25]以及特定主題的教學策略[26]。PCK的不同維度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一個維度的提升會促進教師整體PCK的發展。國際科學教師培訓項目往往從一個角度切入來發展科學教師的PCK,例如聚焦于教學策略的科學內容故事線、學生對特定科學內容的思考等。
連貫的科學內容故事線(A Coherent Science Content Storyline)指的是將科學課或科學單元中的科學概念(Science Ideas)進行排序并相互聯系,幫助學生構建一個對他們有意義的連貫“故事”。具體而言,有效的科學內容故事線的策略包括“將科學內容觀點與活動聯系起來”和“將活動與主要學習目標聯系起來”,強調在活動前、活動中和活動后將觀點與活動聯系起來,以及將活動與整體學習目標聯系起來。“將內容觀點與其他科學觀點聯系起來”強調了科學內容故事線在各課之間聯系的重要性;“為學生提供使用與學習目標相匹配的內容表征的機會”是指使用類比、隱喻和直觀表征(如圖表、圖解、圖形、概念圖、模型[27]和角色扮演)來表達主要概念,使科學概念對學生來說更加具體和真實。
學生對特定科學內容的思考(Student Thinking About Specific Science Content)是教師進行教學設計、實施和反思的重要依據,因此需要關注學生的思維,特別是了解學生對科學現象的常見思維方式[28]。揭示、支持、挑戰學生思考的策略包括:(1)引出學生的概念和預測;(2)提出探查性、挑戰性問題[29];(3)讓學生參與對數據和觀察結果的解釋和推理;(4)讓學生通過各種方式在情境中使用和應用新概念;(5)讓學生通過總結工作“建立連接”[30]。在了解學生思維和想法的基礎上,教師需要進行回應,推動學生的思維發展。了解學生思維的方法包括提問[31]、觀察和分析學生作品[32]或記錄單[33]等。
1.4數字化背景下增強科學教學的信息技術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普及,平板電腦等數字設備逐漸成為教育體系的一部分。科學教育也不例外,越來越多的學校和教師在科學課上使用科技手段,如運動傳感器、溫度探針等。科學課程中技術的普及有助于進行探究式學習,技術為動態可視化、數據收集[34]、概念建模和探索虛擬環境提供了新的機會,使用技術進行探究式學習可以促進學生對科學內容的理解。
那些對技術輔助探究學習感興趣的科學教師往往缺乏獨立開發課程的時間和資源。有研究團隊創建了專門用于技術增強型科學教學的免費開源在線課程門戶[35],包含大量基于探究的科學課程,其中使用最為廣泛的是WISE學習環境① (Web Based Inquiry Science Environment)。在科學教學中,有些主題無法直接進行探究(如板塊構造),教師、技術人員、研究人員和學科專家共同設計的WISE探究項目,能夠促進學生對特定主題領域相關內容的學習。技術增強的在線平臺一方面能夠將難以直接動手操作的實驗通過計算機模擬實現可視化,有利于學生建構科學概念;另一方面,平臺通過嵌入式的形成性評價,可以獲取學生學習數據[36],幫助教師掌握學生想法,進而助其調整教學計劃和教學策略。
2國際科學教師培訓的典型模式
2.1體驗—實踐—反思
體驗—實踐—反思是最為常見的教師培訓模式,包含以下3個環節:(1)親身體驗:教師以學生身份體驗科學探究[16][23][26][37]、科學建模[27]、工程實踐[38]等活動。(2)教學實踐:教師根據課程中學到的內容對學生進行教學,這種教學實踐使教師能夠立即運用他們新學到的內容,并在低風險的安全環境中嘗試。(3)教學反思:在教學實踐環節,在有些項目中培訓者會進行觀察,與授課教師進行合作反思和討論;有些項目則以在線互動平臺為媒介,教師分享自己在教學中的困惑、錯失的機會以及成功的策略,同組的教師或培訓者能夠同步看到并回應。已有研究證明該模式對教師的信念和實踐有積極影響[39]。
以氣候變化項目為例,一年一度的氣候學院是聯邦政府所資助研究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推動美國中大西洋地區全面實施氣候變化教育。氣候學院的設計由氣候科學家、學習科學家、教師教育者、實踐者和政策相關者共同參與,旨在為參與教師創造切身體驗,加深他們對氣候變化內容的理解,同時提供實施氣候教育所需的教學支持和資源。培訓包含以下3個部分:(1)為期一周的集中暑期工作坊;(2)四次針對疑難氣候變化概念的在線研討會;(3)兩次面對面的后續研討會。
在為期一周的集中暑期工作坊中,教師可以直接接觸數據、進行實驗,并參與基于探究的戶外活動,展示氣候對當地環境的影響。在夏季研討會的每天早晨,主辦方都會設置一個互動演示,讓教師參與其中。這些在早餐期間進行的“晨間挑戰”活動,旨在激發教師們在剩余時間里就內容知識發展和基于證據的教學實踐進行深入討論。在上午和下午的其他活動中,教師們會參加戶外考察,探索當地的微氣候,動手模擬氣候變化對洋流的影響等。為了促進學習與實踐之間更緊密的聯系,參會教師會單獨或以小組形式設計一個具體的教學計劃,該計劃基于他們所教的年級、科學課程以及各自的課堂需求進行。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教師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來設計和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案,并與同行分享,獲得反饋意見。在自己的課堂中實踐之后,教師參加了“現場故事”集體分享活動,反思自己的收獲和需要的幫助[40]。通過支持性的專業學習環境,培訓幫助教師完成并持續開展實踐轉化。
2.2示范—模仿
示范—模仿是人類社會傳遞并接受經驗和技能的教學模式,也是培訓活動中最為常用的模式之一[41]。該模式以認知學徒制為指導,強調在現實任務的情境中學習,提供支架幫助學習者執行任務,并逐漸增加任務難度[42]。
基于視頻分析的科學教師學習(The Science
Teachers Learning from Lesson Analysis,STeLLA)項目是一項基于視頻的實踐分析類培訓項目。該項目的核心是教師基于課堂錄像分析科學內容、科學教學和科學學習之間的互動,教師在 STeLLA 項目負責人的協助下,以小組(5~10 人)形式開展學習。STeLLA 教師親自講授4~6節課,并對教學進行分析。課程是由項目研究人員設計的,這些教案將成為教師培訓的課程材料,為教師初步使用所教策略提供示范和支架。之后,學習小組的一半成員先授課,并進行錄像(第一輪),整個研究小組共同分析錄像、評估學生作品和前測,并修改課程計劃供另一半教師在第二輪使用(第二輪教師重復這一過程)。在下一階段,每個學習小組轉到一個新的內容主題領域(如從電轉到食物網),研究人員的支架和結構化作用有所減弱,但仍然存在。在該階段,項目組沒有向教師提供教案,教師們既在小組內也在自己的課堂上,就第二個教學內容進行備課,且研究人員的指導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支架和指導逐步撤去[30]。可以發現,教師首先從示范者的視頻案例中學習,然后他們在自己的課堂上制作視頻案例,并從自己和學習小組內其他教師的視頻案例中學習。
再比如,參加了包含教師研討會、博物館學習和課堂科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等課程的培訓后,科學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反思、行動并修改規定的科學課程,并就研討會中學到的科學本質增加了為期兩天的“什么是科學”主題教學。教師們還增加了探索能量和氣候變化的實地考察以及博物館學習等額外教學內容[43]。教師所做的改變幾乎都是對自己所參加培訓的“復制”,模仿培訓者的活動改變自身教學。
2.3基于課程材料的嵌入式學習
很多時候,科學教師培訓是為了落實國家的科學教育改革政策而開展的。在改革的背景下,不同的研究團隊開發了很多新的課程材料,而對于科學教師的培訓往往嵌入到支持他們使用課程材料的過程中[22][44]。因此,我們把這樣的培訓模式稱之為基于課程材料的嵌入式學習,該模式與我國的教材培訓較為類似。
例如,戴蒙德(Brandon S. Diamond)等學者開發了一套完整的五年級科學課程,與當地州的科學內容標準保持一致,課程材料包括學生用書、教師指導手冊、科學用品以及在線補充材料。所有使用該課程的五年級科學教師都參與了為期5天的工作坊:前3天在暑期,主要內容是當年12月到次年5月將要教授的課程;第4天在次年1月中旬,聚焦于1月到4月中旬要教授的課程內容;最后一天在次年5月的年終工作坊,主要反饋一年的使用情況并為下一學年做計劃。除集中的工作坊外,該培訓項目還包括學校現場支持,即研究團隊為使用課程材料的教師或學校管理人員提供幫助。現場支持頻率為每4~6周一次,全學年共計4~6次。現場支持的內容包含制定課程、共同授課、關于額外材料(例如家庭學習、實驗室管理、補充評估材料)的建議、提供物資以及現場指導,現場指導包括進一步解釋科學內容和指導實施探究活動[6],這些都有助于教師科學素質的提升。
2.4以課例為核心的個性化指導
以課例為核心的個性化指導是指科學教師通過實踐學習,即通過教學進行學習。沒有正式的培訓課程,培訓者(科學教師教育者)與教師參與一系列學校活動,包括備課、上課、教學反思等[45],教師接受一對一的個性化指導。科學教師和培訓者在實踐共同體中共同合作[46],科學教師在安全且富有支持性的氛圍中分享他們的實踐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困惑,培訓者為教師提供支架性支持和指導建議[47]。指導包括以下步驟:(1)教師向培訓者發送課時計劃;(2)培訓者在課前給出評論和建議;(3)培訓者觀察教師的授課;(4)教師和培訓者討論需要關注的教學要點;(5)教師和培訓者共同制定下一節課的目標。關注的教學要點可能包括提問、如何鼓勵和組織討論、形成性評價任務等[48]。
基于課例研究的一對一指導能夠從教師的實際需求出發,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同時也為教師和培訓者提供了批判性對話的空間,能夠更好地發揮教師主動性。該模式常常以學校為單位開展,即培訓者與學校建立合作關系。以課例為核心的個性化指導培訓效果最好,但相對而言成本較高,培訓能夠覆蓋的教師群體有限。
2.5真實參與科學實踐
有一類教師培訓項目不是開展一個高度模擬的科學探究項目,而是為科學教師提供與科學家并肩工作的機會,讓他們真實參與科學實踐工作[49]。因此,與科學家的共同活動和互動是自然的,而不是精心安排的。
例如,巴拿馬運河項目—國際教育合作研究伙伴關系(Panama Canal Project-Partnership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Education,PCP-PIRE)旨在確保教師獲得收集化石的實踐經驗,教師與科學家團隊一起參與科學探究,通過古生物學框架了解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并獲取與古代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進化相關的知識。具體活動包括史密森學會熱帶研究所(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STRI)科學家的正式演講或報告、巴羅科羅拉多島熱帶雨林和新博物館的有講解參觀,以及教師在科學家和實習生的協助下,在巴拿馬運河的遺址現場尋找和挖掘化石。為了提供背景信息,科學家向教師分享了該地區的生態和地質歷史,并解釋了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每個工作日的晚上,教師們都會與負責該項目的教育協調員會面,與科學家們一起回顧當天的活動,并探討將實際經驗轉化為課堂教學的方法。教師不僅與科學家一起參與科學體驗,還參與了通過辯論構建科學知識的討論[50]。
根據參與者的自我報告,這些經歷對于參與教師的科學思維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真實的沉浸式科學探究體驗是必不可少的,教師通過參與科學家的討論和實踐學習,并開始吸收科學價值觀。這種融入科學家思維方式的過程對于教師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實踐至關重要,但此類培訓需要與科學家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因為一些科學家可能不愿在研究過程中配合教師。
2.6協同教學
協同教學(Co-Teaching)模式是指教師與同事、合作教師(該角色類似我國的師傅)、大學指導教師共同教學來學習科學教學。當大學指導教師觀察課堂時,學校鼓勵他們與教師或實習教師協同教學,而不是站在教室后面觀課和評價。這種參與方式使指導教師能夠在同一時間和地點與教師共同體驗教學和學習,實現研究與實踐之間的統一。協同教學允許他人公開批評和評價自己的教學,這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最好方式,教師通過專家解決問題時的“出聲思維”進行學習。每節課結束后,協同教師會向主講教師提出意見和反思,并討論如何改進,這種開放的溝通會激發每個人去嘗試不同的方法[51]。
托賓(Kenneth Tobin)等學者報告了他們培養新教師的協同教學模式,并展示了主講教師安德里亞(Andrea)、實習教師伯特(Bert)及其指導教師肯(Ken)、研究人員邁克爾(Michael)共同教授生物學課程中單因子雜交的教學片段。在該片段中,安德里亞是主講老師,三位協同教師(伯特、肯和邁克爾)都有不同的經驗,他們坐在教室的不同位置,關注著正在進行的課程,并在適當的時候貢獻自己的力量。
安德里亞:多少人有藍色眼睛,又有多少人會有棕色眼睛呢?
基莎(Keesha):各占50%。
安德里亞:很好,把它寫下來。
基莎:[寫下來]
伯特:你知道它在遺傳學中的另一個名稱嗎?你什么時候深入到研究遺傳學?當想到隱性純合時?[暫停] 實際上,我們要做的是一次雜交試驗。
肯:它叫什么?
安德里亞:雜交試驗。
伯特:雜交試驗,他們已經開始確定基因型了。
肯:[指向邁克爾] 有人有問題。
在這段對話中,安德里亞和伯特都為這堂課做出了貢獻。肯的問題也是一種貢獻,因為很可能有其他參與者沒有聽到或不知道伯特在說什么。肯還作為輔助教師幫助邁克爾加入了對話,因為伯特和安德里亞都沒有注意到他舉手要加入對話[51]。
3國際科學教師培訓對我國的啟示
教師的持續發展和學習是改善教學質量的核心,也是政策對教學實踐產生效果的關鍵。我國高度重視科學教師的培養與培訓工作,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實施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養計劃的意見》《關于加強小學科學教師培養的通知》《中小學幼兒園教師培訓課程指導標準(義務教育化學學科教學)》等多個政策文件。教育部及各省區市也開展了國培計劃、中小學名師名校長培養計劃、名師工作室等多種類型的教師培訓項目。學界對有效教師培訓的特征已經達成了共識,包括內容聚焦、主動學習、集體參與、足夠的持續時間以及連貫性[52]。本研究通過對國際56篇教師培訓項目研究論文進行分析,也發現了一些有益規律,并據此為我國教師培訓提出幾點啟示。
3.1將科學知識學習與教學法相結合
科學知識與教學法都是科學教師培訓內容的關鍵主題。提升培訓項目的效果和效率是教師培訓持之以恒追求的目標。國際科學教師培訓的準實驗研究發現,將科學知識與學科教學法相結合的實驗組,其科學知識成績超過了單純學習科學知識的對照組[30]。這證實了教師對科學知識的學習應與教學法相結合的觀點。
科學教師的學科知識和學科教學知識是預測學生學習最重要的指標,也是教師培訓最為重要的目標。但是,單純教授科學知識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與教學法相結合。與教學法相結合的科學知識學習是基于課堂情境的,允許教師在課堂中重復實踐。與工作(課堂教學)直接相關能夠激發教師的學習動機,從而提高他們的參與度,同時學習成果也能更持久保持。
3.2關注科學教師的實踐轉化
通過對國際科學教師培訓典型模式的凝練,我們發現體驗—實踐—反思、示范—模仿、以課例為核心的個性化指導、協同教學等模式都以教師的教學實踐為核心,真實參與科學實踐的模式也包含“與科學家們一起回顧當天的活動,并探討將實地經驗轉化為課堂教學的方法”。因此,國際科學教師培訓模式都特別關注教師的實踐轉化。無論學習了什么主題的內容,教師都必須轉化為自身的教學實踐,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對學生產生影響。
我國的教師培訓項目主要包含專家講座、參觀考察、聽評課等不同的形式,從學習參與的程度而言,仍然處于聽人講、看人做的學習程度,“自己做”的環節體現不夠。以協同教學為例,該模式較為適合新教師以及轉崗教師(由其他學科轉任科學)的培訓。我國的新教師培訓也采取師徒制,配備骨干教師擔任新教師的師傅。師徒結對多停留在師傅與徒弟之間的相互聽課以及師傅對徒弟的指導上,協同教學這種“共同做”的深度交流較為少見,值得嘗試。
從聽講輸入、觀察學習到實踐輸出,是一個遞進和深入的過程。科學教師培訓項目應當更多關注教師的實踐轉化,在課程中設置包含課堂實踐、成果交流等實踐模塊,并在教師實踐轉化過程中提供陪伴式的專家支持和指導,通過成果交流為教師搭建展示自身教學和跟同行對話的平臺,真正實現教師課堂教學行為的轉變。
3.3開展對培訓項目的追蹤性評價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影響是長期的,教師培訓同樣也不例外。尼克(C. Nichol)等學者研究了科學教師參加培訓對于學生科學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一年前參加培訓教師所教的學生成績顯著優于剛剛完成該項目的教師所教學生。這表明,教師需要時間來實施新的教學策略[9]。因此,我們要了解教師培訓項目的效果,也需要開展對培訓項目的追蹤性評價。
當前,我國對于教師培訓項目的質量評價主要集中在參訓教師的滿意度調查、教師的態度變化等方面,需要有更多基于實證的方法來研究教師培訓的效果,特別是教師的改變對于學生的影響,建立從教師培訓到教師的知識、觀念和行為改變,再到學生成績提高的證據鏈條。同時,也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探索影響教師培訓效果的因素,揭示在職教師從學習到實踐轉化的機制,為有效的教師培訓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新華社.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并發表重要講話[EB/OL].(2023-02-22)[2024-05-22].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2/content_5742718.htm.
田麗杰,李佳,姜春明,等. 教師培訓如何調節知識與信念對教學實踐的影響——基于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小學科學教師調研 [J]. 教師教育研究,2023,35(4):50-57.
王震,周丹華,盧婧,等.我國小學科學教師培訓現狀、問題及發展建議——基于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31134名教師的大規模調研[J].中小學管理,2023(1):52-55.
Brennan M. Teacher Training,Curriculum Reform Seen as Key to U.S. Science literacy[J]. 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News,2010,74(31):53.
?dalen J,Brommesson D,Erlingsson G ó,et al.Teaching University Teachers to Become Better Teachers:the Effects of Pedagogical Training Courses at Six Swedish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19,38(2):339-353.
Diamond B S,Maerten-Rivera J,Rohrer R E,et al. Effectiveness of a Curricular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at Improving Elementary Teachers’Science Content Knowledge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Outcomes:Year 1 Result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4,51(5):635-658.
Yang Y,Liu X,Gardella J A. Effects of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on Science Teacher Knowledge and Practice,and Student Understand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Concept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20(6):1028-1057.
Duncan Seraphin K,Harrison G M, Philippoff J,et al. Teaching Aquatic Science as Inquiry throug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Teacher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ent Outcome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7,54(9):1219-1245.
Nichol C,Chow A,Furtwengler S. Year-Lo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Fifth Grade Student Science Outco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8:1-19.
Chen J L,Mensah M F. Toward Socially Just Science Teaching throug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cience Teach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Agency of Two Elementary Teachers of Color[J]. Science Education,2022,106:385-411.
Nichols K,Burgh G,Kennedy C. Comparing Two Inquir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in Science on Primary Students’Questioning and Other Inquiry Behaviours[J].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2017,47(1):1-24.
Bryce T,Gray D. Tough Acts to Follow:The Challenges to Science Teachers Presented by Biotechnological Progr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04,26(6):717-733.
Michailidi E,Stavrou D.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6Kt08bDYZIvIaYxlFYweFg==f a Nanotechnology Teaching-Learning Sequence through Post-Induction Science Teacher Mentor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22,44(2):297-323.
Feldman-Maggor Y,Tuvi-Arad I,Blonder R.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 Online Course on Nanotechnology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Teach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22,44(16):2465-2484.
Clíona Murphy,Smith G,Broderick N. A Starting Point:Provide Children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with Scientific Inquiry and Nature of Science[J].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2019,36(12):2083-2109.
Wheeler L B ,Bell R L ,Whitworth B A,et al. The Science ELF:Assessing the Enquiry Levels Framework as a Heuristic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5,37(1):55-81.
Svendsen B. Mediating Artifact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5,37(11):1834-1854.
Tong F H,Irby B J,Lara-Alecio R,et al. A Randomized Study of a Literacy-Integrated Science Intervention for Low-Socio-Economic Status Middle School Students:Findings from First-Year Implement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4,36(12):2083-2109.
Lara-Alecio R,Tong F,Irby B J,et al. The Effect of an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 on Middle School English Learners’Science and English Reading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2,49(8):987-1011.
Magnusson S,Krajcik J,Borko H. Nature,Sources,and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for Science Teaching[M]//Gess-Newsome J, Lederman N G. Examining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1999:95-132.
Gustafson B,Guilbert S,Macdonald D. Beginning Elementary Science Teachers:Develop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uring a Limited Mentoring Experience[J].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2002,32(3):281-302.
Lee O,Hart J E,Cuevas P,et 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Inquiry-based Science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of Diverse Student Group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41(10):1021-1043.
Jaber L Z,Dini V,Hammer D.“Well That’s How the Kids Feel!”—Epistemic Empathy as a Driver of Responsive Teach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21(2):223-251.
Van Aalderen-Smeets S I,Van Der Molen J W. Improving Primary Teachers’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by Attitude-Focu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5,52(5):710-734.
Mant J,Wilson H,Coates D.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Conceptual Challenge in Primary Science Lessons on Pupils’Achievement and Eng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07,29(14):1707-1719.
Vivante I,Vedder-Weiss D. Examining Science Teachers’Engagement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 Multimodal Situate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23,60:1401-1430.
Miller A R,Kastens K A.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s of Targe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round Models and Modeling On Teachers’Instructional Practice and Student Learn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8,55(5):641-663.
Quarderer N A,Mcdermott M A. Examining Science Teacher Reflections on Argument-Based Inquiry Through a Critical Discourse Lens[J].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2020,50(2):2483-2504.
Oliveira A W . Improving Teacher Questioning in Science Inquiry Discuss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47(4):422-453.
Roth K J,Garnier H E,Chen C,et al. Videobased Lesson Analysis:Effective Science PD for Teacher and Student Learn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1,48(2):117-148.
Sabel J L,Forbes C T,Flynn L. Elementary Teachers’Use of Content Knowledge to Evaluate Students’Thinking in the Life Scien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6:1-23.
Heredia S C. Exploring the Role of Coherence in Science Teachers’Sensemaking of Science-Specific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Science Education,2020,104:1008-1040.
Falk A. Teachers Learning fro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lementary Science: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J]. Science Education,2012,96(2):265-290.
Geier R,Blumenfeld P C,Marx R W,et al. Standardized Test Outcomes for Students Engaged in Inquiry-Based Science Curricula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form[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45(8):922-939.
Littenberg-Tobias J,Beheshti E,Staudt C. To Customize or not to Customize? Exploring Science Teacher Customization in an Online Lesson Portal[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6,53(3):349-367.
Gerard L F,Spitulnik M,Linn M C. Teacher Use of Evidence to Customize Inquiry Science Instruction[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47(9):1037-1063.
Johnson C C,Kahle J B,Fargo J D.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Sustained,Whole-Schoo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Student Achievement in Scienc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44(6):775-786.
Maeng J L,Whitworth B A,Gonczi A L,et al. Elementary Science Teachers’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Design into Science Instruction:Results from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7,39(11):1529-1548.
Lotter C,Smiley W,Thompson S,et al. The Impact of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del on Middle School Science Teachers’Efficacy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qui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6,38(18):1-30.
Drewes A,Henderson J,Mouza 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esign Considerations in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Teacher Enactment and Student Lear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8,40(1):67-89.
教育部師范教育司. 更新培訓觀念變革培訓模式[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35-36.
R.基思·索耶.劍橋學習科學手冊(第2版)[M]. 徐曉東,楊剛,阮高峰,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21: 114-132.
Maulucci M S R,Brotman J S,Fain S S. Fostering Structurally Transformative Teacher Agency through Scien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5,52(4):545-559.
Pringle M R,Mesa J,Hayes L. Meeting the Demands of Science Reforms:A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Practicing Middle School Teachers[J].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2020,50:709-737.
Van Der Valk T,De Jong O. Scaffolding Science Teachers in Open-Inquiry Teach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09,31(6):829-850.
Goodnough K. Addressing Contradictions in Teachers’Practice through Professional Learning:An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8,4:1-24.
Kaderavek J N,Paprzycki P,Czerniak C M,et al. Longitudinal Impact of Early Childhood Science Instruction on 5th Grade Science Achie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20,42(7):1124-1143.
Paprzycki P,Tuttle N,Czerniak C M,et al. The Impact of a Framework-Aligned Scien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on Literacy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of K-3 Students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7,54(9):1174-1196.
Davidson G S,Jaber Z L,Southerland A S. Emotions in the Doing of Science:Exploring Epistemic Affect in Elementary Teachers’Science Research Experiences[J]. Science Education,2020,104:1008-1040.
Mclaughlin C A,Macfadden B J. At the Elbows of Scientists:Shaping Science Teachers’Conceptions and Enactment of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J].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2014,44(6):927-947.
Tobin K,Roth W M,Zimmermann A. Learning to Teach Science in Urban School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38(8):941-964.
Desimone L M. Improving Impact Studies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Toward Better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asures[J]. 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9,38(3):181-199.
(編輯 顏 燕 和樹美)
International Science Teacher PD Programs:
Content,Models,and Insights
Sun Huifang1 Li Xiuju2
(Beijing Institue of Education,Beijing 100044)1
(China Research Institu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Beijing 100081)2
Abstract: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science teachers is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science education put forward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era,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56 SSCI articles reporting on in-service scienc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reveals that the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cuses on themes such as integrative and cutting-edge science content knowledge,science inquiry including multiple models and variations,diverse perspectives on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and enhancing science teach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ix typic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des have been distilled from the analysis:experience-practice-reflection,demonstration-imitation,embedded learning based on course materials,individualized guidance through lesson study,real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and co-teach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this study offers insights for in-service science teacher training in China: integrating science content knowledge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cience teachers,and conducting follow-up evaluations of training programs.
Keywords:science teachers;science content knowledge;science inquiry;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del;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ffect
CLC Numbers:G53/57 Document Code:A 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3.007
收稿日期:2024-05-25
基金項目:北京市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青年專項課題“家校社協同視域下中小學災害教育系統化實施的模式構建研究”( CDCA21103)。
作者簡介:孫慧芳,北京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科學教育、科學教師培訓,E-mail:1140030853@qq.com。李秀菊為通訊作者,E-mail:littlej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