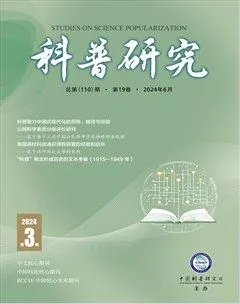在深度參與中構建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信任
[摘 要] 當前構建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信任,亟需“參與轉向”,這要求公眾深度參與科學實踐。公民科學快速而深入的發展,不僅在實踐層面很好地示例了公眾深度參與科學,而且反映了以往公眾理解科學、公眾參與科學及公眾信任科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頗為典型的問題是公眾在參與科學中缺乏積極性、主體性、具身性及公眾的過度參與。以公民科學為參與形式,公眾通過不同程度的具身參與,不僅真正融入了科學實踐,獲得了以往非具身參與難以企及的默會知識和深度理解,而且為信任科學奠定了經驗基礎。公眾深度參與科研活動產生的對科學的熟悉、理解及具身經驗,是其信任科學的重要前提。由此,基于深度參與構建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在具體的公民科學實踐中成為可能。公民科學的快速發展啟示我國在推進公眾理解、參與及信任科學工作時,一要進一步提升對公民科學素質和公眾參與科學的認知,深刻認識公民科學素質的多個維度和公眾參與科學的多元目的;二要加強相關政策制度,將政府支持與民間自治相結合;三要從組織和技術兩個層面加強公民科學實踐方式的創新。
[關鍵詞]公民科學 公眾理解科學 具身 信任 深度參與
[中圖分類號] G315 [文獻標識碼]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3.009
目前,人們普遍認識到公眾理解科學和公眾信任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如何更好地使公眾理解科學和構建公眾對科學的信任仍是公眾參與科學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是一類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公眾參與科學實踐[1]3,為公眾理解科學和信任科學的理論研究及實踐提供了新思路。公民科學廣義上指的是“公眾積極參與科學研究任務”[2]1。這樣的界定無疑過于籠統,但“單一或狹隘的定義可能會將各種活動排除在公民科學之外”[2]19。總之,迄今可見的30余種公民科學定義幾乎都包含以下要義:公眾積極、主動、具身地參與科學研究,為相關的公民科學項目作出實質性貢獻[2]15-18。
當前公民科學的快速發展,既受益于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也與對公民科學的迫切需要相關。具體而言,一是一些科學研究的數據密集型特征日益突出[1]5;二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普及,使人們參與公民科學變得更便利和廉價[1]6。盡管公眾參與科學的深度與方式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它們都突出了公眾對科學知識生產的直接參與,這是“公眾參與科學模式的一種潛在轉變”[3]。這種“潛在轉變”與希拉·賈薩諾夫(Sheila Jasanoff)所說的“參與轉向”[4]大體相同。在這種轉變背景下,公民科學在歐美各國快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揭示了以往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一些重要不足。對中國而言,科學傳播、公眾理解科學、公眾參與科學的當務之急是“從規范性邏輯、工具性邏輯向實質性邏輯的跨越”[5],要實現這種跨越,通過公民科學推動公眾深度參與科學是可選路徑之一。
總體來看,國內外學界對公民科學及與之相關的科學傳播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由于公民科學在歐美國家有頗為豐富的實踐,國外學界的公民科學研究不僅注重對其內涵和外延的探討,而且特別重視對如何借助公民科學推進科學傳播、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方法論的研究,如對草根公民科學組織在風險傳播及評估方面的作用的研究等[1]81-82, [2]1-12, [3][6]。相比之下,國內學界的公民科學研究還有較大的推進空間。國內學者除述評國外學界的公民科學研究之外[6],還就公民科學的知識生產方式、對科學傳播的推動、科學民主化等及中國的公民科學實踐狀況做了一定的理論探討[7-10]。然而,已有研究從公民科學的角度探究公眾理解、參與及信任科學等還不夠全面而深入,尤其未基于公民科學實踐系統地分析這些問題并提供解決思路。有鑒于此,本文基于公民科學實踐探討以往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向深度參與的轉變,進而分析這種轉變對構建公眾理解和信任科學的意義和作用,最后對中國推進公眾深度理解、參與及信任科學提出啟示。
1從公民科學看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1公眾不充分理解和參與科學
長期以來,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公眾的被動參與。造成這種被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一些公眾僅僅被視作研究對象,甚至成為被動的數據提供者[11],其遵循的是公眾參與科學的“工具性邏輯”,這點在當前的中國公眾參與科學中也有體現。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舉辦的多場次轉基因大米品嘗會,主要是為了消除公眾對轉基因大米的疑慮,帶有一定“形式正確”的色彩[5]。
從西方科學實踐來看,由于公眾缺乏主動性和主導地位,其參與科學被工具化和政治化,公眾在科學實踐中扮演了見證者和研究資料提供者的角色,也被當作使科學決策合法化的政治手段,其目的已經脫離了理解科學和信任科學,甚至適得其反[11]。這種情況往往出現在受政府資助的科研機構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公眾參與科學中,因為“這是一種在沒有真正致力于共享社會產品的情況下提高研究資助和研究影響的策略”[12]51。此種“參與”往往并不能使公眾真正地理解科學,反而造成了對科學不正確或片面的理解。被動參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當公眾意識到自己充當了“工具人”或政治決策見證人后,其對科學家和科學的信任勢必降低。
如今,雙向互動和對話是科學傳播的首選方式[2]479,這需要讓公眾積極主動地參與進來。這里所說的“參與”在英文世界是“involvement”,而非“participation”和“engagement”。“involvement”是最為積極主動的參與,這意味著“在有些情況下,公眾在研究本身的規劃和實施中發揮著積極作用,甚至可以選擇要解決的科學問題”[11]。相比之下,傳統的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往往表現出惰性,公眾在其中頗為被動,甚至很多科學實踐缺乏與公眾的直接利益關聯,而脫離實際地認為“公眾是一種被動的均質的群體”[5]。然而,公民科學實踐能在無形中打破橫亙在科研機構、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隔膜,讓公眾成為主動的參與者,在其中實現自我價值,以構建雙向互動的科學傳播。
1.2公眾淺層理解和非具身參與科學
隨著公眾參與科學越來越被要求實質化[5],走馬觀花式的非具身參與很難達到讓公眾理解和信任科學的目的。不論是傳統科普方式,如文字科普和實地科普,還是“科學公眾日”這樣的公眾理解與參與科學活動,在深入理解和參與科學方面依然有不小的發展空間。因為,這些參與活動所呈現的多是科學知識和科研成果,或者讓公眾對科研“驚鴻一瞥”,而不是深入科學現場,這會導致公眾理解科學的“赤字”,即公眾對科學過程的理解不足[2]63。就參與科學而言,上述這幾種方式還不充分,因為它們沒有使公眾具身地參與到科學研究的過程中。
公眾參與科學的困難不僅來自主觀因素,而且有客觀的技術根源。主觀因素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科學家并未公平對待公民作為研究人員等的身份,而是將公民視作免費科研勞動力,這在一些公民科學實踐(如某些科研眾包)中有明顯表現。例如,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平臺上的一些科研眾包項目,看似是公民科學實踐,其實是一種低微報酬的數字勞動。技術根源是指科學實踐包含了大量的默會知識,只有真正“社會化”進入(socialised into)科學實踐的人,才能掌握這些默會知識[13]。當下西方社會公眾對科學權威的信任度在顯著下降[12]7,這種情況在中國也有表現[14]。盡管引發這些不信任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但公眾缺乏對科學實踐的了解與認識是重要原因之一。
淺層參與往往帶來對科學的淺層理解,也很難修復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在傳統公眾參與科學中,呈現給公眾的主要是既定的科學知識或特定時空下的科學實踐,而不能將公眾帶入科學現場和持續的科學實踐中。淺層參與能避免一些科學爭論,這或許是一些人不希望公眾深度參與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公眾深度參與科學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如不僅會讓科學家卷入一些政治爭論,而且會引發公眾對官方關于科學技術的解釋的懷疑[1]35。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公眾對科學及其研究過程缺乏充分而深入的了解,也可能引發更嚴重的不信任危機。只有將公眾吸納到科研中,對公眾開誠布公,才有望提升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信任。
1.3公眾過度理解和參與科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科學技術與社會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STS)研究揭示了科學實踐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科學知識生產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兼受后現代主義等思潮的影響,科學實踐的理性形象被解構了,科學被認為與政治糾纏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人人都可以參與到有關科學技術的爭論之中。
在科學及專家的權威被不斷侵蝕和貶損的情況下,公眾參與科學可能演變為一種科學技術民粹主義,這在當前的西方社會有較為普遍的表現[12]1。在公眾參與科學日益向政治化轉變的同時,當前的很多事件表現出了“后真相”的特征,即人們更愿意相信能夠迎合自己情感需要的情況,而不再關心這些情況是否符合客觀事實。由此,公眾參與科學被政治團體利用,進而造成公眾對科學的過度理解和參與。
公眾參與科學的興起與反科學精英密切相關,而反精英往往是民粹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故二者具有天然的親緣性。公眾參與科學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是對科學自治的解除。“完全科學自治”的主張是“只有專家才有能力對科學及其軌跡做出決定,而‘民意’在這種審議中不起作用”[15]。今天,盡管“民意”介入科學實踐已具有合理性,但衍生了一種擔憂——人人都是專家。與此相應的一個典型事件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任命的環保官員對氣候科學有效性的否認[16]5。有鑒于此,亟待構建合理的公眾參與科學模式,以使公眾正確地理解科學和重塑對科學的信任。公民科學已有頗為充分的實踐,其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對構建合理的公眾深度參與科學大有裨益。
2在公民科學的深度參與中理解和信任科學
2.1公眾參與科學的方式和態度向深度、主動及具身的轉變
從公民科學來看,當前構建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信任中存在一些重要問題,公眾參與科學的方式和態度也亟需轉變,即增強參與的積極主動性和具身性,以達到對科學的深度理解和參與。這些轉變在歐美國家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現實圖景。例如,歐洲各國搭建起來的國家公民科學網絡,吸引了有各種目標的參與者,這些平臺“形成了國家公民科學信息中心”[2]450。
什么是深度參與?對深度參與作一個清晰的界定無疑較為困難,但可以參照公民科學實踐嘗試對其進行界定。歐洲公民科學協會的“公民科學十大原則”(The Ten Principles of Citizen Science)指出,“公民可以作為貢獻者、合作者或項目領導者,并在項目中擔任有意義的角色”[17]29。由此來看,在公民科學實踐中,公民要么作為正式科研人員的協助者,要么作為科研活動的主導者。作為協助者,公民在科學研究中一般扮演次要角色,如為科學家收集數據和處理數據。作為主導者,公民在科學研究中一般扮演主要角色,如制定研究框架、技術路線及研究方法,與科學家在認知方面基本享有平等地位。當然,根據公民在科學研究中所作貢獻和參與深度的不同,可以將公眾參與科學劃分為5個梯度,即合約型、貢獻型、協作型、共創型、學院型,前面2個梯度中的公眾只是參與科研的一個階段,后面3個梯度則是全程參與[18]。在一些公民科學項目實踐中,公民與科學家平等合作,甚至能夠“以一種自主的方式設計和實施有效和穩健的研究過程”[2]202。公民科學實踐的多樣性,可以包容不同背景和技能水平的參與者[19]。因此,深度參與是相對于前述的被動參與、淺層參與及過度參與而言的,且現實中的“深度”會因科學實踐中公眾的角色而發生變化。如果必須對深度參與作出界定,那么,作為協助者的公眾參與是初級深度參與,而作為主導者的公眾參與是高級深度參與,二者皆是深度參與,只是二者的級別有所差異。
即使是公眾主動參與科學,也存在兩種主要方式。一種是思維層面,如公眾參加科學技術研究決策活動,在決策中發表意見和建議,甚至直接參與相關決策,但幾乎不“動手”參與到具體研究之中,因而缺乏具身性;另一種是實踐層面,即通過行動具身地參與到科學實踐之中,其角色與正式的科研人員類似,因而具有較充分的具身性。盡管這兩個層面的參與皆主動積極,但不無差異。思維層面的參與不能夠深入科學實踐,尤其是未具身地走入科學爭論的核心,因此很難稱之為深度。而實踐層面的參與往往包含思維層面的參與,公眾是完備意義上的科學共同生產者之一,這是一種協同治理框架下的科學實踐[12]52-54。事實上,當前公眾對政治和科學等的普遍不信任,也增強了他們參與的意愿[20]51。在公民科學框架中的公眾參與科學,公眾在意的往往是表達了自身意愿和參與其中,并且獲得了學習和社交的機會[21]。
2.2重新認識科學實踐中的公眾及其對科學的理解
傳統的線性科學傳播模型認為,“科學家被視為真正知識的制造者,這些知識還將得到簡化。公眾被視為毫無差異的個體,他們是知識的被動消費者”[22]7。早期對公眾的這種角色定位存在嚴重的誤差。然而,隨后所做的轉變依然“微弱”,還是將公眾視為科學的消費者、支持者、見證者、參與者[22]12。盡管通過對“赤字模型”(此種模型中的公眾被認為是科學知識的缺乏者和被動接受者)的批評,公眾不再被認為是完全無知和被動的,但消費者、支持者、見證者、參與者等角色幾乎無一例外地界定了公眾對科學的被動參與、淺層參與和淺層理解,公眾在其中依然以被動角色為主。
事實上,公眾并非像傳統刻板印象中的那樣是被動和無知的[12]102。公眾不僅可以在科學實踐中成長為專家(如美國艾滋病活動者),而且可能已是未經認證的專家,即基于經驗的專家(如英國坎布里亞牧羊人)[23]60-62。由此,在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框架下,應該“開放地對待不同的理解和知識”[24]168。總之,“案例研究表明,很多公眾(更多時候是其合法代表)能夠熟練地運用科學知識,并加入到科學討論中來”[22]159。基于純粹的規范視角,公民科學及其構建起來的網絡受科學問題和好奇心驅動,其目標是貢獻新知識,同時為貢獻者提供利益和為社會生產附加價值[2]450-451。值得注意的是,將公民科學項目引入學生教育可以很好地提升學生對科學的理解和參與[25]。盡管在公民科學實踐中很難將上述目標和價值完美地實現,但公民科學在逐漸消除以往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中存在的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
公眾已經不滿足于對科研成果或科學知識的了解和掌握,而是要深入到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即走向科研現場,這是一種通過直接“動手”而具身地理解科學的方式。與之相應,所謂“公眾理解科學”,其旨趣已經超越了公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而特別重視科學實踐中公眾的直接互動與合作,公眾對科學運作的整個過程往往充滿了參與欲望,尤其是那些與自身利益緊密關聯的科學實踐。對于與公民直接相關且影響巨大的科學實踐,公眾與科學家的開放交流在相互間的理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12。對大量公民科學實踐結果的考察可以表明,公民科學實踐不僅能增強他們對科學內容的理解,有時還可以使人們了解科學的過程和本質。尤其是共創型公民科學項目,公眾對科學實踐的參與往往最為深入,故對公眾理解科學的積極影響最為深刻[25]。還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科學實踐的多樣性帶來了認知實踐的多樣性[3],這也為公眾從多個維度理解科學創造了條件。
2.3在深度參與中構建信任關系
公眾對專家意見的信賴是“公眾理解科學中的一個(或者唯一一個)核心問題”[22]159。關鍵是,如何才能構建公眾對科學、專家及其意見的信賴呢?“只有在熟悉的世界信任才是可能的……沒有所有的先前的經驗,我們不可能付出信任”[26]26。公眾對科學的信任,無疑需要建立在對科學實踐的“熟悉”之上。當前,關于科學危機的爭論頗為激烈,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也愈演愈烈[2]8。科學信任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是公眾對科學實踐缺乏認識和參與,或者說不熟悉科學實踐。在傳統的公眾參與框架下,公眾對科學的認知往往是對科學知識的了解和掌握,而非對科學知識生產過程的了解和掌握。通過深度參與科學,公眾成為科學實踐的主體之一,這為構建公眾對科學的信任提供了重要條件。
以往構建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常常過于依賴科學家、科研機構、科普單位對公眾的單向灌輸與宣傳。特別是當專家與政府及其他機構的利益密切關聯在一起時,公眾對其表現出了極為嚴重的懷疑[14]。在利益關聯難以徹底切斷的情況下,科學實踐和技術決策的開放及透明是解決公眾對科學懷疑的可行方法之一,“目前在世界上許多國家被采納和制度化的公眾參與議程,為公眾對科學信任的減少提供了一種潛在的補救措施,乃是一種富有成效的方式”[12]5。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在與社區環境密切相關的研究項目中,“當地居民參與研究過程的程度增加了公眾對研究結果的信任”[27]。公民具身參與公民科學創造的控制感和透明性、獨立科學機構的參與及公民參與者同該項目科學家的積極互動,共同促成了這種信任[28]。這也可能改善和加強社群與研究人員之間的伙伴關系[29],進而為在他們之間構建牢固的信任關系創造重要條件。此外,公民科學實踐中的科學對公眾及所有利益攸關方的開放性,為充分溝通和建立信任創造了可能空間[30]。
當然,盡管通過公民科學實踐可以修復和構建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但也可能引發相反的問題,即加深二者之間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主要是職業科學家對公民科學項目及其公民參與者的不信任,尤其是對公民提供的數據的不信任。在擯棄偏見和傲慢的前提下,通過在參與方式、數據收集等方面的進一步規范化、開放及交流,公民科學可以在科學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在一些公民科學實踐中得到了證實,關鍵是在公民科學的領導者與參與者之間構建相互尊重的關系[31]。與此同時,適當的公民科學確實可以修復和加強公眾與科學家之間的信任關系[2]215。反之,抵制和排斥公眾參與往往會引發對科學的不信任。現實中的一些公民科學就源自公眾對決策者的不信任,而公眾參與則可能“引發一場基于獨立數集的有意義的對話,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增加信任”[2]363。因此,開放性的公眾深度參與科學是化解信任危機和重建信任關系的可選道路。
3對中國推進公眾深度理解、深度參與及信任科學的啟示
3.1進一步提升對公民科學素質和公眾參與科學的認知
中國各界已認識到了推動公眾深度理解、參與及信任科學的重要性,這從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踐[5]中可以看出。但就公民科學實踐的發展而言,中國各界還需進一步提升對公民科學素質和公眾參與科學的認知。
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刻認識公民科學素質的多個維度,即公民科學素質不止于對科學知識及科學相關常識的掌握,深度參與科學的動力和能力(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創新動力和能力)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推動公眾參與科學的目的也應該是多維的,除增加公眾的科學知識及其對科學的理解和信任之外,在深遠意義上還應將增強公眾的科技創新能力納入其中。例如,德國和奧地利政府將公民科學視作提高公民科學素質和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一種手段[2]39。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32]。因此,中國應該借助發展公民科學之機,推動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的耦合。與此同時,在測評公民科學素質的過程中,應該增加公民具身參與科學的權重,將公民是否有能力“動手”參與科學作為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
另一方面,公民科學實踐表明,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目的和動力是多重的。要調動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積極性和持續性,就必須充分考慮公眾參與科學過程中的成長、發展及自我實現等結果,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關注公眾參與科學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上[33]。這點值得中國在推進公眾理解、參與及信任科學工作時借鑒。盡管多數公民科學項目的主要目的是科學研究,但其在公眾理解和信任科學方面能產生重要的附加價值。就中國而言,應該更加深入地認識到這點,并使它在對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的構想中有所體現,甚至成為其中的一個重點內容。否則,公眾參與科學有可能缺乏內在動力,也不利于公眾對科學的深度理解和信任。
3.2加強政策制度創新:政府支持與民間自治的結合
盡管公民科學具有較大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但依然離不開來自政府的政策支持。只有將政府支持與民間自治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切實推動公民科學的發展。
在歐洲和美國,公民科學得到了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且這些支持的力度往往很大。如美國白宮的《聯邦獎和公民科學授權的實施:2017—2018財政年度》(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 Prize and Citizen Science Authority:Fiscal Years 2017—2018),自2011年以來,歐洲的一些公民科學項目也得到了歐盟第七框架計劃以及“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計劃的支持,迄今約已有2.34億歐元投入與公民科學有關的項目[2]45。中國在科普、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出臺,如《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但還是未能特別突出公眾深度參與科學的重要性,也未見專門針對公民科學的政策出臺,未表現出對公民科學項目的大力支持。中國可以在資金和政策等方面對公民科學進行重點支持。盡管公民科學項目一般由科研機構、社區、社會非營利組織等發起和組織,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美國公民科學近年來的實踐表明,政府在推動國家的公民科學蓬勃發展中具有無法替代的主導作用”[34]。
此外,歐洲的許多公民科學項目的資金來自政府,并且將這些項目與學校教育結合在一起,讓學生與研究人員一起工作[2]39-40,這值得中國學習與借鑒。公民科學制度創新的主體可以是政府機構,也可以是非政府機構,就歐洲而言,已有幾個國家就公民科學制定了國家層面的制度戰略,而科研機構、非政府組織及社區等非政府機構是其制度創新的主體[2]38。中國也應該調動社會機構對公民科學的引導和組織。公民科學在制度創新方面的形式非常多樣,中國似乎更為亟需相關的制度創新,如為國內公民科學實踐制定原則,為公民科學數字平臺建立數據、元數據標準等。在實踐層面,可以嘗試將公民科學項目納入中國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框架,也可以將其與科技創新結合在一起。尤其在將來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中,應該將公民科學作為一個重點內容和提升公民科學素質的載體。
3.3從組織和技術兩個層面加強公民科學實踐方式的創新
促進公民科學實踐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如何發動和吸引公眾持續、廣泛、低成本地參與,這需要實踐方式的不斷創新。就中國現狀而言,公眾參與科學的理論研究走在了實踐前面[5],這或多或少受到了我國公眾參與科學實踐方式創新不足的影響。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大中國公民科學實踐方式的創新。
一方面,要在組織層面加強公民科學實踐方式創新。盡管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公民實踐方式創新受限于國情和地情,但可以在互相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例如,奧地利借助公民科學平臺,建立了不同主題的公民工作小組,以明確參與主題和活動性質;與此同時,奧地利自2015年以來每年都組織一次奧地利公民科學會議,作為奧地利公民科學界內部個人交流的中心活動[2]450。此外,實踐方式創新還要考慮公眾參與的動機與目的,公眾深度參與科學的動機和目的往往因人而異,如有些人因為對動物的深厚情感而參與沙灘環境研究項目[33]。因此,在組織公眾參與科學時,要重視公眾動機與目的的異質性和多元性。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各級科協、學會已建立的組織平臺,嘗試讓公民科學項目在這些平臺上運轉,或基于這些平臺開展組織方式創新等。
另一方面,要在技術層面加強公民科學實踐方式創新。公民科學的開放性和發展壯大,與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創新使用密切相關。例如,隨著智能客戶端(如智能手機)的普及,開發用于公民科學項目的App已引起高度重視,“智能手機帶來了一場公民科學的革命”[2]462。還可以將創新主體向教育機構延伸,如中小學。在國外的公民科學實踐中,僅9歲的兒童就能夠“收集有價值的哺乳動物監測數據,同時親近自然和通過自己的科學發現開展學習”[35]。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這些技術創新,然后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做一些調整。此外,實施和發展公民科學,相應的平臺非常重要,“公民科學平臺是公民科學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方面……可以作為一個國家公民科學的催化劑”[2]440,451。由于公民科學實踐往往在網絡平臺上開展,而網絡平臺可以吸納全球各地公眾參與,故網絡平臺與非網絡平臺同等重要,前者在多數情況下甚至比后者更重要,中國也要加強公民科學平臺(尤其是網絡平臺)的建設,如構建一些專門的公民科學互聯網平臺、App、微信公眾號等,以此為公民科學實踐提供必要的工具。
4結語
長遠來看,公民科學將在各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會日益成為推動公眾深度參與科學的重要方式之一。盡管中國已有多種公民科學實踐,但相比國外還是“青澀”了不少[36]。因此,應該在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和科技創新的框架下,借鑒西方國家公民科學的成功經驗,加強我國公民科學的建設,借此推動公眾深度理解和參與科學,進而增強和重構公眾與科學的信任關系。
參考文獻
詹姆斯·韋恩.數字時代的公民科學:修辭學科學和公眾參與[M].王麗慧,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
Vohland K,Land-Zandstra A,Ceccaroni L,et al. The Science of Citizen Science[M]. Cham:Springer Nature,2021.
Strasser B,Baudry J,Mahr D,et al.“Citizen Science”? Rethinking Scie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J].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2019,32(2):52-76.
Jasanoff S. Technologies of Humility: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Governing Science[J]. Minerva,2003,41(3):223-244.
楊正,肖遙.為何要引入公眾參與科學——公眾參與科學的三種邏輯:規范性、工具性與實質性[J].科學與社會,2021,11(1):115-136.
羅健,李健.國外公民科學項目案例研究綜述[J].科普研究,2021,16(6):68-79.
賈鶴鵬.基于公眾參與科學視角探索“公民科學”的中國路徑[J].科學與社會,2024,14(2):1-13,97.
朱晶,張明君.公民科學與社群科學中的認知勞動分工[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2,44(9):86-94.
陳強強.基于公民科學實踐的科學民主化理論研究[J].科學學研究,2020,38(6):968-975.
方可人,喻國明.參與式科學傳播:公民科研的國際實踐——基于知識圖譜范式的分析[J].東南學術,2020(4):205-217.
Woolley J P,McGowan M L,Teare H J A,et al. Citizen Science or Scientific Citizenship? Disentangling the Uses of Public Engagement Rhetoric in 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s[J]. BMC Medical Ethics,2016,17(1):33.
Mattei P. Democratizing Science:The Political Roots of the Public Engagement Agenda[M]. Bristol:Bristol University Press,2023.
Collins H.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J]. Topoi,2018,37(1):67-77.
郭飛,盛曉明.專家信任的危機與重塑[J].科學學研究,2016,34(8):1131-1136.
Kleinman D L. Beyond the Science Wars:Contempla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J]. 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1998,17(2):133-145.
Collins H M,Evans R,Durant D,et al. Experts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Society,Populism and Science[M]. Cham:Palgrave Macmillan,2020.
Hecker S,Haklay M,Bowser A,et al. Citizen Science:Innovation in Open Science,Society and Policy[M]. London:UCL Press,2018.
Shirk L J,Ballard L H,Wilderman C C,et 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A Framework for Deliberate Design[J]. Ecology and Society,2012,17(2):29.
MacPhail V J,Colla S R. Power of the People:A Review of Citizen Science Programs for Conservation[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2020(249):108739.
Phillips L,Carvalho A,Doyle J. Citizen Voices:Perform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Pasgaard M,Breed C,Heines M,et al. Citizen Science Beyond Science: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for Transformat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itizen Science:Theory and Practice,2023,8(1):1-14.
邁諾爾夫·迪爾克斯,克勞迪婭·馮·格羅特,迪爾克斯,等.在理解與信賴之間:公眾科學與未來[M].田松,盧春明,陳歡,等譯. 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伊萬·塞林格,羅伯特·克里斯.專長哲學[M].成素梅,張帆,計海慶,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Irwin A. Citizen Science:A Study of People,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Bonney R,Phillips T B,Ballard H L,et al. Can Citizen Science Enha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6,25(1):2-16.
尼克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Bedessem B,Gawronska-Nowak B,Lis P. Can Citizen Science Increase Trust in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Delineating Polish Metropolitan Area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2021,17(2):305-321.
Vegt K R,Elberse J E,Rutjens B T,et al. Impacts of Citizen Science on Trust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Trust in Science in a Polarized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ning,2023,25(6):723-736.
Mahajan S,Kumar P,Pinto A J,et al. A Citizen Science Approach for Enhanc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Air Pollution[J].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0(52):101800.
Hecker S. Citize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A Growing Concern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J].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2022,21(7):C09.
Phillips T B,Ballard H L,Lewenstein B V,et al. Engagement in Science through Citizen Science:Moving Beyond Data Collection[J]. Science Education,2019,103(3):665-690.
習近平 .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00.
Haywood K B. Beyond Data Points and Research Contributions:The Personal Meaning and Value Associated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Part B,2016,6(3):239-262.
劉婭.美國聯邦政府推動公民科學發展舉措及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科技資源導刊,2022,54(4):44-50,70.
Schuttler S G,Sears R S,Orendain I,et al. Citizen Science in Schools:Students Collect Valuable Mammal Data for Science,Conservation,and Community Engagement[J]. Bioscience,2019,69(1):69-79.
朱子峽.盤點2017年:中國公眾科學實踐[EB/OL].(2017-12-29)[2024-03-15].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2/398588.shtm.
(編輯 顏 燕 荊祎瀾)
Construct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in Science through Involvement:A Study Based on Citizen Science
Chen Qiangqiang
(School of Marxism,Xizang Minzu University,Xianyang 712082)
Abstract:At present,build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and trust in science requires a“participatory turn”,which calls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deeply in scientific practice. The rapid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itizen science not only exemplified the deep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but also reflecte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building public trust in science in the past. The typical problems are the lack of enthusiasm,subjectivity and embodiment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xces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 citizen science as a form of participation,the public,through different degrees of embodied participation,not only truly integrates into scientific practice,but also obtains tacit knowledge and deep understanding that was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out embodied participation in the past,and also lays an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trust in science. The familiarity,understanding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cience generated by the public involve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prerequisites for their trust in science. Thus,it is possible to build public trust in science in concrete citizen science practic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izen science has provided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public understanding,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scientific work in China. Firstly,further enhance the cognition of citizens’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the multiple purpos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Secondly,strengthen the relevant policy system and combine governmental support with civic self-governance. Thirdly,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the way of practicing citizen science at both the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levels.
Keywords:citizen science;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embodiment;trust;involvement
CLC Numbers:G315 Document Code:A 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3.009
收稿日期:2024-04-19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后期資助項目(23FZSA005)。
作者簡介:陳強強,西藏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哲學、科技史及馬克思主義理論,E-mail:kezhechenq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