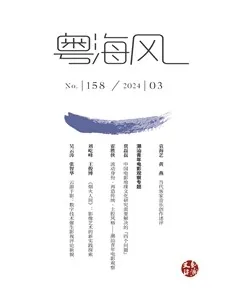魯迅小說中的創傷再現及其應對
摘要:魯迅少年喪父,生活從小康墮入困頓,赴日留學“走異路”中亦頗多艱辛,而后的兄弟失和打擊、與多人筆戰、長期患病等等,魯迅一生經歷的創傷體驗并不少,在其文學生產中,創傷話語亦屢屢可見。他在對創傷的小說再現中,呈現出創傷的挫敗性慣習,一方面指向了傳統致人挫敗的殺傷力,另一方面則說明現代轉換中亦有類似慣習。魯迅亦有復仇創傷的書寫實踐,他強調反抗遺忘和自奴,同時亦有攻擊性乃至同歸于盡的復仇理念。而在其作品中,亦有療治創傷的書寫,其中也是悖論重重。
關鍵詞:魯迅小說 創傷話語 再現 療治 復仇
從宏闊的視野考察魯迅的一生,既可以說這是他不斷探索、批判、搏斗的一生,又可以說是與創傷協商的一生。從他的經歷來看,早期由小康墮入困頓深切感知世態炎涼的屈辱感,亡父后作為長子、長孫和寡母相依為命打點家庭事務的艱難,乃至不得不背井離鄉去洋學堂求學,赴日留學,回國工作后亦遭受各種各樣的挫折(如和教育總長章士釗打官司),哪怕是成為專業作家以后也要面對各式各樣的飛矢刀劍。而在其個人生活中,無論是不幸的包辦婚姻悲劇,還是傷筋動骨的兄弟失和,還有晚年的多愁多病等諸多創傷性事件,伴隨也構成了魯迅的一生。
本文中所指的創傷主要指精神創傷,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對精神創傷的解釋是:“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1] 不必多說,這些(巨大的)創傷會對個體、民族乃至國家產生較大影響,甚至形成了一種“創傷記憶”,而張志揚在《創傷記憶》中如此定義,“所謂民族的苦難記憶或個體承擔的創傷記憶,說到底是各種形式的暴力——自然的人為的、惡的善的、理性的非理性的、政治的道德的、包括話語的——從個人的在世結構的外層一直砍伐到個人臨死前的絕對孤獨意識,像剝蔥頭一樣,剝完為止,每剝一層都是孤獨核心的顯露。我把這種孤獨核心的強迫性意識叫做創傷記憶。”[2]
作為一個聰慧早熟、敏感銳利的作家,魯迅在其文學生產中對創傷進行了大量的書寫,無論是小說還是《野草》中都相當常見。《吶喊·自序》如果從此角度看,就是一個對創傷進行克制性文學描述的生產與再現:被侮辱與傷害的少年亡父、異地求學、“幻燈片事件”的震撼、以文學(刊物)救國理想的破滅,魯迅先生其實用了關鍵詞“寂寞”來概括和應對這諸多創傷的打擊,“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愿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哪怕是回望的言辭中依然有充沛的不甘和滿腔落寞。
有論者指出:“創傷原來是突發的威脅對人產生的影響和后遺癥。跟是男性或者女性都沒有關系,也跟當場逃跑或者戰斗沒關系。可是,在中國文學里勇敢的斗士基本上不知道恐懼;只有女人、孩子和懼怕被閹割的男人體驗創傷。因為文學描寫的創傷事件大部分與國家和家庭有關系,所以創傷也涉及對性別、家庭和民族性的理解和期望。”[3] 所論有相對粗糙和簡單之處,但涉及到創傷的個體性與集體性之間的復雜關聯卻是一種洞見。某種意義上說,魯迅作品中的創傷再現既是個體的,又是民族的,同時,其背后又有更繁復的類型與因果關聯。這里的創傷話語[4],不是單純小結創傷的文字呈現及其形式意義,而是更強調這種內在感受化為文字后的思維/思想運行軌跡,它在化為文學作品時,有些是直接挪用既有的創傷經驗,有些則是化為一種批判姿態、思路,當然,其中也密布了魯迅特色的悖論。
一、再現創傷:挫敗慣習
不必多說,在人生關鍵時期的創傷會對個體產生不容忽略的影響,往往是挫敗感和悲劇感,如果是相對羸弱懦弱的個體,甚至會崩潰。相較而言,提倡韌性戰斗的魯迅先生面對挫折時亦相對堅韌,但同樣敏感多情、才華橫溢的他卻也有不少文字細描:或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或濃墨重彩,或從某角度涉獵,或近乎全面鋪開,在魯迅的三部小說集中,涉及到創傷話語的書寫篇目超過2/3。而且,耐人尋味又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數篇什呈現了挫敗的慣習,這種挫敗土壤一方面來自傳統,另一方面則是大變局中現代轉型的失敗體驗。但不管怎樣,魯迅先生借此再現了創傷的痕跡、層次、類型與共通性。
(一)致人挫敗的傳統
弗洛伊德指出:“一個人生活的整個結構,如果因有創傷的經驗而根本動搖,的確也可以喪失生氣,對現在和將來都不發生興趣,而永遠沉迷于回憶之中。”[5] 相較而言,魯迅先生作為韌性十足的戰士,他并不是弗氏所指的普通一員,但不必多說,創傷經驗對于他卻也有相當明顯的挫傷效力,而表現在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生產中則是對連綿不斷的傳統挫敗力的一再再現。
1. 創傷傳統的普泛性
或許是魯迅自身的不愉快經歷化成了相關書寫的底色,在其小說中創傷話語生產呈現出傳統的卑劣和傷人的普泛性。《狂人日記》中塑造了狂人的形象,但借此揭露的卻是傳統文化吃人的本質。小說中狂人受迫害狂的癥狀不時發作,而月光強烈時尤甚,這毋寧更可視為受傷慣習的經常性條件反射。魯迅從主體的復雜感受和周邊環境的方方面面論證了宏大傳統的糟粕屬性——吃人。
魯迅也書寫了這種創傷傳統在其他層面的殺傷力。比如《孔乙己》《白光》中的男主人公如何被吞噬:孔乙己“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但更令人心寒乃至受傷的則是社會的冷漠,他屢遭傷害卻不過是咸亨酒店(及其社會象征語境)里的可笑談資。而陳士成即使死了也被人羞辱,被剝去了衣褲,其實這是“辱尸罪”,“渾身也沒有什么衣褲。或者說這就是陳士成。但鄰居懶得去看,也并無尸親認領,于是經縣委員相驗之后,便由地保埋了。至于死因,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剝取死尸的衣服本來是常有的事,夠不上疑心到謀害去。”這體現出創傷傳統如何對付階層躍升失敗的傳統知識分子,它也可以傷害賤民[6],比如底層婦女。《明天》中的寡母單四嫂子在獨子寶兒死后其實已經沒有明天,她如此寂寞,卻是被閑漢藍皮阿五借抱小孩時性騷擾,兒子死后她“單覺得這屋子太靜,太大,太空罷了”。不難看出,這又是一個被封建倫理嚴重傷害的個體。《祝福》中祥林嫂其實遭受了多重身心創傷的折磨:從老公祥林去世到被逼二嫁,結果新老公賀老六死于傷寒,乖巧的兒子阿毛又在一時疏忽中被狼吃了,而即使她自己拿出積蓄捐了門檻后依然被剝奪了祭祀時打下手的權利,簡而言之,她其實死于“集體謀殺”。[7] 不難看出,她也是一個長期被侮辱和傷害的對象。
除此以外,也有對其他階層的傷害,如《故鄉》中的老年閏土,可以視為農民代表,被各種事故打擊到只剩下沉默與木訥。又如《風波》中刨除現代性事件的攪局,變成了茶杯里的風波,而塵埃落定后,民國已經過去了數年,最受傷害的依然是底層的兒童,六斤依然是被裹了小腳,結尾寫道:“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卻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著十六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由上可見,傳統的吃人性歷歷可辨。
2. 無法拯救現在的傳統
相當耐人尋味的是,傳統有其糟粕致人挫敗的創傷習慣,但另一面,即使是其精華部分,在面對新傳統、現代性時,亦有其限制可能:要么無法因應新形勢,要么呈現出時代的局限性,這尤其體現在魯迅《故事新編》的書寫中。
《奔月》中曾經立下豐功偉績、射殺封豕長蛇以及驕陽烈日的夷羿最終卻屢遭重創:鄉下老婆子的粗中有細、指桑罵槐已經令其相當狼狽,“五谷不分”(老母雞還是鵓鴣)也顯而易見,而學生逢蒙的中傷、明箭、詛咒更令人狼狽不堪,但相較而言,為師的羿似乎亦有教導無方之錯,但最大的傷害卻是美艷嬌妻嫦娥的背叛——她偷偷服下仙丹私自奔月去了,盛怒之下的夷羿亦有射月之舉,“颼的一聲,——只一聲,已經連發了三枝箭,剛發便搭,一搭又發,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別那聲音。本來對面是雖然受了三枝箭,應該都聚在一處的,因為箭箭相銜,不差絲發。但他為必中起見,這時卻將手微微一動,使箭到時分成三點,有三個傷。”但實際上月亮卻毫發無傷。令人遺憾的是,遲暮的英雄已經無力懲罰月亮[8] 了,即使他之前曾經射落過幾個太陽。《采薇》中彼此讓賢的伯夷、叔齊二兄弟因為不食周粟堅守氣節而不得不逃難,他們即使數次幸免于難(比如遭遇文王軍隊、山大王小窮奇的劫掠,甚至是日益惡化的飲食),但最后的終結者卻是來自阿金姑娘的現實一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們在吃的薇,難道不是我們圣上的嗎!”甚至死后還要遭受流言[9] 的中傷——編排他們貪心不足導致被神拋棄從而自我覆滅。
魯迅先生還寫了傳統主動出擊的無能為力。《起死》中的莊子不聽勸告悍然讓司命大神復活了500年前的骷髏,結果復活過來的漢子卻以歷史記憶(身份)質疑莊子的理論,溝通非常不暢,險以老拳相向,只好求助巡警幫忙。魯迅用這個笑劇說明了傳統面對鮮活現實的自以為是與必然挫敗。同樣的道理亦可來自《出關》:孔、老之爭中認輸企圖走流沙出關的老子其實無路可走,他不僅不被時人理解,而且還被關尹喜以優待老作家的名義進行嘲弄與剝削。易言之,傳統資源并不能拯救現代世界。
(二)慣習統攝的現代
作為一個留日7年的學生,更靠近現代性的魯迅有更多對自我、民族及中國的反省,當然這也可能表征了他們一代留日作家的關懷。“‘支那’之痛也促使留日作家開始由自卑轉向自省。這種自省既包含著對國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也包括了對本國國民性的反思。可以說,日本體驗是中國現代國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資源。中國現代留日作家首先將國民性批判矛頭指向了留日學生界。在一系列以日本為生活背景的文學作品里,他們給我們描繪了一道灰色的風景。”[10] 相較而言,魯迅的日本創傷并不太多,除了對“幻燈片事件”的屢次敘述以外,他也在《頭發的故事》中加以剖析,當然提及了日本時期的剪辮經驗,但該文最深刻的地方卻是一個創傷者的諄諄告誡:“你們的嘴里既然并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帖起‘蝮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
更常見的則是傳統痼習對現代性的圍剿,比如《藥》中夏瑜的經歷,因親戚出賣而被關在牢里的他依然努力勸說眾人包括牢頭“造反”,結果不僅被毆打還被盤剝,但更大的傷害則來自被啟蒙者的不理解,乃至以傳統惡習(用人血饅頭治癆病)進行傷害和屠戮。《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則呈現出革命挫敗之后的妥協,他灰心地接受包括傳統(如為尸骨無存的小弟遷墳)的規定,面對不公也只是發發牢騷,便更多認命。《端午節》中的方玄綽和呂緯甫既有相似之處,即處事的差不多原則,但也更惡劣,他甚至借助曾經的現代性(以胡適的《嘗試集》)打壓他的被啟蒙者——太太,這種創傷恰恰反襯出現代被圍剿之后的集體挫敗。當然令人印象深刻乃至最典型的創傷角色則是來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表面上遵守喪葬禮儀,實際上有自己的原則堅守和情感宣泄方式——他以一頭受傷的狼的形象既震撼了世人、時人,又震驚了普通讀者,“大殮便在這驚異和不滿的空氣里面完畢。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連殳卻還坐在草薦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著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這模樣,是老例上所沒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無措了,遲疑了一會,就有幾個人上前去勸止他,愈去愈多,終于擠成一大堆。但他卻只是兀坐著號啕,鐵塔似的動也不動。”如魯迅好友許壽裳所言:“魯迅是大仁,他最能夠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尤其能夠感到暗暗的死者的慘苦。”[11]
當然也有現代性自身造成的內部傷害。《傷逝》中盤旋著一種哀痛之傷,在刨除道德層面的譴責之外,涓生的直面客觀現實的態度恰恰也呈現出現代性面對舊有傳統浪漫套路的殘酷性:他宣布不愛子君之后的自謀出路實踐卻是對以愛為中心的子君的致命傷害,這可能是“新人”形塑的內部創傷。《幸福的家庭》卻又呈現出擬想的表面,物質現代性在強大傳統世界里的脆弱與不堪一擊,其中又可能彰顯了更復雜的內涵。[12]《弟兄》中書寫作為道德示范“兄弟怡怡”的沛君其表面現代的情感結構在精神分析審視下呈現出傳統私心作祟的內在陰暗,“他看見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鐵鑄似的,向荷生的臉上一掌批過去……荷生滿臉是血,哭著進來了。”他在幻想中在靖甫弟弟死后不斷打擊他的小孩以緩解經濟和精神壓力,這恰恰是對未來希望——兒童的傷害,也是對表面現代的情感結構的反諷。
魯迅小說中的創傷話語也有更復雜的面向,比如從自然進化論到人為的反撥:《鴨的喜劇》中愛羅先珂喜歡以自然的音樂充實北京寂寞的環境,而文中的鴨子卻吃掉了成長中的蝌蚪,這呈現出自然界中弱肉強食或食物鏈對人為設定的反諷,而《兔和貓》中喜歡可愛弱者——兔子的“我”卻要以氰化鉀毒殺強者——貓,呈現出另一種企圖以人力反撥自然淘汰法則的心態。
按照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對創痛/創傷的理解,可以將之分為“歷史性創傷”(historical trauma)與“結構性創傷”(structural trauma)。[13] 簡單而言,魯迅小說中的創傷往往是混雜的產物,但如果非要區分的話,小說中所涉及的壓抑個性的長時間累積的中國傳統往往是“結構性創傷”居多,也即:所有的歷史都是創傷,我們共享了同類的有關文化,而魯迅個體所經受/體驗的各類重大的事件則是“歷史性創傷”,我們可以對之加以再現與反芻。一般而言,對和個體息息相關且“就事論事”的“歷史性創傷”關注更多一些,而魯迅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風格則巧妙融合了二者。
二、復仇創傷:記錄或偕亡
應對創傷的策略其實既簡單又復雜。簡單而言,無非要么療傷,要么消極應對;復雜點說,無論積極消極與否,應對創傷的過程既長期糾纏難以根除,同時又可能衍生出更復雜的轉移、宣泄乃至生產功能。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對待創傷亦態度復雜,但印象最深刻的策略之一則是復仇創傷,以下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論述。
(一)反抗遺忘、自奴
如果從更細致的角度劃分,創傷可以分成自然創傷和人為創傷兩大類:前者主要是指自然災害、生老病死或突發事件帶來的創傷,而后者則是由人自身引發的創傷。人為創傷又可以細分為:(1)個體缺陷導致的挫敗、悲劇;(2)統治階層有意制造的災難或懲罰,從簡單的意義上說,其實也就是出于統治需要有意展開的懲罰或規訓機制。
《故鄉》中的閏土從一個神似哪吒的活潑少年最終變成了一個木訥、苦不堪言的老農(“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這恰恰呈現出各種創傷在他臉上的鐫刻:“母親和我都嘆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不難看出,上述創傷性壓制幾乎是全方位的:物質(包括饑餓)、精神方面的欺壓、重稅、倫理道德,環環相扣層層相逼,閏土已經無力應對了。可以理解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應對創傷,“精神勝利法”可謂應運而生,其中的奴性與自我欺騙顯而易見,或者干脆一點,在專制機構以創傷施壓前自奴,從而避免更直接或更豐富的懲戒。
1. 警醒遺忘
在《頭發的故事》中魯迅先生經由N之口縷述辮子的故事,一方面強調要牢記“雙十節”這個保障現代性習慣得以順利運行的民國新紀元,另一方面也論述了創傷記憶的重要性和韌性應對建議。不難看出,這是一種雙線并進的強調,既要反對遺忘,同時又要牢記現代。而《阿Q正傳》則是另一種套路理解下的復雜文本。
嚴格說來,《阿Q正傳》就是一個阿Q不斷受傷害、被侮辱乃至冤死以及如何應對的悲劇故事,雖然表面上它是逗樂的笑劇,但又復雜地呈現出人為創傷對阿Q的圍剿。毫無疑問,其中一方面包含了統治策略:他被剝奪了姓“趙”的權利而只是無名或被草率命名的對象[14],他不僅被忽略了可能的革命訴求還成了新舊勢力沆瀣一氣的替死鬼,不管新舊勢力都深深地傷害了他(包括新式的錯誤審判與畫押),直至送命;另一方面阿Q自身的劣根性也令人絕望,不管是眾所周知的“精神勝利法”,還是欺軟怕硬、偷摸懶散的秉性都相當和諧地與這種創傷懲戒緊密合謀,他既是一個受害者,又是一個傷害者、施暴者(比如對同道和小尼姑),也是一個自奴者,但無論如何,創傷記憶的有意無意喪失是阿Q悲劇的要因之一。
2. 復仇看客
《阿Q正傳》末尾,臨終前的阿Q終于看清了看客們因因相陳、似曾相識的吃人性,“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近不遠的跟他走”,如餓狼一般貪婪冷酷的眼睛,具有極強的吞噬性,而阿Q是無力復仇這些看客了,但他的創造者——魯迅先生可以。
在《野草·復仇》一文中,指向的批判目標就是看客,“路人們從四面奔來,密密層層地,如槐蠶爬上墻壁,如馬蟻要扛鲞頭。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從四面奔來,而且拼命地伸長頸子,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他們已經豫覺著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鮮味。”但二人只是枯干地面對,最終結果是“路人們于是乎無聊;覺得有無聊鉆進他們的毛孔,覺得有無聊從他們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鉆出,爬滿曠野,又鉆進別人的毛孔中。他們于是覺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終至于面面相覷,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覺得干枯到失了生趣”。在我看來,魯迅借此無聊復仇無聊,主要批判了看客們“焦點模糊”“腦殘嗜血”的劣根性。[15]
某種意義上說,遺忘、自奴乃至看客特征其實部分共享了創傷應對的某些劣根品行,這恰恰是魯迅呈現、批判也反抗的對象,如人所論:“魯迅將國人的痛感認知理解為‘人’主體意識覺醒的重要標記。魯迅筆下的人物用遺忘的方式消解現實困境,使他們回避了基于痛感而衍生的反抗行為。面對著國民精神虛空的精神狀態,魯迅冷靜地剖析了這種奴性人物的思維形態,建構了獨特的批判視野,并將之納入其思想改造的價值體系之中。”[16] 此中真是充斥著復雜的因果連環辯證。
(二)攻擊、偕亡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魯迅先生在其作品中往往有極強的攻擊性,也包括相當激烈和繁復的復仇情結,雜文首當其沖,其次是散文(如《女吊》《二十四孝圖》等),而小說中亦不乏此類書寫。簡單而言,這和魯迅先生的創傷感及其超克密切相關。但我們不應該輕視這種攻擊性的復雜性,如夏濟安所論:“眾所周知,他對當前的問題總是采取極端的立場,而且積極擁護進步、科學和文明。但這并不是他個性的全部。如果不把他的好奇,他對自己所憎惡的事物同時又懷著隱秘的渴望和愛戀等等估計在內,也不能代表他的天才。若是只把魯迅看作一個吹響黎明號角的天使,那就低估了這位中國近現代史上尤其深刻而又病態的重要人物。他確實吹響過號角,但他吹出的樂聲陰沉而譏諷,希望中透著絕望,是天堂的仙樂交織著地獄的悲鳴。”[17] 其中既有天才,又有病態,頗令人感慨。
《鑄劍》即使不結合“宴之敖者”的衍生解讀——給屋里日本女人趕出來(兄弟失和)的創傷性事件指向,也可以判斷它也是創傷性寫作。優柔寡斷、淘氣好玩的眉間尺走向成熟的精神催化劑就是其亡父的冤仇未報的真相震驚,但初經人事的他也遭遇到俗世的困擾與糾纏,復仇之神黑色人幫他解圍并告知他如何復仇,于是他奉上了寶貝青劍與自己的頭顱。實際上黑色人也是傷痕累累的存在,他本身也是創傷的集大成者和需要療治的人:“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但我要報仇,卻并不為此。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靈上是有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最終結果(不得不)變成了創傷的狂歡:黑色人在發現眉間尺頭顱無法戰勝王時便主動自刎加入戰場,“他的頭一入水,即刻直奔王頭,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幾乎要咬下來。王忍不住叫一聲‘阿唷’,將嘴一張,眉間尺的頭就乘機掙脫了,一轉臉倒將王的下巴下死勁咬住。他們不但都不放,還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頭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們就如餓雞啄米一般,一頓亂咬,咬得王頭眼歪鼻塌,滿臉鱗傷。”這個有點狂歡[18] 色彩的結局呈現出復仇者、復仇之神與大仇人同歸于盡的悲涼,但同時有關創傷的悲情、憤怒與壓抑卻也隨之擴散了。
某種意義上說,同歸于盡是一種非常決絕而悲壯的復仇方式,也是瓦解創傷的激烈對策,這和主張韌性戰斗的魯迅氣質有契合之處,畢竟魯迅先生同時也強調血性和飛揚神采,他曾經激情四射地寫道:“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華蓋集〉題記》)他也大聲疾呼:“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五)》)但除此以外,魯迅也通過批判個體、群體、國民劣根性來平復或升華創傷體驗,這既是一種自我療治,又是一種新的現代性建構,如人所論:“文明痼疾的補償性反應這一思路和結論,無論是適用于個體的魯迅還是我們整體的社會文化,都至為到位與有效。創傷、病態破壞和改變了魯迅的常態人生,但補償機制卻使他獨辟蹊徑建構和完善了自我。”[19]
三、療治的悖論
有論者指出:“創傷敘事是人在遭遇現實困厄和精神磨難后的真誠的心靈告白。也只有通過真誠的心靈告白,心靈的創傷才能得到醫治。從這個意義說,創傷敘事是對創傷的撫慰和治療。”[20] 從此角度看,魯迅作品中的創傷話語也是對自己創傷記憶的一種療治,但由于魯迅先生的復雜性和深刻性,在其療治中亦有悖論。
(一)直視與自虐
對魯迅一生影響甚巨的母親魯瑞(1858—1943)其實相當清楚魯迅的某些人格特征,正所謂“知子莫若母”,俞芳在《魯迅先生的母親回憶魯迅先生》中說:“太師母說:你們的大先生從小就很懂事,辦事能干。先是爺爺介孚公下獄,接著太先生臥病三年,醫治無效,吐狂血而逝世,從此沉重的家庭擔子就落在他的肩上。在那艱難的歲月里,他最能體諒我的難處;特別是進當鋪當東西,要遭受到多少勢利人的歧視,甚至奚落;可他為了減少我的憂愁和痛苦,從來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惱和遭遇。而且,對于這些有損自尊心的苦差事,他從來沒有推托過,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辦好,將典當來的錢如數交給我,不吐半句怨言。”[21] 而實際上,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魯迅也寫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夫子自道。
一方面,魯迅先生是勇于直視自我的創傷的,在其作品中屢屢有所呈現。《過客》中的過客在對話中提及:“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夠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哪里呢?”過客的疲乏和受傷顯而易見,而當小姑娘讓他用一塊布裹傷時,他先接后拒(received而非accepted),因為背后的愛讓人沉重不堪。過客身上當然承載了魯迅的形象,但走向安逸乃至沒落的老者亦然。[22]
《復仇(其二)》當然可以有多種解讀角度,如復仇大眾、現實關懷(尤其是關涉兄弟失和)、血肉宗教[23] 等等,但相當耐人尋味的則是作品中屢屢提及他沒有喝止痛的調料酒,而是悉心清醒體驗釘殺的痛楚,“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著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歡喜和大悲憫中。”這種切膚之痛直至死亡讓他刻骨銘心,一方面可以直視殘酷的罪惡的現實,另一方面則讓他體驗到拯救俗世的艱難,又是一種清醒自虐。
《頹敗線的顫動》中的老婦人面對來自親人的綿密而且巨大的遞進式傷害,向我們呈現出一種直視、憤怒且反抗的姿態,“她開開板門,邁步在深夜中走出,遺棄了背后一切的冷罵和毒笑……她于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甚至這種氣勢波動天地,也是一種應對創傷的不滿與宣泄過程。或許令人震撼的則是《墓碣文》,“抉心自食”,創痛劇烈,這是直視自我/探索自我和慘烈自虐的完美結合:墓碑和“我”是一種復雜的分裂和整合關系,而整個文本又是“我”的自剖記錄,魯迅甚至還借用了“詐尸”的策略與手法,讓“復活”的主體繼續自我表述,呈現出它的樂觀性和預見性,在毀滅中呈現出同歸于盡的歡喜,乃至狂歡。[24]
(二)自塑與利他
論者指出,魯迅的創傷體驗其實有助于他個性的形塑,“這種創傷性體驗(缺失性體驗)也促進了魯迅獨特個性與思維方式的形成。如果說魯迅早年所接受的浙東學術與‘師爺氣’的熏陶為他的獨特個性與思維方式奠定了一個基本的初型,那么這次‘家庭變故’的巨大的物質與精神的創傷,則是一種契機,加速了這一獨特個性與思維方式的形成。”[25] 這的確是合理的推斷,但可以推展的是,這種自塑有其復雜性:一方面,其中不乏對自我的深切解剖和正視(如前所述);另一方面,其中又有對優秀品質乃至民族脊梁的贊許與弘揚。
《一件小事》恰恰呈現出解剖和弘揚的雙重指向。事發現場是一個被車夫別倒的老女人,“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發,衣服都很破爛。伊從馬路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沒有上扣,微風吹著,向外展開,所以終于兜著車把。幸而車夫早有點停步,否則伊定要栽一個大斤斗,跌到頭破血出了。”“我”的判斷是,“料定這老女人并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但車夫毫不理會。某種意義上說,這里弘揚的是車夫的“慎獨”和勇于擔當精神,相較而言,“我”的自私顯得渺小,但不應忽略的是,這種自省本身也是一種自我提升,“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結合本文論述的創傷話語角度,車夫樹立了一個典范:如何處理哪怕是不那么明顯或嚴重的創傷?
《長明燈》中的男主人公瘋子被關在社廟中,作者寫道:“他也還如平常一樣,黃的方臉和藍布破大衫,只在濃眉底下的大而且長的眼睛中,略帶些異樣的光閃,看人就許多工夫不眨眼,并且總含著悲憤疑懼的神情。”而在和其他村民對話時,“他兩眼更發出閃閃的光來”,并堅稱“我放火”,升華了“熄掉他”的理念/口號,雖然他最終無法實踐理念,但他這種歷盡艱辛依然癡心不改的反抗精神無疑令人欽佩。
除此以外,魯迅先生還有面對創傷勇于反抗的篇章,如《淡淡的血痕中》,魯迅以叛逆的勇士對抗顓頊、狡猾的造物主[26],“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其中既包含了對奴役的破解,同時又亮出反抗與建構的旗幟寄望于改造國民劣根性的人類自強——新國民或新世界得以產生。[27]
魯迅先生在臨終前不久撰寫的《這也是生活》中有一句名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呈現出先生的格局、視野、現實關切以及精神追求。而從創傷話語視角關注亦然,也正是有這樣的超越性高度、鮮活性體驗,他的文學生產才會如此與眾不同、匠心獨具,如人所論:“盡管他還要承受‘生之創傷’的不斷置換和重現,但是隨著以文藝為核心的各種精神資源的不斷累積,他個人的人生體驗終于和民族的、社會的體驗契合、凝聚在一起,他不但治療和修復自己的創傷體驗,而且將自己內在的情緒和思想轉化為文藝的高度意義結構,以大無畏的姿態去治療民族和社會的心理痼疾和精神創痛。”[28]
結 語
魯迅少年喪父,生活從小康墮入困頓,赴日留學“走異路”中亦頗多艱辛,而后還有兄弟失和打擊、與人筆戰等,魯迅一生經歷的創傷體驗并不少,在其文學生產中,創傷話語屢屢可見。他在對創傷的小說再現中,呈現出創傷的挫敗性慣習,一方面指向了傳統致人挫敗的殺傷力,另一方面則說明現代轉換中亦有類似慣習。魯迅亦有復仇創傷的書寫實踐,一方面他強調反抗遺忘和自奴,同時亦有攻擊性乃至同歸于盡的復仇理念。而在其作品中,亦有療治創傷的書寫,其中也是悖論重重,比如直視和自虐并存,自塑中的自剖、利他互補等等。
作為敏感銳利、胸懷天下的文學巨匠,魯迅先生的許多書寫都是從己(及周邊)出發,但又絕不自戀式陷入一己的悲歡,而往往具有宏闊的視野、熱切的關懷以及深刻的挖掘。其創傷書寫也不是單純的情感宣泄或調侃報復,而是建基于“個”之上進行更深入多元的文化隱喻建構:一方面指向了造成各類創傷的文化土壤、機制及其代言人的形形色色表現,其雜文書寫尤其值得關注和仔細探勘;[29] 而另一方面也找尋一種療治創傷的文學、文化以及精神結構改造可能,《朝花夕拾》中也不乏精彩嘗試。易言之,魯迅的創傷書寫既是個體的,又是集體的;既是情感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批判的,又是建構的,充滿了繁復的自覺與辯證。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注釋:
[1] [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16頁。
[2] 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61頁。
[3] 耿德華(Edward M. Gunn):《斷裂的強迫重復:論創傷的表述策略》,《文藝研究》,2013年,第10期。
[4] 有關話語的界定和使用可參拙著,朱崇科:《魯迅小說中的話語形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5] 同[1],第217頁。
[6]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論魯迅小說中的賤民話語》,《中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1期。
[7]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魯迅小說中吃的話語形構》,《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8] 這里的月亮當然也是月精,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論魯迅小說中月的話語形構》,《新世紀學刊》(新加坡)總第9期,2009年,12月,后收入朱崇科:《魯迅小說中的話語形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9]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女阿Q或錯版異形?——魯迅筆下阿金形象新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10] 蘇明:《“支那”之痛:現代留日作家的創傷性記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1期。
[11] 許壽裳:《魯迅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頁。
[12] 朱崇科、陳沁:《“反激”的對流:〈幸福的家庭〉、〈理想的伴侶〉比較論》,《中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2期。
[13] 具體可參Dominick La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Baltimore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14] 在我看來,命名洋名阿Q有著魯迅先生獨特的追求,包括是無處可逃的備選,指涉的含混等。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魯迅小說人物命名中的解/構辯證》,《玉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
[15]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3頁。
[16] 吳翔宇:《“痛感”認知的開掘與審思——魯迅小說的創傷美學分析》,《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17] [美] 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萬芷君等合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頁。
[18] 更多論述可參拙著,朱崇科:《張力的狂歡——論魯迅及其來者之故事新編小說中的主體介入》,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19] 賈振勇:《魯迅:創傷·病態·吹響黎明號角的天使》,《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第42頁。
[20] 季廣茂:《精神創傷及其敘事》,《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第65頁。
[21] 俞芳:《魯迅先生的母親談魯迅先生》,《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4期,第190-191頁。
[22]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執著與曖昧:〈過客〉重讀》,《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7期。
[23]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現在式復仇的狂歡:重讀〈復仇(其二)〉》,《創新》,2016年,第2期。
[24]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互看的奇特與靈思:〈墓碣文〉重讀》,《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期。
[25] 王曉初:《家庭變故:魯迅的創傷性體驗與求索精神》,《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第7頁。
[26] 具體可參拙文,朱崇科:《魯迅作品中的“造物主”身份及悖論》,《文藝爭鳴》,2014年,第5期。
[27] 同[15],第313頁。
[28] 賈振勇:《掮住黑暗的閘門:創傷體驗與魯迅的自我救贖》,《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2期,第31頁。
[29] 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1924—192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