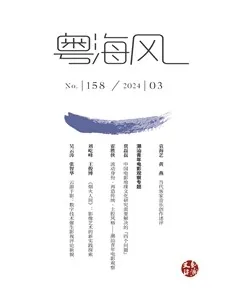“樂音”與“噪音”之辨
摘要:從“在場”到“在網”,社交媒介下的網絡文藝出現了斷裂性、生成性等聽覺范疇的“事件”之變。便捷的聲音媒介建構了新型的場景美學,網絡文藝通過“聲音”增殖了情感維度的藝術體驗,音頻社交軟件突出了網絡文藝的走心互動與情緒感染的社交核心。同時,“聲音”的考察也是“聽覺文化”的題中之義。在韓炳哲的“非物”視域下,商業巨鱷開辟的耳朵經濟與“信息資本主義”能否畫上等號?社交媒介的“聲音”是令人安寧的“樂音”,還是淹沒大眾的信息“噪音”?對此,我們需要保持一種清醒的認識:“聲音拜物教”很可能讓聽眾心甘情愿地陷入“聽而不見”的吊詭中。
關鍵詞:網絡文藝 聽覺文化 非物
近年來,網絡文藝成為當下最重要的文化景觀之一,引發了傳播學、文學、新聞學等領域研究者的熱烈討論。學界的關注點,多集中于媒介文化研究與類型敘事學分析。前者主要立足外來媒介理論資源,探究新媒介與網絡文藝之間的互動關系;后者則著力論述網絡小說的綜合性類型特征,及其對傳統敘事資源的承繼與創新。網絡文藝的興起、傳播與興盛,互聯網平臺功不可沒,可是,互聯網作為視聽兼備的社交媒介,學界似乎更習慣在網絡文學網站等視覺平臺上做文章,即使是視聽兼備的聲像應用,也側重于視覺文化分析,比較而言,以“聽覺文化”為切入點的網絡文藝探究仍是少數。因而新媒介文化視域下的網絡文藝研究進展得如火如荼,但其“失聰”的癥狀,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一、從“在場”到“在網”:
作為聽覺“事件”的網絡文藝
1877年,愛迪生留聲公司推出錫箔紙圓筒留聲機以來,“聲音產品”歷經一百多年的迅速發展,容貌大變。無論是20世紀的盤式、盒式錄音帶,還是新世紀以來,數字技術與激光高密度技術結合下誕生的激光唱片——即CD,或十多年前風頭正盛的數字播放器ipod、mp3,這些隨“時”而變的聲音載體,以今視之,已屬單向度傳播的“舊”媒介范疇。直到互聯網技術出現,智能手機興起,音頻應用流行,“聽書”這一活動才在互聯網時代煥發新春。
把時間拉回前朝,“聲音產品”雖然是晚近的概念,但“聲音”卻是許多前輩藝人養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中國有相聲、評書等靠“說”的藝術,也不乏京韻大鼓、單弦牌子曲、揚州清曲等“唱”的藝術。當然,中國傳統曲藝中,“說”與“唱”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曲藝品種說唱結合,有些似說似唱,有的還加上樂器伴奏。總之,這些藝人靠著獨特的技能,在特定的場合為觀眾(聽眾)獻上一場極具藝術性的演出,其中“聲音”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甚至可以說是最主要的表演要素。專門的表演人員,以茶樓、酒樓、戲院等固定地點為表演場所,與觀眾面對面交流,演出具有此時此地性、場地化等即時特征,按照中國“聽書”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可稱為“在場聽書”。所謂“聽書”,此“書”非單指書籍,廣義上:“凡是包含有價值的知識、信息的形態、介質、載體都可以稱為‘書’,或者說‘書’指代所有有價值的知識和信息”[1]。今人的“有聲閱讀”,以及聽音樂、聽新聞、聽廣播劇等活動,與前人的“聽書”,在價值內容與娛樂意義上,并無大異。不同的是,“在場”變為了“在網”,精密的機械振動取代藝人的肉嗓子,數字化的精確儲存與輸送代替了常演常新的節目。如此觀之,互聯網時代的藝術確實拋棄了本雅明所說的“靈韻”。[2]
“在網”的聲音,也帶來了其他的可能。相比較“在場”的演出,網絡音頻應用播放的“聲音”,早就超越了時空的限制,只需要手指輕點播放按鈕,現代人便能輕易享受一場高保真的聽覺盛宴。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的同事洛根,在《理解媒介——延伸麥克盧漢》一書中論證有聲書之便捷時,引用了丹佛大學弗蘭克·丹斯的一段話:“上個星期,我的妻子和我開車從丹佛到伊利諾伊州的伊文斯頓來回旅行。在旅途中,我們幾乎自始至終聽吉姆·戴爾朗讀的《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我們盡情享受這本朗讀的書,我們一道大笑,毛骨悚然,議論情節之復雜,陶醉于他五彩繽紛的聲音。”[3] 那時正是ipod、mp3等數字播放器盛行之時,由于有聲書“閱讀”便捷,洛根一度建議出版商將其作為文本出版的另一形式。mp3有別于廣播電臺的“我播你聽”單向度傳播模式,用戶可以根據自身的喜好,在移動的聲音載體上,相對自由地下載、上傳與選擇播放。雖然機械復制時代的廣播電臺、數字傳輸的mp3、ipod不具備“在網”的新媒體的種種新特征,如雙向傳播、組合與整合、互操作性、社群區分等,但“在網”之于“在場”的部分媒介優勢至此已經顯露。
“社交型”媒體平臺(如微信、推特、微博)深入人心之時,以有聲閱讀應用為代表的音頻軟件在近十年間異軍突起,它們以“聽覺文化”復歸的姿態睥睨時代,至今聲勢已頗為浩大。有聲閱讀應用依靠便利的移動端,收復了廣播電臺失守的領土。以喜馬拉雅FM、蜻蜓FM、懶人聽書為首的音頻軟件,憑借著場景伴隨、情感陪伴、雙向互動等新媒介優勢,在新時代閱讀陣地戰中跑馬圈地,獲得了令人矚目的市場份額與用戶。2011年,中國首家網絡音頻應用“蜻蜓FM”誕生,蜻蜓FM以“更多的世界,用聽的”為口號,上承廣播電臺時代,下領中國移動音頻潮流。隨后,懶人聽書(2012)、喜馬拉雅FM(2013)、荔枝FM(2013)、企鵝FM(2015)等網絡音頻應用如雨后春筍相繼出現。這些音頻軟件的播放內容覆蓋文化、科技、曲藝、有聲書等多種類型。近年來,音頻市場規模一路向好,據《傳媒藍皮書:中國音頻傳媒發展研究報告(2022)》統計,就用戶規模而言,目前喜馬拉雅FM穩居第一位,總用戶數超過4.8億,月活用戶2.5億,“2021年,全國主要音頻門類中,移動音樂、移動聽書與廣播電臺用戶規模位居前三,分別為7.29億、6.37億與5.30億。”[4] 音頻軟件的崛起以及用戶規模、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意味著已經出現了一種以“聲音”為主的娛樂范式,不可否認,“在網”聽音樂、聽相聲、聽書以及以“聲”為賣點的音頻軟件為用戶帶來新的“聽覺”維度的文藝體驗。
“在網聽書”之于“在場聽書”,不僅“書”的形式大變,而且“聽”的方式也日新月異,如何摸排與厘清這種變化帶來的文藝沖擊,是網絡文藝研究急需落定的一子。進入互聯網時代,上述有聲閱讀的特點更加矚目,同時,新媒體與聽覺文化攜手共進,“讀圖時代”“視覺中心”的統治霸權,正受到以新媒體為載體的聽覺文化的“挑戰”。基于此,聽覺與視覺之“辨”正在進行時,國內外學界“出現一種從聽覺、聲音入手來思考社會、歷史、文化、科技等方面問題的研究取向。它考察人們生活在怎樣的歷史和現實的聲音環境里,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去聽,體現了怎樣的社會關系”[5]。考察“聽覺文化”的轉向并非本文力所能及。本文的旨歸是探究社交媒體中,與“聽覺(聲音)”有關的網絡文藝具備了哪些視覺文化之外的審美特質?在社交媒體中,我們到底“聽”到了什么“新”東西?
學者胡疆鋒立足于新時代的網絡文藝之“變”,借助“事件”理論,把握網絡文藝的斷裂性、生成性等事件性,認為“事件視閾中,文藝批評的重點不再是網絡文藝是什么,而是網絡文藝能讓什么發生,批評對象有何變化或出現了何種悖論,重點思考‘誰是作者/讀者’‘作品變成了什么’‘誰在批評’等問題,這種研究推動了新媒介藝術批評的轉型”[6]。借用胡疆鋒的學術理念可以這樣提問:網絡文藝攜帶的“聽覺”特質,如何以“事件”進行追蹤與捕捉?
二、社交媒體與網絡文藝的聽覺轉向
今日之“聲”與前技術時代之“聲”的重要區別不在迥別,而在微殊。以“聲音技術發明與電子媒介的繁榮”[7] 為物質基礎的聽覺(聲音),在新一輪媒介“復活”中以“原創性的復活體”的面目出現不足為奇,可其“嶄新的性質”[8] 作為過去的聽覺與當代社交媒體雜交的產物,卻不容小覷。在網上聽書、聽新聞、聽音樂、聽節目成為當代獨特的一種網絡文藝活動;語音聊天、游戲派對、聲音匹配也是社交媒介中不容忽視的交際形式,事實證明,堅實的物質基礎讓聽覺(聲音)蛻變為了更加純粹且獨立的審美媒介,作為聽覺“事件”的網絡文藝獲得了“聲音”維度的獨特生命力。當代“聽覺文化”的崛起及復歸,不僅更新了“聽覺”的音容笑貌,并且以社交媒介為平臺的網絡文藝也增添了新時代的音軌,為用戶帶來了如下“嶄新的性質”。
(一)“聲”臨其境:網絡文藝建構新型美學場景
在《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中,斯考伯和伊斯雷爾認為“場景”是涵蓋了基于空間和基于行為與心理的環境氛圍,并與實時感知、實時搜索、實時處理等互聯網系統相聯系。[9] 梅洛維茨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指責戈夫曼等人過于近視,只把場景視為在某時某地發生的面對面交往,而沒有看到場景的含義已經擴展為“可以接觸社會信息的某種模式”,物質場所與媒介場所“同為人們構筑了交往模式和信息傳播模式”。[10] 盡管二者研究旨歸不同,但都承認了“場景”與互聯網及電子信息的聯姻關系。如今,用戶借助聽覺媒介將信息引入耳道,無論是打電話交流、還是聽歌娛樂,用戶在“場景”中的“耳濡目染”已具備了新型美學品質。
“場景”美學的形成離不開耳朵與眼睛相互配合,電子信息從耳入腦,眼睛捕獲實時景色,二者獨立又互補,聲音信息與視覺影像合謀,共同建構了用戶的“場景”體驗。如丹佛大學弗蘭克·丹斯在車上聽《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產生的“大笑”“毛骨悚然”等氛圍,固然有小說內容與聲音相得益彰的審美效果,但也不能忽視其妻子在旁,窗外景色的外界感知輔助。除了打發無聊,更多用戶善于利用耳機的貼耳性創建新型的“在場”,并通過目光所及,創造無限的空間體驗。通勤路上戴上兼具降噪和虛擬連接功能的耳機,外界的嘈雜、內心的郁悶就可以不同程度地被音樂之聲蕩滌。因此,網易云音樂、QQ音樂、酷狗等各大音樂平臺上并不缺為用戶提供“通勤路上的動力補給”的各類通勤歌單。網易云音樂上“通勤路上的行動旋律”歌單被10萬多人收藏。上班與下班之路,前者急需提振精神,后者迫切需要消散疲態,“放空大腦,單純地享受音樂和路上的景色”或者“一邊聽歌一邊看風景一邊想心事”[11],都不失為通勤途中的“場景”帶來的美學體驗。駕輕就熟者,甚至挑選出“快速通過河上的橋時的場景”的專屬歌曲,至于城市霓虹燈下該聽什么,同樣需要用戶的主觀擇取。營造一個私人空間,加注自己的想象與情緒,構建屬于自己視角的美學“事件”,成為網絡文藝特有的聽覺浪漫。
英國蘇塞克斯大學教授邁克爾·布爾將此類聽覺與視覺同構的場景狀態稱為“街道美學”。根據“場景”的不同,或許還有“操場美學”“家庭美學”“商場美學”,等等。相關分析報告顯示,我國網絡音頻應用的使用場景一般為:通勤場景、居家場景、夜間場景、工作學習、運動、親子,其中高達80%的用戶在開車、坐地鐵、坐公交車、騎車等通勤場景收聽音頻。[12] 作為接受者,聽眾身體出席,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感官聯用,同步進行,一同入景,享受由聽覺主導、視覺配合、情感聯動,多感官募集而來的“擬態”之境。聽音樂、有聲書、相聲評書、新聞、歷史故事的文藝活動,取消了傳統式“在場聽書”的聲景一致,新型美學場景建構下,聽覺尋找視覺、景象配合聲音,美學性召喚將“他者”帶入用戶自己的幻想世界,布爾將ipod呈現的這種美學效應稱之為“視聽綜合擬態”。
聽覺向度的文藝活動與傳統的文藝現象,以及重視視覺基礎的網絡文藝批評,在文藝形態、接受場景、感官調用等方面都發生不小的錯位。“聲音”可以縫補碎片化時間,便捷地為用戶帶來新的文藝體驗,同時,耳機里的聲音可以充當現實世界的背景音,激發用戶的審美感知。用戶將文藝活動帶入日常生活中,在視、聽的完美配合下,一場由內(內容想象、情緒感發)及外(窗外的景象、消失的他者)的美學場景建構而成。
(二)“聲”入人心:網絡文藝的情感維度
不僅與“視覺”合作可以顯奇能,“聲音”也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在視覺關閉、聽覺依然靈敏的睡前,許多人通過“聽”使自己更好地入睡,充分發揮了“聲音”特有的伴隨性功用。
以音頻行業的領頭羊喜馬拉雅FM為例。由郭德綱授權的專輯《郭德綱21年相聲精選》,截至2023年10月17日已經累計播放32.6億次,有865.4萬的訂閱量。其中一條優質評論為“我賭我是評論區中年齡最小的,今年15還是個女孩,特別喜歡郭老師,每天都得聽著相聲睡覺,特別好”[13]。該專輯評論區有一互動問題為“你喜歡在什么時候聽相聲”,80%的人投給了“睡覺前”的選項,其余分別為“休閑放松”(10%)、“通勤路上”(6%)、“干飯時”(4%)。出于睡眠的特點需求,有博主甚至專門整理出了相聲的“無唱助眠版”。有聽友寫道:“聽相聲入睡聽到后面你聽的就不是包袱的內容了,而是兩個人對話的聲音。郭德綱于謙的相聲,音色是厚重的,語速也是不急不緩的,節奏也平穩。聽的時候會非常放松,而且也是因為這種表演自然得像聊天,會給我一種安全感。放松加安全感,入睡肯定快。”[14] 相聲、評書等傳統敘事藝術的講述節奏、藝人的聲色、說話的氣口等都有助于聽者進入某種舒緩狀態。顯而易見,社交媒介悄然改變了口頭敘事藝術的“在場”價值,“在網”的曲藝正淡化為純聲音符號,其敘事內容、審美價值、藝術形式被抽空。因此,與其說人們期待傳統曲藝在網絡中上演一場高保真的文化展示,不如說人們對這類藝術作品的閱讀期待,很大程度上已經由娛樂欣賞轉向了“聲”入人心的情感陪伴。
相比“敘事”的催眠,睡眠應用意在通過專業愈療催眠曲、天然白噪音、腦電波等聲音,阻擋外界噪音的同時,喚起人類某種原始的安穩感。在小睡眠 App中,用戶可以任意組合多種白噪音為自己助眠,如夜闌聽雨、雨打芭蕉、風吹竹林等自然天籟,也有物理課、英語課等人文聲音。“當我們在選擇音效的時候,就可以同時選擇‘三個音頻’,比如我選擇了‘雨打芭蕉’‘嬰兒酣眠’和‘搖籃小曲’,這樣再配合上3D的環繞音效,仿佛我就是那個在雨夜中被媽媽哄睡的嬰兒一般。”[15] 這恰如其口號“給你一個嬰兒般好睡眠”。白噪音這種單調的、可預測的、無意義的聲波,如上述的自然之聲,可以持續單調地刺激聽者,誘發其睡意,因而一些博主直播助眠內容,創造穩定的觸發音(asmr),如低語、剪頭發、流水、火柴燃燒、傾倒碳酸飲料、掏耳朵等,此類觸發音能夠獲得不少的關注,也就不稀奇了。當然,這些聲音也可以伴隨用戶學習、工作。人聲、歌聲、流水聲、雨聲、風聲,雷聲,聲聲都可以入耳,它們可以為欲眠或行為中的用戶營造一種“存在的穩定性”式的情感安撫,同時,新媒介下的主體具身性得以強化,并為主體接受提供了新向度的感受體驗。
(三)同“聲”相應:網絡文藝的交往性功能
社交媒介通過即時互動、群體交流等技術優勢,以看電影、看劇、看視頻時的實時彈幕為表征,產生了區別于傳統靜觀式審美的“社交型”文藝場景。論者黎楊全提出的這種新型社交場景具有“交流性”“集體情緒體驗”“社交性”等特點,從而為文藝批評新增“交往性”的評價維度。[16] 現在,媒介的交往互動屬性已經成為文藝活動中的重要綱領,Soul、小回音等音頻社交軟件正在放大文藝活動的“交流性、集體情緒體驗”等社交功能。
與往日服務于游戲聊天的“頻道與房間模式”不同,今天的“語音匹配,靈魂社交”雖延其內核,但后來者居上,“聲音社交”已成為新一代社交媒介的基礎功能。以社交軟件Soul(2016年上線)為例,Soul App主頁面不僅專設了“語音匹配”板塊,還有“群聊派對”“Soul游樂園”等以“聲音”為主要吸睛點的社群交際欄目。在語音匹配中,軟件通過算法為用戶匹配聊天對象,聊天限時3分鐘,志同道合者,可以互相關注,從而暢聊無礙;若是話不投機,那么任意一方可以隨時掛斷,另覓佳音。在“群聊派對”“Soul游樂園”板塊,有閑聊嘮嗑、興趣交流、唱歌聽歌、趣味辯論、心動速配的派對類型,也有異世界的回響、狼人殺等依托聲音交流的線上游戲。目前Soul的月活躍用戶已經超過3000萬,其中“95后”用戶為主力軍。[17] 與其打壓“Z世代”興趣喜好,或正氣凜然地斥其為異端,不如大膽承認“新媒介語境下文藝消費與傳統的不同,在于消費的并不只是作品本身,還在于作品外的交往互動”[18]。小回音、赫茲、樹洞、聲昔等軟件,其提供的消費內容并非只限于審美性價值,更多的是將“社交”作為自家主打賣點。如Soul的閑聊嘮嗑、唱歌聽歌,小回音“聞聲識人”的交友邏輯,音樂、朗誦、故事等文藝形式固然重要,但“以聲交友”無疑是對“社交媒體”的另一注釋。
在視頻、小說等文藝作品中,以彈幕、本章說、間貼為表征的互動性屬性,確實形成了穩定、有效的“互動儀式”,同樣,“同聲相應”過程中“聲音”所營造的“現場”氛圍與關注焦點也是文藝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個人的聲音不斷變化,或高揚、或低吟、或激蕩、或慢拖等變化”,連接他人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由此麥克盧漢才將聲音認定為“可使人感受到親切的媒介”。[19] 走心互動與情緒共鳴恰恰是“Z世代”追求的文藝內核。音頻社交正在為大眾提供類似口頭文學傳統的文藝形式,講述能力、話題選擇、氛圍營造、情緒表達成為社交媒介“交往性”的主要構成要素。Soul曾經的口號為“建立真實連接,擁抱社交真諦”[20],連接是否“真實”?何為社交“真諦”?固然需要進一步考察,但是作為聽覺“事件”的網絡文藝正在構建一種以聲音連接他人的“社交型”文藝場景,從網頁聊天室、語音聊天軟件、1對1電話語音,發展到如今的在線k歌、音頻社交、音頻播客……激變的文藝形式正在呼喚“聲音社交”維度的文藝批評。
三、“樂音”與“噪音”之辨
現代媒介之新“聲音”,不再是前技術時代飄轉即逝的一次性用品,飛入尋常百姓家后,“聲音”的生產加工、儲存傳輸、接受解碼、消費對象等工業環節,已超出人體生理與機械物理的范疇,進入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學科的批評領地。需要警惕的是傾聽所得的“聲音”——是可慰孤獨、令人安寧的“樂音”,還是屬于“非物”世界中交流過剩的“噪音”?這恰是聽覺文化所關心的范疇:“‘造音’(聲音由誰,以何種媒體,在何種場合或環境中,出于何種目的被制造出來)和‘聽音’(聲音由誰,通過何種媒體,在何種場合或環境中,出于何種目的被動或主動地‘聆聽’的)。”[21]
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非物》中指出,“噪音”并非單指聽覺層面的“聲音”,更是“無休止的、外延的、過剩的交流的產物”[22],海嘯式的信息帶來的是對視聽感官以及注意力的污染。微信的聊天消息、語音電話可以隨時入侵手上的方寸之地;抖音、快手等只要輕點軟件圖標,聲像立馬可以乘流量而來;小紅書、嗶哩嗶哩、新浪微博永遠沒有止境的推送總讓人流連忘返……大眾更愿意用對信息的獲得、占有、體驗取代與現實大地秩序的穩固聯系。韓炳哲引用他人之語道出了“非物”世界的信息霸權:“在當下,非物全方位地涌入我們的周遭世界,它們正驅除著物。人們稱這些非物為信息。”[23] 今日“聲音”媒介恰逢其時,背后是萊文森樂觀的媒介進化論使然,還是意味著“非物”正在進一步開墾聽覺荒地?面對時代的風暴,若只做出張耳傾聽的姿態,而不審視“聲音”背后的價值立場與意識形態,未免對聽覺(聲音)的復活過于樂觀。[24]
首先,“聲音分裂”營造“街道美學”、戴上耳機搭建私人空間——這是否也意味著人們對信息、數據以聲波形式侵擾注意力這一行為的縱容?網易云音樂宣稱“音樂的力量”、喜馬拉雅FM喊出“每一天的精神食糧”口號,無論是網易云音樂打造的“云村”社區,還是“讓聲音和知識像水和電一樣無處不在,隨取隨用”[25] 的豪言壯語,用聲音連接世界固然是社交型媒介賦予網絡文藝的新鮮一面,借此,數字聽覺人可以抵抗被異化為‘交流的無奈’的現實圖景,實現“美好的棲居”[26],但另一方面,耳朵在清晨、早晚通勤、午后和睡前等多個視覺“盲區”的時間段中被溫柔地征用,2020年移動端活躍用戶的日均收聽時長達到141分鐘[27],以韓氏視角觀之,或許可以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傾聽世界、關注自我卻是以犧牲物世界的“安寧”為代價的。
24小時全天候營業的耳朵在“補償視覺”的大旗下,正淪陷為資本與商業新開發的信息試驗地。疫情期間,擁有2億多用戶的游戲語音平臺Discord將經營重心從“為游戲玩家聊天”轉移到“為社區和朋友聊天”。[28] 2020年上線,主打即時性的音頻社交軟件Clubhouse,在扎克伯格與馬斯克形成的名人效應下,語音聊天室功能迅速招募到了大量粉絲。國內音頻軟件喜馬拉雅FM在2020年一季度內營收增長32%,蜻蜓FM在疫情期間推出旅游音頻節目與疫情防控音頻討論,有聲圖書館、朗讀亭、城市有聲故事等線下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項目陸續上馬。[29] 不難看出,資本對耳朵的重視說明網絡的“視覺內容”已經相對飽和,而“填充耳朵”正在被眾商業大鱷視為文藝領域的新蛋糕。“非物”世界的信息與數據被歸化為資本與商業的輕騎兵,正在對新發現的沃土發動蠶食計劃。在資本的宣傳下,用聲音“連接”世界似乎是年輕人的潮流選擇,可是藏匿于口號背后的狼子野心并非路人皆知。用戶在社交媒介上形成的“連接”是否真實,何為社交“真諦”,更多是取決于“充滿商業動機和強制性的連接邏輯”,[30] 而非大眾信以為真的“同聲相應”。音樂頻道、播客直播、語音聊天房間、白噪音房間等社交空間的建立是為了彌補現實人生的種種缺憾,還是為了將“聲音”納入資本的“景觀化”王國,從而為信息與數據的攻城略地,開辟“耳朵經濟”的新戰場?
再有,網絡文藝的劣質作品泛濫——信息不僅過剩,且在人工智能與固定套路的合謀下,同質化內容可以迅速生成、上傳與傳播。以解說短視頻為例,質量高的視頻解說不僅要有貼切精彩的解說文案,還需搭配跌宕起伏的敘述聲音。如電影類解說視頻,用戶往往注重解說者加入的短小精悍的“要言妙道”或“戲謔調侃”,至于原影片的故事時長、視覺要素、敘事結構、拍攝手法等原始構素倒變成其次要目的。由此網友不禁感慨道:“大家的追劇方式都變了,以前是守著騰訊/優酷/愛奇藝,現在是抖音/B站(嗶哩嗶哩)隨緣追。”[31] 其實解說視頻的制作并不復雜,創作的思路無非是聲音加影像,解說加音樂,難的是如何在既有的元素中認真呈現文案、剪輯、解說、音樂等各種要素的合作關系,高質量解說者,諸如嗶哩嗶哩平臺的博主“阿斗歸來了”“聽wo姐說”“大象放映室”等,“阿斗歸來了”善于在平淡口吻中講述跌宕的故事,后兩位也各有所長,以現在來看,這些博主能夠口碑與市場雙豐收也是實至名歸。但一些粗制濫造者憑借AI語音加解說模板,在短時間內大批量地生產此類視頻牟利。這類視頻千篇一律地采用大氣渾厚標準男聲、詼諧幽默年輕活力聲音、知性自然女聲等AI語音,配置以“注意看,這個女生叫小美”“注意看,這個男生叫小帥”等解說模板,明目張膽地以低劣把戲攫取大眾的注意力。互聯網內容泛濫的舊疾,已然悄無聲息地爬上了耳朵的地盤。在注意力被奪取這件事上,韓炳哲認為我們自身也不能幸免于斥責,交流的信息恰恰是雙方互動完成的:“網絡上的數字化圈地產生了許多噪音。領地的爭奪讓位給了注意力的爭奪。占有也采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我們不停地制造出必須讓其他人點贊的信息。”[32] 借助互聯網媒介開放的視覺與聽覺傳輸的快速通道,以內容交流為基礎的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必然導致人與內容的連接量的增長,隨之而來的后果可能是內容價值密度下降,加之算法的監視,短視頻解說被觀看、點贊后,也意味著流量管家將源源不斷地供給同質化內容。因而一些觀點認為把“反連接”加入互聯網游戲規則中,也就理所當然了。[33] 瑞士學者考夫曼指出當網絡取代了心靈回音室后,“在越來越公開的或集體性的場合中大聲朗讀,在那里,所有人聽的是同一件事,被激起的是同一種情感,在同一時段里歡笑或哭泣”[34]。互聯網盛宴中,以奪取“注意力和公眾關注度經濟”為目標的文學景觀,何嘗不適用于當今短視頻同質化的趨勢。
“聲音政治批評”的提出,正是想要強調“‘傾聽’是被聲音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產物”,“聲音”實質是由聲音編碼程序制造出來的聽覺泡沫,而“聽覺”也就被動化為一種“由耳朵的開放性和特定的接收心態而產生的信息幻覺”。[35] 這也是周氏與王敦商榷的核心觀點。城市里,商場的背景音樂,喇叭的廣告叫賣,地鐵、公交車上的語音播報,銀行與餐廳的號碼提醒,以及無所不在的聲音外放,人們放下手機,暫時遠離視覺影像并不難,可要遠離噪音卻顯得不現實。人們對嘔啞嘲哳的噪音容易察覺,可在“聲音拜物教”下,人們像饕餮般主動追求悅耳的聲音,沉溺于“人機共聲”創造出來的主體或自我中而不自知。網絡文藝深入耳朵的實際情況可能是:喜馬拉雅FM的“不無聊聽單”并不能打發無聊,只能進一步深化“群體中的孤獨”,特克爾之問“我們對科技的期盼越來越多,卻對彼此的期盼越來越少”[36] 值得警惕。通勤路上的聲音與環境共建的美學空間,或許只是一種隔絕一切才是見真我的荒誕幻覺,我們不禁思考,用戶用精神的想象性連接取代了人們的現實存在,是否是丟了西瓜撿芝麻?Soul、小回音等音頻社交App通過聲音遮蓋主體信息換來的暢聊,很可能攜帶著男女求愛的原始欲望,通過軟件算法推送有一定幾率得遇佳音,但性騷擾、語言攻擊、聲音歧視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助眠的相聲曲藝、白噪音與音頻社交中的“聲控”,前者被“聲音拜物教”宣揚的“情感被神圣化”控制,后者只接受悅耳的聲音,“聲音”被抽空了一切現實意義,只淪為空洞的響動。由此,相聲曲藝、歌曲音樂、抑或交流的聲音在社交媒介的語境下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能指,只以抽象意義而存在,人們陷入了“聽而不見”的吊詭中,更不必說那些絢幻卻又無實在意義的背景音、特效音。顯然,每個人都被“聲音”規訓為慣性行為者,并樂此不疲地以為自己處于聽覺主義中心,可事實上,人們已經陷入一廂情愿而又虛幻的自我表意中,這正是“梵音聲音的文化邏輯”。
“聽就好了,就有了消費,就有了滿足,何必‘見’?‘語音中心主義’乃是用聲音創造‘面對面’的‘見’的幻覺,現在,‘聽覺中心主義’只追求‘聽’。”[37] 這段表述與韓炳哲立足于物與非物世界的發見異曲同工:“安靜不制造任何東西。因此資本主義不喜歡安靜。信息資本主義產生的是交流的強制。”[38] 所謂“安靜”,在韓的語境中幾乎等同于尼采的“心的守護靈”,只有達到了“安靜的”“無名的”狀態,人們才有可能“進入與無名事物的關系中”[39],這恰恰是“物”世界的應有秩序。如今,人們不僅要不停地“看”,繁重的注意任務隨著聲音媒介的崛起被分配給耳朵,“非物”世界的信息噪音正在全面合圍“物”世界中幸存但仍留有可侵犯空間的你我。
從“在場聽書”到“在網聽書”,“聲音”受社交媒介蔭庇在數字時代競發出新一輪生機。強調作為聽覺“事件”的網絡文藝,并非有意與“視覺文化”爭高低,而是想通過呼應新時代的“聽覺文化”轉向,描繪聽覺文化視域下網絡文藝有聲的一面,期待一種“具有影、音、文字的多維立體的表達范式”[40]。作為聽覺“事件”,網絡文藝在新型審美空間的建構、情感陪伴價值與“社交型”場景層面向大眾展示了自身獨特的一面,同時需注意,網絡文藝中的“噪音”與“樂音”之辨。尤其是商業驅使下,缺少相應行為規范以及相較于文字、圖像更難以監管的音頻類App,“嶄新的性質”中同樣暗藏許多問題與弊病,諸如求愛騷擾、自我表意、聲音歧視、審美固化等現象,如不進行適當的“去事件化”,恐怕文藝評論難以成為“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41]。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事件理論視閾下的中國網絡文藝批評研究”(項目批準號:22AA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
[1] 吳釗:《中國式“聽書”發展四階段論》,《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2] 劉國強:《走進機械復制時代的相聲藝術》,《東方藝術》,2022年,第4期。
[3] [加] 羅伯特·洛根:《理解媒介——延伸麥克盧漢》,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頁。
[4] 顏春龍、申啟武、牛存有、賴黎捷:《傳媒藍皮書:中國音頻傳媒發展研究報告(202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239頁。
[5] 王敦編:《聽覺文化研究·譯文卷》,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頁。
[6] 胡疆鋒:《作為事件的網絡文藝與新文藝評論的再出發》,《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6期。
[7] 倪愛珍:《聽覺文化轉向的發生語境與研究路徑》,《文藝評論》,2017年,第6期。
[8] [美] 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千紀指南》(第二版),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頁。
[9] [美] 斯考伯,伊斯雷爾:《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趙乾坤、周寶曜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頁。
[10] [美] 約書亞·梅洛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
[11]《上班通勤路上的你會選擇聽歌嗎?你有哪些寶藏歌單?》,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8644924,2024年6月23日。
[12]《中國音頻市場年度綜合分析》,易觀分析,https://www.analysys.cn/article/detail/20020579,2024年6月23日。
[13] https://xima.tv/1_qW4B1ct?_sonic=0,喜馬拉雅FM,2024年6月23日。
[14]《為什么聽郭德綱相聲更容易入睡》,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8859801/answer/1913102958,2024年7月22日。
[15] 口袋新媒體:《失眠神器!【小睡眠】也有黑科技,無痛喚醒,一鍵小睡》,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4463303,2023年12月23日。
[16] 黎楊全:《走向交往詩學:彈幕文化與社交時代的文藝變革》,《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
[17] 孤城:《社交平臺Soul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書,2021年月活人數超3100萬》,It之家,https://www.ithome.com/0/627/268.htm,2023年12月25日。
[18] 黎楊全:《從審美性到交往性:社交媒體語境下文藝批評的范式變革》,《社會科學輯刊》,2023年,第2期。
[19] [加]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27—330頁。
[20] https://www.soulapp.cn,Soul官網,2023年11月3日。
[21] 曾軍:《轉向聽覺文化》,《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22] [德] 韓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謝曉川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23年版,第130頁。
[23] 同[22],第3頁。
[24] 王之琳、胡疆鋒:《“風暴已經來臨,你我只需側耳傾聽”——中國聲音/聽覺文化研究回顧》,《音樂與聲音研究》,2021年,第1期。
[25] https://www.ximalaya.com/more/aboutus,喜馬拉雅FM,2023年11月27日。
[26] 晏青、何麗敏:《數字聽覺人:數字時代的聲音主體與實踐》,《東岳論叢》,2023年,第8期。
[27] 吳科任:《喜馬拉雅沖擊“耳朵經濟”第一股 全場景月活躍用戶已達2.50億》,中證網,https://cs.com.cn/ssgs/gsxw/202105/t20210502_6163816.html,2023年12月1日。
[28] 杜浩男:《全球青年群體音頻消費現狀與趨勢》,《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3年,第8期。
[29] 陳瑤:《疫情激活在線音頻市場》,第一財經網,https://www.yicai.com/news/100600052.html,2024年6月23日。
[30] 胡疆鋒:《社交媒體時代文藝評論的連接與反連接》,《社會科學輯刊》,2023年,第5期。
[31] 牛片網:《抖音上很火的影視解說配音都是從哪兒來的》,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442564349,2024年6月23日。
[32] 同[22],第168頁。
[33] 彭蘭:《連接與反連接:互聯網法則的搖擺》,《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2期。
[34] [瑞] 樊尚·戈夫曼:《“景觀”文學年版,第媒體對文學的影響》,李適嬿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69頁。
[35] 周志強:《聲音與“聽覺中心主義”——三種聲音景觀的文化政治》,《文藝研究》,2017年,第11期。
[36] [美] 特克爾:《群體性孤獨: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周逵、李箐荊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頁。
[37] 同[35]。
[38] 同[22],第128頁。
[39] 同[22],第99頁。
[40] 禹建湘:《空間轉向:建構網絡文學批評新范式》,《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11期。
[41]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