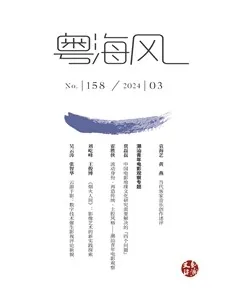人類社會和諧圖景的想象
摘要:林語堂在海外創作的長篇科幻小說《奇島》,精心構建了一個中西文化雜存、不同種族的人和諧共處的烏托邦世界。盡管充滿了虛幻色彩,但不乏對西方殖民史和人類科技發展的反思與批判精神。同時,通過對勞斯的形象的塑造,道出了林語堂關于中西文化融通的理想。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林語堂試圖用中國道家文化之“道”去建構泰勒斯島上的文化圈,開啟了一種想象人類新文明的路徑。盡管其中關于文化融合的設想比較遙遠,但是凸顯了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必然趨勢。因此,這部小說將科學性、幻想性與哲理性融為一體,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具有啟發性。
關鍵詞:《奇島》西方文化 道家文化 烏托邦
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林語堂是一個奇跡,不僅因為他將“幽默”一詞介紹給了國人,還因為他的英語寫作讓西方讀者很早就知道了他的作品,也激發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林語堂身居國外時,一直在思考文化、文學與人生之間的關系,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呈現不同文化融合的景觀,展現出人類社會的理想圖景。《奇島》(又譯為《遠景》)便是他在1955年用英語創作的一部奇特的小說,這部小說有意將故事發生的時空設定在21世紀的某個與世隔絕的南太平洋孤島上,演繹了一個他心目中的理想國,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科幻小說代表作之一。
一、對西方文化的想象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是向海外開拓殖民地的歷史,充滿了冒險精神,也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尤其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許多無名的海中荒島被發現,被開發,有的成為航運補給站,有的成為軍事基地。與此同時,許多島嶼上的資源被掠奪,西方現代文明方式也開始占據主流,取代原有的土著文化。因此,西方各國對外殖民的歷史造成了文化沖突的發生,改變了世界文化地理的格局,也推動了西方荒島文學的發展。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金銀島》和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神秘島》等,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家喻戶曉。對于從小接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林語堂來說,這些作品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創作的《奇島》在某種程度上沿襲了西方荒島小說的模式,描寫了在太平洋泰勒斯島上發生的故事,從一個側面展現了西方殖民的歷史。
美國人芭芭拉·梅瑞克和保羅是地學測量工作者,他們乘坐的飛機在航線迷失后,被迫降落在南太平洋的一個熱帶島嶼上。保羅去世之后,為了適應島上的生活,芭芭拉·梅瑞克改名尤瑞黛,她在這座島上發現了奇異的景觀:裸游的女子、神秘的火葬、復活的希臘文明……這令她感到迷惑不解。通過與人類學家艾瑪·艾瑪的對話,她進一步了解了小島開發的歷史,她恍然大悟:這座島嶼與歷史上的歐洲殖民地十分相似,但又有差別,原來這是一個新的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逐漸適應了島上的生活。
在這部小說中,泰勒斯島是一個奇異的存在,拓展了尤瑞黛的文化視野,也見證了她的成長。她通過與勞斯的進一步接觸,開始了解這個小島上的法律。而勞斯對孔子學說、弗洛伊德心理學的評價和對新型社會的展望,則顯現出他廣博的視野與前瞻性的眼光。可見,勞斯是小說中的中心人物,透過他與幾個女性的交談,不難發現他儒雅的氣質。他具有典型的紳士風度,是林語堂欣賞的一類人物:智慧而灑脫、幽默,注重細節,不失禮儀。尤瑞黛身處小島,由不適應到適應,乃至沉浸于小島生活,完成了人生的蛻變。她的蛻變是在新的環境下實現的,她見證了以海島為中心的西方殖民地發展的過程,也釋放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奇島》描寫女性的地方比較多,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女性渴望解放的愿望,其中女性對自我的欣賞耐人尋味。小說在第二十九章有一段描寫居住在海邊房間里的奧蘭莎對自己裸體雕塑的感想:
在柔和的燈光下,大理石仿佛有了生命,整個線條如此神奇、微妙。微曲的手臂隱入長長的頭發里,光線掠過,閃著漣漪般的光澤,光滑、斜傾的身軀從腰部以上向后微傾,頭部斜斜偏向一邊,臉上掛著神秘誘人的微笑。這真是雕刻藝術的一大勝利,借由物質的媒介,不只表現出了一種精神,還表現出了無言的思想,一種感覺,捕捉住了剎那間的永恒。它好像在向她訴說著什么,傳達著一種訊息。仿佛雕刻家正在說:“這是人類精神、形體完美的幻想。”[1]
女性自我價值的實現有多種途徑,在家庭生活中的自主性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的擔當,都能讓女性感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而讓藝術家根據自己的裸體進行雕塑,則讓自我進入一種理想化的境界,實現了女性的自我認同,這是一種古希臘古典藝術的體現。林語堂是一個標榜個性自由的作家,他塑造這樣一個西方女子的形象,足見他的良苦用心。泰勒斯島儼然一個古希臘社會,古希臘的法律、藝術都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呈現。同時,新型制度的推行則讓女性找到了自我存在的價值。
在文學家眼里,歷史不是一堆材料,而是構成故事不可缺少的鮮活元素。好的小說要演繹歷史,更要超越歷史的束縛,推陳出新。魯迅的《故事新編》可以說是較早以全新的視角演繹歷史與神話傳說的成功之作,這部小說集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巧妙地將古今生活融為一體,激活了歷史,更反思了現實。林語堂旅居海外多年,對西方殖民的歷史有自己的認識,他所虛構的這個與世隔絕的島,并非遠離了人世間,而只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海上空間。來這里拓殖的移民及其后代,延續的是古希臘文明之光,他們通過現代社會制度將其發揚光大。林語堂既沒有夸大歷史,也沒有美化歷史,他講述了一個在孤島冒險的故事,但不再是簡單的求生,而是在細節中審視了文化殖民,顯現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融合。這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歷史的激活,體現了他對西方文明的冷靜審視態度。
眾所周知,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是西方人以所謂的現代文明驅逐土著人的原始文明的歷史,有著明顯的種族歧視色彩,但許多西方人并不以為然,有的甚至因此產生種族優越感。因此,這部作品最初以英語出版,迎合了許多西方讀者的口味,成為他們重溫自己民族歷史的一個文學文本。而當它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之后,又給一些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一扇窗口。尤其在其小說《京華煙云》被改編成電視劇之后,帶動了大眾對林語堂其他小說的閱讀熱。作為一名身居美國的中國人,林語堂是以“他者”的身份去看待西方殖民歷程的,即《奇島》在審視西方殖民歷史的同時,表現了對未來和諧世界的憧憬。其中的“西方形象”滿足了不同讀者的期待視野。對西方讀者而言,這樣的“西方形象”可能成為他們引以為豪的榮耀的象征;而對中國人而言,這樣的“西方形象”可能是他們未曾充分了解,因而會用獵奇的眼光尋找蘊藏于文本之中的西方文化的蛛絲馬跡,尋找一種自由的精神,用以觀照現實。
二、對道家文化的大力推崇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道家文化并沒有像儒家文化那樣受到重視,這是由于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推儒家文化為正宗,并將其作為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法寶。儒家文化中的等級觀念為歷代統治者津津樂道,滿足了他們的需求,但極大地約束了普通民眾的心理,使他們形成了一種順從統治者的奴性思維方式。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崇民主、科學,讓許多人開始從封建等級制度的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尋找個體的自由。道家文化以推崇自然為根本,尋求人生的快樂之源,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產生過重要影響,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林語堂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這在新舊文化交替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顯得較為突出,既反映出一些中國作家的文化保守主義姿態,也促進了不同文學流派的形成。文學是對社會、人生的審美觀照,龍溪縣(今福建漳州)坂仔村的童年生活對林語堂的性格產生著重要影響--“他小時候,是一個無憂無慮而又好動的孩子。經常涉足于山野、禾田或河岸邊,盡情地呼吸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氣,欣賞日落時的奇景,和氣吞萬象的高山雄壯景色。這使他驚異于大自然的神奇變幻,并常常幻想怎樣走出這四面皆山的深谷,更是培育了他酷愛自由、不受束縛的個性,以及熱愛故鄉山水之情。”[2] 可見,林語堂的童年經歷為其人生奠定了基礎,也使他成為道家文化虔誠的追隨者。
作為“論語派”散文的倡導者,林語堂主張從自我出發,遠離政治的束縛,追求生活的樂趣。他曾用一首詩道出自己對道家思想的理解:
愚者有智慧,
緩者有雅致,
鈍者有機巧,
隱者有益處。[3]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消極避世,是樂天知命的道家思想的集中體現,林語堂深受啟發,他在《以放浪為理想的人》中談到自己的人生志趣:“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認為文化須先由巧辯矯飾進步到天真純樸,有意識地進步到簡樸的思想和生活里去,才可被稱為完全的文化;我以為人類必須從智識的智慧,進步到無智的智慧,必須變成一個歡樂的哲學家,也必須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樂,這樣才可以稱為有智慧的人類,因為我們必須先有哭,才有歡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覺,有醒覺而后有哲學的歡笑,另外再加上和善與寬容。”[4] 這與道家“見素抱樸”的主張十分相似,也為他后來的小說創作奠定了基調。
“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過度,性格勝于事業,靜勝于動。一個人能不受禍福的擾動,才能獲得內心的寧靜。”[5] 在《京華煙云》中,林語堂精心刻畫的中心人物姚木蘭,可以說是道家女兒的化身,為人謙遜而和藹,與世無爭。她喜歡山水之美,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多次希望回到美麗的江南。在她身上,幾乎看不到世俗的紛爭,只有順乎自然的浪漫。也許有人因此批評這一人物身上的個人主義思想,其實,她是一個有著堅定信念的女性,她渴望自己的故鄉依舊美麗,這正是中華民族由來已久的根性意識的流露。在《奇島》中,林語堂除了通過對話展現西方殖民史外,還將敘事視角轉向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遠離戰爭和掠奪后的詩意生活,寄寓了林語堂的人生理想:遵循自然之道,享受閑適之樂。《奇島》特意刻畫了一個桃花源一般的海上世界,讓人產生遐想。在泰勒斯島,土著、歐洲人、美國人、俄羅斯人之間不是敵對關系,而是一種和諧共存的關系,他們之間互不干擾,各自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泰勒斯人按照原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著,完全獨立于現代文明之外。在勞斯管理的社會里,法律制度日益健全,公共服務機構應有盡有,人盡其才。同時,勞斯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翻譯過中文散文《宦海談渡》,贊賞中國人深廣的智慧。他尊重女性的選擇,充分體現了現代文明社會的男女平等觀。在回答尤瑞黛提出的問題時,他指出:
普羅米修斯對命運不屈服,他認為他才是宇宙的主宰,自然不是。每當人聰明過度,想背叛自然,自然就還以顏色,毀滅他,使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跛了足。[6]
因此,在勞斯看來,人類無法主宰自然,更不能踐踏自然。他相信神話的象征性語言,認為它充滿想象力,是人類敬畏自然的產物,可以幫助現代人從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中清醒過來。他奉勸處于苦悶期的青年阿席白地:
不要征服自然,要和它并存。自然對人類不含敵意,它是你的朋友。[7]
可見,勞斯是海島上的精神領袖,在他的眼里,只有順應自然,方能讓自我充分釋放,找到生活的樂趣。他相信中西方文化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長期以來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觀念,也反映了林語堂追求中西合璧的文化理想。尤瑞黛的性情由憂慮變得乖巧,她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了自我的價值,她不再沉浸在過去的歲月里,已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懷抱,自然界的靜謐讓她獲得了新生。林語堂在小說中讓一個美國人用親身體驗去感悟敬畏天地自然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這顯然與西方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不同,不再將人類視為地球的主宰者,而在適應自然中陶冶性情,與自然和諧共生,逐漸達到人生的佳境。
在林語堂的文化體系中,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就其文學創作而言,他對道家文化的詮釋占據了重要的位置。“林語堂的文學創作處處透射著對未來人的深思和對美好人格的烏托邦追求。可是他的文本卻能給人以自由、灑脫、自然、柔和的審美享受,絲毫不給人沉重之感。本質原因在于他深諳道家之‘道’。”[8] 林語堂是一個主張個體自由的作家,從《京華煙云》到《奇島》,他以不同的敘事策略呈現了道家文化之精神,這在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彰顯了他將世俗生活藝術化的人生理想。
不可否認,中西文化是差異性的存在,“一個實體的宇宙,一個氣的宇宙;一個實體與虛空的對立,一個則虛實相生。這就是浸滲于各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異,也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西方人看待什么都是用實體的觀點,而中國人則是用氣的觀點去看的。”[9] 這說明中西文化的表現形式不同,功能也有差異。林語堂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在西方人的幽默與中國道家的出世精神之間找到了契合點,并借《奇島》中主要人物的性情變化展露出來,彰顯了中西文化融通的可能性。因此,《奇島》的故事顯得海闊天空,給人一種海市蜃樓般的虛無感。
可見,《奇島》對道家文化的推崇,顯現了林語堂試圖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姿態,這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歷史傳統,但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都需要在交流中汲取彼此的元素。誠如莊偉杰所言:“林語堂始終堅守一個東方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以智者的立場,企冀將淵深廣博的中國文化以通俗化又藝術化的方式傳遞給世界,將逼近真實的‘中國形象’近距離地呈現在西方人士面前,一來可能引起西方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關注,二來可以逐漸消解西方人士想象中的落后野蠻的東方形象的歪曲,糾正因此而造成的不平等、乏尊重的歧視或誤讀。”[10] 這正是林語堂的獨到之處,他在小說中以委婉的敘述方式,演繹了道家的逍遙精神,激活了故事,還原了“中國形象”。
三、反思科學技術,追求人性解放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循序漸進的過程,從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到高樓林立的現代社會,人類始終離不開自然,也離不開科學技術。自人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科技革命日新月異,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活的質量,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能源是人類生存的必需,但是長期的開采,已經導致地球能源大規模減少,環境污染加劇,急需新的能源來補充,于是,利用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成為現代文明社會的首選。在20世紀50年代科學技術還不夠發達的年代,林語堂在《奇島》中描寫勞斯關于科學的高論和格魯丘發明的太陽能技術,在當時無疑讓人大開眼界。
在《奇島》中,勞斯在與尤瑞黛的對話中表現出對古希臘哲學(在希臘文里,哲學是“愛智”的意思)的推崇:
愛智是不斷地自由地求知,是最美好、最高貴的愛。其中包括了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科學在內,勇敢地自由探討自然和事物的成因。[11]
在勞斯眼里,科學也是一種哲學,這就道出了科學的實質:透過自然現象,尋找科學規律,發現真理。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科學也不是萬能的,在現實生活中,科學是一柄雙刃劍,一旦將科學推向極端,必將導致意想不到的惡果。例如,烈性炸藥的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的進程,也危害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可見,科學理性無法代替人文理性,只有以人為本,辯證地看待科學的發展,才能讓科學真正地造福人類。
格魯丘在水壩附近探索太陽能發電的可行性,但他對一些科學家的原子彈發明表示不滿。可見,他相信科學技術的力量,但不唯科學技術至上,而是從實際出發,探索通往生活便捷之路。這也是林語堂通過這一人物要凸顯的意義,即科學技術無論如何發達,都不能為所欲為,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推進技術進步,造福人類,才是科學技術的正道。
自歐洲文藝復興以后,封建的神學受到廣泛的質疑,資本主義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民主、科學和人性解放成為人類追求的共同目標。以人為本,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價值,是人性解放的基礎。林語堂自由灑脫的個性決定了他的創作指向。《奇島》在第四十三章描寫了艾音尼基節日,展現了眾人狂歡的情景,表現了藝術的巨大吸引力。勞斯朗誦了自己創作的詩《原子》,用類比的手法解釋了原子的結構,道出了祈求和平的心愿。原子能是科學史上的重大發現,在利用它推動工業生產的同時,也導致了核戰爭的危機。勞斯在詩中反思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殖民的歷史,倡導人文精神的復蘇,將節日推向了高潮。
林語堂說過:“我覺得藝術、詩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輔助我們恢復新鮮的視覺、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種更健全的人生意識。”[12] 這表明了他的快樂主義人生觀,希望通過崇高的精神愉悅消除世俗生活的煩惱,改良社會。在艾音尼基節上,歌舞藝術大放異彩,讓島上的人充分釋放了自我,增強了凝聚力,顯示出人人平等的烏托邦氛圍,此后,島上的家庭關系日益融洽。
“處于上升地位的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思想是關于‘自由’的思想。部分來說,這是一種真正的烏托邦思想,也就是說,它包括了為了實現一種新社會秩序的元素,這些元素有助于瓦解先前存在的秩序,而在實現之后確實有一部分被變成了現實。”[13] 這說明烏托邦的性質在于:試圖打破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建構平等而和諧的人類精神家園。在多元文化雜存的現代社會,利益之間的博弈顯得比較突出,造成了人際關系的復雜化。泰勒斯島顯然不同于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在這個烏托邦王國里,老斯斯是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他果敢、自信而民主。小島上各種文化并存,不同民族的人在對話溝通中,實現了情感與思想的交流,相安無事。與此同時,勞斯以自然的人性論為基礎,反思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沒有拒絕外來世界送來的藥品和書籍,足見其思想的開放性與變通性。
科學幻想小說不是童話,不靠擬人手法塑造藝術想象,而以科學預見為基礎,以跨越時空的想象吸引讀者,但其中心依然是故事中的人類生活與夢想。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當前共同面臨的話題,優秀的科幻小說關注的是人類未來居住的環境以及人類心靈的成長,只有以藝術的想象超越當代生活,才能出奇制勝,贏得讀者的青睞。“林語堂因有了理性和科學觀念而懷疑教條式的宗教信仰,同時也由于他相信人需有信仰、價值而與惟科學、惟物質和邏輯理性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14] 他創作《奇島》的年代正處于世界“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對峙,構成了針鋒相對的二元空間,東、西方文化無法開展對話。“閩南的村落家族正如其封閉性并不那么厲害一樣,它的排他性也不那么厲害,對外來文化表現得比較寬容。”[15],經過時代的洗禮,閩南人形成了開放、兼容并包的精神。在閩南文化的啟發下,林語堂形成了自己的個性。首先,在坂仔村的童年生活奠定了林語堂的人生價值觀,使他養成了無拘無束的性格和探索未來世界的興趣。他曾經說過:“我以為我的心思是傾于哲學的,即自小孩子時已是如此。在十歲以前,為上帝和永生的問題,我已斤斤辯論了。”[16] 其次,林語堂保持了作為閩南之子的生活習慣,以飲閩南功夫茶為樂,以吃閩南菜為本。他對閩南飲食文化的認同,是其快樂人生觀的體現。他甚至將飲茶上升到一種精神境界,指出:“飲茶者需要細品慢嘗,志趣相投的朋友聚在一起借飲茶之際消除彼此的煩惱。在這里,我們最好忘掉茶本身。”[17] 所以,林語堂有感于“冷戰”時期的局面,深知這樣的對峙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他希望通過不同文化的交流,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渴望構建一個和諧共處的大同世界。他所虛構的海上孤島及島上人們的生活方式,既不是歷史的重現,更不是現實生活的翻版,而是他精心構想的一個未來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中西文化相交融,人人平等,自由和快樂成為大家追求的終極目標,面積不大的小島隱喻的是林語堂心中理想的人類社會模式。
“文藝作品都是以有限的形象表現無限,從而超越有限而進入無限自由之境。不達此境,不可能創作出杰出的文藝作品。”[18] 小說《奇島》中的人物形象不多,但是比較集中。筆者認為,一方面,它聚焦海島,通過人類學家艾瑪·艾瑪的眼光,盤點了文化的變遷,宣告了以強取豪奪為目標的西方殖民主義文化的終結;另一方面,林語堂以大海為參照,擁抱一切有益于人類社會進步的文化,試圖用中國道家文化之“道”去建構泰勒斯島上的文化圈,開啟了一種想象人類新文明的路徑。盡管其中關于文化融合的設想比較遙遠,但是凸顯了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必然趨勢。
結 語
在林語堂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奇島》顯得比較特殊。它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小說,沒有追求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而是在日常生活描寫中顯現人物的個性,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它也有別于一般的科幻小說,沒有描寫“超人”,而是在平靜的敘述中彰顯順乎自然的人性。其中的海島并不是荒無人煙的,而是一個充滿煙火氣、融通古今、涵蓋中西文化的審美載體,是林語堂精心構建的烏托邦世界,充分體現了他追求的包容、融通、樂觀、知足的理想境界。在全球化的21世紀,不同民族的文化處于不斷的碰撞與交流之中,面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有驚喜,有收獲,也不乏失落感。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無法更改,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共同遵守的規則,從而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這是他們賴以依存的精神家園;另一方面,在面對人類命運的共同挑戰時,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需要攜手合作,要從文化沖突論中解脫出來,大膽進行自我革新,以構建和諧、文明的世界秩序。因此,重讀《奇島》,不難發現,林語堂設想的跨文化、跨世紀的“桃花源”般的人類社會和諧圖景在當下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本文為湖南省社科成果評審委員會項目“新世紀二十年中國文學的海洋生態書寫”(編號:XSP24YBC02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城市學院人文學院)
注釋:
[1] 林語堂:《奇島》,張振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248頁。
[2] 劉炎生:《林語堂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3]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越裔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頁。
[4] 林語堂:《我這一生:林語堂口述自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頁。
[5] 同[3],第158頁。
[6] 同[1],第121頁。
[7] 同[1],第130頁。
[8] 肖百容:《林語堂小說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頁。
[9] 張法:《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
[10] 莊偉杰:《林語堂:跨文化對話中的解讀》,《華文文學》,2008年,第3期,第49-54頁。
[11] 同[1],第228頁。
[12] 同[3],第140頁。
[13] [德]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李步樓、尚偉、祁阿紅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46頁。
[14] 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頁。
[15] 陳燕玲:《閩南文化概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3-84頁。
[16] 同[4],第5頁。
[17] 同[4],第295頁。
[18] 張世英:《藝術當追求提高境界》,《人民日報》,2018年5月22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