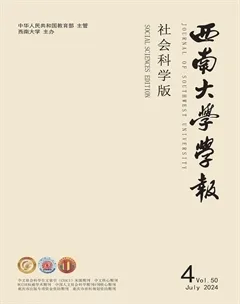數字勞動如何成為勞動?
摘 要:數字勞動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創新概念,和受眾商品、免費勞動、非物質勞動、玩勞動等易混同的概念群一起進入國內視界,傳入后其迅速吸引了國內學者關注,數字商品、數字必要勞動、數字剩余勞動、數字剩余價值等新概念也接連出現,數字勞動相關研究成為學界熱點。然而,面對資本與數字技術耦合下的信息化資本主義,我們不能簡單地在來自西方的數字勞動理論后面“接著說”,而是要在理論喧囂之后回頭進行“冷思考”,橫向剖析數字勞動、非物質勞動概念的發展史與內涵,縱向深入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各自的理論目的與論證理路,這樣才能達到對數字勞動概念“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徹底理解。深入概念史演進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意大利自治社會主義面對資本進入人們生產領域之外的情感、休閑和娛樂生活,共同選擇了“回到馬克思”,即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核心范疇構建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最終結果是因誤解或曲解馬克思的核心概念而偏離唯物史觀。總的來說,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理論中,馬克思核心概念出場的背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性和革命性的根本退場。真正的“回到馬克思”,需要從“生產力總和”決定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上來審視數字勞動難題,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科學技術生產力與知識勞動是揭示數字勞動屬性、內涵與本質的前提。
關鍵詞:數字勞動;非物質勞動;福克斯;科學技術生產力;知識勞動;勞動異化
中圖分類號:F49;F0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24)04-0101-13
20世紀末期以來,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算法等迅速迭代的數字技術在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休閑活動方式,數字化生存成為時代的顯著特征。數字勞動(Digital Labor)概念的出場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人們日常使用電子設備的行為納入資本主義生產場域的最初探索。吳歡和盧黎歌是國內較早引介數字勞動及相關理論的學者,其對數字勞動概念的詳細闡述和高度評價[1],深刻影響了此后國內數字勞動研究的立論基礎和研究方向。
國內學者圍繞數字勞動的內涵、特點和性質形成了不同的理論觀點。其一,數字勞動是一種以非物質形式呈現的生產性勞動。付文軍認為數字勞動是一種以“非物質生產”為典型特征,同時兼具間接性、碎片化和虛擬化的生產勞動,是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2]。孟飛和程榕指出數字勞動是一種對虛擬的勞動對象直接進行認知加工的有目的的生產勞動[3]。其二,數字勞動是一種雇傭體系之外的生產性勞動。劉偉杰和周紹東指出,數字用戶的日常活動都應被納入數據商品的生產過程中,這些非雇傭數字勞動實質上依然從屬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是形成數據商品價值和剩余價值的重要源泉[4]。曲佳寶結合勞動過程三要素指出數據商品生產過程包含無酬的非雇傭數字勞動[5]。其三,數字勞動是一種以是否可以數據化為標準的生產勞動。藍江認為:“在數字勞動這里,物質與非物質的區分不再重要,數字的收集與分析已經跨越了休閑與生產、物質與非物質的分界,而是直接將可以數據化和不可數據化作為全新的區分標準。”[6]其四,數字勞動是一種由數字必要勞動和數字剩余勞動構成的生產性勞動。溫旭將數據二因素、數字勞動二因素及數字剩余價值作為剖析數字勞動價值的基本理論框架[7]。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學者強烈反對將數字勞動作為一種生產勞動。孫蚌珠和石先梅認為不能將無目的使用數字設備的活動稱為勞動[8]。更有學者直接對數字勞動概念的學術合法性提出質疑,余斌認為數字勞動不符合政治經濟學相關術語的運用規則,是俗語而非學術用語,因此更談不上將其稱為勞動[9]。吳靜提出數字勞動的研究熱潮使得數字時代勞動的討論進入了簡單化的局面,“‘數字經濟—數字資本—數字勞動’這樣的線性的總體性理論恰恰是我們在面對不斷發展、分化、發酵的數字現實的最大的理論障礙”[10]。
綜合來看,自數字勞動研究熱潮興起以來,關于數字勞動的闡釋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都形成了相當數量和質量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國內學者大多承襲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對數字勞動的定義,但由于福克斯本人對數字勞動概念界定的模糊性,讀者在理解時也對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作出調整,所以學者們使用的數字勞動概念內涵并不相同。其次,數字勞動、非物質勞動、免費勞動、玩勞動等概念常常被作為內涵一致的概念混同使用,概念邊界不清晰。事實上,以上兩個問題可以歸結為最后一個問題,即對于數字勞動概念處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即缺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數字勞動概念的過程、數字勞動相關概念群之間關系的辨析研究。相比于前期的研究熱潮,目前關于數字勞動的研究熱度已經稍有降溫,但這也是探究數字勞動概念本質的成熟時期。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回頭溯源數字勞動概念的思想史對于更進一步理解數字勞動概念本質是必要的。
一、“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數字勞動概念史厘析
面對“舶來品”數字勞動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厘清數字勞動概念學術史脈絡的基礎上,剖析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對數字勞動問題的研究緣起,是真正理解數字勞動概念內涵的前提。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還是自治社會主義?——數字勞動概念的緣起探究
數字勞動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的新概念,一般認為是意大利學者蒂茲納·特拉諾瓦(Tiziana Terranova)于2000年首創。嚴格來說,數字勞動作為俗語早已存在,而特拉諾瓦首次將數字勞動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概念在論文中提出,并認為數字勞動本質上是為數字經濟生產文化的“免費勞動”(Free Labor)[11]。稍加追溯這一界說的根源就會發現,免費勞動概念是意大利自治社會主義學派毛里齊奧·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于1996年提出,并與非物質勞動概念相互解釋,以反映信息技術時代工人遭遇剝削的新形式[12]。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在概念創新的路徑上不期而遇、相互借鑒,試圖建構信息技術時代的社會批判理論,二者雖不能說是理論流派的競爭,但也有各自的理論意圖。實際上,免費勞動、非物質勞動、生命政治等概念群是屬于自治社會主義的,受眾勞動、免費商品、產—銷品、數字勞動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創制的概念群。
數字勞動概念形成學術熱點之時,出現了將兩個學派的概念群混同甚至等同理解的現象。這種狀況也有其原因,如特拉諾瓦界定的數字勞動,既是“免費勞動”的同義詞,又隱含以“免費勞動”解釋“數字勞動”之意。再如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后起之秀福克斯,在特拉諾瓦還將數字勞動限定于互聯網領域的部分職業時,福克斯已將數字勞動概念的涵蓋范圍擴展至社交媒體及其相關的礦石開采、材料加工、網絡、電腦設備等通信和信息技術(ICT)整體行業鏈條,甚至福克斯認為這還不能顯現數字勞動概念的意圖,其更大的理論目標是建構一種多層面概念化的數字勞動理論工具箱,在重釋馬克思《資本論》范疇體系的基礎上,賦予無酬勞動、免費商品等概念以新內涵,最終建構一個完整的數字勞動理論體系[13]11。可以說福克斯是將數字勞動概念傳播開來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學者,國內外對數字勞動概念的理解也主要來自福克斯,因此福克斯將受眾商品、免費勞動、無酬勞動、非物質勞動等概念轉變為數字勞動的下位概念并加以改造的解釋路徑,是造成數字勞動、非物質勞動、物質勞動等概念混同和等同性誤解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自治社會主義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概念群的分辨是厘清數字勞動概念學術史的前提,這并不意味著兩個學派的概念群是絕對孤立的關系,相反,兩個學派在時間序列和邏輯序列的雙重互動中相互引證、激烈爭辯,最終共同選擇了“回歸勞動”的理論路徑,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豐富、深化數字勞動的概念內涵。
在“回歸勞動”的理論路徑上,福克斯憑借數字勞動理論工具箱被廣泛熟知,然而“數字”與“勞動”的耦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從“商品”到“勞動”的理論深化過程,如果僅僅停留于福克斯及其《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一書,就會對數字勞動的理解處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程度。福克斯在成為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之前,首先是一位傳播學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學者對其產生了深刻的理論影響。1977年,傳播政治經濟學創始人達拉斯·斯邁茲(Dallas W.Smythe)發表《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一文,提醒人們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傳播的復雜作用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斯邁茲在文章中創造性地提出受眾商品理論,意指商業資本家與媒介資本家將受眾聽廣播和看電視的“注意力”作為商品打包出售給廣告商[14],這樣的“注意力”剝削現象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盲點所在。但是,此時的受眾商品因沒有生產勞動的滲入連非商品的產品都算不上,又如何成為商品?這樣的理論質疑使受眾商品概念陷入困境。美國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意識到僅停留于“商品”層面不夠,因此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推動了“回歸勞動”的理論轉向,表示“‘傳播’若要在語言、意識形態與意義的展示平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先要讓‘勞動’與傳播產生一種互動關系”[15]。這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更深一步。與斯邁茲同一時期,也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產生深刻影響的還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他的文化唯物主義將文化本身視為一種物質生產[16],這契合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表達傳媒領域物質生產問題的需要,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威廉·亨寧·詹姆斯·赫布爾懷特(William Henning James Hebblewhite)更是在威廉斯和福克斯的共同影響下提出產銷者(Produser)的概念[17]208。
福克斯與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敏銳地注意到了馬克思在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中的熱度逐漸上升,據兩位學者統計,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標題中含有關鍵詞“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者/的”或“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2008至2011年期間,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的年平均發表數為247.5篇,相對于1998至2007年的每年125篇和1988至1997年的每年172篇有所增加”[17]6。這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表現出極大的研究興趣。在這樣的背景下,2012年福克斯聯手莫斯可主持召開了一次題為“馬克思歸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研究對當今傳播學批判研究的重要性”的學術研討會。為克服數字媒體時代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盲點”,福克斯分別在2014和2016年出版《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在信息時代讀馬克思:傳媒研究視角的〈資本論〉第1卷》,前者被看作數字媒體時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數字勞動理論研究的集大成者[13]1,后者則被西方學界譽為“傳媒版的《資本論》”[13]1,數字勞動的研究熱潮由此興起。
(二)數字勞動概念的內涵之辨:物質性與非物質性
從時間序列上來說,雖然席勒已經提出了“勞動轉向”,但是此時傳播政治經濟學在論證傳播領域的生產問題時更多還是受到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的影響,直接從文化的物質生產性論證傳媒領域受眾的勞動性,還處于一種比較模糊的理論表述階段。這個問題由自治社會主義的拉扎拉托予以解決,拉扎拉托在1996年明確使用“非物質勞動”概念,這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得以概念化和具體化,可以說自治社會主義的非物質勞動概念在邏輯序列上進一步穩定了數字勞動的理論根基。從定義來看,非物質勞動就是“生產商品的信息內容與文化內容的勞動”[12]。拉扎拉托認為,馬克思依據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二分法得出物質生產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已經過時,馬克思所忽視的非物質勞動已經成為現實,依從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二分法已經不可能看穿生產勞動過程中知識勞動從屬于資本的問題,非物質勞動已經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社會關系的典型體現。可以看出,拉扎拉托雖然曲解了馬克思關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辯證關系的重要論述,但他提出的非物質勞動概念已經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的基礎概念,兩個學派都在非物質勞動概念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理論創新。
可以說非物質勞動概念對揭示信息技術時代資本主義的剝削發揮了奠基性作用,與拉扎拉托同一學派的理論旗手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合作發表了《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引發了自治社會主義的復興。奈格里和哈特在他們的理論中并沒有突出數字勞動概念,而是表述為非物質勞動。為進一步鞏固非物質勞動理論根基,他們相繼發表《大眾》《大同世界》,由此構成信息技術時代大眾解放如何可能的歷史辯證法三部曲。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從三個層面闡釋非物質勞動:首先是計算機深度控制和改變了原有的生產過程;其次,相比于傳統大工業生產,符號化、精神化的生產更為突出;再次,生產過程已經涉及處理感覺和態度的情感勞動[18]32。顯然,這個非物質勞動已經包含了物質生產勞動,出現了矛盾。后來他們將第一個層面的含義舍掉,只保留后兩層含義[19]。似乎第二、第三層面屬于意識、精神層面,與非物質勞動概念自洽,也稱之為非物質產品勞動、精神勞動,或數字勞動。但是,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發出了一個強力回應:“網絡化的數字信息系統沒有任何非物質性……若將網絡化的數字信息系統描述為非物質的工作過程,恰恰說明了此人是數字信息系統的門外漢,也更不會構建出一個關于新媒體的批判性理論。認識到新媒體獨特的物質性是觸及并理解新媒體批判理論的前提。”[20]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更明確地表示,奈格里和哈特的所謂非物質勞動依然是物質勞動概念[21]。奈格里和哈特在回應批評的辯論中認識到非物質勞動概念的模糊性問題,因此進一步澄清其存在的領域:一方面,“圖像、信息、知識、情感、符碼以及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的價值增殖過程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質性層面”[22]99,這些圖像、信息、知識、情感和符碼構成非物質勞動的生產內容。另一方面,“生產這些非物質商品(或者物質性商品的非物質方面)的勞動形式,可以稱為心腦勞動(Labor of Head and Heart),其中包括服務業、情感性勞動以及認知勞動”[22]99,即非物質勞動。雖然奈格里和哈特并沒有簡單地以非物質勞動指代腦力勞動,而是特別強調非物質勞動的“生產過程也同時需要腦力和體力”[22]99。但是奈格里和哈特從根本上改變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邏輯,不是從勞動過程而是從勞動結果的非物質性來定義一種新的勞動形式,然后以此來支撐他們的生命政治哲學,這樣的概念內涵從一開始就是無力的。對此,哈維(David Hary)指出,奈格里和哈特應當“更加認真對待馬克思‘非物質但卻客觀’的論述,并且更多討論‘客觀的’這一方面”[23]。哈維意在強調,以非物質形式呈現的精神、情感和文化勞動滲透在現實的物質勞動過程中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如果忽視生產過程生產力的客觀性,過多強調生命政治的主體性就離開了歷史唯物主義,就會將生產決定生活顛倒為生活決定生產[24]。
進入2010年后,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福克斯依然面臨物質性與非物質性難題,但相比于奈格里和哈特,福克斯不是從勞動結果的非物質來論證新的勞動形態,而是首先將數字勞動定位于物質性勞動[25],以數字勞動為總體概念框架,把非物質勞動、無酬勞動、免費商品等概念作為其下位概念,來試圖構建一個數字勞動理論工具箱[13]11。福克斯在定義數字勞動概念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自己計算機專業背景的優勢,福克斯認為不論是計算機制造還是互聯網連接的信息技術都離不開礦石開采、硬件材料加工、通信設備聯通等物質性勞動;軟件設計、程序控制雖然是精神層面的腦力勞動,但這是人腦加工物質材料,從而使精神勞動凝結于物質產品中的過程,因此總體上不需要區分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數字勞動歸根到底就是物質性勞動。福克斯將圍繞互聯網而形成的產業鏈條全部納入數字勞動體系,這是廣義的數字勞動概念。在狹義上,福克斯以數字勞動概念指稱互聯網用戶瀏覽網頁、讀聽廣告、購物、發表意見等活動。這種區分有利于福克斯深度分析計算機、互聯網、信息技術產業鏈高端剝削低端這一資本主義全球范圍內的剝削現象,這是世界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利用發達數字技術剝奪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現實。就數字勞動屬性來說,福克斯將非物質的精神勞動定性為物質性勞動,剖析資本主義與數字技術合謀形成新的剩余價值的獲取方式;就存在形式來說,福克斯將數字勞動的涵蓋范圍擴展至整個信息技術產業鏈條和廣泛的數字用戶。可以說,福克斯的數字勞動概念在內涵的廣泛性與深刻性上超越了特拉諾瓦的數字勞動。
從概念內涵上來說,福克斯從廣義上將通信和信息技術產業鏈條上的所有勞動都納入數字勞動范圍,從狹義上將原本不屬于雇傭勞動的休閑娛樂活動作為數字勞動內涵;奈格里和哈特則是將產生圖像、信息、知識、情感和符碼的所有行為稱為勞動。對比之后不難發現,不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還是自治社會主義都在嘗試將傳統勞動之外的人類活動納入生產勞動范圍,這就將問題推進到另一個層面:馬克思關于勞動與活動的劃分標準過時了嗎?在西方思想史上,活動是自主、自由的領域,勞動指的是奴隸的勞作行為,這一劃分標準直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發現勞動創造價值才真正改變。馬克思從大的方面區分了創造剩余價值的生產勞動和雇傭體系之外的休閑活動,在勞動上又區分了自愿表現個人興趣特長的勞動和被奴役的勞動,這是商品生產時代對勞動與活動的劃分。可以肯定的是,當今時代并未超出馬克思所設定的商品生產時代,勞動依然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那么福克斯、奈格里和哈特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為什么執著于將不屬于勞動范圍的休閑活動納入生產勞動之中呢?這需要縱向深入到他們各自的理論論證中去尋找答案。
二、數字勞動概念的論證邏輯:馬克思的形式出場與實際退場
福克斯在《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中單列“卡爾·馬克思的理論介紹”一章,并表示其“基本的理論框架是馬克思的”[13]29。奈格里和哈特高度評價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也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并在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基礎上建構知識無產者的主體革命理論。至此,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核心概念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得到“隆重出場”。但是,概念的形式出場不代表理論的根本貫徹。縱向深入自治社會主義和傳播政治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論證可以發現,福克斯借馬克思的勞動、商品和剝削等概念構建數字勞動理論體系,將不屬于勞動范圍的休閑活動納入生產勞動之中,實際上違背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奈格里和哈特則將社會變革的根本力量寄托于抽象的“諸眾”,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中的核心內容就此被抽離。因此,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理論中,馬克思核心概念出場的背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性和革命性的根本退場。
(一)奈格里和哈特:為塑造革命主體構建生命政治生產力理論
奈格里和哈特構建了一條先回到馬克思再“超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論證邏輯。奈格里重釋了馬克思的《大綱》,確立了從物質生產勞動向非物質勞動概念演進及論證的理論基座。1978年奈格里流亡法國期間參加了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主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講座,把講座提綱集結為《〈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奈格里批判阿爾都塞“嚴重低估了《大綱》的價值”[26]3,認為《大綱》不僅是通向《資本論》的道路,而且埋藏著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主體性理論,《資本論》突出了生產力決定的客觀性,而《大綱》預設了無產階級革命主體理論。基于此,奈格里認為“《大綱》是馬克思革命思想的頂點。伴隨這些筆記本而來的是理論—實踐層面上的斷裂,我們從中能夠發現革命行動以及它既不同于意識形態又不同于客體主義之處”[26]38。這里所說的斷裂是《大綱》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演進的重要環節而獨立,并因此與《資本論》的勞動價值論相割裂,這是奈格里強化革命主觀性及其主體塑造的理論奠基。
奈格里認為《大綱》的“機器論片段”是馬克思理論張力的最高點[26]178。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史區分為協作勞動、工場手工業勞動、大機器生產勞動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是工人勞動“形式從屬”資本,以大機器作為生產工具的生產完成了“實質從屬”,而其后果是工人的“活勞動”從屬于“機器”的死勞動,活勞動成為沒有意識的機器的肢體,成為機器看護和生產的調節者,但奈格里卻認為這里潛藏了革命主體性的重要論說。馬克思指出,機器不是自然界生長但又是依賴自然之物通過人的產業勞動創造出來的,“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27]102。奈格里從“一般智力”獲得靈感并以之為核心概念,認為在資本生產邏輯上,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同時為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和資本家占有工人勞動的剩余時間創造了條件,但工人作為主體在資本生產之外占有自由時間來獲得主體性的發展。實際上,這是奈格里在這兩個方面獲得主體性論證的雙重邏輯,就前者的資本客觀邏輯來說,他認為在馬克思的工資理論中,工人的必要勞動量與資本交換是具體勞動轉化為抽象勞動的對立,構成了抽象價值包含具體勞動的對立,在大機器生產體系中“使概念的二元論得以迸發而且采用主體的雙重形式”[26]168。也就是工人的工資是作為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獨立變量,與固定資本的大機器體系相對立,工人爭取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斗爭反過來促使資本家提高科學和技術的固定資本生產力,工人又成為二者之間的中介,這是取消抽象勞動統治的可能條件。奈格里在“一般智力”概念之下引出了“社會工人”的概念,也就是大工業的分工是社會分工,而科學和技術生產力的提高更加促進社會分工,工人占有自由時間成為社會再生產的主要形式。
可以說,“正如《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便是奈格里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26]1。馬克思在《大綱》中提出的“一般智力”成為奈格里和哈特論證非物質勞動概念的重要基礎。奈格里和哈特認為,拉扎拉托界定的非物質勞動概念只局限在物質生產的表象,這對深刻的社會問題只是隔靴搔癢。奈格里和哈特在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基礎上,引入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深入到計算機、信息網絡時代的普遍交往維度,使“一般智力”得到“交往勞動”的重新定義,以抽象的象征性分析和解決問題的互動式勞動構成交往勞動的主體性,由此“交往勞動”作為主體自主的勞動形式、生產和操縱情感的勞動成為生命政治的核心問題[18]31-32。實際上,這里埋藏了奈格里和哈特“雙重矛盾”的辯證法,即將交往勞動等同于生命政治主體自覺勞動的應然,同生產和操縱情感的勞動相對抗,同時還存在情感勞動與被操縱的情感勞動相對抗。在這種雙重矛盾中,情感勞動既具有生命本體的規定性,又具有“物質的、肉體的生產力”[18] 32的原生力量,這是突破矛盾二重性的本體的原生力量。但是奈格里、哈特對情感勞動的界定是模糊的,大體包括健康服務、娛樂工業、自我服務、網絡交流等,在論述上主要表述為“服務性勞動”。這是受到了斯密和馬克思的影響,斯密把非生產性勞動等同于服務勞動,即不創造價值的勞動,馬克思一方面批判斯密對其概念界定有問題,另一方面認為從商品生產角度來說斯密是對的,但服務性勞動是否具有生產價值要看是否進入商品生產階段,在大機器時代服務性勞動的生產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奈格里和哈特認為被馬克思所忽略的不僅是第三產業的服務性勞動日益增長,還有第一、二產業在信息技術滲透下逐漸打破勞動者階層、生產地域等局限的趨勢。他們認為如同大機器時代工人活勞動實質從屬資本一樣,情感勞動在資本的操縱下構建了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帝國。如何打破這一僵局呢?奈格里和哈特給出的答案是:從“一般智力”向“交往勞動”轉變,以生命政治生產力激活被操縱的情感勞動。信息時代的情感勞動被操縱是工業社會向后現代信息社會轉型的發生學,即從身體和思想規訓、控制而來,消解操控的邏輯是將發生學的順序顛倒過來,也就是基于科學、知識、情感和交往的力量來激活“生命政治生產力”,它既存在于個體的肉體和思想中,也存在于普遍交往和互動式勞動中,在“社會工人”的再生產中個人的主體性和自覺聯合的社會生產力主體構成解構資本的力量。可見,奈格里、哈特重構了生產力概念,這種生產力的格局體現在生命政治的內在性和非物質勞動外在性的統一體,其表現形式就是科學的、知識的、情感的和交往的、交互式勞動的力量。這顯然不符合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28],更不符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內涵。
(二)福克斯:以信息生產力的異化論證數字勞動即異化勞動
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福克斯批評奈格里和哈特把非物質勞動概念作為“不精確的知識工作”而引向知識勞動非物質性的唯心主義軌道[13]471。同樣,福克斯也認為斯邁茲的受眾商品理論解釋力不夠。對此,福克斯做了兩項基礎性的理論工作:
第一,區分勞動和工作兩個概念。福克斯認為《資本論》第一卷中恩格斯所加的注釋,即“英語有一個優點,它有兩個不同的詞來表達勞動的這兩個不同的方面。創造使用價值的并且在質上得到規定的勞動叫做work,以與labour相對;創造價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計算的勞動叫做labour,以與work相對”[29]61,這是馬克思區分勞動和工作的標準。福克斯指認,馬克思在德文著作中使用Arbeit是工作和勞動的混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廢除勞動”的模糊表述,實質上是廢除異化勞動而保留“工作”,馬克思所說“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29]56是對工作的歷史闡釋,是人與自然界物質變換的自然必然性。福克斯斷定,自階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以來“勞動是一種必然異化的工作形式,在其中,人類無法控制和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及生產結果……工作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利用技術改造自然和社會,從而創造出滿足人類需要的商品和服務”[13]35。顯然,這種詞義學的論證邏輯是不盡如人意的,但為他解釋數字勞動等于異化勞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構建信息生產力系統。福克斯以勞動力(活勞動)、勞動資料(固定資本的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材料)三大要素構建信息生產力系統。從發展邏輯看,信息生產力既是馬克思所說“一般智力”機器體系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當代的“一般智力”的知識生產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勞動主體的生產力是知識創造的腦力和體力消耗,勞動工具是數字設備、互聯網和數字平臺等,勞動對象是信息資源,勞動產品是數據商品。福克斯堅定認為信息具備生產力的物質屬性,“信息生產力”既是知識生產的結果又是數字媒體時代代替大機器固定資本生產力的典型特質,信息生產力的作用機制就是平臺為積累資本而運用定向廣告,將用戶數據商品化并剝削數字勞動的過程[13]448。
相比于斯邁茲受眾商品理論中的單向度受眾,福克斯認為網絡信息技術已經使受眾和直接商品生產者聯系起來,受眾在作為媒介觀眾的同時還是商品生產的重要勞動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系是生產數據商品這一產銷品。由此受眾便在傳統雇傭體系之外進行無酬的生產勞動,這是進一步分析“玩勞動”的理論激活點。受眾聽音樂、看電視的“玩”是自愿的、娛樂的、享受的活動,是滿足自我精神需要的“工作”,但這是經由數字平臺來實現的。“平臺”作為固定資本是信息生產力的體現,因此“玩”也就參與了平臺資本的增殖過程。福克斯和奈格里、哈特一樣,從馬克思的“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29]582的“總體工人”向“社會工人”轉變出發,確認“玩勞動”是“玩”的“工作”的異化。福克斯認為社會工人創造價值是勞動力的結合形式,依循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異化的四重邏輯(勞動結果的異化、勞動過程的異化、與人的類本質異化、人與人異化),得出“信息生產力”體系整體異化,即“主體與其自身的異化(勞動力為資本所用且被資本控制),與客體的異化(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以及與主—客體關系(勞動產品)的異化”[13]43。
數字勞動與信息技術生產力一起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整體異化”。那么該如何突破這種整體異化呢?福克斯根據馬克思關于勞動與工作的劃分,提出與數字勞動相對應的“數字工作”(digital work),相比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互聯網公司,數字工作發生在“由直接用戶集體擁有和控制的”[13]448工人階級社交媒體,這些社交媒體的最大特點是“以非商業和非盈利為導向”[13]448。在福克斯來看,世界互聯網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它可以在數字勞動的殘酷剝削中深化媒介資本積累;也可以“發展成一個由日常用戶共同創造和控制的工人階級的互聯網”[13]452,這樣“基于公有的互聯網將是一種真正的社會媒介”[13]452。值得肯定的是,福克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互聯網平臺中看到了私有制的局限性,進而提出了基于公有制的互聯網平臺,這是符合社會發展未來趨勢的。然而,這樣的公有制互聯網是抽離了商品經濟和資本關系的理想世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29]9-10。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因社會化大生產與私有制不可調和的矛盾而走向崩潰,但這個結果絕不是由強行抽離商品經濟和資本關系來取得的,福克斯借由馬克思核心范疇構建起來的數字勞動理論體系也因此成為一種空洞的共產主義暢想。
比較而言,奈格里和哈特關于非物質勞動的論證既離開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又陷入知識無產者主體革命的主觀性困境。福克斯在信息生產力邏輯上構建的數字勞動異化理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存在三個不可忽視的理論問題:其一,對工作與勞動的區分,如果福克斯看到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受馬克思勞動概念影響在亞里士多德“制作”概念基礎上作出的勞動、工作、言說的區分,可能就不會出現這種僅停留于詞義的工作與勞動的劃分,將使用數字媒體的“玩”說成是工作的異化,以及把勞動全部作為異化來處理是不恰當的。其二,生產力系統的異化未能在資本統治社會生產力的邏輯上來論證,甚至還回到未形成科學勞動價值論的青年馬克思的人本學邏輯,這是一種不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體系的異化從根本上來說是科學技術在資本的操縱下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形成全方位控制的表現[30]。其三,奈格里、哈特以及福克斯都因遠離科學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而陷入一種不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總體上來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生產力理論在奈格里和哈特的自治社會主義、福克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再次出現,但是概念詞匯的重復出現絕非理論意義的一以貫之,這樣先“回到馬克思”又“偏離馬克思”的做法終究無法真正解決數字勞動理論難題。
三、在數字科技生產力的發展中探尋勞動真相
西方學者所發起的數字勞動概念爭論,在敞顯這一概念本身問題的同時也凸顯了對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學習研究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對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具有積極作用。”[31]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大的距離,但這些西方學者置身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提出的一些創新性概念對于我們認識現代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奈格里和哈特、福克斯以非物質勞動和數字勞動指代信息技術變革下的勞動范式轉換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們對社會生產力的結構性變化及異化的闡釋,卻沒有在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上來論證。面對信息技術給生產生活帶來的“格式塔”般的變革,真正地“回到馬克思”要求從生產力總和決定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上來審視數字勞動,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科學技術生產力發展下的知識勞動來審視數字勞動的屬性、內涵、特質等才更具科學性,這樣更符合一定社會歷史條件限制下的數字勞動從屬于知識勞動的本質屬性。
(一)基于“一般社會知識”的知識勞動在大工業生產力中居于統治地位
在唯物史觀視界,數字勞動是從馬克思所處時代的以“一般智力”為標識的機器體系發展而來的知識勞動,生產勞動之外的聽音樂、看電視、線上購物等休閑活動不屬于數字勞動的范圍。奈格里和哈特、福克斯等人從“一般智力”來立論數字勞動的生產力屬性有合理性一面,但為了反駁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所堅持的后工業社會理論,知識勞動概念沒有在他們的理論中著重凸顯。有學者考證馬克思的所有文本中只有一次使用“一般智力”概念[32]。怎樣理解“一般智力”?按照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史的論述,機器是從生產資料轉化而來的固定資本,是自然科學應用的技術化結果,也就是“過去的勞動”成果運用于商品生產。馬克思從這一意義上說,“一方面,直接從科學中得出的對力學規律和化學規律的分解和應用,使機器能夠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樣的勞動。然而,只有在大工業已經達到較高的階段,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的時候,機器體系才開始在這條道路上發展;另一方面,現有的機器體系本身已經提供大量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發明就將成為一種職業,而科學在直接生產上的應用本身就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性的和推動作用的著眼點”[27]99。科學向機器體系轉化的中介是技術,而技術又是使科學原理獲得機器物質外殼的手段。科學原理一旦獲得技術的物質外殼,機器就具備了生產力屬性,如此,馬克思在《手稿》中說“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27]94,在《資本論》中進一步說明“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29]418。
從文本上看,馬克思有時用科學包含技術,有時用科學和技術來闡明機器體系作為固定資本的生產力,這也構成科學技術或科技生產力的話語來源。實際上科學和技術處于不同層面。科學一般指觀念的、學說的、推理的理論知識,而技術的早期是制造技藝,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制作—技藝”。基于經驗的制造工具及其使用的工藝活動貫穿人類歷史,到大工業時期雖然經驗的技藝并未消逝,但科學原理與制造機器的技術構成一對辯證關系,即從科學原理的技術化和應生產生活的技術要求創新理論相互促進,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作為生產能力的具象化也就具有生產力的屬性。哈貝馬斯最早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位的生產力[33],就是從科學和技術已經構成“體系”途徑來說的。實際上,馬克思在機器體系的論述中已經指出了這樣的認知,“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是取決于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一切科學的發展,本身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27]100。從這一方面來說,“一般智力”可以理解為科學技術水平所決定的現實生產力,但這里的科學是以自然科學為主同時也包括社會科學。顯然,“一般社會知識”與“一般智力”相等同,這是馬克思在“工藝學”語境實現的。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時,高度關注拜比吉、尤爾等這些非典型經濟學家的工藝學的著作,他們在人與機器體系關系方面所構建的工業心理學對馬克思超越斯密、李嘉圖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說大工業作為對象性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34]192。這里的心理學是指人的創造性勞動喚起自然力的本質性力量和生產過程中分工與協作的力量的總和,在這個總和中生產“一般智力”的知識勞動居于統治地位。
(二)在資本邏輯下的社會生產力中審視知識勞動的實質地位
知識勞動是基于“對象化的知識力量”的概念化表達,它居于生產過程的統治地位,但在社會生產力結構中就成為“資本生產力”的條件和總體生產過程的環節。在關于生產力概念的討論中,一般認為馬克思沒有對生產力做出總體的明確的界定。誠然,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因論證主旨不同而使用個人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力、集體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大工業生產力、主體生產力、客體生產力等。實際上,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闡述“社會不可選擇”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不可選擇”時強調了生產力是“應用能力”[35]。所謂“應用能力”,即運用智力、體力、自然力的總和。這應當確認為馬克思總體的生產力概念。這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對生產力的兩處論述是一致的。在一般意義上,“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29]59,這可以說明生產力與勞動生產力相等同,同時也說明效率是衡量不同生產部門生產力的尺度,還可以區分個別生產力與社會生產力。馬克思指出了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29]53。這些決定因素被理解為權威的生產力“五要素”而區別于“二要素”“三要素”說[36]。由此可以確認,對個體勞動者來說,勞動生產力是勞動者智力和體力的總和,從物質生活資料生產能力來說,勞動生產力是勞動主體運用智力和體力制造生產工具塑形自然之物轉為生產和生活資料的能力,是構成性的關系存在。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生產力相等同,但這不是個別生產力的簡單相加,而是“社會”條件下的“結合”形式所構成的結構。社會不是結晶體而是人們相互作用的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社會關系的經濟基礎,生產力的各要素構成生產關系的物質載體,因此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以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對生產力也有反作用。社會生產力是構成性的,是社會再生產的問題。馬克思指出:“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27]102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產過程中,“資本生產力”占據總體性的統治地位,科學和技術勞動已經成為資本生產的環節,“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而科學反過來成了生產過程的因素即所謂職能。……資本不創造科學,但是它為了生產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37]。也就是說,雖然知識勞動在構成性的社會生產力結構中占統治地位,但是知識勞動在生產關系上實質從屬于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生產力的典型體現。
(三)在精神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的辯證關系中把握知識勞動
馬克思恩格斯在首次闡發唯物史觀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了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人的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之后,深刻闡釋了人的“意識”[34]531-533。這種以人的存在為對象的“關系意識”,是人類在創造社會歷史的同時超越動物的顯著標志,其特性在于“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34]534。馬克思恩格斯在分工和所有制的歷史邏輯上分析了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分工具有的決定意義,在《大綱》中明確把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并列使用,并指出統攝了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解體“只有在物質的(因而還有精神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才有可能”[38]。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深刻批判庸俗經濟學家忽視精神勞動的問題。庸俗經濟學家們以資本生產力的獨立性來解釋剩余價值,馬克思則深刻指出科學向生產工藝轉化是資本生產力的前提,作為固定資本的機器體系就是機械化時代生產工藝的凝結,通過使用機器來提高效率進而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資本家贏得競爭的必然選擇,這一效率提升的過程就是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雙重消耗過程。但這些庸俗經濟學家對以上經濟事實選擇視而不見,所以馬克思指出“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只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39]348。庸俗經濟學家的看法來源于斯密關于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分,根源還在斯密。斯密對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以是否創造商品價值來區分固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但以物化形態作為非物質生產的尺度又是錯誤的。馬克思指出,因為斯密考察的是物質財富生產,“在精神生產中,表現為生產勞動的是另一種勞動,但斯密沒有考察它……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和內在聯系只有在物質生產就其自身的形式被考察時,才不致流于空談”[39]345。在斯密看來,知識勞動不是直接的穩定的物化的物質財富,而是將其作為非物質生產勞動隱匿掉。在馬克思看來,非物質勞動不只是斯密所說的家仆的服務勞動,還包括科學技術的、文化的勞動,這些只要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所以斯密不會考察資本生產過程的非物質勞動與物質勞動的辯證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同時,揭露了資本家通過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降低固定資本投入、提高機器性能來達到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是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一起”[40]的。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論證邏輯上知識勞動作為精神勞動具有兩種形態存在,即直接滲入商品生產過程的和在商品生產之外的勞動。前者作為被資本家購買的知識勞動力直接參與商品生產,后者則作為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器官的獨立力量而存在。當然,就知識勞動的直接的現實與潛在生產力來說,那些還未轉換為直接使用的生產力的知識還是潛在的。
總的來說,一方面,從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發展邏輯上來看“數字勞動”概念,其屬性是知識勞動,其中科學技術勞動占主導地位。就數字勞動的領域來說,福克斯所界定的廣義數字勞動行業鏈條過長,采礦和計算機材料加工不是數字勞動的范疇;看廣告、刷視頻、聽音樂等既不是勞動也不是數字勞動。數字勞動應限于信息和通信領域的知識創新及其應用和管理勞動。數字勞動屬于知識勞動,并不是知識勞動的全部,并且是否居于知識勞動的統治地位仍需進一步討論。另一方面,就數字勞動的異化問題來說,觀照抽象資本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是合理也是必要的,但數字勞動異化的根源在于資本生產力統攝下科學技術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勞動的異化,對數字勞動異化的根本性揭露不應離開馬克思關于資本與科技生產力關系的辯證理論。
四、結 語
在思想家們的文本中學術概念具有規范、創新、再規范的特點,相同術語的歷史連續并不意味著內涵和外延等同,運用概念科學反映事物本質以及內涵的與時俱進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態度。綜合來看,數字勞動指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理論背景下,伴隨數字技術變革而出現的與通信和信息技術(ICT)相關的各類生產勞動和使用數字設備的人類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和自治社會主義的理論努力告訴我們,資本已然滲透到傳統生產領域和非生產領域中,進入人們的情感、休閑和娛樂生活,因此完全忽視信息技術革命下生產勞動和生活方式“格式塔”般的變化是不可能的,但同樣貿然構建新的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力理論不僅無法徹底洞悉數字勞動的本質,還有可能破壞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科學性與革命性。從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總和”決定社會歷史規律的理論路徑上審視知識勞動,尤其是數字科技勞動所蘊含的蓬勃生產力是當代高效能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數字勞動的生產屬性本質上來源于知識勞動。在非生產領域,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和自治社會主義者對科技異化的警醒值得我們關注,但將人們使用數字設備的休閑活動直接歸屬于勞動是不合理的。不論是科學技術生產力還是人們復雜的知識勞動生產力只是提供創造價值的可能性,而不提供創造價值的現實性,數字勞動發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使同一活動在不同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下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我們不能苛求馬克思將數字化生存時代的問題全部預設并解決,以制度保障科學技術生產力和知識勞動生產力的最大程度發揮、規避資本對生產生活的侵蝕是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著重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吳歡,盧黎歌.數字資本與剩余價值規律的新表現——數字經濟時代馬克思資本理論的再闡釋[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10-17.
[2] 付文軍.數字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J].江漢論壇,2021(8):40-47.
[3] 孟飛,程榕.如何理解數字勞動、數字剝削、數字資本?——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J].教學與研究,2021(1):67-80.
[4] 劉偉杰,周紹東.非雇傭數字勞動與“數字化個體”——數字經濟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嬗變及啟示[J].西部論壇,2021(5):34-45.
[5] 曲佳寶.數據商品與平臺經濟中的資本積累[J].財經科學,2020(9):40-49.
[6] 藍江.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的數字勞動批判[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11):73-83.
[7] 溫旭.對數字資本主義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辨析[J].思想理論教育,2022(6):46-51.
[8] 孫蚌珠,石先梅.數字經濟勞資結合形式與勞資關系[J].上海經濟研究,2021(5):25-35.
[9] 余斌.“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5):77-86.
[10] 吳靜.算法吸納視域下數字時代勞動新探[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8-15.
[11] TERRANOVA T.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Social text,2000(2):33-58.
[12] 毛里齊奧·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上)[J].高燕,譯.國外理論動態,2005(3):41-44.
[13]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4] SMYTHE D.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J].Canadiam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7(3):2-21.
[15] 丹·席勒.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M].馮建三,羅世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4-5.
[16]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王爾勃,周莉,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11.
[17]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馬克思歸來:上[M].“傳播驛站”工作坊,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18] 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楊建國,范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9] HARDT M,NEGRI A.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108.
[20] POSTER M.Hardt and Negri’s information empire:A critical response[J].Cultural politics,2005(1):101-118.
[21] 肖恩·塞耶斯.現代工業社會的勞動——圍繞馬克思勞動概念的考察[J].周嘉昕,譯.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7(1):33-41.
[22]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23] 大衛·哈維.解釋世界還是改造世界——評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J].王行坤,譯.上海文化,2016(2):49-59+64.
[24] 張一兵.非物質勞動與創造性剩余價值——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國》解讀[J].國外理論動態,2017(7):35-48.
[25] 謝芳芳,燕連福.“數字勞動”內涵探析——基于與受眾勞動、非物質勞動、物質勞動的關系[J].教學與研究,2017(12):84-92.
[26] 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張梧,孟丹,王巍,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8] 張厲君.普遍智能與生命政治——重讀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斷》[G]//許紀霖.帝國、都市和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155-156.
[29]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0] 朱春艷,王卓倫.數字時代拜物教的癥候分析與可能消解路徑[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6):133-143.
[3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5.
[32] 孫樂強.馬克思“機器論片斷”語境中的“一般智力”問題[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10-18.
[33]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62.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43.
[36] 衛興華,田超偉.論《資本論》生產力理論的深刻內涵與時代價值[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7(4):21-31.
[3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6-357.
[38] 張一兵.經濟學革命語境中的科學的勞動異化理論(上)——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研究[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2):47-62.
[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0]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6.
How Does Digital Labor Become Labor?
An Analysis of the Argumentative Logic of the Western Marxist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
Abstract: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as an innovative notion from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has introduced to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together with similar concepts such as audience commodity,free labor,immaterial labor,and play labor. Upon its introduction,it quickly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Chinese scholars,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concepts like digital commodities,digital necessary labor,digital surplus labor,and digital surplus value. Consequently,research related to digital labor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However,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where capital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re intertwined,it is insufficient to merely follow Western digital labor theories. Instead,we must engage in a “calm reflection” after the theoretical clamor,conducting a horizont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and connotations of digital labor and immaterial labor concepts. Vertically,we should delve into the theoretical objectives and argumentative frameworks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autonomous socialism. This dual approach will facilitat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encompassing both its existence and its underlying principles.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se concepts reveals that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alian autonomous socialism,in response to capital’s encroachment into the emotional,leisure,and entertainment lives of individuals,collectively opt to “a return to Marx.” They construct their social critique theories using the core categories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However,the result often deviate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ue to misunderstandings or distortions of Marx’s core concepts. Overall,i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autonomous socialism,the appearance of Marx’s core concepts paradoxically signifies the fundamental retreat of Marxist theoretical scientificity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A genuine “return to Marx” necessitates examining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aws determined by the “aggregate of productive forces.” Correctly recognizing the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and knowledge lab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s essential for unveiling the attributes,connotations,and essence of digital labor.
Key words:digital labor;immaterial labor;Christian Fuch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knowledge labor;labor alie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