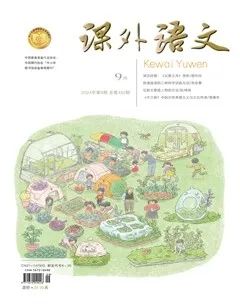學習《吶喊》,體會閱讀寫作“一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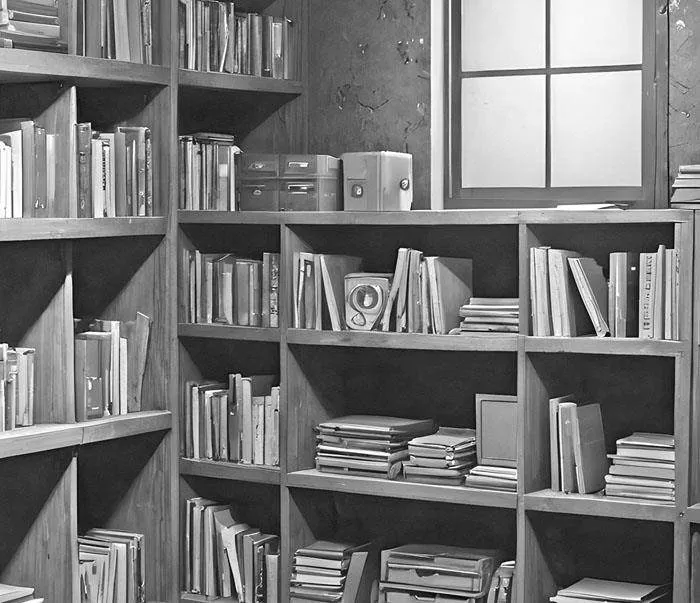
“閱讀”與“寫作”,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葉圣陶曾經說過“閱讀是‘吸收’的事情,從閱讀,咱們可以領受人家的經驗,接觸人家的心情;寫作是‘發表’的事情,從寫作,咱們可以顯示自己的經驗,吐露自己的心情”。從表面上看,閱讀與寫作是關于“輸入”和“輸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學活動,但事實上,兩者內在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正是閱讀決定了寫作的起點,而寫作也同樣成就了閱讀。就拿魯迅在寫《狂人日記》時的情況來說,其揮灑下的筆墨也盡數是“仰仗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那時,俄國以及東北歐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涌入中國,激發了“五四”一代人的愛國熱情,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為主的文學革命者以徹底決絕的姿態扛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紛紛從外國文學中汲取反壓迫反侵略的革命思想與文學技巧,并創作出了諸多流傳至今仍有振聾發聵之效的佳作。可以說,若無這百來篇外國作品,魯迅最終也難將那從中習得的“小說作法”運用得爐火純青,使其小說中所體現出的人、事、物達到活靈活現的地步,為后代人從《吶喊》《彷徨》中讀出那個時代的革命激情提供富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一、閱讀《吶喊》,學會塑造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魯迅曾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為了喊出五四時期反帝反封建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的“最強音”,《吶喊》塑造了眾多個性鮮明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如淪亡的孔乙己、被斬首的夏瑜、麻木不仁的阿Q、封建禮教的犧牲品閏土……各色人物呈現出了在封建制度殘害之下扭曲的人性以及卑劣的靈魂。那么,我們要如何學習魯迅塑造人物的手法為寫作服務呢?尤為重要的一點便是還原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環境是人物性格形成和發展的基礎,脫離環境的人物形象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物形象的特征實際上就是對人物所處時代環境的反映。就拿魯迅筆下的“阿Q”形象來說,他是一個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落后農民的典型形象。作為未莊社會里無田無地、孤苦伶仃,生活充滿了屈辱和痛苦的一個小人物,阿Q終日過著居無定所、顛連困苦的生活,遭受著被人侮辱謾罵甚至是無厘頭的毒打。在嚴重的封建經濟剝削以及封建政治壓迫之下,阿Q便逐漸形成了自尊自大、自欺欺人等鮮明的個性特征。但作者在塑造這一形象時并沒有對其身份做出詳盡的解說,而是將他作為一個連接著社會各階層乃至城鄉的紐帶進行描繪,這說明作者沒有把他看作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是上升至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的高度,突出了其“精神勝利法”的普遍適用性,從而顯示出時代背景之下人物形象的共同特點。個性化與典型化就這樣既矛盾又統一地交織在阿Q的身上,使我們感受到了魯迅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對時代環境因素所做出的深沉思考。
二、閱讀《吶喊》,領悟別具特色的敘事結構
魯迅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和思想家,可以說中國現代小說在他手中開始又在他手中成熟。《吶喊》中的許多篇章都體現出了魯迅在敘事結構上的精巧構思:離去—歸來—再離去,“看”與“被看”是魯迅小說最常見的兩種敘事模式,無一不具有匠心獨運的韻味。例如,《在酒樓上》就采用了“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歸鄉模式。從表面上看是“我”回歸到故鄉當中,實際上則暗含著呂緯甫“精神歸鄉”的另一條線索,兩者交相呼應,形成了一個復調。小說中的情節伴隨著兩個經歷、身份相似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的對話而展開,其中之一便是呂緯甫。他是一個曾經終日探討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進步青年,這是呂緯甫對于封建舊道德與舊禮教的“離去”。但如今他卻變成了教“子曰詩云”的先生,這又是對封建舊道德與舊禮教的“回歸”。這一來一往、一離一歸與魯迅思想中矛盾的兩個側面相呼應,體現出知識分子在“沖決與回歸”之間的徘徊和迷惘,開拓出更深層次的閱讀體驗。
而在我們實際的寫作過程中,同樣可以學習魯迅寫作中的層級性敘事結構寫法,將情節劃分成不同的層次,有主有次,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不同情節之間的關聯性,構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例如在《孔乙己》這一篇文章中,作者所采用的是“看”與“被看”的敘事結構,其中一共設置了三層“看”與“被看”。首先,孔乙己與酒客之間就形成了一層“看”與“被看”。孔乙己自認為是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身份與他實際的“被看”地位——充當人們無聊生活的笑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中讓人為那個年代知識分子荒誕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遭遇感到唏噓不已。其次,魯迅并沒有選擇孔乙己或者是酒客來充當敘述者,而是讓酒店里的小伙計來充當,以旁觀者的視角同時觀察孔乙己和酒客之間的互動,這樣便形成了第二層“看”與“被看”。最后,隨著情節的向前發展,小伙計也參與到故事當中去,而在這一切的背后又有一個神秘的“作者”在看,形成了最后一層“看”與“被看”。從總體上來說,這三層“看”與“被看”形成了既非單一又是動態的敘事結構,層次感和整體性極強。若我們能夠在寫作過程中對不同的情節做出安排,勢必會大大增強故事的內在邏輯性,在反復推敲之后使文章散發出非同凡響的藝術魅力。
三、閱讀《吶喊》,體會語言運用的魅力
品讀這本小說集中的語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其古典美和詩意美。從古至今,數不盡的文人追求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在魯迅的《吶喊》中得到了突出顯示。可以說,魯迅善于將詩歌的韻味融入到小說創作之中,融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從而使作品的字里行間都洋溢著濃濃的詩意。例如在《社戲》中寫道“像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起伏的連山”,《狂人日記》中富有象征性、蘊藉性的事物等,二者都營造出一種如詩歌一般含蓄朦朧的意境,也正因如此,許多人將魯迅的小說稱作“敘事詩”。
回歸到初中階段的寫作來說,文章的優秀與否往往與我們對語言的雕琢和推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為了尋求更高水平的評價,不少學生都會盡可能多地采用修飾語、關聯詞等來建立語言之間的聯系,以求達到讀者對于美的期盼。但在超過一定的限度之后,便可能會給人一種雕琢繁蕪之感,有失水準。這主要歸結于我們對寫作語言的錯誤認知,只一味地將細膩、華美看作評價語言運用水平的唯一標準,殊不知語言的準確、凝練、精當往往會比繁復更具魅力。正如在初讀《吶喊》之時,我們可能總感覺字字句句都寡淡無味,無甚咀嚼之必要。但實際上,魯迅文中之語并非未經雕琢的,而是將描寫與諷刺熔于一爐,不露聲色地展現出語言的力度美。即使是普通的幾個動詞,也能夠連成富有動感的畫面,引人入勝。正如《藥》中 “(康大叔)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寫了康大叔在擔心華老栓反悔的心理之下迅速將人血饅頭“塞”給他的情節。魯迅并沒有贅述,對“迅速地”“趕快”等副詞進行修飾,反而是略去細節,直接抓住主干,一連用四個簡潔利索的動詞,展現出康大叔動作之敏捷迅速,從而間接令人體會到其貪婪的劣根性。語言生動流暢,絲毫不拖泥帶水,給人以一氣呵成之感。如此我們在閱讀《吶喊》之時,自會感受到其語言運用的獨具匠心之處,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傳統的文學創作觀念,自覺打磨寫作技巧,為語言文字的精雕細琢和反復推敲提供借鑒。
閱讀是永無止境的。不可否認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短暫的一生中窮盡人類文學長廊中包含的所有文學養料。究其根本,在于總是有人在不斷地將閱讀的感悟轉化為寫作的動力,以富有個性的創作豐富著文學寶庫。保持對閱讀與寫作的喜愛是發現生命美好與希望的精神動力。正如吳晗所說:“讀書是學習,摘抄是整理,寫作是創造。”閱讀和寫作之間的距離說近不近,說遠也不遠,卻需要我們用一生的熱愛去踐行,不畏閱讀之艱澀、寫作之困頓,從而經歷磨煉,最終達到文學至境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