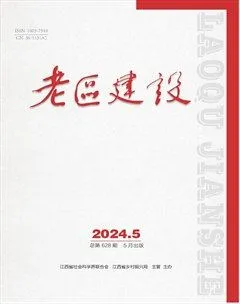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機理及路徑
摘 要:湖北省鄉村地區革命文物眾多,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有助于延伸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場域,提升文化內涵,擴大社會影響和推動革命教育。目前,湖北省依托革命文物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過程中存在社會主體協同參與不夠、革命文物開發方式單一、革命文化深度嵌入乏力、革命教育虛化現象頻現等問題,需從圍繞協同治理統籌建設主體、聚焦迭代創新優化建設方式、立足革命文化完善建設主題、著眼革命教育豐富建設內容等方面優化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路徑。
關鍵詞:革命文物;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革命老區
中圖分類號:G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7544(2024)05-0079-09
《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提出“依托革命文物開辟公共文化空間、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1]。革命文物作為革命歷史的遺物和遺跡,承載著黨和人民英勇奮斗的光榮歷史,是弘揚革命文化、傳承紅色基因的重要載體,依托革命文物建設公共文化空間、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意義重大。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湖北省鄉村地區曾是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留下了大量寶貴的革命文物。[2]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持續深入,湖北省鄉村群眾基本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滿足,相關公共文化服務需求不斷攀升,依托革命文物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十分必要。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有助于鄉村地區革命文物的活態保護,推動提升革命文物保護利用效果,也有助于豐富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類別,促進革命文化、紅色基因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不斷滿足革命老區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總之,響應國家政策導向,依托革命文物開辟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推動革命老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時代命題,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目前關于依托革命文物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專題研究較少,但圍繞紅色文化資源、革命文化等融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研究較多,主要集中在融入問題、融入路徑及相關功能。在融入問題上,多集中在紅色文化、革命文化的功能釋放和作用發揮,如高春鳳認為部分傳統村落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未能充分發揮紅色文化資源的作用[3]。在建設路徑上,賀芒等以某地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為例,認為組織以紅色文化為主題的活動能夠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4];傅瑤認為紅色旅游是鄉村紅色文化空間的建設載體,能傳承紅色精神、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解決鄉村文化空間建設空心化問題[5];楊麗新以文化宮為例,認為村群體大多有著深刻的革命記憶,以此為基礎將紅色歌曲融入其中,有助于提升鄉村文化產品的吸引力和可觀賞性[6]。在相關功能上,賀一松等以村落祠堂的公共文化空間為例,認為村落祠堂的傳統功能弱化,形成了包括紅色文化教育在內的多項時代功能,對于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具有指導意義[7];耿達等以銀河村銀河文化空間為例,認為鄉村文化空間承擔著紅色黨建等功能,是重要的紅色文化場所[8]。總之,在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大多以紅色文化資源、革命文化為研究對象探討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以革命文物為研究對象的較少;在研究內容上,現有研究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問題、路徑等為主,系統性探究以革命文物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機理和路徑較少。革命文物作為鄉村生活及鄉村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構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重要載體,亟需開展相關研究以加快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進程。基于此,本研究以湖北省為研究個案,嘗試探討依托革命文物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機理和路徑,提升革命文物保護利用效果,滿足鄉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
一、革命文物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概念
(一)革命文物
革命文物一詞較早出現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征集革命文物令》,被認為是“一切有關革命的文獻和實物”[9]。隨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護歷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關于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等文件中[10-11],革命文物的界定從可移動文物擴展到不可移動文物。1989年,在全國革命文物宣傳工作會議上,革命文物被認為是“1840年以來歷次革命斗爭的遺址、紀念性實物和遺物,是全部歷史文物的重要組成部分”[12]。2016年,國家文物局頒布《關于加強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指出“革命文物是我國文物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深厚滋養,是弘揚革命傳統、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13]。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國家文物局關于印發〈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的通知》等文件對革命文物內涵進一步明確,指出革命文物承載著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史,展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革命歷程,是革命文化的載體,在愛國主義教育、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4-15]。總的來說,革命文物被認為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中形成的可移動的或不可移動的遺物和遺跡,承載黨和人民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革命風范。革命文物源自革命歷史,歷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積累了豐厚歷史價值、教育價值、經濟價值和藝術價值,是豐富公共文化內容、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有效支撐,更是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方式。
(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較早提出“文化空間”概念,2000年我國學者王列生在《文化的貧困與文化的解困》中較早提出了“公共文化空間”一詞。[16]相較于文化空間,公共文化空間側重于從“公共性”的角度出發,強調空間的開放性以及公眾的可進入性、可參與性,注重“文化性”和“公共性”相結合。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提出“加強各級各類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打造新型城鄉公共文化空間”[17],強調“創新公共文化管理機制和服務方式,推進文化惠民工程互聯互通、一體化發展”[18],進一步豐富了公共文化空間內涵。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公共文化空間思想的延伸,是鄉村文化生產和供給的重要基地,是推動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有效支撐。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大家的日常生活都在鄉村這個公共空間里開展,鄉村因此成為中國社會最為基礎、最為傳統的公共文化空間單元。[19]隨著研究和實踐的深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概念逐漸清晰,一般被認為鄉村群眾在特定的場所,利用公共文化資源開展文化生產、文化享受,承載著鄉村群眾的文化記憶,展示著鄉村社會的獨特魅力[20-21]。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類別越發多樣,主要包括物質、心理和意識文化空間,涉及文化廣場、農村書屋、鄉村祠堂、文化禮堂、農家茶館、文化戲臺等多個場所。
二、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機理
(一)延伸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場域
革命文物是與革命歷史有關的遺物和遺跡,包括革命舊址、革命紀念館、革命志士故居等不可移動文物,以及革命書信、革命旗幟、革命標語等可移動文物。從革命文物的構成來看,利用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都能推動建設不同類別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延伸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場域。一方面,大型的革命舊址、紀念館等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載體。湖北省部分鄉村地區的革命舊址、紀念館等在規劃和建設過程中,常以鄉村群眾的公共服務為導向,無償提供革命歷史推廣以及相關讀書學習、影視觀賞等服務,這在本質上就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一些可移動文物或小型的不可移動文物,也可推動建設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微場域。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不僅僅只有大型的、能夠容納多人的文化廣場、農村禮堂等,還有通過革命書信、革命徽章等構建的微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以滿足不同鄉村群眾的文化需求,如隨著數字技術賦能革命文物,促使革命書信、革命徽章等在虛擬文化空間集聚,延伸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微場域。
(二)提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內涵
革命文物是中國近現代革命運動的重要產物,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見證者,積累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以文化內容為核心的特定空間場所,集聚了休閑閱讀、藝術活動、文化沙龍、創意生活等多項文化活動,將革命文物融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有助于提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內涵。一方面,革命文物豐富了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內容。革命文物在演化發展中累積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既展現了革命年代的重要歷史敘事,也見證了和平年代的文物保護歷程。將革命文物融入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讓參觀者認知文物背后的革命故事、感受文物保護傳承的艱辛歷程,推動豐富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內容。另一方面,革命文物提升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價值。革命文物從初步形成到演化發展,歷經多個歷史階段,具有豐富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教育價值等文化價值屬性。革命文物融入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充分發揮革命文物的文化價值屬性,助力提升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內涵。
(三)推動擴大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社會影響
革命文物源自革命歷史,承載著大別山精神、長征精神、抗戰精神、中原突圍精神等寶貴革命精神,展現了近代以來中華兒女在反帝反封建道路上的堅定不屈、艱苦奮斗、開拓進取等品質,尤其是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運動中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救國救民的偉大理想等。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鄉村文化的供給場所,是鄉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載體,將革命文物中蘊含的革命精神融入湖北省鄉村文化供給中,幫助提升鄉村人民群眾對于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踐行,激勵鄉村人民群眾賡續紅色血脈、傳承革命精神,助力提升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社會影響。具體來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在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留下了大量寶貴的革命文物,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及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新中國成立后,革命文物所承載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逐漸轉化為地區的文化標識,成為新時代鄉村人民生產生活的精神內核。將革命文物融入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能夠喚醒廣大鄉村人民的革命精神情結,促使人民群眾主動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生活,積極傳播新時代鄉村建設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風尚,提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輻射范圍和影響效果。
(四)強化革命文物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黏性
利用革命文物開展革命教育是對革命歷史的宣傳和對革命精神的傳承,是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的核心要義,也是鄉村公共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以革命教育為紐帶,能夠有效聯結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和鄉村公共文化建設,促使革命文物更好地融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進程。一方面,革命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斷提升,促使革命文物保護利用與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趨向深度融合。隨著黨史學習教育、主題教育等的開展,革命教育迅速成為相關活動的重要內容,革命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快速提升,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得到進一步強化。另一方面,在數字技術賦能下,革命教育方式不斷創新,為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提供新機遇。在數字技術的形塑下,革命教育的課堂設置、授課時間等發生變革,如Web3.0、云空間、虛擬網絡逐漸成為開展革命教育的有效方式。隨著革命教育方式變化,諸多鄉村革命文物被移到線上云端,有助于提升革命文物保護利用效果,推動打造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新范式。
三、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困境
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在建設主體、建設內容、建設方式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優化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進程中,相關建設主體、建設方式、建設主題、建設內容等仍存在諸多問題。
(一)建設主體方面:社會主體協同參與不夠,造成公共文化服務的供需壁壘
社會主體協同參與是匯集社會各界主體力量推動革命文物參與鄉村公共文化內容供給,以滿足鄉村群眾公共文化服務需求。近年來,在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引導下,社會各界對鄉村公共文化內容供給的支持度和參與度持續提升,極大地改變了以往僅靠文物保護單位或基層鄉鎮、社區、村委會等開展相關建設的局面。由于社會主體在人員組織、機構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參差不齊,造成社會力量形成的合力不強,容易產生公共文化服務供需壁壘。如在鄂西北山區部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來自武漢、襄陽等城市的企業家聯盟、志愿團體利用革命文物積極開展紅色文化宣傳、革命歷史普及等公共文化活動,但由于部分社會主體臨時性介入,對于鄂西北革命歷史、大巴山地區風土人情等認知深度不夠,照搬武漢、襄陽等平原居民的傳統慣例,導致不同主體間的活動內容同質競爭、活動內容與山區群眾需求錯位,使得相關公共文化活動的供給和需求存在隔閡,產生供需壁壘,造成活動“熱鬧多”,百姓“掌聲少”,不利于革命文化、革命宣傳等相關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的持續開展。
(二)建設方式方面:革命文物開發方式單一,造成保護利用與公共文化服務疏離
革命文物開發方式是在有效保護基礎上對革命文物形態和價值的再挖掘、再接續。通過拓展革命文物開發方式,將革命文物開發與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有機融合,能夠推動革命文物保護利用,豐富公共文化服務內容。然而,湖北省部分鄉村在公共文化空間建設過程中,對于革命文物的開發方式較為單一,常常停留在革命文物的形態維護、歷史宣傳等,以革命文物為核心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開發方式不多。如鄂西民族地區的部分鄉村嘗試挖掘湘鄂西根據地內革命舊址的歷史脈絡、文化價值,推動打造鄉村文化宣傳基地,但是革命舊址開發利用重點常常落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物理空間建設上,未能結合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特色構建適宜的活動空間、精神空間,容易造成革命文物保護利用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兩張皮”。這種較為單一的開發模式,表面上看推動了革命文物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但實質上很難對基層群眾生發出自然的、長久的吸引力,導致革命文物保護利用與公共文化服務疏離。
(三)建設主題方面:革命文化深度嵌入乏力,造成公共文化服務的精神內核趨弱
革命文化深度嵌入是將革命文物所承載的革命文化有機融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各個維度,逐漸形成以革命文化為核心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主題,推動革命文化成為相關公共文化服務的精神內核。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迫切需要將革命文物所承載的革命文化嵌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讓鄉村群眾在公共文化空間中感知革命歷史、感受革命精神,提升鄉村群眾在大變局中的定力和辨別力。然而,湖北省部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對于革命文物的理解不到位,導致革命文化深度嵌入乏力,造成公共文化服務精神內核趨弱。如鄂東大別山地區部分鄉村盲目照抄武漢等附近大城市地區革命文化開發利用經驗,缺乏對鄂豫皖根據地革命文物的系統整理及文化挖掘;精英俘獲現象嚴重,只注重開發土地革命時期鄂豫皖根據地內名聲較大、保存較好的革命文物,對中共創建初期、抗日戰爭等時期形成的革命文物開發利用不足。這些開發方式不利于深度挖掘本地革命文物所承載的革命文化,容易造成革命文化與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割裂,很難形成以革命文化為核心的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主題。
(四)建設內容方面:革命教育虛化現象頻現,造成公共文化服務的教育向度失衡
革命教育是利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對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教育,是依托革命文物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利用革命文物開展多樣化革命教育,有助于滿足鄉村群眾的文化娛樂、精神享受等需求,也有助于推動實現以文化人、移風易俗等目標,從而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在價值,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長效化發展奠定基礎。當前,隨著革命教育逐漸成為國家文化安全以及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其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規劃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湖北省部分鄉村地區嘗試將革命舊址、革命遺跡等打造成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然而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和運營中,革命教育存在虛化問題。如鄂中曾經是鄂豫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首府,相關革命文物是中小學生、社會成人開展抗戰精神教育的重要支撐。該地部分鄉村嘗試利用新四軍第五師相關革命舊址開展中小學生抗戰精神教育活動,但相關活動缺乏常態化、長效化的規劃和執行;部分地區將革命教育焦點放在中小學生身上,針對社會成人開展抗戰精神教育的規劃和實踐不足,革命教育虛化現象容易造成公共文化服務的教育向度失衡。
四、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路徑
(一)圍繞協同治理統籌建設主體
協同治理是多元化利益相關主體在特定規制和目標下,相互配合、協力合作,推動實現過程高效、結果高質。當前,隨著社會各方力量參與到革命文物保護利用以及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需要以協同治理理念統籌各方分散力量,形成強有力的建設動能。首先,以鄉村群眾需求為導向,明確建設主體協同治理的方向。協同治理的出發點之一就是厘清鄉村群眾的現實需求,明確各建設主體在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的職責。要以湖北省鄉村群眾需求為導向,通過“鄂匯辦”“最鄉村”等湖北地區人民群眾常用、常見的融媒體客戶端主動收集鄉村群眾需求,分類構建鄂西山地地區、鄂中平原地區、鄂東丘陵地區等多元化數據庫,打通建設主體與群眾需求間的信息屏障,促進破解當前供需壁壘難題。其次,以體制機制建設為前提,形成建設主體協同治理的基礎標準。體制機制是建設主體協同治理的規章制度,是維護建設主體協同治理的基礎條件。要按照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關于加強新時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湖北省革命文物保護條例》等文件規定,結合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實際,擬定革命文物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基礎標準,構建常態化、長效化實施機制。最后,以政府單位引導為重點,保障建設主體協同治理的進程。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務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對于建設主體協同治理具有重要引導作用。要以湖北省革命文物保護單位、基層鄉鎮以及社區或居委會等政府單位為核心,以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融媒體中心等官方媒介為載體,統籌社會各界分散力量。
(二)聚焦迭代創新優化建設方式
迭代創新是對現有運行模式的改革和升級,推動個體在復雜環境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當前依托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方式較為單一,限制了革命文物的效能發揮,亟需通過迭代創新優化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范式。首先,在物理空間基礎上強化心理、活動等多類空間建設,是當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方向。一方面要利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等根據地留下的大型革命遺址及相關革命紀念館建造綜合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另一方面要利用名人舊物構建微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如圍繞土地革命時期董必武、徐向前等革命領導人在鄂豫皖根據地使用過的毛筆、書信等構建微型展覽空間。其次,在感官享受的基礎上豐富群眾情感體驗。情感體驗是群眾文化需求的主要目標之一,也是公共文化服務的核心內容。要圍繞鄉村群眾情感體驗,將湖北省革命文物建設成集懷舊、革命、鄉村等元素為一體的綜合文化空間,促使鄉村群眾在感官享受的同時,最大限度獲得相應情感體驗。如根據湘鄂西根據地革命歷史,結合鄂西民族地區風土人情,將鄂西民族地區革命文物打造成以革命文化為核心、以民族風情為特色的多元化文化空間。最后,在傳統范式基礎上注重數字技術嵌入。數字技術是國家發展導向,也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技術支撐。要利用數字技術推動革命文物形態維護和價值挖掘,利用數字技術建構數字紅色文化體驗空間,推動數字化導覽、虛擬人講解、情境性再現等相互融合,為革命文物推動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奠定基礎。
(三)立足革命文化完善建設主題
革命文化是革命歷史中留下的思想、行為以及相關生產生活方式,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基礎條件之一。當前,革命文物所承載的革命文化在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革命文化嵌入力度不夠。首先,努力挖掘和整理湖北省本地革命文物及相關革命文化。湖北省革命文物是湖北地區革命歷史的重要見證和文化標識,要系統整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湘鄂川黔等根據地的革命文物,梳理地區革命文物所承載的革命文化,積極挖掘不同革命時期、革命地域的文化特色,如恩施地區的民族文化與革命文化相互交融、荊州地區洪湖水文化與革命文化相互輝映。其次,對當地革命文化的內在核心要充分吃透,推動塑造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精神內核。要認真梳理革命文物的發展歷史及相關背景,弄懂吃透地區革命文化的核心要義,尤其是本地革命文化與中國革命文化的關系,如黃石龍港革命舊址曾是湘鄂贛根據地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中央蘇區的戰略策應地,革命文化蘊含著地區人民的革命反抗精神,也飽含著地區人民與中央蘇區的血肉聯系。最后,圍繞革命文化不斷豐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主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主題具有多元化、系統性等特點,在以革命文化為基本遵循的前提下,重點將中共創建初期到解放戰爭時期所形成的革命文物融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中,避免開發過程中的精英俘獲問題。
(四)著眼革命教育豐富建設內容
革命教育是使受教育者繼承和發揚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優良作風和高尚品德,是國家主題教育活動的核心內容之一。當前,利用革命文物開展革命教育成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內容,但革命教育方式及內容存在部分問題,限制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作用。首先,圍繞革命文物蘊含的革命精神,建立常態化、長效化革命教育體系。常態化、長效化革命教育體系是革命教育得以持續開展的基礎,是推動革命文物融入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支撐,要在教育方式、教育時間等方面形成詳細的約束規制。如按照《湖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管理辦法》規定,在村規民約中約定革命教育的時間和方式,推動革命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其次,按照主題教育活動要求,擴大革命教育的社會覆蓋面。革命教育的社會覆蓋面關系到教育的影響程度及范圍,既要圍繞青少年開展革命教育活動,又要吸引社會成人參與到革命教育項目中。如孝感宣化店鎮曾是中原突圍戰役重要發生地,可利用中原突圍遺址對中小學、社會成人開展革命教育,宣傳中原突圍中蘊含的愛國主義精神、奉獻精神、協作精神,擴大革命教育的社會覆蓋面。最后,圍繞革命教育進一步豐富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內容。重點在品德教育、移風易俗、以文化人、技能學習等方面擴大革命文物參與湖北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范圍。如圍繞恩施五里坪革命遺址群、黃石龍港革命遺址群的革命歷史,將革命舊址群打造成集黨日主題活動、廉政教育、紅色研學為一體的多元化公共文化空間;利用楚劇、漢劇等湖北省代表性非遺,創作表現紅色革命歷史的作品,豐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內容。
參考文獻:
[1][15]國家文物局.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EB/OL].(2021-12-24)[2023-08-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31/content_5665933.htm.
[2]劉杰,李雁.湖北重要革命文物史跡選粹[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3]高春鳳.傳統村落公共文化空間的保護與振興策略[J].長白學刊,2019,(6).
[4]賀芒,簡娟鳳.主體互惠:平衡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生產的標準化與差異化——基于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分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1,(5).
[5]傅瑤.鄉村振興戰略下鄉村文化空間建設路徑研究[J].農業經濟,2021,(4).
[6]楊麗新.鄉村文化供給的再組織化及其實踐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東前社區的考察[J].圖書館,2023,(8).
[7]賀一松,王小雄,賀雨昕,等.鄉村振興視域下農村傳統公共文化空間的復興與重構——基于江西蓮花縣村落祠堂的調研[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9,(6).
[8]耿達,王躍賢,趙瑞芳.縣域視角下城鄉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機制與路徑研究——以鶴慶縣為例[J].圖書館,2023,(8).
[9]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普遍征集革命文獻實物的命令[R].山西政報,1950,(9).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R].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6,(14).
[12]李耀申.中國革命紀念館事業的回顧和展望(一)[J].中國博物館,1995,(2).
[13]國家文物局.關于加強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EB/OL].(2016-07-01)[2023-10-15].https://www.gov.cn/xinwen/2016-07/01/content_5087356.htm.
[14]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EB/OL].(2018-07-29)[2023-10-15].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7/29/content_5310268.htm.
[16][19]李林.新時代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1.
[17][18]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EB/OL].(2022-08-16)[2024-04-05].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20]陳波,李晶晶.文化高質量發展視域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指標體系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21,(8).
[21]宋文婭.空間價值凸顯:鄉村振興背景下農家書屋的新形態[J].老區建設,2024,(2).
Mechanism and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With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Hubei
Gao Wei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rural areas of Hubei, and the promo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Hubei is conducive to extending the construction field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enhanc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expanding social influence, and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subjects, single development method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sufficient embedding depth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frequent weakening phenomenon of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To optimize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in Hubei with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e on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ptimize construction methods through iterative innovation, improve construction themes based on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enrich construction content through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責任編輯:程文燕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與模式研究”(18YJA760061)。
作者簡介:高威,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