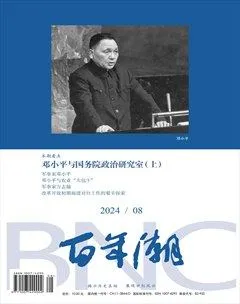公誼救護隊首次延安之行






1946年2月,公誼救護隊運輸隊在英國人任桐年的帶領下將中國福利基金會委托其運輸的七噸醫療物資,從重慶運抵延安。在延安期間,任桐年考察了幾所國際和平醫院開展醫療衛生工作的情況,在返回重慶后撰寫考察報告并提交給宋慶齡,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爭取外援提供依據。公誼救護隊此次的運輸活動不僅極大緩解了延安醫療物資匱乏的困難,也奠定了此后與中國福利基金會合作,向解放區輸送醫療隊開展醫療培訓和醫療服務的基礎。
開展人道救援
公誼救護隊是1914年在英國成立的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基督教公誼會信徒和拒服兵役者提供開展人道主義救援等替代服務的機會,幫助他們以此來豁免兵役。
一戰結束后,公誼救護隊解散。1939年公誼救護隊重新組建,1941年組織中國救援隊來華開展醫療物資運輸和醫療救護活動。1947年公誼救護隊更名為公誼服務會,1951年結束服務撤離中國。

公誼救護隊自開展運輸活動以來,就希望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運送醫療物資,卻因國民政府的封鎖禁運而未能實現。解放區除戰場繳獲和從日占區、國統區秘密購買外,很難直接得到來自國際援華團體提供的援助。為改善解放區的醫療衛生狀況,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前線作戰,1938年宋慶齡創建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在國際社會和海外華僑中募集資金、藥品、醫療器械等物資,通過八路軍辦事處運輸,國際友人交郵,美軍飛機空運等方式運往各解放區,支援解放區保育院、國際和平醫院和八路軍制藥廠等醫療衛生建設項目。基于人道主義救援的共同目標,公誼救護隊與保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1944年保盟通過公誼救護隊把美國紅十字會捐贈給國際和平醫院的一部大型X光機運至重慶,后經史迪威的幫助,這部X光機被空運到延安。1945年,宋慶齡還曾致函公誼救護隊暨中國國際救濟委員會工作人員邁克·哈瑞斯,對其向保盟捐贈物資表示感謝。然而無論是保盟還是公誼救護隊,都難以打破國民政府對解放區封鎖禁運的壁壘,解放區直接接受外來援助的途徑長期受限。
實地考察延安
外來援助的重要渠道是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1943年,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聯總)在華盛頓成立,其任務是負責在戰后統籌重建損失嚴重且無力復興的同盟國參戰國家。中國作為遭受戰災嚴重的國家,是最主要的受援國。1944年1月,國民政府設立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行總),負責接收和分配聯總提供的救濟物資。1945年7月,中共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簡稱解總)宣告成立,董必武任解總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伍云甫任秘書長。解總主要負責同國民政府和聯總談判施行援助,在解放區接受和分配援助物資等事宜。雖然按照聯總章程,聯總應不分政治派別,公平地分配救濟物資,援助一切受戰爭破壞的地區,但是在行總的操縱下,98%的救濟物資給了國民政府控制區,整個解放區只得到2%的救濟物資。這種不公平分配,完全違背了聯總“任何時候救濟物資絕不應被用作政治武器”的決議。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將為解放區爭取應得的救濟物資作為與國民黨談判的一項重要內容。9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在重慶的各國援華救濟團體負責人參加在桂園舉行的茶會。毛澤東在茶會上致辭,向保盟、公誼救護隊等援華團體表示感謝,并希望他們繼續給解放區以援助。宋慶齡代表保盟表示:“過去救濟多為戰時救濟,今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而在建設方面,仍將繼續予以幫助”。此后,宋慶齡積極與外國救濟機構及行總聯系,致函加拿大紅十字會駐重慶辦事處、美國紅十字會中國分會工作人員德拉蒙德以及行總署長蔣廷黻,請求繼續援助解放區以及保盟援建的國際和平醫院。10月,保盟即向延安空運30箱藥品。保盟駐延安代表馬海德在收到這批物資后,立即回函并提供了一份急需的藥品和醫療用品清單。
1945年12月,周恩來與行總署長蔣廷黻多次磋商后,就解放區救濟事宜達成六項諒解,明確“救濟不以種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歧視”。同月,宋慶齡發表《保衛中國同盟聲明》,宣告保衛中國同盟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中國福利基金會將繼續在中國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中間起聯系作用,也將繼續在國際上吁請道義、物質和技術方面的援助,以度過戰后的困難時期。15日,宋慶齡致函解總秘書長伍云甫、業務主任林仲,表示需要中共臨時救濟委員會提交中國福利基金會給解放區寄去的現款的用途和詳細報告,以便轉告國外捐贈者,同時詢問向國際和平醫院運輸物資的路線。中國福利基金會計劃通過公誼救護隊將募集到的七噸醫療物資運往延安。
公誼救護隊指派任桐年作為承擔此次運輸任務的運輸隊隊長。任桐年,英國人,1941年參加公誼救護隊中國救援隊,曾任公誼救護隊曲靖車隊基地負責人,后到重慶開展運輸工作。1945年12月27日,任桐年和公誼救護隊成員應邀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解總主任董必武的宴請,在席間他向鄧穎超、錢之光、王炳南、龔澎等人詳述了公誼救護隊的宗旨和工作內容。在給家人的信中,他這樣寫道:“他們對于我們講述的關于公誼救護隊的事情,我們做了什么和為什么這么做,非常感興趣。”1946年1月7日,由周恩來、馬歇爾、張群組成的委員會,就《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的具體條文進行討論磋商。1月上旬,國共雙方正式簽署停戰協定。這為公誼救護隊的延安之行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外部條件。
1月21日,任桐年率領其他六名公誼救護隊隊員,隨行三輛滿載七噸醫療物資的卡車,從位于重慶四公里的基地出發,卻很快因車輛故障而被迫返回。23日車隊再次啟程,經遂寧、三臺、綿陽,越過劍門關到達廣元,經七盤關進入陜西境內,在漢中的褒鎮稍作停留后,又經過幾天的跋涉,于30日到達西北交通重鎮、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模范城雙石鋪。公誼救護隊與中國工業合作運動、雙石鋪培黎學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42年,公誼救護隊的工作人員唐遜參與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后擔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外文秘書、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執行秘書等職,與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榮譽主席宋慶齡保持著密切聯系。公誼救護隊工作人員羅伯特·紐威爾和恩迪·布雷德在雙石鋪培黎學校擔任機械師和英語教師。公誼救護隊赴甘肅玉門油田運輸汽油的車隊也常在雙石鋪停駐。所以當車隊一行入住雙石鋪的中國工合招待所時,就遇到了由約翰·洛克和歐文·杰克遜帶隊的、剛從玉門油田返回的另一支車隊。


在雙石鋪度過農歷春節后,2月5日車隊前往寶雞,在寶雞將卡車裝上開往西安的火車車皮。到達西安后,任桐年聯系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駐陜辦事處指派工作人員王文源陪同車隊前往延安。車隊克服糟糕的路況和寒冷天氣的影響,最終于13日到達延安。
公誼救護隊抵達延安后,參加了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蘇井觀、副部長傅連暲舉行的座談會,解總、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各科科長、延安電影團攝影師以及《解放日報》記者參加了座談會。蘇井觀和任桐年分別介紹了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領導下八個解放區各醫院為軍民提供醫療服務的情況和公誼救護隊在華開展人道主義救援活動的情況。隨后,任桐年一行參觀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詳細詢問了醫院近年來接收捐贈的情況。在延安期間,車隊成員受到毛澤東的看望慰問,受邀和朱德共進晚餐,和中共領導人一同觀看京劇《大名府》。在即將離開延安之際,車隊成員每人都獲贈一條延安生產的毛毯。任桐年還收到衛生部領導贈送的畫作和軍服,但同時也遇到了一個讓他感到棘手的問題:中共方面請求車隊運送40名工作人員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公誼救護隊是以反對暴力和戰爭為原則的人道主義救援組織,在華以運輸醫療物資和救濟品為主,曾專此向國民政府行政院申請豁免運輸士兵和軍需品。任桐年向重慶公誼救護隊總部請示后,得到了“根據情況自行判斷”的回復,最終他決定將這批“未攜帶武器”的八路軍運往重慶。車隊于2月22日啟程,3月9日抵達重慶。
提交報告攜手救援
中國福利金基金會成立伊始,針對戰后救濟工作的新形勢,宋慶齡特別強調:“我們需要精確和最新的報告,這樣我們就能切實地為我們的工作開展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今后要募集現款和捐贈物品將日益困難了,現在戰爭已經過去了,人們就更傾向于考慮他們自己的憂患,而對別的國家的救助也就喪失了興趣。如果我們希望獲得援助,那就要有受援的報告和清單”。為了解延安和各解放區的醫療衛生狀況,依此向聯總、美國援華會等救濟機構申請救濟物資,宋慶齡通過致函、派遣人員到解放區考察等方式收集解放區的需求信息。1946年1月,她委托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分署代表、奧地利記者嚴斐德去淮陰、淮安考察,了解新四軍華中軍區所需醫療設備和物資的詳細情況;致信馬海德、伍云甫,希望盡快提供陜甘寧邊區藥品供應和醫療設備的情況。同樣擔負考察任務的任桐年在回到重慶后,撰寫完成《關于解放區醫療服務機構的報告》,詳細匯報了解放區醫療服務組織及國際和平醫院開展醫療工作的情況,并于3月11日提交給中國福利基金會。
任桐年在報告中將第十八集團軍衛生部、各邊區政府衛生處、解放區救濟委員會列為解放區主要的醫療服務組織。這些機構實際上擔負著不同的職能。第十八集團軍衛生部指的是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它是1945年由中央軍委衛生部和中央衛生處兩家機構合并而成的,是中共衛生系統最高行政指導機關,負責管轄黨、政、軍屬各級衛生機關。各邊區政府衛生處屬于邊區衛生系統,如陜甘寧邊區衛生處是1941年下設于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下的衛生組織機構,負責執行全邊區的衛生工作。解總則是解放區救濟工作的負責機構,擔負制定醫療和公共衛生政策,收集統計數據,聯絡救濟工作,指導救濟物資的分配和使用等職責。值得一提的是,解總表示所有計劃在解放區開辦醫院或派遣外籍人員到解放區kRnHxHH8yFH2vmQ/lYJNtg7p5nBAH0zIQECS6uP/1do=傳教的教會機構,需通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與之聯系。解總對此表示歡迎,并強調尤其希望醫生和護士到解放區來。

國際和平醫院是抗戰時期由保盟接收國際援華團體的援助,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設立的戰時醫療機構的統稱。報告對國際和平醫院的情況進行了匯報,指出“中央軍委總衛生部管轄八個解放區的衛生工作,國際和平醫院被納入在內,解放區所有的醫院都被稱為國際和平醫院”。
報告高度評價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院、第二院,認為其工作標準高,可以與國民政府中央醫院相媲美。這里提到的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院就是延安中央醫院。國際和平醫院第二院是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任桐年發現這兩家醫院都存在醫療設備匱乏的問題。延安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院全院只有一只腕表,四個醫生合用一個聽診器。延安國際和平醫院第二院只有兩套手術器械,當要治療10個戰傷病例時,卻因要等待器械消毒而不得不推遲手術。在醫療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醫院克服困難,竭盡全力開展群眾醫療服務,成功遏制流行病腦膜炎,治愈70%的沙眼病例。任桐年發現,到第一院附屬門診部候診的人群中起碼有30%是普通群眾,由于治療和配藥都是免費的,群眾來院看病的數量逐年遞增。對于其他的國際和平醫院,任桐年匯報道,因未實地考察所以難以判斷這些醫院是否能達到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院、第二院的標準,但他轉引了美國軍醫卡司伯格關于晉綏解放區第八分區醫院的報告,指出第八分區醫院“工作人員士氣高昂,傷員撤離情況好”,存在的問題是“醫院缺少合格的外科醫生、手術設備,對骨折的治療不夠”。而且由于部隊戰斗機動性強,使得醫生難以在關鍵的最初八小時內對傷員實施腸道手術,醫院護理工作僅以包扎和食物供應為主。


對于邊區衛生系統,任桐年主要匯報了陜甘寧邊區政府開展公共衛生和醫療培訓的情況。他列舉了八路軍軍事醫療服務人員的統計數字,指出其中的3400名醫生中約80%曾在延安中國醫科大學或白求恩衛生學校受訓。此外,每個軍區也有護理學校,開設有護理學和醫學培訓課程。報告還列舉了邊區醫療衛生工作中存在的困難,指出從1941年到1944年由于國民政府的封鎖和禁運,整個醫療衛生系統藥品匱乏,只能依靠延安制藥廠生產的有限的替代品。除了藥品匱乏,教材和醫學期刊也極度短缺。任桐年詳細記錄了蘇井觀開列的急需藥品和書籍的清單,并表示公誼救護隊可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安排下,將醫療用品從郴州和常德運往延安或西安。在最后總結中,任桐年充分肯定了邊區工作人員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這里沒有官僚機構的拖泥帶水,工作極有效率,不論是護理員工、化驗室技師還是醫生,都保持了相當的醫療水準,而且他們的水準比國統區的很多醫院甚至教會醫院還要高”。最后他建議,“我覺得如果派對醫院工作有豐富經驗的人,最好是醫生,在不久的將來直接來,將是件極好的事情,不只訪問延安的醫院,還要去解放區其他的國際和平醫院”。
1946年4月13日,宋慶齡向美國援華會執行主任米爾德里德·普賴斯轉遞了任桐年的報告,闡明了國際和平醫院對醫務人員的迫切需求,表示要繼續向聯總和行總呼吁,爭取對國際和平醫院的援助。根據嚴斐德的調查報告,宋慶齡向國際紅十字會募集到援助蘇北解放區建設一座現代化醫院的整套設備。為持續向解放區運送物資,她寄希望通過公誼救護隊開辟通向延安及解放區的運輸路線。最終在宋慶齡的斡旋推動下,1946年12月,公誼服務會第十九流動醫療隊從鄭州出發,乘坐美軍飛機將中國福利基金會募集的3.5噸醫療物資運往延安。1947年3月,第十九流動醫療隊另外兩位醫務人員從南京出發,攜帶另外3.5噸醫療物資到延安。1948年4至6月,公誼服務會將中國福利基金會援助邯鄲國際和平醫院的90箱醫療物資運往石家莊。此外,公誼救護隊此次延安之行也奠定了其與中國福利基金會合作向解放區輸送醫療隊開展醫療培訓和醫療服務的基礎。1946年12月,公誼服務會第十九流動醫療隊到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培訓醫務人員,后跟隨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第一后方醫院轉戰陜北和山西,為西北野戰軍提供醫療救護。1948年中國福利基金會與公誼服務會商定,新西蘭對外救濟團體聯合會來華工作人員先在公誼服務會所辦醫院進行短期實習,待熟悉情況后再送往指定單位服務。淮海戰役期間,公誼服務會第二十四流動醫療隊在河南永城開展救護,醫治大量解放軍傷病員。
公誼救護隊作為人道主義救援組織,通過與中國福利基金會合作,向解放區運送醫療物資、輸送醫務人員,支持解放區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公誼救護隊的人道主義救援活動,為緩解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創傷作出了貢獻,也因此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責任編輯崔立仁)
作者: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