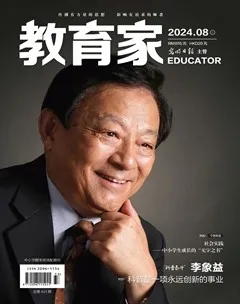看見中小學生社會實踐“綜合征”
為什么許多孩子不喜歡參加社會實踐?是什么導致不少社會實踐僅停留在表面?本刊編輯部對數位孩子、家長、教師進行了訪談,讓我們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當前中小學生社會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小北 初中生 天津市
“好學生”做久了,我似乎很難回到那個自己最喜歡的狀態了。
初三這年,我用一整年的時間去彌補自己前兩年落下的功課,晚上連做夢都在解二次函數題。好在最后的結果沒有辜負自己,我考出了令師長們感到意外的好成績。填報志愿時,我有幾所同檔位的學校可以選擇,大家對它們的評價有“高進低出”“低進高出”兩類,而我心儀的學校屬于第一類。很多人說這所學校里有很多“閑白兒”,建議我去管得更嚴的學校。但我沒有半點猶豫,我知道自己的生活里不能只有知識學習,我喜歡這所學校開放的氛圍,也期待那些被很多人稱作“閑白兒”的課外活動。
我很早就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卻很難通過學校的知識學習找到答案,越發期望與真實社會、不同人的接觸。但無論是學校、家長還是同學,很少有人能理解我的這種渴望,按照我媽的說法“小孩子搞好成績就可以了”。
初中時,學校也曾組織過一次社會實踐,聽說那是一次上級指示開展的“學農”活動。我媽同意我報名參加這次社會實踐活動的原因很簡單,“聽說可以進檔案,對之后的升學有幫助”,結果我們只是坐大巴到遠郊的大棚里逛了一圈。初二暑假,我按捺不住內心的躁動,獨自踏上了認知世界的道路。因為父母離異,他們日常又不聯系,我向雙方撒了謊,帶著200塊錢開始了20多天的外出“流浪”生活。我想打些短工養活自己,但因為未成年又干不長,很少有店鋪愿意用我。我去餐館打過下手,也在小鎮上擺過攤。有過露宿街頭,也被好心大叔收留過幾晚。我與餐館老板娘和拾荒奶奶成為朋友,向擺攤大叔取經,在做過“市場調查”后,找他借了一筆“啟動資金”開始了自己的生意。那段日子不算長,但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也逐漸消解了自己的迷茫。這就是所謂的見天地、見蒼生、見自己吧。
回來后,我沒有和任何人提起這件事,因為我不覺得他們會理解我,當然,我也不需要他們的理解。
在外人眼里,初三的我像是換了一個人,成績一直在進步。只是一年的苦學之后,那個被我關起來的自由灑脫的靈魂似乎很難找回來了。原本這個暑假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現在總是瞻前顧后,似乎什么也沒干成。
澤寶 高中生 河北省
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旨在讓學生走出課堂,接觸社會,增長見識,培養實踐能力。然而,現實總是與設想有著不小的差距。接到編輯老師發來的調查表,我轉到了幾個同學群,綜合同學們的意見,我們認為學校開展的社會實踐有如下幾個“槽點”。
活動重復性高:有的同學小學六年,有三次社會實踐都去了海洋館,而且每次幾乎都是同樣的流程,毫無新意;還有同學說他們初中時每年社會實踐都是去敬老院打掃衛生、陪老人聊天。
缺乏實際收獲:從小學到高中參加了很多次社會實踐活動,多數是去某個場館參觀一下,聽聽講解,并沒有什么實質性收獲。明明是為了完成任務,還要我們假裝很感興趣,寫心得體會的時候也要寫得積極向上,真是形式主義。
與學生興趣不大相符: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的場所幾乎都是學校和老師定下的,為什么不能讓我們自己選擇感興趣的實踐活動呢?這樣不是更有動力嗎?我們希望學校和老師在設計和安排活動時,可以更多地考慮學生的需求和興趣,讓社會實踐活動變得更加有意義和有趣。
與實際生活脫節:學校安排的社會實踐活動內容往往跟實際生活沒什么關系。比如我們今年社會實踐的主題是學農,但我們所去的農業基地似乎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看不到任何現代農業的痕跡,同學開玩笑說“咱們好像穿越了”。
缺乏反饋機制:活動結束后,如果同學們提出什么建議和意見好像都沒人理,學校也不問問我們到底學到了什么,感覺我們的聲音完全被忽視了。老師更關心的是我們的社會實踐報告和照片,至于我們是否學到了什么,好像并不重要。
組織和管理有待加強:我們今年為期4天的社會實踐活動,去了某個學農基地,最后一個晚上,竟然有教官和某個宿舍的男同學們一起喝酒、通宵聊天,這真讓人懷疑基地的資質。還有,老師千叮嚀萬囑咐不允許帶任何電子產品,但是到了基地,我才發現,全班竟然沒有幾個同學不帶,我成了最“孤獨”的那個。既然有紀律,就應該嚴格按照紀律去要求、去管理,否則以后再組織活動,豈不成了“放羊”?
葉子 小學生家長 廣東省
我心中理想的社會實踐是讓孩子通過參加活動學習實踐技能,加深他們對社會的了解,但如今我身邊不少孩子和家長反饋這些活動只是走走形式。
去年暑假,我所在的城市發起小學生“爭章”活動。學校給每名小學生發了一本手冊,鼓勵他們通過參加各類社會實踐活動收集印章,每完成一項就能在手冊上蓋一枚印章。集滿10個后,就能得到獎狀。居委會會定期組織一些公益活動,在公眾號上發放限定名額,家長們便在線上競相報名。我們社區的居委會組織孩子去河邊附近撿垃圾,搶到名額的家長需準備垃圾袋、手套、垃圾鉗等工具,帶孩子到指定地點參加活動,之后社區工作人員組織孩子拉開橫幅,拍幾張照片,發到班級群和學校公眾號上,就算潦草收尾了。
由于公益活動名額有限,抽中的家長自是滿心歡喜,未中簽的則想方設法,或轉戰其他居委會爭取機會,或托關系請居委會中認識的工作人員幫忙搶名額。同時,一些旅行社看中商機,推出不少學生一日游活動,比如組織孩子去采摘、參觀博物館等,并承諾參與即可獲得印章,且不需家長陪同,只要支付幾百元費用,人數越多價格越優惠,所以家委會偶爾也組織家長組團報名。
據我了解,不論是上述哪種活動,孩子們參加的興趣都不高。一次,學校在清明節前后組織學生參觀烈士陵園,我問孩子參觀之后的感受,他不停向我吐槽,說整個過程又累又熱,有的學生走到一半身體就受不住了,但學校并沒有做任何應急準備,還有人中暑后只能被老師背回學校。至于學到了什么,孩子并沒有明顯的感受,只是告訴我,以后都不愿意參加這類活動了。聽他這樣說,我也對之前為他報名感到后悔。
吳濤 綜合實踐教師 浙江省
我所任教的學校對于綜合實踐教育方面相對重視,且做得比較好。饒是如此,我依然遇到不少困難,其中最大的阻力來自家長。盡管國家規定綜合實踐為必修課程,但作為副科,即便學生僅拿到B等級,在升學、考試中也不會受到實質性影響,因此,絕大部分家長并不重視這門課程,在他們看來,參加這些需要耗費孩子大量精力,對考試沒什么幫助,還會擠占補習主科的時間,屬于得不償失的投入。
不少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積極性確實比較低。有的在報名時就表現出抵觸情緒,有的在中途提出家里有事、身體不好等原因申請退出,更有學生坦陳退出是由于家長反對。有一次,實驗班里一名叫小江的學生報名主持一項調查項目,前期調查工作已全部完成,但在即將輸出項目成果、參加比賽排練的關鍵時刻忽然失去了聯系。后來,我從其他學生口中得知,是因為家長沒收了他的手機和電腦,切斷了他與外界的聯系。
此外,社會環境中不友好的態度也是阻礙學生做好社會實踐的原因。不少人對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抱有偏見,不僅不愿配合調查,還會出言諷刺。我帶學生外出調查時,總能聽到有群眾用浙江方言說我們做這些是“空頭”,意思是我們只是在作表面文章。誠然,有些社會實踐項目存在種種問題,但在未深入了解學生具體行動與目標的情況下妄加評判,很容易給那些興致勃勃做實踐的學生“潑冷水”,挫傷他們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