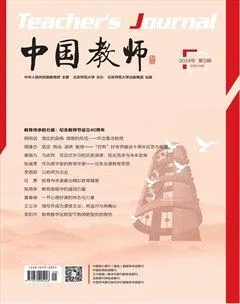以教師為志業
【摘 要】教師職業是飽含價值載荷的“志業”。教師是一個價值概念,教師之“志”是教師之“業”的價值根基。教師志業既是社會結構的價值期待系統,更是教師自身的價值自致系統。教師應處理好“致”“志”“自”三者之間的關系,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慎獨自省、躬行歷事四個維度下功夫,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統一在“傳道、授業、解惑”之中,將職業、樂業、志業融為一體。
【關鍵詞】教師志業 價值期待系統 價值自致系統
教師之所以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教師職業是一份飽含價值載荷的“志業”,能夠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統一在“傳道、授業、解惑”之中。“志業”乃是以高度的熱情和奉獻精神從事的職業和樂業。教師職業不僅是謀生的飯碗或手段,更是實現教育傳承、社會發展和個體成長的重要的價值力量。
一、教師之“志”是教師之“業”的價值根基
如果說“授業、解惑”的主要功能是育“才”,那么,“傳道”的主要功能則是育“人”,而“人”是“才”之價值根基,用康德的話說,就是“人是目的”。進一步講,教育教學的知識技能是“業”之根本,能夠幫助教師“游于藝”;而根植于教師內心深處的價值根性才是“志”之根本,能夠幫助教師“志于道”。正如帕爾默在《教學的勇氣》中寫到的:好的教學不能被降低到技術層面,真正好的教學來自教師內心深處的自身認同與完整[1]。
“教師”作為“師”,首先是一個價值概念。從詞源學角度來看,教師這一概念來源于拉丁語Pedagogue,原意是指擔任監護任務的奴隸或衛士,其責任是指引(agogos)孩子(paides)去學習[2]。教師這一概念的始基是一種“價值善”:Pedagogue是孩子的引路人,這就意味著教師必須將孩子引領“好”,明確自己要以善的方式來引領孩子,明確知道要將孩子引向何方,教師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價值引領。
正如蘇格拉底所言,雖然我們可以將教授這些行為—精于做生意、造船、技藝訓練以及諸如此類事情的行為,其目的在于獲得財富或身體健壯—的人稱為教師,但事實上,我們所說的教師,指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引導人從童年開始就追求美德,使之抱著熱情而堅定的信念去成為一個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從正義[3]389。教師自身應該是純潔的、高尚的、是善的,他們必須為孩子們再現好人的希望與心懷[3]407。因此,教師職業的根基在于“價值善”:以善的方式,傳授善的內容,以達到善之價值引領的教育目的。即使是純粹技術性的手段、方法、工具,在教師這份職業中也要受到“價值善”的規約,否則就不能成為“師”,教師之“志”乃是教師之“業”的價值根基。
二、教師志業承載了社會系統的價值期待
教師之“志”首先代表了整個社會之“志”,是整個社會對美好生活和價值之善的期待。在中國,對教師職業的記載可追溯至周代。周代的教育制度較為完善,教育機構包括庠、序、學、校等。教師被稱為“師”或“夫子”,是社會結構中知識的傳授者和道德的示范者。孔子被尊稱為“夫子”“萬世師表”,體現了整個社會系統對教師的知識尊重及道德期待。從最早的“師”和“夫子”,到秦漢時期的“博士”,再到隋唐時期的“國子祭酒”和地方教育機構中的“教諭”,以及宋元時期的“教授”和“訓導”,每一階段的稱謂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制度設計。這些稱謂不僅是職業名稱,更是對知識、學問和教育者的尊重,也是中國社會對教師職業的崇高的價值期待。
在西方,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Philosopher)被視為教師,這意味著,教師所教導的內容不局限于具體知識,還包含了倫理和生活方式。到了中世紀,由于教育主要由教會掌管,故而教師角色主要由牧師/神職人員(Clergyman/Cleric)承擔,強調的是宗教身份與教育職能的結合。到了啟蒙運動與現代早期,教師(Teacher)這一稱謂開始被廣泛使用,反映了教師職業的專業化和世俗化。這一時期,教師角色已廣泛承擔了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功能,社會系統對教師提出了明確的角色規約及價值期待。與Teacher相近的還有Educator這一稱謂,強調教師角色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中的教育專長,反映了教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興起。
三、教師志業是教師自身的價值自致系統
社會系統的價值期待具有外在規約性,而教師的自我價值期待則是內在生成性的,是使教師成為一種“志”業的內在價值根基。用唐君毅先生的話講,就是“道德自我”之建立,這一建立的過程永遠是人格內部的問題,永遠是一種內在的價值生活[4]。
1917年11月7日,馬克斯·韋伯在德國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報告廳舉辦了一次重要的演講,主題為“以學術為志業”。韋伯用“Beruf”(天職)來表示“志業”,示為神圣的事業、靈魂的事業:含有崇高的意義,類似于英文calling(呼喚)[5]。在韋伯看來,“志業”的含義超越了單純作為謀生手段的職業,“志業”是一種懷有信念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動。實際上,對于教師職業而言,這種精神活動的內核乃是教師的自我價值期待系統,是教師的價值自致系統。
1. 教師之“致”
“致”的功夫直接影響了教師“志”之境界。以教師為志業,意味著教師要在“致”的維度下功夫。教師之“致”至少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做”或“為”,乃躬行實踐之意。“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茍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6]972二是“至”,乃“達到”之意,強調教師作為一種志業所能夠達到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6]971
2. 教師之“志”
王陽明在貴州龍場講學訂立學規之時,曾以四事相規,而首言“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6]974作為一名好教師,其專業成長的關鍵也在于立志,立志乃是致心中那清清然之良知之基、之始[7]。教師職業的崇高、偉大,最終必須落實為教師立志成為一個具有完整德性的大寫的人,而且要在充盈自身德性的基礎上,立志為整個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成為大先生。教師要為自己“立志”,有志于成為一名“好”教師,堅定不移地守好自己立德樹人的價值本分。
3. 教師之“自”
無論是“致”,抑或是“志”,均依托于“自”。在談到“自”的層面時,就會引出“職業”“志業”之外的第三個概念“樂業”。如果致、志,最終要落實為一種能夠“自”驅動的價值使命的話,職業就需要成為樂業,才能最終轉化為志業。在樂業的層面談志業,就會明晰“德福一致”的倫理學基本原理。實際上,在志業層面,教師的辛苦付出恰恰是一種精神愉悅和幸福體驗,孟子的君子三樂是也。教師的辛勞付出,能夠為教師帶來“精神享用性”。做一名好教師,做一名無私奉獻的教育者,教師樂在其中、樂此不疲。教師的幸福感不依賴于外在的獎勵,而來自內在的心安,教師職業成為樂業,成為可以充分張揚自己生命意義和幸福追求的志業。
“自”是“志”與“業”的黏合劑,使志能夠成為業,使業能夠成為志。在黏合的過程中,包含幾個不同的階段或境界。第一,零度參與。在此階段,“自”中是沒有“志”或“業”的,此時的“自”缺乏道德主體性,是離散的原子式的個體。第二,漫不經心的參與。這種情狀類似于在商場漫無目的閑逛的顧客對商品的瀏覽。在此階段,教師職業是一份隨時可以換掉的“飯碗或工具”。第三,儀式規程式的參與。在此階段,教師只需完成“規定動作”即可。第四,迷戀式的參與。正如馬克斯·范梅南所說的,教育學是一門迷戀他人成長的學問。我們可以接著這句話來講:教師是一份迷戀學生成長的樂業,教師癡迷其中,樂此不疲。阿莫·那什維利說得精彩:誰愛兒童的嘰嘰喳喳聲,誰就愿意從事教育工作,而誰愛兒童的嘰嘰喳喳聲已經愛得入迷,誰就能獲得自己的職業幸福。第五,價值使命和意義追求。這樣的境界與韋伯所言的“志業”,以及馬斯洛所言的自我實現及精神超越異曲同工,教師個體的價值實現與教師職業的社會使命已實現深度的視域交融。
概言之,“自”指向教師專業成長過程中“道德自我”之建構,能夠為教師的職業行為找到內在的道德主體性,賦予職業行為以價值根性。如果說教師“職業”更多承載了外在的社會系統對教師角色的價值期待,那么,教師“志業”則更多強調教師“自”身的“致良知”的價值修養及價值實踐過程。教師志業是將外在于教師個體的社會系統的價值期待,轉化為教師自身的價值實踐系統的過程,是將“期待角色”轉化為“自致角色”的過程。
四、教師志業修養的具體路徑
1. 格物致知與認知修養
以教師為志業的第一步在于,通過“格物致知”從而獲得認知修養。此處所謂格者,乃正也;所謂致者,乃求得也。從認知修養的層面看,格物致知即窮究事物之理從而獲得對于事物的正確認知[8]。教師應對教師職業之“志”具有清晰深刻的理性認知,只有根基于此,才能為教師的“明明德”打下堅實基礎。從德性修養的層面看,格物的知識即是“明明德”的知識,格物之目的乃是為了“盡人性”,進而獲得誠明之知,格物致知,即是在行事接物上求至善之知而入正道也。在“志”的層面,“格”之對象并非自然之物,而是心中之善。通過職業認知修養,教師最終獲得人倫之知,即倫理道德原則、修己治人的道德認知,使教師在認知層面深悟倫理關系和做人做事的價值原理,從而提升自己的認知修養,在格物致知的過程中將真、善、美融為一體。
2. 誠意正心與情感養成
若要踐行教師之“志”,教師還需要在涵養道德情感上下功夫。道德情感是教師對所要遵守的道德規范所產生的體驗、態度的綜合。向善的道德情感,能夠使教師的職業道德認知獲得深層的情感認同,使教師獲得自愿遵守職業道德規范的內在動力。教師自發、真誠地體驗和表達,指向教師涵蘊自身的完美人格和道德美善的成長過程[9]。在此過程中,“誠意正心”是關鍵,是促使教師從格物致知的道德認知階段進入到實踐階段的樞紐環節。所謂“誠意正心”,是在格物致知的基礎上,正確、坦誠地對待自己的內心情感,教師的一言一行都要自然而然地由心而發、由心而生,此乃仁德之基。教師對教育事業和學生的“真情”是發自教師內心最原始、最真實的樸素情感,這種情感是“實感”,來自教師生命存在本身的真實而無任何偽裝表演的生命感知和感受[10]。“誠意正心”要求教師避免偏頗之心,克制不良的欲望和動機,不讓其牽制本心而影響專注做事,要求教師以端正的心思及清醒的理智來調整、涵養自身的情感勞動,以保持中正平和之心,從而做到情理兼備、修身養性。
3. 慎獨自省與意志修養
志業之志,關鍵在于道德意志,是幫助教師克服困難、立德樹人的動力和保證。堅強的道德意志能夠幫助教師自覺克服困難,排除障礙,堅決履行職業道德義務,實現職業道德理想,而且教師堅強的道德意志會對學生的意志品質和道德人格產生重要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具體路徑上,《禮記·中庸》提出“慎獨”的修養建議,要求在無人監督的獨處情況下,仍然能夠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堅守道德信念,不讓念頭或言行違背內心深處的道德律令,時刻不忘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堅持在“隱”處和“微”處下功夫,對自己的念頭、言行進行反思、監督、管理,并持之以恒地堅持,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中磨礪出堅定的道德意志。
4. 躬行歷事與實踐磨礪
教師之“志”業最終要落實為教師“致”的實踐。做公正的事才能成為公正的人,有勇敢的行為表現,才能成為勇敢的人。以教師為志業,要求教師不斷地躬行歷事。所謂“躬行”,即學以致用、身體力行、親身實踐。一方面,道德修養的過程要求“躬行”,做到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另一方面,獲得道德知識之后也應“躬行”,通過親身實踐加深理解,將道德經驗與道德智慧化為己用。所謂“歷事”,就是“在事上磨”,即經歷不同事務的磨礪,在做事中不斷修煉。“歷事”可以礪心、養心,尤其對從事教師職業這樣一種高度復雜并具有道德挑戰性的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修養價值。
概言之,教師應通過事的不斷磨礪,提升業務能力,增長道德智慧,涵養道德情感,磨礪道德意志,養成道德行為,通過躬行歷事與實踐磨礪,最終將職業、樂業、志業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 帕克·帕爾默. 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M].吳國珍,余巍,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
[2] 馬克斯·范梅南. 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M].李樹英,譯.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50.
[3]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3[M]. 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 唐君毅. 道德自我之建立[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
[5] 馬克斯·韋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 康樂,簡惠美,譯.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52.
[6] 王陽明. 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李西順.教師專業道德建構——以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為分析工具[J].教育研究,2022,43(1):72-80.
[8] 王緒琴.格物致知論的源流及其近代轉型[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2,34(1):94-99+128.
[9] 羅國杰.倫理學(修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47.
[10] 李西順.教師情感勞動概念界定的三個誤區[J].教育學報,2024,20(2):54-63.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畢業生就業政策研究”(課題編號:AIA220017)研究成果。
(作者系蘇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