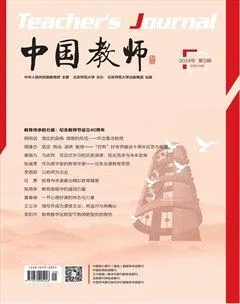割裂與彌合:以歷史解釋系統建構學科核心素養
【摘 要】歷史作為一種“存而不在”的客觀存在,需要由歷史解釋來彌合歷史材料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裂痕”。歷史解釋素養在歷史學科五大核心素養中居于核心、關鍵地位,因此,歷史解釋素養培育是系統性建構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有效途徑之一。主要策略有:以唯物史觀賦歷史解釋之值,以時空觀念夯歷史解釋之基,以史料實證現歷史解釋之實,以家國情懷鑄歷史解釋之魂。
【關鍵詞】歷史解釋 唯物史觀 時空觀念 史料實證 家國情懷
歷史距今而遠去,是一種“存而不在”的客觀存在。它的“遠去”與“存在”共同決定了歷史與現實中的人具有在時空、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間隙[1]。因而認識歷史的基本方式離不開考古發現,繞不開對歷史的探究、推論、想象。通過史料實證,歷史可以被復原,人們可以無限接近歷史真相,但純粹以史料呈現的歷史與歷史真相之間終歸是有“裂痕”的,這道裂痕需要由歷史解釋來彌合。
一、歷史解釋和歷史解釋核心素養的意蘊
歷史是“過去的事”或“對于過去事的記憶”;解釋是“分析原因,說明理由”,強調對事物意義的說明和闡釋。將二者結合所形成的“歷史解釋”則內涵豐富。杜維運認為,歷史解釋是疏通、比較歷史事實及其所包含的相互關系,以發現其中意義的過程。歷史解釋以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為基礎,其本質是一種敘事[2]。李劍鳴認為,歷史學家選取的歷史事實或明辨歷史事實的“真相”,都包含了其對事實意義的理解,因此,確定歷史事實是一切歷史解釋的基礎[3]。張耕華認為,歷史解釋包括史料解釋和史事解釋。前者包括讀懂史料的字面義,探求書寫者的原意、引申義(限于文字類史料);后者則側重探討歷史原因或是用某種理論來解釋原因,即借助一個普遍規律和初始條件來對某個史事進行解釋[4]。歷史解釋素養是《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和《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22年版)》中共同提出的五大核心素養之一。徐藍對于歷史解釋核心素養的內涵解讀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依據是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基礎是辯證、客觀地理解歷史,目標是養成理性分析和客觀評判歷史事物的能力、方法與態度[5]。可見,歷史解釋素養強調了“事實”與“解釋”之間的關系,借助歷史解釋,學生可以從史料中獲取或接近歷史真相,并在解釋歷史中培養分析、說明、評判歷史的關鍵能力、必備品格,形成正確的歷史觀。因此,歷史解釋彌合了史料、史實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裂痕,使得歷史從史料堆砌、史實羅列走向歷史認知主客體統一的富有“思想”的歷史。
二、依托歷史解釋系統建構歷史核心素養的策略
歷史解釋素養依托其核心、關鍵的地位,融通了歷史學科五大核心素養,使得諸素養由個體走向整體,以“整體功能優化”之態勢促成了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系統性建構。
1. 以唯物史觀賦歷史解釋之值
唯物史觀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是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方法論,是迄今為止最具科學性、最為思辨性的歷史哲學體系。無論是高中還是初中的歷史課程標準都指出,歷史教學應當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闡釋歷史的發展與變化。唯物史觀亦是歷史學科五大核心素養的靈魂,是學生歷史學習和教師歷史教學的理論基礎和理論保證。因此,歷史解釋的“底線”和“上線”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和“對于唯物史觀的理解程度如何”而決定的。倘若沒有立足于唯物史觀來進行歷史解釋,就背離了歷史本身,脫離了科學而陷入歪曲、虛無的歷史認知旋渦之中,沒有守住“底線”的歷史解釋必然是毫無價值的;倘若對于唯物史觀的理解是淺薄的,對于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方法論運用是不嫻熟的,那么對于歷史形成的認識必然是浮于表象而難抵本質的,所對應的歷史解釋也必然是相對機械而片面的。
例如,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其規律性的,從縱向看,人類歷史經歷了不同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由此所引發的不同社會形態的更迭。這樣的規律性存在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并在低級社會向高級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尤為明顯。聚焦于中國古代史,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奴隸社會瓦解、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因此,對于該時期所發生的劇變務必立足于唯物史觀來作出歷史解釋。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組成社會結構的三個層次因素并闡明了三者間的辯證關系,因而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劇變也應當從這三個層次要素切入。恩格斯認為,鐵是在歷史上起過革命作用的各種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種原料[6]。一方面,春秋晚期“冶煉生鐵,鑄造鐵器”的現象已經普遍存在,說明該時期已經逐步完成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轉型。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牛耕的逐步推廣,使其成為農業生產中最強大的動力。“鐵農具”和“牛耕”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的重要標志,并引發了政治、經濟、文化、階級關系等方面的劇烈變革。最直觀的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大量荒地被開墾成為“私田”,諸侯為激發奴隸的生產積極性變更了生產關系,并逐步下放了土地所有權,“奴隸”“奴隸主”的階級關系開始向“地主”“農民”的階級關系轉變。當諸侯所擁有的土地日益增多并大大超過王畿時,井田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井田制的崩潰引發了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的全線瓦解,西周奴隸統治系統的終結宣告了中國社會開始步入封建時代。對上述過程的闡述,運用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基本理論,將春秋戰國時期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從本質上進行深度解釋。
唯物史觀深刻闡釋了人類社會更迭中的作用機制,演繹了歷史的發展并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歷史各種內外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可見,立足于唯物史觀的歷史解釋,方才可以由淺入深,直抵本質,引導學生抓住歷史發展的“關鍵少數”,使得歷史解釋從單向、片面、機械走向綜合、全面、辯證,從而實現歷史解釋的增值。
2. 以時空觀念夯歷史解釋之基
任何歷史事件都處于一定的歷史時間及特定的地理和社會環境中。歷史時間除了所指的歷史時期外,還包括該時期內所關聯的歷史內容及該內容在該歷史時期產生的作用、影響。歷史空間主要指歷史事件所處的地理環境及歷史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7]。時空觀念即在特定的時間聯系和空間聯系中對事物進行觀察、分析的意識和思維方式。同時,時空觀念亦是歷史解釋的一種特定視角,因為觀察歷史的發展與變化,對歷史進行客觀評述必然離不開“時間演進”和“空間范圍”所構成的框架。可見,時空聯系是構成歷史最基本的關系之一,樹立時空觀念則是歷史解釋的基礎。
例如,如何理解中華文明的起源及發展具有多元一體的特征?中國并不是從一個點上發展出來的,在這片后來被稱為“中國”的土地上,從新石器時代到約公元前1000年,各個區域的不同文化逐漸接觸、互動,彼此交融,最終摶合成一個具有高度同構性的中華文明[8]。夏、商、周時期正是中華文明摶合的主要時期,因此,對于夏、商、周三代的關系理解是理解“多元一體”形成過程的關鍵。從時間演進來看,夏、商、周三代是一種“更迭”關系,但綜合時間、空間來看,夏、商、周并不是純粹的先行后續、取而代之的關系,而是前后相續的三個共主。時間上,夏的時間最早,之后商取代了夏成為共主,再之后周接任共主,它們存在和發展的時間有很大一部分是重疊的。空間上,夏文化位置居中,商文化偏東,周文化偏西,當夏成為共主時,其東方的商文化已經存在;當商成為共主時,夏文化也依然沒有被消滅;當周成為共主時,專門分封商的后裔繼續發展商文化。因此,綜合時間和空間因素,夏、商、周之間存在的共時關系和歷時關系同樣真實、同等重要。當然,夏、商、周同樣發生著深刻的交融,尤其是在周王朝存在的時間里。周王朝建立了完備的統治制度,形成了特有的周文化。而周文化的核心、關鍵部分被保留下來,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綜上可見,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周王朝,中國從一個多元錯落的文化領域摶合成為近乎單一的文明系統,這便生動演繹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及發展具有多元一體的特征。
時空觀念為歷史解釋提供了特定的時空框架。以時間為經,才能觀察、理解、認識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辨明其階段發展的特點,探尋其演進的內外動因;以空間為緯,才能明晰人類活動的場域,觀察歷史進程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相交織的聯系。因此,時空觀念是歷史解釋的基礎,只有回歸于歷史發生的時空,方能辯證地看待、敘述、評價歷史,作出契合客觀存在的歷史解釋。
3. 以史料實證現歷史解釋之實
相較于其他人文學科,歷史學注重“邏輯推理”和“論證實證性”。具有實證意識并學會運用歷史證據,是歷史學習和培養歷史思維的重要途徑。正如柯林武德所說:“歷史學是通過對證據的解釋而進行的……歷史學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釋證據。”[9]因而對于史料實證,應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一是對史料進行辨析,去偽存真,選取可信的歷史資料;二是以史料為依據還原歷史真相,能夠在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據此進行歷史敘述,提出歷史認識。在這兩個維度的基礎上,體悟并逐漸養成實證精神,以實證精神來正確看待歷史與現實。
例如,歷史上著名的長平之戰中的“白起坑趙”,可以從多個史料來進行實證分析。《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后所亡凡四十五萬。《史記·趙世家》記載:七月,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余萬皆坑之。對照分析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四十余萬趙軍被白起坑殺(活埋)”在《史記》中的記載是存在分歧的:一說“四十余萬”是趙軍在交戰中傷亡及被坑殺(活埋)的數量之和,一說“四十余萬”即被坑殺(活埋)趙軍的數量。那么,究竟哪一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呢?可聯系其他文獻資料,進行合乎邏輯的推理。在《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中記載著白起與秦王的對話: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史料記載,秦、趙在長平之戰中分別投入六十余萬、四十余萬軍隊。如果秦在戰中傷亡過半,那么以秦軍的戰力推算趙軍在戰中的傷亡人數,進而推斷趙軍被俘人數達到四十五萬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坑”有“大批集中屠殺”“集中埋葬于大坑”的釋義,類似于后世的“萬人坑”[10],據此也可推斷長平之戰中的“活埋四十五萬趙軍”的說法存疑。此外,還可以選用實物資料進行二重印證。根據《長平之戰遺址永錄1號尸骨坑發掘簡報》中的尸骸照片及記載,在60個未經破壞的個體中,近半數頭與軀干分離或僅有頭骨無軀干。因此,可推測這些人應是死亡在前,埋葬在后。坑中僅有1人可能是被活埋[11]。根據文獻資料、實物資料的相互印證以及邏輯推理,長平之戰中“白起坑殺(活埋)四十余萬趙軍”的說法是存疑的。但上述史料重現了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大、殘酷性強、戰爭中存在坑殺戰俘等現象。
所謂“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歷史解釋應當以史料為依據,以歷史理解為基礎。有“信度”的歷史解釋,前提是對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辨析,如果條件允許則應注意孤證不立、多重論證,辯證、客觀地看待歷史,解釋歷史表象背后的深層因果關系,不斷接近歷史真相,并將歷史描述出來從而重現歷史的客觀存在。
4. 以家國情懷鑄歷史解釋之魂
學習和探究歷史不應局限于歷史本身,而應具有一定的價值關懷,要充滿人文情懷,并關注現實問題。這體現的便是歷史教育的根本旨歸—家國情懷。學習歷史,學生應當以服務于國家強盛、民族自強和人類社會進步為使命,從而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塑造健全的人格,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只有以家國情懷為指引的歷史解釋,才能凸顯歷史課程立德樹人的教育根本任務,落地歷史教育的育人價值。
例如,如何理解北宋時期“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君子之爭”?趙匡胤、趙光義等北宋開拓者推出的“重文輕武”“中央集權”舉措一方面解決了五代十國時期“武將專權”“地方割據”的痼疾,另一方面也導致在宋神宗時出現了“不得不變”的時局。“王安石變法”不失為扭轉北宋頹勢、實現國家富強的有益之舉。然而,對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的過度推崇,會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推到正義的對立面,狹隘地將“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分歧”視作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其實不然。《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司馬光回答皇帝的問話,說: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王安石則在其所著的《周公》中寫道: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可見,無論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還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都在尋找“治國平天下”之策,只不過二者所主張的策略不同而已。因此,在王安石與司馬光身上均可見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所指的一種“自覺的精神”。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涌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12]。王安石與司馬光同為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表現出對國家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國家富強的不懈追求是其對國家和民族深情大愛的轉化產物,這是我們從“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君子之爭”中應當提煉的,是指向家國情懷素養培育的教學立意和育人價值。
歷史解釋雖然源于過去,但關懷的卻是現在和未來,其目的在于人類的幸福以及對未來的美好希冀[13]。歷史教育需要的不是歷史的“冷眼旁觀”者,需要的是完成歷史與自我交融的歷史傳承者。家國情懷正是亟須被注入歷史解釋的一種觀照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結歷史與現實的情感要素。歷史解釋也只有注入了家國情懷,才能真正沁入心田,使得歷史教育的價值在人性激蕩與生命躍動中落地,實現人的靈魂洗禮和精神重鑄。
綜上所述,歷史學科五大核心素養是內含邏輯關系的統一體,這就決定了歷史解釋的“從無到有”“由淺入深”“由此及彼”絕不是無緣無故、隨心所欲的,而需要觀照五大核心素養進行系統性建構。立足唯物史觀,歷史解釋方顯價值;增強時空觀念,歷史解釋方有根基;堅持史料實證,歷史解釋方成信史;注入家國情懷,歷史解釋方可鑄魂。總之,歷史遠去而存在,歷史的真相需要有這樣的解釋,歷史的意義更需要有這樣的解釋。
參考文獻
[1] 郭元祥,王秋妮.參與歷史:歷史想象及其能力培養[J].課程·教材·教法,2021,41(11):108-115.
[2]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64-165.
[3] 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279.
[4] 張耕華.釋“歷史解釋”[J].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17(17):10-17.
[5] 徐藍.關于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幾個問題[J].課程·教材·教法,2017,37(10):25-34.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2.
[7] 薛偉強,范紅軍,陳志剛.中學歷史課程與教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185.
[8] 楊照.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2:文明的基因[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9-11.
[9] 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M].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0.
[10] 孫繼民.考古證實“坑殺”并非活埋[J].中國語文,1997(5):392.
[11] 徐崢.教學策略:歷史概念間的橫縱聯系[J].中小學教師培訓,2021(6):63-67.
[12]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558.
[13] 賴立新,劉道梁.論歷史解釋素養表達的情感屬性[J].中學歷史教學,2022(2):16-18.
本文系2023年杭州市基教教研課題“三維·五融·四階:指向‘課程思政’的歷史情境化教學實踐研究”(課題編號:L2023051)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省杭州市丁荷中學)
責任編輯:趙繼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