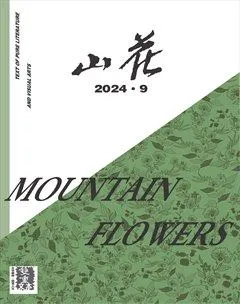赤水少年游
上高中時,一年夏天,跟父母賭氣,碰巧又剛讀到法國詩人蘭波,受了“生活在別處”這句話的蠱惑,發狠心去貴州浪蕩了一大圈。
今天去追溯,再難想象那二十多天是怎么度過的。只背了個有破洞的舊黃挎包,揣著平時攢的不足百元的盤纏,和一張臟兮兮的省際地圖。連洗換的衣服,也沒帶上一件,就怒沖沖地出了家門。記得真切的是,直到將手伸進小鎮長途車站的售票窗口,才橫下心,暗里咬定了目的地。一個全然陌生之處:貴州。
一種少年人特有的盲目而激越的膽氣,充溢全身。沒有一丁點對各種危險的預判。倉促間選定貴州,其實是受了些父親的影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小鎮上,父親是一個非常醒目的漂泊者,跟足不出縣的絕大多數當地人不同,他是一個推銷員,每年有八九個月,他操著鼻音渾濁、拗口難懂的桐城腔,到偏遠地區的中小學校推銷毛筆。我估摸這些以兔毛、豬鬃、黃鼠狼尾毛制作的毛筆,質量未必多么精良,所以父親跑得越是僻遠,毛筆的銷路,似乎就越好……我心底一直刻著幅黑白畫:好幾個除夕,年夜飯前,我帶著弟弟妹妹站在寒風中的老橋頭,等著父親歸來。我們流著鼻涕,縮著脖子,跺著腳,仿佛聞到他從異鄉帶回的煉乳罐頭、蘋果、奶糖這些珍稀玩意兒的奇特香氣。晚上,他講的那些離奇故事,在我們眼前展開過一個神秘的世界,我第一次聽到彝族、溶洞、天葬這些詞兒,還有那些令人吃驚的風習……當他在飯桌上不停拍大腿講著,他呼出的空氣、打的噴嚏、每一次停頓,都讓全家人緊張。而他講得最多的一個地名,就是貴州。
這幾日,好一頓顛簸!自合肥飛貴陽,換車至遵義匯川,再到珍酒的趙家溝基地。隔了這么漫長時光,終又來了赤水河流域。這真是很奇妙的一種感受——不管是途中昏昏欲睡時偶爾睜眼看向窗外的一剎,還是在下榻賓館落地玻璃前靜立的片刻;不管看見的是山林、村寨、隧洞,還是嘈雜的集市、清冽的溪水、排隊過閘的貨車長列——每一眼,仿佛都不是第一次看見,而是一種喚醒和重逢。黑白舊膠片中的記憶影像,似是幽閉在體內細胞壁深處,就等著這一瞬的按鈕按下,恍惚中被釋放出來,重播了一遍……只是這重播,另加了一層鮮亮的油彩。
當年楞頭楞腦的少年游,真個是漫無目的,又全無顧忌。四下里游蕩啊,每一天,仿佛總有揮霍不盡的蠻力,要快快地卸掉;要挖開體內的一道壩,讓里面堵著的水,痛痛快快地泄出來。全不在乎走到的,是哪個縣、哪個鎮,也沒有記下任何一筆當地風土人情。當時就從不上心,后來更是淡泊得全記不起353f1f1c548a718fa02c60043220b7fbad459b4e40b5d872bd03a74111379970,以至于想寫下點什么,路線、地名、情節總是亂作一團,前后矛盾。不過,這么多年,讓我感念最深的始終是,不管浪跡到哪一塊,貴州從無一人欺我少年窮。扒運煤車也好,搭賣菜的輕卡、蹭鄉間拖拉機也罷,有時對話嘰里咕嚕,一個字也聽不懂,但這少年心里,似乎從沒為什么事兒慌張過。
而記得最牢的,有兩處細節:一是在山間廢橋洞里,睡了兩個晚上。拱形老橋洞,離卵石密布的谷底有三四米,即便這是夏末,谷中也沒什么流水,更沒見到傳說中赭紅咆哮的河水。只是星空真的像是伸手可觸,仿佛有億萬顆星星鋪織的璀璨天幕,就蓋在這老橋上。我在夜色中昏沉沉睡去,又不斷地醒來。實在是太累了,躺下就像一攤淤泥。后來反復回味這段畫面,倒真有點奇怪了,這樣臟的山中廢橋洞,怎么竟沒有一點蟲蚊叮咬,更沒啥野獸侵擾,讓兩個少年睡得這么安生。
另一件,是某個晌午。從拋錨熄火的貨車上下來,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半山道上。蒸騰的暑氣一層層晃動著,能看得見。貴州的夏天,比安徽涼爽,偏這一小塊熱得讓人招架不住。山道像襁褓一般寂靜。糙得皮開肉綻的路面,有幾塊殘存的劣質柏油曬化了,走上去,腳底像踩在幽暗又強勁的拉力中,仿佛要將人定在蒸籠般的路面上。我的硬塑涼鞋原本就裂了大口子,沒走幾步,后半截竟生生拽斷了,只好一瘸一拐往前走,又疲又餓。轉過一處山腳,忽地眼前一亮,大喜過望。山坳處,竟有一家豎著招牌的小飯館子。小跑過去,堂屋無人,喊了幾嗓子,仍沒人應答,就坐在小板凳上等。從后門吹來的穿堂風,沁涼入骨,滿身臭汗一下子干爽了。過了好久,一個精瘦的矮個中年男人從門外抱著捆柴火進來。問,想吃啥?我指了指土墻上粉筆寫的菜單第一行,就它了,豬油炒飯。便宜。
沒一會兒,一股我沒法描述的香味兒猛地鉆入鼻孔。豬油炒飯,來了。接下來,應當先是狼吞虎咽,吃到一半時,忽然就放慢了。是不忍心一下子吃完的憐惜感?多年后,看周星馳一部影片,見到一個菜名“黯然銷魂飯”,仿佛才從記憶中這份味道上,恍然回過神來。吃罷,抹抹嘴,愣了一會,忽地猛拍了一下桌子。
“店老板,再來一碗!”
是不是喊的店老板,記不清了。老板是哪一年才有的稱呼?但猛捶桌子那一下,力道確有點失控了。插筷子的老竹筒,嚇了一跳,從桌面咕嚕嚕就滾了下來。
這次來貴州的前一晚,正碰上幾個詩人在合肥夜聚。我又講起少年遠行中,結交王遷的事。王遷和我差不多的年紀,又黑又矮,眼窩深凹,性子特悶的一個人,可以兩天不說一句囫圇話,但寫起信來,又是個讓人害怕的超級話癆。那些年,他給我寫的信,很少有十頁以下的。王遷是土城一帶的人,除了添油加醋轉述他爺爺講的鹽幫、船幫、馬幫、茶幫、酒幫、戲幫、棧房幫、袍哥會等舊時“土城十八幫”的逸事,就是每封信要問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問題。答王遷之問,一度是最讓我頭皮發麻的事兒。但毫無疑問,我對他信中描繪的川鹽入黔、風云際會的水陸大碼頭土城相當著迷。我還專門買了一本分省地圖,辨別土城、習水、赤水河等一籮筐的地名。只可惜,這次來,沒去成土城,更是完全沒有線索找到我和他曾住過的廢橋洞。九十年代后的幾次搬家,讓兩個萍水相逢的少年間大撂的書信,早就沒了蹤跡。
大概在1995年前后,王遷到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后,突然地跟我斷了音信。后來我通過網絡等各種方式企圖捕捉他的蹤影,多年了,依然一無所獲。也不知我最后寄他的一幅字,他收到沒有。王遷一家人都嗜酒,他經常跟外婆、父母四人圍桌而飲,每次都要喝到桌傾椅倒。那段時間,我迷上草書大家林散之的字,就順手抄了林散之的一副聯給他:“乘月歸田廬,千載論交唯紀叟;大江流日夜,一生低首是宣城”。
怕他看不懂,我又附了封信講講誰是紀叟。李白寄居敬亭山下的宣城時,跟城中釀酒的紀老頭交好,常常深夜在小巷中的這家小作坊買醉。紀老頭孤老無依,死時也很是冷清。李白為他寫了這首短詩:“紀叟黃泉里,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這是不是李白唯一為真正底層人寫下的詩?不敢確定。一直偏愛這首小詩,情真意切,我覺得比《靜夜思》好。
王遷給我寄過好幾個小陶罐封裝的赤水河醬酒。那些年,安徽人的舌尖只對古井貢一類的濃香酒敏感,這可是曹操舉杯高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老牌子呀,印象中,沒幾個人愿意為醬酒一醉。近幾年,大家忽然都對醬酒趨之若鶩了。想想王遷當年寄來的,是真正地道的土醬瓊漿,翻箱倒柜再去找時,也早沒了蹤跡。
這次由皖入黔,在兩邊朋友小聚的餐桌上,我又講起多年掛在嘴邊的一個說法。要講中國物產,真算得上蒼厚愛的,其實只有兩樣:安徽涇縣產的宣紙和赤水河邊產的醬酒。這兩樣,是極特殊小氣候下的產物,在世上任何別處,都不能復制。要做出上好的宣紙,必須集齊四件東西:韌性最佳的皖南青檀樹皮、涇縣小田塊的砂田稻草、兩條小河匯聚時酸堿度適中的河水、黏性奇特的皖南野獼猴藤汁。普天之下,能集全這四樣的,也就涇縣那一塊地兒。而釀造這世上最美醬酒,需要赤水河畔特殊微生物菌群、從紫砂巖層穿行而生的礦化水、支鏈淀粉成分特別的紅纓子糯高粱、秘而不宣的醬釀工藝等等,別處又哪能湊得齊?沒有了宣紙,古來的書畫藝術將寡淡幾許;沒有了赤水河畔的醬酒,今天國人的生活,似乎也少了份神采。造化之功,奇妙不可盡述,用愛因斯坦的話講,老天設定的造物密碼,誰也篡改不了。
在糟香撲鼻的珍酒車間,我目擊了“走糟”“踩曲”工藝。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切近地踏入名酒的核心工序。車間的柱礎上、磚縫和墻角,斑駁的薄苔中,處處散發著時間與發酵后糧食混成的獨特氣味。好酒中,自然地蘊藏著時光的秘義。據說珍酒釀造的用水,是赤水河流域的地下水。碰巧前兩年我受詩人梅爾邀請,到訪過鄰近綏陽縣的十二背后溶洞群。梅爾曾指著約一人高的石筍說,滴水凝成這根筍子,需要七億年時間。這赤水河的地下水,點點滴滴,穿縫過隙,層層提純、釀制,最后成了一杯瓊漿。好酒中,當然也包含了對人的生命的相逢、相認。精壯漢子走糟,精巧女工踩曲,也仿佛是人的蓬勃生命以這種滲透的方式,進入到酒的釀制之中。人世間,無論是“濁酒一杯喜相逢”“西出陽關無故人”,還是“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哪一場酒,不是生命與天地萬物之間、生命與生命之間的深刻對話?我應向那個在舊光影中埋頭吃著豬油炒飯的少年,敬一杯酒嗎?
另外,從資料中我得知,因珍酒快速擴產的催動,附近山民們種植的“懶漢高粱”價格,比別處高出了三到四倍。這個數字最讓人開心,因為我熟悉一粒種子從入土到入倉的艱難過程。每一粒,每一人,每一杯中,其實都有著關于利益、情感與生命發現的動人故事,此處且按下不提。
古往今來的酒之好,其實最關鍵的,還是它包含了人之寄托。在我抽屜深處的日記本中,我曾為赤水河邊的少年游,寫了一句詩:“今夜,河水不會高于我發燙的嘴唇。”
嘴唇滾燙,可能因為與好酒相逢,也可能因為一些更為內在的東西。人在少年時,酒是眼界、豪情、游歷與憧憬,是朝向來日的催化劑。中年之后呢?正如此刻微酣中走到堤上吹風的我——酒是體內無礙無顧、時而陷于記憶與執念的一場少年游。一場無邊無際,也無始無終的少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