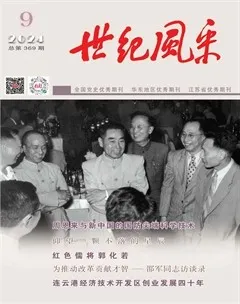紅色儒將郭化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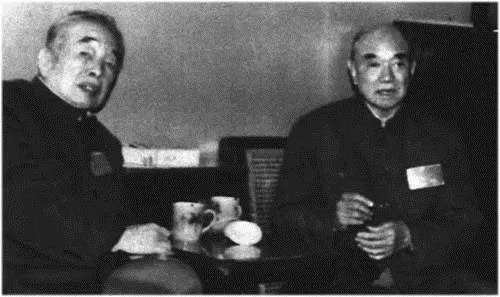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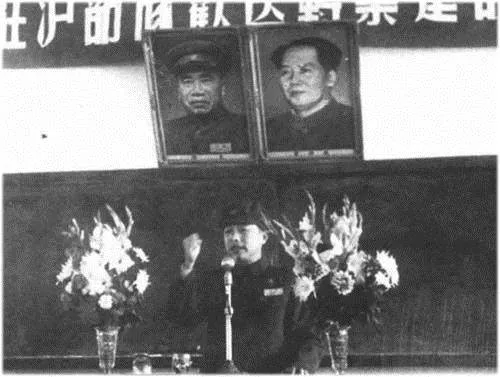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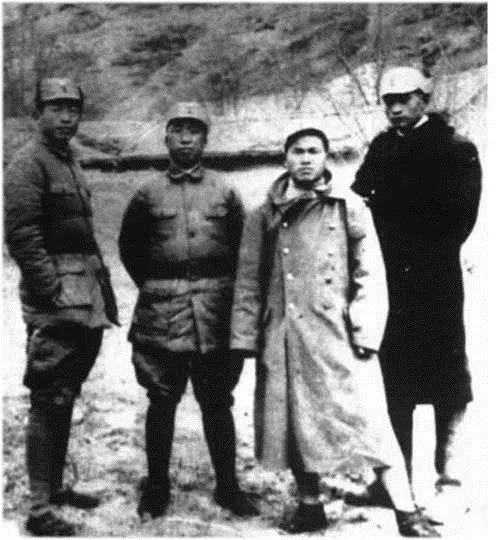
郭化若,1904年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中將,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1925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了南昌起義隊伍,不久,受黨組織的委派前往莫斯科炮兵學校學習,一年后回國,主動追隨毛澤東、朱德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建設,是毛澤東的軍事教育顧問。他能文能武,是人民軍隊杰出的軍事教育家、軍事理論家,被周恩來稱贊為“共產黨的秀才”,為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賀龍評價為“我軍大大的功臣”。
白手起家建特殊兵種
1930年9月,紅一方面軍第二次攻打長沙久攻不克。戰后,毛澤東對此原因進行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敵之工事歐式的重層配備,鐵絲網、壕溝等計八九層”,而紅軍“只有肉搏沒有重炮破壞敵之工事”。毛澤東的精辟分析,深深地烙在郭化若的心上。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建一支我們自己的強大的炮兵和工兵。
9月24日,郭化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帶領機關的一些同志深入到安源礦工中做籌款和擴大隊伍工作。他驚奇地發現,有的工人不但懂爆破,還能搞到很多炸藥。他眼前一亮,一個想法瞬間涌現出來:這完全可以建一支自己的工兵。他馬上把這一發現和想法向毛澤東和朱德匯報。毛澤東非常開心地說:“打長沙要是有爆破組開路,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應當組織一些礦工入伍,組建一個工兵隊。”朱德接著說:“要得。要建立一個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能炸碉堡、能挖防空洞的工兵隊。”
按照毛澤東和朱德的指示,郭化若開始著手組建工兵隊。他與工會的同志一起,將礦上既懂爆破技術又自愿參加紅軍、思想基礎不錯的工人挑選出來,共挑了140多人。為了使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能快速地成為紅軍的一支勁旅,郭化若抓緊時間對他們進行軍事訓練。他把隊伍集中在一個操場上,首先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讓大家明白參加紅軍的意義和建立工兵隊的重要性;其次進行分班編排,按照紅軍每班10人,三班一排的編制,讓大家自愿組合,并推薦出班長、排長、隊長;再次是進行隊列訓練,從立正、稍息、向左向右看齊等基本動作練起,然后循序漸進地轉至行軍動作;最后進行難度更高一點的射擊、爆破等戰術訓練。通過科學高效的軍事訓練,這些由工人組成的工兵隊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許多技術,學到了必備的軍事知識和殺敵本領。10月3日,工兵隊的重要作用在攻打吉安城時就顯現出來了,架云梯、炸碉堡樣樣精通而又迅速。10月7日,在吉安后河草坪召開了工兵隊成立大會。從此,紅軍隊伍中正式有了工兵。
同時,郭化若深知,如果紅軍也有無線電通訊隊,那就意味著紅軍有了“千里眼”和“順風耳”。每次作戰命令發出后,他都會特意注明要各部隊注意收集敵人的無線電臺和技術人員。很快,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紅軍繳獲了國民黨的一部電臺,還俘虜了10名無線電人員。遺憾的是,這部電臺還是被砸壞了,只能收報,不能發報,只能算是半部電臺。郭化若得知后,深知這些都是寶貝,要求務必送到紅一方面軍總部。開始,被俘的無線電人員很害怕,連自己的真實姓名都不敢說。郭化若一個一個地找他們談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留下來為紅軍服務。經過耐心細致地做工作,10名無線電人員都愿意留下來當紅軍,尤其是不僅懂報務還懂機務的王諍。1931年1月3日,在寧都東韶戰斗中,紅軍又繳獲了一部完整的收發報機。為了更好地統一管理和發揮好這些人員和電臺的作用,郭化若經過深思熟慮后,鄭重地向毛澤東建議組建一支自己的無線電通訊隊。1月中旬,經毛澤東、朱德批準,紅一方面軍無線電通訊隊正式組建,王諍任隊長,共100多人。這就是人民軍隊歷史上的第一支無線電通訊隊。
無線電通訊隊成立后,雖然只有一部半電臺,但郭化若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一是抄收新聞,打破了蘇區消息閉塞的局面;二是開辦了無線電訓練班,為紅軍培養了大量的無線電技術骨干;三是進行技術偵察。正因為有了無線電技術偵察的幫助,紅軍痛痛快快地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在紅軍無線電臺的組建過程中,郭化若的保密意識特別強。他制定了許多具體的保密紀律規定,建立了紅軍獨特的通信制度,電臺之間不許自行通話,新編電報密本,密本再加密表,密表常常更換,最重要的軍事機密則一報一密,嚴格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電臺專用電鍵由警衛員負責攜帶。1931年5月底,紅一方面軍無線電總隊成立,下設5個分隊,分別隸屬于紅三軍、紅四軍、紅十二軍、紅三軍團和后方建制。
后來,郭化若在延安組建了人民軍隊第一所炮兵學校——延安炮兵學校。他創造性地提出了炮兵軍事教育教授的8種方法,即集體研究、少講多做、搞實驗教育、按步前進、各科配合、以典型推動、應組織教育、經常考績,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培養了大批的高素質的炮兵人才,成為八路軍炮兵的搖籃。賀龍稱贊他是“我軍大大的功臣”。
頭頂“托”帽辦抗日紅軍學校
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1932年7月,郭化若被調離了紅一方面軍代參謀長崗位,到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同時還莫名其妙地被打成“托派”,開除了黨籍。1933年10月,紅軍軍事學校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郭化若任總教官。1934年10月,紅軍大學改編為干部團參加長征。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學校,郭化若任訓練處長。頭頂“托派”帽子的郭化若顧慮重重,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信任和鼓勵下,走馬上任。在辦學的過程中,他遇到很多實際困難,教學無教材,訓練無器材,原有的教材不僅不適應抗日形勢的變化和新的作戰對象、作戰條件的變化,而且在長征中也遺失得差不多了。面對這些困難,他沒有退縮,心無旁騖地想盡一切辦法逐一地解決,盡快地使學校教學活動走上正軌。
針對沒有教材的現狀,他集思廣益。首先是借鑒外國的。他組織人員收集國外的教材,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找到了蘇聯紅軍的條令、條例和野外勤務教程、德國的步兵操典、日本的戰斗綱要等。其次是親自編寫新的教案。郭化若根據紅軍的作戰經驗和實際情況,借鑒外國做法,夜以繼日地編寫了步兵、炮兵及工兵等教材。這些教材經毛澤東批準后,在學校施教,既解決了學校“有槍無子彈”的困境,又滿足了教學的需要。
針對沒有器材的難題,郭化若就因陋就簡,組織大家就地取材,上山砍木材做單杠、木馬等體育器材,找石塊、黃土制作沙盤。射擊訓練缺少訓練子彈,他就著重組織學員精練瞄準、擊發。他對學員們說:“我們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實實在在管用的東西。別看今天我們用的訓練器材土了些,可訓練的效果用到戰場就能打敗敵人。”
他通過改革訓練方法,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目的。他采取操場練兵和野外演習為主,沙盤作業、課堂講解為輔的方法,著重進行野外訓練和夜間訓練,力求使大家掌握夜間山地的遭遇戰、伏擊戰、游擊戰中進攻、防御、追擊、退卻、偵察等戰斗手段。
1936年初,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擴編為抗日紅軍大學,郭化若任第三科的訓練主任。1936年11月29日,成立抗日紅軍大學第二校,郭化若任教育長。1937年3月,學校又改名為慶陽步兵學校。郭化若因人施教、因需施教,針對學員畢業后絕大多數要分配到游擊隊去的實際情況,及時建議教育內容除了仍以軍事、政治、文化課為主外,還需要增設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與拉丁文的課程。沒有教材,他就自編軍事課講義,以淺顯易懂的問答形式編寫了《抗日的步兵戰術問答》,對有關班、排、連會涉及到的戰術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很受學員們的歡迎。他還著重抓戰術技術訓練和軍風軍紀教育,要求每個學員戰術技術上過得硬,作風上過得硬,使學員們實彈射擊平均命中率達到96%,軍風軍紀也有很大進步。總校教育長羅瑞卿稱贊他“在嚴格軍風軍紀和加強技術方面作出了榜樣”。
“亦官亦文”研究古兵法
1938年夏,郭化若任軍委一局局長。毛主席鼓勵他說:“當官又寫文章,亦官亦文,兩全其美。”
全國抗戰之初,雖然相當數量的國民黨正規軍及地方軍對日寇進行過積極抵抗,但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堅持一貫的反人民立場,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實行單純防御戰略,進行片面抗戰路線,使國民黨幾百萬軍隊形不成堅強的戰斗力,結果開戰15個月就丟失大片國土,讓日寇輕而易舉地打到了廣州、武漢,囊括了華北、華中的大片土地和華南的要地。有一天,毛澤東對郭化若說:“國民黨中的頑固派,花崗巖腦袋,不承認游擊戰的戰略地位,不搞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處處招架,處處挨打,能不打敗仗嗎?”“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寫點關于古兵法的文章,宣傳點運動戰思想對國民黨的軍官,搬古兵法,他們懂,聽得進,講馬列,講唯物辯證法,他們聽不進。”郭化若深知毛主席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運用古兵法的典范,也深刻領悟了毛主席這一席話的用意,就是要通過對古兵法的宣傳幫助國民黨廣大官兵正確認識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實行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學會“古為今用”,從而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郭化若很快找了一些關于古兵法的資料進行潛心學習與研究。他在查閱古代戰例時,認為“赤壁之戰”這個戰例非常好。當年,曹操率領號稱80萬大軍南下攻吳,正是因為孫權聯合劉備,又采取了正確的火攻戰術,才能在赤壁大敗曹軍。于是,他通過《赤壁之戰及其對民族抗戰的啟示》這篇文章告訴大家,中華民族團結則存,分裂則亡。我們的民族團結,長期合作,不但要創造出抗日中的新“赤壁”的戰績,使日寇像曹操一樣“引軍北還”,東歸三島,還要使國共的合作長期發展下去,建立起獨立幸福的新中國。接著,他又寫了《齊燕即墨之戰的初步研究》一文。他在文章中全面分析了2200多年前齊國在抗擊強敵入侵時轉敗為勝的戰例,認為:“齊國能轉敗為勝,除了采取了正確的戰法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軍民團結一致,堅持抗戰到底。”“在我國現時的抗日戰爭中,日寇只能逞兇于一時。人民中有無限的力量潛存著,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配合軍隊作戰,就能最終打敗敵人,取得抗戰勝利。”
這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1939年2月和4月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上。許多國民黨軍將領閱讀了這兩篇文章,感觸頗深。有的還給雜志編輯部來信,說讀了郭化若的“赤壁之戰”“即墨之戰”等文章之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謂“切中時弊矣!”
除此之外,郭化若還研究《孫子兵法》。《孫子兵法》是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珍貴遺產,是指導古代戰爭取勝的武器和法寶,對當今的戰爭也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郭化若打算寫點有關《孫子兵法》方面的文章,讓《孫子兵法》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毛澤東知道后非常支持,并指導他說:“要為了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去讀孫子的書,要精濾《孫子兵法》中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對戰爭指導的法則與原理,并以新的內容去充實它。研究孫子,就要批判和反對那些曲解孫子的思想和貽誤中國抗戰戎機的思想。”“首先要深刻地研究孫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哲學思想以及包括孫子以前的兵學思想,然后對《孫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孫子兵法》。”郭化若按照主席的指點,廣泛收集資料,認真閱讀,到處請教,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寫出了《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文章一發表,影響深遠,就連國民黨的高級軍官也高度關注,紛紛向周恩來打聽作者的情況。周恩來自豪地對他們說:“郭化若是我們共產黨的秀才。
從此以后,他一直沒有中斷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受到海內外廣大學者的贊揚和高度評價,一致認為他是當代最有權威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專家。
嘔心瀝血編戰史,但留點墨在人間
新中國成立后,南京軍區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負責編寫新四軍抗日戰爭史和第三野戰軍解放戰爭史的工作。這是一項任務艱巨、系統性很強的工程。南京軍區只有郭化若既有實戰經驗,又精通軍事理論。陳毅也指示此項工作必須由郭化若來負責。由此,從1959年開始,郭化若就把主要精力逐漸放在編戰史上。
在郭化若的領導下,戰史編輯工作緊張而有序地開展。首先成立了編審委員會,加強編寫力量的組織領導,還特邀陳毅任編委會主任。其次充實戰史編輯室力量,增加編寫人員,由郭化若直接領導。再次廣泛收集史料,全體編寫人員通過各種渠道廣泛收集戰史資料,還到各地進行實地調查采訪,挖掘各種文件、記錄、戰例、戰役戰斗等大量史料,然后進行整理研究。
在編寫戰史工作中,他始終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導原則,實事求是地反映新四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在抗日戰爭中和解放戰爭中的真實面貌。在編寫新四軍戰史時,他要求工作人員一定要反映劉少奇在皖南事變后為重建和發展新四軍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重要貢獻。對于戰史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與編輯室的同志商榷探討,力求史實準確,觀點正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于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他從不先下斷語、做結論,而是廣納良言匯聚眾智,從而達到認識上的一致。同時,他還經常向陳毅、粟裕、譚震林、張云逸、鄧子恢等領導同志匯報、請示,聆聽他們的指示和修改意見。在戰史編輯室全體人員的辛勤努力下,于1963年底,南京軍區編印了《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兩部書。一些老同志看了這兩部書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戰史真實客觀,反映歷史全面,是部不可多得的歷史好教材。
1973年12月,中央軍委任命郭化若為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雖已年近古稀,仍精神滿滿,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的工作中。在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三部戰史和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時,他把端正指導思想放在首位。他一再強調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要突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作用。他還強調,編寫戰史,就是要通過敘述戰爭的進程,展現毛澤東思想如何在實踐中指導中國革命戰爭不斷取得勝利。為此,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大家統一了指導思想。為了啟發大家的思路,幫助大家排除寫作中遇到的困難,他經常把自己在毛澤東、朱德身邊工作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以及多年從事軍史、戰史研究工作的體會,人民軍隊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敘述這些重大事件時應該把握的觀點,有些具體事件的寫法等分享給大家。初稿寫出以后,他發揚民主,以普通一員的身份參加逐章逐節的討論。在他悉心指導下,終于在1987年完成四部戰史的出版工作。
1988年,他回顧自己60多年的經歷,作詩一首《人民武裝斗爭回顧》,詩中寫道:“六十年來多少事,但留點墨在人間。”郭化若留下的“點墨”,給后人學習研究中國人民武裝斗爭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