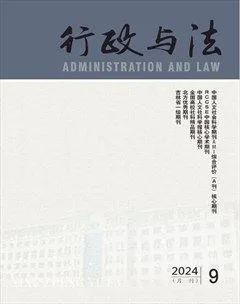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現實困境與紓解
摘 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作為區域協同立法的特殊形態,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而推動國家重要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具有巨大的現實需求,2023年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十三條為區域協同立法制度提供了明確法律依據,但在實踐中,由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各立法主體間存在層級差異與權限差異,在立法合法性、立法權限、立法主體平等性、立法程序方面仍然存在問題,阻礙區域協同立法制度的發展。可以通過法律解釋方法、遵循地方立法權的“最大公約數原則”、建立健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特殊備案與生效機制來紓解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現實困境,完善區域協同立法運行與保障機制,有效適應新時代區域高質量發展要求。
關 鍵 詞: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區域協調發展;地方立法權;現實困境
中圖分類號:D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24)09-0064-12
一、問題的提出
區域協同立法是充分發揮地方立法權靈活性配合地方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1]“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作為解決地方發展問題的錦囊妙計,能夠統籌在地緣上具有一定關系的省、市等區域共同致力于同一發展問題,以系統性發展視角和相互協調配合的發展辦法推動一定區域實現共同發展,尤其是在針對大氣污染治理、流域保護等環境問題時地方各區域的協同配合顯得尤為重要。我國最早的地方區域協同立法實踐源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早在2014年學界便開始了對地方區域協同立法的研究。[2]最初在區域協同立法研究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區域協同立法的合法性問題,地方立法權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的授權,在區域協同立法的探索階段,地方立法機關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指引,在立法實踐中存在對地方區域協同立法合法性問題的擔憂,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新《立法法》第八十三條明確了我國地方區域協同立法的合法性,成為地方以區域協同立法推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法律依據。
深入貫徹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理念的眾多戰略舉措包括有東北振興、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區域性發展戰略,同時也有具體到省的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隨著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實踐的深入,在區域協調發展的主體方面開始出現不同層級的地方協調發展與合作,例如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中的“滬通”“滬杭”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跨越地方行政層級的區域協調發展也帶來了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需要,實踐中出現了跨級區域協調發展的實例。如在成渝地區,雙方因在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發展目標方面高度一致,其良好效果一直被視為同舟共濟合作發展的典范,成都作為四川的經濟重鎮與重慶市開展雙城經濟圈建設合作也是雙方順應發展趨勢的一項重要舉措,通過此類跨級區域協調發展對于具有特殊地緣關系的省市充分利用周邊發達省市資源具有非凡意義,能夠將高層級地方的區域經濟優勢和教育文化等優勢能量輻射到周邊區域,構建起地方新發展格局,推動周邊區域實現共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
跨級區域協同立法指的是不同級別的立法主體在共同發展目標的指引下協同立法的合作行為,在實踐中多表現為直轄市與其他省份的市進行協同立法。跨級區域協同立法能夠進一步豐富我國地方區域協同立法實踐的類型,滿足特殊地區的區域協同立法實踐需要,充分利用高層級地區的優勢資源帶動區域共同發展,但是隨著立法實踐的深入也產生了諸多問題與質疑。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跨越行政級別的協同立法在立法權限、立法主體、立法程序等方面都存在諸多的沖突與矛盾,協同的前提是合作雙方具有一致性,但跨越層級的立法主體在級別一致性方面易產生“分歧”,雙方在級別上的天然差異使協同目標能否真正實現成為了問題,本文從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在現實應用中的困境出發,結合我國區域協同立法的發展路徑與制度設計目的等內容,意圖構建出一條既能夠推動跨級別地區以區域協同立法推動區域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又能規避立法主體由于層級矛盾帶來沖突矛盾的協同之道。
二、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基礎
(一)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現實需求
跨級區域協同立法是不同層級的地方區域實現協調發展的重要法治路徑,隨著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在各地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跨級區域協調發展實踐,如太忻一體化等省會城市與周邊設區的市的區域協調發展,以及構建成渝雙城經濟圈等直轄市與省會城市的區域協調發展,再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涉及地方省級行政區與特別行政區的區域協調發展,各種形式的跨級區域協調發展層出不窮,本文主要研究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形式為省、市之間的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以及省、市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跨級區域協同立法。
區域協調發展在實踐中對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具有強烈的現實需求。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作為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區域協調發展實例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總的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為我國區域發展的重要力量,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審議《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時指出,要通過完善發展理念和區域協同合作機制將成渝雙城經濟圈打造為我國區域協同發展的高水平樣板。[3]2021年1月,滬蘇浙兩省一市共同聯合印發《上海大都市圈空間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是對2017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構建上海大都市圈理想圖景的具體落實,《規劃》將上海市同周邊的蘇州市、南通市、寧波市等8個城市以“1+8”的形式劃入上海大都市圈建設范圍,充分發揮上海的地區優勢,建立以上海為核心、周邊地區為基礎推動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卓越大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建設是新時代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現國內國外雙循環格局的重要舉措之一。上海大都市圈的建設必然涉及上海與周邊城市的具體區域協調發展事項,也必然會涉及到直轄市與設區的市之間的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隨著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需求也不斷提升。2017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出席《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四方協商一致共同簽署了該協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我國在區域協調發展領域的重大突破,是我國建設“一帶一路”戰略樞紐和構建“引進來”“走出去”雙向平臺的重要戰略支點,承載了我國重大發展戰略職能。[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同于一般的區域協調發展,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省級行政區的協調發展屬于跨法域區域協調發展,從立法層級上來看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限高于省級行政區的立法權限,因此特別行政區同省級行政區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制定的協同性立法文件也屬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從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上海大都市圈建設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都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內容,未來我國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領域存在著巨大的立法需求。
(二)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現實特點
⒈具有國家戰略屬性。以區域協調發展的方式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大勢所趨,跨級區域協調發展作為特殊形態的區域協調發展主要分布于國家重點發展區域,如成渝雙城經濟圈、上海大都市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跨級區域協調發展項目,這些發展戰略都已經被上升為國家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5]國家重點戰略的實施和推進不能脫離法治的軌道運行,因此,跨級區域協同立法成為了保證跨級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合法性的重要舉措,故而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也具備了國家戰略屬性。明確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國家戰略屬性有利于對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相關法律規范作出正確的、合目的的解釋,意味著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具備更加深刻的發展內涵和歷史使命。面對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存在的沖突與矛盾應當從有利于推動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發展的角度進行解釋和處理,依托國家重點發展戰略推動實現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⒉立法主體的非一致性。區域協同立法是推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法治途徑,雖然各區域在關系上具有一定競爭性,但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合作內容中更多體現的是合作與協同,因此,區域協同立法也必然反應出各合作區域的“共識”特征,這一特征要求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具備協同立法人格的平等性、行為的共同性和立法法益的一致性。[6]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在前述三個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人格平等性方面,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屬于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在行政級別上具有一定差異,不同級別之間的立法主體在進行立法協商對話時難以形成平等的協同關系,難以跨越行政級別帶來的鴻溝。在行為共同性方面,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在行政級別上的差異也帶來其公權力屬性的差異,高層級立法主體掌握較大的話語權而低層級立法主體則掌握較小的話語權,前述問題并非針對立法權限而是指在具備共同立法意志的前提下協同立法的實施與執行問題,例如直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施行難度就要小于設區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因為后者的法律實施與執行還需要得到上級人大的批準,可見,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在行為的共同性方面也存在矛盾。立法法益的一致性方面,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由于主體層級的差異,在利益考量方面也存在差異,例如省級立法主體要兼顧全省各市的發展,而設區的市立法主體更多考慮自身的利益,雙方在立法法益的衡量與協商過程中也存在立法法益的沖突矛盾。
⒊立法權限存在差異。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在層級上的差異必然帶來立法權限的差異,根據《立法法》規定,省級人大可以在不同上位法沖突的情況下制定地方性法規,而設區的市的人大在遵守上位法的前提下只能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生態文明建設、歷史文化保護、基層治理等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規,省級人大的地方立法權限顯著大于設區的市人大。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種省級行政區與特別行政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更是存在巨大的立法權限差異,特別行政區與內地法律屬于不同法域,其在立法方面的自由空間也遠大于內地省級人大的地方立法權。設區的市只能在規定事項范圍內制定地方性法規,省級人大在遵守上位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規,特別行政區則擁有了更為自由的立法權限,不同層級的協同立法主體之間的立法權限存在巨大的差異,由此也給協同立法一致性的實現帶來了挑戰。
三、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現實困境
區域協同立法制度在最初發展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對協同立法合法性的質疑,在法律尚未明確規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時法治風險成為了區域協同立法制度發展的困境。[7]隨著《立法法》的修改,我國在法律層面確立了區域協同立法制度,但法律的修改并未使得區域協同立法面臨的困境全都隨新法消弭,隨著區域協同立法形式的豐富,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在實踐中應運而生,這種特殊的區域協同立法形態在實踐運行過程中由于其跨級的特殊性為區域協同立法的落地生根帶來了諸多挑戰。
(一)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面臨法治風險
隨著《立法法》的修訂,區域協同立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確認,但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形式還存在一定爭議,一方面在法律規范文義解釋的角度存在歧義,另一方面實踐中的一些區域協同立法行為也存有法律風險。
⒈法律規范具有模糊性。《立法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會員會可以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前述法律文本在表述內容存在不同理解,一方面,可以解釋為A類立法主體和B類立法主體都可以進行區域協同立法,但A類立法主體只能和同類進行區域協同立法,B類同理;另一方面,可以解釋為A類立法主體可以和同類也可以和B類立法主體進行區域協同立法。由于《立法法》第八十三條對于立法主體的設置采取了并排的方式,因此不能明確是否允許省、自治區、直轄市級人大同設區的市、自治州級人大開展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但在實踐中已經出現了眾多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例如廣東省已經率先開展“1+N”模式,其中1指的是省級立法,N則是相關地市的地方性法規,法律規范的模糊性給區域協同立法的發展進程帶來了挑戰。[8]
⒉以非法律形式替代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區域協同立法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但在立法推進的層面還存在一定困難,地方區域協同立法進程中仍然存在以政府間合作協議、紅頭文件等形式開展的“協同立法”,這些協議雖然具備一定優勢能夠有效推動協同立法工作的開展,但是在合法性和執行力層面也存在著明顯劣勢。[9]前述在區域協同立法實踐中的問題也存在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中,并且這些問題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領域只會更加嚴重。合法性層面,地方政府間約定形成的區域協同立法合作協議并無法律依據,法無授權不可為作為公法領域的基本原則普遍適用于一切行使公權力的行為,地方政府之間簽訂區域協同立法合作協議于法無據,因此帶來了巨大的法治風險,其合法性得不到保障就會導致區域協同立法成為一紙空文。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立法主體在行政級別上有高低之分,如果不同級別的地方政府通過合作協議或紅頭文件的形式進行區域協同立法合作,當產生責任問題時則會由于立法主體間的權力大小差異帶來追責難、責任分配不公等問題。執行力層面,由于本身這種合作協議和紅頭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當出現違反協議內容的情況時難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主體之間本身就存在著權力的鴻溝,如果高層級立法主體違反協議內容,低層級立法主體很可能由于“勢單力薄”而吃“啞巴虧”,無法訴諸正當的救濟途徑。
(二)協同立法的一致性與跨級立法權限存在沖突
協同立法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法治手段,要求立法主體之間在立法目的和立法內容上具有一致性。如果立法目的和立法內容無法達成一致就難以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轉而形成各自為戰的發展模式,一般的區域協同立法在立法目標和立法內容層面只需各方立法主體能夠在利益分配、組織協調、統籌安排等方面通過協商談判達成一致,就能在立法目標和立法內容上具備一致性,從而制定出高效服務于區域協調發展的區域協同立法。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由于立法主體層級的不同,在立法權限上也存在較大差異。《立法法》第八十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可以在不違背上位法的情況下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是第八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只能在城鄉保護、環境保護等規定的范圍內制定地方性法規,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在立法權限上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也為實踐中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一致性的實現帶來難題。如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屬于國家重點戰略,這種跨級區域協調發展模式離不開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但經濟圈建設與城鄉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環境保護等內容相去甚遠,重慶市作為直轄市可以在經濟建設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成都市卻無權在此領域制定地方性法規。目前的區域協同立法形式主要還是各方立法主體通過區域協同立法機制達成一致,具體地方性法規的制定還是各自通過地方立法程序進行,成都市即使同重慶市在經濟建設方面的立法達成一致其也難以通過成都市人大的立法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規。這種情況下對《立法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的解讀就出現了分歧,該條規定協同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在本行政區域或者有關區域內實施”,那么在成都市無權制定經濟建設法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通過協同立法機制,在雙方達成一致后,由重慶市人大制定服務于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地方性法規,同時規定適用于成都市。這種由高層級立法主體利用較大的地方立法權制定地方性法規并規定實施于另一低層級立法主體所在區域的行為就帶來了合法性的質疑,因為此種情形雖然在形式上符合《立法法》第八十三條規定的“在有關區域內實施”,但在實質上突破了成都市的地方立法權限制。
(三)立法主體跨級帶來平等性質疑
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往往在行政級別上存在較大差距,主體間行政級別的差異帶來了權力大小的差異,直接影響到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對于利益分配事項等內容的話語權問題。協同意為各方互相配合,配合意味著不同主體間的關系應當是平等的而不能是上下級領導關系,但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中各立法主體在行政級別上存在著大小差異,在行政體制內很難認為這些立法主體是平等關系,由此便產生了對協同立法主體平等性的質疑。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范疇內的平等包含三層含義,即主體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10]在主體平等層面,私法范疇內主體平等意味著雙方權利義務對等,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保護法》中規定了許多增加經營者義務的條款,其目的就是為了平衡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平等關系,由于經營者本身處于優勢地位所以要給予消費者更多的保護以保障雙方主體在民事法律關系中處于平等地位。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中,由于具備了協同性的要求因此對公權力主體之間的平等性也提出了要求,權力不對等的立法主體在不平等的關系下難以制定出能夠平衡協調各區域利益的協同性法規。在機會平等層面,反映到跨級區域協調發展中應當指的是各地區各區域在協調發展戰略中,享有的發展機會和競爭機會是平等的,但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中由于立法主體之間具有行政級別上的差異,即使低層級立法機關不屬于高級立法機關的直接下級也會出于現實行政體制的考慮受到高層級立法主體的影響,在發展機會和競爭機會方面高層級立法主體往往掌握更豐富的優質資源,使得那些低層級立法主體在本身權力小于高層級立法主體的情況下,更加難以與高層級立法主體站在同一起跑線享受協調發展的成果。在規則平等層面,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中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救濟程序的問題,無救濟則無權利,如果協同立法的內容得不到落實就需要通過相應的救濟程序來進行維權,但是在跨級立法主體之間由于主體權力層級的差異為救濟權的落實也帶來了困難,如廣東省“1+N”的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之間,如若代表“1”的省級立法主體違反了區域協同立法的協議內容,那些屬于其下級的“N”將難以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來維護自身的權益,上下級的領導關系打破了協同立法關系中的規則平等,使得規則成為了約束低層級立法主體的單方面約定。
(四)跨級主體立法程序不同帶來協同立法障礙
在區域協同立法實踐中,一般的協同程序表現為各方立法主體通過協商一致制定區域協同立法的合作綱領性法律文件,各方立法主體根據區域協同立法文件的具體要求各自根據相應的立法程序制定具體的地方性法規,如在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區域協同立法實踐中,浙江省、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共同協商確定了一個區域協同立法的標準范本供協同機制內的各成員省市制定地方法規使用。[11]本質上區域協同立法就是在協同立法目標的指引下各立法主體按照各自立法程序制定具有協同性關系的地方性法規的過程。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不同于一般的區域協同立法,由于立法主體層級出現差異導致立法程序的不同也為協同立法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憲法》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實行備案制,并且在備案之前法律即生效,《立法法》規定省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在公布后三十日向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備案,但設區的市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則不是備案制,而是報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若未得到批準則該法規不發生法律效力。特別行政區立法和省級地方性法規均實行備案制,雖然二者在立法權限上不同,但在法律生效方面還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然而設區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規卻必須經過省級人大常委會的批準才能生效,使得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主體在立法程序上出現了差異。備案制與審批制的差異主要表現為法律生效時間的不同,前者公布即生效而后者需等待上級批準若未得到批準則法律不發生效力,對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而言則增加了協同立法失敗的風險。這種風險在實踐中表現為當各層級立法主體就某一區域協調發展事項達成協同立法的一致后分別各自制定了地方性法規,高層級立法主體的地方性法規在公布后發生了法律效力,但低層級立法主體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不被上級立法機關批準,于是就可能出現協同立法而不能協同生效的尷尬境地,區域協同立法往往是多方利益平衡的結果,某一個區域的地方性法規不發生效力對于其他參與協同立法并且制定的法規已經生效的地區而言是不公平的。
四、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困境紓解
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作為跨級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跨級區域協調發展往往能夠充分利用高層級立法主體的優勢資源并整合區域資源統籌發展目標推動跨級區域實現協調發展。
(一)以法律解釋完善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授權性規定
《立法法》第八十三條并未明確規定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但在現實已經存在大量的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實踐,從實踐成果來看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無論是在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還是上海大都市圈建設等領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法律層面明確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的合法性至關重要。在不適宜通過立法程序修改的情況下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法來證成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合法性顯得更為可行。目的解釋是緩和機械性嚴格法治的重要方法,根據現實主義法學派的觀點,法律條文出現空白或矛盾是一種常態,依據目的解釋的方法對規范進行解釋能夠有效消除條文的不確定性,填補條文的空缺,而此處作為法律解釋依據的目的則指的是表現在法律文本中的法律目的。[12]對《立法法》第八十三條的規定進行目的解釋,探尋該規范的目的是否包含了跨級區域協同立法,本質上就是在探究區域協調發展的立法目的中是否包含了跨級區域協調發展,前文中已經闡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具有國家戰略屬性,《立法法》在修改過程中專門制定了相關的區域協同立法機制,應當肯定的是第八十三條的規范目的為鼓勵以區域協同立法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但不能單從區域協同立法屬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上位概念解釋出規范目的包含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結果,因為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在法律效果和立法程序、立法權限上均有別于一般的區域協同立法,但從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結果導向來看,其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目的的實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證明了這是一項有利于推動區域協同立法制度發展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有益制度。因此,應當認為《立法法》第八十三條的規范目的包含了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使其在基本法律層面具備了合法性。通過法律解釋方法肯定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能夠及時緩和由于法律模糊性帶來的不利影響,還能夠通過表明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的合法性減少政府間以非法律形式替代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行為,推動我國區域協同立法事業在法治軌道運行。
(二)遵循地方立法權限的“最大公約數”原則
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作為區域協同立法的特殊形態,在本質上屬于地方人大通過行使立法權致力于同一發展目標的協同性行為,而非單一立法主體的主導性立法行為。因此,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過程中,各立法主體都需要通過行使各自的地方立法權來完成協同立法的目標。《立法法》對于各層級立法主體地方立法權的權限作出了不同規定,省級人大可以在不與上位法沖突的情況下制定地方性法規,但設區的市級人大只能在城鄉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規,二者立法權限存在差異。同時《立法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協同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在“本行政區域或者有關區域內實施”,由此便產生了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時,高層級立法主體制定低層級立法主體不具有立法權限的法規內容并規定此項法規適用于相關低層級主體轄區的合法性問題。這種立法行為在形式上符合《立法法》第八十三條規定,但在實質上突破了地方立法權的限制,不應當允許此種跨級區域協同立法行為的出現。對于《立法法》第八十三條規定的“在本行政區域或者有關區域內實施”應當作出限制解釋,即“在有關區域內實施”的前提必須為有關區域對于此類事項具有地方立法權。如在同省內跨級協同立法時,省級人大可以指定只在某市內適用,因為其具有對此事項的地方立法權。但是在前文所述的跨省協同立法的情況下則不允許,因為A省雖然擁有經濟建設的地方立法權但該立法權的范圍僅限于A省內,如果約定在B省b市適用,雖然在形式上符合其制定經濟建設法規的立法權限,但在實質上突破了省級地方立法權的適用范圍,擴大了地方性法規的適用范圍,同時也有侵犯B省人大的地方立法權之嫌。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不能避免各立法主體在立法權限上出現差異,但能夠避免立法主體突破地方立法權的情形。為保障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合法性,避免協同立法突破地方立法權限而導致立法無效,應當在協同立法時遵循地方協同立法的“最大公約數原則”,即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各主體在進行協同立法時只能針對所有立法主體都具有立法權限的事項進行協同立法,立法范圍就低不就高,由此能夠保障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合法性,保證相關立法內容能夠得到切實有效的執行。
(三)建立健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的特殊備案與生效機制
⒈構建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內容的備案指導機制。《立法法》規定設區的市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需要報請省級人大批準,由此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開展過程中對于低層級立法主體來說要面臨協同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不被上級人大批準的風險。區域協同立法需要各地區立法機關就需要協同發展的事項達成一定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就具體事務在實踐工作中的分歧進行協商談判,在缺乏外在強制力的約束下,協同立法更多依靠的是各立法主體不斷在談判協商中達成的立法共識。[13]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過程中,經過長期談判協商達成的立法共識如果在制定地方性法規后才報請上級人大機關審批則會加劇立法風險和立法成本,一旦法規不被批準那么在長期立法談判中付出的各種努力和經濟成本將付諸東流。因此,有必要確立針對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內容的備案指導機制,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制度中加入上級人大對參與協同立法的低層級立法主體擬立法內容的備案指導,規定當低層級立法主體與高層級立法主體展開跨級區域協同立法合作時應當將協同立法的談判過程和內容報上級人大備案審查,上級人大根據備案內容及時指導低層級人大協同立法工作,當上級人大認為立法內容不妥當時應當提前介入,對相應的立法工作作出指導,針對潛在的問題早發現早解決,避免因事后否定地方性法規效力造成立法資源的浪費。
⒉構建地方性法規協同生效機制。特別行政區法律和省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在生效方面都實行備案制,但設區的市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需經過報批程序才能生效,并且在實踐中即使同為省級人大在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方面的生效時間也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例如在長三角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立法協同工作中,蘇皖浙滬三省一市的協同立法進程耗費數年之久,從最初2015年《安徽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審議通過到2017年12月上海市才完成了對《上海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的修訂,雖然各立法主體在協同立法層面達成了一致但在立法生效實施的時間不同步影響了協同立法的效果。[14]在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中表現為各立法主體根據《立法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區域協同立法工作機制”建立地方性法規協同生效機制,在具體制定協同性地方性法規時明確約定該項法規的生效條件為各個協同立法主體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都通過審議,由此能夠確保各立法主體制定的協同法規同時生效,既保障了協同立法的一致性,又能夠維護各立法主體的協同利益。
結 語
《立法法》的及時修改適應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目標,有效推動了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進程,從京津冀、長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區域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區域協同立法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法治保障能夠確保區域協調發展路徑在法治軌道上運行。跨級區域協同立法作為區域協同立法的特殊形態,對于豐富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樣態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制度目前在立法主體層級、立法權限沖突、立法程序銜接等方面尚存有待完善的空間。我國區域協同立法制度尚處于建構階段,目前還未形成完備的區域協同立法制度。[15]一方面需要在實踐中依靠地方立法不斷探索的經驗來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國家從法律制度層面繼續完善立法頂層設計,實現以區域協調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22-10-26(01).
[2][6]賀海仁.我國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樣態及其法理思考[J].法律適用,2020(21):69-78.
[3]秦鵬,劉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協同發展的理論邏輯與路徑探索——基于功能主義理論的視角[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44-54.
[4]蔡赤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挑戰[J].廣東社會科學,2017(4):5-14+254.
[5]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EB/OL].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18/0913/c40531-30290140.html.
[7]韓業斌.區域協同立法的合法性困境與出路——基于輔助性原則的視角分析[J].法學,2021(2):146-159.
[8]王保民,王琣.區域協同立法的工作機制及其優化[J].地方立法研究,2023(3):37-53.
[9]陳建平.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區域協同立法:問題、成因及路徑選擇[J].重慶社會科學,2020(12):108-118.
[10]張文顯.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J].中國法學,2014(4):5-27.
[11]毛新民.上海立法協同引領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與經驗[J].地方立法研究,2019(2):50-59.
[12]陳金釗.目的解釋方法及其意義[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4(5):36-44.
[13]周澤夏.區域協同立法:定位、特色與價值[J].河北法學,2021(11):85-99.
[14]汪彬彬.長三角區域立法協同研究[J].人大研究,2021(3):24-32.
[15]黃蘭松.區域協同立法的實踐路徑與規范建構[J].地方立法研究,2023(2):18-38.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lief of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Yu Xun, Wei Jianyu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striv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s a special form of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is crucial to the realisation of the goa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then to promote the realisation of the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goals.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has a huge demand for legislation, but in practice,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legality of legislation, legislative authority, equality of legislative subjects, and legislative procedures, which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coordinated legislation system, which can be solved by the method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system.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mechanism of special filing and entry into force of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Key words: cross-level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cooperat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local legislative power; realistic dilemma
(責任編輯:王正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