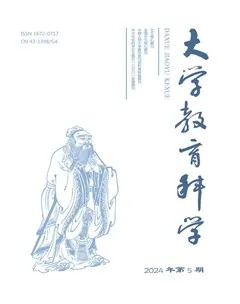塑造國家意識: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創新
摘要: 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是我國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戰略。知識生產是研究型大學的核心職能,知識生產模式創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本體建構的關鍵指向。新型研究型大學知識生產的本質追求是超越國家科學競爭效應中的跟跑狀態與依賴現象,這就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學把國家意識作為知識生產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探索以國家意識為邏輯起點和以知識生產內外部要素反映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的知識生產新模式,通過知識生產模式創新實現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本體建構。
關鍵詞:新型研究型大學;知識生產模式創新;國家意識;要素體系;共治體系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4)05-0019-09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強高校基礎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把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主要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是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世界科技發展大勢與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判斷提出的重要戰略布局,是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戰略部署,成為我國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戰略舉措。研究型大學的核心職能是科學研究,即知識生產,研究型大學在民族與國家中的重要戰略地位主要以知識生產為基礎。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承載著重要使命,在對既有研究型大學、西方發達國家與地區新興研究型大學的超越過程中,應該把知識生產模式創新作為本體建構的關鍵指向,通過知識生產模式創新實現對知識生產跟跑狀態與依賴現象的超越,從而達成新型研究型大學自身的本體建構。
一、新型研究型大學與知識生產模式 創新的本質追求
新型研究型大學是中國本土提出的一個創新概念,其辦學實踐可以追溯至2012年創建的南方科技大學及其后陸續創建的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等一批新建的研究型大學。有學者將這些以新型研究型大學為創生與發展目標的大學的共同特征歸納為,“新世紀出生、新理念導航、新教師隊伍、新學生養成、新內在形成、新外在優勢、新競爭態勢、新主體舉辦、新機制運作以及新體制保障”[1]。隨著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持續發展,這些大學與中國既有研究型大學在辦學理念、機制創新、體制保障、實踐策略等方面逐漸形成一定差異。與此同時,在對新型研究型大學本質特征、戰略發展的認知與實踐上面臨著很多爭論與難題。諸如,新型研究型大學究竟新在何處?為什么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應當如何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等等。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命題,迫切需要學界在理論上進行深入探討。
在發達國家與地區,與中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相對應的是,2011年前后阿特巴赫等學者提出的新概念——新興研究型大學或加速研究型大學[2]。這批大學包括洛桑聯邦理工學院、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奧林工程學院、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浦項科技大學等。發達國家與地區涌現的這批大學的共同特征是,“不同于通過卓越計劃(excellence initiatives)或者其他戰略嘗試得以提升改善的現有大學,這些高校都是新興大學”“擁有大量的經費投入”;“從初創到一流”“以‘加速’(accelerated)的方式追求學術卓越”。阿特巴赫等學者認為,“吸引人才”“把跨學科作為院校基因”“可持續的經費支持”“規范的治理”等是這批大學興起的“基本驅動力”[3]。深入分析阿特巴赫等學者對這批大學興起動因的詮釋不難發現,這些動因實際上也是既有研究型大學面對現代社會知識化的深度演進而謀求發展與轉型的基本策略。
那么,在發達國家與地區興起這批新興研究型大學的根本動力究竟是什么?為什么不通過變革既有研究型大學來實現其特定目標呢?上述原因“似乎都還只是操作層面的原因,未能回答更深層的問題”。深層次原因應該在于“知識”,“這些大學無一例外都是以工程、計算機、生命科學等前沿科技領域為核心……這些學科的特點不僅僅是跨學科,而是融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于一體的跨學科領域。這些大學所關注的不是純基礎學科,也不是純應用學科,而是兩者兼備的知識領域……在傳統的大學中,雖然也可以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也可以局部進行模式2的知識生產,但是由于傳統的大學總體上還是建立在學科邏輯的基礎上,所以全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很難真正推廣。因此,必須另起爐灶,才有可能建立一種與模式2相適應的科研和人才培養模式”[4]。按照陳洪捷的上述觀點,這批大學興起的深層次原因歸結起來就是,積極應對吉本斯等人所說的知識生產模式2以及探索構建相應的人才培養模式,這是新興研究型大學和西方發達國家與地區既有研究型大學之間的關鍵差異。如果進一步追問這批大學積極探索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用“中心—邊緣”的世界科學體系結構觀點來分析①,就是在現代社會知識生產模式轉型過程中還裹挾著“國家科學”的“競爭效應”[5]。而無論是新興研究型大學積極探索知識生產模式轉型,還是既有研究型大學積極適應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追求國家科學在全球科學中的中心地位則是兩者的關鍵共相。
中國為什么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什么不通過對既有研究型大學轉型的方式來實現其目標?毫無疑問,既有研究型大學同樣面臨著現代社會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時代要求,但不可否認的是還面臨著重要的國家使命,即擺脫與超越發達國家在知識生產方面精心打造的“中心—邊緣”等級秩序,在“國家科學”的“競爭效應”中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建設教育強國,實現從跟跑狀態到領跑狀態的超越。由于中國既有研究型大學在很長一段時期的跟跑過程中形成的知識生產依賴現象以及相應的知識生產模式,很難在短時間內進行整體性轉型[6],所以,顛覆這種知識生產模式在時間與資源上需要付出超常成本。隨著國家科學中的競爭效應愈發凸顯、21世紀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加快推進,創生一種新型研究型大學來促進知識生產模式創新,就可以在大學與知識生產模式創新的機會、方式、時間、資源等方面進行低成本的重建、最佳方案的設計以及最少路徑的依賴。也就是說,通過新型研究型大學與知識生產新模式的互構與互創,實現對知識生產跟跑狀態與依賴現象的超越,是中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本質追求。這也是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以及西湖大學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得到“國家重點支持”,確立“趕超世界一流”“國家使命”等戰略目標的重要緣由。
新型研究型大學本質追求的實現要求把國家意識作為知識生產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探索構建一種以國家意識為邏輯起點的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所謂知識生產模式,就是吉本斯等人所說的知識生產的“理念、方法、價值以及規范的綜合體”[7],是知識生產目標、方式、評價等內部結構性要素,知識生產主體、生產資料以及兩者之間互動關系等外部結構性要素,在主體的知識生產意識作用下形成的系統化集成。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創新,既要反映知識生產模式從模式1向模式2、模式3轉型的時代之變,更要反映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建設教育強國的國家使命,把國家意識作為知識生產模式內外部結構性要素建構的邏輯起點。以模式1為代表的傳統科學的主要特征是,以“科學的”“學術興趣”為知識生產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追求知識的科學化目標與“科學共同體”的認可,“學院組織”科學家是科學活動的主體,科學活動的認知論、知識論、方法論遵循“牛頓典范”,形成具有鮮明特質的“學院科學”①。在近四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科學”知識形態分化等原因,企業、政府研發機構等組織不斷參與知識生產并形成異質于“學院科學”的“產業科學”“政府科學”[8]31、40,進而形成以大學、企業、政府研發機構等“部門”為載體的傳統“科學”知識生產的整體性模式——“部門化科學”,也可以稱為寬泛意義上的模式1。模式1知識生產的總體特征是,生產目標與社會需求分立、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分立、學科分立、知識生產主體分立。
模式2知識生產的主要特征是把“應用情境”中“知識”的“供應與需求”作為知識生產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追求知識生產的主體協同、部門融通、學科溝通以及過程反思,強化知識生產的社會責任,尋求對以“學院科學”“部門化科學”為表征的模式1的突破②。在模式1向模式2轉型的思維框架基礎上,許多學者基于發達國家知識生產狀況,從不同維度提出了“模式3”概念,其中,卡拉雅尼斯等人從創新生態學視域構建的模式3理論具有一定代表性。模式3知識生產的核心特征是,在“地域空間層次”“研究層次”“教育層次”等維度構建知識生產目標取向的“多層次”;在“部門集群”“知識集群”等構成的創新網絡上的每一個節點構建知識生產要素復雜聚集的“多節點”;通過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有機結合構建知識生產過程復雜連續體式的“多形態”;通過不同社會角色主體參與知識生產構建主體結構的“多邊”。這些特征概括起來就是形成以公民科學為表征的“四螺旋科學”,進一步尋求對模式1的突破;適應“高級知識經濟社會”與“全球本土化”趨勢[9],尋求對模式2的突破。
然而,當我們真正站在全球視角反思模式3知識生產圖景時,不難發現其對模式2超越的有限性。模式3所構建的“全球創新生態”是以發達國家為軸心的創新生態系統,所追求的“全球本土化”是以發達國家為對象的本土化。模式1向模式2再向模式3的演進實際上主要從發達國家視野刻畫了科學社會化與社會科學化加快推進以及科學—社會共同體加快型構的發展趨勢,但如何真正站在全球視野特別是后進國家視野促進科學全球化的加快實現,促進后進國家科學的迅速發展,還需要知識生產模式的深度創新。這種以國家意識為邏輯起點的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可以稱為“知識生產模式4”或“模式4”,這既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本體建構的核心指向,也是對既有研究型大學、新興研究型大學進行本體性超越的關鍵所在。
二、新型研究型大學知識生產模式創新的國家意識
知識生產國家意識的塑造,既是科學從純粹知識活動向社會活動轉型后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特殊國情、大國地位的時代需要。黨的二十大確立的重要主題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興國”“強國”“國家戰略”“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二十大以來黨的方針政策的一個重要指向。以前沿科學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為戰略目標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塑造知識生產的國家意識,既是國之所需,又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內生邏輯。知識生產的國家意識集中體現為知識生產主體在國家科學的競爭效應中,把國家科學的主體存在、戰略目標作為知識生產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并進行知識生產模式內外部結構性要素的建構。一個國家中,知識生產主體的國家意識表現為,從基礎層位價值追求向高階層位價值追求發展和分布的金字塔形態。基礎層位價值追求是主體知識生產國家意識的基礎,主要體現為把科學技術創新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在基礎層位價值追求基礎上形成的高階層位價值追求,主要體現為在國家科學的互動中搶占制高點,在關鍵核心領域形成國家科學的核心競爭力和全球競爭力。世紀之交,美國為了應對激烈的國家科學競賽提出“保持在所有科學前沿領域領先地位”的戰略目標,“美國科學家必須在所有主要領域的前沿中進行工作,以長期保持和促進我們的競爭地位”[10]20。美國的科技戰略目標充分體現了知識生產的美國國家意識以及美國國家意識中的高階層位價值追求。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本質追求與戰略目標內在地指向知識生產的中國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而知識生產模式4就是以中國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為邏輯起點,通過內外部結構性要素與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的相互建構獲得整體性生成。其中,內部結構性要素對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的反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知識生產目標的國家立場
知識生產目標的國家立場就是把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作為知識生產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充分發揮國家意識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定向”功能[11]15,進而將這種精神追求與價值定向轉化為解決特定問題的目標。按照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知識生產目標的國家立場就是將知識生產對象聚焦于引發并破解科學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科學中的科學與技術革命問題。它主要體現為三方面:一是常規科學中聚集大量共同指向的反常科學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會影響國家科學中一些學科領域的整體性突破;二是常規科學中出現亟須破解的反常科學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會影響國家科學中一些關鍵領域的突破和主動權;三是常規科學中出現長時間難以破解的反常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成為國家科學中的老大難問題[12]。上述問題實際上是國家科學中“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頸問題”[13],可以統稱為國家層面科學技術瓶頸問題(以下簡稱國家瓶頸問題)。17世紀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胡克定律等具有科學革命意義的重大發現的提出,從根本上說就是英國科學共同體把國家瓶頸問題作為知識生產目標,開展那些“能夠幫助英格蘭謀求經濟上的統治地位的發明活動”、選擇“自己國家國民經濟中最迫切的特殊問題”[11]193,208作為研究課題的結果。
在現代社會的知識化與全球科學中國家科學競爭效應的雙重變奏過程中,把國家瓶頸問題作為知識生產目標,既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國家之間利益博弈與科技競賽的必然要求。國家瓶頸問題的本質屬性與表現形態具有復雜性,把這些問題作為知識生產目標需要采取針對性的知識生產策略。第一,國家瓶頸問題主要是復雜的超學科問題,它們既不是單一學科域定的知識問題,也不是既定學科范式中的問題,而是復雜的跨學科、超學科或學科革命問題。雖然不同學科都能感知與體驗到破解這些問題的緊迫性,但囿于學科知識規訓往往難以切入,勢必要求模式4突破傳統的學科邊界或學科范式,以問題域為研究對象,形成多學科或超學科的知識生產方式。第二,國家瓶頸問題主要是復雜的跨部門問題,這些問題不單單存在于同質性部門當中,大學、企業、政府等異質性部門也都有呈現或都能感知到,但由于知識生產方式、能力、資源等方面限制往往無法破解這些問題,勢必要求模式4突破傳統的部門與組織邊界,在不同部門與組織之間形成知識生產的集體行動。第三,國家瓶頸問題往往處于知識生產過程的斷裂帶,創新出現斷層,既可能是基礎研究中的前沿難題、應用研究中的工程技術難題,也可能是產品開發中的關鍵核心技術難題,這些難題無法得到系統與徹底解決,勢必要求模式4突破知識生產過程的科學—技術線性分工習性,形成知識生產—應用一體性的良性互動循環。
(二)知識生產方式的國家創新
所謂知識生產方式的國家創新,就是以原創性解決國家瓶頸問題為目標,通過塑造知識生產的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超越組織、部門等知識生產主體之間邊界,統合不同風格主體知識生產方式的優勢,基于學科而又超越學科,形成知識生產過程(生產—應用)與生產內容(科學—技術)縱橫交織的一體化運作模式。學科是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等不同形態知識生產的主要載體,學科形態一旦建成,就在知識邏輯與制度邏輯的雙重作用下,形成以知識的集成化為目標、以特定知識范式為規訓工具的知識運行機制[14]。學科知識運行機制的核心內涵有三:其一,知識運行機制是復雜的系統工程,知識運行主體包括大學、企業、政府研發機構等多樣化部門與個體,知識運行過程包括生產、傳播、應用等多個環節。其二,知識運行結果指向科學知識或技術知識或兼而有之的系統化集成。其三,由于內在的知識邏輯與外在的制度邏輯的雙重作用,知識運行在主體、過程、結果、邏輯理路等方面形成了“學院科學”“產業科學”“政府科學”等不同風格主體科學。“學院科學”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學研究人員”為主體,以“論文和期刊”為知識載體,“為知識而研究”[8]23-24、35;“產業科學”以“企業研發人員”為主體,以“專利”或技術秘密為知識載體,形成“應用研究”或“開發研究”[8]35-36;“政府科學”的特點為“既是政府資助的,又是在政府實驗室里進行的”研究,主要基于“市場失靈和公共物品”而選擇研究問題[8]40-42。模式1時代知識生產的主要特征是不同風格主體科學處于分立狀態,形成“部門化科學”,模式1的核心指向是“學院科學”,而模式1向模式2與模式3演化的本質就是追求“學院科學”與“產業科學”“政府科學”的融合。
國家瓶頸問題的超學科性、跨部門性以及知識生產—應用一體性等特征,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塑造知識生產的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形成知識生產方式的國家創新。其基本策略是,吸收“學院科學”的優勢,尊重科學的自發性,強調基礎科學知識生產,致力于國家瓶頸問題在科學原理層面的破解;吸收“產業科學”的優勢,根據產業技術發展需求規劃知識生產目標,強調知識生產著力于解決產業技術發展中的問題,運用基礎科學知識破解產業技術發展中國家瓶頸問題的原理與方法;吸收“政府科學”的優勢,針對“市場失靈和公共物品”進行問題選擇,促進知識生產目標向破解國家瓶頸問題匯聚。概括起來,知識生產方式的國家創新就是以國家瓶頸問題為中心,充分利用學科知識運行機制,超越單一學科規訓甚至學科規訓,形成跨學科甚至超學科的知識運行機制。一方面,從基礎科學層面破解問題,并逐步向應用領域轉化,形成從基礎到應用方向的技術化應用與拓展。另一方面,根據應用領域需求從技術層面破解問題,然后逆向引發基礎科學知識生產,實現從應用到基礎方向的科學化還原與超越,最終實現前沿創新與轉化循環之間的互動,即知識生產過程(生產—應用)與生產內容(科學—技術)的一體化運作。
(三)知識生產評價的國家標準
知識生產目標國家立場與知識生產方式國家創新的實現程度需要通過知識生產評價的國家標準進行評判。知識生產評價是知識生產利益相關主體對知識生產目標的達成度、方式的合理性、效益的滿意度等知識生產績效進行評估的過程。知識生產評價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評價標準的選擇是最為關鍵的環節。既有研究型大學崇尚“學院科學”知識生產方式,知識生產評價推崇“學科法則”,把學術論文、學科影響力、學科價值等作為主要評價標準,以學科發展為主要尺度,把學術刊物的影響因子、學術論文的被引次數等“不是評價學術水平與創新貢獻的直接依據”作為評價標準[15]。更有甚者,在科學全球化過程中弱化知識生產的國家意識,通過“SCI評價標準”逆向驅動知識生產的方向與選題,并將這些評價標準與知識生產的資源投入、績效分配、獎勵機制等有機聯系起來。可以說,學科法則及其衍生的強化發達國家科學、弱化發展中國家科學的SCI評價標準已經成為解決國家瓶頸問題的重要障礙。
知識生產評價的國家標準意指把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作為知識生產評價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綱領,把國家瓶頸問題的破解程度與知識生產方式的國家創新作為內在評價標準。其主要指向有三:一是在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互動中追求國家瓶頸問題的原創性與突破性解決,追求國家科技創新的核心競爭力,擺脫長期以來追蹤西方發達國家大學知識生產選題方向與運行機制的路徑依賴[16]。二是追求破解國家瓶頸問題的綜合能力(諸如,從基礎科學到技術開發的整體性問題解決能力,人才、設備、經費等知識生產資源的集聚能力),超越SCI評價標準的工具理性,追求知識生產的價值理性。三是追求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互動中知識生產能力與人才培養能力之間的互動,促進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過程、方式、要素之間的互嵌,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全球科學視野、科學的本土化應用能力,把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度等作為知識生產評價標準。這些解決國家瓶頸問題的突破性、整體性、可持續性評價標準,集中體現為知識生產能力的超越性。
三、新型研究型大學知識生產模式創新的支持策略
“科學不能依靠自身單獨生存”[17],“所有科學技術活動都不是與世隔絕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域境(context)、政治域境和經濟域境中進行的”[8]8。知識生產模式4的構建需要通過知識生產主體、生產資料以及兩者之間互動關系等外部結構性要素的系統化重建來支持內部結構性要素的邏輯生成。當下,我們可以運用中國傳統的“共治”思想來型構這些外部結構性要素的內在邏輯關系并賦予其時代精神內涵。“共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在于治理主體之間以及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之間的共生,強調利益相關主體特別是權力主體圍繞共同目標實現,形成主體間的雙向互動與互利互惠以及主客體間的相互建構與共生共存。新型研究型大學運用共治思想構建模式4的支持策略就是通過外部結構性要素與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的雙向建構,形成主體共治、知識形態共治以及利益共治的治理體系。
(一)主體共治策略
主體共治就是打破社會體制分立與社會分工隔閡,統合大學、企業、政府等不同部門與不同學科中的知識生產主體,圍繞知識生產目標形成互動合作的集體行動。由于國家瓶頸問題的超學科性、跨部門性、知識生產—應用一體性、評價超越性等特征,知識生產過程(生產—應用)與生產內容(科學—技術)需要形成一體化運作,這就對知識生產主體間關系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學構建不同于既有研究型大學的內外部治理結構,促進知識生產主體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形成“集體行動的邏輯”。問題的難點在于,不同部門與不同學科當中的知識生產主體,如何圍繞國家瓶頸問題,超越組織邊界區隔、組織職能分化、生產過程分裂、區域資源阻隔、體制機制分立等方面的規訓,推動跨部門、跨組織、跨學科、跨國界集體行動的形成,促進大學內外部知識生產主體共治格局的形成。
公共選擇理論代表人物奧爾森認為,不同主體構成的“小集團”,基于社會分工與自身立場的理性設計,容易形成“大集團”集體行動的困境。破解國家瓶頸問題,對于“大集團”的國家和社會來說具有“公共性”,但對于不同部門與不同學科中的“小集團”來說,能否為公共性的“大集團”利益去努力,則存在零和博弈、正和博弈等多種境遇。在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同在、小集團利益與大集團利益并存的情況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18]2。奧爾森提出,促進不同主體從“排他性”的“小集團”走向“相容性”的“大集團”,關鍵在于通過兩種相互聯系的激勵方式形成集體行動:一種是以“使命認知”及其衍生而成的文化環境等非經濟性手段為基礎形成的“社會激勵”[18]56-57,關鍵策略是不同部門與不同學科中知識生產主體基于社會分工與社會文化形成知識生產的共同使命;另一種是以“物性資源”及其衍生而成的制度設計等創新性手段為基礎形成的“選擇性激勵”,關鍵策略是“對個人偏好的價值要大于個人承擔集體物品成本的份額”[18]50。
公共選擇理論對構建主體共治格局的重要啟示是,新型研究型大學要把國家意識中高階層位價值追求作為不同部門與不同學科知識生產主體形成集體行動的“社會激勵”基礎,促進不同主體形成破解國家瓶頸問題的使命意識;在承認主體社會分工、組織邊界以及資源稟賦優勢的基礎上設計“選擇性激勵”,激發不同主體參與集體行動的內在驅動力,促進不同主體功能的差異化發揮。首先,基礎科學知識在應用上的間接性決定它只有通過應用研究或者與產業結合進行研究才能破解實踐中的問題,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學需要在問題識別、應用預測、市場需求、經費投入等方面與企業進行互動。其次,由于知識生產結果的不確定性,新型研究型大學需要在科學前景、社會需求、風險防范、經費投入、應用預測等方面與風險投資機構進行互動。最后,由于國家瓶頸問題往往圍繞市場失靈的彌補或公共物品的供給等問題,政府經費投入成為知識生產主體互動關系形成的重要推動力,新型研究型大學需要在問題識別、社會需求、經費投入等方面與政府進行互動。
(二)知識形態共治策略
知識形態共治即知識生產主體充分利用不同形態知識的運行規律與功能優勢,超越知識形態分化的界限,形成科學知識技術化應用與技術知識科學化超越的轉化循環。知識生產區別于其他社會生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生產資料的復雜性,包括既作為生產對象又作為生產原料、生產工具的人類認識成果的知識性生產資料,以及作為生產工具的實驗設備等物質性生產資料。其中,前者是影響知識生產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所謂知識性生產資料,其核心就是用什么樣的知識進行生產以及生產什么樣的知識。知識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其中知識形態是分析知識生產問題的關鍵視角。根據知識的認知與實踐的生成順序、功能優勢、相互作用、運行規律等方面關系,知識主要分為“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兩種形態。“科學知識是關于事物原因的、必然的、普遍的、永恒的認識”[19]139,主要回答事物“是何”與“為何”。作為人類一種“魔法”的技術知識在人類認識與實踐中也逐步演化形成自在的“知識體系”[19]217,219,表現為“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一種裝置、一種方法或一個流程”[20],主要回答事物“如何”與“應何”。
由于近現代“科學成果的迅速積累還是不可避免地迅速導致勞動分工”[21],知識生產的專業化與部門化相互建構、相互促進,加快了部門化科學的型構,進而促進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兩者在生產方式、存在形態等方面形成不同特點。科學知識主要按照知識本身的邏輯,由“學院科學”及“政府科學”生產,往往忽視知識的技術化應用,主要處于主體認知自在狀態。技術知識主要按照產業發展的邏輯,由“產業科學”及“政府科學”生產,往往忽視上升到科學原理層面,主要處于產業應用層面,處于主體實踐自為狀態。隨著現代社會知識化的深度演進,“在技術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技術離人們的勞動經驗越來越遠,科學理論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在科學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科學離人們的感覺經驗也越來越遠,實驗設備、技術手段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以至于“科學日趨技術化,技術日趨科學化”[19]223。但是無論如何,“兩類知識間的鴻溝”是難以消除的[22],其本體差異、模糊邊界、轉化循環及其衍生而來的表達載體、資源利用、績效評價等方面問題成為影響模式4建構的重要因素,需要通過知識形態共治來促進知識生產過程(生產—應用)與生產內容(科學—技術)一體化運作的形成。
回溯主要發達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演替可以發現,二戰前后英國逐漸偏離世界科學中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視基礎科學知識生產,忽視科學知識的技術化應用與技術知識的生產。二戰之前,“英國擁有世界1%的人口,貢獻了8%的科學出版物,取得了9.1%的世界科技引文。但與此恰成對比的是,二戰之后,英國經濟競爭力持續下降,而且與主要經濟大國之間差距不斷擴大。反思上述事實,問題并不在于可以因此懷疑科學知識生產在當代的重要性,而在于要改變關于科學知識與技術創新關系的傳統觀念”[23]。與之相反的是,二戰結束之后,作為后發外生型國家的日本在科技方面迅速崛起,關鍵戰略是在知識生產方面建立了國家創新系統,大學、企業、政府等不同部門將知識生產定位于“巴斯德象限(Pasteur’Quadrant)”[24]。“日本科學技術政策所強調要加強的‘基礎性研究’卻并非是本來意義上的‘基礎研究’,而是‘基礎的研究’或‘基礎技術研究’。實際上它包括著、以至于主要是指某些帶有實際應用目的的基礎性技術研究。”[25]二戰后日本國家創新系統知識生產的這些特點實質上就是知識形態共治,即不同部門與不同學科中知識生產主體在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生產過程中進行互動,圍繞重大課題形成科學知識技術化應用與技術知識科學化超越的轉化循環,而大學的主要職責是發揮不同主體之間互動、不同形態知識轉化循環的“發動機功能”。新型研究型大學要充分發揮不同形態知識轉化循環的發動機功能,就必須以國家瓶頸問題為中心,基于學科而又超越學科,統合部門化科學的各自優勢,積極推動不同知識生產主體之間的信息互動與功能互補,特別是在問題識別、應用預測、學科交叉、知識轉化等方面發揮不同主體的驅動作用,形成知識形態轉化循環的集體行動。
(三)利益共治策略
知識生產關系包括知識生產主體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多重關系,其中資源投入與績效產出之比形成的利益關系是影響知識生產模式建構的重要外部結構性要素。其關鍵是促進不同部門與學科的知識生產主體共同投入物質性生產資料,在此基礎上取得高效產出,科學合理地進行績效分配,實現知識生產資源投入、績效產出、績效分配整個過程的利益共治,從根本上促進主體共治與知識形態共治的形成。由于全球科學中國家瓶頸問題的復雜性,知識生產所需要的資源無法由大學、企業、政府等不同部門中單一主體投入,所以,這就需要我們打破資源的主體歸屬界限,共同投入知識生產資源,吸引全球科學資源,同時追求知識生產績效的最優化,形成資源投入與績效產出的利益共治機制。
利益共治是多重利益關系的整體性建構,既包括知識生產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又包括知識生產主體的投入與產出利益關系,需要從不同視角進行綜合設計。第一,在時間方面,短期內能夠實現產業化應用的知識應該采取以市場化投入為主的策略并進行相應的利益分配;短期內無法實現產業化應用,只能產生公共效益或者需要長期投資的基礎科學知識,則應該采取以政府投入為主、市場化投入為輔的策略。第二,在空間方面,需要打破資源歸屬的組織界限、部門界限、區域界限、國家界限,根據問題解決需要形成資源投入的集聚效應。第三,在資源方面,需要對智力資源、物質資源、資本資源、科學資源、技術資源等不同性質知識生產資源進行整合,對資源投入、績效產出、績效分配的全過程進行系統評估與綜合設計。概言之,利益共治是多要素、多過程、超地域、跨界限的復雜建構,新型研究型大學不僅需要動員不同部門與學科主體共同投入資源,形成資源投入的集聚效應,而且需要根據資源投入規模、績效產出進行績效分配,形成績效分配的溢出效應,同時,還需要聚焦國家瓶頸問題的有限領域,采取小規模辦學策略,科學設計內外部治理結構,形成知識生產的即時效應。
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取得和維持“世界科學中心”地位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建造大科學裝置,“提供推動世界水平的研究所需要的物質基礎設施,包括提供最先進的儀器設備,提供世界水平的信息和通信系統”[10]6。由于國家瓶頸問題的解決往往需要大科學裝置,大科學裝置投入機制的構建便成為利益共治的難點。其重要原因在于,資源投入巨大而績效難以在短期內產出或難以按照預期目標進行評估,需要在資源投入與績效產出的效益、效應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與設計,形成利益共治機制。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可行策略是發揮“邊界調控功能”,即在資源投入與績效產出的邊界劃分與協調過程中充當“鼓動者”與“協調人”角色。從解決國家瓶頸問題的利益大局出發,動員不同部門與學科主體形成共同投入資源的集體行動,根據資源投入規模、績效產出進行績效分配,促進資源投入與績效產出形成良性循環,關鍵是要促進不同部門與學科主體基于國家意識形成投入與產出的利益關系。正如美國在世紀之交形成的基于國家利益的科學與技術發展使命,“科學——既是無盡的前沿也是無盡的資源——是國家利益中的一種關鍵性投資”[10]13“技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技術上的全球領先地位對于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26]等目標理念成為利益共治策略的觀念基礎與行動指南。
四、結語
通過對新型研究型大學及其知識生產模式創新的本質追求、內外部結構性要素等方面的整體性建構可以看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創新不僅深刻反映以模式2、模式3為基本標識的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時代變革,更重要的是深刻反映全球科學背景下中國國家科學趕超的目標使命。這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本體建構的核心指向,是對既有研究型大學、新興研究型大學進行本體性超越的關鍵所在。新型研究型大學主要圍繞模式4進行本體性構建,我國的一些頂尖研究型大學也在一些學科、領域甚至整體上探索模式4的知識生產,體現模式4的戰略目標。相形之下,我國大學系統中眾多既有研究型大學、應用型院校以及技能型院校知識生產的國家意識主要定位于中階層位與基礎層位的價值追求,戰略目標主要定位于區域引領與服務功能的實現。從歷史角度看,新型研究型大學探索的知識生產模式4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是全球科學與國家科學之間互動以及國家科學之間博弈的產物,是國家科學與高等教育創新體系的組成部分。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實踐的不斷發展,我們亟須構建基于國家意識而又超越國家意識的知識生產模式,通過知識生產模式的不斷超越推動中國特色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新發展。
(本文寫作中得到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龔放教授、鹽城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榮博士的指導,在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沈紅.新型研究型大學,“新”在哪里?[J].復旦教育論壇,2021(6):5-7.
[2] Altbach P G,Salmi J.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M].Washington:World Bank,2011:63-64,333-334.
[3] 菲利普·阿特巴赫,等.新興研究型大學:理念與資源共筑學術卓越[M].張夢琪,王琪,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1-11.
[4] 陳洪捷.新型研究型大學崛起的深層原因[J].復旦教育論壇,2021(6):9-11.
[5] 謝宇,亞麗珊德拉·A.齊沃德.美國科學在衰退嗎?[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119-120.
[6] 趙炬明.從跟跑到領跑:美國的經驗與中國的未來——中美科技競爭下美國科學體系與研究型大學制度研究系列之一[J].高等教育研究,2023(1):25-45.
[7] 邁克爾·吉本斯,等.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M].陳洪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
[8] 布里奇斯托克,等.科學技術與社會導論[M].劉立,等譯.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9] Carayannis E G,Campbell D F J.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FREIE)Ecosystem: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Mode 3”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1
(3):340-347,358-367.
[10] 威廉·J·克林頓,小阿伯特·戈爾.科學與國家利益[M].曾國屏,王蒲生,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
[11] R.K.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M].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2]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81-83.
[13] 佚名.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 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
[14] 龔怡祖.學科的內在建構路徑與知識運行機制[J].教育研究,2013(9):12-24.
[15] 教育部,科技部.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EB/OL].(2020-02-18)[2023-04-10].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3/content_5486229.htm.
[16] 丁建洋.科學的本土化應用:西湖大學科學活動的邏輯圖景——一種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改革方略[J].江蘇高教,2019(3):30-36.
[17] V·布什,等.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04:72.
[18]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19] 林德宏.科技哲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0] 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什么,它是如何進化的[M].曹東溟,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8.
[21] 亞·沃爾夫.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上冊[M].周昌忠,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5.
[22] 波蘭尼.科學與技術[A].吳國盛.科學二十講[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97.
[23] 李正風.科學知識生產方式及其演變[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254.
[24] D.E.司托克斯.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彥,谷春立,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91-92.
[25] 張利華.日本戰后科技體制與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174,178.
[26] 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技術與國家利益[M].李正風,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50.
Shap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 of New-model Research Universities
DING Jianyang LI Zhifeng
Abstract: To develop new-model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a key strategic initiative for China in its pursuit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power.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 is a crucial direction for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new-model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 essential pursuit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to transcend the state of trailing and dependency i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competition. These universities are not just participants but key players in this competition. This necessitat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to regar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the spiritual trait and value guidelin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y must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wi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whe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reflect the higher-level values pursued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us, new-model research universities achieve their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through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
Key words: new-model research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lement system; co-governance system
(責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