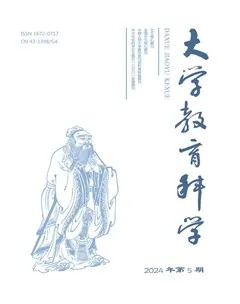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空間溢出和門檻效應











摘要: 研究生教育賦能鄉村振興,是新時代賦予研究生教育的使命,也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基于我國31個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數據構建鄉村振興指數,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空間計量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考察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結果發現: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結果在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處理后仍然成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夠突破空間限制產生輻散效應,對相鄰地區鄉村振興呈現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逐步跨越兩道“門檻”,其對鄉村振興的賦能作用呈現出“邊際遞減后回彈”特征;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助推鄉村振興存在顯著的多維異質性,主要體現在鄉村振興子維度、研究生學歷層次和地區受教育水平三方面。基于此,建議從因地制宜擴大研究生規模、強化研究生人力資本“轉移支付”并開展鄉村數字畫像等方面為鄉村振興事業提質增效。
關鍵詞:研究生教育規模;鄉村振興;空間溢出效應;多維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4)05-0059-12
近十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實現“跨越式發展”。2022年我國在校研究生數突破365萬,研究生規模穩居世界第二[1]。隨著研究生規模擴張,大量畢業生涌入市場,研究生就業愈加艱難。學界有觀點認為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拉低了研究生培養質量[2]、加劇“學歷貶值”和“過度教育”現象[3]、甚至擠占本科教育資源[4]等。但事實上,在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的同時,研究生培養模式也在持續改革創新,研究生教育的社會效益不斷釋放[5]。特別是2023年5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國農業大學“科技小院”研究生的回信中,著重強調了“課堂學習和鄉村實踐結合”的創新培養模式,充分肯定了研究生深入基層一線,為有效助力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發展、服務鄉村振興作出的貢獻。據調查統計,涉農專業的研究生在“三農”領域就業比例已從2017年的40%提高到2021年的80%[6]。
然而,僅靠涉農專業研究生畢業后奔赴鄉村、振興鄉村是遠遠不夠的。隨著數字革命浪潮席卷“三農”領域,我國農業農村正在經歷巨大沖擊。農業農村需要高層次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支教支農需要多類別、多學科的研究生[7]。只有更多有學識、有擔當、有能力解決農業生產中實際問題的研究生奔赴農村,才能逐步改變農村生態;唯有多類別的助力、多學科的協同才能充分發揮研究生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賦能作用。2023年12月發布的《教育部關于深入推進學術學位和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分類發展的意見》指出,我國要提升專業學位研究生比例,大幅增加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數量。也就是說,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將培養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新時代應用型研究生,能夠通過政策引導與制度設計扎根鄉村,促進鄉村人力資本積累。除此之外,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夠加快前沿數字技術創新[8],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為全面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助力。
一、問題的提出
綜觀現有研究,學者較多從職業教育和農村社區教育的角度揭示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9-12]。在農業現代化的新時代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從人才結構、培養特點以及產教融合方式等不同視角尋求鄉村振興的新賽道。目前,研究生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相關研究很少,僅有的研究也以邏輯演繹為主,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大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需要更科學、更有效的證明。以下問題亟待實證驗證:第一,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是否影響鄉村振興,影響程度如何?第二,當前研究生招生并非僅面向本省,畢業生也不只留在本省就業。我國研究生教育資源豐富的省份會產生顯著的“虹吸”和“人才流動”現象。那么,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能否突破空間區域約束,產生輻射帶動效應?第三,長期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在不同地區間發展不充分和不平衡問題十分突出,研究生規模呈現高度集聚化[13]。在此背景下,不同規模的研究生教育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是否存在門檻效應?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基于我國2011—2020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鄉村振興指數,采用STATA17.0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實證考察了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并應用空間杜賓模型考察不同空間權重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空間溢出效應,進一步借助分組回歸和面板門檻模型,揭示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影響鄉村振興的多維異質性,以期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有益參考。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近年來,伴隨著研究生規模持續擴大,高校畢業生的年均增長速度遠高于城市就業崗位的年均增長速度,城鎮就業崗位已無法滿足畢業生的需求[14]。為解決城市“一崗難求”和鄉村“一才難求”的窘境,我國出臺一系列基層就業政策鼓勵和引導高層次人才到中西部、艱苦邊遠地區和鄉村基層就業。加之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相繼實施,基層人才需求大幅增長,前往縣鄉就業已經成為研究生就業的選擇趨勢。邵頔基于Z大學2009—2019年研究生就業數據,闡釋我國“雙一流”高校研究生基層就業現狀,研究發現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選擇縣鄉就業的研究生總人數持續增長,研究生基層就業增長速度呈現“先緩后急”態勢[15]。游蒞薈等進一步分析38所985高校2017—2022年就業質量報告發現,高校畢業生尤其是碩士研究生到基層單位就業比例呈現持續上升趨勢[16]。不難看出,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不但能培養更多高水平人才,還能通過鼓勵性基層就業政策(如“西部計劃”“三支一扶”等專項計劃)為縣鄉基層輸送高層次實踐型人才,實現鄉村人力資本的“外源式輸血”。
與此同時,鄉村振興所需的人力資本也依賴于服務鄉村的學校教育體系[17]。我國相繼提出“鄉村教師支持計劃”“強師計劃”“優師計劃”“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為研究生學歷鄉村教師培養和發展提供完備的支持體系。據教育部統計數據,相較于2012年,2022年我國基礎教育階段研究生學歷的鄉村教師數量實現“飛越式增長”,同比增長278.29%[18]。伴隨著研究生規模擴張、學齡人口銳減以及人才強國戰略轉向高學歷教師培養,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學歷教師進入鄉村隊伍[19]。有研究基于PISA數據證明,教師隊伍中碩士學歷比例每增加10%,學生學業能力平均提升10.2個單位[20]。因此,研究生規模擴張將帶動更多研究生學歷教師進入鄉村隊伍,成為推動鄉村教育發展的強大內生動力,助推鄉村人力資本實現“內生式造血”。已有研究證明,提升鄉村人力資本存量能提升生產要素利用率,正向拉動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有效降低貧困發生率[21]。因此,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為鄉村地區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外生推力”和“內生動力”,進而帶動鄉村發展新質生產力[22],有效促進農民增收,為農民實現“生活富裕”目標賦能助力。
除此以外,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還通過“重構產業、治理生態、反哺教育和知識溢出”等途徑助推鄉村振興。第一,研究生教育作為“科技創新的開創者”和“技術變革的引領者”,其規模擴張能夠推動科技創新和數字技術發展[23],并依托“科技小院”“產學研協同”“科技特派員”等創新培養模式[24],帶動農村科技和產業融合,實現農業產業鏈智能化,助力鄉村“產業興旺”目標的實現。例如,參與科技小院培養的研究生被長期派駐到農業生產一線,在農業生產工作情景中開展科學研究和新型農業技術推廣,解決實際中的農業生產問題。近十年來,隨著研究生規模擴張,科技小院研究生隊伍日益壯大,開展的田間觀摩活動輻射8萬余人,累計培訓農民20余萬人,科技小院成為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有效途徑[25]。第二,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夠推動基礎研究創新[26],進而帶動可持續農業、可再生能源和循環經濟等方面的實踐與創新,建構有效的生態治理措施,提高農村“生態宜居”水平。第三,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意味著縣鄉學生能夠通過各類專項人才計劃獲得更多優質研究生教育的機會,通過制度設計與引導幫助其反哺家鄉、反哺基礎教育薄弱地區[27],推動農村“鄉風文明”建設。第四,高等教育擴張到一定規模后,將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28]。研究生教育作為最高層次的國民教育,其規模擴張能夠產生知識溢出效應,為農村的組織發展帶來“新理論”和“新方法”,有效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治理有效”目標。
由此可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助推鄉村振興的底層邏輯是通過“釋放人才、重構產業、治理生態、反哺教育和知識溢出”賦能鄉村“生活富裕、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為鄉村振興事業提質增效。此外,受我國資源稟賦、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差異的影響,同一地區鄉村振興五個子維度(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因此,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子維度的影響可能會存在維度異質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1: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助推效應且存在維度異質性。
伴隨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和信息化網絡的建設,區域間的位置壁壘隨之被打破,教育人力資本的經濟影響呈現跨地區特征。傳統面板數據對地區間相互獨立狀態的假定無法適用于實際研究需要,越來越多學者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探討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29]。研究生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和知識交流具有外部性特征,呈現明顯的溢出效應。因此,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存在空間溢出特征。一方面,根據地理學第一定律,任何事物之間都有關聯性且距離越近的省份關聯性越強[30]。相近地區的鄉村振興水平可能互相影響,呈現顯著“同群效應”。當某一地區成功利用資源和要素帶動鄉村發展時,可能會為相近地區提供經驗和借鑒,從而促進相近地區鄉村振興的發展。另一方面,本地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可能對相近地區鄉村振興發展造成影響。本地研究生教育規模越大,越容易吸引相近地區的生源前來就讀,產生“虹吸效應”。在接受研究生教育并獲得專業知識和技能后,這部分人才可能回到相近地區就業,這種“人才回流”現象有助于推動相近地區鄉村振興的發展。而且,本地研究生教育所產生的成果更容易對相近地區產生技術溢出效應[31],成果通過學術交流、科技推廣等渠道傳播到相近地區,為相近地區的鄉村振興提供借鑒和參考,形成“擴散效應”。除此之外,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教育資源以及人才需求等方面的迥異性,各地區的研究生教育規模也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32]。隨著研究生擴招政策的持續推進,各省域內研究生教育規模長期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各地能獲得的研究生人力資本存在差異,從而使其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呈現出異質性特征。因此,不同規模的研究生教育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并非是“線性促進”的,如果研究生教育規模發展過度或不足,可能會降低對鄉村振興的正向作用,存在顯著的門檻特征。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2: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相鄰地區鄉村振興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H3: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1.C-D生產函數與固定效應模型
計量經濟學領域關于人力資本與社會發展的測量模型已經相對成熟,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由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共同創造的C-D生產函數[33]345-368。鄉村振興(Yit)是農村地區完整的社會發展目標,而影響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最關鍵的要素即為人力資本。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為鄉村地區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外生推力”和“內生動力”,激發鄉村經濟、社會、政治和生態發展活力。基于此,本研究選取C-D生產函數作為原始研究模型,將技術投入(Ait)、物質資本投入(Kit)和勞動力投入(Lit)逐步納入生產函數。α、β分別表示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如式(1)所示。
以PGit標記研究生教育規模變量后代入 式(1),兩邊同時取對數后并增加隨機誤差項(εt)得到式(2):
鄉村振興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僅基于C-D生產函數控制技術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仍不夠準確。為了精準評估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實際影響,并控制其他潛在變量的干擾,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基礎[34],進一步從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三個方面進行控制lnControlit,并加入省份ui和年份固定效應λt吸收省份和年份的固有差異,進而得到式(3)。經濟發展水平方面,一般來說,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鄉村居民也會更加富裕,有助于推動鄉村振興;市場化水平方面,市場化程度越高,當地市場需求會更旺盛和多樣,有助于鄉村發展特色農產品和旅游業,推動鄉村振興;對外開放程度方面,對外開放水平越高的地區一定程度上會促進鄉村農產品的對外銷售,有助于鄉村振興發展。
2.空間計量模型
1973年克里夫和曼特爾將空間相關性引入實證統計中,避免了傳統計量忽視相關性所導致的偏誤結論[35]。1979年佩林克和克拉森的《空間計量經濟學》一書出版,標志著空間計量經濟學的誕生[36]。近年來,我國已有不少學者在空間計量領域進行不懈探索。吳玉鳴指出,傳統計量不僅忽視空間相關性,也深受均質性假定的局限[37]。若仍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計模型、忽視空間異質性將使得研究結果缺乏應有的解釋力。基于此,為探討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本研究參考范巧和郭愛君構建的嵌入空間計量模型的C-D生產函數[38],構建如下空間計量模型:
式中,ρ為空間自回歸估計系數,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本研究將分別用標準化的反距離矩陣和反距離平方矩陣作為權重矩陣,以此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WlnYit刻畫“相近地區鄉村振興的相互影響”,WlnZit刻畫“相近地區的研究生教育規模以及其他因素相互作用”。
3.面板門檻模型
若僅考慮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線性影響可能會窄化現實。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省域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并非以線性方式呈現,當研究生規模跨越某一特定“門檻”后,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相較之前會發生顯著變化。基于此,本研究借鑒漢森的方法[33]345-368,以研究生教育規模作為門檻變量構造面板門檻模型。面板門檻模型的公式為:
其中,Thresholdit為門檻變量,τ為門檻變量的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
(二)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
由于鄉村振興的多維特性,必須從其內容的多重特征構建指標體系才更科學。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研究參考朱德全等學者的研究[39-42],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個維度出發,構建鄉村振興指標體系。在二級指標的選取上,本研究緊扣鄉村振興的核心概念,優先采用結果性指標而非過程性指標。這樣的選取方法有助于考查鄉村振興的實際發展水平,避免了因指標數量過多而導致的相關性過高問題,同時也避免了指標數量過少而遺漏重要維度的風險。最終,本研究選定了12個二級指標(見表1)。確定好鄉村振興指標體系后,本研究借助熵值法對我國鄉村振興綜合指數進行測度。熵值法具有客觀賦權的優勢,有效規避了依賴專家主觀賦權的問題,從而更加準確、科學地反映各指標在綜合指數中的重要性[43]。
2.核心解釋變量
本研究選取研究生畢業人數作為代理變量[44],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研究生培養具有明顯的周期性,研究生招生人數和在校人數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存在時滯效應。研究生畢業后投入勞動力市場,成為社會生產的要素,是衡量人力資本的合理指標[45-46]。另一方面,研究生招生生數和在校人數可以反映一個地區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情況,但不能全面反映當地高水平人才的輸出數量和質量。因此,用研究生畢業人數作為代理指標能更準確地評估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產生的實際效果。
四、實證分析
(一)研究生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
基準回歸首先以鄉村振興的對數值為因變量,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計方程[式(2)],檢驗基于C-D生產函數下研究生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逐步控制地區效應、時間效應和干擾變量后,利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方程[式(3)],得到表2中的第2列結果。從參數估計值上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的估計系數由基準回歸中的0.494下降到0.175,說明遺漏相關變量、忽視固定效應將會高估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均值效應。根據估計系數的符號來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進鄉村振興。從估計結果來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參數估計值為0.175(p<0.01),表明研究生教育規模每擴張1%,鄉村振興指數平均提高0.175%。在控制變量的檢驗中,對外開放程度和市場化水平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估計系數分別為0.372和0.023),表明地區對外開放程度越大、市場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推動鄉村振興。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γ=-0.061)。可能的原因在于,在“GDP錦標賽激勵”的背景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往往意味著資源更多地向城市地區傾斜,以維護其經濟表現,而對鄉村地區的資源投入則相對不足,從而限制了鄉村振興的發展。這一發現與中心—邊緣理論相契合,也揭示了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對鄉村振興的重要作用。
為驗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研究選取兩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對核心變量進行上下縮尾1%的處理,以剔除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潛在影響。其次,參考已有研究[48],本研究選取研究生在校人數并滯后作為替換的核心解釋變量納入回歸方程。從表2的第3~4列可以發現,穩健性檢驗結果與第2列基本一致,證實了結論的可靠性。
(二)內生性處理
當模型存在遺漏變量、樣本選擇偏誤和雙向因果關系時,基準回歸無法處理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與鄉村振興間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研究利用工具變量法處理內生性問題,選取高校校舍面積作為工具變量。校舍面積與研究生教育規模有高度相關性,但校舍面積一般無法直接對該地區的鄉村振興水平產生顯著作用。在表3中,本研究使用2SLS和GMM方法進行回歸。可以發現,第一階段回歸的F值為19.230,超過了臨界值10,驗證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高校校舍面積的估計系數為0.322,表明校舍面積和研究生教育規模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此外,Kleibergen-Papprk LM和Kleibergen-Papprk Wald F值均超過了10%偏誤下的臨界值,表明所選工具變量屬于強工具變量。
根據估計結果可知,在處理內生性問題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系數為正,進一步說明了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發展有顯著的助推作用。
五、進一步分析
(一)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空間溢出效應
本研究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進一步實證檢驗研究生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空間溢出效應。根據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可知,在2011—2020年期間,鄉村振興和研究生教育規模兩個指標均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鄉村振興水平和研究生教育規模存在正向的空間自相關性,二者在空間分布上呈現集聚現象。隨后,本研究進一步構建空間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空間溢出效應。在進行Wald檢驗和似然比(LR)檢驗后,選取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影響的空間關聯效應。
表4為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結果,在反距離W1和反距離平方W2權重矩陣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系數均為正(σ1=0.137;σ2=0.121),說明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發展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假設1再次得到驗證。從空間自相關性看,鄉村振興指數的空間自相關系數均顯著為正(ρ1=0.340;ρ2=0.316),且至少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相近地區的鄉村振興進程存在空間正相關性。此外,研究生教育規模的空間滯后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有空間關聯效應。研究生教育能夠突破空間限制產生輻散效應,對相近地區產生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也就是說,研究生教育規模較小的省份可以從地理鄰近地區獲得富余研究生教育資源的空間外溢效應,假設2得到驗證。最后,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也與前文結果基本一致,再一次驗證本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二)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子維度影響的異質性
為進一步探究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賦能鄉村振興的具體維度,本研究同樣將鄉村振興指數中的五個維度指標納入回歸模型。由表5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風文明”維度的正向推動效應最大(γ=0.191,p<0.01)。一方面,從人力資本理論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大意味著農村學生可以獲得更多優質研究生教育的機會,更有可能實現教育反哺,促進農村教育現代化發展,持續深化鄉村人力資本,推動鄉風文明建設。另一方面,根據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教育不僅傳遞知識,更重要的是傳遞文化資本。研究生教育培養的高水平人才不僅具備先進知識,還積累了大量的文化資本,能夠通過挖掘和包裝來打造、傳播農村原生傳統文化,多層次、多維度、多渠道提升鄉村社會的文化軟實力,推動鄉風文明建設。與“鄉風文明”維度相比,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治理有效”維度的正向推動效應最弱。治理理論強調良好的治理需要多方主體參與和協作。農村治理有效性受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同時也依賴于農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參與。雖然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可以培養更多“治理強才”,但農村治理涉及的復雜問題需要多方協調與合作,因此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治理有效性的直接影響可能較為有限。
(三)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影響的門檻效應分析
運用Bootstrap方法重復自舉300次的方式對研究生教育規模作為門檻變量的情形進行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研究生教育規模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的P值至少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研究生教育規模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存在自身雙重門檻。
根據表7的估計結果可知,研究生教育規模(本研究采用研究生畢業人數取對數,下同)作用于鄉村振興時存在顯著的自身門檻效應,兩個門檻估計值分別為8.112和9.126。在各個門檻區間中的影響效果均為正向,且至少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當研究生教育規模不高于8.112時,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1%,鄉村振興指數平均增加0.266%。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夠有效填補鄉村地區的高層次人才缺口,提供更多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持,產生較強的邊際效應;當研究生教育規模越過第一個門檻但不超過第二個門檻時,彈性系數下降至0.118%。盡管持續擴張研究生教育規模仍然能夠增加鄉村人力資本,但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就業機會等配套資源不足,導致高學歷人才的邊際效益下降。這種資源配套的滯后性和吸納能力的不充足,使得鄉村振興指數的增長速度放緩,符合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當研究生教育規模越過第二個門檻拐點9.126時,彈性系數回升至0.148%,這可能是因為研究生規模擴張會帶動專業化人才協同發展,研究生人力資本賦能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產生回彈效應。上述研究結果表明,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擴大,其對鄉村振興的賦能效應呈現“邊際遞減后回彈”的趨勢。
為了深入分析不同地區研究生教育發展條件下,研究生教育規模作用于鄉村振興的差異,本研究將不高于8.112、介于8.112~9.126之間和高于9.126這三類區間分別視作研究生教育規模的低等水平、中等水平和高等水平,并求解不同省份的研究生教育規模均值,繪制各省份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年均值區間,如圖1所示。圖1內部兩條參考線分別為第一道門檻值8.112和第二道門檻值9.126,可以看出,各個省份年均研究生規模處于不同水平區域,其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存在異質性。西藏、青海、海南和寧夏研究生規模遠低于第一道門檻值,表明存在明顯的高水平人才缺口;貴州等省份研究生規模介于兩門檻值之間,處于中等水平區域,需采用穩健的擴招策略;北京等省份處于高等水平區域,需合理控制研究生擴招速度,以防過度擴張造成人才浪費。綜上,應結合地區特點,制定具有地方差異性的研究生擴招策略,以更好地適應當地鄉村振興及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
(四)不同層次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博士和碩士研究生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博士生和碩士生規模擴張在鄉村振興中發揮的作用。
由表8的回歸結果可知,博士和碩士研究生規模擴張均能為鄉村振興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有效賦能鄉村振興。但整體上碩士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的回歸系數更大,對鄉村振興的推動效應更加顯著。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解釋。一方面,2020年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高等學校碩博招生人數比約為8.53,但到2022年碩博招生人數比已達8.94。相比于博士研究生,我國碩士研究生教育規模顯著擴大。碩士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夠為鄉村發展提供豐富的多學科人才資源,可能更容易滿足鄉村振興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我國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始終緊密契合國家的發展需求和戰略規劃[49]。2023年12月,我國提出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規模將在“十四五”末擴大到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三分之二左右,意味著我國將培養越來越多專業實踐型碩士,以適應特定職業領域的發展和需求[50]。相較偏向于理論研究和學術創新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更注重將所學知識和技能應用到實踐中,能夠更快地適應鄉村振興領域的導向需求。相比之下,博士研究生影響效果相對較小,但其專業知識和研究能力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理論指導和學術支持。
(五)不同教育水平地區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不同地區受教育水平的差異可能也會影響研究生教育推動鄉村振興的實施成效。為了研究不同教育水平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助推效應的異質性,本研究引入虛擬變量Edui,t,并采用中位數方法進行分組回歸。
由表9的回歸結果可知,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助推鄉村振興的效果在教育水平較高的地區并不顯著,而在教育水平較低地區顯著。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根據相對教育理論和教育位置性商品概念,高等教育的優勢取決于同期群體的教育水平[51-52]。當地區受教育水平較低時,研究生教育與其產生的相對教育位差大,更有可能發揮研究生教育的人力資本效應,人力資本產出率也相對更高,推進鄉村振興的實施效果也就更強。另一方面,稀缺性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性會增加其價值和影響力。教育水平較低的地區相對缺乏高學歷人才,這種稀缺性會放大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從理論上梳理了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賦能鄉村振興的應然結果,并基于2011—2020年中國31個省域的平衡面板數據,系統構建鄉村振興指數,實證研究了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實然影響。研究發現: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不同方式的穩健性檢驗并借助工具變量法處理內生性問題后該結論仍然成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能夠突破空間限制,產生廣泛的輻散效應;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助推鄉村振興存在顯著的異質性效應。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鄉風文明”維度和低教育水平地區的助推作用最顯著、碩士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推動效應顯著高于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教育規模與鄉村振興之間呈現非單調、非線性的關系,即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逐步跨越兩道“門檻”,其對鄉村振興的賦能作用呈現出“邊際遞減后回彈”特征。基于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尊重地區差異,分區域、分層次、有步驟地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讓研究生規模擴張真正能夠賦能鄉村振興。本研究實證發現,研究生教育規模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呈現“邊際遞減后回彈”特征,在各個門檻階段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仍顯著為正,即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并不存在顯著的“天花板效應”。從這個角度說,我國現階段仍可以穩步有序地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全國范圍內同比擴張研究生規模,而是需要采用個性化擴張策略,分步驟、錯位化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尤其是碩士研究生教育規模。比如,西藏、青海、海南和寧夏等地區研究生教育規模低于第一個門檻值,省域人才存量較低,難以發揮規模優勢,更不能充分釋放研究生賦能鄉村的人才聚焦效應。因此,該類地區一方面需要基于高校原有優勢,發揮校友作用,吸引更多優質資本和人才聚集。同時,需加大力度推進研究生教育機構自身的能力建設,通過相對大幅擴招的方式,增加省域研究生人才儲備。另一方面,通過增加高校農村專項計劃等手段,培養更多自愿服務農村、扎根農村的優秀人才。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農村高層次人才保障機制,優化人才成長環境,加強鄉村地區對研究生人才的“吸力”,逐步增加縣鄉研究生人才儲備,以滿足鄉村振興的高層次人才需求。對于北京等研究生教育規模較大的地區,則需穩步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高地,進一步放大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的回彈效應。
第二,強化研究生人力資本“轉移支付”,拓寬剩余人才轉入渠道,有效承接人才紅利,充分發揮空間輻射效應。我國西部地區研究生教育資源配置不足,發展基礎薄弱,協同發展能力低,高校綜合辦學實力和學科實力較弱[53],難以布局增設新型研究生專業,也無法培養更多高質量人才。本研究實證發現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村振興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生教育規模較小的省份可以從地理鄰近地區獲得富余研究生教育資源的空間外溢效應。因此,政府需做好制度的頂層設計,為西部地區承接研究生教育資源豐富省份的人才外溢提供政策支持,助力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可通過建立和完善結對幫扶機制,強化研究生人力資本“轉移支付”,從教育資源豐富地區引育更多高質量研究生人才幫扶并扎根弱勢地區,高效利用高水平人力資本與要素的靈活性和滲透性,充分發揮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的空間外溢效應。除此之外,政府需大力扶持西部地區研究生教育,吸引更多優質資本和人才向西部聚集,改善西部地區研究生教育發展“舉步維艱”的窘境,逐步縮減區域間研究生教育質量差距。
第三,全面開展鄉村數字畫像,勾勒鄉村發展特點,精準匹配研究生教育機構,破解鄉風文明難題。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靈魂,也是推動鄉村發展的重要力量和關鍵基礎。鄉村落后的關鍵是文化理念的落后,是鄉村社會在市場經濟時代所顯現的創新精神不足等因素使然[54]。本研究實證發現,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對“鄉風文明”維度助推效果最為顯著。作為最高層次的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具備豐富的文化資本和創新理念,其規模擴張能夠通過政策引領與制度設計,引育更多高層次人才“下基層”,為鄉村注入更多現代化理念,以現代化理念促進鄉村行動發展,促進形成鄉村振興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建設新農村,各地需全面開展鄉村數字畫像,勾勒各地鄉村發展特點,最大化地拓展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的鄉村振興效應。一方面,根據鄉村特點精準匹配研究生教育服務鄉村的實踐活動,充分把握高層次人才對鄉村文化的挖掘、包裝和傳播能力,多層次、多維度、多渠道提升鄉村文化軟實力,以鄉風文明帶動產業興旺,實現鄉村全方位振興。另一方面,持續拓展“博士服務團”“研究生支教團”等鄉村服務活動,以優質公平的鄉村教育反哺鄉村振興。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研究生教育對教育水平較低地區的鄉村振興助推作用更大。因此,在了解鄉村發展特點后,高校與鄉村需建立個性化、差異化結對幫扶機制,并優先在“教育貧瘠”地區開展試點服務工作,充分釋放研究生規模擴張對低教育水平鄉村的強大賦能力量,逐步形成“以點帶面”的服務格局。此外,服務于鄉村的高水平研究生培養離不開企業提供的基地支持與項目孵化,因此需構建高校與企業深度合作的聯合體,面向鄉村建立合作戰略聯盟,讓研究生在解決實際問題中提升專業本領,服務鄉村振興。總之,政府、高校和企業需形成合力,確保研究生人力資本的有效分配,致力于推進研究生賦能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助力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參考文獻
[1] 李立國,李建龍.優化資源布局與高等教育強國建設[J].大學教育科學,2024(1):14-20.
[2] 徐曉颯.研究生教育質量提升的多元治理視域[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1):131-135.
[3] 李建民,陳潔.中國過度教育的測度:基于美國職業準入的教育標準[J].人口與經濟,2017(5):34-44.
[4] 秦春華.重新認識研究型大學[N].中國科學報,2014-06-19(07).
[5] 胡偉力,張立遷.新時代研究生招生工作職能研究[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3(6):35-41.
[6] 張靜,張蚌蚌,布都會,等.涉農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培養“項目制”改革探索與實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3(10):22-27.
[7] 李鋒亮,周京博.推動研究生教育強國建設 加快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第七屆全國研究生教育學學科建設高端論壇綜述[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4(1):1-7.
[8] 李永剛.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的動力、影響與發展方略[J].中國高教研究,2021(2):77-83.
[9] 王天平,李珍.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取向與實踐路向[J].重慶高教研究,2023(4):14-22.
[10] 陳巖.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社區教育的價值意涵與實現路徑[J].中國遠程教育,2023(10):62-69.
[11] 彭洪莉,朱德全.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多維演進與未來圖景[J].教育發展研究,2022(19):31-40.
[12] 朱成晨.農村職業教育融合治理的共生機制與“超系統”境域[J].教育研究與實驗,2023(5):108-115.
[13] 唐廣軍,王晴.數說2012—2021年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基于供給、規模與結構的視角[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2(5):10-19.
[14] 鐘云華,劉姍.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政策變遷邏輯與發展理路:基于1949—2020年政策文本的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1(2):114-124.
[15] 邵頔.我國“雙一流”高校研究生基層就業現狀、趨勢及改善路徑研究:基于對Z大學2009—2019年研究生基層就業數據的分析[J].中國大學生就業,2022(3):3-13.
[16] 游蒞薈,張特.高校畢業生就業價值取向變化特點及引導策略探析:基于38所985高校2017—2022年就業質量報告的分析[J].中國大學生就業,2024(2):54-62.
[17] 賴德勝,陳建偉.人力資本與鄉村振興[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6):21-28,154.
[18] 教育部.小學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專任教師分課程、分學歷情況[EB/OL].(2022-12-28)[2023-12-18].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
[19] 朱桂琴,張競元,譚小漫,等.研究生學歷鄉村教師主觀心理環境現實困頓與突圍超越:基于25個省的調查分析[J].中國教育學刊,2024(4):83-89.
[20] 姚昊,胡耀宗,馬立超.班級規模、教師學歷如何影響學生學業成績:基于PISA 2018的國際比較研究[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1(5):40-54.
[21] 程名望,蓋慶恩,Jin Yanhong,等.人力資本積累與農戶收入增長[J].經濟研究,2016(1):168-181,192.
[22] 姜朝暉,金紫薇.教育賦能新質生產力: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重慶高教研究,2024(1):108-117.
[23] 李立國,杜帆.我國研究生教育對區域創新的溢出效應研究[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1(4):40-49,90.
[24] 唐繼衛.堅持科技小院人才培養模式 大力推動中國特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J].中國高等教育,2023(12):20-25.
[25] 吳華杰,楊釙.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中實踐共同體的構建:以科技小院培養模式為例[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3(1):24-31.
[26] 趙慶年,劉克,宋瀟.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大的基礎研究創新效應及機制:基于2001—2019年30個省區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3(3):60-69.
[27] 郭叢斌,朱昱治,祝軍.縣域高中背景的大學畢業生碩士入學機會研究[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22(4):97-115,187.
[28] 胡詠梅,薛遠康.高等教育規模與質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基于2003—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J].教育經濟評論,2022(4):17-40.
[29] 方超,羅英姿.研究生教育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兼論研究生人力資本的空間流動性[J].高等教育研究,2017(2):52-60.
[30] Tobler W 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J].Economic Geography,1970(sup1):234-240.
[31] 魏萍,黃容霞.分級研究生教育人力資本的時空分布特征與經濟增長效應[J].中國高教研究,2023(1):64-70.
[32] 劉寧寧,唐玉光.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區域差異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4):1-7.
[33] Hansen,B.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2).
[34] 劉亞男,王青.中國鄉村振興的時空格局及其影響因素[J].經濟問題探索,2022(9):12-25.
[35] CLIFF A D,ORD JK. Spatial Autocorrelation[M]. London:Pion,1973:196.
[36] Paelinck J,Klaassen L.Spatial Econometrics [M].Farnborough:Saxon House,1979:109.
[37] 吳玉鳴.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在省域研發與創新中的應用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5):74-85,130.
[38] 范巧,郭愛君.一種嵌入空間計量分析的全要素生產率核算改進方法[J].數量經濟技術研究,2019(8):165-181.
[39] 朱德全,楊磊.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貢獻測度: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測算分析[J].教育研究,2021(6):112-125.
[40] 徐雪,王永瑜.中國鄉村振興水平測度、區域差異分解及動態演進[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5):64-83.
[41] 舒泰一,張子微,趙田田,等.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時空耦合協調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22(5):3-13.
[42] 程莉,文傳浩.鄉村綠色發展與鄉村振興:內在機理與實證分析[J].技術經濟,2018(10):98-106.
[43] 魏敏,李書昊.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11):3-20.
[44] 范曉婷,張夢琦,陳倩,等.研究生教育規模推動科技創新的門檻效應研究:基于1999—2019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2(8):38-45.
[45] 李鋒亮,王瑜琪.研究生教育在創新驅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21(5):23-29.
[46] 李鋒亮,吳帆,顧袁超,等.碩士研究生教育對省域經濟增長的貢獻[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1(4):64-70.
[47] 樊綱,王小魯,馬光榮.中國市場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J].經濟研究,2011(9):4-16.
[48] 郭叢斌,閔維方,方晨晨,等.碩士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基于專業學位和學術學位碩士生比較的視角[J].高等教育研究,2023(1):68-76.
[49] 馬永紅,朱鵬宇,楊雨萌.學位條例實施以來我國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演進:基于三元邏輯的視角[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1(9):18-28.
[50] 趙文學.研究生就業空間流動與我國研究生教育區域布局[J].高教探索,2023(1):67-73.
[51] 廖麗,李穎暉,李黎明.“相對教育”對代際地位傳遞的作用[J].社會學評論,2022(1):238-256.
[52] Bills D B. Congested credentials: The Material and Positional Economies of Schooling[J].SI:Education as a Positional Good,2016(43):65-70.
[53] 于妍,李明磊.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空間分布、形成機理及優化機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4(1):32-38,85.
[54] 邱世兵,邱婧璇.鄉村振興背景下鄉風文明建設的使命、邏輯與進路[J].重慶社會科學,2023(6):133-144.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tial Spillovers and Threshold Effects
LIU Lili LI Qinghao ZHANG Feng
Abstrac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the mis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also means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realiz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0, and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an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significantly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result still holds after robustness testing and endogeneity treatment; the spatial effect shows that expanding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an break through spatial constraints and produce a divergent effect, show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urrounding areas. The threshold effect shows a non-monotonic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as the scale of graduate education gradually crosses two thresholds, its empowering effec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ginal decline followed by rebou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significant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ub-dimens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stgraduate academic level, and regional education level.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long-term training mechanism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ly carrying out rural digital imaging, expanding the scal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accelerating the layout of emerging agriculture-related majors.
Key word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責任編輯 陳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