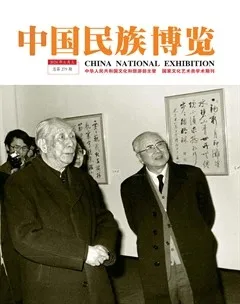探究《鄭伯克段于鄢》矛盾因緣
【摘 要】《鄭伯克段于鄢》中鄭莊公和共叔段兄弟鬩于墻,這背后既有兄長莊公的放縱姑息,母親姜氏偏心袒護,共叔段的貪得無厭。探究《春秋》首篇《鄭伯克段于鄢》背后矛盾的深層因緣,可見其背后禮崩樂壞的時代特色。
【關鍵詞】鄭伯克段于鄢;鄭莊公;共叔段;矛盾緣由
【中圖分類號】K225.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11—032—03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對諸侯的束縛無力,各國之間為爭奪霸權相互傾軋,戰火紛飛,而諸侯國內部為了爭奪統治權的斗爭亦是血腥殘酷,同室操戈的例子比比皆是。《鄭伯克段于鄢》是《春秋》首篇,記錄為“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1]”。《左傳》將其詳細敘事為完整的一個故事。在鄭國統治階級內部圍繞著王位展開激烈爭奪。其中涉及母親姜氏,姜氏之子鄭莊公、共叔段三位主要人物,他們既是鄭國統治階層同時也是母子三人,這場爭斗兼有政治權謀和家庭倫理雙重性質。
一、文本解讀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介紹故事的時間、地點、主人公以及主要情節。也即五月,鄭伯在鄢地打敗段。“鄭伯”,指下文的鄭莊公,鄭莊公是鄭國的第三代國君。“克”,戰勝。“段”,指下文的共叔段,即鄭莊公的弟弟。“于鄢”,介詞結構,這里用做狀語,狀語后置結構。鄢,地名,為鄭武公所滅,其地在今河南省鄢陵縣境內。
根據“春秋筆法”來分析題目,共叔段本是鄭莊公之弟卻不稱為弟,說明他行有不端,不符合弟弟應有之行。兩國交戰,戰勝可稱為“克”,而兄弟之間的矛盾卻“如二君”,可見交戰之殘酷。鄭莊公直接稱其為鄭伯,“譏失教”,諷刺用心險惡。從《左傳》記錄中,可見該事件已經從家庭內部斗爭上升至政治權力的爭奪,兄弟斗爭卻如同敵國。
結合《公羊傳》《谷梁傳》進行分析,《谷梁傳》中“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2]”《公羊傳》中“克之者何?殺之也。[3]”兩者都表明鄭莊公對共叔段是存有殺心的,想要將其斬草除根。共叔段不稱弟,《左傳》中稱所做“不弟”,《公羊傳》中“段失子弟之道矣,[4]”《谷梁傳》中具體解釋“當國也。[5]”即以國為敵,妄圖顛覆政權,從這個角度來看,共叔段行為不僅是違背家庭道德更是對國家秩序的挑戰。關于鄭莊公,《谷梁傳》中認為鄭伯遠去鄢追擊落敗的弟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之云爾。[6]”此舉非常過分。《公羊傳》中“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7]”則認為鄭伯不該將封地,總好過最后要誅殺共叔段。
由上可知,無論是《春秋》還是春秋三傳,對勝利者鄭莊公、野心家共叔段均是批判態度,并且《公羊傳》《谷梁傳》中對鄭莊公的批評程度是高于共叔段的。具體原因可以結合孔子的思想理念來分析。“孔子主張克已復禮,要恢復以前的“禮”,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仁”是孔子倫理核心思想,廣義理解為完善道德修養和人格構成,基礎要有仁愛之心,因此,有手足之悌,有子女之孝,有父母之慈。《左傳》順承此意,以生動細膩的文筆,描寫了這場國君家庭內部的矛盾斗爭,因此,對于破壞倫理秩序的雙方都持批判態度。
《左傳》詳細記錄了圍繞王位的矛盾發展過程,對于最終結果僅寥寥幾筆,僅描述為段出奔共。后文為起到孝道宣傳的作用,特意安排潁考叔巧諫莊公,母子二人黃泉相見的結局。原文中鄭莊公取得了政治斗爭的勝利,捍衛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共叔段出奔保全了性命。姜氏被接回安享晚年,看似是大團圓結局。然而,這場權力爭奪的悲劇究竟是誰造成的?我們將從文本內容、時代背景進行分析。
二、時代背景
周王朝初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9]”即宗法制、分封制,將貴族分封到各地。周公“制禮作樂”,統地建立了一整套有關“禮”“樂”的完善制度。包括“畿服”制、“爵謚”制、“法”制、“嫡長子繼承”制和“樂”制等。
在一系列禮樂制度的運轉之下,周朝是孔子理想中的政治環境。西周末期,“烽火戲諸侯”周幽王寵幸褒姒,要廢掉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之子。外公申侯為扶持太子聯合犬戎除掉周幽王。宜臼有弒父上位的因素,東遷后開啟東周時代。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春秋戰國周天子對各諸侯國影響力更小。曾出現過鄭莊公儀仗強大軍隊打敗王師,手下射中周桓王肩膀等情況。根據上述史實可見,天子尚且不尊禮法,諸侯國上行下效,周朝的禮樂制度逐漸土崩瓦解。因此其他問題隨之而來。如在國家王位的繼承權上,嫡長子不再是唯一的選擇,統治階級內部圍繞著權力展開爭奪。例如晉獻公寵愛驪姬,想要廢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齊為太子。驪姬設計離間獻公父子感情,申生殞命,重耳、夷吾在各國流亡。在鄭莊公之后,歷史在他兒子們的身上重演,公子突與太子忽的君位之爭如當年一般血腥殘酷。儒家強調的“悌”在權力爭奪前不值一提,同樣母(父)慈子孝也顯得難得。宋襄夫人可以行權除掉宋昭公及其他襄公之孫并另立新君。楚成王想廢黜太子商臣,反被逼上絕路,后商臣即位。趙武靈王因二子奪位,被困沙丘宮活活餓死。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權力之下,親情不值一提,倫理制度也脆弱不堪。正如《孟子》所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10]”
大環境如此,鄭國也不例外。我們從《鄭伯克段于鄢》文本中的主人公分析這場戰爭究竟是誰的錯。
三、主人公分析
(1)鄭莊公作為哥哥,沒有教導弟弟共叔段,反而欲擒故縱,導致共叔段走向深淵。原文中前期一直是共叔段處于上風,最初姜氏替他索要封地先是制、再是京城。身邊的臣子祭仲直言進諫,勸說鄭莊公不要將京城分封給共叔段,一是不符合先王制度,二是京城將是新鄭的一大威脅。在春秋戰國時期,城墻本身就起到護衛內城的作用,京城城墻高大,易守難攻。城內人口眾多,是潛在兵力,并且距離新鄭不遠。若是共叔段盤踞于此,擴充實力,必然難以應對。而鄭莊公卻只是說“姜氏欲之,焉避害?”顯得在母親的威勢下自己無奈且無助,但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一句則暴露了他內心并非如此,實際上在等待共叔段做不義之事,自取滅亡的那刻。
共叔段“命西鄙北鄙貳于己”試探鄭莊公的反應,后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鄭國大夫公子呂多次勸誡鄭伯早日鏟除他的弟弟,不要讓百姓生二心。“無用,將自及”“子姑待之”等說明鄭莊公卻絲毫不急,他對于共叔段必將失敗的結局成竹在胸。此時,若是鄭莊公擔負兄長的責任對共叔段進行懲戒,共叔段可能會收斂自己的野心。然而,共叔段背后是太后姜氏,必定會出面阻撓,而那時鄭莊公又會在道德上陷入“孝、悌”的難題。因此,他耐心等待,處處示弱,他一直在等待共叔段走入自己設下的圈套,以達到鏟草除根的目的。這場等待持續了22年,直到共叔段起兵謀反的那刻,一句“可矣”充滿捕獲獵物準備收網時的喜悅與期待。在這期間鄭莊公真的只是守株待兔嗎?原文中一個細節,共叔段將襲鄭,襲含有偷襲之意,而“公聞其期”說明鄭莊公在共叔段身邊安排了眼線,一直在收集情報。作戰時鄭莊公早有準備,命令公子呂率兵車二百乘(根據童書業《春秋史》中研究一乘為30人,二百乘相當于6000人。鄭初國力較為弱小,二百乘幾乎為全部兵力,原文為“僅二百乘[11]”)迅速應戰。由此可見,鄭莊公對共叔段的一舉一動密切關注,了然于胸,暗自籌謀,而共叔段卻未加防備。
對于鄭莊公,歷來褒貶不一,到宋代蘇軾認為鄭莊公對共叔段并非姑息養奸而是給弟弟改過的機會。現在看來將全部責任歸為鄭莊公身上也確實有失公允。莊公即位之時,年僅13歲T3zuzPT+BiA9YS9vduB71YhxR8rTWtUN9316k9vtwrU=,母親姜氏與周幽王王后為姐妹,背后是強勢的娘家申國。申侯曾因周幽王意圖廢黜宜臼便強硬出手。姜氏在武公在位時都多次妄顧丈夫意愿,現在幼子上位,更加無所顧忌。按照常理來看,鄭莊公前期對母親的妥協、對共叔段的放任也有保全自身的考慮,畢竟春秋戰國時期“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12]”雖有祭仲、子封等良臣輔佐,依舊還是根基不牢。鄭莊公的隱忍不發,從另一個角度也給了姜氏和共叔段收手的機會。鄭莊公曾說“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其糊口于四方。[13]”對共叔段出奔有所反省,因此不能完全用冷酷狠毒來評價此事中的鄭莊公。
(2)共叔段志大才疏,欲壑難填。共叔段本沒有繼承權,但是因為母親偏愛,起了奪位之心。在22年與哥哥對峙的過程中,鄭莊公一直沒有采取行動,共叔段本可以及時收手,但是野心勃勃的他絲毫沒有意識到所為不忠不義,反而越發肆無忌憚。起初還只是隱藏在母親的庇護之下,等到擁有封地之后明知不合制度卻坦然居之。
先是“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此時還是小心試探,見國君沒有反應,便越加放肆,更加輕視君主緊接著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趁機擴大地盤,擴充實力,為反叛奠定了基礎。 將本歸國君管轄的邊境之城收為自己的領地這是對王權的挑釁,共叔段的野心已經暴露無遺。隨后,他“繕甲兵,具卒乘,”秣馬厲兵,又有姜氏做內應,戰斗前的準備看似萬無一失,便要“襲鄭”。起兵叛亂要篡奪兄長的王位,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這也正應了鄭莊公所言“多行不義必自斃”。叛亂不久,京叛大叔段,反映出共叔段倒行逆施,不得民心,對應鄭莊公所言“不義,不昵,厚將崩。”的斷言。共叔段連自己的封地都無法使百姓順服,更何況是龐大的鄭國。大張旗鼓地謀劃叛亂,大肆擴張領土,對身邊的奸細絲毫無察,由此可知貪婪、野心以及政治上的見識淺陋催化了共叔段的奪權之舉。
(3)姜氏的“三心二意”。春秋時期,上層貴族女性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權力,因為“婚姻而具有父系和夫族的雙重身份。”“得寵女性可能會對其丈夫的政治決策產生影響。[14]”因此故事中姜氏夫人參與政事也是有時代特色的。并且在出土的竹簡《鄭武夫人規孺子》中在丈夫武公去世后,姜氏以國有良臣,可以三年無君為借口,拖延莊公執政,為段謀取王位爭取時間。此時的莊公不得不與其權衡周旋,要求對方不得參與政事。由此可見,姜氏在當時朝局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同是親生骨肉,為何姜氏態度截然不同。原因是先秦時期崇尚生育,但也存在拋棄孩子的“不舉”現象。《風俗通義》中就提出了:不舉并生三子,即三胞胎不舉;不舉寤生子,難產之子不舉;不舉父同月子,與父同月生之子不舉;五月五日生子不舉[15];原文中“莊公寤生”,按照難產的解釋,便可以理解姜氏為何厭棄嫡長子,并且古代嬰兒難產被認為是不孝。姜氏厭惡莊公體現出性格中偏執的一面。由于偏愛共叔段,姜氏無視廢長立幼會影響國家安穩,多次向武公請求改立太子。
同時,從身為母親的角度,偏心的姜氏從未給過年幼莊公溫暖。一心想為共叔段后面起事鋪路。立儲君不成,便仗著太后身份咄咄逼人地要求鄭莊公。先是請求發生過叛亂的制,又明知不符合禮制還依舊為其請求富庶的大城京,野心不言而喻。在共叔段肆意擴張,挑戰王權的那些年,作為母親她未起到教導職責加以規勸。反而是在共叔段要偷襲新鄭之時,為他做內應,在此刻,她對長子的生死毫無顧念,狠心冷漠達到極點。一己私心使得國家動蕩、手足相殘、母子反目,姜氏最后也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若是她給年幼的莊公溫暖,教導共叔段忠信孝悌,自己為人正直公正,怕也不會出現手足相殘的局面。
姜氏的偏心、私心、狠心,對兩個兒子截然不同的態度,為后面手足相殘埋下伏筆。身為母親不應該一味寵溺幼子,而應“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16]樊智寧認為公子州吁弒君和王子帶之亂這兩件事的起因,與鄭伯克段于鄢如出一轍,“皆是由于父母的寵愛‘失教’,最終導致手足相殘的家庭倫理悲劇。[17]”
在《春秋》和春秋三傳中,將矛頭主要集中在鄭莊公和共叔段身上,根據儒家倫理道德的標準對他們進行批判。姜氏夫人作為最初的始作俑者卻未提及。同時我們可以發現,春秋時期“兄弟鬩于墻”屢見不鮮,這也是源于禮崩樂壞的時代背景。總之,鄭國內部這場帶有時代特色的內亂母子三人都負有責任。
參考文獻: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
[2][3][4][5][6][7][9][16]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9.
[8]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0]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1]童書業.春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7.
[1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4]林曉雁.西周春秋時期的女性、聯姻與政治格局演進研究[D].昆明:云南大學,2020.
[15]應劭.風俗通義校注佚文[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17]樊智寧.“鄭伯克段于鄢”的家庭倫理責任續考[J].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8).
作者簡介:葉向妮(1992—),女,碩士,山東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教師,研究方向為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