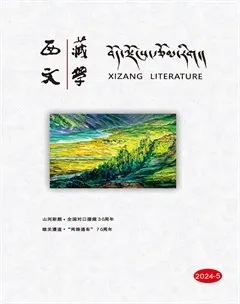長路
這段路向來就是這般寂靜。自西邊蜿蜒而來,往來的貨車像一顆顆砂石落進(jìn)了碎屑巖的大海里,車窗外的一切隨著山伏水曲緩緩發(fā)生變化,陽光從如棉的云層中間透下光柱,照在峽谷的崗巒和雪山峰頂,照著109國道上的貨車司機(jī)們行進(jìn)的地面斑駁了起來。路政員的通訊室里有一部單獨(dú)的步話機(jī),它頻段特殊,凍土層路段大修的任務(wù)即將傳來前,它會(huì)出現(xiàn)極弱的低頻,像峭壁孤獨(dú)的塵埃掉落了下來,信號(hào)隨著荒原的海風(fēng)傳進(jìn)方肅他們道班的無線電里。
這段國道從壘砌在兩邊的山石之間穿行而過,中間沿途很少能看得見什么動(dòng)物,青崖石裸露在昏暗的天空下,方肅偶爾能從夾縫里發(fā)現(xiàn)一些不知名的植物,褐色的雪在路邊融進(jìn)泥漿,慢慢匯向更大的一灘。方肅望著路的另一端隱進(jìn)了曠野里,朝向格爾木,盡頭是云邊雪山,他的心思飄到了那個(gè)方向。
莊春來駐扎在格爾木市區(qū),除了方肅他們,他手底下還有幾支不同方向的養(yǎng)路隊(duì)和路政隊(duì)可以指揮,總站像一張蜘蛛網(wǎng)的中心,青藏公路地表的濕度和凍土層的情況變成了閃爍的二極管和數(shù)字信號(hào)。老路曾經(jīng)帶著方肅和蔣浩東在那個(gè)亮堂的指揮室度過他們各自的實(shí)習(xí)期,現(xiàn)在三人駐守在離昆侖山埡口最近的道班,埡口的山路石橋被風(fēng)卷沙石打磨得足夠堅(jiān)硬。
時(shí)間也被西風(fēng)卷著走,方肅在道班數(shù)過了一年零五個(gè)月,他不怎么跟老路說話,跟蔣浩東更是找不到能聊完的話題。蔣浩東大概是半年前來的,現(xiàn)在還會(huì)每天把頭發(fā)抹得油光水滑,不過臉上已經(jīng)有了和老路、方肅一樣深的皺紋。老路在這個(gè)地方已經(jīng)待了七年,到這兒之前的事他從不向人提起,像他從未記錄下過去似的。
109國道的中間伸出一條硬化路來,鋪進(jìn)了路政監(jiān)測(cè)站大隊(duì)的院子里,這間院子修建在十幾年前,混凝土用料講究,表面至今找不到大的裂縫,只是地坪過于寬敞,顯得兩層蓋板樓孤零零的樣子。老路告訴方肅,當(dāng)時(shí)批地修建的時(shí)候,負(fù)責(zé)石方設(shè)計(jì)的大隊(duì)長在總規(guī)劃圖的面積上多考慮了一點(diǎn),以備長路保障的其他需要。水泥地坪貫通硬化路,空曠的地面持續(xù)囤積了風(fēng)沙,護(hù)欄銹蝕,直到現(xiàn)在他們也沒能完全利用這片閑置的區(qū)域,像是褐色的沙海里浮起了一塊銀白的陸地。
一樓是辦公室,現(xiàn)在和值班室連成通鋪,凌亂的膠鞋里散開臭味,老路的體味和蔣浩東的汗腳味飄在通鋪里。他們二人清晨出的門,帶著道班工人去唐古拉山紀(jì)念碑沿途路檢,大概十點(diǎn)左右回來,出發(fā)時(shí)鬧的動(dòng)靜不小。今天方肅本不必起早,可是老路和蔣浩東出門和回來時(shí)吵得他心里發(fā)緊,蔣浩東清晨發(fā)火的理由是抱怨裝卸東西太麻煩,需要大修的任務(wù)總是來得突然,外出幾個(gè)小時(shí),工具從來用不上幾回,每次搞得車?yán)廴死邸G宄康睦下房偸遣辉趺凑f話,方肅聽他今早說了幾句,只是話音太小,被蔣浩東摔工具的聲音蓋了過去,然后那些工具被人拖著丟進(jìn)庫房里。
方肅起來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接近中午,他往外走時(shí)地上滿是廢紙,幾塊紙板鋪在地上,上頭壓著依維柯的發(fā)動(dòng)機(jī),零件像是剖開的腸肚散落了一地,一灘機(jī)油從紙板下面流了出來,他撿起腳邊被撕剩的半本書,翻看發(fā)現(xiàn)是一本詩集,紙張發(fā)黃,書角卷起,第一頁寫著:
“永無寧靜的片刻,無需以任何方式昭示,我的靈魂,我的饑餓、孤悶,我的猶豫、傷感的詩箋,如此而已,走在空無一人的廣場(chǎng)上,先我而去的人,又猙獰著從四面八方涌來……”
他猜測(cè)那是老路的詩,就把書丟回地上,書頁掀起這里常年囤積下來的一種土腥味道,沉重里摻滿無妄。方肅使勁推開鐵門,讓屋子里的味道平息了下去。
太陽已經(jīng)懸在頭頂?shù)母呖眨矫C實(shí)在懶得抬頭看一眼,只感覺到一股熱流從自己的肩上往里滲。一輛罩著篷布的貨車恍惚間緩緩?fù)黢側(cè)ィ緳C(jī)從那個(gè)狹小的車窗瞧著方肅,那是個(gè)面容黢黑的胖子,遠(yuǎn)遠(yuǎn)地還把手伸起來朝這邊揮了揮。他意識(shí)到自己穿著路政的天藍(lán)色襯衣,這讓司機(jī)認(rèn)出了自己,他死盯著司機(jī)的車子從視線里慢慢蕩了出去,思忖了片刻,方肅想起這是昨晚過磅的第十六輛車,它計(jì)劃駛進(jìn)唐古拉山口開往拉薩。過磅的時(shí)候胖司機(jī)磨蹭了很久,碩大的腦袋從車窗伸出來不停地調(diào)整車輪在磅臺(tái)的位置,方肅知道他們有自己高明的技巧,能讓磅數(shù)降低一些,他以前在服務(wù)區(qū)的雜志上見過整理好的竅門,雜志擺在高速服務(wù)區(qū)吸引來往的長途司機(jī)。
東邊三百米外的加油站成了唯一的風(fēng)景,那里的矮墻環(huán)繞著油臺(tái),幾支油槍挺在油機(jī)前,墻面的紅黃漆皮脫落顯出原始的灰色。
下午老路要從別的隊(duì)借來一輛車,用于他接下來幾天的調(diào)研,最近他不停地在109沿線的單位奔走。老路外出時(shí)總要戴著那雙灰色針織手套,他給人的印象總是一絲不茍,長得卻極沒有威嚴(yán),他身材矮小,面容粗曠,鼻頭通紅,講話時(shí)總要吭幾聲氣才能暢快地說完,口音能分辨出他來自南方。老路的身體很好,幾乎沒見他生過病,每一天他都保持規(guī)律的作息,就算沒有工作的時(shí)候,也要穿著膠鞋盡量往遠(yuǎn)的地方走一個(gè)來回。從昆侖山再往西的路上,他每天都要用鐵锨揚(yáng)幾鏟沙土,把冰雪推到側(cè)溝和路塹里才罷休。
……
站上的依維柯是方肅在接送雁石坪的幾個(gè)研究員回來的路上罷工的,就是那回方肅第一次聽說站上要修建文化公園的事,剛開始那陣子方肅和蔣浩東旁敲側(cè)擊地一直問老路,他總說是沒信兒的事,就算有也不影響路政隊(duì)現(xiàn)在的工作,之后老路離開了一星期,他沒說去什么地方,但是蔣浩東說他朋友看到老路的假條上寫著是去革命文物紀(jì)念館學(xué)習(xí)。如今不斷有新的消息傳出來,老路前期調(diào)研的工作已經(jīng)步入正軌。
雁石坪的調(diào)研車子在去格爾木機(jī)場(chǎng)的路上拉了瓦,距離方肅他們路政隊(duì)十幾公里,莊隊(duì)長在無線電里指示先派車把人接下來,再把車拖到站里檢修。救援工作方肅不需要第一時(shí)間參與其中,路檢后的現(xiàn)場(chǎng)調(diào)度一直是蔣浩東的活兒,因此他整日在方肅面前一副牛哄哄的模樣。那天很早的時(shí)候老路被莊隊(duì)的車接走了,方肅還沒有發(fā)覺站上就剩他一個(gè)人,在無線電里回復(fù)莊隊(duì):“蔣浩東可能去養(yǎng)路隊(duì)工人的道班了。”
莊隊(duì)說他已經(jīng)聯(lián)系過蔣浩東常去的幾個(gè)地方,都沒人看見過他。他讓方肅守在通訊室的無線電跟前,等待他傳來下一步的指示。方肅覺得無聊,不過還是等在通訊室里,他打開電腦上衛(wèi)星地圖的程序,那張地圖是路橋信息局的一個(gè)部門研發(fā)出來,精度極高,方肅輸入了兩遍密碼,他操控鼠標(biāo)往西滑向沿格爾木河彎曲的褐色道路,高山峽谷失去了雄峙的威嚴(yán),變成了平面上毫不起眼的圖像,繼續(xù)順著109蜿蜒前進(jìn),穿行經(jīng)過城市和鄉(xiāng)村,一直到看到拉薩時(shí),莊隊(duì)才在無線電頻道上找他,他才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忘記了那幾個(gè)研究員的事,莊隊(duì)?wèi)?yīng)允等事情結(jié)束他會(huì)收拾蔣浩東,隨后把前去救援的事情安排到了方肅頭上。
那輛車像是肺部患病的老人,進(jìn)出氣都會(huì)傳來劇烈的嗆咳,方肅絲毫不關(guān)心,迫不及待把車開進(jìn)加油站,插上油槍就沖到營業(yè)室想找到田慧,那個(gè)臉蛋暈著濃厚高原紅的藏族營業(yè)員告訴他,田慧今天沒有出現(xiàn),想找她的話往東邊走幾百米,打她的電話試試。方肅想了想還是沒有打電話,開了票就離開了加油站。一路上走得很順利,那三個(gè)研究員已經(jīng)把車推到了一處石崖的天然港灣里,三角牌立在幾十米外,方肅到車前看到他們正躲在里面,抱著氧氣瓶在吸。返回格爾木的時(shí)候,他們?cè)诤竺娌煌5亟腥轮谐痰膬措U(xiǎn),快到機(jī)場(chǎng)又開始輪番打起電話,方肅大概知道了他們?cè)谘闶鹤龅刭|(zhì)和水文站流量監(jiān)測(cè)的研究,三個(gè)人都不是領(lǐng)導(dǎo),最近幾個(gè)研究有了突破,這讓他們很快忘記自己剛才還困在109上的事。
方肅把車開上機(jī)場(chǎng)高速后,問坐在他后邊那個(gè)年齡稍大的男人:“許工,你們這些研究是用來干什么的?”
姓許的研究員戴著一副樹脂鏡框的近視眼鏡,鏡片已經(jīng)老化,整張臉讓人判斷不出年齡,他把雙肩包掩進(jìn)懷里:“可以讓監(jiān)測(cè)水文的精準(zhǔn)度提高。”
“起什么作用?”方肅還是不解。
“跟你做的工作一樣,讓這條長路確保通暢。”他半瞇著眼睛,隔著老舊的鏡片觀察前擋風(fēng)外的高速公路,一旁的路牌逐漸多了起來,他像突然想起什么,“哎,老路負(fù)責(zé)的公園怎么樣了?”
方肅從后視鏡瞧了瞧他說:“公園?哪有什么公園,我不知道。”
“你們一共沒幾個(gè)人,你怎么會(huì)不知道。”
“沒聽說。”方肅想來近期確實(shí)沒有什么值得留意的事發(fā)生。
“你們站上要建個(gè)革命文化公園,畢竟空著一片地方。”
“鳥都沒幾只的地方,修公園誰會(huì)來看。”方肅心里已經(jīng)起了疑,如果有這回事就只有老路知道,他的年齡已臨近退休,何必要瞞著他們。
“小方,你車開得真不錯(cuò)。這次我們哥幾個(gè)沒有你幫忙,真是遇上大麻煩了。”
方肅對(duì)他說:“不用客氣,出門在外,誰都會(huì)遇上需要幫一把的時(shí)候。”
在機(jī)場(chǎng)航站樓門口道別時(shí),方肅在車?yán)锔麄內(nèi)齻€(gè)人輪流握了手,他們的手一點(diǎn)也不像搞研究的那種人,指縫間又紅又糙,皸著裂口,反倒讓方肅想起了道班工人。許研究員又不停地說方肅他們辛苦了,客氣得讓方肅開始反感。幾人離開后時(shí)間還早,公務(wù)讓他有足夠正當(dāng)?shù)睦碛刹恢被氐降腊啵駹柲拘碌膸讞l柏油路剛剛開通,寬敞的街道邊人聲鼎沸,方肅悠閑地開著車在格爾木市區(qū)的大街上閑逛,他最后決定在一家回民館子吃了飯?jiān)倩厝ァ3悦娴臅r(shí)候,方肅仔細(xì)想了想姓許的研究員提到的事,老路為什么瞞著他?如果是個(gè)機(jī)會(huì),不管老路打什么算盤自己也一定要把握住。
……
老路準(zhǔn)備去西大灘兵站前仔細(xì)檢查他借來那輛車的車況,車打火預(yù)熱了很久,蔣浩東之前一段時(shí)間還對(duì)修建文化公園的消息比較關(guān)心,現(xiàn)在早就沒了打聽的興趣,上次他脫崗的事確定要被通報(bào),那之后他對(duì)站上的事就更不關(guān)心了。方肅以為老路今天準(zhǔn)備一個(gè)人前往西大灘兵站,臨出發(fā)前他進(jìn)值班室里問道:“你們哪個(gè)想去西大灘看啊?”
方肅希望蔣浩東能出來回應(yīng)一下,他不想看老路的眼神,那會(huì)讓他沒辦法拒絕。可是值班室靜得出奇,屋子就這么大,他實(shí)在沒地方躲,只能說:“我去吧。”
方肅一直知道西大灘泵站的汽車部隊(duì)。田慧的哥哥在格爾木市人民醫(yī)院工作,她說醫(yī)院里會(huì)接收兵站一些已經(jīng)瘋掉的管道兵。那里面有些兵只是神經(jīng)錯(cuò)亂,在醫(yī)院安靜調(diào)養(yǎng)一陣子就能變回正常人。經(jīng)常進(jìn)出醫(yī)院最后完全瘋掉的也有,那些兵再也沒辦法適應(yīng)正常生活,最后的下場(chǎng)就不得而知了。田慧說以前在高原病科住院調(diào)養(yǎng)的一個(gè)兵,犯病的時(shí)候會(huì)扛著40L的氧氣罐在醫(yī)院來回跑體能,醫(yī)院沒人敢去攔,她哥哥當(dāng)時(shí)是實(shí)習(xí)醫(yī)生,他看了那個(gè)兵的病歷,從模糊的戶籍地和口音判斷出他們是同省的老鄉(xiāng),就找機(jī)會(huì)和他說說話。他在樓梯口的角落找到那個(gè)扛著醫(yī)用氧氣罐的兵,對(duì)他說:“你把罐放下,那是氧氣,不是油氣。”
兵把罐立到墻上,說:“我的管子出問題了,快找人來修。”
他看著兵焦急地附在墻角,把腦袋貼到氧氣罐上檢視,忍不住過去拽了他一把:“完了,你仔細(xì)聽。”
兵扭過頭,已經(jīng)冒出一腦門子汗,眼睛發(fā)紅:“哥,你能不能給我戰(zhàn)友說下,管子憋壓哩,叫他們快些檢修。”田慧哥哥只聽見樓道外響徹的人聲和驚沙拍在墻面的窸窣。
幾天后,田慧的哥哥遇到那個(gè)兵的戰(zhàn)友來醫(yī)院給他送雞蛋牛奶,他給幾個(gè)年紀(jì)都不大的男娃說了那個(gè)兵的情況,最后他問他們:“你們站上的管道最近壓力夠嗎?”
幾個(gè)兵警惕地望著他。
他告訴他們,那個(gè)兵說自己在醫(yī)院能聽見幾十公里外他們油庫管道里的聲音,前幾天他聽見管道壓力不對(duì)。幾個(gè)兵想了很久,對(duì)著他點(diǎn)點(diǎn)頭。
老路和方肅駛過一半路時(shí),遇到騎摩托車遠(yuǎn)途的一隊(duì)人在路邊休整,方肅降下車速,老路搖下車窗問他們需不需要幫忙。那伙人都晃著頭盔,低沉著聲音道謝。開過他們后,老路還盯著后視鏡里看,這段國道到拉薩還有超過1000公里路,騎摩托車前往要費(fèi)不小的勁兒。方肅看老路還望著那伙人,不屑地說:“難過。”
老路說:“跟你是差不多年齡的人。”
“那伙人可比我命好。”
“你的命怎么了?”
方肅覺得老路在故意裝糊涂:“我的命就困在這片荒原里了。”
老路不說話了,方肅覺得自己的譏諷是在報(bào)復(fù)他,可又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
兩個(gè)人許久不說話,車已經(jīng)駛近西大灘,能看見幾幢建筑的時(shí)候,老路開口:“我們站上是要修個(gè)文化公園。”
方肅也已經(jīng)不在乎這件事:“誰都知道了。”
“昨天我和莊隊(duì)長才拿到批復(fù)文件,他順便把小蔣的通報(bào)給我了。”
方肅料定通報(bào)不會(huì)太嚴(yán)重,蔣浩東到這兒的半年時(shí)間里,誰都能看出來他的態(tài)度,他遲早會(huì)從這兒調(diào)走,沒有人愿意來路政隊(duì)。之前,最嚴(yán)重不過是批評(píng)教育。
“莊隊(duì)長還交代了一件事。”
“嗯?你說。”
“他知道你們兩個(gè)年輕人的想法,說應(yīng)該給你們一個(gè)機(jī)會(huì)。”老路說完把車窗搖了上去,西大灘的野風(fēng)暫時(shí)停下了呼嘯,老路看方肅盯著自己,抬手指了指前面的路,他繼續(xù)說,“這個(gè)文化公園建起來,整個(gè)隊(duì)的功能就不一樣了,不僅要保障,還要記錄這條路上以前和將來會(huì)發(fā)生的事。莊隊(duì)的意思是,你們兩人如果能在這件事上做出貢獻(xiàn),可以考慮調(diào)到格爾木專門去做文化宣傳的工作。你們的文化程度都?jí)颍趫嚎诖臅r(shí)間也不短,對(duì)你來說是個(gè)好機(jī)會(huì)。對(duì)小蔣來說,他起碼能給家里掙個(gè)面子回去。”
方肅聽到了自己心跳的聲音,他甚至沒去想“做出貢獻(xiàn)”是什么意思,就決定要把握住這次機(jī)會(huì),他期待了太久。方肅平復(fù)了下心情,可還是發(fā)現(xiàn)自己身上的某個(gè)地方在發(fā)抖:“我該怎么做?”
“這兒是以前青藏公路的源頭,當(dāng)初修建時(shí)留下了很多革命文物,文化公園建起來得拿東西出來陳列。前面那個(gè)兵站是莊隊(duì)點(diǎn)名要我們?nèi)ァ!?/p>
“我們都不搞新聞發(fā)掘,就這樣直接去?”
“這次只是調(diào)研。你和小蔣可以按莊隊(duì)的指示一起幫我,要怎么發(fā)掘資料我也要聽你們的想法。我們?cè)诟咴ぷ鳎總€(gè)人之間都是要相互幫助的。”老路語氣溫和地問,“你家里是不是只有爺爺了?”
方肅一般不和他們提起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和蔣浩東。今天老路告訴他一個(gè)機(jī)會(huì),自己對(duì)他不該防備,而且他知道老路對(duì)他的檔案資料是了解的,沒什么事好瞞,于是說:“對(duì),家里現(xiàn)在就我爺爺一個(gè)人。我沒見過我媽,聽說她是我爸出去跑車時(shí)帶回來的,生下我之后沒過多久就被我爸打跑了。后來我爸從四川拉了一車柑橘,和他當(dāng)時(shí)的另一個(gè)女人一起往西藏運(yùn),過川藏線的時(shí)候貨車在一個(gè)埡口滑翻,掉進(jìn)山坳里,他們的尸首被路過的司機(jī)裝殮在盛柑橘的竹框里,托人運(yùn)了回來。事故發(fā)生那年我剛上學(xué),是在一個(gè)冬天,帶回來的柑橘我們一直吃到了過年。”
老路說:“以后有機(jī)會(huì)還是去把你媽找到。你是不是申請(qǐng)了休高原假?回去好好陪你爺爺,別像在這兒一樣成天想著睡大覺。”
“好。”方肅不想說太多,他媽這輩子肯定是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也沒什么用,他爸在的話一切都還有意義,現(xiàn)在只有他爺爺和他血脈里天生的感情維系著。
到兵站的時(shí)候冰雹降了下來,砸得車頂乒乓亂響。方肅和老路從車后套上藏藍(lán)色的軍大衣和雷鋒帽跳下車往里走。兵站足夠大,在西大灘漫漫谷壑和戈壁里遒勁挺拔著身子,老路跑過去給執(zhí)勤的衛(wèi)兵說明了來意,那個(gè)衛(wèi)兵看上去有些緊張,發(fā)紫的嘴唇剛想打開問老路什么問題,老路把路政員的證件掏出來又把他打斷了。他接過證件看了看,一下子慌亂地不知所措。他鎮(zhèn)定平復(fù)了一下,回到崗哨用步話機(jī)往兵站通了話,里面的人核實(shí)了情況,答應(yīng)派人來接他們進(jìn)去。等待的時(shí)候方肅仔細(xì)觀察那個(gè)衛(wèi)兵,他的年紀(jì)比自己還要小,稚氣和一種威嚴(yán)同時(shí)在他的臉上,方肅想到田慧哥哥醫(yī)院里的那個(gè)兵。
相較方肅,老路表現(xiàn)得很自然。他們被接進(jìn)兵站后,方肅才反應(yīng)過來自己到了部隊(duì)里,他想起那個(gè)衛(wèi)兵腰間鼓起的皮套,提醒自己不該亂打別的主意,一切應(yīng)該按老路的吩咐辦。兵站里充斥著機(jī)械的轟鳴聲,他們被幾個(gè)兵接到油庫西側(cè)的一間辦公室里,這里的噪聲終于小了許多,但老路和一個(gè)軍官說話時(shí)還是不得不提高聲量。煤磚燒旺的鐵爐上坐著沸開的茶壺,窗臺(tái)有一株綠植長得很好,在灰黑的房間顯得翠綠欲滴,讓方肅產(chǎn)生了這間房里會(huì)降下來雨的錯(cuò)覺。方肅能聽出來老路是第一次到這個(gè)部隊(duì)來,但他和兵站的人又好像都很熟悉。老路說明了來意,方肅才知道昆侖山口那座軍人碑就是紀(jì)念西大灘兵站的汽車部隊(duì)。那個(gè)軍官聽過后伸手和老路握了握,道了聲謝,老路和方肅都沒明白他的意思。
軍官和他們客套了一會(huì)兒,說了說兵站的歷史,不久就起身敬禮,沒說一句話,推門離開了辦公室。等了一會(huì)兒后那個(gè)衛(wèi)兵跑了進(jìn)來,他換下了執(zhí)勤的肩章,腰間的皮套也不在了,他朝二人敬禮后才說明他們的意思:“工程部隊(duì)有保密要求,不適合經(jīng)常搞立碑紀(jì)傳形式的工作,您們之后需要什么他們會(huì)盡量配合。”老路趕緊找補(bǔ)了幾句,那個(gè)衛(wèi)兵堅(jiān)持要送他們出站,語氣里已經(jīng)沒有在門口時(shí)那種猶豫。老路實(shí)在拗不過,只能對(duì)方肅說跟著出去。
衛(wèi)兵把他們迎出去,方肅和老路從窗外透過玻璃再瞧那盆綠植,底座的鐵盒已經(jīng)銹蝕得嚴(yán)重,一層薄薄的白漆刷在表面才顯得莊重,上面只寫著兩個(gè)字:忍耐。整個(gè)兵站還咆哮著機(jī)械的轟鳴聲,像是此地偷偷豢養(yǎng)著怪物,它們?cè)丛床粩嗟赝滔逻@里人的情感,留下徹骨的一地空洞。
回到路政隊(duì)后老路讓方肅把通報(bào)帶給蔣浩東,他把通報(bào)丟在蔣浩東床頭,想了想還是把莊隊(duì)長的話告訴了他,蔣浩東并沒有方肅想象中那么激動(dòng),只是翻過身沖方肅笑了笑,說:“多謝你,兄弟。”
方肅問老路西大灘兵站的事怎么跟莊隊(duì)長匯報(bào),老路說:“如實(shí)匯報(bào),大家都能理解。這件事急不得,你們倆可以先了解兵站和其他的情況。”方肅腦子里不斷出現(xiàn)那盆綠植和田慧告訴他的故事,他確實(shí)想查一下那個(gè)兵站的資料,老路告訴他那個(gè)兵站是青藏公路通車后的重大工程,公開的資料很難找到。蔣浩東聽完說他想辦法,不久后他真的把幾個(gè)檔案館的資料整理了出來,里面的內(nèi)容不涉密,足夠他們二人了解那個(gè)兵站和109長路上的其他故事。
方肅為了不漏掉資料里的信息,把所有時(shí)間線又整理了一遍,最后內(nèi)容竟比當(dāng)初他們實(shí)習(xí)期時(shí)候的還要詳細(xì)。一周后老路帶來最新指示,革命文化紀(jì)念館施工方案的設(shè)計(jì)基本已經(jīng)批準(zhǔn)了。
還有一個(gè)消息,方肅的高原假批了,三天后就可以休,假期七天,這樣他就參加不了一小半的參觀學(xué)習(xí)安排,原本莊隊(duì)的計(jì)劃是安排他們輪流去林芝波密、昌都江達(dá)和西藏其他幾個(gè)革命文物保護(hù)單位,還安排了四川的幾個(gè)地方。他們已經(jīng)把值班室整理了一遍,蔣浩東把衣服都收拾了起來。如今方肅只能錯(cuò)過幾天。
老路送方肅去汽車站的路上交給他一個(gè)文件包,里面的文件和他們這陣子整理的資料相差無幾,方肅看老路一直盯著自己,又在車?yán)镫S便翻了一下,一些準(zhǔn)備館藏的革命文物信息記錄得很清晰,那個(gè)銹蝕的鐵盒被人拍得歪斜,兩個(gè)字剛剛能辨認(rèn)出來,照片和其他幾張一起夾在里面,下面寫著一行小字“西部某部隊(duì)贈(zèng),悉數(shù)收訖。”方肅把文件包放進(jìn)背包夾層里收好,臨下車又聽老路說了幾句不要把功課落下之類的話,揮揮手和他道別,匆忙登上了大巴車。
……
換乘的第二輛大巴只能到家鄉(xiāng)的鎮(zhèn)上,徒步走了三公里的鄉(xiāng)村硬化路后,方肅晚上九點(diǎn)左右才到青石村。村子已經(jīng)早早地陷入沉睡的靜謐當(dāng)中,家門口斜倚著幾塊花崗巖墓碑在月下發(fā)著冷光。方肅輕輕地敲了敲鐵皮門,幾秒鐘后家里的燈就亮起來了。方世昌搖開鐵皮門的門閂,吱扭聲驚起幾聲遠(yuǎn)處鄰居家的狗叫,方世昌看清是方肅,趕緊接過他手里的背包,把他往門里迎,嘴里囁嚅著:“又趕了一天路,快進(jìn)來。”
爺爺方世昌是青石村唯一的石匠,以前村子人家里臺(tái)階、食槽、磨盤、碾子、柱墩、石臼都是用錘子和鑿子打出來,人們喜歡在石頭里刻塑自己的家,后來慢慢方世昌能做的活計(jì)變少了,就只打起石碑,從開石到打石他都認(rèn)認(rèn)真真對(duì)待,活人的需要總能找到替代,人死了之后,留下幾句想和后人說的,方世昌就替他們?nèi)Y刻在碑上。
方肅有些累,讓準(zhǔn)備生火做飯的爺爺別忙活,爺倆就只燉開一壺磚茶,喝了幾口睡下了。第二天方世昌早早地起來架起火,給方肅做了早飯,喊他起來吃了點(diǎn)兒。悶向心頭瞌睡多,加上趕車的疲乏,方肅回想不起多久睡過如此踏實(shí)的覺,醒來后難得的清醒。吃罷兩人才喧起來。方世昌還是以前一樣的問題:“路還好走嗎?”
“好著呢。天天有人去檢查。這次有七天假,我們?nèi)ツ膬恨D(zhuǎn)轉(zhuǎn)?”
“你不在別人忙得過來嗎?”
“老路他們都出來學(xué)習(xí)了,其他隊(duì)派人來盯一陣子,我們線有其他安排。”
“那你早點(diǎn)回去,別人還有別人的事兒,麻煩人家干什么。”
“我們站上準(zhǔn)備建個(gè)革命紀(jì)念館,出來都是帶著任務(wù)的。”方肅起身去取來老路給自己的文件包,拿給方世昌看看,“你看,這些是我們最近找到的。”
方世昌顫顫巍巍地接過打開,仔細(xì)地看了起來。方肅吃過飯又覺得一陣倦意襲來,起身說:“老路說我有機(jī)會(huì)可以調(diào)格爾木去,要是每周都有假,回來就方便。”時(shí)間充足,爺爺院子里栽種的杓蘭泛著深郁的紫色柔光,蟲鳥遠(yuǎn)遠(yuǎn)在山澗啼鳴,他準(zhǔn)備趁機(jī)再打個(gè)盹兒,養(yǎng)足精神出去到處逛逛。
晌午時(shí)日頭太過猛烈,方肅被吵醒時(shí)發(fā)現(xiàn)自己渾身汗津津的,屋外傳來幾聲爭吵,他聽出其中有方世昌的聲音,連忙起身跑出去,桌上吃完的早飯還沒收拾,文件包的照片散落了一地。門外兩個(gè)精壯的年輕人不停地和方世昌爭執(zhí),語氣強(qiáng)硬又不敢過分僭越,一會(huì)兒還弓腰敬上煙,方肅過去拉住爺爺,問他們是做什么的。其中一個(gè)看到方肅才停下手上的動(dòng)作:“小方是吧?你在家就太好了。我跟你爺爺訂的碑今天該取走了,你爺爺他非說不認(rèn)識(shí)我,碑也沒給我刻過。”
方肅問:“你什么時(shí)候訂的?”
那個(gè)人說:“上個(gè)月啊。訂金我都給你爺爺了。”
“有票據(jù)嗎?”
“找你爺爺訂碑從來都是不開票,有時(shí)候訂金他都不收。錢倒沒事,碑要是沒刻好就全耽誤了!”
方肅聽他說完這話,心里了然,轉(zhuǎn)頭輕聲問爺爺:“你是忘記給人刻了?”他看方世昌被氣得肩膀發(fā)顫,心里微微發(fā)酸,馬上就要七十五的人,還不讓自己喘口氣。方肅要是在他身邊還能冷臉拒絕上門的人,自己不在的時(shí)候只要來找他訂碑,沒二話就要答應(yīng)。
“胡說八道。這事兒我能忘?他說是謝家的后人/9CEJ4aXYs9MTEvp6tOHWA==,前幾天他家老太還在山里務(wù)勞牲口,好端端的人被他說成已經(jīng)過世一年。”
方肅不知道爺爺哪里出了問題,只能先把他領(lǐng)進(jìn)家里:“你們先等等。”他把爺爺扶到里屋,然后跑出去挪開那副石頭象棋盤,在幾副石碑的中間找到了那個(gè)人故去母親的名字,方肅確定這塊碑出自爺爺之手,而且是近期鏨刻好的。方肅幫那兩人在碑上包上紅布,搬運(yùn)上車就送走了他們。回到方世昌身邊,他正拿著方肅文件里的照片死死盯著,照片里那木制的鐵鍬柄上烙著主人的名字——老路從格爾木將軍樓里找來的那張照片。
方肅輕輕喚他:“爺爺?”
過了許久他才抬起頭,像是中間隔了無法言明的漫長時(shí)間:“你回來啦?”方肅點(diǎn)點(diǎn)頭,內(nèi)心期望一切像此刻一樣正常。
老人又問:“109還好走嗎?”
方肅像昨天一樣回答,“好走,天天有人檢查路況。”
他花白的腦袋又耷拉下去,看著躺在雙手間的照片說:“慕將軍先走了。”方肅不明白爺爺?shù)囊馑迹赝氖趾褪掷锏恼掌氖稚线€能聞到糌粑和酥油的溫暖味道。方世昌又說:“你這回什么時(shí)候發(fā)車,把我?guī)У姐尤ァ!?/p>
“你去沱沱河干嘛?”
“祭奠將軍。你不用管我,先去忙自己的事。把你女人找回來,答應(yīng)人家要好好的。”他抬起頭,聲音冷峭地又提醒道,“以后別沖人動(dòng)手!”
方肅驚起一身汗,后脊背像是有什么東西扎進(jìn)來刺痛了他,陽光熱烈。
方世昌看他的模樣,嘆口氣又輕聲說:“海生,我知道你還在怪罪我。”方肅聽到這個(gè)陌生又和自己血脈相連的名字,才明白他是把自己當(dāng)成了他的兒子。方肅冷靜下來想了想,還是不知道該怎么答復(fù)這些囑托,他幾乎已經(jīng)忘記自己父親的樣子,更不知道他有什么要記恨爺爺?shù)氖虑椋矫C只能搖頭否認(rèn),給他慰藉。方肅這才注意到,方世昌眼神里流動(dòng)著光澤。老人又說:“你媽離開的時(shí)候,你就比方肅大幾歲而已。她一個(gè)女人跑來西北開荒,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支援五年了,身體被糟踐出癆病,一點(diǎn)心氣都剩不下了,好不容易有個(gè)機(jī)會(huì)調(diào)走,誰也不能攔著。我對(duì)不起你,要是答應(yīng)她帶著你走,日子會(huì)比現(xiàn)在過得好點(diǎn),當(dāng)時(shí)我非想著要給自己留個(gè)后,苦了你一輩子。慕將軍最后的一把灰都留在昆侖山了,我天天給人打碑,還沒把自己活明白。”
方肅說:“這些都不怪你,以前你們都沒什么可選的。”
方世昌把烙著“慕生忠之墓”的鐵鍬照片放回到夾層里,沉甸甸的東西讓他雙手顫抖,他把目光從照片上挪開,終于想起給自己抹抹眼淚。他又翻開那堆文件夾里新的一頁,那是存放在波密紅樓里當(dāng)時(shí)筑路隊(duì)留下的一副鑿子,攏共六枚,平整的一頭被敲開了花,像從石崖里長出的鐵骨朵兒。老路在照片下面寫著“昆侖山種不出玫瑰,這里埋葬著最好的花朵。”
方肅不太清楚爺爺之前做過什么,以他對(duì)那個(gè)時(shí)候的了解,平平穩(wěn)穩(wěn)地過自己的日子總不會(huì)有什么錯(cuò)。他對(duì)方世昌說:“開荒的時(shí)候你做什么?是不是在那時(shí)候和我……我媽認(rèn)識(shí)的。”
方世昌笑了:“你以前從來不愛聽我講這些故事的。當(dāng)時(shí)家里能交的東西我全交上去了,從西藏回來的時(shí)候,我身上有點(diǎn)重量的就剩下兩塊鑿子。”方世昌輕輕晃動(dòng)手里的照片,繼續(xù)說,“和照片上這副一模一樣,已經(jīng)沒法用了,當(dāng)時(shí)就是想留個(gè)念想。我拆了家里的鐵,跑到隊(duì)里上交,沒想到不久之后隊(duì)里又分給我一副鋼鑿、一塊大錘、一塊手錘、三塊鉆子,都是嶄新的。我在青年農(nóng)場(chǎng)的主要任務(wù)就是打水磨設(shè)備和建水磨站的石墩,當(dāng)時(shí)開荒的勞動(dòng)強(qiáng)度大,壓力也大,有人熬不下去,提出荒地種不出糧食的意見,很快就被帶走。后來有人又提出,為了保險(xiǎn)起見,應(yīng)該在荒地修一套水利設(shè)備,不僅滿足灌溉,打下來的麥子還能在水磨上盡快磨出面粉。我們青石村哪有河能帶動(dòng)水磨。可是沒人管那么多,當(dāng)天隊(duì)里就選好了原石,來問我的意見。我不敢評(píng)議石頭,只是問隊(duì)長準(zhǔn)備把水磨站修在哪里,我好確定打多大尺寸。隊(duì)長站在一片荒原的中間,他望向四周只能看見還在開墾的支邊青年們,你媽當(dāng)時(shí)就是其中一員。隊(duì)長想了半天才說,‘世昌同志,不要抱怨困難。我們先求有,你也只管有,不僅要有,還有隊(duì)隊(duì)有,村村有,社社有。’我被他的話嚇到了,之后再也不敢說什么,一直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那天那陣荒原上刮起的冷風(fēng)。”
方肅終于聽完這段故事,他迫不及待地問:“你為什么從西藏回來?那些鑿子是怎么回事?”
“我去修路啊。孩子,你剛往西藏跑車的那個(gè)時(shí)候我就給你說過。川藏路我沒走過,你自己要多注意。青藏公路哪里的路況有問題,我都讓你記下來。”
“你說那個(gè)安置的機(jī)會(huì)就是你年輕的時(shí)候去修過青藏公路嗎?”
“那是第二件我對(duì)不起你的事,你喝醉之后常跟別人抱怨起這件事,可是我當(dāng)時(shí)沒有膽子承認(rèn),后來我再也不提起,只希望你也能把它忘掉。”
“為什么要忘掉?多好的機(jī)會(huì)啊,你應(yīng)該讓人知道你做過什么。”
“活著看到路修到拉薩,再沿著長路回到家里,我數(shù)不清安葬了多少解放軍戰(zhàn)士,他們保佑我平安回來。我當(dāng)時(shí)只是駝工,回來后的幾年時(shí)間又發(fā)生了太多事,誰也沒想起來悼念那些死在路上的人。后來過了很久,我才知道當(dāng)初一起回來的幾個(gè)駝工、戰(zhàn)友享受到了政策,我也替他們高興。”
敲門聲響起,有個(gè)腰彎到怪異角度的老人站在門口,方肅和方世昌停下話頭,走到門口把他往家里迎,那老人穿著嶄新寬大的中山裝,紐子扣得緊緊的,他看見方肅在就停在院子里,對(duì)方世昌說:“孫子回來了?我還想找你下棋呢。”
“你眼瞎啦?這是兒子,海生回來啦。”
方肅給老人使了眼色,他看了看方世昌也就明白了,語氣滿是嗔怪:“就你有個(gè)大兒!算了,等你空了我再來。”
老人走了后方世昌望著空曠的門洞愣神,眼神滿是悲哀。方肅問他怎么了,他搖搖頭嘆聲:“許大爺怕后人趕不回來給他入殮,已經(jīng)把自己的壽衣穿在身上了。”
“還想聽故事嗎?給你講完最后一個(gè),我和老許就先走了。”方世昌又翻出幾張照片,一張張仔細(xì)端詳,然后娓娓說,“我跑到湟源偷偷混進(jìn)部隊(duì)里的時(shí)候19歲,爹娘都已經(jīng)不在了,去的時(shí)候我是想當(dāng)解放軍,就插在解放軍的隊(duì)列里,到香日徳時(shí)我已經(jīng)沒有人樣,掉到最后幫駝工牽起駱駝。有幾回隊(duì)伍前面?zhèn)鱽碓庥鐾练说南ⅲ业男膸缀鯊男乜谔顺鰜恚胪皼_可是身上攢不起一點(diǎn)力氣。不過沒多久又有新消息傳來,土匪已經(jīng)被先頭部隊(duì)收拾了。當(dāng)時(shí)駝工間傳著一種說法:這趟路只有帶隊(duì)的首長知道該怎么走,有次在格爾木,我和幾個(gè)駝工被分到解放軍隊(duì)伍里一起打橋樁,不知誰又提起這個(gè)話,大家都不做聲,只有個(gè)黑瘦穿軍裝的人笑著說,‘怕是首長知道路怎么走,不知道這條長路怎么修。’后來戰(zhàn)友才告訴我,那人就是慕生忠。我們一路開石墊沙,修橋鋪路摸索著往前,可是越往前海拔越高,高反越嚴(yán)重,那不是年輕力壯就能扛過去的,越是身體好的人越容易倒下。有個(gè)姓張的班長說自己感冒了頭疼,早上請(qǐng)假在帳篷里多睡了半個(gè)鐘頭,結(jié)果我們?cè)偃ソ兴臅r(shí)候人已經(jīng)去世了。躲過高反沒多久,我們又染上了膿瘡,不少人腿都爛開了,將軍叫人運(yùn)來水蘿卜,才治好了我們。修筑沱沱河路段的時(shí)候我認(rèn)識(shí)了師傅——石匠郝仕貴,那段時(shí)間我們不停地架橋,幾乎是泡在河里趕工,路修到一處寬闊山澗,從地基修葺石方工程太艱巨,引道填不上砂石,大家空有力氣卻使不出來,部隊(duì)被攔在那里整整一個(gè)下午。后來郝師傅想了辦法,在石谷的墻面打上斜柱樁,再往上鋪一層梁做橋面,問題就迎刃而解。在通天河路段,我們不少馱馬被沖倒卷跑,陷進(jìn)淤沙里就找不見了,那個(gè)場(chǎng)面讓我們牧民戰(zhàn)友不停地掉眼淚。路終于修到唐古拉山腳底,我們犧牲的戰(zhàn)友埋在沿路石崖下,剩下的人手腳皸裂,滿是鮮紅的豁口。凍土層堅(jiān)硬到十字鎬也奈何不了,我們分成幾隊(duì)每天輪流上去,待在山頂干活,稀薄的空氣讓身體憋悶,更難受的是在山腰時(shí)看著駱駝背下戰(zhàn)友的尸體。我們就這樣在唐古拉山上修了40天,手里的工具都磨得光禿禿的,我記得是第十七天,我的師傅郝仕貴被馱下了山。”
方肅沒再吭聲,他已經(jīng)了解過那段故事,回想起自己在路政隊(duì)的水泥地坪上望向昆侖山埡口的每個(gè)黃昏,長路漫漫,那時(shí)他沒有想讓自己去記住什么,還以為自己對(duì)過去發(fā)生的事也能全然不在乎。而現(xiàn)在,先他而去的人,又從四面八方涌來,讓他內(nèi)心顫栗。
“10月,我們終于打通唐古拉山,一群人像從地獄搶回了自己的命,嘴唇皸裂、鼻孔糊著血痂、雙腿是紫紅色的淤青和流膿的凍瘡。那時(shí)候西藏這邊,來了不少民工加入,我們知道勝利在望,每個(gè)人都卯足了勁要往前沖。于是我們出發(fā),又卷起礫石、沙粒、碎屑巖。每當(dāng)天光逐漸明朗起來,西藏的清晨會(huì)從青紫色變成血紅色,浸透露水的原野在霧靄深處清晰起來,我們就在那些地方發(fā)現(xiàn)眼前的路已經(jīng)讓當(dāng)?shù)夭刈灏傩招藓昧耍覀儚母駹柲疽宦蜂侁惿笆难埽鹨赖拿}絡(luò),終于和他們匯通在了一起……”
方肅和方世昌約定第二天就一起出發(fā),到昆侖山口再前往沱沱河,如果可以,他們最后也會(huì)停留在拉薩。他們只準(zhǔn)備帶上幾瓶青稞酒用來祭奠。出行的方式還沒來得及商榷,火車或者大巴車對(duì)他們來說都是好的選擇,還未到來的事此刻不成顧慮。方肅給老路打去電話,告訴了他發(fā)生在這兩天的所有事情。老路正在去往林芝的火車上,方肅腦海里出現(xiàn)那個(gè)地方的模樣,印度洋暖流順著雅魯藏布江向上,讓那里氣候溫潤。老路說:“本來想等你回來再說的,我覺得現(xiàn)在告訴你會(huì)更好一些。其實(shí)莊隊(duì)根本沒有說什么機(jī)會(huì),我們做的事還遠(yuǎn)不值得。等結(jié)束回到道班,我們還是我們……”此刻高原的天空藍(lán)得出奇,火車可能穿行到某個(gè)深邃的地方失去了信號(hào),霧靄流動(dòng)在弧形的地平線上,一切有跡可循。
方肅卻只想再去見見109和318沿途的石崖,那里安葬著過去的時(shí)間。
責(zé)任編輯:張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