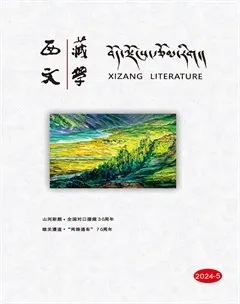天路往事
一
距離我初次踏上青藏公路,至今已近五十年了。當時的我未曾想到,與這條天路有如此的緣分,以后的人生還將多次往返青藏線。時光荏苒,我已從稚嫩孩童變為年近花甲的老人,但那一段從青藏公路進藏的極限體驗,未曾從記憶中遠去。
48年前,在那曲工作的父母休假后返藏,將我和弟弟及小妹一起帶進藏。我們從上海乘坐火車,到達甘肅省酒泉市柳園鎮。出站時,看見四處是茫茫的戈壁灘,僅生長一些紅柳、駱駝刺等耐旱植物。我心想,這個連樹都沒有的地方,怎么和蘇中家鄉滿目青綠、小橋流水、青磚黑瓦的外婆家,差別這么大。
我們在運輸站住了幾天后,父親單位從內地新接的212北京吉普車到了。新車到后,用一天時間采購了水果和副食品,然后我就帶著對西藏的好奇心和對未來的向往,奔赴青藏高原。
二
從柳園到父母工作地西藏那曲,有千里之遙,一路要經過敦煌、大柴旦、格爾木、納赤臺、昆侖山、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唐古拉、安多等地方,海拔漸高,沿途也漸荒涼。我們的車從柳園驅車南下,進入眼簾的是黃褐色的戈壁灘和起伏連綿的沙丘。車行不久,戈壁灘漸漸離我們而去,面前是一望無際的沙漠。
傍晚,我們到達敦煌。在一家當地人開的小飯館用餐后,突然天空難得地下起陣雨,我們在橘紅色的街燈下,冒雨匆忙返回旅館。當晚淋了雨后,體弱的我夜里感覺寒意襲來。裹緊被子,直到天亮前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拂曉,一抹淡淡的曙光在天邊彌散,我們從敦煌出發。沙漠漸漸遠去,小車開始進入山區,山路彎彎,崎嶇不平,黑色的山體全是裸露的巖石,冰冷峻峭。車到稍平緩的路段,王師傅將車停下,讓我們下車方便。車門一開,一股寒氣撲面而來,我全身縮成一團,牙齒抖個不停。
當晚,我們夜宿小柴旦。之后,繼續起早貪黑趕路,經過察爾汗鹽湖,在夜幕降臨之時,一片溫暖的燈光下,我們進入了戈壁城——格爾木。
格爾木是連接內地和西藏的重要中轉站,是通往西藏的“天路”的起點。海拔近3000米,內地初到的人常有輕微的高原反應,在這里常常需適應幾天再進藏。夜里兩點多鐘,已感冒的我,被來運輸站住宿的人亂哄哄的嘈雜聲驚醒。
父母帶我到當地醫院吸氧、輸液后,我的感冒和高原反應癥狀有所好轉。可沒料到,有一天中午,我感覺有點熱,便隨意脫了衣服,冷風一吹,到了夜里就開始發熱并伴著全身酸痛。我不敢和父母說,斗膽隱瞞了自己的病情。
從格爾木到那曲800多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路段約占到三分之二路程,海拔5000米以上的路段也大約有二三百公里。車出市區,過南山口,沿著格爾木河逆流而上,公路彎彎曲曲,我們沿路緩慢前行。傍晚,我們到了大山溝下的納赤臺,寒冷和缺氧向我們襲來。下車后,我感到兩腿無力,整個人昏昏沉沉,同車的人個個就像瘟雞一樣,呼吸急促、行動懶散。
在納赤臺吃飯時,我和弟弟、小妹,第一次嘗到了“天路”上的艱苦生活。由于這里僅有兵站可以吃住,又因氣候惡劣,糧食和副食、蔬菜不能自產,只能從內地運來土豆、大白菜和包菜等貯存在冰窖里。所以晚飯吃的是陳年發黃米飯,以及凍白菜燉豬肉罐頭和脫水的干蒜苗炒凍肉片。母親看我和弟弟、小妹沒有食欲,對我們說:“過兩天就到那曲啦!然后帶你們去拉薩看布達拉宮。”我們的心情頓時像得到越來越多氧氣的汽車引擎一樣,歡快而高亢。
半夜,我全身發燙、酸痛,胸悶氣短,喉嚨里發出呼嚕的聲音。后來,我又吐又泄,心里只有一個念頭——趕快離開這個地方。父母見我感冒了,高原反應也這么嚴重,想著請王師傅送我們返回格爾木,等病情好轉再進藏。可又想到,若因為自家的事,耽誤王師傅不能按期返回,又打了退堂鼓。
三
第二天凌晨,王師傅早起發動車,先給水箱加水,用“噴燈”烤“油底殼”。父親也起床幫忙,和王師傅輪流用搖柄不停搖動發動機,使汽車打火啟動。早起發動汽車,是高強度的體力活,兩人氣喘吁吁輪流搖了半個多小時,才將車發動。
從納赤臺出來,車在黑暗的山脈中顛簸,汽車的燈光切割著寒風,隨著車的蕩漾,有細碎的光粉撲灑在公路旁邊橙黃的沙礫上,好像那里隱藏著無數金屑。
天剛亮,過了西大灘,遙望昆侖山,山峰渾圓、平淡無奇,山嶺連綿起伏。近處灰黃色的山梁、荒蕪的無人區,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的車在慢坡土路上顛簸,激起一片塵土,盡管在車內,也是一身灰土,面目全非。
車在坑坑洼洼的砂石“搓板路”上搖擺著,開車的王師傅蜷在污漬斑斑的藍色羊毛大衣里,好像一粒風干的蛹,緊張地握著方向盤,入定般地注視著前方。汽車跳著芭蕾,輪流翹起一個輪子,車左右騰挪,小車被王師傅訓成有靈性的生命,隨著他的臂膀,做出種種驚險的動作。他全神投入,當車向一側傾斜時候,他的嘴也拼命地向同側的耳根掰扯,直到暴露出所有的槽牙。
道路坎坷,王師傅不失時機地猛踩一腳剎車,打一把方向盤,坐在車里的人都隨之大幅度地左右擺動。我無力地靠在后排座位上,全身的骨頭接榫處像開了縫,胃里如萬條蚯蚓在鉆滾。顛簸的土路,仿佛永遠也走不完。
終于,車子一個急轉彎之后,我忍不住搖下車窗玻璃,將腦袋探出車窗嘔吐。風似刀子呼呼地刮著,掃到臉上生痛。入睡的母親頓時驚醒,見我趴在車窗嘔吐,十分焦急地對父親說:“孩子高原反應嚴重,能不能翻過唐古拉山啊!”終于,過了一會兒,我胃里吐得什么也不剩。
我的太陽穴筋脈“咚咚”跳,身體發燙、臉色發白、嘴唇發紫。母親緊緊地把我摟在懷里,我的腦子被汽車顛得搭錯了弦,漸漸陷入虛脫,意識也逐漸模糊。
一路上風雪迷茫,路面時有暗冰,不時看到翻到溝底的解放牌卡車,王師傅每一次都要說:“看,這就是開車太快,或是太疲勞,打瞌睡才翻車的。”
“也不知道車里的人怎么樣?”父親嘆息地說。
青藏路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昆侖山是鬼門頭,五道梁是閻王殿。”很多人到了五道梁生死兩茫茫。那天,我們到達五道梁,滿天烏云,一點星光都沒有。這里海拔高,是青藏公路上氣候最惡劣的地方之一。車到后,我們直奔兵站求救,可因缺醫少藥,兵站的人讓我們趕緊去修路的工程兵部隊衛生室。
五道梁到沱沱河相距約一百多公里,夏季路面凍土層解凍,導致公路像施了發酵粉一般膨起酥軟,鼓包而翻漿。沿線公路因工程兵部隊復修加固,挖了修,修了挖,真是望不盡的天路,修不完的青藏路。我們車子時而在翻漿的公路上猶如搖擺的醉貓前行;時而緩慢地從修路部隊開辟的便道緩行。原本兩小時多的路程,晃蕩了近四個鐘頭才到沱沱河,打聽到修路部隊衛生室的位置。
那是解放軍一個工程兵連隊的駐扎地。官兵們在山腰的一塊平壩上平整了能容納一百多人的空地,搭起了一片帳篷營地。
一個身著綠色軍裝,穿著長筒膠靴,戴著安全帽的部隊領導接待了我們。他當即叫來軍醫,讓父親把我抱進一頂綠色軍用帳篷里,放到簡易的鋼絲床上。軍醫和藹可親、做事細心,先用聽診器聽了會兒,又摸著我的手號脈,然后向父親詢問我的病情發展情況。檢查完,他很快診斷我患有重度肺水腫,并伴有輕微腦水腫,當即給我吸氧,并配好了藥。
我躺在病床上吸著氧、輸著液,在不知不覺中睡著了。醒來時,帳篷里汽燈亮著,父親穿著軍大衣,身子蜷縮,雙手攏在衣袖筒里,靠在木椅上睡著了。帳篷外,狂風夾雜雪花吹打著,雪水打濕的單薄帳篷嘭嘭作響。透出燈光,我看見帳篷外面有幾個黑色的人影在蠕動,大概是值班的崗哨。我暗想,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他們怎么生活?
過了會兒,部隊領導和軍醫走進來,軍醫給我量了體溫,用聽診器聽了會兒,溫和地問我:“現在感覺好點了嗎?”我感覺頭不怎么痛,心不那么慌了,有氣無力地說:“好些了,口渴想喝糖水。”父親責怪我說:“深更半夜的,從哪里給你糖水喝呀!”
部隊領導連忙對軍醫說:“找司務長領幾個水果罐頭來。”父親急忙阻止道:“孩子的話別當真。”
良久,軍醫拿來幾個圓滾滾的玻璃瓶水果罐頭。在那個物質奇缺、冰天雪地的青藏公路修筑工地,水果罐頭是稀罕食品,部隊官兵除了逢年過節就是只有生病才能吃上。
軍醫拿了一個黃桃罐頭,只見玻璃瓶子雪亮透明,一片片淡黃色的果肉浸泡在玻璃瓶中,果肉色澤誘人。他用起子撬開瓶蓋,拿湯勺喂我。那鮮甜、嫩滑、爽口的黃桃果肉入口,甘甜在嘴里肆意蔓延,我在嘴里含了好一會兒,才不舍地咽下去。接著一勺甜蜜、清涼的果汁落入口中,口舌生津,清涼甜美。那是我從未品咂過的一種甜。仿佛在我胃里頓時溶解,并經由胃漸漸滲入到周身的血管里。
天剛破曉,晨曦微露,我的精神好多了,軍醫給我檢查后,對我父母說:“孩子暫時沒事了,這里醫療條件有限,您們還是趕緊到前面的醫院診治。”
部隊領導見我脫離危險,讓軍醫趕緊為我們準備氧氣袋、藥品,并特意囑咐領幾個水果罐頭讓我們路上吃。父親讓母親去車上拿了些禮物,他感激地對部隊領導和軍醫說:“孩子多虧你們搶救,不然怕是要沒命了。這是從老家帶的咸魚和在格爾木買的蔬菜,一點心意請收下。”部隊領導操著四川口音連聲婉拒道:“要不得,要不得,換了誰都會救孩子的。”母親流下感激的淚水,誠懇地對部隊領導和軍醫說:“您們救孩子一命的大恩大德,我們無以回報呀!”父親動情地握著部隊領導的手久久不松開。部隊領導深情地對父母說:“出門在外誰沒有難事,你們長年在西藏工作不容易,獻了青春又獻子孫。我們部隊修筑青藏路,保障西藏這條‘生命線’,我們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鞏固祖國邊防,建設西藏服務的,我們軍民是一家人,就別客氣了,你們的心意我們領了。”
吃過早飯,告別了部隊領導和軍醫,我們便開始翻越唐古拉山。車行不久,就看到了曠遠荒寂的路邊散落的幾座墳頭。王師傅說:“那些墳頭是進藏部隊修筑公路時犧牲的軍人和民工的墓地,他們是步行進藏來修路的,生命卻永遠埋在了高原上。”那幾處墳頭并不起眼、孤零零地立在一望無際的荒原上。我們的心一下子變得沉重,肅穆地注視著。那些鮮活的生命,已融入雪山大地,成為經過千里青藏線上的人們對生命的一種仰望。
車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上下跳動、左右搖晃地行駛,只聽到車顛簸的吱吱響聲。
下午,翻越唐古拉山口時,我透過車窗,在風雪中不時看到三五成群的道班養護工人,在清掃路面上的積雪。他們中有的人用洋鎬、鐵鍬敲破堅冰并鏟入簸箕,倒入架子車里;有的人用鐵鍬和砂石把附近坑坑洼洼的路面填平。路邊的道牙歪了,用洋鉤勾起來,找砂土墊平扶正。還有的人右手拿著鐵鍬,左手拿著饅頭,嘴里費勁地咀嚼。他們的臉龐被高原風雪吹得黝黑,皮膚粗糙。
路過雁石坪,經過高原反應折騰的我,感覺不那么難受了,頭腦清醒了許多。我們的小車歡快地朝著山下奔跑,公路兩旁是遼闊的草原。無垠的草原上散落著黑帳篷,炊煙從帳篷頂裊裊升起;山坡上散落著覓食的牛羊。快到安多縣城時,遠處草原上散落著土坯屋,屋頂經幡飄揚,風格獨特,遠遠地有藏族牧民向我們招手。這一切都使剛進藏的我和弟弟、小妹感到格外新鮮。
我們沒有在安多停留,連夜趕往那曲,經過幾天長途艱險跋涉,終于在凌晨抵達父母工作所在地——那曲鎮。從此,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在西藏開始新的生活。
四
四十多年前,初次踏上青藏公路那塵封往事,不知不覺已成了我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永遠銘記那些為天路付出青春和生命的、功高至偉的人們;常想起青藏公路上的修筑部隊,懷念那黃燦燦的桃兒和清亮甜蜜的黃桃罐頭味道。
我也忘不了,在藏北安多縣工作的那些年,一些在青藏公路上往返奔波的司機朋友曾給我捎帶藏北草原沒有的蔬菜和日用品的往事,以及休假往返青藏線堵車、陷車時道班工人的營救,和在小小的道班房里,圍著鐵皮爐內燃燒著的牛糞火取暖的場景。
在西藏生活的四十多年里,我見證了雪域高原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其中離不開交通運輸的支撐,離不開四條主要進藏路線。其中,青藏公路承擔了總運輸量的85%。從城鄉建設到國防建設,從機械裝備到柴米油鹽,從鋼筋水泥到針頭線腦,從拉薩到百縣萬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運送數萬噸物資,才有了西藏的今天。當然,除了公路運輸外,現在,還有了運輸能力更為強大的青藏鐵路,以及航空運輸。
1954年通車的青藏公路,當時只是一條公路的雛形,有的地方只是畫了一道線而已,后來慢慢成為沙石路,再后來鋪上了瀝青。因為高原凍土層翻漿和重車碾壓而不停翻修,至今不知翻修多少次了。
今年是青藏公路通車70周年,70年對于一條天路而言,還是一條年輕的路,而對于我而言已漸入老年。追憶四十多年前初次青藏公路之行,真是高路入云端,獨特而驚險,對于我來說是一次深刻的人生體驗,精神的傳承、靈魂的洗禮。
責任編輯:張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