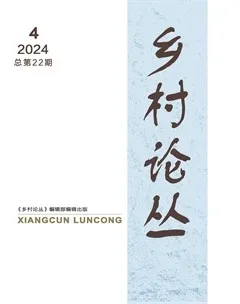與古為新:新質生產力視域下保護發展農業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關鍵問題與實施路徑
摘要:本文深入探討了新質生產力視角下農業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及其在推進農業強國建設中的關鍵作用,闡述了農業文化遺產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多重價值,包括傳統與多樣性、可持續性與適應性、包容性與交流性以及教育性與參與性。通過分析當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面臨的挑戰,提出了具體優化路徑:加強本底調查與保護、增強生態保護措施、加大科技研發力度、激勵社區參與和構建利益共享機制,旨在實現農業文化遺產的創新性轉化和現代農業發展的和諧共生。
關鍵詞:農業文化遺產 新質生產力 現代價值 保護與發展
* 基金項目:2024年山東省鄉村振興專項課題研究項目“山東省農業文化遺產多元價值挖掘及發展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一、導言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強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基,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是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但作為傳統產業和基礎產業,農業在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以及勞動力方面有著其產業特殊性,發展新質生產力并不意味著對傳統農耕文明的顛覆和否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要體現中國特色”,要“賡續農耕文明”,要“把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農業文化遺產是見證和傳承發展農耕文明的重要載體。作為世界上重要的農業古國和農業大國,中國是最早響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倡議的國家之一。截至2023年底,我國共有22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位居世界首位。2022年7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致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大會的賀信中強調,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璀璨的農耕文明,保護農業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責任。中國積極響應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倡議,堅持在發掘中保護、在利用中傳承,不斷推進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方愿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加強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進一步挖掘其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科技等方面價值,助力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農業文化遺產與其他的世界遺產不同,農業文化遺產更強調對農業生物多樣性、傳統農業知識、技術和農業景觀的綜合保護和活態利用,具有活態性、動態性、復合性、多功能性、可持續性、瀕危性和戰略性等特點(閔慶文,2020)。按照糧農組織(FAO)的定義,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這種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農業文化遺產不僅是農耕文明發展的見證,更是兼具科技、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價值的活態系統,它不僅來自過去,更通往未來(閔慶文等,2022)。
二、文獻綜述
目前有關農業文化遺產相關的研究主要呈現三條脈絡:
(一)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的相關研究
已有研究大都認為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是一個跨學科、多維度的領域,它不僅需要學術界的深入研究,還需要政府、社區和公眾的共同參與(李明等,2012;顧軍等,2021;張燦強和吳良,2021),需要采取人文和自然相融合的保護價值觀(石鼎,2022),構建完善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制度體系(張燦強和龍文軍,2020;崔峰等,2023),加強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伽紅凱和盧勇,2023;吳燦,2024)。
(二)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經濟文化價值挖掘利用的研究
已有研究認為,農業文化遺產在推動區域發展,尤其是鄉村振興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推動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張燦強等,2016;劉某承等,2022;王超等,2023)。旅游被認為是農業文化遺產動態保護途徑之一,也是其經濟價值得以發揮的重要手段(閔慶文,2022)。有相當一部分文獻關注了農業文化遺產在鄉村旅游方面的價值挖掘和實現路徑(王欣等,2006;閔慶文等,2007;孫業紅等,2009;蘇明明等,2022),并實證檢驗了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與旅游產業發展存在的顯著正相關關系(劉進等,2021)。此外,農業文化遺產對構建營養健康、綠色可持續的農食系統也具有重要意義(陳俞全,2022)。正因為農業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經濟價值,因此在推動農民增收、實現遺產地居民生計可持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張燦強等,2017;何小榮等,2023)。近年來部分文獻開始關注農業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挖掘和闡釋(李瀾等,2023)。包艷杰和孟曉(2023)從文化接續性的視角出發,認為農業文化遺產是實現文化接續性的一種努力成果,對維護文化連續性具有重要作用。鄭莉等(2024)通過對山東省農業文化遺產工作的梳理指出,擦亮農業文化遺產金字招牌,在復興與傳承農耕文化、推動多功能農業發展與產業融合等多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將農業文化遺產地打造成為文化引領示范片區建設的典型代表,既是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也能為鄉村全面振興開辟新路徑。
(三)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的生態和科技價值的研究
除了經濟文化價值之外,農業文化遺產在增強農業生產系統的適應性,加強自然生態系統對農業的庇護作用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劉旭等,2022)。目前,已有部分文獻從技術和生物多樣性等角度關注了農業文化遺產的科學價值和生態價值。這些文獻大都散見于對典型農業文化遺產地的個案分析。例如,朱有勇(2009)對元陽梯田紅米稻作文化的研究,揭示了農業文化遺產在農業科學價值方面的潛力;趙文娟等(2011)則通過對瀾滄江流域野生稻資源的實地考察指出,野生稻對我國農業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以及提高水稻產量和品質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顧興國等(2018)認為基塘系統是具有獨特創造性的低洼土地利用方式,具有循環生態服務功能;張海超等(2018)則通過對傣族傳統稻作農業生產體系的生態人類學考察發現,傣族傳統稻作是一種高效、理性的生產方式,更有利于可持續發展;陳茜和羅康隆(2021)對湖南花垣子臘貢米復合種養系統的生態價值進行了研究,強調了復興傳統農業系統在生態修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作用。廖會娟等(2023)基于氣候變化響應特征,討論了紅河哈尼梯田文化遺產區的氣候韌性及影響因素。
從已有研究來看,農業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和挖掘,但在科技價值的挖掘和現代應用方面還存在不足。當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遺產的經濟、文化和生態價值上,對于如何將這些傳統知識和技術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用傳統農業的生產智慧助力解決當今農業生產中面臨的環境問題和社會挑戰的探討還不夠充分。換言之,農業文化遺產作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它們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傳統的認知范疇,未來的研究和實踐應當更加注重農業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挖掘,尤其是科技價值的探索,以及如何在保護的同時實現創新發展,讓這些寶貴的遺產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古語有云“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如何在新質生產力的語境下重新審視千年農耕文明的現代價值,如何在保持對農耕文明的尊重和繼承的前提下,將千年農耕智慧為今所用,為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是建設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
三、新質生產力視域下農業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
自2023年9月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系列重要論述,引發了學術界有關新質生產力內涵、理論淵源、重要特征及發展路徑的大討論(周文、許凌云,2023)。農業作為重要的傳統產業和基礎產業,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是由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的,所謂農業新質生產力是指以突破性創新為基礎和前提,以重大新技術產業化應用為主要依托,以現代技術要素為引領,以改善要素投入結構和資源利用效率為標志,以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實現轉型為主要表現的新型農業生產能力(馬曉河等,2024;姜長云,2024)。新質生產力系統具有突出的創新驅動、綠色低碳、開放融合、人本內蘊特性(黃群慧,2024)。在農業強國建設背景下,發展新質生產力,也要從這四大特性著手:一是創新驅動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義,要突出農業科技的自主性和原創性,系統性重構農業科技創新和產業體系(林萬龍等,2024)。二是綠色生態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要注重生態保護和生產力的長期穩定發展(羅必良,2024),增強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三是開放融合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特征,要注重新技術、新業態的拓展,促進技術交流和產業融合。四是人本內蘊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本質特性,要注重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提高農村居民在農業發展中的參與度和獲得感。
農業文化遺產地千百年來積累的種質資源、生產技藝和管理理念對于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強國具有強大的應用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具體而言,從新質生產力的角度來看,農業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農業文化遺產的“傳統性+多樣性”,體現了農業新質生產力創新驅動的核心要義
新質生產力創新驅動的核心要義在于對傳統知識和實踐的深入挖掘以及與現代科技的有機結合,以此推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生產力質的飛躍。農業文化遺產所蘊含的豐富種質資源、生物多樣性維護的傳統知識與技術,以及其獨特的生態智慧,為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創新提供了重要借鑒。第一,農業文化遺產的豐富種質資源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寶貴的遺傳多樣性。據種質資源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庫保存資源超過52萬份,但完成表型與基因型精準鑒定可用于育種創新的只有1萬多份,優質種源“沉睡現象”較為突出。農業文化遺產地被喻為中國良種活態基因庫,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都是在不同的生態環境條件下歷經千百年的長期選育而傳承下來的,相對于現代種質資源基因庫的單品種保護,更具有活態性和可延續性,蘊含著功能育種的珍貴價值。例如,山東省泰安汶陽田農作系統距今已有2600多年歷史,是黃河流域麥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保存有360多份小麥種質資源,年推廣汶陽田小麥種1300多萬千克;山東“嶧城石榴種植系統”栽培歷史已有2000余年,種植品種60余個,超過100年以上的石榴古樹3萬余株,保存國內外石榴種質資源370余個,是世界上最大、最豐富的石榴種質資源圃之一。據研究,這些傳統品種的引入可以顯著提升作物的適應性和生產力,從而增強農業系統的穩定性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第二,農業文化遺產中的生物多樣性為新質生產力的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實踐模式。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通過生物間的自然相互作用,有效控制了病蟲害,減少了農藥使用。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該系統比單一種植水稻的產量提高了約20%,同時減少了30%的農藥使用,有效維護了生態平衡。第三,傳統知識與技術的現代轉化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起到了橋梁作用。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山東樂陵棗林復合系統被譽為“全國最大千年原始人工結果林”,以千年棗林為依托,在“棗糧間作”復合耕作模式的基礎上,拓展探索間作中草藥、油菜、食用菌等經濟作物,發展林下養殖,形成“林—果—禽”間作的可持續發展的良性生態系統;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通過“基上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雍桑”的獨特體系,實現了生態循環鏈“零排放”。通過借鑒和應用這些傳統模式,新質生產力能夠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時,促進農業生態系統的健康和農業環境的可持續性。
(二)農業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性+適應性”,體現著農業新質生產力綠色生態的內在要求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質生產力的綠色低碳要求強調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必須兼顧生態環境的保護與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農業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性+適應性”正是這一要求的生動體現,它們不僅承載著深厚的農耕智慧,也為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在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天時地利”“天人合一”等大生態觀下,農業文化遺產地的農戶因地制宜形成的間作套種、農林復合、農牧結合、稻魚共生等眾多傳統農業技術,既能提升有限土地的利用率,又有助于構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給體系,可以顯著增強農業產業韌性。例如,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山東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群系統”開創了因地制宜、以桑治沙的可持續農業發展模式,形成水土保持功能的農業生態系統,大大改善了當地小氣候和水土環境,在防沙治沙、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資源利用、農業景觀維持等方面產生多重價值,成為兼顧生態治理和經濟發展的沙地農業系統的重要典范。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山東平邑金銀花—山楂復合系統”,金銀花與山楂間作的岱崮地貌土地利用模式,體現土地最大化利用、節物致用、和諧共生的文化理念,形成生態保護與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可持續發展系統。云南哈尼梯田的“四度同構”農業模式,則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將梯田、村寨、森林、水源融為一體,創造了獨特的生態農業系統。哈尼梯田的生物多樣性指數顯著高于周邊地區,其生態服務價值每年高達數千萬美元,凸顯了農業文化遺產在綠色低碳發展中的重要價值。通過保護和傳承這些文化遺產,可以為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同時為新質生產力的創新驅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三)農業文化遺產的“包容性+交流性”,體現著農業新質生產力開放融合的重要特性
新質生產力的開放融合特性強調了在全球范圍內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這要求通過跨國界的合作,共享知識、技術和資源,以促進農業系統的創新與持續進步。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業文化遺產的“包容性+交流性”顯得尤為關鍵,它們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多樣性,而且通過促進不同文化和經濟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土壤。中國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倡議的早期響應者和積極推動者,已有22項傳統農業系統被列入GIAHS名錄,數量居世界首位。此外,福州茉莉花茶系統與法國勃艮第葡萄園、江蘇興化垛田農業系統與墨西哥城浮田系統陸續簽署合作備忘錄,開展“結對子”交流,進一步推動了跨國農耕文明的對話與交流。從包容性來看,很多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通過建立社區參與機制,鼓勵當地農民參與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增強了農業文化遺產的社會包容性。例如,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山東臨清黃河故道古桑樹群系統千百年來積淀形成了“桑林固沙、葚果為生、養蠶繅絲、桑黃養生”為核心的農業文化傳承,并將蠶桑文化、黃河文化、壽文化和孝文化注入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培育之中,有效提升了當地鄉村治理效果。由此可見,通過增強農業文化遺產的社會包容性,可以更好地實現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的良性互動,推動農業農村的高質量發展。
(四)農業文化遺產的“教育性+參與性”,體現著農業新質生產力人本內蘊的根本要求
新質生產力的人本內蘊要求強調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必須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和個體價值的實現。農業文化遺產的“教育性+參與性”在這一要求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不僅傳承了傳統農耕智慧,還促進了社會各界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參與和貢獻。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2015年開始通過編印垛田農民畫教材、開設垛上少年宮、實施千垛滋根等項目讓3000余名孩子了解垛田文化,感受垛田鄉情,其中,千垛滋根項目入選江蘇省中小學生品格提升工程優秀項目。山東省自2024年起開展“四季農遺”系列活動,通過鄉村大講堂等形式,推動農遺文化進村莊、進校園、進社區巡講,舉辦農遺短視頻、攝影大賽等宣傳推廣活動,強化各界對農業文化遺產的認識,培養知農愛農惜農助農情懷,增進了農業文化遺產的社會認同感。
四、新質生產力視域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關鍵問題
當前,很多農業文化遺產地面臨著農業現代化發展與保護農業文化遺產之間的權衡問題。有些人提出,農業文化遺產遺留下的技藝相比現代工藝,其效率是低下的;有些古樹已經沒有生產力了,不結果子,為什么還需要保護它?有些種質資源產量和口感都不如現代品種,還需要繼續保護嗎?老百姓出于增收、生計的考慮,喜歡用新品種,拋棄老的技藝和品種,在大力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當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是什么?應該如何正確處理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系?要回答以上問題,首先要厘清農業文化遺產的本質和獨特性。農業文化遺產被稱為是留給未來的遺產,它的獨特性在于:一是它是“活態”的,具有生產性,且必須在生產發展中保護。二是它是“遺產”,意味著它有比較久遠的歷史傳承。三是它有“文化”內涵,蘊含著先人歷經千百年留下的農耕文明的智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當地的文化精神。之所以被稱為“留給未來的遺產”,是因為它的活態發展以及蘊含其中的歷史智慧和文化密碼。因此,充分發揮農業文化遺產對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還需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需要始終明確活態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屬性是多元的
活態的農業文化遺產通過生產發展而延續多年,如果沒有了生產,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也無從談起。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文化遺產只有一種產業屬性,只能從生產效率上體現價值。傳統的手工技藝可能不如現代技藝生產,古老品種的果實口感不如新品種好,古樹已經喪失了結果的能力,等等。但這些都只是從現代特色產業生產效率的角度考察農業文化遺產的生計屬性,這種考察角度是片面和有偏的。農業文化遺產的生計價值是多元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評審條件中雖然強調了其經濟價值,但同時也強調其景觀價值、文化價值、歷史價值。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后三者的生計屬性逐漸變得更為突出。例如,千年梨樹、千年桑樹本身就是一道風景。通過“賣”景觀、“賣”文化實際上也可以給當地農戶帶來生計收入。此外,農業文化遺產的金字招牌也可以提升農產品自身的價值。像敖漢的小米、青田的稻米、桂河的芹菜,單價都可以數倍于一般的農產品。因此,對于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能僅從農業生產效率的角度去評價其生計價值,而是要從多元的角度挖掘農業文化遺產的生計價值。
(二)需要強化農業文化遺產的歷史保護意識
當前社會上很多人對文化遺產的認知都停留在博物館、展覽館等“靜態”展示中。因為博物館的存在以及各種文物的呈現,讓人可以體會到人類歷史發展的悠久。無論是建筑構件的一磚一瓦,還是日常生活的一瓶一缶,這些文物盡管在現代實用性上不再具有直接功能,但它們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價值都是極為寶貴的。同樣,五千年的農耕文明歷史和千百年的農耕智慧實際上也都蘊含在農業文化遺產之中。這些遺產不僅包括物質形態的古樹、遺傳資源的種質庫和傳統技藝的古法,還包括與之相關的農耕文化中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和藝術表達。它們共同構成了農耕文明的實證,是歷史與自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珍貴財富。如果沒有留存的古樹,沒有可以追溯遺傳基因的種質資源,沒有傳世至今的古法技藝,就沒有農業發展的歷史。農業文化遺產核心區的保護工作,本質上是對歷史見證的維護,它不僅關乎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更涉及對農耕文化精神的傳承。因此,地方政府在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應當將農業文化遺產的核心要素視作與其他文物同等重要的保護對象,避免因這些遺產的活態生產特性而削弱對其靜態保護的重視。通過有效的保護措施,不僅能保存歷史,還能確保文化的連續性和多樣性,為后代提供持續學習和啟發的源泉。
(三)需要尊重農業文化遺產中蘊含的科技智慧
農業文化遺產作為歷經漫長歲月而傳承至今的知識體系,不僅承載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傳統技術,而且體現了一種在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等多重風險沖擊下的生產韌性。這種韌性構成了農業文化遺產對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是一份珍貴的“活遺產”。解讀農業文化遺產中的科研價值,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其內在的生態機制和文化邏輯。農業文化遺產中蘊含的“天人合一”與“和諧共生”的傳統智慧,為現代農業面臨的可持續發展挑戰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解決方案。例如,千年桑樹的生命力不僅是生物學上的奇跡,更是對環境適應性、遺傳穩定性和生態恢復力的深刻體現。探究其背后的生存機制和抗災策略,對于現代農業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品種改良和生態農業模式構建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然而,當前對農業文化遺產的科學研究尚顯不足,對其生態和文化價值的全面解讀仍有待深化。解讀農業文化遺產中的科研密碼,需要尊重其地方性知識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更為系統的研究和探索,以實現其科研價值的現代轉化和應用。因此,保護農業文化遺產不僅是對其歷史價值的尊重,更是對其科研價值開發利用的前提,是實現其與現代農業生產有機結合的關鍵步驟。
五、新質生產力視域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實施路徑
(一)加強本底調查與保護力度,確保農業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和傳承性
一是摸清農遺家底。以聯合國糧農組織和農業農村部建立的農業文化遺產定義和遴選標準為基礎,以省為單位開展農業文化遺產普查工作,構建類型全面、標準明確、權責清晰、科學有效的農業文化遺產資源普查方案。對在種質資源、生產技術等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且目前仍有較強生產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農業生產系統進行深度挖掘、登記入冊,摸清家底,出臺精準政策,加強保護和利用。二是全面普查農業文化遺產地的傳統種質資源情況,查清農業物種資源種類、數量、面積、伴生物種、分布地點和瀕危狀況,從稀有性、重要性、瀕危性等角度開展遺傳價值、文化內涵與產業化潛力評估。三是建立健全多元化農業文化遺產資源保護體系,建立健全面向遺產地農戶的種質資源保護激勵機制,加強宣傳,建設“農民種子銀行”,鼓勵遺產地農戶參與種質資源保護。
(二)強化生態保護力度,確保農業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性和適應性
一是多樣化實現遺產地生態產品價值。鼓勵農業文化遺產地核心區采取原生態種養模式,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提高遺產地的生態產品價值;依托遺產地“土特產”優勢和景觀特色,拓寬產業鏈和價值鏈,開發農耕文化體驗與休閑康養融合發展的新業態,促進遺產地生態產品的價值增值。二是構建多方共享的生態保護利益聯結機制。建立政府、社區、企業等多方參與機制;建立健全遺產地生態與文化保護補償機制和帶動小農戶分享農業文化遺產發展紅利的利益聯結機制,激發農戶參與保護和傳承農業文化遺產的內生動力。
(三)強化科研力度,提升農業文化遺產的教育性和交流性
一是普查保護和開發利用同步推進,推動構建多層次保護、多元化利用的農遺保護利用格局。對于一些極具地方特色且具備較高利用價值的遺產地進行深入開發利用,使其在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中大顯身手,為做好“土特產”文章、推動鄉村全產業鏈升級提供助力。二是聯合研究力量,加大對遺產地種質資源的研發力度。充分挖掘遺產地種質資源傳承千年的生產韌性基因,推動實施“農業文化遺產種質資源挖掘與創新利用”專項,將種質資源與遺產地的生產系統關聯研究,深入發掘遺產地種源的優異基因,定向培育優質、抗逆、高效利用的新種質并推動產業化利用。三是出臺農業文化遺產品牌管理辦法,開發有文化內涵的農產品,加強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標識的設計與推廣。利用數字化手段進行立體化宣傳,如虛擬現實、3D動畫等,保存和再現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核心價值,為價值傳承和旅游開發提供新的手段。
(四)推動社區參與和利益鏈接,提升農業文化遺產的包容性和參與性
強化社區參與,建立政府、社區、企業、農戶“四位一體”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機制,推動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進校園、進社區,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利用。依托遺產地的“土特產”優勢和景觀特色,突出農遺的多元價值,強化遺產地農耕文化體驗區功能,擦亮農業文化遺產“金字招牌”,將農遺核心區打造成為特色鮮明的鄉村振興示范片區,為鄉村全面振興增亮點、增特色。此外,構建多方共享的生態保護利益聯結機制,確保廣大農戶在農業文化遺產保護中受益,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提高遺產地人民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2]閔慶文.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研究的優先領域、問題與對策[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2020,28(09):1285-1293.
[3]閔慶文,駱世明,曹幸穗,等.農業文化遺產: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J].農業資源與環境學報,2022,39(05):856-868.
[3]李明,王思明.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困境與對策[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9(01),30-37.
[4]顧軍,苑利.我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問題與反思[J].貴州社會科學,2021,(09):52-56.
[5]張燦強,吳良.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內涵再識、保護進展與難點突破[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1):148-155+181.
[6]石鼎.從遺產保護的整體框架看農業文化遺產的特征、價值與未來發展[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9(03):44-59.
[7]張燦強,龍文軍.農耕文化遺產的保護困境與傳承路徑[J].中國農史,2020,39(04):115-122.
[8]崔峰,王哲政.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預警評價體系構建與方法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23,38(05):1119-1134.
[9]伽紅凱,盧勇.農業文化遺產供給側改革:矛盾表征、肇因分析與策略選擇[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0(05):189-202.
[10]吳燦.農業文化遺產:地方性知識的生成與演變[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4,53(02):33-41.
[11]張燦強,沈貴銀.農業文化遺產的多功能價值及其產業融合發展途徑探討[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3(02):127-135.
[12]劉某承,蘇伯儒,閔慶文,等.農業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運行機制與實施路徑[J].農業現代化研究,2022,43(04):551-558.
[13]王超,崔華清,蔣彬.農業文化遺產如何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基于共生系統說的貴州從江占里侗寨案例探索[J].廣西民族研究,2023,(03):164-172.
[14]閔慶文.農業文化遺產旅游:一個全新的領域[J].旅游學刊,2022,37(06):1-3.
[15]常旭,吳殿廷,喬妮.農業文化遺產地生態旅游開發研究[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7(04):33-38.
[16]閔慶文,孫業紅,成升魁,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與開發[J].經濟地理,2007,(05):856-859.
[17]孫業紅,閔慶文,鐘林生,等.少數民族地區農業文化遺產旅游開發探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01):120-125.
[18]蘇明明,楊倫,何思源.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與社區參與路徑[J].旅游學刊,2022,37(06):9-11.
[19]劉進,冷志明,劉建平,等.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分布特征及旅游響應[J].經濟地理,2021,41(12): 205-212.
[20]陳俞全.農業文化遺產參與農食系統轉型的現實意義與關鍵議題[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9(03):74-87.
[21]張燦強,閔慶文,張紅榛,等.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目標下農戶生計狀況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27(01):169-176.
[22]賀小榮,史吉志,徐海超.農業文化遺產旅游對鄉村振興的驅動機制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3,37(08):201-208.
[23]李瀾,劉麗偉,馬曉旭.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性開發研究——基于貴州從江稻魚鴨系統保護性開發實踐的思考[J].廣西民族研究,2023,(02):144-151.
[24]包艷杰,孟曉.文化接續性視域下的農業文化遺產[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45(04):123-128.
[25]盧成仁.鄉土中國的命運與農業文化遺產的未來[J].思想戰線,2023,49(04):67-73.
[26]鄭莉,李沛喆,呂文秀,等.山東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發展的探索與研究[J].鄉村論叢,2024,(03):73-81.
[27]劉旭,李文華,趙春江,等.面向2050年我國現代智慧生態農業發展戰略研究[J].中國工程科學,2022,24(01):38-45.
[28]朱有勇.元陽梯田紅米稻作文化——一項亟待研究和保護的農業科學文化遺產[J].學術探索,2009,(03):14-15+23.
[29]趙文娟,閔慶文,崔明昆.瀾滄江流域野生稻資源及其在農業文化遺產中的意義[J].資源科學,2011,33(06):1066-1071.
[30]顧興國,樓黎靜,劉某承,等.基塘系統:研究回顧與展望[J].自然資源學報,2018,33(04):709-720.
[31]張海超,雷廷加.傣族傳統稻作農業生產體系的生態人類學考察[J].云南社會科學,2018,(02):155-161.
[32]陳茜,羅康隆.農業文化遺產復興的當代生態價值研究——以湖南花垣子臘貢米復合種養系統為例[J].貴州社會科學,2021,(09):63-68.
[33]廖會娟,角媛梅,劉志林.紅河哈尼梯田文化遺產區的氣候響應及韌性機制[J].地理科學,2023,43(11):2014-2023.
[34]周文,許凌云.論新質生產力:內涵特征與重要著力點[J].改革,2023,(10):1-13.
[35]馬曉河,楊祥雪.以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J].農業經濟問題,2024,(04):4-12.
[36]黃群慧,盛方富.新質生產力系統:要素特質、結構承載與功能取向[J].改革,2024,(02):15-24.
[37]羅必良,耿鵬鵬.農業新質生產力:理論脈絡、基本內核與提升路徑[J].農業經濟問題,2024,(04):13-26.
(作者單位:1.山東女子學院經濟學院;2.山東省農業農村廳農村社會事業促進處;3.山東省農業農村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