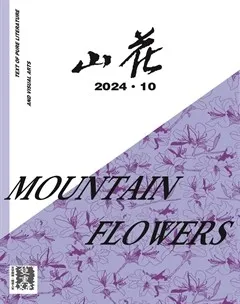創作更重要的是思想新生
藝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覺形態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持續發生著變異,與不同時代特質滲透、互融,形成一條精神卓絕的文化巨鏈承遞著往昔的人文經驗。片段的經驗雖不可復現,但它留給后來者一扇扇思接千載之門以彌合歷史間距、達成深遠的精神邂逅,而它自身則等待被鮮活的觀念、語言喚醒,等待被更新、再造的命運。在油畫研究和創作中,重要的是思想新生,注重融匯中國藝術傳統,將體驗到的動人的感受厚重化,探索“中國油畫”的語言建構和話語體系。
古往今來,即使面對的是人類的共有命題,不同地域藝術家的觀念和語言也是有差異性的,這些差異都極其珍貴、獨特。在我們身處的21世紀,中西古今資源一統、信息過載,世界徹底進入了共時融合的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更為顯著地互滲、交融。當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多維性成為一個顯性特征,當代藝術家需要在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與深層地域意識的差異化之間尋求文化身份的主體性。在我看來,地域的有效性恰恰在于超越了地域表象而顯現出某種獨特性。藝術家需要深度內省、面對真實處境發現并且提出問題。創作思想是不斷被語境、被主體重新定義、不斷更新的思維狀態。地域和時代的痕跡對于藝術家和作品的影響是必然的,但這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隱性的起點。
如何對中華民族傳統文脈進行當代承續與推陳出新是新時代美術怎樣回答好時代之問的關鍵所在。少數民族風情繪畫包含了民族、地域的人文獨特性。中國油畫創作,民族性是一個恒久而宏偉的課題,怎樣用油畫表達民族情懷是油畫創作的核心課題,因此我的創作中,在將傳統民族文化融入當代油畫圖像方面進行了多種實踐,反復論證以油畫的創作語言表現民族精神和時代人文的可能性,而絕非是獵奇般“為圖像而圖像”的編造。在中國傳統浩瀚的語言鏈條中提煉出置于當下的詞匯,并將個人體驗與對少數民族人物命運、處境及精神的理解充分融于其中,將傳統與當代、自我與時代,甚至將理想與現實隱秘的對話寓于其中——不僅是個人化的精神浮現,同時也有著同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同體驗,可以引發觀看者的共情。每位畫家的作品都折射出了創作者之于現實世界、當代藝術、本土文化脈絡的思考。藝術家的知識結構與審美經驗是作品的基座,是重要的思想基礎,藝術家梳理自身與兩者的關系其實是在梳理個人藝術的坐標點。藝術是多種資源的梳理與聚合,但凡有分量的藝術家往往都是很難被簡單歸類,他們的作品通常是多種因素的融生創變,不斷地思想新生,而不單指向某一種因素。藝術的高妙處,恰恰在于其不能直接表達的部分。
如何跳出傳統與日常的思維禁錮,進行當代美術的創新試驗,進而使思想新生,是當代美術創新面臨的難題,但如果轉換思維方式和視角,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創新的維度。達·芬奇曾提出繪畫和雕塑的意義在于“Saper Vedere”(譯為“知道如何觀看”或者是“教導人們觀看”),并認為“只要思索得當,你確能收獲奇妙的思想”。卡西爾提出:“藝術家是自然的各種形式的發現者。”這其中便包含著因思維方式和視角的改變所帶來的藝術表現形式的改變,即思想新生的雙重陌生化。對傳統少數民族人物的創作進行當代性審視與別樣化審美;對少數民族日常社會生活的陌生化審美重構。這兩重維度在藝術創作中也時常相互穿插。
藝術應該無時無刻不在新生中。當藝術創作進入慣性狀態時,藝術家應該反思創作的作用和意義。思想新生后感性的靈力是需要我們歷經長期、反復的實踐才能達至的一種招式渾忘、卻能運用自如的境界。創作時,尋求創新要內容與形式并重,思想維度的內在邏輯,蘊藏在我們每一件作品內部:即使是面對呈現不同題材的單件作品,我們依然可以毫不費力地將它們統一于藝術家的個性化創作范式和個人鮮明的語言特征中,仿佛是在觀看同一件作品。在視覺經驗的汲取方面,我也試圖做到最大限度地展開,一切的經驗都有待于經過篩選,轉生到作品內部。閱讀經驗同樣也不例外。身為創作者要藝理雙修,以思維、思考、思辨作為創作靈感的基礎,讓油畫造型語言從創作角度出發,再從思想的土壤中生發出來。同時藝術家也要堅持深入生活,因為油畫歷來都是要為時代留下形象的縮影,所以油畫家須具備時代新品質,要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不斷提高審美品格,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與傳統視覺中尋找營養并融匯到創作中去。創作者應當跳出小我,融入生活,融進時代,敏銳反映、書寫時代的精神圖譜。精神性寓于生活素材之中,將生活體驗與藝術表達做最大限度的鏈接,對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而言是必要的:人的情緒與情感通常顯現在生活體驗內部,藝術家唯有以最恰當的語言對其進行挖掘,才能為畫面注入真實、感人的力量。我們需要拓展的不僅是技術語言,更重要的是體驗的疆域、生活的疆域、藝術實踐的體系延續與語言轉向。
總而言之,思想新生即如何以不同于傳統和日常的陌生化新思維、新視角和藝術表現形式進行創新,在熟悉性與陌生化的雙重觀照中,作品既具有少數民族人文傳統和日常生活的熟悉感和溫度,又有平中見奇、熟中見生等突破性、典型性和陌生化的新奇感,以及不同于以往的觀看方式和審美創造方式。真正的藝術蘊含敞開的意外感,這一點需要藝術家在約定俗成的邏輯和習慣之外尋找突破口,不斷在全新的視覺經驗之上引發新的思考。創新不應停留在形式層面,更重要的是思想新生。思想狀態的“當代”,顯然比僅僅注重題材的“當代”、材料的“當代”更具價值。面向所處時代,面向深層自我汲取信息,并在此基礎上創建屬于自己的觀念和圖式。身為創作者要以開放的姿態將傳統精神充分內化,取精微契合處發出獨具個性氣息和時代意象的思想新聲。少數民族題材創作更加注重美術創作的地域性、本土性、民族性、世界性和敘事性,在共性與共情中尋求個性化藝術表達。在這個求新求變的過程中,需要我們不斷揚棄自己繪畫語言上不夠純粹的方面和停留在少數民族生活表面的表達,從而在繪畫語言、圖式、動機等方面不斷展現出新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