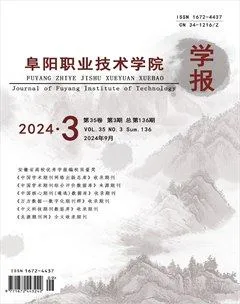魯迅與沈從文鄉土小說的認識價值論
摘要:作為中國現代鄉土小說大家,魯迅和沈從文都對故鄉及當時的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進行了杰出的描繪與反映,不同讀者透過他們的小說了解時代的風云變幻,體察社會發展與變遷下的眾生相,洞悉宇宙人生與人性隱幽,在今天依然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
關鍵詞:魯迅;沈從文;鄉土小說;認識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437(2024)03-0045-06
一、真實性與小說創作
談到文學藝術的認識價值,首先避不開的是如何處理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托爾斯泰有一句話:“寫你的村莊,你就寫了世界”,一個村莊,一方水土,其背后往往折射出來的是大社會。可以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無論其具體內容怎樣,都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反映著社會現實。”[1]
“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文學來源于生活”指向文學的真實性,這是文學認識價值的本源所在,優秀的文學作品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方方面面,倘若文學漂浮于生活之上,或者是對生活歪曲反映,那么也就談不上文學的認識價值。文學的真實性也是文學美感的基礎,真為美之本根,美為真之升華,文學的真實性為作品和讀者搭建了一個有效溝通的橋梁,使不同的讀者在不同時代都可以進入文本,獲得不同的審美體驗,并達到共鳴。同時,文學的真實性也反映出作家的寫作姿態是面向大地,面向蕓蕓眾生的,這是一個優秀作家必備的素質。美國學者勒內·韋勒克與奧斯汀·沃倫在《文學理論》中提到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時說:“處理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的最常見的辦法是把文學作品當作社會文獻,當作社會現實的寫照來研究。某些社會畫面可以從文學中抽取出來,這是毋庸置疑的。”[2]111當然,也不能過于機械地將作品中的事物在現實中都一一坐實,找出它的對應原型,這樣容易陷入死胡同,也曲解了作品本身的意義與韻味,文學藝術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據。“藝術不僅重現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2]110,“實際生活經驗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樣子,取決于它們在文學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藝術傳統和先驗觀念的左右,它們都發生了局部的變形。”[2]80也就是“文學高于生活”,它是作家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一種超越和思考,是以文學的方式介入時代,并對社會生活和人生百態的審視和反思,對人類未來的深層探索,對人性隱幽的剖析和多維度挖掘。
魯迅堅持文學要面向生活,要求文人們要有正視社會現象的勇氣:“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3]255魯迅的一系列創作尤其是他的鄉土小說即是這一要求的杰出體現。同樣,沈從文也強調文學的真實性品格:“一個偉大的作品,總是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4]413“一切作品皆應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偉大作品皆必然貼近血肉人生。”[5]233無論是魯迅筆下的魯鎮、未莊還是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都對舊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思考。因此,要了解二三十年代的苦難中國,了解那個時代人們的愛恨悲歡,就不能繞開魯迅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寫作,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可以了解到近百年來中國鄉村發展的歷史,并在憧憬未來鄉村發展之時有個可貴的立足點。
二、鄉土小說的界定與認識價值
早期關于鄉土小說的論述,最有代表性的為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所指出的:“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6]這段文字透露出三點信息:第一,作者的地域性差異;第二,作品的地方性特色;第三,不盡的鄉愁。茅盾則進一步指出:“關于‘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的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運命的掙扎。”[7]。這里除了指出鄉土小說的地方性風土人情之外,也指出優秀作品對于時代和人類命運的思考。甘肅評論家雷達的看法更為具體:“我認為,所謂鄉土文學指的應該是這樣的作品:一、指描寫農村生活的,而這農村又必定是養育過作家的那一片鄉土的作品。這‘鄉土’應該是作者的家鄉一帶。這就把一般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與鄉土文學作品首先從外部特征上區別開來了。二、作者筆下的這一片鄉土上,必定是有它與其他地域不同的,獨特的社會習尚、風土人情、山川景物之類。三、作者筆下的這片鄉土又是與整個時代、社會緊密地內在聯系著,必有‘與我們共同的對于命運的掙扎’,或者換句話說,包含著豐富廣泛的時代內容。”[8]這里認為鄉土文學的要點有三:一為農村生活;二為地方風物人情;三為時代內容。進入新世紀,丁帆認為:“鄉土小說是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主干,‘鄉土小說’的重要特征就在于‘風俗畫描寫’和‘地方色彩’”[9]1,并說“鄉土小說一定是鄉村、鄉鎮題材的作品,沒有這一前提,鄉土小說便是名存實亡的”[9]25。
可見,鄉土小說的核心要素為:鄉鎮及農村題材,地方性風情習俗,鄉愁,時代與人類命運的映射與思考等,而這些要素同時也是鄉土小說認識價值的根本體現。魯迅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不僅描寫了地方性的客觀之景,亦刻畫了二三年代舊中國特定鄉村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群像,并對當時的時代和個人命運作了深度剖析,呈現出一個有著共同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與信仰的社會共同體。閱讀他們的作品,如楊義所說:“一代又一代會思考的中國人從他的小說中看到了古老的父母之邦的土地、空氣和靈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社會的血脈,探求著歷史的遺跡何在,時代是否前進,從而獲得智慧的啟迪和審美的愉說。”[10]156
三、魯迅與沈從文鄉土小說認識價值的三維審視
鄉村,作為一種物質存在,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社會習俗等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讓他們去愛、去感受、去生活,甚至去承受折磨和苦難,生老病死,代代相傳。無論是魯迅筆下的鄉村世界還是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邊地,他們都以杰出的筆觸展現了一個獨屬于那個時代的政治風云、風土民俗、人情冷暖等。不僅是一種精神文化存在,也是特定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禮儀制度以及信仰的鮮活載體,展現了生活在華夏大地上的鄉村兒女們的精神風貌和情感世界,也表達了魯迅和沈從文對自己所生活過的那片土地深深的依戀與審視。
(一)時代風云的共名與超越
面對一個大的時代轉折,一個優秀的作家不是寫了什么,而是為什么寫、為誰寫、怎么寫,這里就涉及到了作家的價值觀與寫作立場。魯迅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斗而獨立……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11],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直面時代、迎難而上的寫作立場。關于“作家與時代”這個人們時談時新的命題,陳思和教授有一個精彩的概括,即“共名”:“所謂‘共名’是指一種時代的主題,它可以涵蓋一個時代全?族的精神走向。”并說:“一個偉大作家,他是不會回避時代主題的;不僅不回避,他要包容、穿透這個時代主題,使自己的思想超越這個時代的共名”[12]58。
魯迅和沈從文都對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作出了杰出的反映,尤其是魯迅的小說,就一些大事而言,中國的政治風云如辛亥革命、張勛復辟、新文化運動等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出現,并以此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人民的生活面貌,同時又超越自己所處時代的“共名”。以辛亥革命為背景的小說《藥》,寫出了以華老栓為代表的底層人生活的苦難以及骨子里的愚昧、麻木和自私,也寫出了以夏瑜為代表的革命者的大義凜然,然而可悲的是如此視死如歸的英雄,事后卻被淪為了眾人茶余飯后的談資。魯迅以這兩類人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寫他對于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的看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只是一些覺醒者以滿腔熱血去奉獻、流血,是很難使革命走向成功的。另一篇以此為背景的小說《阿Q正傳》,將無業游民阿Q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大背景下,寫以阿Q為代表的底層中國人的苦難以及對革命本身的態度,以此來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以及國人根深蒂固的愚昧、自私、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魯迅以阿Q這樣的小人物來曲折反映時事對于普通人的影響,而不是以一些高官顯貴之人來呈現,更能刺激讀者設身處地去思考,發現自己身上何嘗沒有阿Q的影子。楊義先生說得好:“寫一個慈禧太后尚不足以表達的東?,卻只須寫一個卑微的阿Q,就能夠透視整個?族中無孔不入的病態心理特點了。”[10]165
相對于魯迅以一個戰士的姿態積極介入時代,并對時代的種種問題以文學的形式進行反映與思考。沈從文仿佛是另一種形式,遠遠地逃離時代、躲避現實,沈從文對魯迅有過很高的評價:“對統治者的不妥協態度,對紳士的潑辣態度,以及對社會的冷而無情的譏嘲態度,處處莫不顯示這個人的大膽無畏精神”[5]165,而在談到自己的文學創作時,他卻說:“社會變化既異常劇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卻極其窄狹少變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這個工作越來越落后于社會現實要求,似乎當真變成了一個自辦補習學校中永遠不畢業的留級生。”[5]376那么,沈從文是否只在詩意浪漫的文字中建造著自己的“希臘小廟”呢?答案是否定的。沈從文的這段坦言與其是說自己作品仿佛落后于時代,不如說是一種自謙。沈從文作為作家的黃金時期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此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風云跌宕、內憂外患的時代,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都以各種形式對中國將何處去作了相應的思考。只不過與魯迅不一樣,沈從文從另一方向來思考這個多災多難的古老中國的命運,在看到西方各種思想對人的侵蝕,以及都市男女思想與道德的下滑、人性的扭曲與異化后,他便從民間尋找力量,以健康的人性和蓬勃的自然與生命力來與之抵抗,批判古中國都市化進程的先天性不足。因此,在他的鄉村題材的系列小說中,主人公多大膽地生活,勇敢地愛,自由而無束地舒展生命的力與美。用蘇雪林那句有名的說法就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邁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青起來,好在廿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13]這一獨特的寫作路向,使他從當時的作家群中脫穎而出,站在主流思潮的對立面對時代問題進行反思。
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也并沒有完全回避外面世界的風云變幻。在小說《菜園》中,曾經一個幸福的母親,因兒子和進步青年慘死校場,后半生只能孤苦度日,在這背后是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的白色恐怖,大量屠殺共產黨員的恐怖事實。同樣的背景在小說《新與舊》中也有體現,舊世界正在走向毀滅,新世界還未建立,人們在新與舊的時代夾縫中苦苦掙扎突圍。部分鄉土小說也反映了二三十年代軍閥統治時期底層勞動人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瀕臨破產的嚴峻現實。不可否認的是,沈從文的鄉土小說在觸及一些時事時,盡量采取冷靜描述的角度,很少透露出自己鮮明的政治傾向和情感傾向。他認為:“一個偉大純粹藝術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現實政治家更深刻并無偏見和成見的接觸一切,因此它的產生和存在,有時若與某種思潮表面或相異,或獨立,都極其自然。它的偉大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更形成一種進步意義和永久性。”[14]231沈從文的寫作方式與魯迅的寫作方向盡管不同,但殊途同歸,都體現了對民族前途的深層憂慮,對底層大眾的深情關懷。兩者互相補充,共同構筑了那個時代的民族形象,體現了知識分子可貴的精神擔當。
(二)社會現實的映射與審視
文學作品在社會層面的認識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讀者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體悟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當地的風土民情并感知人物的命運起伏。法國史學家丹納在他的《藝術哲學》中認為,一個作家的寫作主要受種族、時代、環境三種因素的影響,其中他又特別強調地域及風俗對作家的影響作用。魯迅的作品里有許多地方反映了家鄉獨特風俗人情,包括:地方化的動植物和工具——花腳蚊、烏桕樹、芭蕉扇;特有的玩法——狗氣殺、雪地捕鳥;許多風俗——拆灶捐門檻、社戲、迎神賽會;民間故事——“許仙和白娘子”“貓和老鼠”等。沈從文也一樣,其作品多次提到湘西的山山水水、吊腳樓、船夫等、茶峒,“那黃泥的墻,烏黑的瓦”等。其中《邊城》記錄了兩大民俗:端午節的龍舟競渡和走馬路與走車路的說媒方式。一些小說還描寫了湘西鄉村許多年輕男女之間的情愛,尤其是情歌對唱,展現了一種充滿著原始生命活力又不乏浪漫的愛情,這對于處在新時代的年輕讀者,無疑打開了一個新的界面,致使他們重新審視愛情、審視生活本身。而風俗的描寫無不是以作家們的生活為基礎,這對于我們了解那個時代和當時人民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文獻學意義和價值。
然而杰出的作家從不會止步于此,他不僅要在作品中表現出社會是怎樣的,還要揭示為什么是這樣的,即要刻畫出社會的內在肌理與本質。《故鄉》相對于魯迅其他小說,憶舊色彩濃重,小說寫到自己的玩伴少年閏土,腦海里有好多關于“捕魚”“刺猹”“撿貝殼”等稀奇古怪的事,以至于作者在文章中驚訝道:“阿!閏土的心里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 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里高墻上的四角的天空”[3]504。可是如此愛玩會玩的閏土,在作者最后一次回故鄉搬家的時候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手變得又粗又笨像松樹皮,而且見我第一反應便是恭敬地叫了一聲“老爺”。兩組鏡頭,戲劇化的對比,將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承受的苦難與不公鮮活地呈現了出來,正如母親和我的嘆息:“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3]508《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慘遭遇更是將封建舊社會強加在一個女性身上的不公、冷酷及其所承受的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摧殘深刻地表現了出來,揭示了深深壓在舊社會女性身上的“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四大繩索。
沈從文筆下的鄉土世界,不可否認,少了魯迅的犀利、辛辣、嘲諷以及沉甸甸的痛感,但其一些作品亦揭露了統治者的罪惡,書寫了底層人民的苦難。只不過由于沈從文對于湘西這片土地深切的愛與他獨特的寫作追求和審美理想的過濾,使他作品呈現出別樣的詩意和美,但底子確是悲劇的、苦澀的。其以“湘西”為核心的系列鄉土小說不僅謳歌了鄉民們敢愛敢恨、熱烈大膽、奔放果敢的一面,也深刻批判和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敗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麻木自私和不自知。沈從文在小說《丈夫》中著重描寫湘西邊地的一種特殊風俗,年輕婦人通過做肉體生意掙錢養家,“她們從鄉下來,從那些種田挖園的人家,離了鄉村,離了石磨同小牛,離了那年輕而強健的丈夫的懷抱,跟隨了一個熟人,就來到這船上做生意了。”[15]47-48這樣一種不怎么光彩的行為不影響名分和健康,還可以改善自家的生活,以至于“許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來,自己留在家中安分過日子,竟是極其平常的事了。”[15]48使妻成妓,這一典妻與賣淫相結合的勾當,卻是當地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這畸形的生活方式背后,是社會的動蕩不安、生活的不公帶給良善的人們精神和生活的摧殘和壓迫,以至于使他們慢慢適應了這種不光彩的生活而變得麻木順從,而在這背后則是二三十年代多災多難的古老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
(三)人性隱幽的探索與挖掘
一個杰出的作家在寫作時,不是對生活事件的簡單刻畫,而是要寫出時代車輪滾滾向前時對于個體留下了什么。要找出個體在歷史中的位置,以及他的微笑與落寞、苦難與掙扎,這也是文學認識價值的體現,即在作品中要體現對個體的尊重、對生命的思考、對苦難的反思、對人性的審視、對人類終極價值的追求。毫無疑問,鄉土小說主要是將寫作目光聚焦于那一片土地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魯迅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都將“人”作為小說的重點,寫出了一曲曲蕩氣回腸又發人深思的人性悲歌。
魯迅作品始終以“立人”作為寫作核心。所謂欲立先破,如何才能讓一個人真正的“立”住,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就是要正視他、走進他、理解他、挖掘他,甚至解剖他。魯迅的鄉土小說,以普通人的平常悲劇入手,迫使讀者走出自己的舒適圈,進入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他說:“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 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3]3-4
魯迅的鄉土小說里生活著這樣一群人,他們演戲也看戲,生活單調枯燥,卻總是不忘在其中加點料。而由于演戲是將自己置身于一個被“觀”的情境中,多少有點孤單無助,因此魯迅小說描寫更多的是看客,他們總是以群體的形式出現。《祝福》中,人們起初還對祥林嫂有點同情,為她打抱不平,但當她的故事被人們所熟知,并且她總是不厭其煩地向人們傾訴自己悲慘的遭遇,人們便感到厭煩,魯迅捕捉到了這個細節,寫到:“她就只是反復地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眼里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后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16]可見人們對于祥林嫂的看法不是出于同情和熱心,而是生活本身的無聊和單調。魯迅的其他小說如《示眾》《藥》中亦不乏大量的看客形象。錢理群先生甚至認為:“看戲(看別人)和演戲(被別人看)就成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構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17]。盡管程度不同、形象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的點:刻薄狠毒、自私冷漠,且單調無聊、欺軟怕硬,缺乏獨立思考,試圖在群體的行動中獲取安全感的最大狀態,以釋放出平常生活中被壓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在不自覺中竟也扮演了吃人的角色。陳思和指出:“吃人是一種社會環境,人人都有份。這涉及到群眾暴力的問題。”[12]49-50這樣的群眾暴力是古老中國大地上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和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是在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對弱者的隱形傷害。
對于人性的探索,沈從文同樣看到了人性的異化:“惟宗教與金錢,或歸納,或消滅。因此令多數人生活下來都庸俗呆笨,了無趣味。某種人情感或被世務所閹割,淡漠如一僵尸……”[14]32也許是因為他常將自己定位為“鄉下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他執著地構建“希臘小廟”的藝術努力,使他對底層大眾充滿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同情與關心。這一方面使沈從文的人物形象更加舒朗健康,帶給讀者審美的快感,但另一方面也阻礙了他對人物作更深層次的剖析,也因此其小說中的人物少了魯迅筆下的壓抑木訥和無奈沉重。
《邊城》中的翠翠聰明伶俐、單純可人,仿佛是大自然的女兒;老船夫則辛勞本分、善良忠厚,不貪圖便宜,有求必應;船總順順生財有道、正直平和。整個小說的氣氛寧謐自在且詩意浪漫。《蕭蕭》里面的女主人公蕭蕭,可以說是古老中國農村童養媳制度的犧牲品,年僅12歲就嫁給了剛斷奶還不到3歲的幼童做童養媳,生活忙碌卻不繁重,盡管因為沒經得住誘惑做了在當時看來傷風敗俗的事,但她并沒有被夫家及村人逼到絕境甚至死去,最后竟也和丈夫正式拜堂圓房。這讓我們不得不想起蕭紅筆下的小團圓媳婦,同樣為童養媳,一個被殘忍對待以致死亡,一個則在經歷了一系列波折后重新過上了平靜的生活。在蕭紅的筆下,我們看到的是人性的冷漠、無知、愚昧和殘忍。而在沈從文這里,我們看到了人性閃光的一面:溫暖、良善、友愛、純樸,人性的美稀釋了主人公坎坷命運,溫情的人際關系淡化了封建舊制度對人的禁錮。至于其他人物形象,夭夭、三三、貴生、龍朱、水手等,女性多善良溫柔、柔情似水、敢愛敢恨;男性則堅韌頑強、果敢有力;甚至妓女也充滿了人情味;土匪并非無惡不作、殺人放火,相反他們殺富濟貧,仗義疏財。盡管沈從文筆下人物也有缺點和不足,但整個人性的底色是飽滿的。
相比較而言,沈從文筆下的人物要比魯迅筆下的人物更健康、充滿活力,更具有人性和血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沈從文筆下人物的生存環境要比魯迅筆下人物的生存環境更開放,那種來自自然本身的原始之力較為濃郁;二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圍,湘西邊地百姓所受的傳統文化觀念和封建禮教的程度要遠遠低于魯迅筆下生活在魯鎮的人們;三是作者的寫作立場不一樣。魯迅以筆作匕首,剖開人性的縱深,寫出了人物的靈魂。沈從文則是從倫理道德和審美的角度,在湘西這塊土地上找尋現代文明中即將失落的理想人性,以近乎原始主義的書寫姿勢構建他的“希臘小廟”。張新穎先生說得好:“沈從文是在一個比人大的世界里說人性的,和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性論的人性不同,和我們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說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著與人居其間的天地運行相通的信息。”[18]魯迅以批判的眼光看到了人性幽暗且懦弱的一面,而沈從文則以詩意的筆調謳歌健全的人性。
兩種不同的人性呈現,帶給讀者不同的審美體驗。令人嘆惋的是,一百多年過去了,魯迅筆下的人物形象在今天并沒有改變多少,而是在時代的發展中包裝成了新的“看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重新走進魯迅的鄉土系列小說,去感受其中人物的愛恨與悲歡,并從中去思考社會的本質和人性的本來面目。而當我們面對眼花繚亂的世界和各種利益誘惑,盤算著各種利害關系與得失時,對比沈從文筆下的人物,也許可以審視自己獲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從而進一步認識自己以及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本身。
四、結語
魯迅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真實地展現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古老中國面對時代的風云變幻所作出的艱難努力,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中華兒女們的掙扎與守望、疲弱與健全,并以其杰出的筆調刻畫出不同的生命情狀和人的精神世界。作家筆下的那一方鄉土,作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縮影,以其獨特的樣貌,傳達出處于時代大變革時期的作家對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的反思、對國家和個體命運的深層憂慮,不僅深刻地影響以后的文學創作,更啟發著不同時代的讀者以此為鏡,反觀自身,認識人自身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
參考文獻:
[1]狄其驄,王汶成,凌晨光.文藝學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6.
[2]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3]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413.
[5]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6]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55.
[7]茅盾.茅盾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241.
[8]雷達,劉紹棠.關于鄉土文學的通信[J].鴨綠江,1982 (1):69-74.
[9]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
[10]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1]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52.
[12]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3]蘇雪林.蘇雪林選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9:456.
[14]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15]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16]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7-18.
[17]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8.
[18]張新穎.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