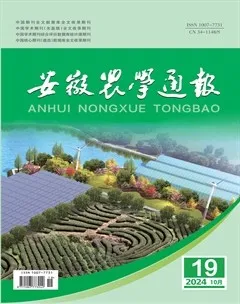致災暴雨對農業生產影響的脆弱性分析






摘要 基于青海省2018—2022年氣象資料、暴雨洪澇災情資料及逐年經濟數據,采用相關分析、曲線擬合等方法分析致災暴雨對農業生產影響的脆弱性程度。結果表明,研究區致災暴雨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范圍主要集中在青海東部及海西州東部,近5年(2018—2022年)來,以2022年出現災情最多,8月出現頻率最高,降水持續時間大多不超過1 d;6 h、12 h及日最大降水量是造成該地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的主要降水致災因子,在抗災能力保持一致時,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隨著降水量的增大呈逐漸增加的趨勢。由于單一要素的脆弱性曲線誤差較大,選擇構建多要素的農作物暴雨災害脆弱性曲線: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0.020×12 h最大降水量-0.146×降水持續日數+0.585。該曲線可為未來暴雨洪澇對農業生產的致災性預估提供參考。
關鍵詞 農作物損失;暴雨;脆弱性曲線;氣象災害
中圖分類號 S1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24)19-0106-05
DOI號 10.16377/j.cnki.issn1007-7731.2024.19.022
Vulnerabilit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isaster causing rainstorm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AO Qianhong ZHAO Minglu QI Caihong
(Qinghai Provinci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Xining 81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rainstorm and flood disaster data and annual economic data of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18 to 2022, the vulnerability of disaster causing rainstorm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analyzed by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curve fitting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disaster causing rainstorm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tudy area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Qinghai and the Eastern part of Haixi Prefecture. In recent five years (2018 to 2022), the most disasters occurred in 2022, the highest frequency occurred in August, and the duration of precipitation mostly not exceed 1 day; 6 h, 12 h and daily maximum precipitation were the main precipitation disaster causing factors that cause economic losses per unit area of crop rainstorm disasters in this area. When the disaster resistance capacity was consistent, the economic losses per unit area of crop rainstorm disasters gradually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cipitation. Due to the large error of the vulnerability curve of a single element, a multi element vulnerability curve of crop rainstorm disaster was selected: economic loss per unit area of crop rainstorm disaster=0.020 × 12 h maximum precipitation -0.146 × precipitation duration days+0.585. The curve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isaster prediction of rainstorm and floo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rop losses; rainstorm; vulnerability curv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近年來,氣候較為復雜多變,極端天氣日益增多,各地氣象災害發生較頻繁,災害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呈上升趨勢。楊昭明等[1]研究指出,減輕氣象災害造成的影響和損失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受地理位置和水汽輸送等因素影響,青海對流性天氣發生概率較高,而暴雨洪澇及其引發的次生災害是該地汛期主要的影響較為嚴重的一種氣象災害[2]。伏洋等[3]研究認為,該地地形復雜、山大溝深且植被覆蓋率較低,受植被及下墊面土壤特征的影響,強降水可能會匯集成山洪,嚴重時會發生泥石流及滑坡等地質災害,進而造成房屋倒塌、農田淹沒,公路和水利設施沖毀等。因此,對于氣象災害的影響研究尤為重要。周成虎等[4]和張婷等[5]研究認為,洪澇災害是由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其中,降雨在致災因子中是較為常見且較具威脅性的因子之一,持續的暴雨是洪澇災害的主導因素之一。關于暴雨災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致災指標、風險評估模型和區劃方法等方面,Li等[6]以暴雨災害發生頻率作為致災指標進行風險評價研究,該方法能描述單一災害的發生,暫不能高效評估災害發生的危險程度。于飛等[7]和陳曉紅等[8]研究認為,災情大小由致災因子、孕災環境和承災體脆弱性共同決定;張安凝知等[9]研究認為,脆弱性是聯系致災因子和承災體的重要橋梁,也是研究暴雨洪澇災損估算和風險評估的重要基礎之一。喻婷婷等[10]研究認為,災情指標的趨勢變化與日益增強的防災減災能力密切相關,構建脆弱性曲線可為洪澇災害災情評估與防災規劃的制定提供參考。
本文依據研究區暴雨災害實況資料及相關經濟統計數據,對致災暴雨對農業生產方面的脆弱性進行分析。可為暴雨洪澇災害防御及建立暴雨洪澇對農業生產的風險影響評估模型提供一定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基本情況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地勢西高東低,境內地形復雜,山大溝深,夏季多出現歷時短、強度大的局地性降水[11]。暴雨洪澇是近年來研究區各類氣象災害中發生頻率較高、影響較嚴重的災害之一,特別是對于農業生產方面造成的影響較為明顯,尤其是2022年汛期多地降水超歷史同期,暴雨洪澇災害頻發,僅農業生產方面的暴雨洪澇災情有近40例,超過2021年全年暴雨洪澇災情總和,造成的農業經濟損失較高。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研究數據來源于青海省2018—2022年氣象資料、暴雨洪澇災情資料及逐年經濟數據。氣象資料包括青海省臺站逐小時降水量及降水時間、日數等,來源于青海省氣象臺;暴雨洪澇災情數據包括受災地區、起止時間、農作物受災面積和農作物經濟損失等,來源于中國氣象局氣象災害管理系統;經濟數據包括青海省逐年農業總產值等,來源于青海省統計局。
通過SPSS 27.0.1.0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統計學檢驗和回歸擬合分析等,構建最優脆弱性曲線模型。
1.3 研究方法
1.3.1 農業暴雨災害時空分布特征 基于2018—2022年青海省氣象觀測數據及暴雨洪澇災情數據,篩選農作物暴雨致災個例,共86例。由于研究區南部的農作物種植面積少,農業災情少且地形及氣候條件差異較大,容易對結果產生影響,因此選擇青海東部及海西州東部地區作為研究范圍,對農作物暴雨致災個例的時間和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
1.3.2 農作物損失數據校正 不同年份的經濟水平以及農作物種植數量存在差異,利用校正系數篩選個例農業災情損失并逐一進行校正。采用逐年農業生產總值對所選個例的農作物暴雨災害損失進行物價水平校正,以2021年經濟水平為準,對2018—2021年農作物暴雨災情數據進行年代校正,得到校正后的農業經濟損失(L)及校正系數。其計算如式(1)。校正后利用2022年災情資料進行檢驗。
L=P_i/P_2021 ×L_i (1)
式(1)中,L為校正后農業經濟損失,萬元;Pi為第i年的農業產值,萬元;P2021為2021年農業產值,萬元;Li為第i年經濟損失,萬元。
1.3.3 主要降水致災因子選擇 將災情個例過程期間最大降水量、日最大降水量、1 h最大降水量、3 h最大降水量、6 h最大降水量、12 h最大降水量和持續日數等致災因子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進行相關性分析,通過描述各個變量間的相關程度,確定主要降水致災因子。
1.3.4 脆弱性曲線構建 脆弱性是指承災體暴露于災害而可能遭受損害的程度[12],通常可用致災與成害之間的關系曲線表示,又稱脆弱性曲線或災損曲線[13]。選擇降水致災因子作為自變量,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作為因變量,利用曲線擬合方法,尋找降水致災因子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之間的近似函數關系,通過構建連續不間斷的曲線近似地代替坐標上離散點之間的函數關系,得到脆弱性曲線方程,最終構建單一變量的承災體脆弱性曲線和多要素的承災體脆弱性曲線。
2 結果與分析
2.1 農業暴雨災害時空分布特征
2.1.1 時間分布特征 從年際變化看,2018—2022年,研究區農業受暴雨災害的情況分為兩個階段,即2018—2020年逐年下降,2020年后逐漸增長。其中,2022年出現災情次數最多,這與2022年8月多次強降水天氣過程有直接關系(圖1A)。從月際變化看,5—9月均有災情出現,其中8月出現最多,為52例;7月次之,為21例;5月最少,僅有1例(圖1B);7—8月出現的災情次數占總次數的84.8%,與暴雨的年內分布規律相吻合。從降水持續時間看,56%的個例持續1 d,27%的個例持續2 d,17%的個例持續2 d以上。從出現時間看,80%以上的個例農作物暴雨災害出現時間均在午后至前半夜,以對流性降水為主。
2.1.2 空間分布特征 從空間分布來看,受地形、地貌影響,農作物受暴雨災害的影響區域比較集中,主要分布在青海東部及海西州東部地區,省內各市州中海南州和海東市農作物受暴雨災害影響較為嚴重,各縣(區)內興海縣和湟中區在2018—2022年農作物受暴雨災害的頻次最高,均出現10例災情;貴南縣次之,為9例。
2.2 農作物損失數據校正
為增強數據可比較性,統一采用校正后的農業經濟損失數據進行分析。2018—2021年逐年的校正系數分別為0.83、0.89、0.92和1.00,農業經濟損失乘以每年的校正系數,即為2018—2021年農作物在同一脆弱性水平下的校正后農業經濟損失,分別為10 193.740、10 843.938、3 884.355和817.760萬元(表1)。校正后的農業經濟損失略低于災情資料數據。
2.3 主要降水致災因子選擇
在承災體均為農作物、抗災能力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與3 h最大降水量、6 h最大降水量、12 h最大降水量、日最大降水量和過程最大降水量均呈正相關(表2),其相關系數依次為0.329、0.521、0.700、0.656和0.336,其中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通過P=0.01統計學檢驗。由于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的相關性較強,因此,選擇其作為造成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的3個主要降水致災因子。
2.4 脆弱性曲線構建
2.4.1 單一變量的承災體脆弱性曲線 從6 h最大降水量、12 h最大降水量和日最大降水量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間的散點分布(圖2)可以看出,經濟損失與單個降水量間的關系呈現明顯的非線性關系。將以上3種主要降水致災因子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進行多種擬合,選擇擬合效果最好的指數函數,構建兩者間的脆弱性曲線。可以看出,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與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間脆弱性曲線的R2分別為0.306、0.414和0.378,且3個曲線模型均通過統計學差異性檢驗(P<0.05)。為判斷擬合效果的合理性,對3個脆弱性曲線模型擬合程度進行評估,基于擬合誤差和殘差平方和的比例計算,得出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與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間擬合曲線的F值分別為20.736、33.239和28.534。對比可知,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與12 h最大降水量間曲線模型的R2更接近1,F值最大,為最優擬合脆弱性曲線。脆弱性曲線表明,在抗災能力保持一致時,農業損失與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間均呈正相關,即隨著降水量的增加,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呈逐漸增大的趨勢。
利用2022年的暴雨災情資料對構建的脆弱性曲線方程進行檢驗。將2022年暴雨災情降水觀測數據代入脆弱性曲線方程,對比實際經濟損失和預估經濟損失,結果表明,60%以上個例的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預估損失誤差率分別在2.6%~113.7%、0.4%~70.2%和4.5%~77.2%,其中,12 h最大降水量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間的脆弱性曲線方程檢驗效果最好,但誤差較大。
2.4.2 多要素的承災體脆弱性曲線構建 尋找單一的降水致災因子與災害損失間的關系不夠全面且誤差較大,因此,需建立多個降水致災因子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損失間的脆弱性曲線。利用多元回歸線性模型,根據不同的降水致災因子變量組合,通過多次擬合試驗,最終篩選出12 h最大降水量、過程最大降水量和降水持續日數的變量組合,并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進行擬合,構建多要素的承災體脆弱性曲線。由表3可知,各降水致災因子的VIF<5,因此,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由模型的F檢驗可知,其通過統計學檢驗(P<0.05),表明致災因子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損失存在線性相關關系,模型中過程最大降水量的t檢驗P>0.05,說明其對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損失未產生明顯影響,因此在模型中剔除。12 h最大降水量和降水持續日數的t檢驗P<0.05,在模型中具有明顯線性關系。依據表3數據,得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式(2)。
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0.020×12 h最大降水量-0.146×降水持續日數+0.585 (2)
3 結論與討論
致災因子與災情損失的關系判斷是災害風險評估的重要一環。本文利用2018—2022年氣象資料、暴雨洪澇災情資料及逐年經濟數據,采用相關分析、曲線擬合等方法,對農業暴雨災害分布特征、主要致災因子選取以及致災因子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1)2018—2022年青海省農業暴雨災害共86例,影響范圍主要集中在東部及海西州東部地區,其中興海縣和湟中區出現頻次最高,貴南縣次之。(2)2022年研究區農業暴雨災害出現次數最多,2020年最少;災情主要集中在7—8月,8月出現最多;56%的個例持續1 d,27%的個例持續2 d,持續2 d以上個例占比較低;80%以上的個例暴雨災害出現時間均在午后至前半夜。(3)6 h、12 h和日最大降水量是造成2018—2021年研究區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的主要致災因子,其中12 h最大降水量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的相關性最強。(4)12 h最大降水量與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的曲線擬合效果在3種主要致災因子中表現最好。脆弱性曲線表明,在抗災能力保持一致時,農作物單位面積經濟損失與主要致災因子間均呈明顯正相關。(5)由于單一變量的脆弱性曲線誤差較大,因此通過致災因子分組擬合構建多要素的農作物暴雨災害脆弱性曲線:農作物暴雨災害單位面積經濟損失=0.020×12 h最大降水量-0.146×降水持續日數+0.585。脆弱性曲線可為未來暴雨洪澇對農業生產的致災性預估提供一定參考。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擬合模型的變量因子考慮較少,基礎樣本數據不充足,未來將進一步補充災情數據,考慮更多的致災因子,建立可信度更高的預估模型。
參考文獻
[1] 楊昭明,李萬志,馮曉莉,等. 氣候變暖背景下青海汛期暴雨洪澇及次生災害風險評估[J]. 中國農學通報,2019,35(3):131-138.
[2] 《青海自然災害》編纂委員會. 青海自然災害[M]. 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伏洋,李鳳霞,郭廣,等. 青海省自然災害災情與特征分析[J]. 高原地震,2004,16(4):59-67.
[4] 周成虎,萬慶,黃詩峰,等. 基于GIS的洪水災害風險區劃研究[J]. 地理學報,2000,55(1):15-24.
[5] 張婷,李怡,李建柱,等. 多源降雨數據融合及其水文應用研究進展[J]. 自然災害學報,2022,31(1):15-28.
[6] LI S J,YUAN J,XIAO Q H,et al.Characteristics of drought and humidification based on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in Weifang City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J]. Agricultur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2,13(4):861-866.
[7] 于飛,谷曉平,袁淑杰. 貴州省農業氣象災害致災因子的風險區劃[J]. 貴州農業科學,2016,44(4):138-141.
[8] 陳曉紅,萬魯河.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的脆弱性與協調性作用機制研究[J]. 地理科學,2013,33(12):1450-1457.
[9] 張安凝知,趙鐵松,陳霞,等. 河北省農作物暴雨洪澇災害的脆弱性評價[J]. 貴州農業科學,2018,46(5):143-146.
[10] 喻婷婷,萬金紅,高路. 福建省暴雨時空演變規律與洪澇災害脆弱性曲線研究[J]. 水利水電技術(中英文),2023,54(12):64-74.
[11] 王江山. 青海天氣氣候[M]. 北京:氣象出版社,2004.
[12] 李鶴,張平宇. 全球變化背景下脆弱性研究進展與應用展望[J]. 地理科學進展,2011,30(7):920-929.
[13] 周瑤,王靜愛. 自然災害脆弱性曲線研究進展[J]. 地球科學進展,2012,27(4):435-442.
(責任編輯:楊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