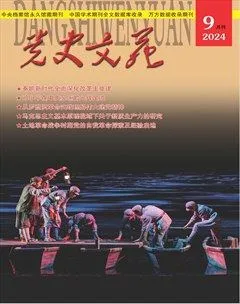馬克思人類解放思想及其現代性思考
為人類求解放是馬克思一生的價值追求和思想主題。馬克思人類解放思想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展現出了恒久的生命力、解釋力和創造力。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中,馬克思對德國社會宗教產生的現實根源、德國社會舊制度的缺陷及政治解放的不徹底性進行分析,進而從政治解放過渡到人的解放,探尋出一條真正實現人類解放的現實路徑。
一、人的解放的起始環節:從宗教批判到回歸“現實的人本身”
在《導言》中,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宗教產生及存在的現實根源。宗教作為一種統治工具,通過信仰的方式將現實世界的苦難描繪為對人類原罪的懲罰,并將人類苦難的拯救寄托在來世、彼岸之上,由此使廣大民眾接受了苦難的現實。因而宗教可以說是為維護現有統治秩序對廣大民眾進行的一場思想控制,使民眾精神上得以自我麻痹,繼而放棄反抗。馬克思一方面強調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另一方面以此為前提,將人的本質的異化問題還原為具體的社會現實問題。
宗教批判是人意識覺醒的重要前提。在《導言》中,馬克思用大量筆墨批判宗教,宗教自詡是締造人類的天神,這種說法是對現實的人、國家、社會真實關系的遮蓋。事實則與宗教描述的完全相反,正是由于“人”的產生,通過制作和使用工具使得生產力不斷發展,出現了國家和社會,繼而有了宗教,因此,宗教是一種顛倒的思維錯亂的世界觀。“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導言》中的這段描述表明了宗教本身具有欺騙性和虛幻性,它空有華麗的外表卻缺乏實質的內容。事實上,現實與宗教密不可分。當人們遭受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和痛苦時,他們往往求助于宗教來求得安慰和慰藉。宗教的興起導致人們無法直面自己的內心深處,而只能依賴宗教獲取短暫的精神安慰。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并不只是單純地對人們所信仰的意識上的宗教進行批判,一場殘酷現實的社會革命才是宗教批判道路上的終點。
費爾巴哈對宗教的批判為馬克思探索人的社會性提供了前提條件。在費爾巴哈的視野里,宗教就是人把自己的“類”本質對象化的結果。這種對象化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所謂的上帝或神不過是人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和人格化并加以崇拜的結果。所謂神靈,不過是以虛幻和異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的本質而已。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費爾巴哈“把宗24027d1230f0ac0cb13efedf26e749143787c83d7289a2d0630b78e0ff69ee36教本質歸結為人的本質”的理論貢獻,另一方面以此為基石,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強調現實中的人是進行一切批判的前提。馬克思通過批判宗教試圖使社會中的人意識到自己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現實壓迫,從而對所遭受的屈辱進行堅決斗爭和反抗,從而為自己謀求真正幸福。
二、人的解放的中間環節:對德國現存制度和國家哲學的批判
資產階級批判宗教,只是批判和自己相對立的宗教,不會給人民帶來現實的幸福。而馬克思反復強調批判宗教的目的是用人民現實的幸福取代虛幻的幸福。這是馬克思同資產階級思想家在批判宗教問題上的根本區別。可以說,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是對現實世界批判的前提。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以德國現實制度為出發點,對指導德國和英法等現代國家發展的相關哲學進行反思,并站在人類解放的視角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實現人類解放的科學性和徹底性。
當時的德國尚未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政治較為落后,與之相對應的生產力也相對滯后。這種情況下,舊體制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因此必須及時摒棄并建立新體制以推動德國社會的發展。德國在當時推行聯邦制,聯邦會議僅僅擁有名義上的最高權力,事實上各個州推行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用以謀取各自的利益。“奧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主要締造者梅特涅作為歐洲封建勢力的代表,掌控著處理德意志重大事務的權力”,這種現實情況嚴重阻礙著德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
如馬克思所言,當舊制度仍認為自身是合理的,下場必然是悲劇的,這會阻礙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德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盲目推崇英法落后的體制,并將其視為現代化的典范。馬克思承認黑格爾在德國國家哲學和法哲學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貢獻,但他進行了進一步反思,他極具前瞻性地看到了政治解放的不足之處,以及現代國家即將面對的一系列嚴峻挑戰,盡管當時德國還沒有達到現代國家的水平。因此,對德國的現存制度作出批判迫在眉睫,從而揭露德國制度使人受盡剝削和奴役,使得人的自由被埋葬的內容,從否定德國腐朽制度開始批判社會現實是德國人獲得解放的必要環節。
由此可見,盡管德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水平相對于現代國家而言是落后的,但德國的國家哲學卻展現出了一定的先進性。德國國家哲學存在的缺陷恰恰是現代國家普遍存在的缺陷——忽視了“現實的人”。以往的哲學是抽象的,未能觸及現實世界,無法實現人類的真正解放。馬克思反復強調,真正的哲學應該直面現實,充分關注處于市民社會中人的真正需求,致力于人的解放的實現。
三、人的解放的實現:無產階級與哲學的同一
在《導言》中,馬克思將現實哲學用以指導德國解放的具體實踐,強調要將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相結合,闡述了無產階級領導德國革命實現人類解放的實踐途徑。其中,無產階級是實現人的解放的“心臟”,哲學是“頭腦”,革命的成功需要堅決徹底的實踐,也需要科學的哲學理論加以指導。
(一)實現人的解放的“心臟”:無產階級
馬克思并不是全盤否定資本主義,而是辯證地論述資本主義所作的貢獻及其致命缺陷。資本固然具有特定“關系”所體現的殘暴、剝削和破壞性,但其本身也肩負歷史使命,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產生積極作用的方面。總的來說,資本是依靠剝削工人創造剩余價值的價值,是一種在物的掩蓋下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否定資產階級以后,馬克思注意到一個新生的階級,他們“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馬克思在《導言》中對無產階級進行了生動描述,指出無產階級面臨無法回避的貧困和痛苦,在飽受壓迫后必然會產生變革的意識,燃起最徹底的革命激情,反對現有階級的統治,在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時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正是基于對無產階級本質的深刻洞察,馬克思闡明了無產階級特有的斗爭精神和革命性質,將無產階級置于人類解放的核心地位。
(二)實現人的解放的“頭腦”:哲學
哲學是研究人的解放的科學,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精神動力和理論武器。革命需要理論指導,理論只有充分把握事物的本質、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行之有效地指導革命。馬克思堅決反對將理論和實踐、哲學和革命割裂對待。無論是完全否認哲學理論,企圖通過直接的行動來改變和創造現實的純粹實踐主義者,還是認為目前的斗爭只是哲學同德國這個世界的批判斗爭,只在哲學理論中的變革就足以改變世界的理論主義者。他們看不到現存的哲學就屬于這個世界,是隨這個世界而產生的哲學,導致他們認為不消滅哲學本身,就足以讓哲學變為現實。而無產階級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須擁有兼具革命性、實踐性和科學性的哲學理論的指導。無產階級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用這一先進理論逐步武裝群眾,使之成為群眾手中的武器,進而實現人類的解放。
(三)實現人的解放:“心臟”和“頭腦”的結合
“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在實現人的解放的過程中,頭腦是哲學,心臟是無產階級。實現人的解放只有在將作為精神力量的哲學和作為物質力量的無產階級結合起來的前提下才能順利進行。因此,必須將科學的理論用以指導無產階級的具體實踐活動及相關革命運動,人的自由聯合體的實現才得以可能。總的來說,理論只有為群眾掌握,才能催生一定的物質力量,為現實的實現提供可能性。同時,無產階級只有把哲學作為精神武器,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四、基于《導言》的現代性思考
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依靠資本驅動、凸顯自由市場作用實現現代化。工業革命后資本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推進現代化的第一驅動要素,技術革新也是由資本在背后驅動,資本成為現代化的最大推手。與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主張走一條全領域、全方位發展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依靠全體人民獨立自主、銳意進取、艱苦奮斗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導向,而人的全面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建設的主要動力。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有關人的解放思想的實踐體現,創造了嶄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雖然也需要通過生產不斷滿足個體需求,促進個體內部、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交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條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的發展道路,是一條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發展道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推動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盡最大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需要,這是當前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生動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升,人民群眾更為充分、平等地占有和享有生存發展的條件、機會,有效地促進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在長期的奮斗歷程中,我們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逐步推進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這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偉大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方式實現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總之,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場關于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思想的生動實踐,開創了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孫凱.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批判性的雙重向度及當代啟示[J].理論與現代化,2017(2):68.
[3]張夢想.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基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視角[J].西部學刊,2023(07),36-39.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
[5]習近平.論黨的自我革命[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23.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陳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