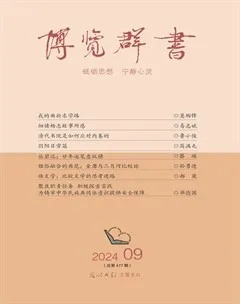清代書院是如何應對內卷的

所謂內卷,簡言之,就是過度的競爭造成了無謂的消耗。古代書院士子的內卷,主要來自科舉考試的壓力,正所謂“書院與科舉是一對難兄難弟”。清代戴鈞衡《桐鄉書院四議》有言:“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為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本來,多大歲數應考、進學,乃至中舉人、成進士,并無明確規定,早一些晚一些皆可。然而,過度競爭的結果,就是大家趨向越早越好,晚了就容易焦慮。由此可以理解,48歲的老秀才蒲松齡寫《責白髭文》,慨嘆“蹉跎歲月,四十無聞,人脫白纻,子尚青衿”,實有種“卷不動了”的無奈。在“高度篩選型”的科舉時代,內卷必然是一種常態。
內卷的產生,一在生存焦慮,二在發展焦慮。士子如果不必經常為生計發愁,也不用過分為出路擔憂,內卷的程度當會有所減輕。在內卷化最為嚴重的清代,書院做了不少努力,旨在緩解士子的生存焦慮和發展焦慮。
書院的膏火助學制度,為寒士提供了生存保障
清代以前,書院有給士子提供經濟資助的,但不是普遍現象。將膏火獎賞與考課制度捆綁,且具有普惠性質的,是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晚清尤甚。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的統計數據顯示,清代書院經費當中,開支數額最大的就是膏火費。
發放膏火費的對象、數額,各書院不盡一致。有按人頭定額發放的,如海州敦善書院,先是定膏火二十名,不分生童,每人按月給銀九錢。道光十七年定為正課二十名,副課二十名。正課生員每月一兩二錢,副課一兩;正課童生每月一兩,副課八錢。(《敦善書院條規》)也有按成績分等發放的,如光緒間黔江墨香書院每年四季大課,每課取生員超等八名,每人膏火錢一千二百文;特等八名,每人八百文。童生上取十名,每人一千文;中取十四名,每人六百文。(《墨香書院規條》)還有專門針對貧困士子的加課,如湖州愛山書院,道光間定貧生額數,給予膏火錢。其超等、特等之別,是按極貧、次貧來區分的。同治間增加額數,并改為“評文以定等次,每月隨課升降,庶于優待寒素之中,仍寓造就人才之意”。(《愛山書院加課貧生課程》)除了膏火費外,花紅、賓興費等也是書院資助士子的名目。
以膏火為主體的助學制度,給寒士提供了切實的生活保障。例如,王樹枏“家寒儉”,入學以后,“歲應府縣書院月課,始稍得膏火獎賞”,藉供家中日用之需。(《陶廬老人自訂年譜》)陳衍“家極貧”,遂“廣應各書院詩賦課作,月得獎賞數金津貼家用”。(陳聲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周鳴春“赴杭應課,課輒冠曹。每一藝出,士子哄傳遍抄,城垣紙為之貴,而一家十馀口即藉是以為活”。(光緒《富陽縣志》)沈恩孚“家貧,倚書院膏火以自給,試輒首列,故每年積有余資”。(蔣維喬《沈信卿先生傳》)王錫彤應衛輝淇泉書院月課,“每月輒獲獎錢數千”。又考取開封大梁書院,“月支膏火銀一兩五錢,足為飲食之需。每月再得獎金,仍可寄家為養”。(《抑齋自述》)柳詒徵每月參加揚州、鎮江的官師課凡七次,“師課膏火少,官課較優,常鎮道、兩淮運司主之者尤優,額定膏火外,前十名皆有花紅銀一、二、三兩不等。試或不利,卷僅文數百文”,“均計之,年亦得百數十千,視館谷為優,第升黜不恒,不能視為固定收入也”。(《記早年事》)此類事例甚多。龔自珍的著名詩句“著書都為稻糧謀”,雖含批評之意,但也反映了清代讀書人經濟窘迫的普遍現實。而書院的膏火獎賞,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士子的經濟壓力。畢竟,就算考取不了功名,考書院也不失為一條生路,“窮儒恃此為活者固大有人也”(殷葆諴《追憶錄》)。
“成圣賢”“做好人”的目標定位,有利于緩解發展焦慮
保障了基本的生存需求,接下來的主要問題就是發展需求。書院師長普遍認為,發展焦慮緣于讀書人的短視。河南學政張潤民《南陽書院學規序》有言:“古之學者以道,今之學者以文;古之學者身心性命,今之學者功名富貴。”霍州知州李培謙《示霍山書院諸生》也講道:“師之所講、弟子所習,不過沾沾于文字之間”,最終目的只是“希冀主司一日之收錄,其于身心性命固未嘗一計及之也”。盯著功名富貴,只重眼前利益,結果只能是越來越卷。何也?功名富貴總共就那么多,所有人都往獨木橋上擠,焉能不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書院師長為士子設計了一條不那么“擁擠”的道路。“今學者開口便云讀書,到底讀書將為甚事?此處宜自猛省。”這是臺灣道兼學政覺羅四明《海東書院學規》中的發問,頗有“棒喝”的味道。讀書到底為何?此問不僅關乎教育的初心,也關乎現實的困境。
覺羅四明給出的答案是“成圣賢”:“人既自拔于流俗,將以圣賢為必可為。”這不是一家之言,而是書院的普遍共識。以乾隆間江西書院為例,南昌《友教書院規條》:“士人當志在圣賢,力求仁義,上通性命,內治身心。”南安《道源書院條約》:“今諸生當志圣賢之德業,以自勵其行能;當志圣賢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書院條約》:“愿諸生當下立志,決以圣賢為可求。”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期許,以制度的形式落實進了書院教育當中。這關乎教育的初心。
同時,“成圣賢”的目標定位,也關乎現實的困境。福州鰲峰書院山長蔡世遠針對有人對“成圣賢”有懷疑、畏懼之心,做了這樣的推理:“求富者未必得富,而人求之;求貴者未必得貴,而人求之;求為圣賢者,取諸其身而已足,而何不能,何不敢乎?”(《鰲峰書院學約》)蔡世遠的本意在鼓舞士氣,言語間也透露了一個事實:功名富貴名額有限,爭奪激烈;而圣賢人皆可為,無需競爭。因此,以“成圣賢”為目標,不存在內卷的問題。而且,“專攻舉業而不得,則必至兩失。專志圣賢而不得,猶不失我之真面。”(李棠階《勸士條約》)“縱不能即幾于圣賢,亦不失為端人正士。”(彭家屏《道源書院條約》)追求“成圣賢”,其風險很小。
也有士子覺得,雖說人皆可以為圣賢,但這個目標畢竟有些高遠。那好,還有一個比較平易的目標,就是“做好人”。南宋朱熹對建陽滄洲精舍生徒講:“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又諭學者》)明代馮從吾在西安寶慶寺(關中書院前身)講學,總結所講要義為:“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諭俗》)以“做好人”為教育目標,更接地氣,也更不容易制造焦慮,因而為清代書院普遍接受。畢竟,“好人”沒有名額限制。人皆可以為好人,這一點更易被認同。
引導士子讀書,助力科名需求,是正面應對內卷的良方
以“成圣賢”“做好人”相期,固然有利于緩解焦慮,但關鍵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圣賢”“好人”宜作為人生的遠期目標,對于絕大多數士子來說,近期目標仍是科舉功名。若能提供通向科名的“秘鑰”,讓士子“卷”出來,才是正面應對內卷的良方。在這方面,書院確有“秘鑰”,那就是——讀書破萬“卷”。
書院本以讀書為主業,讀書何以成為“秘鑰”?這是因為,很多士子只讀應試之書,這不能算真正的讀“書”。北宋蘇軾曾感嘆:“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李氏山房藏書記》)到了清代,這個問題更為普遍。任丘桂巖書院山長邊連寶提道:“近世習舉子業者,把黃邊老墨作半世夫妻廝守,除四書本經而外,一切線裝書俱束而不觀,置之高閣,抱殘守獨,孤陋寡聞。”(《桂巖書院學約八則》)還有更為討巧的,連“四書本經”也甚少注目,全副精力都在《大題文府》《小題正鵠》《試律大成》《四書人物典林》這類“教輔資料”上。在一些士子的認知中,考點“但須索之《五經類編》《四書備考》等書,已足給求,何事重勞搜剔”(章學誠《清漳書院留別條訓》)?問題在于,只讀“教輔資料”,收獲的只能是碎片化的知識;不讀原典,所謂內卷,“卷”的也只是知識碎片。
事實上,走討巧的“捷徑”,是很難“卷”出來的。福州鰲峰書院山長陳壽祺說:“五十年前,墨卷盛行。舉子胸累千篇時文,而卒困于場屋者,不可勝數;其能研究經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為時命所厄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鰲峰崇正講堂規約八則》)鞏秦階道道員姚協贊也對秦州隴南書院生徒講:“根底不深,發而為文亦膚淺而無足觀,其幸取科第者十之一,不能幸得者十之九。”(《諭隴南書院諸生示》)這些都是經驗之談。正因為此,有書院明確規定:“坊間所售石印《大》《小題文府》諸書,最是誤人才智,蔽塞性靈。諸生來院,慎勿攜帶此書,誤人自誤。”(高淳《尊經書院學規》)而能夠“卷”出來的,主要靠的還是博雅閎通。書院鼓勵士子回到原典,“便欲作時文,亦須胸中有一部芝麻通鑒”(邊連寶《桂巖書院學約八則》),“時文雖科舉之學,然非多讀古書不能詣極”(陸耀《任城書院訓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這些博習經史詞章的書院,科舉成績往往不俗。據李兵《書院與科舉關系研究》的研究,兩書院的鄉試錄取率都達到了20%,其生徒“是科舉考試有力的競爭者,占據了當地科舉及第的大部分名額”。可見唯有真讀“書”,方能破萬“卷”。
總的來說,唐宋以后讀書人的內卷,與科舉壓力密切相關。在科舉內卷最為嚴重的清代,書院以膏火制度保障寒士的基本生存(兜底),以“成圣賢”“做好人”引導士子的人生發展(初心),以原典研習助力士子的科名需求(現實),在緩解焦慮、應對內卷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只是,以科舉為導向的“高度篩選型”的社會結構沒有改變,上述努力也無法解決根本問題。20世紀初,書院和科舉幾乎同時停廢。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歷代書院文學活動編年史”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