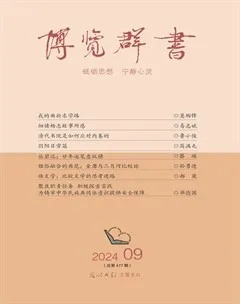大家小書:看什么,怎么看
作家出版社面向青少年讀者,一下子推出了梁歸智先生的四本系列讀物——《一看就明白的〈三國演義〉》《一看就明白的〈水滸傳〉》《一看就明白的〈西游記〉》《一看就明白的〈紅樓夢〉》(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我的直覺是此謂“大家小書”,青少年朋友有福了。因為作者是元明清文學研究專家,也是開宗立派的紅學家,由他來開講中國古代文學四大名著,可謂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碟,張飛賣秤砣——人強貨硬。為什么我敢這么說?因為我是作者的學生,對他還算比較了解。在我看來,作者是真學者,做的也是真學問。他對許多問題想得深,說得透,放得開,收得住,那真是“金猴奮起千鈞棒 ,玉宇澄清萬里埃”。而他所講評的四大名著之所以能讓人“一看就明白”,是因為他高屋建瓴,慧眼獨具,告訴了人們看什么,怎么看的解讀竅門。
看什么
打開《一看就明白的〈三國演義〉》,進入眼簾的第一講、第二講分別是“《三國志演義》的帥哥之謎”和“《三國志演義》的美女之謎”。這題目既新潮,也確實抓人眼球。往里面瞧,作者并非故弄玄虛,而確實是要探討“帥哥:趙云和馬超誰更帥?”“美女:貂蟬和二喬誰更靚?”(P2)他說趙云,那是既長得帥,又在書中“出鏡率”第一。他說馬超,則主要在“身長八尺,體貌雄異”處做文章,因為馬超有羌族血統,野性美十足。于是“曹操見到馬超‘暗暗稱奇’,劉備見到則嘆為‘錦馬超’,羌人都崇拜馬超,其實都是在渲染馬超作為‘混血兒’另類的雄烈壯美,生物學上所謂‘雜交優勢’。就像1987年央視春晚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費翔一出臺,讓人眼睛一亮”(P15)。遙想費翔當年,邊唱邊舞,帥氣十足,活力四射,立馬就成了萬人迷。再遙想馬超當年,“手執長槍,坐騎駿馬,從陣中飛出”,又是何等的氣吞萬里如虎!武功高強,再加“一張演藝明星的臉”,能不叫人癡迷乎?
再如《一看就明白的〈西游記〉》,第一講說的是“孫悟空的本領大小之謎”。因為有一種說法是,取經之前,孫悟空神通廣大,武藝高強;而在西天路上,孫悟空則動不動就得請仙佛幫忙,本領似乎已變弱變小,大不如前。這個看點作者也抓得準,讓人興奮。那么,為什么讀者有這種感覺呢?作者的解釋是,孫悟空原來在體制外,所以他喜歡好勇斗狠,能夠無法無天,但后來幫著唐僧取經,由“體制外的造反者”變成了“體制內的護法者”。既然進了體制內,一味勇猛強悍就意味著蠻干,所以小說必須“表現他人脈廣、關系多,到處都有門路有朋友,都能借助外力幫自己解決問題”(P9)。說得再直白些,就是他必須熟悉各類社會關系,懂得利用各種顯規則和潛規則,如此才能在體制內混得如魚得水。這一解釋本來已新意迭出,但作者依然不滿足于此,而是進一步把《西游記》看作一部成長小說:
應該說一直到被唐僧從五行山下放出來為止,孫悟空都被寫成一個青少年,他的故事都對應著人從出生到少年、青年的成長歷程和青春的反叛,大鬧天宮是反叛的巔峰。而從五行山下出來,保護唐僧去西天取經,就開始進入成人階段,也就是開始生命模式的轉型、自由的轉型。”(P23)
由此生發開去,我便注意到,體制內外之別,青春反叛之美,既是作者讀小說的基本視角,也是提醒讀者看小說的主要入口。再以《一看就明白的〈水滸傳〉》為例,這個問題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此書第三講是談“燕青的‘浪子風流’——《忠義水滸傳》的第二價值導向”,作者在解釋“浪子”的內涵時提到了三種意思:一是浪蕩,二是風流浪漫,三是有錢有能力,所謂人在江湖漂,總得會兩招。而他對第一層意思的解釋就頗有新意:
首先是“浪蕩”的浪。浪子絕對不會是宅男,他必然有反抗性、叛逆性,必定要離家出走、流浪江湖。宅是家,廣義上就是指體制內。體制內不愿意待了,或者待不下去了,總之不管出于何種千奇百怪的原因,主動或被動地離開了體制內,到了體制外。一百單八將,全都符合這一條,各有各的道,但條條道路通水滸、通梁山。梁山泊就是體制外的象征,也就是江湖。“逼上梁山”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好漢都是優秀的“浪子”。他們走上造反的道路,“官逼民反”是外因,本身的“浪子”氣質則是內因。第一個出場的史進,接著出場的魯達,就是杰出的浪子英雄。(P74-75)
既然《西游記》這個神魔世界已有體制內外之別,那么在《水滸傳》這個現實世界講體制內外,就更是順理成章。而浪跡江湖,遠離廟堂,則是做浪子的必要條件。如果此人再英俊瀟灑,風流倜儻,身懷絕技,武功蓋世,那簡直就成了一個完美的浪子。作者說,在一百單八將中,燕青的綽號之所以叫“浪子”,是因為他智商、情商、武藝、氣質、形象都出類拔萃,絕對是蓋世界浪子班頭。而所有這些,都能激發青少年的仰慕之心,追模之意。民間早有“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紅樓”之說,其目的是舉起道德大棒,限制某類人(尤其是青少年)接近它們。但作者卻要告訴人們,四大名著中有青春反叛,有生命力的張揚,有“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的人生快意。這種東西很金貴,是值得我們看在眼里,記在心頭的。
怎么看
看什么作者講得頭頭是道,至于怎么看,他也是有獨家秘籍的,這就是他的“探佚學”或“探佚法”。
所謂探佚,是因《紅樓夢》而形成的一門學問。眾所周知,如今見到的《紅樓夢》,出自曹雪芹之手的只有前八十回,后面的部分(可能是二十八回,也可能是三十回)因種種原因而遺失不見了,于是有了高鶚的后四十回續書。如此一來,就形成了兩個問題:一是高續是否符合曹著原來構思?二是曹著八十回之后的本來面目是何模樣?故事情節如何發展?人物命運怎樣演變?由于曹著前八十回是“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而這種技術又具體體現在作者概括的諧音法、讖語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中,因此,探究后三十回的故事情節走向,人物命運演變,進而指出高續后四十回的種種問題所在,就成了探佚學的主要任務。
讓我們以《一看就明白的〈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結局之謎”為例,略做說明。作者說,后四十回續書中,林黛玉的故事輪廓可概括為:“風聲鶴唳絕食求死;偷聽私語起死回生;調包計泄含恨而亡。”(P61)但通過探佚發現,續書寫林黛玉死前對賈寶玉恨怨交加,這與小說開頭“眼淚還債”的神話背景對比,簡直就是猴吃麻花——滿擰。因為林黛玉固然愛哭,但那是她在報恩還債,“她的哭都是因為愛賈寶玉,心疼賈寶玉,那些情感糾紛小性兒,其實質也是因為愛”(P65)。“而續書的寫法就不是報恩了,撕手帕,燒詩稿,一腔的怨恨。后來王熙鳳就說林黛玉死的時候恨寶玉呢。這就不是眼淚還債的報恩,相反變成以怨報德了。不是還債,而是討債了。”(P66-67)如此一來,續書中的林黛玉,其智商、情商都已大不如從前,也完全不是前八十回的林黛玉了。
那么,若按曹雪芹寫的后二十八回佚稿,林黛玉的結局又該是怎樣的呢?我們知道,八十回以后,賈家內部有關財產繼承權與管理權的斗爭日趨激烈,寶黛關系也成了這場斗爭的一個焦點。為了爭奪財產,趙姨娘、賈環、邢夫人等污蔑寶玉和黛玉有“不才之事”(緋聞)。因賈母病死,黛玉失去了靠山和保護;又因王夫人本來就不喜歡黛玉,她便不讓寶玉再去看黛玉,致使二人處于隔離狀態。隨后王夫人進宮見賈元春,請她下旨讓寶玉娶了寶釵。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政治斗爭,賈寶玉一度離開賈府,處境危險。林黛玉既被賈府各種惡勢力污蔑誹謗,孤立無援,又為傳聞不斷的賈寶玉擔憂傷心,日夜痛哭,最后淚盡而死。“這就是脂硯齋批語說的‘證前緣’。后來賈寶玉去瀟湘館憑吊,林黛玉已經死了半年了,他只見‘落葉蕭蕭,寒煙漠漠’(脂硯齋批語)”(P73)。于是作者概括道,林黛玉在佚稿中的結局實際上是“賈母死去失掉靠山;流言蜚語遭受污蔑;擔心寶玉還淚而逝”。也就是說,“曹雪芹筆下林黛玉的結局,是因為愛而獻身;續書中林黛玉的結局,是因為恨而滅亡。這才是探佚要真正關注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小說的精神境界、價值導向。至于是秋天死還是春天死,是肺結核病死還是投水而死,讀者和研究者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一定非要得出一個唯一的結論”(P74)。
窺一斑而知全豹。縱觀這本《一看就明白的〈紅樓夢〉》,其中的“兩種《紅樓夢》之謎”“賈寶玉結局之謎”“十二釵結局之謎”等內容,作者就是依據探佚之法,大體還原了曹氏紅樓夢的故事真相。我因此前讀過作者《紅樓夢探佚》(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中的部分篇章,就覺得他的這本小書異常親切。實際上,就像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是《存在與虛無》的通俗版,羅薩的《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是《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的通俗版,作者的《一看就明白的〈紅樓夢〉》也是《紅樓夢探佚》的通俗版。經過他的創造性轉化之后,這本書走向青少年讀者已毫無問題。
如果說《紅樓夢》是因為運用探佚之法才看到了事情真相,那么其他三部名著作者又是如何看的呢?通俗地說,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學術些講,是有了一些“癥候閱讀”的意味,即不僅看那些故事講了什么,還要看它沒講什么,而沒講出來的東西甚至比講出來得更加重要。例如,通過分析《水滸傳》中的第一主角宋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作者指出:“宋江本是忠義之人,根本沒有造反的念頭,卻被形勢所迫,最后無奈上了梁山。”“所以,宋江這個人是另類的‘忠義英雄’,《水滸傳》這部書的價值導向是忠義,可謂洞若觀火。”(P13)如果說第一價值導向的“忠義變奏”是明線,是《水滸傳》講出來或面對這部書容易分析出來的東西,那么“浪子風流”作為第二價值導向則是暗線,是隱含在小說深處的一種精神追求。而通過認真梳理浪子燕青的英雄事跡,通過詳細分析小說文本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相接合,作者形成了如下結論:
從《忠義水滸傳》原著的立意來說,燕青所體現的“浪子風流”,是與“忠義變奏”互為表里的另一條文化精神主脈,其背后的思想資源是道家的理想和美學。多才多藝多情的風流浪子,浪跡江湖,遭遇磨難,成長為斗士而做一番江湖事業,待功成后急流勇退,以逍遙自在的隱逸而謝幕。忠而不奴,俊而不艷,燕青把浪子風流作了完美的詮釋。如流行歌曲所唱:風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是自由生長的樹,回到最初的華美。(P85-86)
能把這層意思看出來,說明作者功力深厚,也說明他對看的方法運用得當。我甚至覺得,因為探佚,他已像孫行者那樣,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
如何寫
如前所述,在這四本書里,作者向我們展示了“看什么和如何看”的道理,但他要把這些想法訴諸筆端,表達出來,又涉及一個如何寫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作者恰恰很有心得。
不妨注意一下放在每本書前面的那篇序文:《從“四大奇書”到“四大名著”》。此序寫到最后部分,作者有了如此說法:
本書也鮮明地表現了我的治學個性和特點,可以概括為:悟證靈感迸發,論證展開闡釋,考證補充完善。悟證、論證、考證三者齊頭并進,相輔相成,而悟證和論證是本人的強項,考證則首先是一種借鑒式的宏觀把握,具體的問題,往往需要時才查考比對資料而有意為之。我始終不是在“做論文”,而是在“寫文章”,或者說在寫“論筆”,這是我杜撰的一個詞——隨筆文章其形而有論文之實,突出“靈感”“悟性”,也講究“寫文章”的“筆法”,而不呆板地標榜所謂“學術規范”,我的書文也因此有“可讀性”。(P13)
此處作者前面交代自己的治學特點,后面說明自己的為文特色。而敢于說自己的文章有“可讀性”,意味著作者有底氣,很自信,把“論筆”運用得、拿捏得恰到好處。關于論筆,我以前不僅撰文分析過它的文體特性,而且還有意“盜獵”作者發明的這一概念,活學活用,推而廣之,希望能把論筆寫作精神發揚光大。但如今我讀作者的這四本小書,依然覺得其論筆筆法值得分析。
既然作者每每為文,已然意識到自己的寫作與論文無關,所以他從來都不端“做論文”的架勢,而是轉換成“寫文章”的姿勢。“做論文”有架勢嗎?有。許多人一旦意識到自己要寫論文了,便始而焦慮緊張,終而正襟危坐,然后整些新名詞,寫些長句子,露出翻譯腔,鐘情歐化體。但作者寫文章從來不虛頭巴腦,咋咋呼呼,而是有真意,去粉飾,不賣弄,接地氣,能把天上的道理講到地下來。于是讀他的文章,你頓時覺得他就是普天下深入淺出領袖,蓋世界通俗易懂班頭。
試舉一例。前面說過,作者曾把孫悟空本領的大和小放到體制的內與外中進行分析,但如何才能用平實淺易的文字講出這番道理呢?作者是這樣寫的:
從體制外到體制內,意味著“自由的轉型”。體制外具有體制內所欠缺的野性、欲望,生命的激情之火可能燃燒得更加旺盛。孫悟空保唐僧取經,是皈依了體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命的原創力,因為生命只能在規則中活動,不能為所欲為發泄到極致了。而那些西天路上的精怪,卻成了野性生命自由欲望的象征,下界為妖的天宮神將仙佛坐騎等,也不再是為既定的秩序系統服務,而是在為自己的自由生命奮斗了,動物兇猛,生命的原創力獲得了空前的張揚。孫悟空與妖魔正邪易位,從某種意義上說,本領也應該相形見絀,正如私營企業的活力,勝過公有企事業單位。這是一種“自由的悖論”,可以說體制外是“叢林法則”,體制內是“妥協的藝術”。(P12)
這真是娓娓道來的精彩之論。之所以精彩,是因為作者首先用體制內與體制外打比方,然后又把孫悟空和眾精怪代入到體制內外的具體處境之中,談野性與力量,談規訓與限制,談自由與生命力的張揚。這種談論當然新意滿滿,但有人可能會問,這是不是游談無根?這里面有沒有理論支撐?答案顯而易見,因為這里有生命哲學的涌動,有酒神精神的彰顯,只不過這種理論幻化于無形,仿佛鹽溶于水。如此行文運筆,就既讓論述有了支柱與底氣,也保證了它的深入和淺出。寫到最后,作者又用私營企業和公有企事業單位作比,談活力的多寡有無,讓人在會心一笑之余進一步明白了體制內外的區別。而以“妥協的藝術”和“叢林法則”曲終奏雅,既強化了體制內外的特點,又轉換了看問題的角度,還讓整體論述有了某種高度。如此貼心貼肺地談論之,分析之,讀者豈能無入腦入魂之感?
我還注意到,用今日說法談論古代事情,用古代事情印證今日說法,此為作者論筆寫作的慣用技巧。前面所引的例子已能說明這一問題,下面我再舉兩例,以便加深讀者印象。比如說呂布:“戲曲舞臺上的呂布,是集體育健將的健美、影視明星的靚麗、戰斗英雄的猛勇、帥哥型男的癡情于一身,而成為社會偶像、大眾情人。”(P19)又如說賈元春:“元妃日益受寵,皇帝經常臨幸,當然賞賜也很多。但時間長了,貴妃的身體就發福了,其實就是享受太多了,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都出現了,越來越嚴重,最后就病死了。”(P26)像這種文字,古今對話,今古交融,你說它妙也不妙?
走筆至此,我還想說說“大家小書”的形式之“小”。其實,這四本小書并非橫空出世,而是其來有自。五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曾推出作者的《四大名著經典要義》,我當時就曾讀過一些。但盡管此書就是論筆寫法,卻因為它是按照學術書的樣子做出來的,所以捧讀此書,果然就有了一些高頭講章的味道。如今《四大名著經典要義》一分為四,文字還是原樣,開本卻有變化。由于此版本采用的是很昂貴也讓人看上去很舒服的48開本,再加上裝幀設計新穎,排版舒展大方,立刻就讓它有了“大家小書”的模樣,也讓我有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當我在來回高鐵的長旅上依次細讀這四本小書時,甚至都引起了路人甲的側目而視。他們大概心里嘀咕:這個塵滿面、鬢如霜的家伙怎么在讀小人書?
果如此,那么出版社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因為倘若這套“大家小書”捧在手上是連環畫的質感,讀在心里是人小書的爽感,那么,青少年朋友是不是就有了“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閑看《牡丹亭》”的閱讀享受?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