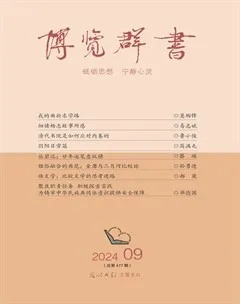戲·冷·虐:《孔乙己》中的生活片段
《孔乙己》是由主人公的若干生活片段連綴而成的小說。這些片段主要發生在魯鎮的咸亨酒店,由于敘事者“我”曾在店里做伙計,便根據“我”的零星記憶將其組合起來。從這些片段及其組合方式中,我們可以窺見作品主題和寫法上的特點。
“戲”與“冷”為主的片段
第一組生活片段是關于孔乙己與酒客(短衣幫)的交往,可細分為兩則。孔乙己一到店,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繼而從“額頭上的新傷疤”說到“偷東西”,再說到“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這些話基本屬實,孔乙只好滿嘴“之乎者也”,說些難懂的話,人們便哄笑起來——這是第一則。孔乙己喝過半碗酒,平靜下來了,大家又撩他:“孔乙己,你當真識字嗎?”孔乙己不屑回答。大家于是追問:“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這就戳到孔乙己的痛處,他臉色發灰,說的話已經完全聽不懂,人們笑得更加開心——魯迅善寫人的刻薄,這兩問便是好例——這是第二則。兩則片段在對孔乙己的傷害上構成遞進關系。站在孔乙己的角度,他此時遭受的對待是“戲”,即人們戲耍、取樂的對象。
第二組生活片段是關于孔乙己與孩童的交往,也可細分為兩則,一是孔乙己教“我”寫字,二是孩子們看熱鬧。這兩則都是順著“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寫的。在孔乙己教我寫字之前,魯迅寫道: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著笑,掌柜是決不責備的……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這段話既寫出“我”參與了“笑”,與之所以還記得孔乙己呼應,也交代了孔乙己主動搭訕的原因。在孩子們看熱鬧之前,魯迅又寫道:有幾回,鄰居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這也是承接第一組片段,孩子們何以過來?是被店里酒客戲耍孔乙己的笑聲吸引來的。過去劃分結構時,我們總是從“笑”“快活”等字著眼,把這兩則與酒客取笑孔乙己的片段視為一律,其實二者的內容指向有所區別:“戲”的成分在減弱,“冷”的氛圍在增強。面對孔乙己的問話,“我”態度相當冷漠,雖沒有出言取笑,但很瞧不起: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嗎?看見孔乙己懇切的樣子,“我”不耐煩地說了“茴”字怎樣寫,見孔乙己還要講其他寫法,我便“努著嘴走遠了”。那些比“我”更小的孩子聞聲而來,只不過要看熱鬧;到了孔乙己跟前,無非想吃茴香豆,孔乙己不再給豆子,也就走散了。至此,孔乙己向孩子們說話這條路徹底斷絕,他作為“人”的存在,在咸亨酒店的空間里只剩被嘲弄、被鄙夷和無可訴說的寂寞。魯迅雖然仍將這些片段包裹在“快活的空氣里”,但強調的卻是“冷”的因子,孔乙己在大人孩子眼里都可有可無,只因暫或使人快活,才沒有淪為“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罷了。
接下來魯迅專門寫了一句話: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然而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這句話單獨成段,很值得注意。1942年,葉圣陶先生撰文指出:
《孔乙己》前一部分是平敘,就是小伙計敘說關于孔乙己的所見所聞,是綜合了平時的經驗來敘說的,并非敘說某時某天的所見所聞,其間沒有時間的關系。后一部分是直敘,……這些都是敘說某時某天的所見所聞,其間有時間的關系。從平敘轉到直敘,插入前面提出的那句話,一方面把以前的平敘總結一下(那句話本身也是平敘),一方面又給前后兩部分立一個明顯的界限。(葉圣陶,《〈孔乙己〉中的一句話》)
葉老站在全篇角度闡述了此句對轉換敘事邏輯的作用,相當精辟。
“冷”與“虐”為主的片段
第三組生活片段共有三則,但核心只有一幕,就是中秋過后,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喝酒時的情形。這一幕在“戲”和“冷”之外,增添了殘酷的色彩。孔乙己被丁舉人打折腿,生命已經垂危,大家還要笑他。掌柜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這回是不是又偷東西了?”孔乙己不再分辯,只說“不要取笑”,并用懇求的眼色看著掌柜。此時又聚上來幾個人,大家圍著孔乙己都笑了。孔乙己喝完酒,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地走去了。這三次“笑”非常震撼,表面看似乎與原先并無不同,所笑的都是孔乙己,笑的內容也都是“偷”,但在被“笑”者,境遇卻與之前大不相同,他黑而且瘦的臉、蒲包上盤著的斷腿、身上的破夾襖和掌心的泥,全被小伙計看在眼里,掌柜和酒客仿佛看不見似的。在稍有良知的人眼里,這就不只是“戲”和“冷”,而是對瀕死的生命的虐待了。
在核心片段前后,魯迅略寫了兩則片段,一是人們議論孔乙己的挨打,二是掌柜念叨孔乙己欠的錢。既然孔乙己可有可無,人們何以在他不在場時提及他呢?答案在“十九個錢”上。因為“十九個錢”,掌柜才會偶然說起孔乙己,酒客才會順嘴提起他被打的經過。在這里,掌柜對錢的關切映襯出對人的漠視,酒客說起孔乙己遭遇時漫不經心的語氣,也表現了人心的“冷”。更重要的是,這一片段為孔乙己最后的出場做了鋪墊,讀者看到這里就會有心理準備,作者便可以專心詳敘孔乙己到店后的情形,而不必補敘孔乙己斷腿的緣由了。后一則寫得更為簡省:自此以后,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柜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這段平常之極的話語使小說的“人情味”降到冰點。掌柜第一次說錢,是在不知情且未見面的情況下,而這兩次則是在已知孔乙己斷腿、親見孔乙己垂危之后。可見,孔乙己的慘象在他心中沒有掀起任何漣漪,他在乎的只有這“十九個錢”,而最終竟不再提,也只因對討錢之事絕望罷了。行文至此,常常出沒于人前,使酒店“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的孔乙己徹底消失了,沒有獲得任何情感的追懷,也未在輿論場上也留下一絲痕跡。整體來看,前一則片段接續第二組片段中的“冷”,進而由“冷”入“虐”,起鋪墊作用;后一則由“虐”回“冷”,起煞尾作用。而孔乙己欠的“十九個錢”則是重要線索,不僅出現在首尾兩端,在核心片段中也被放在顯著位置。掌柜看到孔乙己馬上“伸出頭去”:“孔乙己么?你還欠十九個錢呢!”這樣寫固然是出于可信性的考慮——掌柜平常都提“十九個錢”,見面怎能不提?但更重要的還是為凸顯“十九個錢”在整個直敘部分的線索功能。
當故事在“我”波瀾不驚的講述中走向尾聲時,魯迅有必要借“我”之口交代孔乙己的結局。問題是,一旦給出某種確定性的結局(或死或生),就必須使“我”或其他人對末路的孔乙己發生關切,而這又與主題不合。于是魯迅讓“我”順著“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這句話說下去: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已經死了。“現在”是何時?就是“我”講故事的當下,這個時間點本來無可稽考,但“我”開篇就說過: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這樣便與開篇的“現在”重合起來,形成首尾圓合的效果,也使敘事者從故事中走出來,徹底地完成了使命。全篇最后一句是家喻戶曉的“名句”,論者多從字面意思上理解“大約”與“的確”的矛盾,認為“大約”是因為沒有親見,此刻難下定論;“的確”則是出于事理邏輯的推斷,不死又待如何?其實,這句話還是從敘事者視角來說的:“大約”代表講述人現在的看法,而“的確”則是呼應二十多年前掌柜與客人的談話。掌柜曾問客人:“打折了怎樣呢?”客人說:“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敘述者主動呼應故事中其他人物的話語,會使讀者覺得故事本身更加真實。
《孔乙己》是以主人公為“中介”的小說
細說《孔乙己》中的生活片段及魯迅連綴的方法,旨在申明一個事實:《孔乙己》不是以主人公為中心的小說,而是以主人公為“中介”的小說。說孔乙己是《孔乙己》的主人公,誰都不會反對。但是,他與賈寶玉、別里科夫、桑地亞哥是同樣性質嗎?即以魯迅小說而論,與祥林嫂、子君等也大不相同。在一般作品中,主人公是作家行文的中心:主要情節由主人公的選擇與行動推動;其選擇與行動無一例外地展現主人公自身的內在品質,即“典型性格”。相比之下,《孔乙己》的主要情節大多不由孔乙己推動,而由孔乙己之外的力量推動。孔乙己本人只有表層性格,比如“有自尊心”“好喝懶做”之類,這些性格并不具有“情癡情種”“頑固守舊”“硬漢精神”那樣的特異性和典型性,況且隨著故事發展,也沒有被塑造得更深入——直到被打折腿,孔乙己還是一如既往。
魯迅為何要寫一個看似無關緊要且性格淺表的人物呢?我們看到,小說開頭并沒有直接寫孔乙己,而是寫了酒店顧客的差別以及冷漠單調的氛圍,塑造出階層分明、沉悶壓抑的環境。待到孔乙己出場,魯迅才在醒目位置給出介紹:“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QhNMJ+KKONuXVpIM7QQrPA==”這句話揭示了孔乙己獨特的定位,他是“弱勢”和“異類”的混合,“弱”在社會地位,“異”在大眾觀感。換言之,孔乙己稱得起“典型人物”,但他的典型性被定位在社會角色層面,而不像傳統小說體現在內在品質上。
這樣一來,當孔乙己被“拋進”咸亨酒店的環境中,他就變成“試金石”,以他為“中介物”,可以檢驗社會文明的程度。社會越文明,人們對弱勢群體就越關心、越照顧;對與自己不同的“異類”,也就是只能“站著喝酒”卻非要“穿長衫”的人,就越接納、越包容。魯鎮是相反的,孔乙己越落魄,人們越肆無忌憚欺負他;孔乙己是“異類”,人們就拿他開心,在他將死的時候也不肯放過最后一次取樂的機會。這正是魯迅提起《孔乙己》創作動機時說的“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魯迅,《〈孔乙己〉附記》),也是孫伏園轉述的“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孫伏園,《關于魯迅先生》)。其實,中國社會是允許“苦人”茍活的,但前提是必須按照大眾給定的人設,時時顯示痛苦、可憐和無助,才能免于傷害;中國社會也肯于接納異類,但前提是必須強大,強者的與眾不同,即便過分、荒唐,會成為民眾的趣談軼事,就像丁舉人,沒人說他不該打折孔乙己的腿,反過來還要說孔乙己自己活該。魯迅深刻在于,他并不單純批判一般社會中同情心的匱乏,而是通過孔乙己的遭遇,再現了中國社會“冷漠”與“勢利”合二為一的叢林法則,以及人們對這套法則的習以為常。
從寫法上看,既然把孔乙己作為“中介”,就要把他一次次“投放”到環境中,使他能與周邊發生反應,這時作家會遇到兩個難題。第一,由誰把他“投放”出去,也就是敘事視角問題。傳統的第一人稱視角或上帝視角,不能很好達到目的,因為兩者都難回避對主人公性格心理的細致描寫,也就不便集中展現人們對待主人公的方式。為此,魯迅假托“小伙計”的口吻講述孔乙己的遭遇,既然是小伙計是“旁觀者”(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對孔乙己的“刺激”),那他就只需陳述耳聞目睹的事實,而不必過多地顧及孔乙己怎么想。這種視角的應用,與人物的性質與功能是高度匹配的。第二,把孔乙己一次次“投放”到環境中,必然產生一些敘事的碎片,這些碎片在主題上既不能重復,又要有相關性,彼此之間還要銜接緊湊、過渡自然。魯迅在這一點上幾乎做到了天衣無縫:不僅有條不紊地表現出三組片段整體上的層進關系(由“戲”到“冷”到“虐”),還舉重若輕地寫出了三種對待之間的融混關系(“戲中有冷”“冷中有虐”“虐中有戲”),輔以關鍵處簡明扼要的過渡和總結,通篇給人渾然天成的審美效果。古人作文,以“不能增刪一字”為美,但古來少有臻此境界者,白話文更是鳳毛麟角——《孔乙己》庶幾近之。
語文教學對《孔乙己》的誤讀
《孔乙己》自1919年發表以來,研究者汗牛充棟,但在文本分析路向上始終存在不同程度的偏頗。最常見的,就是沿用傳統思路,把《孔乙己》看作以人物為中心的作品,把孔乙己本身的性格命運作為賞析的重點。在此思路之下,孔乙己往往被當作“讀書人”或“知識分子”,其悲劇根源往往與科舉制度、封建等級文化等掛鉤:魯迅在這篇《孔乙己》里再接再厲地向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他從破落的舊知識分子孔乙己的身上……最終被反動統治階級打死的悲慘歷史,暴露了封建科舉考試制度——科舉的毒害……(徐中玉,《孔乙己研究》);《孔乙己》不僅揭露了封建禮教和科舉制度的吃人本質,而且辛辣地嘲諷了作為孔孟之道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的文言文對孔乙己的毒害(金芹,《關于〈孔乙己〉寫作年月及其主題思想的探索》)……這樣的觀點不勝枚舉。
新中國成立以后,《孔乙己》被大多數教科書選作課文,而“教參”采納的仍是特殊年代的陳舊解讀,這就影響到教師的授課,進而通過語文課堂影響了全體國民的閱讀接受。考察改革開放以來40多位知名語文教師的教學設計,有30多位都把教學目標定位在“引導學生理解封建科舉制度對人的毒害”上。時至今日,問起中小學生對《孔乙己》的觀感,也往往隨口提到“科舉制的毒害”。誠然,從文本內容上看,科舉制對孔乙己是有影響:第一,影響了孔乙己的身份認同,他窮得叮當響,還要保持讀書人的體面。第二,影響了孔乙己的話語習慣,他滿嘴“之乎者也”,很難與人交流。第三,影響了孔乙己的生活方式。考科舉、求功名的人大多不愛體力勞動,孔乙己也一樣,不但好喝懶做,有時還會偷東西。但是,這些影響并不是魯迅表現的重點,而且也不必然造成孔乙己的悲劇。古代多少生員舉子落榜?難道落榜就要“小偷小摸”,小偷小摸就一定會被打折腿?有人說,孔乙己的腿是丁舉人打折的,這是科舉制迫害他的鐵證。丁舉人是具體的人,怎能與科舉制畫等號呢?除非科舉制規定落榜者一概打折腿,我們才可以說這是科舉制的毒害。
任何經典文本的解讀,都可以也應該是多維和多元的。但是,教學解讀畢竟不同于可以任意發揮的休閑閱讀,我們必須從語言文字荷載的事實出發,講證據,講邏輯,講審美。置生動鮮活的生活片段于不顧,置行文特點于不顧,單純分析主人公的性格心理,甚至將悲劇原因生硬扣到科舉制上,顯然是不合適的。《吶喊》中還有一篇《白光》,講了一個屢試不第的讀書人落榜后發了瘋,輾轉死在深山里的故事。只消讀讀這篇文章,大家自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批判科舉制了。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