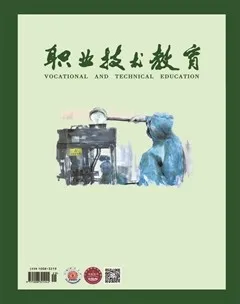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研究

摘 要 深化產教融合是高職院校與企業協同育人的著力點。以共生理論為分析框架,剖析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可以總結為校企作為共生單元的兩類主體之間能量交互不匹配、產教融合政策對企業的支持力和約束力偏弱、社會對高職院校培養人才質量認同度低以及未形成一體化與互惠共生的人才培養模式。從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三方面進行分析,探究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內涵,建構人才培養模式。以此提出要確立校企產教融合的共同利益目標:以資源交互促進新能量生成;治理校企產教融合的共生環境:以制度化促進校企行動自覺;激發校企產教融合的共生意愿:強化實體組織建設實現利益共享。
關鍵詞 共生理論;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4)29-0022-06
產教融合是職業教育的基本辦學模式,是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工作。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在深化產教融合方面創新性提出了打造市域產教聯合體、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開放型區域產教融合實踐中心的新任務。人才是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尤其是隨著科技迅猛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提出迫切需求。作為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主陣地,高職院校深化產教融合不僅是其與企業協同育人的著力點[1],也是當前滿足人才培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迫切任務。從現有研究來看,學者對高職院校產教融合育人展開相關研究[2][3][4][5][6],主要采用資源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三螺旋理論等,但現有理論框架尚未充分體現高職教育產教融合的特性,且在與實踐的結合方面略顯生硬[7]。由于共生理論蘊含的內在邏輯是合作共贏,與高職院校產教融合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基于共生理論構建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對于解決當前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面臨的困境具有現實意義。
一、共生理論對于構建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解釋力
(一)何為共生理論
共生理論起源于生物界,最初是指不同物種之間因對方存在而受益的共同生存和協同演化的生物學現象。生物群落中的共生是普遍現象,其揭示了合作共贏是自然界中生物生存和進化的基本法則。1879年,德國生物學家安東·狄·百瑞(Heinrich Anton de Bary)將“共生”定義為“不同種屬因為生存需要,按照某種特定模式形成的互利關系”[8]。20世紀50年代,共生理念逐步滲透到哲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等領域,成為具有普適性的理論研究范式[9]。共生組織的結構模式及共生行為的交互模式是決定共生系統狀態的重要因素;所有共生單元聯結形成的共生體能否生成新的共生能量以及生成新能量的多少是衡量共生關系質量的核心。
(二)共生理論分析框架的基本邏輯
1998年,我國經濟學者袁純清首次以共生理論作為分析框架探討經濟學問題,其將共生系統劃分為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三個維度,認為在一種共生系統中共生單元是參與主體,共生模式是能否生成新能量的關鍵,共生環境是決定共生關系的重要外部條件[10]。有學者將共生關系分為兩種:共生行為關系和共生組織關系。并對這兩種共生關系的行為表現進行描述,其中共生行為關系表現為寄生關系、偏利共生關系、互惠共生關系等;組織共生關系表現為點共生關系、間歇共生關系、連續共生關系及理想的一體化共生關系等[11]。共生單元及共生關系是共生體的內部條件,也可以說是共生系統或共生體,而共生單元之外的其他因素及其相互關系是外部條件,被共生理論稱之為共生環境。還有學者將共生理論應用在社會領域,其核心觀點是社會共生且按要素分配,要素分配的前提是“要素共生”,即所有的“共生”都與資源相關,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共生論”。社會共生論認為,“共生”是在無法排除任何共生對象的客觀前提下,主觀地實現人類社會交往中照顧各方利益和理想的最佳機制和架構。因此,社會共生理論的邏輯,就是通過合作互補、公正平等及共同發展的基本思路,最終形成對稱互惠一體化共生的格局[12]。總之,共生理論分析框架的基本邏輯,是從識別共生現象開始來分析共生單元的結構及交互關系。共生單元是構成共生體的基本能量生產和交換單位。在本文中,以高職院校和企業兩類主體作為產教融合共生體的共生單元,政府作為另一個共生單元起調節作用。在產教融合過程中,高職院校和企業這兩個共生單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形式就是二者的共生模式。在產教融合模式中,既反映校企之間的物質信息交流關系,也反映校企之間的能量互換關系。
(三)共生理論對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解釋力
共生理論對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具有很好的解釋力。一方面,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目標和質量事關當前國家新興戰略行業的發展,因此,在高職院校和行業產業之間,組織的邊界壁壘必然要打破,且必須進行資源和要素的動態交互,以最終形成社會共生關系,才有可能實現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成為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這與共生理論的假設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產教融合的各方主體之間,必須是共生關系,并通過實現各自的利益訴求相互依存和彼此影響,形成共生機制,才能真正彌合影響產業和教育深度融合的鴻溝。共生理論起源于生物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生物學家們一直探尋和研究各個群落中生物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并得出結論:個體或群體勝利或成功的秘訣,不在于強者壓倒一切的“本領”,而在于其在群體中密切聯合的能力[13]。產教融合共生單元的兩類主體均能影響人才培養過程,共生單元之間共生關系的交互效果都會在人才培養質量上有所體現。由于本研究重點關注在校企目標相對一致的前提下,高職院校人才培養過程的產教融合問題,因此,共生理論可以分析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模式的產教融合困境,并預測二者作為共生單元的產教融合效果。
二、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存在的困境
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是指高職院校和企業有效融合,優化整合高職院校的教學體系,校企共同協商制定人才培養計劃和育人內容,形成校企共治的人才培養機制。盡管,高職院校與企業之間具有建立共生關系的良好基礎,對人才培養的目標具有相對的一致性,但在協同育人方面仍然存在諸多困境。
(一)校企作為共生單元的兩類主體之間能量交互不匹配
在共生關系中,共生體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核是二者交互生成共生能量,且二者產生能量的能力相互匹配。高職院校和企業以產教融合的方式形成一個社會共生體共同培養人才,在此過程中,由于實際上多是以簽署一個協議,或者共建一個項目的方式,即以點共生或間歇共生的模式為主,很難形成連續共生的模式。在人才培養上,高職院校承擔的任務和責任遠大于企業,新知識、新技能的傳授主要在學校完成,企業所發揮出的作用非常小。由于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必須要經過實踐的鍛煉,他們的培養不能單單在高職院校完成,必須充分發揮企業提供實習崗位、新技術知識等功能,確保培養出的人才不僅是知識型人才,更是技能型人才。
(二)產教融合政策對企業的支持力和約束力偏弱
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與企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具有相對的一致性,這決定了學校和企業之間具有建立共生關系的基礎,但這需要政府發揮紐帶作用。從國家已經發布的一系列關于產教融合的政策來看,一方面約束力不夠,主要表現為政策均是多部門聯合發布,大多采用的是“鼓勵”“推動”“引導”等字眼,并未有實質性約束的條款來要求企業參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另一方面,盡管國家提到將采取土地、稅收、信貸、獎補等手段支持企業參與產教融合,但是政策缺乏針對性與可操作性,具有具體落實作用、行業性強的政策極少。此外,我國尚未對產教融合進行單項立法,缺少效力級別高且約束力強的法律法規。
(三)社會對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質量認同度低
2021年,《教育家》雜志聯合多家教學和科研院所在全國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并發布了《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大型問卷調查報告》,報告顯示社會群體普遍對高職教育的認可度較低。與地方對高職教育的支持程度、社會對學歷的崇尚、傳統文化對職業教育的偏見均有一定的關系,但最核心的因素是所培養人才的質量不符合產業和社會發展的需求。高職教育所培養人才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和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的深度和密切程度相關,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最終要轉化為企業的人力資源,為企業和社會發展服務。因此,需要企業深度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但是企業參與人才培養的意愿并不強烈[14],從而導致不良循環。
(四)未形成一體化與互惠共生的人才培養模式
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VaKGrPDaBKZ32hGpYj5ZJI3dm5ftgHU0lZv1BAI01FM=最理想的模式是一體化共生模式。但在現實中,從組織共生來看,企業與高職院校之間在人才培養方面多以點共生、間歇共生為主,校企合作的偶然性和隨機性較大,長期性和穩定性較差;從行為共生來看,校企合作培養人才大多是“校熱企冷”,企業參與人才培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導致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處于一種寄生和非對稱性互惠共生的狀態。由于一體化與互惠共生的人才培養模式尚未形成,學生缺少足夠到一線實習實踐的機會,所學習的知識和技能與一線崗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導致畢業后的崗位勝任力不高。
三、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
(一)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內涵
人才培養模式由人才培養理念、培養過程及培養方法所構成。人才培養模式主要包括規定和規范兩個問題:規定是指“培養什么樣的人”,即培養什么規格、什么層次的人才,屬于培養目標問題;規范是指“怎樣培養符合培養目標的合格人才”,屬于培養方式、培養手段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內涵,也是人才培養目標的本質屬性。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建立起政府、高職院校、企業三個共生單元構成的彼此外向的共生機制,協同推進,充分發揮共生主體的優勢,設定共生體的目標,即規定共生體“培養什么樣的人”,并朝著這個目標努力;二是建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職業素養等內向機制的共生共融有機結合,以生產共生體的新能量,促進所培養人才的質量提升和全面發展,這一過程實現了對目標的規范,即“怎樣培養符合培養目標的合格人才”;三是以政府制度供給、資源整合、經費支持等落實國家高職教育產教融合政策的具體實踐。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是在內外共生機制的共同驅動下,在國家政策的范疇內建立起的高職院校的培養目標和產業企業的用人標準之間高度統一的共生性產教融合關系。
(二)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
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除了基于共生性產教融合的內涵,還需要充分考慮各種現實因素。首先,將高職院校、企業作為共生主體單元,以共生新能量的產生作為共生體的使命;其次,基于高職院校和企業各自的利益訴求,二者之間彼此提供符合對方利益訴求的資源,形成共生資源,以促進共生新能量的生成;再次,政府以協調和政策性支持作為另一個共生單元,引導校企共生體緊密合作,相互依存;最后,以共生機制促進校企共生行為模式和共生組織模式逐漸向理想的共生模式轉變,并同時促進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機制形成并良好運行,生成共生體新能量,實現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因此,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維度包括:共生單元資源交互、共生行為模式轉變、共生組織模式轉變、共生新能量生成,見圖1。
共生單元資源交互是指高職院校和產業作為產教融合共生體的主體共生單元,彼此之間進行資源的交互,企業為高職院校提供培養人才的真實工作場景,以及將企業的生產標準、工作程序、崗位要求、職業素養以及企業實踐能力指導教師等,高職院校為產業企業提供智育服務以及為企業提供能滿足企業當下及未來發展需求的高質量人力資源。
共生行為模式轉變是指校企產教融合行為模式逐漸從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對稱互惠共生向對稱性互惠共生轉變。根據共生理論,高職院校和企業產教融合共生行為的模式有四種:寄生共生模式、偏利共生模式、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和對稱互惠共生模式。當前校企產教融合模式以非對稱互惠共生模式居多。在理論上,高職院校和企業的產教融合共生行為模式應該根據校企雙方的實際需求來選擇,并不存在絕對的最佳行為模式,但在校企產教融合人才培養行為模式中存在一定的趨向性,對稱性互惠共生的產教融合人才培養行為模式是最穩定、最理想的行為模式,其對稱性及互惠資源與利益分配機制使得高職院校、產業企業、政府等共生單元主體處于最平衡的共生狀態之中,在這一狀態中,校企優勢資源相互交流和補充,彼此的利益高度耦合,資源、信息、能量都達到最佳效率狀態。
產教融合組織模式轉變是指高職院校和企業的共生組織模式由點共生逐漸轉變為理想的一體化共生組織模式。在共生理論中,共生組織模式有多種形式,包括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以及一體化共生等組織模式。點共生組織模式是指高職院校和產業企業的某一次合作;間歇共生組織模式是指高職院校和企業在一定時間段內的多次合作;連續共生組織模式是指高職院校和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的長期合作;一體化共生組織模式是指高職院校和企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戰略合作共生體,彼此的發展要素需要對方提供資源和支持,信息、技術、資源在共生單元主體之間自由循環流動,共生單元之間基于發展要素的融合而彼此成為一體。
共生能量生成是共生單元通過資源交互、共生行為逐漸趨向對稱性互惠共生模式、共生組織逐漸趨向一體化共生組織模式,產教融合共生體產生的新能量以高質量、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形式呈現,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得到企業和社會的認可,具有良好社會適應性的人才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效果顯著提升。
四、共生理論視域下高職院校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實踐路徑
(一)確立校企產教融合的共同利益目標:以資源交互促進新能量生成
高職院校和企業進行共生交互的產教融合,應首先確定共同的利益目標,以共同的利益目標優化校企的產教融合共生關系。高職院校通過和企業聯結培養具有良好社會適應性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企業通過和高職院校形成產教融合共生體而獲得企業發展急需的人力資源。這類社會適應性良好的人才作為稀缺資源,是高職院校和企業形成共生性產教融合關系的主要紐帶,也是校企進行產教融合育人的共同利益目標。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具有公益性的本質屬性。企業參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但企業最重要的屬性是盈利,因此在承擔培養人才任務時,企業期望能夠和高職院校有資源的交換,并通過和高職院校形成產教融合共生體所產生的新能量獲得利益。
高職院校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能提供給企業所需的資源主要有兩大類,一是所培養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二是企業所需的引領技術發展的高深知識。提升所培養人才質量需要和企業形成共生關系,為企業提供引領技術發展的高深知識是高職院校和企業形成深度產教融合關系的關鍵路徑。因此,高職院校不但要強調打造“職”的屬性,而且必須注重發展“高”的內涵。作為類型教育的高職教育,應以涵養“高”為突破點,和具有更強“職”屬性的企業形成共生體時,才能提供企業所需的資源,才能形成能量交互匹配的格局,從而有利于二者的共生關系互惠互利,合力生成新能量。
(二)治理校企產教融合的共生環境:以制度化促進校企行動自覺
高職院校和企業的產教融合初期主要靠政府頒發的政策來驅動,其表征是不得不在政策驅動下形成松散的合作。但是現行的相關政策對高職院校和企業大多是用“鼓勵、推進、引導”類條款,這些條款對高職院校和企業的支持力和約束力都不強。要破解高職院校和企業產教融合約束力偏弱的外部政策環境等困境,需要將高職院校和企業的產教融合相關政策制度化并轉化為行動自覺,形成產教融合政策執行有效的共生關系圖景。制度化要求所關涉的組織行動及背后的制度邏輯具備合法性,高職院校和企業之間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制度化需要通過制度邏輯合法性的重構來實現。
高職院校與企業產教融合制度合法性建設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強產教融合制度立法建設。以強制性規則形式促進制度供給范式從政策型向法治化轉變,增強政策對校企雙方的支持度和約束力,以政策制度保障產教融合模式從點共生或間歇共生向長期一體化共生關系轉變。二是強化產教融合制度體系的建設。注重規制性制度、規范性制及文化-認知性制度等多元制度的系統性和互補性,以制度驅動產教深度融合進而生成最大化的共生能量。例如建立企業用工制度、高職學生到企業實習制度、稅收優惠制度、行業規范和標準等的交互補充等。三是形成高職院校和企業的產教融合文化認知框架。制度要真正起作用,在特定場域必然外顯為高職院校和企業的行為結構,而其內核必然是對制度的認同。因此,應在法治化制度建構的基礎上,高職院校和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充分協商和溝通形成產教融合的文化認知框架,對產教融合制度產生認同并內化為“我應該這樣做”的行動邏輯認知,形成從政策驅動到文化認同的轉變。
(三)激發校企產教融合的共生意愿:強化實體組織建設實現利益共享
利益訴求是高職院校與企業建立產教共生體的底層邏輯,是高職教育和產業合作的內在驅動力。在滿足雙方利益需求的基礎上,還必須鼓勵高職院校和企業共建實體組織。作為共生性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實踐載體,以實體組織產生的共生體新資源和新能量保障校企雙方共同利益的實現和共享,并以此激發高職院校和企業雙方積極參與產教融合的意愿。
校企產教融合實體組織的建設是實現校企共同利益的關鍵。具體來說,一是建設由大中型企業和高職院校共同出資的產業學院,并且將產業學院建在企業之中而不是建在高職院校之中,這樣高職院校的學生定期到產業學院更可能進行真實工作場景學習;二是政府通過政策調控,擴大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范圍,鼓勵和允許更多的中小企業參與高職教育教學,這些企業不建產業學院,但是接納學生到企業定期進行師徒制方式的實習實訓;三是在高職院校舉辦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二級學院,非產教融合型企業也可以通過參與混合所有制二級學院的形式深度參與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參與專業設置、教學設計、課程嵌入、教材開發等,將職業能力、行業產業標準、崗位要求等融入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這三類實體組織的建立,將高職院校和企業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互利共生,產業和教育互為一體,形成互惠一體化共生的產教融合人才模式。
參 考 文 獻
[1]魏春艷,方益權,衡孝慶.基于知識形態的新工科產教融合機理探究[J].中國高教研究,2022(2):89-94.
[2]聶建強.產教融合:高校知識產權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困境與出路[J].中國大學教學,2023(12):38-45.
[3]沈黎勇,齊書宇,費蘭蘭.高校產教融合背景下人才培育困境化解:基于MIT工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6):146-151.
[4]趙林度.產教融合視域下物流人才培養模式創新[J].中國大學教學,2021(12):18-23.
[5]徐婷.高校產教融合育人模式下的工程技術人才培養——評《應用型高校產科教融合生態系統的研究》[J].中國教育學刊,2022(12):122.
[6]曾孝平,顏芳,曾浩.新時期電子信息類工程人才培養模式探索與實踐[J].中國大學教學,2023(Z1):11-18.
[7]趙子聰.基于協同理論的產教融合工程人才培養模式建構與路徑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2022:28.
[8]AHAMDJIAN V. Symbiosis: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association[M].UniversityPress of New England,1986:10.
[9]任潔.共生理論視角下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研究[J].襄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1):52-54+77.
[10]袁純清.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27.
[11]毛才盛,田原.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產教融合發展路徑:共生理論視角[J].教育發展研究,2019(7):7-12.
[12]趙國強.共生理論視域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路徑研究[J].河北企業,2019(2):77-78.
[13]洪黎民.共生概念發展的歷史、現狀及展望[J].中國微生態學雜志,1996(4):50-54.
[14]王湘蓉,孫智明,王楠,等.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大型問卷調查報告[J].教育家,2021(17):7-23.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Cao Yanmin, Wang Meng, Li Xingzhou
Abstract Deepen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s a key focus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Using the theory of symbiosi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issues in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mismatch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entities in the school-enterprise symbiotic unit, weak support and constraint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ies on enterprises, low social recognition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mutually beneficia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By analyzing the symbiotic unit, symbiotic model and symbiotic environ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the symbiotic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it. The practical paths of this model include: establishing a shared goal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promoting the generation of new energy through resources interaction; governing the symbiotic environmen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promoting the conscious actions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imulating the willingness for symbiosis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o achieve shared benefits.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uthor Cao Yanmin, PhD candidat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Shijiazhua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Beijing 100875); Wang Meng, PhD candidat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hando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Foreign Affairs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Xingzhou,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作者簡介
曹艷敏(1974- ),女,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石家莊工程職業學院科技處處長,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組織人力資源管理,職業教育管理(北京,100875);王萌(1974- ),女,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博士研究生,山東外事職業大學教育質量評估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職業教育管理
通訊作者
李興洲(1965- ),男,北京師范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教授,研究方向:職業教育基本理論、職業教育與鄉村振興(北京,100875)
基金項目
河北省2023年度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河北省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動力機制研究”(20230205081),主持人:曹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