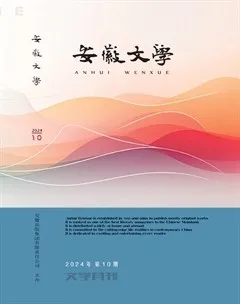為虎作倀
一
老宅已不復存在。深草掩蓋了拆除的蠻橫,半塌的土墻搖搖欲墜,只有柚子樹全然不理會周圍的寂寥,落了一地黃色的臺灣柚。曾祖母在世時,每談起這座老屋,都帶著尖酸的挖苦,仿佛這是她苦難的見證。但在死前,她卻一直念叨著老宅后院的柚子樹。我望著車窗外被荒藤落葉覆蓋的廢園,不知道她見了會有何感想。
上山的車絡繹不絕,人們都盼望著討個好彩頭。好不容易找到一處空閑的車位,大殿里已人滿為患。往日誦經的早課取消,僧人們記錄著香和蓮花燈的數目。四處縈繞著白煙,氤氳在人之間的是鼎沸的聲響。照例是一盞蓮花燈,三根香。先前由我的壓歲錢交付,待我畢業之后,便由我這個小輩出面購買,以求家庭和順。
母親已經將花茶泡好了。父親一手端托,一手掂蓋,輕輕地拂了拂,蓋與碗發出清脆的聲響,抿一口,放下。我照做。表妹剛睡醒,口渴,端起碗一飲而盡。叔父瞪了她一眼,又轉頭夸贊我。父親搖了搖頭:“這孩子前幾年也是這樣。現在總算省事了。”他們又談起昨日的團年,搜腸刮肚回想一嘴帶過的人名。父親追憶歲月時,我便去幫母親燒水。寺里只有小壺,一桌人喝一輪便需要重燒。鐵壺發出輕微的爆裂聲,煤氣的火光,像一朵卷曲的藍菊花。母親搭了一塊毛巾在端把,坐在小木凳上看視頻。我讓媽進屋坐,她倒說我沒有陪好長輩。鐵壺吐出最后一口白氣,劇烈的噗噗聲消失后只聽見隔壁房中的寒暄。母親怨我連續三年考公失利,在學校教書也沒有拿到編制,我自然知道這是她的心里話。大概是等得太久,母親的手都凍僵了,一哆嗦,剩下的小半壺開水便澆到了母親的鞋面和褲腳上。洇染出的水跡,看上去像老人尿了褲子。所幸冬天穿得厚實,水僅浸濕了加絨外褲。
“大過年的,”母親罵道,“真是晦氣。”
我讓母親到車上換條褲子,她說,風一吹便干了。父親在屋內詢問水燒好了沒,母親高聲應道燒好了。我攔住母親,叫她趕緊的,先去換褲子。母親愣了片刻,說:“你和你的父親倒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她的話像一顆生硬的石子,打在我的心口。
將鐵壺里的水摻入溫水瓶中,拎進屋,不知道他們還要聊多久,便又回到齋廚里重新燒了一壺。剩菜盛在塑料盒里,敞放在木桌上。昨夜是滿桌的紅火。東坡肘子、紅燒魚、辣子雞……一盤盤肉菜上桌,服務員如同街頭雜技人,腳不沾地,穿梭在圓桌之間。椅子還沒有坐熱,便被父親拎起來到鄰桌敬酒,敬了一輪,剛吃兩夾菜,又有親戚領著小孩來敬酒。敬來敬去,推杯換盞,接二連三的咣當聲響起,像是廚房里母親操弄鍋碗瓢盆的聲音。
他們談論不景氣的股市,自家的孽子,別家的好,似乎這便是最佳的下酒菜。嘴巴說干,暫時歇氣時,便聊起了去世的曾祖母。他們記起她喜歡吃紅星路的兔頭,還有鹽市口的蕎麥面,講起她從前的壞脾氣,都一笑而過,全當作值得緬懷的趣事。曾祖母在世時,眾人都需要看她的臉色。她當了半輩子的小腳媳婦,丈夫咳嗽一聲都忍不住發抖。所幸丈夫早死,家中兒孫眾多,她便找回了閨中小姐的脾氣,稍有不順心的事情便呼天搶地,幾家的兒媳婦都躲著她。爺爺是長男,自然接下了照顧她的擔子。眾人這才舒心,紛紛說這是莫大的福氣,一家子人,承歡膝下。
曾祖母在世的最后半年里,她徹底無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起初,她還會因為尿了自己一身而羞愧不已,別過臉罵我,到后來,已是麻木地被我托起屁股,擦拭下體。一個月的護工費要三千,家里的房貸沒有還清,家里人都咬著牙,不愿落得不孝的壞名聲。奶奶說,自己當了一輩子窩囊兒媳,現在婆子媽卻是這副模樣,她連半分怨恨都生不出了,也怪傷心的。她不由分說地把所有事情推給了我。于是,我上班前給曾祖母墊一張尿不濕,到了晚上再取下。
眾人口中那個親切的曾祖母太過陌生,我無法參與談話,只能在旁桌啃兔頭。我將兔頭掰成兩半,拔出它的舌,這舌腌得極其入味,又含住上半部分,吮吸它的腦花。旁邊年幼的孩子已經坐不住,嚷著拿過手機,在父輩的交談中玩“王者榮耀”,問候隊友的祖宗八輩。表妹問我玩嗎,我說:“之前會玩,現在已經手生了。”表妹嫌惡地看了我一眼,說:“你還不如坐到那桌去。”我笑,聽著表妹毫無顧忌的話,想象很多年后他們的模樣。叔父說,兒時,父親可是爬樹的高手,能爬到樹梢摘最紅的李子,膽子大,半夜帶著生產隊的孩子看鬼火,進城工作后人才變得板正起來。父親笑著和他碰了碰酒杯,說:“人老了,不比當時。”他又轉過來教育我,說我吃不得苦,要是他有我這樣的條件,肯定干出一番事業。我只能點頭,因為我也不知道,同歲的父親究竟是怎樣的。
他們吃倦了,呷一口酒,又開始抽煙。媳婦都讓自家丈夫少抽一些,他們板起臉,讓她們不要說掃興的話,一年到頭一大家子只能聚這么一回。表叔多次叮囑我,給曾祖母燒紙錢時記得帶好酒,在墳頭上灑一圈。我說:“還要帶兔頭。”他連聲附和道:“對,對,對。”大家喝得盡興,便生出了平日里沒有的好心,合計著明日一起為老人家上香。父親不無夸耀地說,自己每年都到寺里拜一拜,不求佛保佑,但求心安。眾人皆說,這才是真正的悟。
父親總說我沒有悟透,所以才想東想西,平添煩惱。
在寺里短暫住過的居士養了幾缸荷花,正放在住所前的空地,現在只剩下枯瘦的荷梗立在幽綠的死水之上。缸中生了綠藻,見水面有漣漪閃過,我湊近一看,竟瞧見其中生了一群銀灰色的魚苗。漣漪漸漸大了,抬頭,發現天空飄起了小雨。
“嗡”的一聲悶響,古鐘敲響。鐵壺的聲音趨為平靜,水開了。
二
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名士馬拯攜仆冶游瀟湘,遇一古寺,推門而入。寺中有一老僧,長眉修髯,皓然勝雪,修為精湛,邀馬拯入室喝茶。二人相談甚歡。老僧說山居鹽酪用罄,馬拯遂令其仆下山購買。少頃,老僧與仆皆不見人影。山徑上有一隱士,入舍歇息。隱士說,方才上山時望見有虎食人,食盡人肉,竟變為一老僧。話畢,老僧踏入云屋,合十問好。馬拯見其須上沾血,惺惺作態,恐其變虎食人,遂依其行事。當晚,馬拯與隱士歇宿偏堂。子夜時分,虎嘯大作,幸二人早有防備。天亮,老僧溫言叩門,邀二人圍爐烹茶。馬拯與隱士合力將老僧倒掀至井中。二人分刮財物,下山而去。遇一獵人,邀暫住。二人應允。
深更,云氣氤氳間現出人形,又唱又跳,或男、或女、或僧、或道,齊口大喊:“他們殺了和尚,又要殺將軍!”少頃,白額大虎至。獵人執弩箭,直貫虎心。而虎倀又至,如喪考妣,齊聲哀號:“誰人又殺我將軍?”馬拯破口暴喝:“無知野鬼,為虎所殺,反哭元兇!”倀絮言良久,如煙消散。三人齊聲大笑,歡然而別。
兒時上山時曾聽方丈講過這個傳奇,聽起來像是盜版的聊齋,一連幾日做夢,都見著白霧狀的野鬼。我問,倀究竟是什么。父親說,你需要悟。他曾經在五歲時被方丈摸頂,以保佑此生平安,于是每年初一都來寺里還愿。寺隱于崇州西北群山之麓,共一座大殿、兩座偏殿、一口古鐘。鐘旁有一樹環抱古碑,現在已經完全不見古碑的蹤影,只有木瘤上掛著的牌子寫著:樹抱碑。相傳那碑由蜀王朱椿題字,至今已沒有記載。如今,講傳奇的方丈已經圓寂,舍利子放在大殿的后方。我已經忘卻了他的模樣,只記得他偶爾摘下土黃色僧帽后光溜的腦袋。他喜歡吃老面饅頭,愛到后山摘茼蒿菜,煮一大鍋分給前來上香的旅客。八十年代第一次重修古寺,他從自個兒腰包里掏錢。可惜錢不多,只重修了供奉金像的大殿。2003年,一個虧了幾千萬的房地產商來寺里祈福,剛到寺里,便接到電話,一個制藥商買了三幢房屋,于是轉虧為盈。房地產商大喜,向寺里捐了一大筆錢,重修古寺,連那口古鐘都置在了新建的亭中。后來他又經歷了金融危機,雖說也到寺里求佛保佑,但古寺并沒有顯靈。兩個月后,他宣布破產。
這個故事時常被后來的僧人說起,來寺里求清閑的居士也稱古寺為風水寶地,但他們都隱去了后半段。父親曾是房地產商的員工,當年分得了一套房,便記得完整的故事。但父親從未向他人說起,在寺里碰見僧人向居士介紹古寺時,只是一笑而過。偶爾聽到親友抱怨不順,他也會讓他人上山,來古寺里拜一拜。
半年前,曾祖母去世前,我們正在寺里燒香。這自然是父親的主意。醫院打來電話,通知曾祖母在剛才走了。她中Dq1Ik1zLLvUlhw9PWE2+0f3f/ZTC8XPG6aSn5Jy1Y1E=途清醒了片刻,交代護士立遺囑。遺囑只有寥寥幾字,說將所有從閨房帶出的東西留給我。眾人都清點過家中的遺物,彼此心知肚明,遺物不過是一袋線裝書和一塊玉鐲,于是沒有異議,只道曾祖母疼我,又囑咐我年年來寺里燒香,不要辜負了她的心意。我聽著寺里的鐘聲,覺得佛突然伸出赤腳,踹了我一下。
曾祖母說,自己看見了倀。我將此事說給父親聽,他思量一陣,只讓我不要亂講。我記起方丈講述的傳奇,竭力回想那時的答案,卻只記得父親讓我參悟。我問寺里的僧人,倀是什么。他們驚詫地望著我,又問倀字是哪一個。我說,為虎作倀。他們恍然大悟,說,便是那行壞事的替死鬼。說罷,他們又看向我,似乎在疑惑我為什么會突然提起這個故事。方丈的回答絕不是這一個,但我依舊點點頭,解釋道,這是老人家的疑問。僧人夸我孝心可嘉,又說我自有福相。我持香深叩,長久地伏在蒲團之上,來壓住內心的酸澀。我決非他們口中的孝子,也不愿意像旁人那般,將家庭時刻含在嘴中,再掉幾滴眼淚。對于曾祖母,我是恨的,但似乎也不是在恨她。大多數時候,我都坐在一旁,而她躺在床上。聽見她咳嗽,我便倒水;每隔一個小時,拿來便盆,扶她坐下,然后將屎尿倒掉,等待母親和我輪班。
我、母親、奶奶,我們總是按照這個順序輪換。
曾祖母是一位講究的老太太,未出嫁前是重慶造船廠富商的女兒,結婚之后隨丈夫到了四川閬中。出嫁時無比風光,嫁妝是十根金條,光是咖啡的杯具便帶了足足五套。可惜到了六十年代,家道中落,大部分的首飾都典賣出去,只余下一塊成色不好的玉鐲子。金條如今在何處,子子孫孫都說不清楚,只在佛像前盼望老人家回光返照,造福后人。
年輕時,她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最困難的日子也是如此。年過八十,醫生說,她不能再喝了,家里人便沖一杯,讓她聞氣味。要現磨的,速溶咖啡會挨得一頓好罵。我將磨好的咖啡粉倒入濾杯中,壓平,倒入燒開的熱水,兩分鐘后,再將咖啡杯放在她的鼻下。這氣味似乎是她的命數,她短暫地睜開眼睛,問,是阿煥嗎?阿煥是爺爺的乳名,有時候,她也會叫父親。我一遍遍地告訴她,我不是,但她始終沒有記住。父親說,她老糊涂了,讓我不要放在心上。但她分明知道,我不是她的孫子。她總是用咳嗽命令我。
上山前一晚,我將磨好的咖啡粉帶到醫院,在開水房的藥味和消毒水的氣味里沖了最后一杯咖啡。例行公事地放在她的鼻下,忍耐著半分鐘的流逝。我以為她再也不會睜眼了。忽然,她握住了我的手,插著針頭的手掌顫抖著。
她說:“我看見了倀。”
我將玻璃杯放到一邊,反握住她的手,輕輕放在病床上。在我小時候,她時常講一些奇怪的故事,人們都說她得了失心病。父親只叫我聽著。她重復著,虎吃人,人變鬼。等我年齡稍長,才從書中讀到,那替死鬼便是倀。《山海經》中記載,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壘,主閱領萬鬼。害惡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老虎吃鬼,天命注定,但難以飽腹,遂馴鬼為倀,以人為食。倀助紂為虐,雖為虎食,卻心甘情愿為虎尋覓食物。世人不解,遂有為虎作倀之說。這大概和老方丈講述的傳奇是一個東西。
我環視著病房。這里除了我和曾祖母,并無其他活物。
“你瘋了。”我告訴她。
她的眼睛瞪得極大,混濁的眼珠轉動著,像是泥潭里不斷陷落的石子,我幾乎能聽見細微的嘎吱聲。我慌忙起身,想叫醫生進來查看。她不知從何處生出了氣力,在病床上拼命掙扎。手胡亂揮,腳使勁蹬,語無倫次喊著“母親”,又扭向一旁,哭得像個孩子。她的腳比我的巴掌還小,身體蜷縮,似乎正遭受著滅頂的疼痛。她又張開身子,每根手指都向外伸,竭力想抓住些什么,像一張瀕臨斷裂的弓。我曾見過她的無數張臉,也曾在深夜里替她摳痰時想過——倘若我的手繞住她纖弱的脖頸,明天怕是會輕松些許。
但當我直面她的衰老,卻只覺得惶恐。
玻璃杯被掃到地上,碎了。她用手心擦去臉頰上的淚水,又用手指去擦眼角的淚水,呼吸漸漸平歇,語氣也變得和緩起來,似乎認出了我,輕聲呼喚著——敏兒,敏兒。我一聲聲回答著她。她如同一枚孱弱的葉片,眼睛緊閉,又忽地睜開,惴惴不安地握著我的手,確認著我的存在。最后,在閉上眼睛之前,她哆嗦著說:“對不起。”
我怔愣了一會,才蹲下身收拾玻璃片。我無從得知,她究竟看見了什么才如此驚惶。在玻璃杯舉起又放下的半刻鐘里,她是如此害怕。
古鐘敲響了,沉重的聲響在寺里回蕩,似乎永遠不會停歇。母親叫我拿票打齋飯。菜照例是茄子燴四季豆、蒸南瓜、炒油麥菜和青菜湯。眾人各自放下票,拿一碗,尋一空位坐下。父親問我早上去哪里了,怎么不見人影。我低垂著頭,只說自己思念曾祖母,于是在后院走了一圈。親戚夸:“不像我家那討債鬼,你們家的孩子就是來還情的,孝順,又讀得書,將來肯定很有出息。”母親笑著說:“孩子只會死讀書,現在工作編制都沒有拿到。”父親更是連連搖頭,說我不穩重,再夸幾句尾巴都要翹到天上去。
他們又談論起我的婚事。見我神色不快,母親連忙按住我的肩,附在耳邊說:“大家都是關心你才這么說的。”我心里依舊不樂意,不愿自己像是砧板上的豬肉,被人指點議價。父親投來一瞥,我便噓了聲。表妹羞憤地看著我,似乎比我這個當事人還要著急。我安撫地沖她笑笑,她倒是火冒三丈地站起來,說:“不吃了。”表叔吼了一聲,沒用,于是連連搖頭:“這孩子。”表嬸說:“得好好教一番,這性子結婚后指定要吃不少虧。”母親接話,說:“我們家這孩子也是,性子比一頭牛還倔。”我聽不慣母親在外一味謙虛,甚至到了貶低我的程度,不知她只是口頭上說,還是心底便是這般想的。或許是后者吧。她向來不喜歡我的性格,總教我要顯得拙笨一些,才能好好生活下去。我不信,和她爭辯幾番后發現無法改變她的觀念,便漸漸變得沉默。她始終是我的母親,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我也學會了和外人一起,笑話她時不時鬧出的錯誤。她在笑聲里大笑,似乎她天生便是這般愚笨。
齋飯的時間結束了,鐘聲顫巍巍地在古寺里響起。父親笑道,這敲鐘的僧人怕是剛才沒有吃飽飯。大家都一同笑起來。我卻覺得,這鐘聲比重復的撞擊聲好聽。
三
我主動提出,去尋表妹。父親滿意地點點頭,又讓我教育表妹幾句。偏殿供奉著送子觀音,這兩年上香的人已經漸少了。表妹見我,扭頭就走,朝另一個地方去了。我追上去,主動邀她到潭邊走走。她滿不在乎地說:“那個小石潭有什么看頭。”我說:“心誠則靈。”她笑了,挖苦道:“你還不如買一只招財貓回去。”院中飄浮著冷冷的氣,陽光穿過竹林,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影。石桌石凳都泛著白光,殘損的石碑臥在草叢之中。將草撥開,才發現碑下是一只神龜。赑屃,龍之九子之六子,用以馱碑。我摸了摸它的頭,青苔上還殘余著沒有消散的露珠。我讓表妹也來摸,據說觸碰它可以帶來好運。她說:“老古董。”
“怎么又惹你生氣了?”我只當她在耍小性子。她憤憤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竟帶著憐憫,支支吾吾半天,只道我這幾年的書白讀了,還沒有之前腦袋清醒。我心里門兒清,畢竟我也是從那個歲數過來的,心里不免多了幾分惆悵,但面上仍在笑,又問她怎么個白讀法。她被我問急了,大吼:“你怎么和父母一個模子里刻出來,只知道教育我!”說罷,她便跑了,背影很是倉皇,只留下我愣怔在原地。
“又是一年了。”門檻邊的老人冷不丁說道。
想著剛才的家事被老人看在眼里,我不由臉紅,只能應道:“又是一年。”老人十幾年前便在這里了,負責打掃和看管偏殿,性格古怪,但和我倒聊得投機,也算得上相熟。平日里沒有什么人來,他便抄讀四大名著。他沒有剃度,卻和其他僧人同吃同住,每天清晨和晚間都在大殿里念誦,膝蓋處打上了重疊的補丁。他說,自己是舍不掉山腳下的那口烤鴨才遲遲不肯皈依的。所以,每年上山時,我都會給他帶半只色澤油潤的脆皮鴨。他摸出兩個杯子,斟滿,自顧自地碰杯,嘴唇一噘,便是一塊吮得精光的骨頭。據說,他是一個富商,年輕時干了不少胡鬧事,老了便到寺里誦經燒香,以求心安。前年他的兒子來寺里鬧過一回,惹出了不小的動靜,最后捐了一筆錢才平息了寺里的喧囂。他究竟犯了什么過錯,無人知曉。每當有人向寺里的僧人問起,就連看房門的都支支吾吾。父親遠遠地瞧他一眼,便躲開了。于是每年,我都到偏殿求清凈。
酒是好酒,香醇,但是并不辣嘴;鴨是土鴨,極入味,又有嚼勁,能撕成細條,放入嘴中反復吮吸。旁邊的一口枯井沒了。我小時候喜歡趴在青磚上往井中丟石子,聽枯葉柔軟的顫動。某年和表妹一起看了鬼故事,兩人害怕從古井中爬出長發女鬼,都不敢靠近,你戳我推,還嘴硬道,并不可怕,最后撒腿就跑,不愿意在此多待。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紅磚色的涼亭,漆色尚新,在這灰撲撲的庭院中,又嶄新又蒼老。
老人又枯瘦了一些,身上散發著劣質墨水的味道,眼窩深陷下去,像緩慢沉落的地基。我問:“又開始抄經文了?”他搖了搖頭,稱自己沒有毅力,只是寫著玩罷了。他曾經抄了八十回《紅樓夢》,《水滸傳》寫到第二十三回,便合書睡覺。一連睡了兩日,醒來之后便下山,提著一只烤鴨和一瓶紅星二鍋頭,在偏殿喝得大醉。僧人拿他也沒有法子,只求他在來往的香客前嘴巴嚴實,不要破壞了祈福的靈氣。
《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是他最喜歡的故事,每年我上山,他都要講一回,當作烤鴨的謝禮。我推托不過,又覺得貿然闖入了他的清閑之地,便當作租金,耐著性子聽他講那武松打虎。“只見那武松舉起哨棒,運足力氣,騎在虎背之上,左手揪頭,右手猛擊,直將那吊睛白額的大蟲打得鮮血淋漓,一命嗚呼。”說到盡興之處,他不免手舞足蹈。我笑道:“幸好武都頭沒有遇見倀,否則就成了虎口中的一塊酒糟排骨了。”他的手中還拿著鴨腿,問我:“怎么突然說起這物來了?”我正愁心里堵得不舒服,便將曾祖母去世前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若有所思,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猛地將杯子扔在石階上,摔得粉碎。我被嚇了一跳,以為自己勾起了他的傷心事,連聲說道:“這都是大半年前的事情了。”
我幫老人收拾殘局,他說不用,又把瓷片和另一只完好的酒杯揣入了兜里。老人見我手上戴著玉鐲,隨口問:“戴了幾年?”我說:“剛好三年。”他笑:“這可不是你們年輕人喜歡的玩意。”我說:“但求心靜。”他笑得胡子都吹起來了:“你一個小姑娘,求心靜做什么,這都是要入土的老人家該做的事。”我告訴他,自己三年前曾經在大殿鬧過一回事,之后便一直戴著。老人一頓,說自己想明白了,又低聲感慨:“原來是你呀!”
那時也是大年初一,曾祖母尚未糊涂,還說得動話,稍有不稱她心意的事便將他人罵得狗血淋頭。我沒有在上海找到工作,剛大學畢業,又沒有積蓄,于是回到家鄉打拼,和父母同住,照顧曾祖母的責任再次落到了我的頭上。大學四年已經讓我習慣了都市的生活。早上七點便擁擠的道路,總是“難產”的城市,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又淡漠的聯系。剛回家的幾個月里,我苦不堪言,不熟悉的工作崗位,并不信服我的學生,說一不二的父輩,總是向我抱怨的母親和奶奶,都讓我迫切地想要逃離這個家庭。
上山的時候很冷。霧靄之中,初升的太陽都帶著冷意,腳步自然就慢下來。待到廟里的時候,其他親戚已經到齊了。曾祖母被兩個當地人用滑竿抬上來,二表姑邀功似的替老人家端上熱茶,四表叔將輪椅展開,將曾祖母抱上軟墊。父親惱怒地瞪了我和母親一眼,又連忙推著輪椅往大殿里去了。早課已經開始。十幾號人低聲念誦,氣象莊嚴,佛像下的香爐升起裊裊的白煙。我凍得手腳哆嗦,只顧著將雙手焐在袖口之中,又昏昏沉沉,打著哈欠。待念經結束,曾祖母被父親推著先出大殿。路過我時,她用指節敲了敲輪椅的扶手,見我沒有理會,又皺起眉,用膝上的拐杖重重打了我一下,神色不耐煩地吩咐道:“咖啡。”她如此理直氣壯,仿佛我生來便是要替她端茶倒水,我竟口不擇言:“想聞你自個兒倒去。”父親立刻大喝,又低頭向曾祖母賠不是,說我還沒有睡清醒。眾親戚瞧了,手忙腳亂地勸架,紛紛讓我道個不是。一見他們狗模狗樣,我便氣不打一處來,吼道:“值錢的東西早沒了,你們眼巴巴討好也沒用,什么都沒了!”我又指向曾祖母微怔的臉,帶著惡毒的喜悅,笑說:“老不死的東西,只會在別人身上出氣。”
眾人都愣在原地,就連收拾蒲墊的僧人見了,也退到了一邊去。直到父親大喝一聲,將我的名字吼得擲地有聲,他們才如夢初醒,羞憤地指責我,罵我怎么想法如此齷齪。我被眾人團團圍住,一時唾沫橫飛。混亂之中,我看見曾祖母的神色,她是如此震驚和受傷,仿佛第一天正眼瞧見我這個曾孫女,微張著嘴,手緊緊攥住領口。我帶著勝利的喜悅,將佛像前的供臺推翻在地。香爐里的香灰和香全撒在了地上,瓜果撒落一地,蘋果骨碌碌地滾到了輪椅邊。曾祖母盯著我,抿著嘴,忽地哭了。她用手心擦去臉頰上的淚水,又用手指去擦眼角的淚水。但是眾人都被突如其來的巨響所震住,沒人注意到她突然間的落淚。
僧人忙不迭地跑來,一口一個佛祖保佑。父親面上掛不住,于是又買了兩個蓮花燈,供奉在佛像前。下山之后,他把我叫到房中,本以為免不了一頓責罵,誰知道他竟給了我一個玉鐲,讓我時刻戴在身上。在頭頂冰冷又斑駁的白光下,他鄭重其事地說:“辛苦你了,孩子。”隨即他又皺起眉,說這是你應該做的,不應該對家里人充滿怨恨。
似乎是從那天起,曾祖母開始老糊涂。她漸漸忘卻了兒子和孫子的姓名,父親看望她時也不會清醒,但每當我將咖啡放在她鼻下時,她都會短暫地睜開眼睛,問道:“是敏兒嗎?”我從沒有回答。她或許是想轉世投個好胎,才在死前裝作一個良善的老太太;抑或是擔心死后沒有人給她燒紙錢,所以又記起了我這個曾孫女。我和她從沒有心平氣和地交談過,她所有的故事,我都是從父輩口中得知。每當看見她一動不動地躺在病床上時,我都在恍惚間看見了很多年后的自己——我也正在死去。
那口頑固的古鐘又響了起來。竹林簌簌回響,幽長不絕。群鳥驚飛,寺里似乎又來了新客。不斷有人上山祈福,以求此生平安。老人說,他要去睡了。不是午休,也不是晚睡,他似乎陷入了一種昏昏然的狀態里。我向他告別,不知道明年上山,他是否還在那里。
“倀,”他驀地說道,“人也。”
“倀,人也。”我重復著這句話。
我依舊想不起來,方丈在講述傳奇時究竟給了怎樣一個答案。父親總是讓我去悟,但是他的參悟似乎不是我所想的那個。我想起曾祖母留給我的一袋線裝書,其上字跡規整,一筆一畫。在最后一頁,她寫道:“東西都留在柚子樹下。”
車繞著彎曲的山路向下行駛。天空是一種奇妙的灰藍色,在重重的樹林中閃現。老宅早已不見蹤影,野草茂密,土墻上的青苔一點點增長。柚子樹上還懸著幾只柚子,樹下是滿地的深黃。車子正在遠去,我再也聽不見沉悶的古鐘,只聽見山林間的鳥鳴。不知道曾祖母在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否是這樣的聲響。我正在下山,明年的今日,我將會再次上山。
責任編輯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