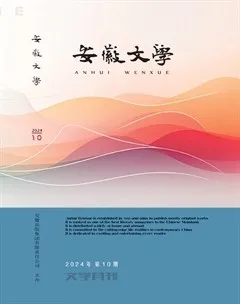胡楊戀
一
存于世間,我們總會與這個世界上的一些事物形成牽絆。一些神秘而又復雜的機緣使其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獨特存在。胡楊,這一種樹木,是我在這世間諸多關切之一。我想你一定熟悉很多樹,比如楊柳、松柏、梧桐、銀杏、國槐、桑、竹、梅、桃,還有桂樹、香樟、榕樹等。畢竟我們生活在草木中國,一個有著漫長的農耕文明的國度。樹木不僅構筑了我們生存的家園,還影響著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的思維方式,形塑了我們的語言,表征我們理想的模樣。
已是近二十年前,我研究生畢業(yè),來塔里木大學工作,和愛人坐著火車,從祖國的東部到西部,一路見證了從草木葳蕤、滿目蒼翠到遍地荒涼、寸草不生的變化,在走過遼闊的戈壁灘之后我才真正體悟到綠色的可貴,意識到有樹的地方才有人家。那一抹綠啊,是生命的顏色。那一棵棵樹,標識了我們人類生存的界限。在西部,在新疆,在這戈壁荒漠上,樹木以其卓然的姿態(tài),衛(wèi)兵的模樣,讓我不得不向它投注敬仰的目光,成為我參悟的對象。
二
第一次“見”胡楊是在2006年的國慶假期,那時我來新疆也不過一個多月。我們迫不及待地一起騎自行車去看地理書里存在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我想去看沙漠,卻意外地邂逅了胡楊。它就一棵一棵孤立在大漠的邊緣,每一棵駐守著一個土丘,那么孤獨,那么滄桑,我才從同事口中得知它的名字叫胡楊。后來我發(fā)現,在學校的道路兩旁,就長著高高大大的胡楊。原來所謂的“初見”,其實已經有著許多次的擦肩而過了。真正見識胡楊之美則要等到那年的十一月初。因為愛人在阿克蘇帶學生實習,我趁周末搭車去與他相會。開車的是胡師傅,很巧,他也姓胡,四川人,妻子是兒科醫(yī)生,工作比較忙,他選擇跑車,時間相對自由,能夠照顧家。那天已近中午,胡師傅連早餐都還沒有吃,他是從阿克蘇開車先送客人來阿拉爾的。他問我吃過飯沒有,說:“現在只有你一個人,還要再等三個人,趁現在的時間我們去吃個抓飯吧?我請你。”我再三推辭,讓他自己去就可以,他卻不肯,說不能把客人單獨留下。我最終還是陪他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抓飯。后來,在去阿克蘇的路上,大地像著了火,金色的胡楊如詩似畫,撲面而來,讓我震撼,沉醉。
此后,只要有機會,我每年都會去看胡楊。第二年,女兒出生才兩個多月,系里組織一起去胡楊林采風,我和愛人抱著女兒也一起跑去了。我看到不同時間的胡楊。春天的那抹新綠碧如翡翠搖蕩我的心;夏天脫了鞋子,把腳伸進沙子里,坐在它的綠蔭下,享受酷暑中的這一方陰涼;秋天,在一片金色中,我感受它的通透、壯麗、崇高、輝煌;而在dYG2EAvffgZg4sg3ArlgzMX37ycw/Lem3ZvhumTQN94=冬天,我觸摸它的枯寂,震驚于它的空靈、純凈,那是有霧凇的日子,那是落雪的日子。我看活著的胡楊,也看那些枯死的胡楊。睡胡楊谷,在它們死亡的睡眠里可有安詳?我分明聽見千軍萬馬不屈的吶喊。魔鬼林,置身其中,能夠感到陰風颯颯,那是一番地獄的模樣,有魔鬼的狂笑,靈魂的哭泣……
人們說胡楊“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三千歲的胡楊讓我看到自己的渺小。而作為一個物種,它更是長壽。作為白堊紀——古第三紀時期的荒漠河岸孑遺物種,新疆庫車千佛洞和甘肅敦煌的化石證明,胡楊距今已有6500萬年的生長史。在漸新世末—中新世初,這種華夏植物區(qū)原產的樹種從東向西遷移,已成為中亞河谷林的重要樹木。它經歷了生存環(huán)境的劇烈變遷。原本它所生活的塔里木盆地乃一片古地中海,空氣濕潤、水源充足,生態(tài)環(huán)境良好,但在地質作用下,海水退卻,大漠生成,氣候干旱,環(huán)境日益惡化,很多物種被淘汰,胡楊卻迎著如刀似刃的沙脊在這死亡之海生存了下來。“塔克拉瑪干”就這樣成了“胡楊的家園”,胡楊以其頑強和堅韌令我敬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終身學習”思想指導下,界定二十一世紀社會公民必備的基本素質,認為主要包括四大支柱: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合作、學會做人。胡楊可謂是變化中尋求生存的典范。
作為“活著的化石樹”,它見證了海陸變遷,度過了冰川時代,而今更是面臨著生存環(huán)境進一步惡化的考驗。為了活下來它作出了哪些改變呢?首先,胡楊又被稱為是“異葉楊”或“變葉楊”。這是因為其幼樹與成年樹在葉片形狀上有明顯不同,而且同一株成年樹樹冠上部和下部枝條上的葉形也明顯不同。在幼樹或嫩枝以及樹冠下部枝條上的葉子呈線狀披針形,狹長猶如柳葉,平滑光澤,可以減少水分蒸發(fā),隨著成長向上,胡楊樹葉也逐漸鋪展,變成卵形、腎形、扇形、心形……同一株樹可以有七八種以上形狀。為了減少水分蒸發(fā),胡楊葉面呈現蠟質化,而且從幼樹到成樹,葉子的顏色也會從幼樹樹葉的翠綠色逐漸變?yōu)槌蓸錁涔谏喜康幕揖G色,因此,胡楊有時也被稱作灰楊。同時在水分充足時胡楊會枝葉繁茂,舒展大方,色澤鮮亮,而在天氣干旱時,則少長枝葉,細小疏落,收縮枝葉以度時日。這就是我初見胡楊它并未讓我驚艷的原因。其次,胡楊還有著發(fā)達的會找水的根系。主根最深可達地下百余米,而側根及水平根系則向四周擴展,密如蛛網,遇到有水的濕土以后,就會頑強地向那里發(fā)展,一株胡楊樹根系可以擴大到數十平方米以上。胡楊的根能夠聞到水、嗅到水,跟著水走,荒漠里哪里有水胡楊就會跟到哪里,哪里有胡楊就證明哪里曾經有河水流過,而且其根部、莖部細胞還有很強的貯水能力,與駱駝相似,在吸飽了水分以后,即使斷絕了水源,它也能正常生存一段時間。而在水分充足時,胡楊還可以長出不定根以防洪水浸泡。再次,胡楊具有靈活多變的繁殖方式。胡楊兼有有性的種子繁殖和無性的根蘗繁殖兩種繁殖方式。胡楊種子又多又輕,大約在7—9月成熟,正值天氣炎熱、河水漫溢時節(jié),大量帶有冠毛的種子隨風隨水飄散到兩岸的河漫灘上、積水湖泊的淺灘上、潮濕的干溝底部和農業(yè)區(qū)輸水渠道邊坡水線上等,在6小時內即可生根發(fā)芽,快速生長,第二年便可以站穩(wěn)腳跟,不怕大風吹襲。同時,胡楊又常靠根蘗串生,形成“一棵胡楊一大片”的奇觀,灌溉、挖溝、斷根等方式常促使蘗苗大量繁殖。更有趣的是,胡楊本為雌雄異株樹木,但在一些罕見情況下,竟然在雄花序中夾雜著幾朵雌花,或雌花序中夾雜著幾朵雄花或夾有兩性花,為了生存、繁衍,胡楊之變真可謂令人瞠目結舌。
胡楊既獨立又會合作共處。作為綠洲河岸林中的高大落葉喬木,它是維護荒漠河岸林生態(tài)平衡的植物、動物和微生物有機組合的生態(tài)關鍵種(key species)。它與檉柳、沙棗、駱駝刺、梭梭、甘草、蘆葦、羅布麻等許多植物伴生,與野兔、野雞、野豬、野駱駝、馬鹿、黃羊、狐貍、鵝喉羚、小鳥、猛禽等上百種野生動物以及數不清的微生物共生,更不要提胡楊為我們人類提供了生存棲息的家園。胡楊與所有這些動植物、微生物以及荒漠、河流構成了一個生命共同體,一個和諧美麗的大家庭。
胡楊懂得奉獻,甘于奉獻。據統計,我國現有胡楊林面積占全球胡楊林總面積的61%以上,而塔里木河流域分布的胡楊林面積約占我國現有胡楊林面積的91.1%。從胡楊在我國境內的分布來看,無論是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還是新疆廣大地區(qū),都是我國國境意義上的邊疆地區(qū),尤其是新疆,是名副其實的祖國邊疆。胡楊扎根在我國邊疆環(huán)境最惡劣的地方,與孤寂為伴,不慕繁華,抵御風沙,默默奉獻,只為給大漠戈壁披上綠裝,點燃生命的希望。胡楊不僅在這死亡之海的邊緣創(chuàng)造了一方綠洲,守護了萬千生靈,成就了無用之大用,而且它全身都是寶。其木質堅硬,耐潮抗腐,是上等的建筑和家具用材,可以用來建房子,做搖籃,修墓地,制作面盆、板凳、桌子、床、馬車和捕魚用的獨木舟——“卡盆船”等一應生活用品。據說,胡楊木在發(fā)音上還具有獨到的作用,是制作一流小提琴的首選木材。此外,胡楊木料、樹枝還可以用來取暖、烤肉,胡楊的葉子被稱作“空中草場”,營養(yǎng)價值很高,是喂養(yǎng)牲畜的優(yōu)良飼料。胡楊的根可以驅蟲,花可以外用止血。胡楊淚,即胡楊堿,清熱解毒,主治咽喉腫痛、胃痛、胃酸過多,還可以用來發(fā)面、制肥皂、熟皮子,因為它具有良好的脫脂、脫膠作用……在傳統社會,胡楊全方位融入了西部人民的生活,從出生到死亡,從日常生活到精神信仰。
胡楊之于華夏文明的構建長期以來并未被重視,它蔭庇了古西域廣大地區(qū),守護了絲綢之路,而今更是為處身于現代社會中忙碌、焦慮、內卷的人們提供精神療愈,為我們社會文化的發(fā)展指引方向。昆侖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根,華夏文明的精神之源。《山海經》中記載的早期昆侖神話,包含著許多奇異的動植物,貫穿著靈物崇拜觀念,是原始宗教的載體。欒木、珠樹、文玉樹、玗琪樹等都是不死樹,扶桑、若木、建木等更是宇宙樹,是溝通天地的媒介,人神交往的天梯。張騫是第一位在昆侖山地區(qū)做長途旅行的知名探險家。從大月氏返回中原的途中,他沿著當時被人稱作“南山”的昆侖山北麓自西向東行進了一兩千公里,在回到長安以后,將自己的見聞報告給漢武帝。后來西漢的使者多次經過這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史記·大宛列傳》)這里的河為黃河,漢武帝將于闐河(今和田河)確定為黃河之源,其發(fā)源之山為昆侖山。而這里也同時是胡楊的故鄉(xiāng)。雖無史料,但可以確定胡楊曾經陪伴過張騫,陪伴過班超、甘英、玄奘……
胡楊,在我國古稱“胡桐”,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多蒹葭、檉柳、胡桐、白草。”《水經注》《本草綱目》等對其均有記載。“胡桐”之名,還出現于我國眾多醫(yī)藥典籍中,有“胡桐淚(律)”或“梧桐淚(律)”的說法。我國河西走廊以西地區(qū)也稱胡桐為梧桐,而“律”為“淚”俗語的訛稱。“胡桐淚”即“胡桐樹脂”,在唐代傳入內地,具有治療毒熱的功用,或作為焊接金銀器焊劑之用。此外,敦煌文獻還載有“梧桐餅”,即以“胡桐淚”和面所制成的餅。“胡桐”之稱沿用至20世紀50年代,當時我國科學工作者對新疆進行大規(guī)模科學綜合考察,確定胡桐屬楊柳科楊樹屬,遂改稱為“胡楊”。古人之所以將“胡楊”稱為“胡桐”,王守春教授認為“胡桐”一詞可能是由意譯和音譯這兩種命名方式結合而產生。其“桐”字可能是音譯而來,古代漢族人取“Tohlak”(胡楊的維吾爾語名稱,意為“最美麗的樹”)一詞的第一音節(jié)“To”,再加以鼻音化,變?yōu)椤癟ong”,取漢字中帶“木”旁的“桐”作為對音,再在前面加上“胡”字以示西域物產。但我們可以看到胡楊樹無論是其花序還是葉片形狀、大小都與楊柳科樹木更為接近,而與內地的梧桐樹在外在形態(tài)上差別巨大,這不得不讓我思考胡桐與梧桐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發(fā)現,它們都是一種高貴而又神圣的樹,一種具有高潔品格的樹,一種能夠吸引金鳳凰——那些具有赤子之心、精忠報國的熱血兒女的樹。能夠表達孤獨、傷感、懷念、思戀等復雜情感的樹,能夠彈奏美妙動聽音樂的樹。如此看來,命名為“胡桐”在文化上、情感上是極為貼切的。對那些無論因為何種原因漂泊異鄉(xiāng)的游子,在這一片戈壁大漠中見到“胡桐”,就是到家了,它帶來歸屬感、安穩(wěn)感。家在擴大,延伸,不再流散。而改名為“胡楊”,無疑,更為科學準確,它代表著我國融入現代世界秩序的努力,更具平民性,在繼承傳統楊柳審美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出更積極昂揚的楊樹審美文化。
而對于那些自古以來就生活在西域的少數民族同胞,胡楊就更是他們的家園,它的確就是最美麗的樹。羅布泊孕育了樓蘭,他們以粗大的胡楊制成獨木舟,以挖空的胡楊木做葬具,而在樓蘭被沙漠埋葬后,也是零星可見的胡楊木材殘片在告訴人們樓蘭的存在。尼雅是受尼雅河滋養(yǎng),胡楊林孕育,由胡楊木構筑于沙海中的一方文明,有用一根胡楊木做成的獨木橋,有完全以胡楊木搭建的房屋,“那是一處中外考古學家公認的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木結構城市遺址”(徐剛《大森林》)。在第482號木牘佉盧文書中記載:“活樹嚴禁砍伐,違者罰馬一匹;如砍伐活樹樹杈,則罰母牛一頭。”這可以說是兩千年前我國最早的森林法。這些曾經被胡楊樹滋養(yǎng)、守護的古國消失了,我們可能無法準確地知曉導致它們消失的原因,但我們知道它們的存在一定和胡楊有關。試想,如果沒有胡楊,在西部尤其是塔里木盆地這一片干旱少雨的土地上是否還能夠有人類生存?是否還能有西域廣大地區(qū)的繁盛?還能有絲綢之路上東西方之間的商貿往還?也許依舊會存在,但是可提供給人類活動的空間一定大大縮減,生存的困難程度一定會大大增加。
胡楊見證著絲綢之路或者玉帛之路的繁華,守護著生存于這一方土地上的人們,給他們帶去生命的蔭庇,情感的慰藉,溝通著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文化,給人們帶來精神上的激勵、鼓舞與信仰。胡楊分布地域廣闊,在歐、亞、非大陸都有天然林存在,集中于中亞、西亞和地中海區(qū)域。據說1801年法國的一位植物學家在幼發(fā)拉底河岸邊發(fā)現了這種長著既像楊樹又像柳樹不同葉子的樹,以幼發(fā)拉底河的名稱定其拉丁學名為Populus euphratica(幼發(fā)拉底楊)。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對它有過記載。《圣經·詩篇》第137節(jié)提到了一種樹,有的翻譯為柳樹,但問題是巴比倫沒有柳樹,這一誤會據說源于近代植物分類學家林奈,他誤將胡楊視為垂柳了,準確的翻譯應該是:“我們坐在巴比倫河畔/一想起錫安就禁不住哭了/在河邊的胡楊上/我們把豎琴掛了起來。”胡楊是一種屬于世界的樹,它可以成為溝通中外文化尤其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文化、情感的橋梁。
胡楊還可以給今天快節(jié)奏生活下嚴重內卷、心靈焦躁的人們以綠蔭。它一方面因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不斷因時因勢而變,努力生長;另一方面,卻又安時處順、窮通自樂、逍遙自得。任世界滄桑巨變,它固守著自己的領地,不慕繁華,不問甘苦,以世界上最為荒涼的大漠戈壁為家。安守物候節(jié)律,從容面對四季流轉。胡楊是安靜而沉穩(wěn)的,每年春天,世界已經花紅柳綠,蜂舞蝶繞,直到3月底胡楊方始萌芽,直到5月葉片才真正展開,搖動那一片翠綠。胡楊是先花后葉植物,胡楊花低調而內斂,雄花序多為紫紅色,雌花序則兼有紫紅色和黃綠色兩種,在一片灰黃的環(huán)境中透著一點點生命的驕傲和尊貴。雄花先開,雌花繼之,以沙漠戈壁4月底5月初的狂風為媒,孕育生命的種子。夏天腳下的土地在燃燒,頭頂的烈日在炙烤,胡楊頂著一樹碧葉經受生命的考驗。8月胡楊種子成熟,從開花到種子成熟長達150余天,是楊屬植物中花果物候期最長的樹種。花期和春汛基本吻合,種子散布期和秋汛完全吻合。胡楊的生長、開花、散葉、結實……無不應和著周圍的環(huán)境,與風與水與陽光密切相關,積極進取卻又平和從容。
人們熱愛胡楊,受著胡楊精神的鼓舞,既愛它扎根大地的奮斗精神、奉獻精神、創(chuàng)造精神、和合精神,也愛它擁抱天空的超拔精神、夢想精神。一棵棵胡楊就是荒漠里的一簇簇泉,一根根火炬,一座座豐碑。胡楊給了在荒蕪中行走的人們以慰藉,在沒有生命沒有人煙的大漠戈壁,看見了胡楊就看見了希望;胡楊點燃了人們的夢想,它驅散大地的荒涼,在十月金秋讓世界如詩如畫,堅守值得,等待值得;胡楊傲岸,挺拔,張揚,不屈,即便死去,也不改鐵骨錚錚,曾經活過,曾經奮斗過,曾經抗爭過,曾經輝煌過……胡楊是生命的大寫者,詮釋者,它創(chuàng)造了生命的傳奇,書寫著生命的神話,張揚著崇高壯麗的夢想精神。胡楊的夢想是自我成就、自我實現的夢想,是智慧通透、空靈自由的夢想,是綠色中國、綠色地球的夢想,是多元共生、繁榮昌盛的夢想……
三
追根溯源,何以會戀上胡楊?也許是因為我是一個從鄉(xiāng)村走出來的小女孩,在兒時就喜歡徜徉林間,在那里摘野花野果,捉知了猴,在樹蔭下讀書……林子總讓我感覺自由而又快樂,那是一個靜謐而又生機勃勃的空間;也許是因為我受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我們是借草木鳥獸俯仰天地,觀照自我,陶冶性情,達成物我感應,精神融通;也許是因為我竟然因為種種機緣,今生有幸,生活在這塔克拉瑪干邊緣,從教于王震將軍創(chuàng)辦的這所大學——塔里木大學。而這是一所從胡楊林中成長起來的綜合性大學,他提出要“用胡楊精神育人,為興疆固邊服務”,我在這里持續(xù)受著一代代如胡楊一般為興疆固邊事業(yè)作出貢獻的人們的感染……我在對“胡楊精神”的思考中,重新回到胡楊樹的身邊,重新看到這種樹,看到和這種樹生活在一起的人,看到這種樹在我們華夏文明中的地位,看到這種樹在中華文化產生、發(fā)展中的作用與貢獻,看到它帶給我們的生命的指引和社會發(fā)展的啟示。我們需要回到源頭,在那生生不息的豐沛與活力中感受它給我們的浸潤。置身在林間,感受這一樹木帶給我們的希望與力量。
胡楊曾經以“胡桐”的姿態(tài)立于祖國的邊疆,參與著華夏文明的宏大敘事。作為一種文化樹種,它與我國屯墾戍邊事業(yè)的發(fā)展息息相關,張揚著理想主義的精神內核與價值訴求。大約是在1909年,晚清政壇碩儒宋伯魯在赴伊犁途經精河托多克胡楊林時寫下《托多克道中戲作胡桐行》:“君不見額琳之北古道旁,胡桐萬樹連天長。交柯接葉萬靈藏,掀天踔地紛低昂。”作為戊戌維新變法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宋伯魯在變法失敗后四處流亡,幸得伊犁將軍長庚賞識,請他赴伊犁做幕僚。宋伯魯所描繪的胡楊林,是一個類似于陶淵明的桃花源,卻更具原始生命力,能夠容納萬物,具有革新叛逆精神的空間。我們從他對胡楊的描繪中能夠感受到宋伯魯雖然生活在沒落的晚清,壯志未酬,生活落魄,卻依舊不失大儒風范,其胸襟氣度,樂觀曠達,令人欽佩;其縱橫天地、探索宇宙的豪情,對真理和信仰的執(zhí)著追求,均不失為我輩楷模。宋伯魯開我國文學中胡楊書寫之先河,他讓胡楊加入了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大合唱,發(fā)出它的豪邁之音,低沉而又婉轉的喧響。
而在新中國成立后,胡楊才真正得以被“看見”,被書寫,從《三棵胡楊樹下》到《大森林》,從《胡楊英雄樹》到《我和胡楊的約定》,從《胡楊蕭蕭》《胡楊淚》到《山前該有一棵樹》……胡楊樹成為許許多多像胡師傅一樣勤勞而又善良的人的精神寄托,給他們帶來情感上的撫慰與激勵,召喚著他們在逆境中奮勇拼搏,用自己的雙手去建設自己的美好家園,成就一個高大、蓬勃、絢麗的夢想。新世紀以來,我國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均盛贊胡楊精神,他們將胡楊視為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精神的象征,互助團結的象征。扎根,挺立,傲然,從一棵樹到一片林,胡楊終于從歷史的背景走到了歷史的前臺。
胡楊表征的是一種理想人格,它是隱士,是英雄,是歷經滄桑而初心不改的智者,是偉丈夫,也是美嬌娘,它兼具“雌雄同體”,變化萬千。它將離別的鄉(xiāng)愁化為安靜自處、康健有為的怡然自得。它是見證者,參與者,也是召喚者。它見證邊疆的落寞與繁華,戰(zhàn)爭與和平,迷失與回歸。它參與著家園的建構與解體,歷史的述說與沉默,召喚著希望與夢想。它是中華民族精神在西部邊疆的呈現,執(zhí)著頑強,風華絕代。
然而,對胡楊的高歌贊頌卻沒能使它避免淚灑沙海的悲劇,它身軀的高大有用卻時常為它招來斧斤之禍。盲目地毀林開荒、截源斷流、過度采伐、放牧等,導致胡楊林面積銳減。據新疆林業(yè)勘察設計院調查,塔里木盆地胡楊林總面積,1958年為780萬畝,1978年減少到420萬畝,二十年間減少了46%。今年5月的一場暴風雨更是讓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胡楊的脆弱,一棵一棵大樹在我面前倒下,原來大漠英雄樹也不耐狂風,它也會被吹倒,被折斷,被摧毀。太過干旱,它也會枯死。也會畏懼蟲害,疾病……胡楊立在大漠的邊緣給人類以守護,也同樣需要人類給它以保護。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大漠胡楊相得益彰,成就西部的壯美。大漠因胡楊的存在而更顯浩瀚壯闊,絢麗輝煌;胡楊賦予大漠以生動的靈魂,挺拔向上的力量。人類學家摩爾根說:“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搖籃,世界文化的鑰匙遺失在了塔克拉瑪干,找到這把鑰匙,世界文化的大門便打開了。”這把鑰匙會是胡楊樹嗎?會和胡楊樹有關嗎?無論如何,伴隨著森林旅游、樹木療愈、休閑文化的興起,她正召喚著我們,就如小時候母親呼喚我們的乳名,喊我們回家。
責任編輯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