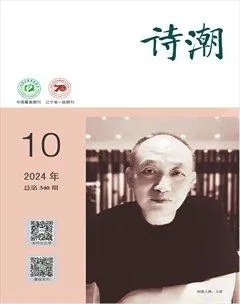一種抵達極限之境的擊打力
在反復閱讀凸凹的詩歌后,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他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詩人嗎?簡單化地將一個著名詩人歸類,恐怕是不太嚴謹的,但他詩歌厚重而硬朗的在場感和抵達感,那種擊打人心的力度,又一再加持我的這一印象。凸凹是做到了用真心和生命寫詩的,我設想,如果他不寫詩,也可能會借助其他文字體裁去抒發他的情緒和情感的(事實上他也是著名小說家),但恰好“發現”了詩歌,瞬間他和詩歌語言的對視和唇語,兩者皆被照亮,乃至點燃。他的每一首詩,讓我感覺都不是一時興起寫就的,哪怕是很平凡如“牙膏皮”那件事,如此生活中的小事件卻承載了一個時代的悲喜與辛酸,它就像平常的一張廢紙,上面卻留有他驚顫式體驗的文字。抑或我們可以從詩歌的抒情性方面來討論,可以說凸凹的詩,不是純粹的敘述體,更不是淺顯的抒情體,他的詩是流動的、跳動的,但流動的不是水花,跳動的也不是火焰。外象沉靜的內部,是激越和焦黃,這是我們能體味到的,即他用生命體驗生命,用呼吸體驗呼吸,用心跳體驗心跳。由此,可以下結論的是:他是真寫詩,寫真詩,他的詩沒有絲毫跟風造作之嫌,也不是圖消遣或發泄,而是有一種歷史責任感,時代鼓點的催使,或語言之魔附著于身的靈光乍現和諸多機緣巧合的投射。總之,他的詩彰顯時代,拒絕頹廢,內質沉實,情感豐盈。
我閱讀了凸凹自1986年以來不同時期的代表作,總體觀感,他的情緒一如既往地沉靜,絕少因激奮而產生嘶啞式的破音,他詩歌的語言敘述方式不拘一格,乃至他的“變化”也不是呈線性規律的,你會發現有不同風格間的橫跳,但又不是徘徊式的,他始終在追求“抵達”一種“極限之境”,即用最少的字、最佳的節律感,最能呈現表達空間的構筑。所以,凸凹大量的詩歌中沒有“重復感”。一種情緒或發現,他說過了,寫成詩了,就讓這首詩成為一個坐標,就如一棵樹占據了森林中的一個位置,而且每一棵樹形態各異。當然,某種體察可能會有分期式遞進的表達,但總體上他的詩,沒有形成自我的“詩歌詞典”,詩中的意象或細節也都是唯一的,他是他自己的“瓦解”和“重建”。這可能與他豐富的人生閱歷相關,他沒有如很多詩人那般因各自相對固定的生存空間的影響,而將自己“定位”于某一區域,從而形成自己“取之不竭”的題材庫或精神王國。凸凹的精神世界是繽紛萬象的,或光怪陸離的,也是遷移、流轉與幻變中的,也許這也是他的每一首詩都能讓人為之驚艷,每一個句子都像是第一次讀到的原因。當然我這么說,并非否認凸凹詩歌毫無個人風格,他的“個性”,我覺得更多地還是體現在詩歌精神境界的無限拓進和語言的精確“狠勁”上,當然由此去辨識他的詩歌又有些困難,因為他是不確定的。比如他的《天上的人》組詩中,寫給若干詩人、名人或親人的,除了人物的不同,每一首詩的敘述方式,也都是“量身定制”的,不得不令人嘆服,不可否認,詩人想把每一個悼念中的人“寫活”,他做到了。如寫給詩人傅天琳的《檸檬黃了》,“檸檬”:“最酸的黃/最香的黃/最美的黃/最誠實的黃/——最好的黃”,濃縮于檸檬,并聚焦于檸檬的“黃”,多么純粹的立意和抵達!寫給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放牧詩》,如歌如泣,層層推進延展,自成陡峭、拐彎和圓潤:“水稻的共和國/你發明了亞當,又發明了夏娃/一粒水稻的開天辟地/一茬一茬過來,一茬一茬過去/你的一直在增加又/總比水稻少一粒的同類/在來去之間,有了來去”,這首詩有奇突的抵達人心的力,那么銳利,又那么舒心。我認為,凸凹完成一首詩歌,也完成了他自己,但還不一定令他滿意,他追求的是更接近邊界的抵達,而非某種完整性。那么,請問他抵達了嗎?從讀者這里看,他已抵達,但詩人或許仍心有不甘。
凸凹詩歌切入的角度“刁鉆”而精準,有點狠,但又不失雅致和風度,同時推進得穩妥而細膩,可靠又神奇,并將詩一步步推向高遠。他詩歌的切入點一開始并不總讓人驚嘆,但隨著文字的推進,你會驚呼妙哉。如《最怕》這首詩,寫的是男女朦朧初戀的情節:“最怕和哥在山上/在山上也無妨/最怕飄來偏東雨/飄來偏東雨也無妨/最怕附近有巖洞/附近有巖洞也無妨/最怕哥拉妹子鉆進去/哥拉妹子鉆進去也無妨/最怕燃起一堆柴火/燃起一堆柴火也無妨啊/千萬千萬莫要妹子烤衣裳”,他沒有寫情感的火焰,而是寫火烤衣裳,一切合情合理。詩人寫母親的《去火車站,或凌晨接母》,就是一首切入后迅速旋飛的節奏,步步驚心又荒誕,讀畢又承認生活就該是這樣子的,整首詩一氣呵成,由不得讀者去作“理性”推斷,所以凸凹詩所形成的一種“邏輯”或“氣場”,又有些攝人心魄而迷人。我注意到,詩人很注重詩歌“頭三句”的力量,力求一下就“逮”住你,而且一首詩的“起跑”決定了后續的旋轉速度和力度,既能讓整首詩的氣息貫穿始終,又保持著自然開合的姿態:“凌晨五時,母親,我來了,站在你面前/你看見的,不是北站夜燈的眩影,不是/三分之一:這會兒,母親,我是你全部——/全部的小,全部的大……”再如《母說,或家史》,一上來就是:“外爺,一支從未謀面的槍/響了整整一下午,打死的/是外爺自己。”讀者會情不自禁地往下讀,從而“陷”得越深,但詩歌語言的自然散裂,并非一種刻意的埋設或“引人上鉤”,他始終是真誠的,也是真實的,幻化的是語言,由語言自身的開闊性與自由飛行和碰撞,如宇空,才能產生真正的光亮或深淵,還是這首詩,當我讀到:“歐洲自行車外圈/五十年代革命路,左右卷舌,莫名打旋/耳朵問題是一輩子的問題,聲音的膽子/在耳障中閃電、打雷、轉彎,成為/高調與危塔”時,感到母親及至親的切膚況味是具體的,也是真實的,同時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真實或人類之痛,因而凸凹詩歌切開的是一個“入口”,而后續的遞進與打開,方能呈現人與存在更大的格局。這一點其實是很重要的,凸凹總是精心地將小人物和小事件構成時代的“微雕”,從細微處體托出大格局——無非是詩歌語言實踐中,具體與抽象、局部與天下、個人與群體、現實與虛幻間,對詩人事關命運和生命的關注和釋解力的考驗。正如這首詩中的“家史”,也是“民族史”或“人類史”,這首詩也會超越時代,對更遠闊的時空負責,如詩的結尾:“中間一直是中間/愛情、操心、跳塘未遂”。再如《蚯蚓之舞》,更是“以小博大”的范例,蚯蚓可算是天下最柔弱細小的生命體了,但它也能“驚天動地”,首先我得嘆服詩人的“選材”,二是他選定的生活中“排它”的力,三是蚯蚓的格局折射出的生命關懷:“蚯蚓的舞/排開土、排開大地∥蚯蚓的舞/排開地獄,和亡靈∥為了這天塌地陷的柔柔的一舞/蚯蚓把體內的骨頭也排了出去”。
讀凸凹詩的時候,時常也會想到一首詩在他內心的醞釀過程,是否也會有一個預設的高度和遼闊?答案應是否定的。正如前述,他有話要說,恰好想起了詩歌,并無靠一首詩的面世給自身增值的打算,如他的題材,非常寬泛,了無計劃,仿佛存乎于機緣。我想問:他寫詩時,會不會忘了自己正在寫詩呢?詩人在創作時,不可能太清醒,也不會太昏沉,而是一種“忘乎所以”和混沌“狂放”,并無清晰的“功利心”。他內心要抵達的,服從于一腔情緒和渾然天成的語言功力,而這也是不自覺的;正是這種“不自覺”,讀者也才能不自覺被一首詩所驚魂攝魄。比如在讀《沱江十七行》的時候,就感覺到了詩人當時的心境恰如一江之水的翻滾和混濁,水里的影子和浪花的喧響。詩人遇山水而想起家國和父母,并非志氣崇高,而是一個文人,在那一刻自然的心跳和呼吸。我想,如果秉持的不是“平常心”,那么一首詩的功效就不是完成自己,而是成就另一番事業,就偏移詩歌之魂了。詩中的“聽過太多的聲音/最好聽的,是母親的聲音/從未見過外爺、外婆/夜深人靜,我在聲音里看見了他們//他們,還有卵石和魚/一聲不吭,在聲音里咚咚走動/河水分走兩岸,向山上爬去”,這樣的句子,甚至連寫好了會發表于某刊也不會想的。
凸凹的詩歌,因其純粹和“真”,已然成為對文本高度自治的詩人,無欲則剛,有容乃大,我認為,這種與詩歌“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是對詩歌的敬畏和尊重。再來看《大河》這首詩,大河是無名的,也是抽象的,甚至寫的也不是“水”,而是“血”,我相信詩人寫這首詩時,肯定沒有被一條具體的河流感動,而是生活中的另一條河,橫亙于面前,身在其中,隨波逐流,但詩人并不想刻意“抬高”這條河,或歌贊,或詛咒,只能接受它,害怕它,又擺脫不了它——因為它就是命運自身,誰能跳脫開呢?詩中寫道:“這條大河,我不知道它從哪里來/還到不到哪里去。而那個黃昏的場景/不僅在夜晚,甚至白天,都會不時出現/仿佛一個夢魘,一種幻象,大得不流動/只有那水的聲音,日夜轟鳴、咆哮、讓我驚怵”,或許有讀者會認為這首詩荒誕不經,但我認為,他寫了最真的“真實”,只不過他用了最簡單的體驗和認知,最自然的呼吸和良心。
要說一說凸凹詩歌細節或意象的力量。敘述需要有質量的情境和細節,是客觀的,但又應是精心挑選的。虛假的或夸張的,過于抒情的并被賦予主觀定性的細節,一定是無效的。細節即詩歌的內核,因細節8luhQadNdCZGnQcwoY5Rb3+KljRWfGSlR4xyVH1edc4=和意象的生動可以省卻“抒情”,由讀者自己去作出不盡相同的體味。凸凹詩歌中的細節僅僅是坦陳,哪怕有些“欲言又止”,但絕對實在。他所敘述的人和事很平常,但卻勾勒出人性化的活劇。詩人寫患病的父親的《送行詩》,沒有大呼小叫和涕淚滂沱,卻撼人心扉,靠的也是由細節所架構的意象的閃爍。詩中對父親形象的刻畫,是具體的,又是詩性的:“一閃而過的風,刀子樣/將窗外的物事割脫了形/像細胞、化療,將一個人的尊嚴/打成鬼,又打成人——就是不打成/我少年鏡中的原形”,詩人在表達一種真實,還不如說是在表達一種誠懇,或文學性的自我觀照。詩歌中的細節或意象可能有所指涉,也可能是人生經驗中的痛苦或夢想,但有必要將之變形,更有感染力和思考力,或賦予平凡的細節以靈魂。凸凹作為一個詩人,一邊潛心于專業創作,一邊理解生活,同時用詩歌將他捕獲的經驗進行提純和分類,使之具備了寓言化的效果——包括那些讀起來顯得荒誕的情節。從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一窺詩人既平凡又獨特的人生歷練,比如曾在國家“大三線”十幾年的工作,使他比大多數人多出另類神秘體驗,必然也會影響到詩中細節的表達,一種“變形”后的不同時空并現交疊的意象呈現,但真實仍是它們的“底料”。歷史、現實、冷靜表象下的焦慮和預感,是凸凹詩歌細節排布的主要方式,如《釘子與墻》這首詩,布景極簡,但寓意深刻,細節只有一面墻和無數的釘子,至為關鍵的是:詩人的不信邪和墻面就是釘不了釘子的現實:“我相信/僅僅是為了叫我相信/這面墻才讓所有的釘子彎曲”,我無意推導這首詩的指涉,越簡單的詩往往越缺乏明確的答案,反而可能是永久的疑惑和追問,這首詩類似于哲學質詢式的探險,但它又不是哲學詩。從這首詩看,當“我”舉起第一枚釘子時,應是滿懷快樂遐想的,從第N顆釘子開始,直至最后一顆,詩人的心態是純粹的,即相信總會有一顆會釘上去,遺憾的是一顆也釘不了——細節和意象雖簡單,或重復,但每一顆釘子彎曲的過程,難道不是一種思考力的遞進嗎?詩的開頭與結尾有關系,也沒有太大關系,是“我”的思考被織入其中,并一步步如花朵最后綻放。凸凹詩的意象組合,經常以一個怪異的現象開頭,然后由此順藤摸瓜般取得奇異之果,或他是用心靈的體驗布下的“迷魂陣”。我很少從他詩中讀到憂郁無助的句子,即便是驚懼,也坦然承認并接受,然后很快回歸于鎮定;他的詩中也極少有青春般騷動不安的詞,即便是很早期的詩,也已顯示豁達式的大氣和“無所謂”,仿佛早已對人生日常和注定命運有了認識;他的很多詩中有一種“緩慢”跳動的節奏,指向明確的未來,或回歸源頭,而當下尚在霧中,如《石達開之死,或凌遲的東大街》,那一刀接一刀,共“一百多刀的時間/打開秘宮,又被拖進更大的/秘宮”,這個“秘宮”是不可測的,只是最后的一塊活肉落下才會見分曉——又是可測的;再如《我》這首詩,“我”有多面性,存在各種可能,偶然一點推力或拉力,或誰多事戳破某一層紙,“我”就是另一個樣子,詩中的“我”,也可能是“我們”,只不過凸凹坦然陳述而其他人心懷惴惴,但我更相信詩中的某些細節,同時發生在凸凹身上的可靠性,這實際上也是他慢慢長大、老去的一個過程,每一步都有未知難測,每一天都同時身馭生與死,這首詩的結尾實際回歸人類的源頭:“如果把體內的那些個我喊出來/世界就成了汪洋/如果把體內的那些個女人喊出來/我就成了全人類”。
不可忽視凸凹詩歌獨特的精神氣息是其主要的辨識路徑。
凸凹是有“脾氣”的,或有態度的,但這一點并非每一個詩人都做得到,或意識得到。要命的是,這種氣息的生成大體與生活中的詩人是同一的,而不能出現兩種氣質。說到這兒,幾乎可以肯定,詩歌的“個性”源自詩人的天性或人生煉獄后的磨難,裝是裝不出來的。很多讀者在讀凸凹的時候,很容易被詩中的“狠勁”和憤憤然所感染,但我感覺凸凹的詩與那些被憤怒情緒所統攝的詩人,是完全或根本不同的。凸凹詩歌中的“憤懣”幾乎介于澄明透徹和郁積牽慮之間,詩人骨血里的正直、仗義和善良,也都是同步展現于精神層面,他的詩有一種“霸氣”,并不霸道,源于他對人類的深切關懷和一種大格局的追求,或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執拗和堅執,他的“沖動”方式就是“放任”語言的突圍,力求從被稱為日常的生活中,剔出多出來的部分,再加以追根溯源,責任與使命的擔負與預設——我在想,詩人面對的也許是一塊堅石頑壁,他能怎么樣呢?當然最終他建立了自我詩歌情感的可靠,以及文本的價值,這就夠了。正如詩歌《我》中寫的:“記得在心紙上寫過反標,又撕碎,點火焚去”,生活于那個年代的少年詩人大多干過這種事,與詩人成年后乃至老去后所表現的,都屬于一種情況:在詩歌中取得勝利,或妥協,絕不是哀傷。《一列火車可以打多少把菜刀詩》是凸凹詩歌的代表作之一,對這首詩太過隨意或太淺顯地解讀,都可能誤讀詩人。把一列火車和菜刀并列于詩,這本身就如螺絲釘炒大白菜,極難相牽連,更難出詩意,問題卻在于上火車不能攜刀的規定,引發了詩人的思考:菜刀可以切人,而人也可以傷人——這首詩最關鍵的還不是菜刀,而是“坐在火車上,又突然有一種感覺/那是坐在刀鞘中的安泰”,即每個人只要時機成熟,都可能是一把刀,混跡并為害人間。詩人在此表達的,是對社會現象的憂慮,但凝聚在一把菜刀上,或破舊的火車皮可以打成多少把菜刀上,卻是一道難解之題。
凸凹對詩歌本身的看法,有更系統的論述,他在《詩論》中寫道:“每行詩都是一條鞭子打人/好的詩只一鞭頂多三鞭就解決問題/問題是讀者的七寸大多長在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首詩中能滲透出詩人的什么氣息呢?這源自詩人對自我內心的辨別和對讀者投射力的關注,強大的自信和定力,以及個體寫作主張的堅持,做自我統攝的“王”,這既是詩人的“野心”,也是一個大詩人必備的素質——如湯養宗所言:“一個詩人的寫作指認就是自己的美學范疇。”同時凸凹期待“一鞭子”“頂多三鞭”解決問題,既是一種美學追求,也是詩性需求,即擊打力的精準和簡約,但這是很難做到的,問題就在于讀者的“七寸”變化莫測,或如神授般的擊打力,可遇而不可求,如命中十環的靶心,是來回多次晃動的結果,所幸多是來自運氣,而非實力或勤奮。所以凸凹這三句詩的“詩論”,確實道出了一個成熟詩人的追求和困厄,就這首詩而言,他已成功,擊中天下詩人的痛點。凸凹作為我敬重的前輩詩人,他的很多詩章深深“打擊”了我,而且是一鞭子,至多三鞭子令我拍案叫絕,期待他持續發力,寫出更多更好的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