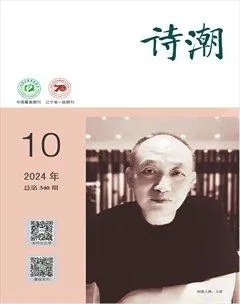韓東寫作的會心會意
一
“寫得跟真的一樣。”
新購韓東兩本小說集,《狼蹤》一點一點讀完了;《幽暗》推薦給兒子,以為他不讀,結果開學時他塞進行李箱,拿走了。寒假回來,問他讀了沒有,說是讀了。問他感覺咋樣,他給我說了開頭這一句。
對于沒經過文學作品閱讀和寫作熏陶因而缺乏經驗的兒子來說,這一句,也許最為真實地表達了他的感受。
小說,本是虛構,韓東的小說,似更不以我們常說的“故事”見長,那么這“真”,也許就是一種近乎直覺的評價。
而此前,以一個資深讀者的身份,我曾寫下過這樣一段話:韓東的小說、散文、詩歌中,經常會出現一些相同、相近的細節或情節。這與博爾赫斯的互文有所不同。這些相同或相近,不斷強化讀者對韓東寫作“真實性”的印象。尤其當這些細節、情節在他的小說中出現,認知中小說原本應有的虛構性,沒有減弱,反而強化了“真實性”。這很奇怪,又很迷人。讀著讀著,會覺得一個作家的寫作,無論哪種文體,無論如何變化,用以支撐的精神底色和生命質地,始終是一樣的。而這,也可能“控制”并在經意不經意間形成一個作家的寫作方向。
兩相對照,我不由得產生一種驚異感。或者說,這是韓東創造的另一種《奇跡》?
不要來反駁我,說此真非彼真。“真”在韓東這兒,與我們藝術中討論的“真與假”,真實與虛構,有相同又有不同。個人約略理解,是一種綜合性的但又無須分析的感覺。有時,我們站在藝術的角度,有時站在現實的角度,有時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兩者之間不停切換或把兩者有意無意進行混同,生出一種我們所謂的“真”。但韓東對“真”,不是在概念中推演,而是在語言和生命構成的作品中體現、呈現和表現。不錯,韓東的“真”,始終未離開藝術的場域,未離開生命和藝術給我們創造的“真”本身。
真,在韓東這兒,是他創造出的一種至高藝術境界。
二
不同文體之間,在重復嗎?材料的單一,或貌似匱乏,以及不斷的出現、閃回,都有可能給人帶來這樣的印象。或許這一點,在比較昌耀和佩索阿時,我早已解除了心結。而不斷的閱讀,讓我意識到,看似“纖弱”的韓東,始終在“挺進”,堅韌不拔,靠近自己心目中“藝術的樣子”。作家就是“匠人”,藝術就是手藝。的確,他和一直畫圣維克多山的塞尚,有得一比。由此,像不主張藝術的“進步”一樣,他也不執著于新的題材會帶來“新的意義”這樣的思維定勢,而是似乎在消除題材本身所謂固定意義強加的影響;所有的題材,在他這兒,每一個都不會輕易放棄,而是試圖“寫透”,正如詩歌《白色的他》;同時,又暗中悄悄打通,各個題材像生命、時間、生活、存在等中“活著”的一部分,一種整體寫作框架和情感(情緒)框架逐步形成,互為焦點與背景,互為主角與配角,互為演員與觀眾。這殊為不易,且很難得。
韓東的寫作,展示了一個作家創造的全過程。克服貌似重復帶來的單調乏味,進入并專注于寫作本身,艱難而又喜悅,充滿挑戰而又奇跡不斷,生命與語言、與作品體現出來的質地奇妙合一,合體。
有朋友說,韓東的詩,可以作為“榜樣”;我知道,他說的并非僅僅是外在的一種樣式,而是一種極少數作家才可修得的寫作精神。
三
“這是什么意思呢?”
小說《兔死狐悲》臨近結尾時,當送走張殿后,隔天“我”來到曾經生活多年的地方,“我”看見“換了打扮”的何嫂,騎著她剛剛逝去的丈夫張殿的摩托、后座帶著他們穿上短裙的女兒畫畫,“輕快無比地”遠去時,不禁問:
離開這里已經很多年,一般我是不來的。統共來過兩次,一次碰見張殿,一次碰見何嫂和張畫畫,這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說,走在人群中,“我流淚了”,“那滴本該由張畫畫流出的淚水,從我的眼睛里流了出來”。
這是“兔死狐悲”的本意嗎?是僅僅在寫類似于“兔死狐悲”這樣一個故事,還是在寫我們共同的“命運”“結局”?也或者,還有更深的,對生命本身的感受和理解?韓東的詩和小說,看起來都很樸素,很簡單,但始終意味“深厚”,一言難盡。
“我沒有家鄉故土,或者文學上的精神家園,死者和離去的人所空出的位置是我所謂的情感源泉,也是寫作所需要的根據。”
當讀到《五萬言》里的這句話時,我停了下來,覺得這句話,也許可以基本概括韓東的寫作。
“死者和離去的人所空出的位置是我所謂的情感源泉”,讓我震撼。翻動閱讀記憶,想想,無論是長篇小說知青三部曲,還是他新近的中短篇,無論是詩集《重新做人》《他們》《奇跡》,還是四十年詩選《悲傷或永生》,韓東確乎是在“空出的位置”開始他的寫作,是填補某種寫作的空白,更是“生命的扎根”“情感的扎根”。
四
那么語言呢,根是否也扎了進去?
西蒙娜·薇依曾說,“話語是用來表達事物關系的”(《重負與神恩》)。如果我們承認,薇依所說的“話語”某種意義上就是語言的話,那么,韓東所說的“詩到語言為止”,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詩就是事物之間的關系,而語言,是用來表達這種關系的。
語言如同另一種事物,當它面對這種關系,其實就構成、生成了它與這些事物之間的一種或多種新的關系。而要與這些事物、事物的關系,處于一個恰切的位置,那么,這個“表達”的過程,必然會有許多與生命個體、觀念等相適宜的手法與技藝。不錯,這個過程,我們說的是由語言發起的創作。
個人理解,韓東選擇了去除語言的文化修辭,弱化甚至拒斥那種夸張的、表層的戲劇性,他讓事物之間的關系,如其所是,也“在”那兒;他的語言,對準“當代生活”,樸素,精確,充滿耐心,一點點抵達他所認為的那個核心,那個“真”。
韓東的《五萬言》,充滿洞見;這些詩學方面的思考,與其作品的高度契合,也同樣在表明,韓東心中對自己的“作品質量”有明確的要求和衡量“標準”。有時候,從朋友圈看到,他在一首首修改詩作,用“及格”等來表明他的滿意度,這不僅是習慣,更是一種態度,并同樣包含寫作精神的不懈實踐。從“空處來”,甚至有時候寫“空”,寫虛無,但從不落于“空洞的空”“空泛的空”。他的寫作很“具體”,依靠的是生命感(生命力)浸潤、融入的細節。這樣的細節,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騎車帶著小女孩——”,讀到這兒時,我停頓了一陣,想到接下來的“情景”,應該在一首詩中出現過。果然,“回頭看了我一眼,眼眸仍然那么清亮”,“已經是春天了”。這是我最近剛讀到的《兔死狐悲》中的細節。
而翻開《路遇》一詩:“她們還要活下去,并且/這就開始活下去。/她一溜煙地騎過去了/一溜煙……”
一樣,又不太一樣。就像,虛無中的真實,真實中的虛無,而“愛真實就像愛虛無”。
他大量寫母親等親人的詩,寫皮蛋等動物的詩,寫生命中出現過的那些人與事的詩,還有那些小說,一筆筆、一字字,都十分細膩、細致,情感上不離尋常而又直指存在和生命深處,客觀,但讓人潸然淚下。他沒有煽情,而是如細雨般,一點點滲透進心的泥土。
換句話說,讀韓東的作品,不要觀念先入;作為一個讀者,若真有所得,“這都是由于用心傾聽/不急于發出自己的聲音”。
五
最早讀到韓東,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了,但那時僅限于《有關大雁塔》,覺得其背后立意,還是在為了反對什么,比如,對文化的過度想象;在韓東這兒,詩就是最真實地切近日常生活與內心感受。是對北島“做一個人”的“英雄觀”的進一步后撤:在詩歌中做一個日常的人(這依然是另一種“英雄”)。而對“詩到語言為止”,覺得詩就是語言表面上的那點意思,無須過度闡釋與解讀。
及至再次斷續讀到,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甲乙》這樣的經典,雖然讀到的時候,不由得想起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空心人》等作品,想起法國自然主義的一些小說,甚至想起“下半身”寫作,但無論是語言控制力、硬度和力量,都絕對一流,令人驚嘆。《這些年》這樣的作品,似乎多了一些歲月和經歷帶來的溫情,可語言上依舊冷靜,“不動聲色”,十分克制;《格里高里單旋律圣歌》與早期的《我聽見杯子》一樣透明純粹,但分明,語言與生命的契合度更為精準,有了新的方向和“語氣”。而《長東西》,可以看出韓東在語言面前的“小心翼翼”,對語言的尊重和對“物”的切近在同時進行,他如同那個扛長東西的人,在不斷地轉換角度、調整方向,旁觀者不知道怎么完成的,但“汗水擦亮的長東西”,“逐漸從深淵中升起”,這幾乎接近寓言和元詩了。
他真的達到了寫詩如說話。他在用說話的語氣敘述一件具體的事,細微的生命感覺、情緒等。
讀不到韓東的那些年,我以為他的寫作中斷了,而正是這“與世隔絕”的“幻覺”與事實,讓人誤以為韓東的寫作是近乎天才般的寫作。當然不是這樣。從韓東的隨筆集中,甚至他的小說中,韓東作為一個作家,常年在不停地寫。那寫讓他對語言有了新的認識,對“物”,對事物之間的關系,對生命和藝術有了新的理解。寫作沒有讓他對語言“疲勞”,而是始終保持對語言的信任。他的寫作,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作品”。
他的作品“就在這里”。
合上他的詩集和小說,合上他的詩學隨筆和散文,如同曾經有過的那樣,我可能會長久離開,尤其作為一個寫作者,害怕過深的沉迷會打亂自有生命節奏下的我的笨拙的腳步。但我知道,我合不上我的心。我的心會時不時穿行于他的文字中,會在讀西蒙娜·薇依時,在讀到真切的生命和匠心時,忍不住從書架上隨意抽出他的一本書,再讀一遍,或一篇,一首,一行,慢慢體味、品咂。
韓東的真,與愛,與手藝,與生命的會心會意,我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