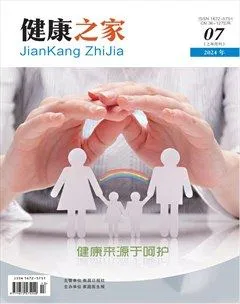子宮內膜癌的靶向藥物治療研究進展
摘要:當前子宮內膜癌對化療藥物的耐藥性問題較為突出,亟需尋找更有效的治療手段。近年來,隨著對子宮內膜癌發病機制、表觀遺傳修飾作用機制以及信號傳導通路研究的不斷深入,靶向藥物為子宮內膜癌臨床治療方案的擬定提供了新思路。主要對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拮抗劑、PD-1/PD-L1抑制劑、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表觀遺傳修飾抑制劑等一系列靶向藥物在子宮內膜癌治療中的研究進展情況展開綜述,為臨床用藥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子宮內膜癌;靶向藥物;PD-1/PD-L1抑制劑;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表觀遺傳修飾抑制劑
子宮內膜癌屬于臨床常見婦科惡性腫瘤,近年來其發病率不斷升高,嚴重威脅女性生命。現階段,臨床上治療子宮內膜癌的手段較多,其中手術切除最為常用,而藥物、放化療屬于輔助治療手段。對部分雌激素依賴型、無生育史的早期患者一般會使用孕激素類藥物給予保守治療,從而有效保留其生育功能;對轉移、復發患者一般除了使用孕激素、芳香化酶抑制劑等藥物外,還會使用卡鉑、多柔比星以及紫杉醇等一系列化療藥物;對晚期患者而言,手術前也需通過適當化療來縮小腫瘤,確保手術切除效果[1]。在此期間,機體對化療藥物的耐藥性屬于亟待解決的問題。近年來,隨著對子宮內膜癌發病機制、表觀遺傳修飾作用機制以及信號傳導通路研究的不斷深入,諸多靶點均已被證實和子宮內膜癌的發生、發展有關,同時相關靶向藥物也成為該病治療的新選擇。
1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拮抗劑
該受體屬于現階段臨床研究較多的一種分子靶點,據統計,全世界范圍內已正式使用的藥物超過20個,包括拉帕替尼、吉非替尼、厄洛替尼以及曲妥珠單抗等[2]。EGFR屬于ErbB受體家族的成員,其子宮內膜癌患者機體內的水平呈異常高表達狀態,且表達量越高通常患者預后越不理想。按照結合位點差異,EGFR拮抗劑有單克隆抗體、絡氨酸激酶抑制劑之分,其中單克隆抗體的代表性藥物為曲妥珠單抗,其對于子宮內膜癌、胃癌等惡性腫瘤的治療效果與安全性仍在研究階段。作為首個上市的靶向單克隆抗體,西妥昔單抗可被應用于非小細胞肺癌、轉移性頭頸癌以及轉移性結直腸癌等惡性腫瘤的治療中。有研究指出,西妥昔單抗對于進展性子宮內膜癌患者的疾病控制率約17%[3]。吉非替尼作為絡氨酸激酶抑制劑的代表性藥物,治療惡性腫瘤不僅可獲得確切療效,且毒副反應較少,患者通常可耐受[4]。
2 PD-1/PD-L1抑制劑
PD-1主要在初級B細胞的表面以及T細胞的表面表達,參與此類細胞的分化與凋亡過程。PD-L1蛋白主要在活化B和T細胞、心肌內皮細胞、抗原提呈細胞、巨噬細胞以及胸腺皮質上皮細胞中表達。PD-1可有效結合腫瘤細胞內PD-L1,對T細胞產生一定抑制作用,發揮抑制抗腫瘤免疫應答的作用。研究發現,PD-1抗體與PD-L1抗體自身均無殺滅癌細胞的能力,主要是通過抑制GVaJWIg0yEI6Y8PXLwPzw7GVDVEjBwRDbsV1Rt2ycQY=PD-1/PD-L1所介導的信號傳導來有效激活T細胞,借助機體免疫系統達到抗腫瘤的目的[5]。有研究指出,PD-1以及PD-L1抗體對于胃癌、肺癌等諸多惡性腫瘤均有一定療效,同時相關不良反應也可借助固醇類藥物進行緩解[6]。
目前,PD-1/PD-L1免疫療法中的常用藥物包括帕博利珠單抗、阿特珠單抗以及納武利尤單抗。研究發現,PD-1抑制劑具有療效持久、安全性良好以及抗癌譜廣等一系列優點,讓很多晚期惡性腫瘤患者看到了治愈的曙光[7]。其中阿特珠單抗作為一種IgG1單克隆抗體,同時也是2016年符合歐盟相關標準的首款抗PD-L1類藥物。有研究指出,其對復發性子宮內膜癌的病情控制率為13%[8]。
3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抑制劑
作為一種具有較高特異性的促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VEGF可通過有效結合其受體來改善內皮細胞的存活、生長等狀態。相關藥物包括阿伯西普、貝伐珠單抗、莫替沙尼、雷珠單抗以及阿西替尼等。其中貝伐珠單抗屬于一種單克隆抗體,可通過與VEGF受體進行結合并有效滅活其生物活性來縮小腫瘤組織微血管,避免新生血管的大量形成,發揮抗腫瘤的作用。該藥屬于現階段臨床治療腎細胞癌、非小細胞肺癌、轉移性結腸癌等惡性腫瘤的常用藥,將其單用于子宮內膜癌患者的治療中也可發揮良好的生物活性。有研究指出,貝伐珠單抗治療子宮內膜癌可讓患者獲得較長的無進展生存期(>6個月)以及總生存期(>10個月)[9]。尼達尼布、西地尼布均屬于VEGF絡氨酸激酶抑制劑,目前已被嘗試應用于子宮內膜癌的治療中。有研究指出,對復發性子宮內膜癌采用西地尼布治療,有1/3左右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超過6個月,總生存期超過1年[10]。也有研究指出,對復發性子宮內膜癌患者使用尼達尼布治療,有超過1/5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超過6個月,總生存期超過10個月[11]。
4 表觀遺傳修飾抑制劑
現階段已上市的表觀遺傳修飾抑制劑包括西達本胺、阿扎胞苷、貝林司他、地西他濱以及貝林司他等。表觀遺傳學屬于一種研究非DNA序列變化所致基因表達改變的學科,表觀遺傳修飾涉及DNA甲基化、非編碼RNA、內含子、基因沉默以及組蛋白修飾等方面,主要調控方式包括DNA甲基化、非編碼RNA以及組蛋白修飾。和遺傳變異存在明顯差異的是,表觀遺傳修飾具有可逆性、動態化等特征,所以表觀遺傳因子極有可能是諸多惡性腫瘤預防和化療增敏的靶點。
總體來說,作為早期診斷子宮內膜癌的有效生物標志物之一,表觀遺傳因子對于該病治療靶點的深入研究存在重要的臨床價值。
4.1 DNA甲基化
研究發現,DNA甲基化與基因沉默、胚胎發育障礙以及X染色體失活等一系列異常現象存在一定關系[12]。DNA甲基化不僅可促使轉錄與轉錄調控因子無法有效結合啟動子,進而造成抗癌基因轉錄沉默,而且還會對原癌基因產生一定激活作用,參與惡性腫瘤患者病情的發生與發展過程。研究發現,CpG島異常超甲基化所引起的轉錄沉默屬于除了基因缺失與突變外的造成抗癌基因失活的主要機制[13]。
DNA甲基化轉移酶與諸多惡性腫瘤發生、發展有關,這也是惡性腫瘤臨床治療與一些新型抗癌藥研發的關鍵性靶點。有研究指出,TMEFF2、CDH13等基因狀態異常甲基化屬于早期診斷子宮內膜癌等惡性腫瘤的潛在性標志物,同時也是臨床治療此類疾病的潛在性靶點[14]。
4.2 組蛋白修飾
組蛋白修飾一方面改變染色質的結構,另一方面也對基因表達產生一定調控作用。組蛋白乙酰化與DNA復制、基因激活等存在一定關系,去乙酰化對抗癌基因轉錄產生抑制作用可提升致癌基因表達量。組蛋白乙酰化修飾主要涉及具有功能拮抗作用的2種酶,即組蛋白去乙酰化酶、組蛋白乙酰基轉移酶,前者產生的去乙酰基化作用可提高核小體結構的緊密性,對基因表達較為不利;后者可對組蛋白賴氨酸殘基產生一定催化作用,促進其乙酰化,從而對組蛋白電荷產生中和作用,進而有效促進基因的表達。一般情況下,二者處于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有助于提高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穩定性。一旦細胞轉化,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水平將明顯升高,造成二者水平失衡,進而導致抗癌基因的表達受限,引起惡性腫瘤。
子宮內膜癌患者機體內組蛋白精氨酸甲基轉移酶5(PRMT5)呈高表達狀態,且其表達量和腫瘤分化存在正相關的關系,一旦PRMT5基因沉默,將導致腫瘤細胞侵襲、遷移等能力減退;另外,PRMT5還可利用其他方式來抑制細胞凋亡,比如提升c-Myc水平來加快細胞增殖速度,同時上調Bcl-2以及下調p53基因等[15]。丁酸鈉、曲古霉素A均為臨床常用的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可通過促進腫瘤抑制基因轉錄來抑制子宮內膜癌細胞繁殖,且毒副反應較少。其中曲古霉素A屬于一種鏈霉素代謝產物,可通過與組蛋白去乙酰化酶結合以有效抑制其生物活性。研究指出,低劑量應用曲古霉素A可促使子宮內膜癌細胞逐漸向健康細胞分化,同時對于健康細胞不會產生毒性反應[16]。有研究指出,丁酸鈉可有效抑制子宮內膜癌細胞的正常生長,且不會出現明顯毒性反應。但其半衰期較短,一般僅為5 min,導致其臨床應用明顯受限[17]。
4.3 非編碼RNA
這類RNA包括siRNA、tRNA、miRNA等,均屬于不會翻譯成蛋白的功能性RNA類型。其中miRNA含有22個左右核苷酸,可通過結合靶mRNA相關轉錄區,對基因表達產生負性調控的作用。如果在有抗癌基因功能miRNA呈異常低表達狀態時,使用外源性miRNA可達到抗腫瘤的目的,而在有致癌基因功能miRNA呈異常高表達狀態時,使用相關靶向抑制劑便可有效抑制惡性腫瘤患者病情的發展。有研究指出,子宮內膜癌患者機體內miR-152水平呈低表達狀態,采取相應措施促進其表達狀態恢復,便可對腫瘤細胞生長發揮抑制性作用[18]。
5 結束語
近年來,很多子宮內膜癌的治療靶點被發現,這也讓其靶向治療得到了明顯突破,特別是對復發性以及晚期患者的療效較為可觀,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現階段,靶向治療在子宮內膜癌治療中的應用不太多,大部分還在試驗期。相比于常規療法而言,靶向治療的毒副反應發生率較低,而且聯用多種不同類型的靶向藥物可能會提升療效。同時,腫瘤組織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可視為惡性腫瘤早期診斷的生物標志物,這也給該病的臨床治療提供了新思路。今后還需進一步研究該病的發病機制,積極尋找一些潛在性標志物,努力研發具有多靶點的靶向藥物,從而有效攻克子宮內膜癌臨床治療這一難題。
參考文獻
[1]弓翠萍,白愛峰,常捷芳.分子靶向治療聯合化療對晚期子宮內膜癌的臨床療效[J].臨床醫學研究與實踐,2018,31(31):32-33.
[2]趙也恬,韓旭.子宮內膜癌的靶向治療研究進展[J].中國醫藥,2022,17(6):953-956.
[3]王磊磊,郭顯廳,王秀瑩.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基因在子宮內膜癌中的研究進展[J].大連醫科大學學報,2023,45(5):459-463.
[4]劉紹穎,范典,鄭博豪,等.子宮內膜癌靶向治療新進展與前沿展望[J].中國癌癥防治雜志,2021,13(2):121-125.
[5]陳啟立,路會俠.CTLA-4與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子宮內膜癌新進展[J].海南醫學,2024,35(2):301-304.
[6]王朝,韓雪,張愛霞.LIPI評分對PD-1/PD-L1抑制劑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效果與預后的價值分析[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23,33(6):55-60.
[7]陳琦,仰珈儀,王秀麗.PD-1/PD-L1抑制劑治療皮膚惡性腫瘤研究進展[J].中國麻風皮膚病雜志,2023,39(3):212-217.
[8]劉鷗萱,胡悅欣,林蓓.PD-1/PD-L1抑制劑治療晚期或復發性子宮內膜癌的臨床研究進展[J].現代腫瘤醫學,2021,29(8):1449-1456.
[9]闞穎.貝伐珠單抗聯合化療對子宮內膜癌患者血清PRL水平及療效的影響[J].基層醫學論壇,2023,27(1):29-31.
[10]邵佳琪,宋捷,何惠,等.子宮內膜癌治療藥物的研究進展[J].藥物評價研究,2021,44(9):2028-2035.
[11]吳海芳,孟祥玉,許恒毅,等.Ⅱ型子宮內膜癌相關基因突變及靶向治療研究進展[J].基礎醫學與臨床,2019,39(2):277-280.
[12]劉莉.分子靶向治療藥物在子宮內膜癌中的研究進展[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連續型電子期刊),2019,19(23):130,134.
[13]李莉,蘆小珊,辛佳純,等.免疫與靶向治療聯用:子宮內膜癌治療新視角[J].國際婦產科學雜志,2022,49(1):5-9.
[14]田東立,蘆恩停,張頤.復發性子宮內膜癌輔助治療的研究現狀與展望[J].腫瘤預防與治療,2021,34(5):469-473.
[15]吳昭怡,黃金智,張慶余,等.靶向PI3K/AKT/mTOR通路治療子宮內膜癌的研究現狀[J].醫學信息,2022,35(12): 68-72.
[16]周琳芝,陳秀慧,孔憲超.子宮內膜癌的胞內分泌與靶向治療[J].國際婦產科學雜志,2020,47(6):632-636.
[17]王懿琴,陳曉軍.子宮內膜癌的分子診斷與靶向治療[J].實用婦產科雜志,2022,38(8):565-569.
[18]曹海敬,薛嫚,李芳,等.子宮內膜癌靶向藥物治療研究進展[J].中國新藥與臨床雜志,2020,3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