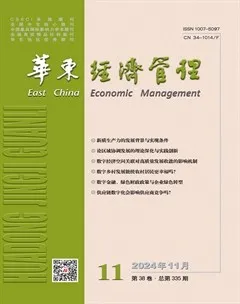論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深化與實踐創新

[摘要:區域經濟是國家經濟的空間基礎。無論是基于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的歷史經驗,還是基于理論分析,或是基于具體實踐,區域協調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經歷了四個歷史階段和三次理論演進,進行了戰略基礎、極點支撐和功能分工等探索實踐,逐漸步入高水平協調發展階段。但也面臨區域要素流動受阻、區域發展極化、區域功能分工程度較低和區域產業轉移緩慢等新問題。基于此,文章提出新時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具體思路:完善資源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優化重大基礎設施布局,細化區域功能分工,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體系,以新質生產力賦能區域協調發展。
關鍵詞:區域功能分工;區域協調發展;全國統一大市場;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097(2024)11-0008-10 ]
Theoretical Advancement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i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UN Jiuwen, YIN Sha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Regional economies constitute the spatial foundation of a nation's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underscored b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narrowing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four distinct historical stages and three theoretical evolutions. This progression has involved the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foundations, pivotal support mechanisms, and functional divisions. Consequently, we have gradually transitioned into a phase characterized by high-leve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owever, new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including restricted mobility of regional elements, polariz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ow levels of regional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sluggish regional industrial relo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essay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enhancing system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mobility of resource elements,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refining regional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ower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regional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一、引 言
區域經濟是國家經濟的空間基礎。黨的二十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中國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強調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發展總體穩步向好。2023年,中國GDP達到126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連續兩年保持在1.2萬美元以上,接近高收入國家人均水平的門檻(1);城鎮化率達到66.16%,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同時,四大板塊(2)的相對差距正在逐步縮小,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生態環境不斷改善。在競爭有序、共享共贏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形成和健全的背景下,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這充分顯示,面對即將到來的“十五五”時期,區域協調發展將繼續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本文擬探討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深化與實踐創新,并提出實現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具體思路。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意義
無論是基于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的歷史經驗,還是基于理論分析,或是基于具體實踐,區域協調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一)歷史意義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始終是黨指導區域經濟發展的邏輯主線。對于中國這樣幅員遼闊、地區經濟差距顯著的大國而言,實現各個區域協調發展和提升國家發展整體效能是現實的需要。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七十多年,中央根據發展階段的不同來調整區域發展戰略,中國區域協調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雖然不同時期區域協調發展的側重點不同,但對于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和實現經濟增長均有重要意義。這些區域協調發展的歷史經驗為新時代的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和借鑒,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正式提出之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大體經歷了低水平協調的均衡發展和不協調的非均衡發展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眾多學者致力于平衡沿海與內地的協調發展。第二個階段,自改革開放到二十世紀末(1979—1998年),在鄧小平同志“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下,通過先非均衡發展,再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1999年起,中央逐步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按照發揮比較優勢、加強薄弱環節、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逐步形成主體功能定位清晰,東中西良性互動、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趨向縮小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明顯增強,但是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因此,中國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對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需要進行理論深化和實踐創新。
(二)理論意義
主流經濟學理論通常會忽略空間這一維度,這就不可避免地忽視了區域關系。實際上,區域不是孤立存在的,特別是隨著交通運輸網絡和信息網絡建設完善,區域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區際聯系對于區域自身發展和整體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了區域間如何發生聯系,以及區域聯系的成本和收益,為探索區際關系、解決不平衡發展問題和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學解釋。從區域協調發展的定義來看,“協調”的含義是“配合適當、步調一致”,這必然以區域之間的聯系為基礎。由于區域是有層級之分的,一個區域既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空間主體,也屬于更高一級區域內部的區際關系問題。但無論從哪一個空間層級來看,解決好區際關系貫穿了區域協調發展過程的始終:第一,區域協調發展能夠突出區域的比較優勢。區域協調發展并不是要求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達到同一水平,而是根據各地區的實際發展條件,在微觀經濟規律和市場機制的支配下,通過促進要素合理流動、深化合理分工,使得各地區都能基于自身比較優勢取得良好發展。第二,區域協調發展能夠密切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強化區域間分工合作。區域協調發展通過優化產業布局、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區域合作與競爭,以及實現社會、文化和環境的和諧,能夠促進區域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分工更加合理、社會經濟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并收斂(覃成林和姜文仙,2011)[1]。第三,區域協調發展通過政府再分配保障區際關系的公平正義。生產要素會根據要素報酬最大化原則向發達地區流入,在實現效率優先的同時,地區間的差距也會拉大。區域協調發展強調政府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和優化社會公共政策,正確處理區域間公平與效率的問題,這與以私有財產和不加節制的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三)現實意義
新時代要求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思想不斷創新,以適應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區域實踐進入了新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區域協調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新時代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這需要發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引領作用,為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提供高效、安全、韌性、有力的區域支撐。一方面,新時代要求通過區域協調發展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根據中國新發展階段、新歷史任務、新環境條件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新時代的重要理論成果。新發展格局要求打破區域之間要素流動的行政壁壘和空間障礙,培育形成全國統一的資源要素市場和產品服務市場。這就需要發揮區域發展戰略功能作用,通過區域協調發展促進要素自由流動、產業合理分工,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拓展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新時代要求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區域協調發展能夠縮小區域差距、解決不平衡發展的問題,最終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體相當(蔡之兵,2023)[2],由此看來,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工具,也代表了對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期望。
三、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演進與深化
從辯證的視角看,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與中國區域發展實踐的變化是辯證統一的。縱觀新中國成立至今七十多年的歷史,大致經歷了低水平協調的均衡發展、不協調的非均衡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和高水平協調發展四個階段(李蘭冰,2020)[3];同時,區域協調發展理論也經歷了分工與協作、要素流動與一體化、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等創新發展,指導了中國區域協調發展四個階段的轉變過程,逐漸形成了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理論,具體如圖1所示。
(一)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源起:分工與協作
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低水平協調的均衡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初,為建立戰略防御型經濟布局,著力改變工業集聚于沿海地區的狀況,我國實施向內地推進的均衡發展戰略。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提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述強調通過均衡布局發展經濟,最終走向共同富裕。這一階段中國區域間生產力分布不平衡的現象得以緩解,區際關系的矛盾極大改善;但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整體經濟增長優勢不明顯。這就需要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指導,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和整體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
分工與協作理論轉變了低水平協調發展的現實情況,改善了區域經濟發展和整體經濟增長水平都較低的狀況。分工與協作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每個地區都根據自然優勢和競爭優勢進行生產,地區經濟必然能得到發展;每個地區找到并利用自己的優勢來發展產業,整體經濟必然也是一片繁榮。一方面,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認為各地區根據自然優勢和競爭優勢進行生產,能夠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專業化基礎。超乎人力范圍之外的氣候、土地、礦產和其他相對固定狀態的優勢是自然優勢,經濟和科技發展所取得的更好的生產條件是競爭優勢。按照自然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而形成區域經濟地域分工,提升生產效率和實現規模經濟,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的繁榮。另一方面,各地區通過因地制宜和分工協作,可以形成經濟發展的集體力。對于協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中提出,“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區域協調發展的形成,就是這種集體力發展與壯大的過程。
(二)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演進:要素流動與一體化
區域協調發展第二個階段的特征是不協調的非均衡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采取了梯度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路徑,極大地調動了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性。改革開放至2010年以前,中國多數年份經濟保持兩位數左右增長。但是經濟發展中一個突出問題是東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發展差距拉大。為此,中國區域發展的思路要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兼顧”轉變,地區發展戰略由突出重點區域向各地區協調發展轉變。這一過程中,倒逼了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創新發展。
不協調非均衡發展的區域協調發展實踐,倒逼區域協調發展理論向市場驅動的要素流動和政府引導的區域一體化演進。要素流動和一體化既可以增進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工,也能夠密切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是區域協調發展向更高階段演進的體現。一方面,要素資源在空間上高效集聚,深化區域分工程度,有利于實現地區經濟發展。在實踐中,由于各個地區的自然優勢和競爭優勢存在客觀差異,各地區的要素報酬也必然存在差異(李晨,2024)[4]。在區域之間不存在流動壁壘的情況下,資本、勞動、創新和數據等要素遵循要素報酬最大化原則,流向邊際收益更高的地區(洪銀興,2020)[5],使得要素配置和空間分布格局更有效率。根據新經濟地理理論,運輸與貿易成本是阻礙要素流動與規模集聚的重要制約因素。為促進資源要素流動,降低落后地區資源要素流動成本,這一時期我國相繼建設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國道主干線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樞紐等一批重點工程,強化了要素流動和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區域一體化能夠有效地突破各地區所形成的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由行政邊界形成的市場分割(李洪濤和王麗麗,2020)[6],實現整體經濟的“普遍沸騰”。區域之間通過統一的領導,編制一體化的發展規劃,制定一體化的發展政策等措施,有利于促進交通與信息一體化、制度一體化、區域與產業之間的協作以及強化經濟聯系與區域貿易(孫久文,2021)[7],實現更高層次的區域協調發展。在區域一體化理論的影響下,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通過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和體制障礙,朝著市場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新格局邁進。
(三)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深化: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經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階段,中國區域協調程度有了明顯提高,呈現重點地區優先與協調發展并進的特征(李蘭冰,2020)[3]。然而需要認識到,在區域協調發展階段,雖然要素流動性和市場一體化水平顯著提高,但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并沒有真正形成,市場主體地位和產權歸屬、市場保障體制機制沒有確立、重點行業領域壟斷現象突出,部分地區的市場分割行為或者地方保護現象仍然存在。對此,需要進一步深化區域協調發展理論,以經濟合作和區域分工打破行政壁壘、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加速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新時代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的開啟,標志著中國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導向,注重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的再一次深化。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具有規模巨大、結構完整、功能強大、機制靈活和環境優化等內在性質,有助于打破地域界限、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一方面,建立統一的市場機制有利于實現資源要素自由流動。新古典學派認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實現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關鍵。在市場機制下,市場遵循內在的運行規律,通過價格、競爭、供求、激勵和約束等機制共同調節要素自由流動(洪銀興,2020)[5],提升要素報酬和整體經濟效率,形成集聚外部性和擴散效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市場機制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市場價格決定機制,即各類市場參與者能夠依據價格信號評估其經濟行為的機會成本,并依據市場交易原則,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從而推動資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方向流動;其次,市場通過選擇機制,決定市場主體的優勝劣汰;再次,市場具有激勵作用,通過獎懲分明的機制,激發要素和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根據市場機制,廠商會比較各地區成本收益的結構,會選擇勞動力充裕,工資低廉的地區進行投資。勞動力也會根據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流向那些低失業率、高收入的地區。發揮不同地區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或要素稟賦優勢,實現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從而有助于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另一方面,發揮政府職能是必要保障,要加快形成政策統一、規則一致、執行協同的全國一體化運行的大市場體系(劉志彪,2022)[8]。事實上,在解決地區差距問題上不能依據新古典經濟理論倡導的“放任主義”,而是要強化政府的引導作用。這就要在市場一體化基礎上,繼續深化改革,加速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針對行業壟斷和不當競爭行為,瞄準“畫地為牢”和地區封鎖等頑疾,全面拆除有形無形的壁壘,促進高水平協調發展(肖金成等,2022)[9]。
四、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具體實踐及面臨的新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逐漸步入高水平協調發展階段,我國區域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區域協調發展也面臨一些新問題。
(一)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具體實踐
1. 戰略基礎: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
“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戰略構成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基礎。一方面,四大板塊的協調是考慮地理位置并以行政區劃所形成的“政策覆蓋區”的協調發展,強調的是對區域板塊的政策指導和發展定位。“十四五”規劃綱要指出:“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地區崛起、東部率先發展,支持特殊類型地區加快發展,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崛起等主題,先后召開座談會,對新時代四大板塊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一,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發揮其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的引領作用;第二,開創中部崛起新局面,搭建起東中西區域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橋梁,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空間樞紐,具體要將武漢、長株潭都市圈定位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軸心,在長江、京廣、隴海、京九沿線打造中高端產業集群;第三,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定位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重要經濟中心,將關中平原城市群建設作為促進西北、西南聯動的關鍵支柱;第四,推動東北振興取得新突破,在改造提升裝備制造等傳統優勢產業的基礎上,立足東北三省實際,適時培育寒地冰雪、生態旅游等新型業態,以全國需求引領帶動加快融入全國大市場。另一方面,“三大支撐帶”(3)與“四大板塊”形成了疊加效應。回顧“十一五”“十二五”期間采取的四大板塊劃分思路,盡管在地理上實現了對國土的全面覆蓋,但同時也暴露了板塊間發展水平差異顯著以及相互聯系不足等問題。“十三五”期間,中國提出“三大支撐帶”戰略,形成了“四大板塊”和“三大支撐帶”的區域新格局。“三大支撐帶”強化了“四大板塊”之間的內在聯系,并通過疊加效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其中,共建“一帶一路”促進了東北地區融入東亞新發展格局,加強了東北在東北亞區域合作、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長江經濟帶是連接東部、中部和西部的關鍵紐帶,有助于促進東中西板塊之間良性互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通過輻射效應,帶動東北和西部地區聯動發展。
2. 極點支撐:五大經濟區
五大經濟區建設通過輻射作用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培育了全國的增長極和動力源。五大經濟區以一域帶全域、以發展促平衡,解決國土空間的重點區域發展問題。京津冀結合北京科技創新優勢和天津先進制造研發優勢,深化對河北的幫扶,通過創新合作和知識溢出聯通京津冀技術創新廊道,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兩個新城,落實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務;長江經濟帶堅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結合本地科研優勢和人才優勢,推動形成新場景新業態新模式,形成區域發展新動能,統籌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提升區域融合水平,增強區域協同聯動;粵港澳大灣區借鑒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的跨行政區邊界共建經驗,參考東京灣區“多核互聯”的跨區治理經驗,建設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湛茂都市圈,同時借鑒舊金山灣區多組織協同的網絡治理經驗,部署“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深度一體化融合,推動多主體聯合創新和知識溢出;長三角實現創新鏈和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推動科技成果順利轉化,統籌龍頭帶動和各揚所長,發揮引領帶動作用;黃河流域以水定產、以水定城、以水定人,修復生態和盤活經濟并舉。
3. 功能分工:主體功能區
以主體功能區戰略促進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主體功能區的提出,標志著國家已經意識到區域協調發展要從產業分工向功能分工轉變。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都經歷了產業分工向功能分工的轉變。Bade等(2004)[10]對德國在互聯網時代城市產業專業化的研究發現,德國的城市產業專業化經歷了由部門專業化向功能專業化的轉變。Duranton和Puga(2005)[11]發現,美國城市的部門專業化水平也在逐漸降低,而功能專業化水平在不斷增強,城市間產業分工正由部門分工向功能分工轉變。主體功能區以空間功能分割為基礎,強調區域間的功能聯系,有利于破除區域競爭思想,避免局限于區域“小循環”,實現區域間良性互動,進而使資源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有序共享,實現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按照不同地區的主體功能定位中國對城市化地區、主要農業區和生態地區進行分類精準施策,形成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國土開發有序的空間發展格局。第一,以城市化地區作為空間動力源。2022年6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指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率先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產業結構,有序疏解中心城區一般性制造業等功能”。這就需要提升城市群、中心城市的人口和經濟的承載功能,發揮邊緣城市生產制造功能,形成產業鏈延伸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第二,以農產品主產區推進“三農”現代化。優化農業生產布局,加大農產品科技投入和推廣,延長農產品產業鏈,培育商貿零售、文化旅游等新業態,優化農產品主產區的空間結構。第三,以生態功能區協調經濟發展和生態治理。轉變高消費、高污染的工業化發展方式,發展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產業。在遵循主體功能區和區域分工要求的前提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承載能力進一步增強,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能源資源富集地區和邊境地區的保障能力將進一步提升。
(二)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問題
1. 區域要素流動受阻問題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還存在堵點,主要體現在要素資源市場(劉志彪,2022)[8]。
一方面,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交易流通中存在堵點。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數據成為數字經濟和區域發展的核心要素,是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支撐。與傳統有形要素不同,數據要素不受物理空間限制,可以在虛擬的網絡世界傳播,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低成本復制等特征(蔡躍洲和馬文君,2021)[12],與其他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會帶來放大、疊加、倍增效應。但與此同時,數據要素面臨的情境變得更加復雜,空間錯配現象可能更為嚴重(董直慶和胡晟明,2020;陶長琪和徐茉,2021)[13-14]。一是,相較于傳統要素而言,以比特形式傳播的數據要素涉及復雜的權屬關系、權益分配、隱私保護和國家安全等多個方面問題,在區域間的流動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蔡躍洲和馬文君,2021)[12]。二是,數據要素被圈定在壟斷企業和大市場中,新進入企業的市場空間受到擠壓,導致壟斷企業所在行業和區域的數據資源配置失衡。大型機構和龍頭企業,特別是互聯網巨頭企業控制大量數據資源,形成了數據壟斷并提高了市場進入壁壘和轉換成本。這些大型企業大多集聚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增長極地區,造成的數據壟斷導致數據要素在區域間流動性較弱。
另一方面,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傳統要素難以在地區間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制約了高水平的區域協調發展。當前,中國商品端有97%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由市場定價,但要素端的土地、資本、勞動等要素配置的效率低、質量差,導致資源的低效配置和利用,為區域協調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負面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和張其仔,2021)[15]。微觀上,要素不合理配置導致企業難以獲取所需的生產要素,使用者需要為僵硬的交易和管理制度支付高要素成本,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中觀上,資源在某些區域或行業過度集中(王怡穎,2023)[16],而在其他區域或行業則出現短缺,造成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下降,導致產業結構失衡和區域差距擴大;宏觀上,不合理的要素配置導致資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無法實現社會總產出和居民福利最大化,影響區域協調發展。
2. 區域發展極化問題
區域發展極化問題存在于城市群和腹地之間。城市群和都市圈具有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兩面性,對于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這類發展成熟的城市群,擴散效應發揮主要作用,城市群可以通過集聚效應促進周邊地區經濟增長,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動力源。而對于成渝都市圈、關中城市群等內陸城市群和都市圈,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這些城市群和都市圈處于培育過程,尚未到發揮擴散作用的階段。同時,老工業基地的中心城市自身老化問題突出,例如,東北地區至今沒有一個萬億元城市,中心城市的市場潛能不足,擴散乏力(張可云,2024)[17]。這種差距導致了城市群與周邊區域的不平衡,限制了區域發展。
區域發展極化問題也存在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城市吸引了農村資金、勞動力等要素集聚,導致區域極化現象始終存在。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成功的背后,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即各類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和各類經濟要素向具有更高經濟效率和經濟收益的城市匯聚,在地理空間上向城市聚攏,產生了集聚效應(張可云等,2022)[18]。由于集聚效應的存在,城市吸引了農村大量的資源要素,在提高城市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城鄉公平問題(孫久文和李承璋,2022)[19]。就如何擺脫上述農村經濟發展的困境,學理上和實踐中有大量文獻或做法從頂層設計、制度優化、機制設計等層面進行了探索,包括提出就地城鎮化、三產融合等舉措。然而,農村仍然面臨一些現實困境,如空心村、“3861”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農村缺乏產業支撐,導致人才流失和收入不均等現象。
3. 區域功能分工程度較低問題
盡管功能分工思想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主體功能區戰略為區域功能分工提供了實踐思路,但在實踐中,由于存在信息壁壘、中心城市帶動力不足等問題,中國區域功能分工和空間布局尚未完善。第一,地區間數字基礎設施水平的差異限制了區域功能分工。企業跨區域交流需要考慮通信費用、組織成本和時間成本等信息溝通成本,由于不同地區、不同規模城市的數字和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存在差異,企業跨空間組織和溝通成本較高。這限制了以“總部+基地”“研發+生產”“生產+服務”等形式布局產業鏈的延伸和功能分工。第二,城市化地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同質化現象突出。隨著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成為中國區域發展的動力引擎。從產業生命周期的角度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尚處于產業擴張階段,這一階段需求增長的空間比較大,產業技術進步快,具有較大的利潤空間。因此,各個區域大力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打造“千園一面”的創新示范區和產業園區,導致區域間產業競爭激烈。同時,服務業、數字創意產業和新能源產業則呈現高地區集中度狀態,存在地區壟斷、惡性競爭的可能。第三,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以傳統產業為主,產業缺乏創新化、品牌化和高端化意識,容易導致企業陷入價格競爭,造成市場飽和與利潤下降。這種現象在落后地區更為明顯。例如,過去在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由于缺少跨縣域層面的統籌協調與總體規劃,部分資源稟賦相近的貧困縣并未遵循差異化與錯位發展思路,確定產業項目時會出現跟風趨同現象(李冬慧和喬陸印,2019)[20]。
4. 區域產業轉移緩慢問題
隨著要素成本持續上漲、外貿環境變化和疫情沖擊疊加效應出現,當前中國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勢頭明顯減弱。如以紡織業、服裝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或外向型加工行業加速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從而削弱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葉振宇,2023)[21],影響產業轉移過程和產業鏈完整性(李雯軒和李曉華,2021)[22]。這導致無論是新興產業還是傳統產業,基本仍呈現東中西的梯度分布。一方面,產業轉移在東部地區集中化態勢更為明顯。包括化纖、紡織、鋼鐵、多元化工等在內的傳統制造業逐漸向更有效率和成本優勢的東部地區集聚,擠占地理空間并抬高要素成本,不利于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芮明杰,2018)[23]。另一方面,“雁陣”模式的大規模產業轉移并沒有發生,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缺乏足夠的產業支撐和發展動力。這是因為隨著高鐵等快速交通工具普及化,勞動力要素的空間流動更為便捷,勞動力差價反映的只是附著在勞動力上的生活差異,不是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同時,東部地區也存在土地要素成本較低的區域。中西部地區的傳統要素優勢不足,導致產業向本地區轉移緩慢,就業問題十分突出。姚鵬等(2022)[24]發現,要素價格扭曲、市場營商環境等進一步擴大了東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和市場優勢,削弱了中西部地區的相對成本優勢,導致傳統產業轉移被抑制及產能回潮現象出現。
五、實現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具體思路
新時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完善資源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優化重大基礎設施布局,細化區域功能分工,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體系,以新質生產力賦能區域協調發展。
(一)完善資源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
要加快新型要素和傳統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改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這就要求加強區域間改革舉措的協調配套與聯動集成;關鍵是完善數據、土地、勞動力和知識等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對于數據要素而言,加強市場數據登記平臺與區塊鏈存證平臺、公證機構等的互聯互通,引導市場內的數據產品安全合規地開展交易;建立數據市場統一的數據標準,完善數據交易基本法律法規,構建數據監管與治理的協同機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數據要素統一大市場。對于土地要素而言,需要扭轉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財政的發展模式,改革地方政府壟斷土地市場制度,推動城鄉土地“同地同權”,構建信息平臺以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建立交易平臺提供交易場所,確立劃撥、出讓、轉讓、租賃、入股、抵押等各種形式的交易路徑、交易規范和監管保障機制,加快鄉村土地要素流動和市場自由配置。對于勞動力要素而言,強化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進一步改善人口登記制度、戶籍制度改革與地方政府激勵掛鉤的制度化關聯,降低區域間勞動力流動成本,加快鄉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于知識要素而言,增強國家科技治理能力,完善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優化科技體制的頂層設計,建立規范有序、充滿活力、互聯互通的知識產權運用網絡和統一規范的交易制度,建立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的雙向溝通機制(蘇繼成和李紅娟,2021)[25]。
(二)優化重大基礎設施布局
協同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是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需求。首先,要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平臺搭建,深入實施“東數西算”等重大生產力布局項目,構建“互聯網+”對接平臺。圍繞強化數實融合、智能優化、融合創新支撐,布局建設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其次,要構建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格局,推動公路、鐵路、港口等多種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點對點連接,優化交通網絡布局,形成區域之間的高效網絡連接通道,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流通,助力形成高效產業循環體系。合理、可持續規劃現代流通體系,打通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最后一公里”。最后,促進線上線下基礎設施的互動發展。以智慧物流為發展目標,完善智慧物流的技術配備,制定新計劃,推進物流企業智能化改造,培育超市、驛站、物流中心等新物流業態(何黎明,2019)[26]。加快建設數字化流通企業,樹立一批先進的流通行業標桿,實現行業之間的信息共享(汪旭暉和趙博,2021)[27]。同時也要建立健全流通行業法規,明確流通管理部門權責,推動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創新,在價格制定、交易規則、質量標準等多方面建設完善的評價體系,促進現代物流體系的品質建設。
(三)細化區域功能分工
細化區域功能分工,有利于強化區域聯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第一,要深入分析區域特征、因地制宜提升區域專業化水平。根據城市的比較優勢,打造創新型城市、青年發展型城市、低碳城市,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和人才吸引力;要充分利用農產品主產區的當地資源、人力優勢,培養經濟支柱產業、壯大特色優勢產業、推動農產品主產區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改善地區產業結構單一的局面,以特色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對于生態脆弱地區,要有序遷出部分人口,降低生態壓力,對于遷出人口可以實施一定生態補償;開展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工程,加大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力度;還可以建立資源開發補償機制、衰退產業援助機制、新興產業扶持機制。第二,加快提升區域的國際化、文化匯聚和智能化功能,將傳統的單一功能向多功能轉化,通過細化的區域功能劃分,提升各個區域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增強區域發展韌性。第三,把功能分工提升到區域戰略高度。細化區域戰略的空間尺度,由現在的東中西部和東北的“四大板塊”向西部地區演化,分為西北和西南兩部分,形成“五大板塊”;抑或向東部沿海地區演化,分為沿海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形成“七大板塊”的空間格局。
(四)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體系
新時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要構建高水平、均衡化和現代化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體系。第一,以全國中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為核心,打造城市群和都市圈兩大增長極。培育城市群和都市圈成為中國人口、產業的重要載體,增強城市群、都市圈綜合承載能力。同時,優先發展大城市周邊縣城,重點完善交通和產業配套設施,做大城市配套產業,同鄰近大城市做好產業關聯、要素流動和基礎設施配套,把周邊縣城建設成為大城市周邊交通便利、功能互補、產業配套的衛星城。周邊縣城也要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挖掘縣城歷史文化,以城鎮特色產業帶動鄉村產業發展,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利用現代技術打通縣城和鄉村的物流通道,連接縣城和鄉村的產業加工鏈。第二,落實區域重大戰略,推進經濟帶、經濟區的協同發展。以長江經濟帶和黃河生態帶為主軸,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主要支點,聯合哈長、遼中南、山東半島、粵閩浙沿海、長江中游、中原、關中、蘭西、呼包鄂榆、天山北坡、北部灣、寧夏沿黃、山西中部、滇中、黔中等城市群,形成國家國土空間布局的骨架。第三,四大板塊并重,加快大經濟區之間的協調發展。東部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先行區,其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正逐漸向高技術和高附加值方向轉型,要吸引并整合優勢資源,實現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加快前沿領域技術突破;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新格局中,要充分發揮可再生能源和礦產資源、生物資源、自然和文化景觀等比較優勢,在開發過程中注意生態保護;推動東北全面振興要把握好體制機制的深層次矛盾,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持續深入優化營商環境。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深化東中西部產業協作”。東中西部協作能夠實現跨區域優化資源配置,是形成四大板塊合力、提升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水平的重要途徑。第四,開發海洋國土,推進陸海統籌發展。中國有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陸海統籌要促進陸海在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環境保護等方面全方位協同發展。協同推進海洋生態保護、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權益維護。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協同一體的綜合治理體系,節約集約利用海洋資源,促進海洋開發方式向循環利用型轉變,打造可持續海洋生態環境。
(五)以新質生產力賦能區域協調發展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新時代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未來思路。新質生產力是指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催生的新時代先進生產力,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又一大理論成果(孫久文和周孝倫,2024)[28]。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一是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推動短板領域補鏈、優勢領域延鏈、新興領域建鏈,形成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相互滲透、交叉重組融為一體的創新動態,形成和諧一致、配合得當的創新體系。要充分發揮龍頭企業鏈主優勢、平臺效應和示范引領帶動作用,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制度創新,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產業鏈上下游協同發展。二是政府要支持各地圍繞稟賦優勢、著眼未來發展,前瞻布局謀劃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重點行業領域的融合集群發展,打造細分領域的標志性產業,以產業需求牽引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推動前沿技術多方向、多路徑探索和跨學科跨領域交叉應用,開辟新的巨大增長空間,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力和安全性。三是以實體經濟作為基礎,提高實體經濟智能化水平。通過連接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實現數字技術對物理世界的賦能和升級。具體要加強工業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建設,推動5G、工業互聯網、新材料等技術領域發展,引入自動化設備和智能控制系統,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從而加快傳統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加強信息技術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推動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并舉,協同共建新的產業形態。
注 釋:
(1)2022年,我國人均GDP達到了85 698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2 741美元。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2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低于1 085美元的為低收入國家,1 086~4 255美元的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4 256~13 205美元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于13 205美元的為高收入國家。2021年高收入國家的下限為12 695美元。詳見: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ew-world-bank-country-classifications-income-level-2022-2023。
(2)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以四大板塊為主體的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戰略:堅持實施推進西部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在繼續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同時,謀劃布局并推動實施了“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統籌東中西、協調南北方,進一步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
參考文獻:
[1]覃成林,姜文仙.區域協調發展:內涵、動因與機制體系[J].開發研究,2011(1):14-18.
[2]蔡之兵.從區域戰略到區域政策: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方向與思路[J].學術研究,2023(9):104-110.
[3]李蘭冰.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邏輯框架與理論解釋[J].經濟學動態,2020(1):69-82.
[4]李晨.以區域協調發展推動0x4giVcCrmWgQvl5eViwtQ==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J].廣東社會科學,2024(1):274-283,287.
[5]洪銀興.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J].經濟學家,2020(2):5-14.
[6]李洪濤,王麗麗.城市群發展規劃對要素流動與高效集聚的影響研究[J].經濟學家,2020(12):52-61.
[7]孫久文.以區域合作促進區域發展新格局形成[J].開放導報,2021(4):7-14.
[8]劉志彪.全國統一大市場[J].經濟研究,2022,57(5):13-22.
[9]肖金成,劉守英,陳航,等.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大意義、基本思路和認識發展(筆談)[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1-22.
[10]BADE F J,LAASER C F,SOLTWEDEL R. Urban Specializ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Empirical Findings for Germany[R]. 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Kiel Working Paper,2004.
[11]DURANTON G,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5,57(2):343-370.
[12]蔡躍洲,馬文君.數據要素對高質量發展影響與數據流動制約[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38(3):64-83.
[13]董直慶,胡晟明.創新要素空間錯配及其創新效率損失:模型分解與中國證據[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2(1):162-178,200.
[14]陶長琪,徐茉.經濟高質量發展視閾下中國創新要素配置水平的測度[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38(3):3-22.
[15]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張其仔.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路徑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21(2):80-97.
[16]王怡穎.新中國成立以來區域平衡發展的邏輯進路——基于馬克思主義要素配置理論的分析[J].經濟學家,2023(1):15-24.
[17]張可云.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成效與發展趨勢[J].人民論壇,2024(3):40-44.
[18]張可云,莊宗武,韓峰.國內超大規模市場、人工智能應用與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J].經濟縱橫,2022(7):1-12,137.
[19]孫久文,李承璋.共同富裕目標下推進鄉村振興研究[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9(3):12-19.
[20]李冬慧,喬陸印.從產業扶貧到產業興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困境與創新趨向[J].求實,2019(6):81-91,109-110.
[21]葉振宇.新時代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經驗成就與現實思考[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51(3):39-49.
[22]李雯軒,李曉華.新發展格局下區域間產業轉移與升級的路徑研究——對“雁陣模式”的再探討[J].經濟學家,2021(6):81-90.
[23]芮明杰.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戰略思路、目標與路徑[J].中國工業經濟,2018(9):24-40.
[24]姚鵬,李慧昭,孫久文.工業用地價格扭曲、產業轉移與產能回潮[J].經濟學動態,2022(10):81-100.
[25]蘇繼成,李紅娟.新發展格局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對策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21(7):100-111.
[26]何黎明.發展智慧物流的四個關鍵[J].物流技術與應用,2019,24(6):69.
[27]汪旭暉,趙博.新發展格局下流通業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內在機制與政策思路[J].經濟學家,2021(10):81-89.
[28]孫久文,周孝倫.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國土空間體系:內容構成、動力機制與構建思路[J].改革,2024(3):104-112.
[責任編輯:陶繼華]
收稿日期:2024-05-30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中國沿海地區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與政策耦合研究”(42071155)
作者簡介:孫久文(1956—),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享受教育部的政府特殊津貼,研究方向:區域經濟;
殷 賞(1996—),女,河北石家莊人,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研究方向:區域經濟,數字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