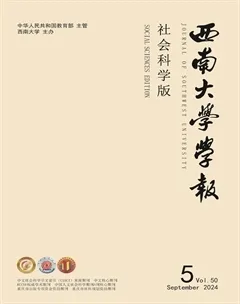作為標識性概念的“中國精神”:語義生成與政治闡發
摘 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展示出“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歷史韌性和實踐耐力,是以“改革精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生動體現。“改革精神”是“中國精神”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集中體現,極大豐富了“中國精神”。作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標識性概念,“中國精神”有其獨特的生成語境和演進過程。“中國精神”孕育和萌發于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自覺探索,奠定了這一概念以“中國魂”為核心的原初語義;生成與演進于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拓展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之雙重語義;規范并深化于新時代以來的理論創新,發展為兼具“宏觀的理論架構”和“微觀的實踐敘事”的話語體系。基于概念史考察,“中國精神”概念發展呈現諸多基本面向:根據時代發展調整“中國精神”內涵;平衡“中國精神”的“學理性”和“政治性”;“中國精神”的升華需要落實到個體層面的精神創造;以“中國精神”為發力點拓展“以中國為方法”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以系統觀念統籌把握概念發展規律,不僅能夠筑牢“中國精神”的概念根基與知識坐標,還有利于講好中國故事、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
關鍵詞:中國精神;概念語義;中國魂;民族精神;時代精神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24)05-0056-12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深入剖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科學系統地規劃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部署,繪制出進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戰略藍圖。全會展示出“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歷史韌性和實踐耐力,是以“改革精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生動體現。“改革精神”是“中國精神”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集中體現,極大豐富了“中國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3年就明確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1]235這標志著“中國精神”作為一個重要政治概念首次提出。隨后,習近平總書記希望文學創作和社會科學研究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2]。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3]從實踐層面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立足新的歷史坐標提出“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弘揚企業家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堅持用改革精神和嚴的標準管黨治黨”“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等具體要求[4]。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從學理上對“中國精神”概念語義正本清源,在實踐中捕捉概念發展,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中國精神”作為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標識性概念,是中國人精神面貌、精神風格、精神氣質的集中表征,是加快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力量,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中國精神”作為政治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學界從前提與基礎[5]、演化與整合[6]、反思與重構[7]、功能與價值[8]、傳承與弘揚[9]以及與其他概念的關系[10]等角度,為開拓“中國精神”研究、講好“中國精神”故事做出努力,彰顯出學界追求精神之獨特性的理性表達。政治概念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繁榮。近年來,隨著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研究成為學術增長點,特別是學界為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所作出的努力,持續提升著“中國精神”的理論深度和實踐廣度。
作為一個內生性的標識性概念,“中國精神”有其獨特的生成語境和演進過程。本文嘗試從學術、社會、政治的視角為“中國精神”概念的發展和演進建立一個綜合立體的解釋框架,分析“中國精神”在具體歷史時期的語義發展和話語內涵,梳理“中國精神”學術闡發的基本邏輯,追溯“中國精神”的歷史起源,回答政治話語影響下“中國精神”的規范形態與實踐形式有怎樣的發展。在研究材料方面,本文以學術文獻、黨和政府重要文獻作為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分析樣本,主要有以下來源:第一,為了掌握學界對“中國精神”概念的闡發邏輯,本文對專門研究“中國精神”概念的學術著作進行收集,以“中國精神”為題名對CSSCI期刊學術論文進行檢索,盡可能提升文本研究的科學性和學理性;第二,為了挖掘“中國精神”概念的生成語境,對概念涉及的歷史著作和文化典籍進行檢索,以期拓展文本研究的縱深度和延展性;第三,為了厘清政治話語對“中國精神”的塑造過程,以“中國精神”為關鍵詞在“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成果總庫”中的“黨和國家重要文獻”欄目中進行檢索,進一步提升研究材料的權威性。此外,“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數據庫”也是本文依托的重要電子資源。上述材料共同構成本文的文本資料依據。
學界的系統研究提升了概念的精準性、科學性和認可度并推動概念的普遍化轉向。基于不同領域的學者關于“中國精神”的知識生產,有助于多角度考察概念的內涵語義。目前研究走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借由挖掘“中國精神”的理論基礎以闡釋概念內涵。
其一,從什么是“中國精神”的認識論角度進行探討,剖析“中國精神”的“根”與“源”。徐偉新認為,從中華民族早期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中可以窺見“中國精神”的歷史源頭,如“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治理目標、“民惟邦本”“以仁治國”“無為而治”的治理方式、“重義輕利”“和而不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相處之道等[11]。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從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澄明“中國精神”的學理根基和價值導向。張三元等提出,中國精神超越資本主義精神的根源在于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的糾偏,強調“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對塑造中國精神的基礎意義[12]。薛慶超等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升華凝結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譜寫馬克思主義同中華文明相得益彰、中國與世界和諧共處的壯美樂章”[13]。
其二,從如何把握“中國精神”的方法論角度進行闡釋,厘清“中國精神”的“內涵”與“外延”。佘雙好認為,“中國精神”概念在當代中國的特定內涵應當從政治話語中進行把握,主張采取“守一望多”的策略,“守一”是指守住“中國精神”的內核,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望多”就是要把握“中國精神”是一個不斷形成和塑造的概念,持續為概念增添新的中國元素、歷史特征、時代特色、國際特征和世界意義[8]。左亞文等立足概念特征的辯證關系,即“中國精神是傳統與現代、實然與應然、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厘定了“本體致思、思維方法、認知理論、人本學說、價值取向、道德規范、行為方式、意志品格”在概念中的功能定位與價值意義[14]。
第二個方面,借由探討“中國精神”的培育傳播以呈現概念樣態。
其一,突出“中國精神”對人的引領和塑造,概念的育人樣態在教育目標與“中國精神”的內涵契合與實踐互動中得以形象呈現。劉鐵芳等提出以中國精神引領個體成長,就是要做“有根、有魂、有能的中國人”,“有根”就是“有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底”,“有魂”就是“有深厚的民族認同感”,“有能”就是“有能力融入時代,擔當民族復興大任”[15]。由此可見,“中國精神”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可以通過“中國人”將自己對象化為客觀現實,而“有根”“有魂”“有能”則標識出“中國精神”的基本維度。何小英等認為“中國精神”既是激發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思想基礎,又是養成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品質的道德基礎,還是指向積極進取、開拓創新、艱苦奮斗、與時俱進的行動指南[16]。“中國精神”能夠具體呈現為一種思維方法、一種道德規范、一種行為方式等,對人們的精神生活起著約束和導向作用。
其二,聚焦“中國精神”對中國故事的凝練和國家形象的打造,概念的傳播樣態在傳播載體與“中國精神”內涵的交融互濟中得到闡釋和傳達。楊凱等從英雄形象的視覺建構出發,指出“創傷性身體”表征著愛國主義、奮發自強的民族形象,“生產性身體”反映了勤勞勇敢、樂觀向上的個體形象,“集體主義群像”代表了中國人踐行集體主義價值觀,主動將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的社會形象[17]。李文玲從“中國精神”弘揚傳播要求的角度,論述“中國精神”的“本來”“外來”“未來”三維樣態,“本來”指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沉淀下來的思想理念、傳統美德、處事方法、美學追求、人文關懷,“外來”指經過優化改造、辯證取舍后的國外文化、理念、品質,“未來”指與日俱增的民族集聚力量、動員感召能量、厚積薄發效應[18]。
第三個方面,借由剖析“中國精神”在不同領域的生成機制以拓展概念應用。
“中國精神”具備文學、藝術和美學的闡釋力,逐漸通過文藝作品賦形于大眾語境,進而延伸“中國精神”概念的敘事場域。一方面,注重“中國精神”的賦能作用。袁祖社將“中國精神”提升至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立的邏輯起點和切入點的高度,認為“探究中華民族以及中國人的‘精神性存在’,是當代中國的人文學術話語建構的核心使命和中心議題”,這種“精神性存在”是“相對穩定的”以及“獨特的”,從表現形式上將“中國精神”定義為一種“精神氣質、心理特質和意志品質、人道情懷”,從呈現內容上概括為“一代代中國人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7]。陳虹認為“中國精神”作為一種社會心理資源和社會心理正能量,可以具體化為價值導向、精神激勵、認知主導、情緒疏導、人格塑造、行為規范等形式在建設良好社會心態的過程中發揮作用[19]。
另一方面,探析“中國精神”的淬煉過程。蔣述卓等提出新中國文學是中國精神的審美表達,包括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和“民族團結精神”,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的“反思精神”“改革開放精神”和“與時俱進精神”,南方談話以來文學的“多元共融精神”以及新時代以來文學中的“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這些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學精神就是“中國精神”的具體呈現,同時也是“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雙向互動的結果[20]。魏崇輝考察了“中國精神”概念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中的發展演變,提出“中國精神”蘊含了深厚歷史積淀、黨的有力領導、民族強勁韌性的基本維度[21]。潘雯將“中國精神”上升至民族審美范疇,指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這一靈魂是“傳統的”“文化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的”[22]。
綜上所述,學界在闡釋“中國精神”概念內涵、呈現“中國精神”概念樣態、拓展“中國精神”概念應用方面作出了諸多努力,但“中國精神”是一個需要正本清源、不斷豐富內涵的概念。這是由于:第一,“中國精神”本身包含著太多元素、價值、內容,其概念愈發呈現出模糊性、多義性和流動性的傾向;第二,“中國精神”具備“既存性概念”和“建構性概念”的雙重特征[23],概念的內涵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在不斷發展演化。如果不從本源上勘定“中國精神”概念,易導致其淪為抽象的話語符號和空洞表達,由此引起概念的“泛化”甚至精神的“矮化”。既有研究中從概念史意義上探討什么是“中國精神”以及“中國精神”這一本土化概念是如何建構起來的成果還比較匱乏,因而,立足相關文獻對“中國精神”進行概念史梳理就顯得格外重要。以語義的形式呈現概念在具體歷史時期的內涵,是透析“中國精神”演進過程的重要方法。該方法以“語義連續性”為基礎,以“概念空間”為知識導向,在“充分描寫”的基礎上尋求“解釋的充分性”[24],能夠呈現“中國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定內涵,有利于筑牢“中國精神”的概念根基與知識坐標。
二、“中國精神”概念的孕育與萌發
“中國精神”是在中國古人“日用而不覺”的日常話語中孕育萌發的。從詞源上考釋“中國精神”,需要從“中國”的主體意識出發,以空間的、歷史的、實踐的方式,建立起與中華文化和現代化實踐的深層次鏈接。“中國文化精神發端于伏羲,積蓄于炎黃,大備于唐虞,經夏、商、周三代而浩蕩于天下。”[25]從概念構詞看,“中國精神”由“中國”和“精神”兩個雙音詞構成,表明“中國精神”的研究和敘事對象是“中國”的精神面貌、精神風格和精神氣質。這不僅強調了“中國精神”概念的空間范圍,更在時間維度彰顯出“中國精神”概念醞釀的文化底蘊,還在實踐維度賦予了“中國精神”概念生長的動力源泉。對“中國精神”的文化傳統和實踐傳統進行考察,能從本源意義上理解“中國精神”概念的生成脈絡。中華文化為“中國精神”提供豐厚滋養,現代化實踐標記“中國精神”的發展軌跡,二者共同構成“中國精神”概念孕育萌發的重要資源。
(一)“中國”標識出“中國精神”概念孕育生成的基本語境
“中國”一詞古已有之,較早出現在《詩經·民勞》《尚書正義》《史記·武帝本紀》等文獻之中。《詩經·民勞》注:“中國,京師也。”[26]這里的“中國”意為“首都”。《尚書正義》:“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27]這里的“中國”范圍指周人所居關中、河洛地區。《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28]此時華夏諸國將南東西北四境諸民稱為蠻、夷、戎、狄,“中國”指內地華夏諸國。上述概念主要作為地理政治概念而存在,昭示“中心—邊緣”格局下的中央集權和朝貢秩序。這與“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概念還相去甚遠。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成為民族國家的泛化性自稱,但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作為一個現代多民族國家的簡稱出現,概念孕育生成的基本語境才明確下來。
(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新挖掘是溯源“中國精神”概念的重要方法
“中國精神”作為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獨特文化精髓與民族品格,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重要支撐。“中華傳統文化及其精神是中華民族在人格精神、倫理情感、實踐智慧及其整體的精神境界上所達到的高度與極致。”[29]只有自覺地深入中華文化的特征本質及其歷史演進的脈絡,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中國精神”概念的內在邏輯和深層結構。在商務印書館編纂的《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精神”有名詞(jīnɡ shén)和形容詞(jīnɡ shen)兩種用法。在“中國精神”組詞下的“精神”(jīnɡ shén)一詞大致有三層含義[30]:一是指人的精氣、氣節和元神,相對于形骸而言;二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一般心理狀態;三是指宗旨或主要意義。除了直接提及“精神”一詞,在諸多文化典籍和歷史著作中散落著表征古人精神氣節的語句,典型的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31]“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32]“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33]8“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33]29古典文獻中暫時尚未發現將“中國”與“精神”組合為固定短語的用法,但與之相近的有“國魂”“華夏精神”等。上述概念和話語的廣泛傳播,構成了“中國精神”起源的重要線索,可以看作是“中國精神”概念的濫觴。
(三)救亡圖存的自覺探索是“中國精神”概念孕育發展的現實動力
真正意義上關于“中國精神”的探討,是西方文化沖擊背景下中國人民開展救亡圖存的自覺探索。不少知識分子對“國民性”展開探討,以“中國人的精神”彰顯“中國精神”,通過“中國的脊梁”“民德”“民智”“民力”等指代“中國精神”,逐步豐富了“中國精神”的概念形象。首先,對“中國精神”的把握不能脫離生存于中國歷史文化情境中的中國人。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說:“真正的中國人身上有一種內斂、審慎、節制的圓融品質,就像一塊經過千錘百煉的金屬呈現的質感一樣。”[34]從中國人身上的獨特品質可以窺見“中國精神”的概念縮影。其次,對“中國精神”的把握不能脫離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集體意識。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35]“脊梁”是“中國精神”的形象表達,點明了“中國精神”堅毅剛強的特點,使“中國精神”的概念生動形象地躍然紙上。最后,對“中國精神”的把握要勾勒出“精神”的語義維度。嚴復說:“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36]這里的“民力”“民智”“民德”,指血氣體力、聰明智慮以及德行仁義,點明了精神層面的智慧、品德與健康體魄同等重要,逐步充實了“中國精神”的語義維度,多角度描繪了“中國精神”的概念輪廓。梁啟超提出“中國魂”概念:“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為此懼……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37]他結合社會現實提出的“中國精神”現實形態便是“中國魂”,是一種民族氣節,同時強調軍事力量、民族抵抗精神對振奮“中國魂”的重要意義,奠定了“中國精神”的語義基礎。
三、“中國精神”概念的生成與演進
隨著概念輪廓逐漸清晰,“中國精神”從日常話語表達轉向政治話語敘事。在對概念共識性理解的基礎上,經由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國精神”由“中國魂”的原初語義逐步拓展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雙重語義。這既體現了“中國精神”語義發展的繼承性和創造性,同時也彰顯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歷史進程。
(一)“中國精神”形成了“民族精神”的基本語義(1921—1949年)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以全新角度呈現和詮釋“中國精神”,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精神”相結合,賦予“中國精神”概念以革命指向和反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內涵,明確了“中國精神”內含“民族精神”的基本語義。毛澤東1938年在《論持久戰》中提到的“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力”[38]503,就是中國精神的具體呈現,是通過革命斗爭奪取勝利的勇氣和決心而展現出來的革命精神。毛澤東又提到日本帝國主義“要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38]615。此時,“中國人的民族精神”是“中國精神”在這一時期的集中表達,代表著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英勇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
毛澤東還通過贊揚中國人的精神主動性刻畫“中國精神”的基本特征:“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39]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成為“中國精神”概念發展的里程碑。1949年新中國成立,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40],標志著“中國精神”正式擁有了自身獨立發展的現實基礎。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建構“中國精神”概念,“民族精神”語義得到浮現。
(二)“中國精神”孕育出了“時代精神”的語義線索(1949—1978年)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邁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新階段,“中國精神”概念孕育出“時代精神”的語義線索,蘊含著“生產建設”的基本內涵。周恩來說:“工人階級應該用自我犧牲的精神來努力生產。”[41]84劉少奇說:“因為生產事業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乃是全體人民一切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礎。”[41]5271952年,中央號召整編轉業建設的軍隊“以同樣的忘我戰斗精神,去學會生產建設的技術,為加強國防建設、發展國家經濟而奮斗”[42]。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建設成為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基本認知,構成了“中國精神”概念的“時代精神”語義內涵,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內在變化和國家發展的建設要求。
這一時期,“中國精神”的“民族精神”語義更加明確。1949年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要繼續“以革命精神和愛國精神教育部隊的指揮員和戰斗員”[41]6,這里的“革命精神和愛國精神”就是“民族精神”語義的充分詮釋。《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進一步提到:“我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具備著高度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我們各族人民之間的關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友愛團結,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蓬勃昂揚。”[43]由此,“民族精神”語義進一步概括為“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對不斷發展著的“中國精神”概念的精準提煉與概括。
(三)“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語義交匯(1978—2012年)
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加快了對“中國精神”概念的形象塑造和培育,“中國精神”概念形成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雙重語義。一方面,“民族精神”語義及其內涵得到明確和定型。199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指出,民族精神是一種“自尊、自信、自強”的力量,需要通過“深入持久地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來培養[44]874。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對“民族精神”概念內涵進行提煉:“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45]1260這標志著“民族精神”語義的基本內涵成熟定型,成為當今“中國精神”概念內涵的重要指向。
“時代精神”語義內涵發生創造性轉變。1978年,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少同志的思想還很不解放……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44]2,隨即中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全新政策,“中國精神”概念形象呈現嶄新面貌,為拓展“中國精神”概念的語義內涵提供了重要契機。“時代精神”代表“中國精神”的概念語義頻繁出現在黨和政府的重要文獻中,其意涵在1985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得到首次呈現:“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以改革創新和開拓前進的精神,積極投入到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偉大實踐中去。”[44]406“時代精神”被具體表述為“改革創新和開拓前進的精神”。黨的十四大報告說:“在全黨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精神,尊重科學、真抓實干的精神,顧全大局、團結協作的精神,謙虛謹慎、崇尚先進的精神,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44]674這是“時代精神”的具體展開。2006年,胡錦濤指出,“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45]1570,“中國精神”概念中“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雙重語義得以交匯,“中國精神”概念的語義結構更加明晰。
“中國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思想價值和精神支柱,其概念語義在文化交融和時代演進中不斷充實和發展。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時期,“中國精神”以“中國魂”為核心的原初形態得以呈現。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精神”概念形成了“民族精神”的基本語義,被賦予了鮮明的革命指向和反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價值。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孕育出“時代精神”的語義線索,并被賦予“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建設”的基本內涵,“民族精神”語義更加明確。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之前,“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雙重語義交匯,由此筑牢了“中國精神”概念的語義結構及基本內涵。
四、“中國精神”概念的規范與深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全方位多角度闡釋“中國精神”,不斷拓寬“中國精神”的內涵與外延,為“中國精神”注入強大生命活力,使“中國精神”概念逐漸明晰化、實踐化、具體化。習近平總書記最早對“中國精神”的論述是通過“中國夢”這一目標設定實現的,點明了“中國精神”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途徑,明確闡述了“中國精神”的內涵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一)新時代“中國精神”概念的理論架構
對于“中國精神”這一宏大概念及其背后的深層邏輯,習近平總書記在認識論層面進行了澄明,包括弘揚“中國精神”的理論指導、踐行“中國精神”的實踐準則、新時代“中國精神”的精粹內核以及“中國精神”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為更好把握“中國精神”的精髓要義提供了有力指導和切實遵循,推動“中國精神”概念逐步走向規范和成熟。
首先,弘揚“中國精神”的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46]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是“中國精神”的理論指導,不斷吸收新的時代內容,與時俱進地解決新的時代課題,為“中國精神”提供賡續啟迪。
其次,新時代“中國精神”的精粹內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47];黨的二十大閉幕會明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48]。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觀點、新戰略,深刻把握了時代的主題和發展的新要求,彰顯了“中國精神”的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集體智慧和精神力量的結晶。
再次,“中國精神”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46]。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價值導向和道德準則,貫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對人們思想行為起著引導和規范作用,具有強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中國精神”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
最后,踐行“中國精神”的實踐準則——持續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持續深化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49],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他要求,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意識形態工作,“用富有時代氣息的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50]。事實上,文化建設與精神傳承二者具備很強的相關性。文化建設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和措施,推動精神傳承、創新和發展。文化建設既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也為精神傳承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環境。在實踐層面踐行“中國精神”應當同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二者一體兩面。
(二)新時代弘揚“中國精神”的實踐敘事
“中國精神”概念在更深層次上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賦予其現實性。這一現實性是指這種精神必須真正成為國家或民族成員思維和實際行動的內在動力,而不是抽象的符號或口號。進一步說,這種精神需要在具體領域得到實際運用,為這一共同體所共享,并實際約束、規范著擁有這一精神的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注重加強“抓典型”對展示、弘揚、闡釋“中國精神”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推動概念在更廣范圍內發揮效用。這個典型包括典型行業群體、典型年齡群體以及典型代表。這些典型群體或代表能夠在傳播正能量、弘揚優秀品質、樹立正確價值觀方面起到模范帶頭作用。習近平總書記主張典型模范率先展示、弘揚、闡釋“中國精神”,目的在于借助榜樣模范的示范力和影響力,形成全社會共同弘揚“中國精神”的良好局面。通過分析習近平總書記對典型模范弘揚中國精神的重要指示,準確把握實踐領域如何踐行“中國精神”,從而促進概念的現實轉化。
首先,行業群體弘揚“中國精神”的實踐敘事。習近平總書記指示文藝工作者,“不斷創作生產優秀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唱響主旋律、傳遞正能量,塑造中國形象、弘揚中國精神”[51]。習近平總書記囑托新聞出版工作者,“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52]。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2]。習近平總書記稱贊載人航天事業工作者,“載人航天事業的成就,充分展示了偉大的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堅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決心和信心”[53]。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體育健兒,“生動詮釋了奧林匹克精神和中華體育精神,為祖國爭了光,為民族爭了氣,為奧運增了輝,為人生添了彩”[54]。正如山地自行車女子奧林匹克越野賽冠軍李洪鳳曾說:“訓練吃苦了,比賽就會輕松一點,才能在賽場上升起國旗,為國爭光。”[55]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扎根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行業群體要更好地把握自身優勢,為弘揚“中國精神”、傳承中國根脈、展現大國形象接續奮斗。這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4]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和是“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4]的集中體現。
其次,關鍵兩頭弘揚“中國精神”的實踐敘事。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抓住廣大青年和老同志這關鍵兩頭,發揮他們在弘揚“中國精神”中的獨特優勢和顯著作用。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重視青年在國家建設、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多個場合論述了青年弘揚“中國精神”的重要作用。他認為青年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的生命力所在”[56],提出青年要“用眼睛發現中國精神,用耳朵傾聽人民呼聲,用內心感應時代脈搏”[57]。這些要求充分激勵著青年群體以實際的行動、主動的態度弘揚“中國精神”。這在《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白皮書中得到印證:“新時代中國青年以更加自信的態度、更加主動的精神,適應社會、融入社會,參與社會發展進程,展現出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和能力,成為正能量的倡導者和踐行者。”[58]另一方面,老同志是“中國精神”的見證者和傳承者,忠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對“中國精神”內涵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見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發揮老同志的政治優勢、經驗優勢、威望優勢,組織引導老同志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好聲音。”[59]概言之,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關鍵兩頭要以弘揚“中國精神”為發力點,充分發揚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青年富有活力和創新力,推動“中國精神”的創新發展;老同志則憑借豐富的經驗和智慧,為“中國精神”的賡續傳承提供堅實支撐。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中國精神”的廣泛傳播和深入發展。
最后,優秀黨員和勞動模范弘揚“中國精神”的實踐敘事。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涌現了一大批勇于擔當、敢闖敢干、無私奉獻、不斷創新的杰出代表,他們在工作崗位上積極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具備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深刻詮釋了“中國精神”的豐富內涵,為全社會樹立了弘揚“中國精神”的典范。優秀黨員不僅在工作中勇攀高峰、追求卓越,更在平凡崗位上默默奉獻、銳意進取。他們敢于直面困難和挑戰,勇于擔當責任,不斷開拓創新,以實際行動踐行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顯著貢獻。原廣西百色市樂業縣百坭村第一書記黃文秀曾言:“百色是脫貧的主戰場,我有什么理由不來呢?……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這就是我的使命。”[60]習近平總書記肯定了優秀黨員和勞動模范的榜樣作用,指出:“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是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楷模,他們以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卓越的勞動創造、忘我的拼搏奉獻,為全國各族人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61]優秀黨員和勞動模范在新征程上要充分發揮典型示范作用,加強團結協作、形成合力,加快將“中國精神”轉化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力量。
五、結 語
概念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社會歷史發展變化對概念的形塑作用,而反思概念發展過程、規范概念發展方式不僅能夠促進概念的科學化、深刻化、普遍化,還能有效提升知識生產的規律性和適用性。“中國精神”作為一種標識性概念,其建構過程具備相當的典型性和復雜性。這是由于:一方面,“中國精神”的演進充分體現了概念累積性發展的一般特征和“日常概念—學術概念—政治概念”[62]的轉化過程;另一方面,概念內涵的豐富性、歷史背景的深遠性、時代特征的多樣性和地域文化的差異性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使“中國精神”概念演變過程變得復雜而深刻。正是如此,從方法論層面把握概念建構的基本面向,要求以系統的觀念統籌把握概念發展規律,不斷強化概念的引領性和標識性。
(一)根據時代發展調整“中國精神”概念內涵
“歷史沉淀于概念,概念語義是時代精神的濃縮。”[23]概念所處的時空變化帶來語義內涵及其表現形式的不同,“中國精神”自孕育生成之日起就與時代緊密相連。在中國古代,“中國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氣節,表現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堅毅的美好品質;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中國精神”發展為興國安邦的精神支撐,呈現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雙重語義;新時代,“中國精神”作為凝心鑄魂的精神動力,展現為不同領域的實踐敘事。概念與時代發展的互動,既能打磨概念的辨識度,使之成為更加規范成熟的標識性概念;又能提升概念的認可度,使之與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并成為中國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園。守正創新是概念建構的基本原則,也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貫徹的原則之一。根據時代發展調整“中國精神”概念內涵,一是要對本質性要素進行提取和確定,把握概念“模糊的精確”的特點,并非時代發展中正向的積極的精神元素都屬于概念的范疇;二是對擴充性內容進行捕捉和分析,避免概念被時代進程所淘汰;三是對共識性內容進行提煉和把握,實現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溝通。
(二)平衡“中國精神”概念的“學理性”和“政治性”
“中國精神”作為一個明確概念被政治話語提出之前,學界在醞釀準備、引入界定、溝通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概念的共識性理解和概念的吸納轉化能力,決定了“中國精神”由政治話語最終確定并調適,這反過來又能提升概念在學界的研究層次。可見,“中國精神”概念的發展與調適反映了當代中國知識生產的環節和流程,也彰顯出概念的“學理性”和“政治性”的有效互動。不難看出,概念的“學理性”與“政治性”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張力。這是由于,一方面,學術研究注重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追求基于事實和證據的客觀性和規范性;另一方面,政治話語往往涉及到情感認同和價值判斷,帶有明顯的價值傾向性和意識形態色彩。如果“中國精神”的“政治性”過強,會導致概念的意識形態屬性偏重,概念理解容易出現“單一化”的傾向,限制了概念的可對話性。同時,又要規避概念理解碎片化及概念價值屬性弱化的風險。一個可能的路徑是,建構起日常話語、學術話語、政治話語之間的互動橋梁,串聯起宏觀敘事和微觀敘事的基本場域,推動概念形成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三)“中國精神”概念的升華需要落實到個體層面的精神創造
“中國精神”以何種姿態完成新的認知、新的闡釋、新的創造,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提供精神動力的基本使命?毫無疑問,“中國精神”不是先在地被確定為某種固定的形態及特征,而是通過個體層面的精神創造所呈現,再經過官方話語進行提煉和表達。個體層面的人能直接觸摸到時代的、現實的社會肌理并呈現出特定的精神狀態,對“中國精神”的闡釋具有先天優勢。因此,推動概念的普遍化轉向,對個體表現層面的精神內容和精神意象進行及時捕捉,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日常生活與官方話語之間的距離,是“中國精神”概念升華的重要契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4]。一方面,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闡釋“中國精神”,在堅持概念基本語義的基礎上,對概念進行社會化處理,做到概念的可溝通、可對話,逐步擴展概念適用范圍;廣泛征詢人民群眾對“中國精神”的理解和多角度搜集代表“中國精神”的典型人物和案例。另一方面,科學規范概念的使用和理解,逐步實現不同領域概念使用的分級管控;設立“中國精神”概念要素的評判標準,厘清并區分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精神與概念的關系及其對概念的意義,防止概念因無限擴張和泛化而失去其本原意義。
(四)以“中國精神”為發力點拓展“以中國為方法”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57]以中國為方法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求研究將“中國”作為提出命題、建構理論、選擇方法、確定路徑的前提和關鍵[63]。“中國精神”的概念研究亦是如此。必須承認,對“中國精神”的概念內涵進行抽象和概括存在相當的難度,以中國為方法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莫大的幫助。“中國”不僅標識出“中國精神”概念孕育生成的基本場域,還作為一種特定文化、普遍性知識內在地嵌入概念之中,構成概念中更鮮活更具建構性的“情境知識”,對概念理解起到“不言而喻”的效果和作用。以中國為方法探討“中國精神”概念,至少包括三重內涵:一是“中國精神”孕育于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是勞動人民的精神呈現;二是“中國精神”肇始于現代化進程,是民族復興的精神集聚;三是“中國精神”發展于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感召。一定意義上,現實中的“中國精神”概念還不夠飽滿,不僅缺乏相應的理論依據來抽象概括“中國精神”的整體性特征和全部內涵,更無法描繪現實生活中復雜且鮮活的“中國精神”的個體呈現。而“中國”作為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方法論,為理解“中國精神”提供優質情景和內容補充,是概念研究的無盡寶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精神”概念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在于書寫宏大的中國社會演變史,以此拓展“以中國為方法”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2] 習近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J].求是,2019(8):4-8.
[3] 習近平.黨的偉大精神永遠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J].求是,2021(17):4-20.
[4]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N].人民日報,2024-07-22(1).
[5] 左亞文,黃路平.試論中國精神的前提性問題[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3(3):66-75.
[6] 鄒紹清.論中國共產黨構筑中國精神譜系的百年歷程與基本經驗[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1-15.
[7] 袁祖社.“中國精神”的文化—實踐自覺[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14-24.
[8] 佘雙好.深刻理解中國精神在當代中國的特定內涵[J].思想理論教育,2019(5):28-33.
[9] 史宏波,黎夢琴.在強化中華民族集體記憶中弘揚中國精神[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1(6):179-186.
[10] 李忠軍.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J].社會科學戰線,2014(3):31-39.
[11] 徐偉新.論古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探尋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歷史源頭[J].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1(6):5-13.
[12] 張三元,李齊.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與中國精神的弘揚[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12):118-127.
[13] 薛慶超,薛靜,劉伊純.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習近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J].統一戰線學研究,2022(1):1-15.
[14] 左亞文,高曉英.中國精神的本質規定及其內在邏輯[J].理論探討,2021(5):40-46.
[15] 劉鐵芳,徐巾媛.以中國精神引領個體成人:中國少年培育的課程策略探究[J].全球教育展望,2023(7):24-34.
[16] 何小英,李曉衡,蘇美玲.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大學生“中國精神”培育[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5):107-110.
[17] 楊凱,張小琴.中國精神隱喻:中國故事影像意義生成的視覺修辭分析[J].當代電視,2023(2):48-53.
[18] 李文玲.中國精神弘揚傳播的時代要求[J].中國編輯,2018(9):15-18.
[19] 陳虹.論中國精神在培育良好社會心態中的作用[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4(1):48-50.
[20] 蔣述卓,李石.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生成[J].中國社會科學,2021(2):82-101.
[21] 魏崇輝.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中中國精神概念的流變[J].湖湘論壇,2023(1):13-24.
[22] 潘雯.中國精神: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關鍵詞[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6(4):69-75.
[23] 郭忠華.歷史·理論·實證:概念研究的三種范式[J].學海,2020(1):56-63.
[24] 成軍.當代語言類型學的視角轉換:從形態、功能到庫藏[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145-153.
[25] 司馬云杰.中國精神通史:第1卷[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1:自序1.
[26] 周振甫.詩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445.
[27] 尚書[M].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213.
[28] 司馬遷.史記[M].韓兆琦,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1112.
[29] 胡海波.中國精神的實踐本性與文化傳統[J].哲學研究,2015(12):114-121.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689.
[31] 孟子[M].方勇,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109.
[32]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92.
[33] 周易[M].楊天才,張善文,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34]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M].李晨曦,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11.
[35] 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2.
[36] 南京大學歷史系,國營紅衛機械廠《嚴復詩文選注》注釋組.嚴復詩文選注[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5:54.
[37] 梁啟超全集:第2集[M]. 湯志鈞,湯仁澤,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90.
[38]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 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725.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61.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388.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46]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1).
[47]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4-11.
[48]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閉幕[N].人民日報,2022-10-23(1).
[49] 習近平對全國道德模范表彰活動作出重要批示強調 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精神動力和道德滋養[N].人民日報,2015-10-14(1).
[50] 習近平.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J].求是,2019(1):4-8.
[51] 習近平就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 堅定人民信心振奮人民精神[N].人民日報,2017-09-28(1).
[52] 習近平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N].人民日報,2021-05-11(1).
[53] 習近平會見神舟十號載人飛行任務航天員和參研參試人員代表[N].人民日報,2013-07-27(1).
[54] 習近平在會見第31屆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時表示 中國隊加油!中國加油![N].人民日報,2016-08-26(1).
[55] 弘揚中華體育精神 展現良好精神風貌[N].中國體育報,2023-10-05(3).
[56] 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05-03(2).
[57] 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N].人民日報,2022-04-26(1).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青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
[59] 習近平在會見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時強調 認真做好新形勢下老干部工作 傳承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N].人民日報,2014-11-27(1).
[60]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宣傳部.學習黃文秀優秀品質走好新時代長征路[J].紅旗文稿,2020(12):27-31.
[61] 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4-29(2).
[62] 楊雪冬,季智璇.政治話語中的詞匯共用與概念共享——以“治理”為例[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1):74-88.
[63] 何艷玲.好研究是當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兼論“中國”作為方法論[J].中國行政管理,2020(4):56-63.
“Chinese Spirit” as an Iconic Concept:Semantic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Elucidation
MENG Xian,WEI Chonghui
(College of Marxism,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al resilience and practical endurance of “seeing reform through”,which is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eform Spirit”.The spirit is a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greatly enriches it meanwhile.As an iconic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ese Spirit” has its unique generation context and evolution process. The “Chinese Spirit” was nurtured and sprout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scious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salvation and survival,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riginal semantic concept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Soul”;It was generated and evolved from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CPC,expanding the double semantics of “spirit of the nation” and “spirit of the times”;It is regulated and deepened throug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ince the new era,gradually developing into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combines “macro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icro practical narrativ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u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irit” presents many basic aspects:adjust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Spiri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balancing the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Spirit”;the sublim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needs to be put into individuals’ spiritual strengthening;taking “Chinese Spir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as the method”. By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concepts,not only can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and knowledge coordinates of the “Chinese Spirit” be firmly established,but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a well and showcasing the real,authentic,and comprehensive images of China.
Key words:Chinese spirit;conceptual semantics;Chinese soul;spirit of the nation;spirit of the age
責任編輯 韓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