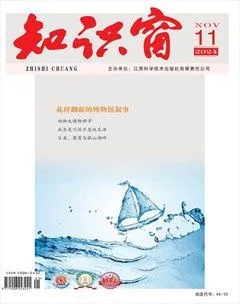游子的時光膠囊
老李:
好久不見!
這是我成為背包客在路上漂泊的第二年。迄今為止,我已經獨自走過中國的27個省(自治區、市),103座城市。怎么樣,我走過的地方是不是比你多?
想不到吧,你那循規蹈矩的女兒竟然叛逆了。畢竟19年的學生生涯已使她讀破萬卷書,她自然要趁風華正茂時行萬里路。這一路見山河湖海奇絕,品風土人情萬種,她才發現原來人在美景面前,總是難免笨嘴拙舌,詞窮語塞,才發現文字確實有著貫通感觀、穿越古今的力量。
還記得小時候,你陪我背過的那些詩嗎?幼時懵懂無知,背詩也如囫圇吞棗,好在那些年的棗核終于在一趟趟的旅途中汲足了養分,長出了茂密的枝葉,末梢正與感知美的突觸相接,記憶中的字句就忽然跨越千年,與眼前的美景交融,沁入胸腔,便有浪潮激蕩。
爸爸,我直到親歷之后,才真正知曉那些詩詞的精妙。
我在青海湖邊親眼見過“青海長云暗雪山”的奇景,才知邊塞詩為何壯闊蒼涼;打內蒙古曠遠的草原上走過,才知“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的比喻有多傳神;賞過杭州晴雨時的西湖,才知它為何“淡妝濃抹總相宜”;觀過鵬城日落時霧氣彌漫的海面,才知何為“煙濤微茫”,又為何“信難求”。
最難忘的還是2023年“五一”假期期間入晉,恰逢黃金周,我提前半個月都買不到火車票,無奈只能坐上長途大巴,苦熬9個小時才抵達山西。
彼時的北方,正是沙塵暴頻發的時節。下車時已近黃昏,卻不見殘陽如火,只見漫天的沙塵裹著一輪白日,像極了明晃晃的月。我忽然想起王之渙《登鸛雀樓》的那句“白日依山盡”,也終于明白為何“依山盡”時分的太陽不是紅日,而是白日——
想來也許正是登樓時適逢塵靄蔽日,使王之渙不能望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念頭才應運而生。
爸爸,在旅途中,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古老的文字仿佛有了生命,我與它們重逢,共鳴顫震,終于明白旅行的意義在于感受與經歷,而文字的意義在于記錄與留念。
這么說來,文字也是一個時光膠囊呢。
所謂時光膠囊,就是那些能儲存記憶的容器,視、聽、嗅、觸、思、情都能貯藏其中。打開的剎那,它就能帶溯流而上,回到事情發生的時候,記憶與情緒就一同浮出水面。
有關我們的時光膠囊,其實我偷偷存了不少,正好可以借著這封信,拿幾顆給你瞧瞧:一顆叫“廣播”,一顆叫“白霧”,一顆叫“夜路”。
你還記得那臺老舊的收音機嗎?只有當豎直長長的天線時,才能聽得清晰電臺里頭的字句。電視、電腦、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廣播成為幾乎被淘汰的媒介。可是爸爸,只要一聽到那密密匝匝的沙響和略微失真的人聲,我就會想起小時候秋冬的清晨,你喜歡早早地醒來,在被窩里聽廣播。那是我記憶里最溫暖的畫面之一,當年廣播里循環過的歌,時至今日我還能哼出來。
還記得小時候我問過你,為什么人在冬天的時候會哈出白氣嗎?你告訴我,熱氣遇冷會凝結,就成了我看到的霧。2023年冬末,我乘火車硬臥到鄭州,清晨出火車站覓食,在街邊喝了一碗羊肉湯。煮湯的大鍋沸騰著,白茫茫的霧就是冬日里最動人的煙火氣。忽然,我想起小時候你送我上學時一起在路邊攤吃過的小餛飩,它們也是從這樣騰著霧氣的大鍋中撈出,游進小小的碗里。一碗下去,渾身都暖和起來,我就覺得冬日不寒,萬事不難了。
你還記得我小時候怕黑嗎?我如今已經不怕了。那天在烏蘭哈達火山腳下,我一個人睡在租來的車里。在內蒙古的火山群中,我看到滿天的星子、淺淡的銀河。那時的我忽然很想你,想告訴你,我的膽子變大了好多,早已不再像小時候那樣,天一黑就連樓道都不敢走,非要你下來陪著才敢上樓。
爸爸,這些封存已久的時光膠囊本不該輕易打開的,因為回憶襲來時,人就不能不思鄉。
我一直覺得,思鄉的人念的總是童年的溫存和最依戀的人。
2024年4月,我漂泊到了長沙。前些天去開福寺數羅漢求簽,求得的簽文上有詩云:“游歷他鄉夢縈歸,身心不一久徘徊;縱有玉床纏玉帶,哪有自己家鄉美。”
我拿著那張簽文,在殿外坐了很久。也許是該回去看看你了。
爸爸,又是一年冬去春來。
回去的時候,我會折一枝他鄉的柳,捎給故鄉的你。
自古“柳”字就有“留”意。愿這枝柳條能代我留在你身邊,讓你知曉,無論我身在何處,你都是我的歸屬。
想你的女兒:小李
202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