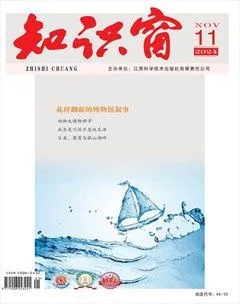他鄉夜色也撩人
我的伊斯坦布爾行程是在夜色中打開的。
圓月掛在舷窗外將我迎接,海面上倒映著的入海口城區的萬家燈火和我的心情一起閃亮。俯瞰那片大地,它的歷史無比深厚。隨著飛機的下降,我已經能看得見燈光作筆勾畫出的城市輪廓。
出了阿塔圖爾克機場,我們的出租車駛入機場高速,這條路一直鋪展到42千米外的金角灣。周末的小巷似乎還沒醒來,還要晚些才能入住預訂的客房,我們在咖啡店門口遙望對岸朦朧的尖塔和樓群,辨識著這些建筑的名字和由來:海岬最高處的托普卡帕宮掩映在樓群和樹林中被大海擁得緊緊,世界唯一有六座宣禮塔的藍色清真寺混在如叢林般的尖塔里難以辨認,灰蒙蒙的馬爾馬拉海鉆過拜占庭城墻的缺口,更寬的海面對面就是我生活的亞洲。此時,那似乎已經遙遠,我看不清楚哪里是少女塔,哪里是歐亞大橋。
因為倒時差,一整個白天我都睡在金角灣新城區的加太塔下舊樓里那張柔軟的床上。終于起床,我走出戶外,天已黑盡。燈光搖晃,像是掀起了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浪。在這個春風沉醉的夜晚,我與伊斯坦布爾正式相識。
我走過一條條小巷,石板路并不平坦,像這個城市的命運,充滿了坎坷、陡坡。我慢慢摸索著前行,向著海岸方向走去。
路上饅頭大小的卵石磨損著我的腳掌,高高低低的梯級折騰著我的腿。夜色里的漫游,雖然看不到喘出的粗氣,也能嗅到馬路邊的海風氣息。我在公交車站臺的角落處坐下,歇息著,觀望著,像一個偷窺者,悄無聲息。
在站臺座椅邊,有一對在暗夜冷風中相擁的年輕人。他們肩并肩,緊緊相偎,呢喃細語,生怕驚動了這寂靜時分。旁邊是沒有星辰打攪的夜空,是藍得閃亮的河流緩慢地流向大海,聽不懂土耳其語的我靜坐著,直到一個漂亮的金發女郎向我問路。
我打開手機地圖,打開翻譯軟件,竭盡全力地用我對伊斯坦布爾路途的一知半解,和她一起找到了她今夜的目的地。她致謝而去,走向車站背后小巷里的客棧,背影漸漸遠去。
在后來的幾天里,我天天都會去街頭、海邊,與伊斯坦布爾的夜晚接頭。每個夜晚,不管有沒有下雨,有時還是在子夜時分,我都沒感覺到孤獨。再深的夜色,都會有陪伴著我的伊斯坦布爾的貓,它們似乎無所不在,似乎像人一樣自由,悠閑。
伊斯坦布爾是名副其實的“愛貓之城”。夜深人靜,人們已入睡休息,貓卻像輪班的另一個主人。守在餐館門前,它們像個侍者;趴在商店的貨架下,它們形同保安;在公園廣場的燈光下,它們大搖大擺,或者睡在站前座椅上,占了乘客的座位。伊斯坦布爾的貓介于家養和流浪之間,它們不屬于某家某戶,而是任自己高興,游蕩于街坊之間,處于一種半家養、半野生的狀態。它們親近自然卻不排斥與人類接觸,與人類親密卻又保有自由與天性。那種自由自在,那種泰然自若,遠勝過我這兩腳直立行走的,時不時在夜色中目光惶然的生物。
有天晚上,我在客棧附近兜了幾圈仍沒找到正確的房間。伊斯坦布爾的網絡信號一般,我跟著手機地圖導航,卻總是繞著一條巷子轉圈。突然拐角處走來一只貓,我發現它很像早間我在客棧門口早餐店喝牛奶時,守著我面包屑的那個毛團。我突發奇想,循著灰貓的方步,躡手躡腳尾隨其后。神奇的是,我真的看到百尋不見的門牌——11號。
奧爾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寫道:“在我的童年時代,高樓大廈少之又少,夜幕降臨時,城里的房屋和樹木、夏日戲院、陽臺和窗戶的第三度空間都一抹而去,賦予城里歪斜的房舍、曲折的街道和起伏的山丘某種黑暗風采。”
這段幾十年前的伊斯坦布爾夜幕,與今天大同小異。它是一個我看不清楚面目而值得去慢慢認識的城市。來來去去,似乎有一種牽掛,系在身上,離去了,卻斷不了。當飛機在子夜時分騰起時,我揮別腳下的燈海,默默地說:“我會再來的。因為喜歡,因為夜色撩人而讓人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