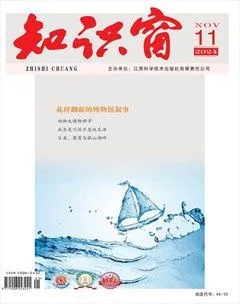馬福良:掐絲如發(fā),鏨刻入心
在華夏五千年的文明長河中,無數(shù)手工藝人憑借一雙巧手,將歲月與匠心凝聚成一件件不朽的藝術(shù)品。其中,花絲鑲嵌技藝以繁復(fù)精細(xì)、華麗典雅而獨(dú)樹一幟。有這樣一個(gè)匠人,他的雙手如同會(huì)施魔法,能將一根根纖細(xì)的銀絲編織成精美絕倫的花絲鑲嵌工藝品。他就是花絲鑲嵌技藝的國家級(jí)代表性傳承人馬福良。
自幼年起,馬福良就生活在花絲鑲嵌的世界里,那些細(xì)膩入微的、光華流轉(zhuǎn)的花絲鑲嵌作品,如同無聲的語言,講述著家族的故事與榮耀。他深知,這份技藝不僅是物質(zhì)的創(chuàng)造,還是精神的傳承。經(jīng)過多年的勤學(xué)苦練,馬福良能“掐”出直徑0.10毫米的銀絲,這是迄今為止花絲鑲嵌工藝可以達(dá)到的最細(xì)花絲。
然而,馬福良并沒有滿足于此,他開始嘗試將現(xiàn)代科技融入傳統(tǒng)工藝,引入激光焊接法等先進(jìn)技術(shù),提高了花絲鑲嵌技藝的精度和效率。他還積極探索新的材料和設(shè)計(jì),將花絲鑲嵌技藝應(yīng)用于更多領(lǐng)域,如首飾、擺件等,讓這門技藝更加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但如何將細(xì)花絲完好地焊接在一起?花絲越細(xì),控制焊火的難度就越大,為了攻克這個(gè)難題,馬福良反復(fù)試驗(yàn),不斷調(diào)整焊火的溫度和時(shí)間,終于找到了最佳的焊接方法。
每當(dāng)一件新作品的構(gòu)思在馬福良的腦海中成形,他便如同一個(gè)即將啟程的探險(xiǎn)家,滿懷激情地踏入未知的領(lǐng)域。在《天壇》這一作品創(chuàng)作之初,馬福良不僅搜集了大量的資料,還實(shí)地考察,力求將天壇的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都精準(zhǔn)地呈現(xiàn)在作品中。為了呈現(xiàn)天壇的宏偉與精致,馬福良采用了極致的細(xì)花絲技藝。那些細(xì)如發(fā)絲的銀絲在他手中仿佛被賦予了魔法,編織出了一幅幅令人嘆為觀止的圖案。在焊接環(huán)節(jié),他更是將溫度與時(shí)間控制到了極致,確保每一根銀絲都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牢固又美觀。當(dāng)《天壇》最終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時(shí),它不僅是一件技藝高超的藝術(shù)品,還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理解與尊重。
然而,隨著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加速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花絲鑲嵌技藝的傳承面臨斷代的危險(xiǎn)。為了將技藝精確無誤地傳授給下一代,馬福良開啟了“師帶徒”的傳統(tǒng)模式,他注重理論與實(shí)踐的緊密結(jié)合。在他的工作室里,新入門的學(xué)徒要從最基本的搓絲學(xué)起。那是一場(chǎng)手與心的對(duì)話,每一次的搓動(dòng)都需傾注全部的耐心與專注。馬福良會(huì)親自示范,手把手地教學(xué)徒如何控制力度,如何感知銀絲的微妙變化,直到那兩根銀絲在他的手中仿佛被賦予了生命,緩緩融合成一根細(xì)如發(fā)絲的完美花絲。
到了更復(fù)雜的掰花和焊接環(huán)節(jié),馬福良更是傾囊相授。他會(huì)讓學(xué)徒先觀察他的每一個(gè)細(xì)微動(dòng)作,理解其中的邏輯與美感,然后鼓勵(lì)學(xué)徒自己動(dòng)手嘗試。除了傳授技藝,馬福良還注重培養(yǎng)學(xué)徒的藝術(shù)素養(yǎng)和創(chuàng)新能力。他常常帶領(lǐng)學(xué)徒參觀博物館、藝術(shù)展,引導(dǎo)他們從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靈感,同時(shí)鼓勵(lì)他們將現(xiàn)代設(shè)計(jì)元素融入花絲鑲嵌作品,使傳統(tǒng)技藝煥發(fā)新的生命力。
掐絲如發(fā),鏨刻入心,這是馬福良對(duì)花絲鑲嵌技藝的最好詮釋。馬福良用實(shí)際行動(dòng)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匠人精神,讓花絲鑲嵌這門古老的技藝煥發(fā)出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