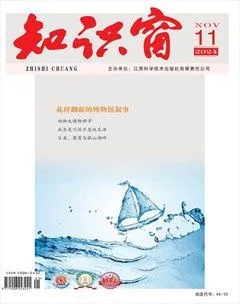記住每一朵花開的時間
有一回,巴黎殿堂級珠寶藝術世家尚美巴黎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舉辦了一場以植物為主題的展覽。他們從70多家世界博物館精心挑選了400多件珍貴展品,創作年份橫跨7 000多年,細致地展示了植物的方方面面。這里有新石器時期的植物筆壁畫,有需要梵蒂岡批準才能外借的《千花掛毯》,還有莫奈的《睡蓮》。為了讓展品呈現出自然的狀態,尚美巴黎特別使用了微彈簧工藝,用珠寶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動態的“植物標本”。比如,細看展會上的某個花冠,你會發現它在光線下的影子跟真正的植物并無二致;再如,某個繡球花胸針隨著布展人員的擺放而晃動,好像被輕輕拂過的一陣微風吹動了花瓣。
除了珠寶做的“植物標本”,展覽上還有繪畫、雕塑、織物、時裝等各種藝術形式的作品。在五花八門的展品中,有兩件繪畫作品很特別,那就是由16世紀宮廷畫家朱塞佩·阿爾欽博托創作的《春》和《夏》。它們是盧浮宮特別為尚美巴黎的這次展覽出借的。看這幅《春》,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個少女的側臉,有鼻子有眼。可當你靠近觀察才會發現,那張側臉上是玫瑰,是百合,是雛菊,是芍藥!原來,這幅肖像畫是由這些植物組成的。這幅肖像畫中一共有80多種花,并且都是在最美的花期綻放的樣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片葉子的脈絡與每一朵花瓣的姿態。看著百花在少女的臉上綻放,你會感受到植物天然的生命力,像是走在春天一樣。要知道,《春》創作于歐洲文藝復興的大背景下,那時畫師們的繪畫主題大都是“人”,比如神話里的女神、現實中的貴婦等。在絕大多數人都認可“人”才能構成理想美的時代,朱塞佩卻堅持讓植物成為畫里的主角,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那么,朱塞佩是怎么把植物畫得如此細致的呢?這與他作為宮廷畫師的經歷有著很大關系。那時,他侍奉的國王非常喜歡收集奇花異草,甚至專門在皇宮里建造了植物園。有了這樣的先天條件,朱塞佩可以深入地觀察每一種植物。比如《春》里面的80多種植物,它們的花期是不同的,朱塞佩要想畫好它們,必須記得每種花開的月份和具體時間段,再分別去寫生記錄。有一回,朱塞佩在畫一朵百合時,有個仆人走過來,他連忙做了一個“噓”的姿勢。仆人不解,卻也不敢動。朱塞佩神秘地說:“花開是有聲音的,我怕你吵到她!”仆人聽完撓撓頭,更加不解了。朱塞佩卻再也不多說一句話,只顧低頭畫畫。據說每一幅由植物組成的畫背后,他寫生的草稿都有好幾本。并且,這些寫生草稿還因為嚴謹這個特點被同時代的博物學家拿去做科學研究。正因如此,當同時代畫家還在描繪人的理想美時,朱塞佩已經通過與植物的朝夕相處畫下了他所看到的真實美。
對于普通人而言,大自然里的植物很多是大同小異的,因為它們的形態看起來差不多。實際上,植物每時每刻都在悄悄地、細微地生長著。大多數人不會留意到,但藝術家盯得可緊呢。他們與朱塞佩一樣,聽得到花開花落,秉承著“記住每一朵花開的時間”的創作理念,這樣才能做到復刻植物最真實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