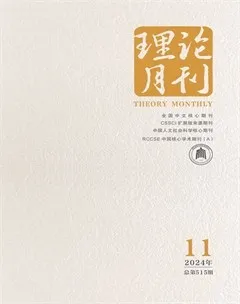胡塞爾陷入唯我論了嗎?
[摘 要] 胡塞爾的超越論現象學歷來被指責為唯我論。雖然在“第五沉思”中他聲稱已經揭示了唯我論的假象,但這依然沒有阻止之后的研究者對其現象學提出唯我論批評。其中一些批評者認為,即便同感問題得到澄清,胡塞爾哲學中的唯我論問題依然存在。其理由在于: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始終未被動搖;在胡塞爾那里缺少與超越論自我真正同等源初的他人。這些理由顯然不夠充分,可從三個方面反駁這一批評:其一,重新解釋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強調其認識論特征;其二,揭示超越論自我與交互主體性經驗的區別;其三,說明他人作為與“我”同等源初的構造主體的可能性。
[關鍵詞] 胡塞爾;現象學;交互主體性;他人;唯我論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11.016
[中圖分類號] B516.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11-0148-11
作者簡介:胡文迪(1992—),女,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后。
現象學研究者大都會同意胡塞爾對同感和交互主體性的討論旨在說明世界的客觀性。不過在相關著作和手稿中,他更明確提到的是現象學所面臨的唯我論指責。對此,無論是在早年的《現象學的基本問題》(1910/1911秋季學期講課稿)中,還是在較晚的《笛卡爾式的沉思》中,人們都可以找到相關說明。在這些文本中,胡塞爾也明確宣稱,借助對同感的現象學分析,唯我論假象已經得到揭示。因此,現象學,尤其是超越論還原之后的現象學,不應該再被指責為唯我論。
在批評者眼中,胡塞爾自我辯解的力量是微弱的,超越論現象學依然被認為是唯我論。這些批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意見認為,在以《笛卡爾式的沉思》“第五沉思”為首的文本中,胡塞爾對同感的分析并不成功,“結對”“相似性統覺”等概念并不足以解釋我們對他人的經驗。但仍能在胡塞爾現象學內部對胡塞爾澄清同感的方式作出修正,以說明超越論的交互主體性。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黑爾德(K. Held)。另一種意見認為,雖然胡塞爾在有限程度上澄清了同感,克服了笛卡爾意義上的唯我論,但由于現象學的主體性特征,他無法從根本上克服超越論的唯我論。因此,超越論現象學必須接受唯我論的標簽。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托尼森(M. Theunissen)、瓦爾登費爾斯(B. Waldenfels)、孫小玲等。
胡塞爾對同感的現象學分析盡管存在瑕疵,但通過在其內部進行一些修正和解釋,完全可以證明:胡塞爾在其現象學體系內成功澄清了同感,并揭示了唯我論假象。這大致符合第一種批評的立場。然而,由于胡塞爾沒有充分解釋超越論交互主體性及其與超越論自我的關系,第二種批評也顯得十分合理。但如果人們從胡塞爾的角度理解超越論自我的作用、作為超越論主體的他人,以及超越論自我同他人及交互主體性的關系,這一批評便會不攻自破。因此,本文著重考察以托尼森等學者為代表的批評,在澄清超越論主體、交互主體性及其關系等問題的基礎上,對這種批評作出回應。
一、胡塞爾現象學面臨的唯我論指責
在討論交互主體性之初,胡塞爾就預料到了對其現象學的唯我論批評,他也對這種批評作出了回應。這里不再重復這類批評,而主要關注澄清同感之后他再一次面臨的唯我論指責。在“第五沉思”中,在借助結對和相似性統覺說明了對另一個自我的經驗,也就是陌生經驗(或同感)之后,胡塞爾說出了下面這些易受批評的文字:
(1)在超越論的具體中,與這個共同體相對應的是一個相應敞開的單子共同體——我們稱之為超越論的交互主體性。我們幾乎無須說,單子共同體純粹是在我這個沉思著的自我中,純粹來源于我的意向性而為我地(für mich)被構造出來的,然而是作為這樣的共同體,它在每一個在“他人”這種變式中被構造出來的對象那里被構造為同一個,只是在另一種主體顯現方式中被構造,并被構造為其自身必然帶有的這同一個客觀世界。
(2)唯我論的假象被消解了,盡管這句話保持了基本有效性:所有為我而存在的東西,最終都從我自身、從我的意識領域得到了其存在意義。1
在通常的解讀中,這兩段文字都表明他人和單子共同體是“我”的同感的意向相關項,兩者在“我”的意向性中被構造為“為我”的存在。盡管共同體也在其他自我中被構造,但總的來看,共同體和其他自我最終依然是超越論自我的意向相關項,仿佛是沒有獨立性的附屬物。第二段文字似乎更是包含著顯而易見的矛盾,以至于澄清同感之前和之后的情況似乎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因為,超越論自我依然是唯一的、絕對的主體,他人作為“為我的存在”,最終是“從我的意識領域得到了其存在的意義”。而胡塞爾后來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中對超越論自我的“孤獨性”的說明,似乎也與前面的說法相互印證,再次加強了自我的絕對性和他人的依附性:
(3)……是我實行了懸擱,即使這里有好些人,他們甚至現實地與我一起實行懸擱,但是對于我來說,在我的懸擱中,所有其他的人連同他們的整個活動—生活也都包含到世界—現象之中,而這種世界—現象在我的懸擱中只是我的世界—現象。懸擱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哲學上的孤獨狀態,這種孤獨狀態是真正徹底的哲學在方法上的根本要求,在這種孤獨狀態中,我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個人,它由于某種甚至得到理論上辯護的固執……使自己從人類社會中隔絕開來,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知道自己屬于人類社會。我并不是那個總是具有自然有效性中的他的你和他的我們,以及他的由別的主體構成的總的共同體中的一個我。2
以上三段文字常常是批評者們指責胡塞爾現象學沒有真正克服唯我論的基本依據。對于上述第二段文字,從批評者的角度看,人們甚至可以說:與胡塞爾的看法恰好相反,如果“所有為我而存在的東西,最終都從我自身、從我的意識領域得到了其存在意義”這句話的有效性沒有被取消,唯我論假象就不可能被揭示。例如孫小玲就認為,盡管胡塞爾克服了笛卡爾式的唯我論,但是在這一過程中超越論自我的地位始終未被動搖,甚至共同體“都只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且“只能從‘我’之中獲得其意義與有效性”1,因此現象學沒能真正擺脫超越論層面的唯我論。孫小玲的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托尼森。根據托尼森的看法,“第五沉思”看似揭示了超越論唯我論假象,實際上又重新把超越論現象學帶入了唯我論,超越論交互主體性的澄清只是其超越論現象學的完成2。不過,他們眼里的這種“完成”,并非耿寧所說的是對超越論主體性作為交互主體性的進一步“闡明”3,而只是超越論自我的“自我解釋”。也就是說,“在對自己作為最終的構造者的肯定之中,我重新回到了自身的孤獨之中,這種不僅是起點處的而且也是終點處的孤獨標志著先驗主體共同體的不可能性,從而也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胡塞爾的主體際性論的最終界限”4。顯然,他們的批評矛頭最終都指向了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構造作用。
盡管托尼森承認,在胡塞爾那里,除了自我對他人的構造,也存在他人構造自我的說法;但他認為,這種可能性有一個隱含前提,即只有當他人在自我之中被構造為超越論主體后,他人才能成為構造自我(客體)的主體。與此同時,托尼森還認為,被他人構造為客體的自我成為單子共同體中的一員,由此也就喪失了其“源初主體”(ursprüngliche Subjektivit?t)的地位。因為“將由他人構造的自我貶低為我本身的一種脫源樣態,并對其宣稱我作為源初自我的地位,就已經是對他人的貶低”5。而另一位批評者瓦爾登費爾斯盡管肯定超越論自我在現象學中的作用與價值,卻認為在胡塞爾那里自我的優先性始終沒被動搖。雖然胡塞爾一再提高他人的價值,但是當他人作為“原自我”(Ur-Ich)而出場時,自我也就成為“原真的原自我”。當他人作為“另一個唯一者”而出場時,自我就是設定“另一個唯一者”的唯一者,縱使這個他人也被設定為另一個超越論自我。總之,如果自我的優先地位始終未被顛覆,胡塞爾的現象學也就必然無法免于唯我論的指責6。就如托尼森所認為的那樣,自我的這種絕對優先性帶來的問題是,他人可以從源初的自我這里汲取存在意義,“而我卻不必從在那里的他人處汲取我源初的存在意義”7。因此,瓦爾登費爾斯也認為,在胡塞爾那里缺乏真正的與自我同源的他人。
總而言之,在批評者看來,胡塞爾現象學作為唯我論有以下兩個應被指責的特征:第一,超越論自我是原自我,他人和交互主體性的意義來源和有效性基礎就在于這個自我。由此,他人是自我的意向相關項,以意向性的方式被包含在自我中。在意向性關系中,超越論自我是絕對的,而他人是相對的。第二,胡塞爾的超越論現象學抹殺了他異性,因此與自我同樣絕對、同等源初的另一個自我是不可能的⑧。
二、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
針對第一個特征,本文將在這一節和下一節分別從超越論自我的作用,以及超越論自我同交互主體性經驗的區分這兩個角度作出回應。這一節的分析旨在解除對“他人和交互主體性被意向性地包含在自我之中”“從我的意向性中獲得其存在意義”“現象學還原使超越論自我處于一種絕對孤獨中”等說法的誤解,從而反駁將超越論自我看作唯我論標記的主張。
先從對意向性的說明開始。對于現象學研究者而言,“意向性”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概念,指意識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與之相應,某物也總是被某種意識行為所意指的某物。這一概念也適用于同感。在胡塞爾這里,同感的基本含義是對他人(陌生自我)的經驗,他人在同感這種意識行為中被意指。“被意指”意味著,他人從我的意向性中獲得其存在意義,我對他人存在與否的設定有經驗依據而非憑空杜撰,據此我對他人的設定才是合法的1。“意義”在這里則指的是意向對象2,也就是意向相關項(Noema),它是我形成“他人”這個對象之經驗的核心。意義核本身的被給予也與意向行為不可分割3,例如觀察他人的行為動作、聽到他人的走路聲音等等,自我將所有這些不同的經驗在同感行為中綜合成關于他人的經驗,從而在同感意向中指向他人。
當胡塞爾談及他人和交互主體性從自我中汲取意義時,一方面,他強調的是這種經驗的屬我性。也就是說,是我對他人的經驗,而被我經驗到的他人則是對我而言的他人。另一方面,他強調的是關于他人的經驗離不開相應的意識行為(同感),通過意向性行為及與之相關聯的諸意義核心的綜合,作為對象的他人才能真正被我經驗到。因此,“超越論的交互主體性……純粹地在我之中”這句話指的就是:超越論的交互主體性以意指的方式,而非作為實項Rce9ee2rlQ42fWBV7L7WLqD71DUmWRDu+wIevl5L4tA=或實項部分被包含在我之中。同樣,在談到同感時,胡塞爾所言的他人在我之中,并非指他人被把握為自我的一部分,而是指他人被我意識到,或我具有關于他人的經驗。總之,他人和單子共同體都以意向性的方式被包含在我之中,而不是像我在內知覺中直接經驗到其自身那樣被經驗到。因此,他人和共同體沒有消融于超越論自我中。從這里也可以看到,胡塞爾在對同感的論述和相關術語的使用方面有著強烈的認識論色彩。事實上,在同感的問題上,他首先關注的就是認識論層面的問題,即我對他人的經驗以及他人存在與否的設定是如何可理解的。這些討論非但不會加強超越論自我的絕對主體性,反而會因其對他人的不可通達性的承認1而強化他人的主體性。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澄清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在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確切含義。在胡塞爾對同感的解釋中,連批評者們也一定會同意的是:不能從時間先后的角度去理解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在瓦爾登費爾斯看來,胡塞爾的意向性有三個特征:(1)具有對面物(Gegenüberhaben),(2)合目標的意指(zielgerechtes Meinen),(3)視域意向性2。對于同感來說,這三個特征分別意味著:(1)排除了相互性,(2)意指行為只是從自我單方面地發出,因而(3)他人在世界總視域中是被排除的。意向性的這三個特征共同形成了自我相對于他人的優先地位。此外,在意向性中,處于主動的、優先地位的自我是一個絕對主體。這體現在托尼森指出的胡塞爾現象學中自我的三個特征上:“不涉世”(Unweltlichkeit)、“向來我屬(Jemeinigkeit)”和“絕然獨立”(Absolutheit)3,這三個特征都指向絕對的、唯一的自我。
同時,我們還應清楚,在胡塞爾那里,超越論自我是通過懸擱和超越論還原獲得的。但它并不是還原超越物后的直接剩余物,而是作為“內在的超越”的不可被還原之物。關于這個自我,胡塞爾指出,它“屬于每一來而復去的體驗,它的‘目光’‘通過’每一個現實的我思而朝向對象”,它是“原則上的必然之物,在體驗的所有真實的和可能的變化中,它作為絕對的同一之物,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被看作諸體驗本身的實項部分或要素”4。
超越論還原與胡塞爾使用的所有現象學還原方法一樣,一個最基本的目的是審查“某些觀點的合法性”,這關涉的是一種“權利/合法性,一種設定通過在它之中被設定之物的直觀被給予性而獲得了這種權利/合法性”5。簡言之,現象學還原的目的就是對設定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進行檢驗。無論是超越論自我,還是“第五沉思”中的原真自我,都首先在這一目的之下被理解。盡管自我在胡塞爾那里的含義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在同感中,自我及其直接經驗主要被理解為設定他人的依據或基礎。
正如瓦爾登費爾斯所說,對胡塞爾而言重要的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徹底的自身負責和自身合理化”。與這種徹底主義相聯系的是“對絕對確定性的尋找”,而能夠保證絕對確定性的只有“意識的絕對”。胡塞爾的這些目標“一方面指向進行奠基的真實性,另一方面指向意識”6。確實,在闡明現象學還原時,胡塞爾常常以笛卡爾“我思”的絕然明見性為參照點,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地位也在這一背景下不斷得到凸顯。胡塞爾對同感和交互主體性的討論也循著這條線索展開——相較于我對他人的經驗,“我思”以及我的直接經驗內容更具明見性。
顯然,在意向性和現象學還原中得到強調的自我的優先地位及絕對性,與胡塞爾在現象學中關心的問題有關,也就是認識的可能性問題1。因此,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也應該從認識論角度來理解。絕對性意味著絕對不可被懷疑的認識,在這種認識中沒有任何預設,絕對無疑之物恰好是超越論還原之后的剩余物。作為貫穿這些剩余物的不可被還原者,超越論自我也具有絕對性。而優先性指的是超越論自我從第一人稱視角出發所獲得的經驗具有奠基作用,它是最確定的和最不可被懷疑的認識,其他的認識都在這個牢靠的基礎上被建立起來。
瓦爾登費爾斯盡管看到意識(或“我思”)及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的含義及重要作用,但仍然批評這種絕對性和優先性會導致自我與他人的不對等,或者如托尼森所說的,他人與超越論自我不具有同等源初性。在他看來,他人在我之中被構造,也就意味著通過我對他人的經驗而得到設定,這類似于“我允許了陌生的要求,我才會回應”這種做法。只有當“他人的請求先于我的主動性”,這種不平等的限制才可能被打破2。
事實上,無論是瓦爾登費爾斯,還是其他類似的批評者,從一開始就將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放入了預先想要討論的對話關系之中,也就是在存在論和實踐哲學中來理解自我相對于他人的絕對性和優先性。在這一背景下,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便是“我—你”的社會關系的優先性。這是一個“更高階的問題域”3,它在胡塞爾那里以超越論現象學為基礎。但這種替代方案則相反,是把“我—你”的社會關系當作超越論現象學的前提。他們從存在論和社會哲學的立場批評胡塞爾,其實已經超出了胡塞爾討論同感的問題范圍。他們在胡塞爾那里尋找他根本就沒有提出的問題的答案,勢必會失望。而且對于瓦爾登費爾斯的例子,我們還可以提出這樣的反駁:只有當我聽到了或意識到了他人的請求,我才能加以回應。其中或許依然不存在瓦爾登費爾斯所說的平等,但也并未排除他人與自我具有同等的主動性和相互獨立性的可能。
在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中,我們確實無法找出瓦爾登費爾斯所要求的那種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嚴格的平等性。因為自我經驗總是具有相對于他人而言的確定性,在自我權能性的輻射范圍內,距離我的直觀經驗越遠的認識,越不具有明見性和確定性。但通過對意向性和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的解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胡塞爾對超越論自我的強調至多只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自我學,而與存在論上的唯我論無涉。
三、超越論自我的交互主體性經驗
超越論自我首先是超越論還原之后剩余下來的特殊“超越物”,它也可以在反思中被給予,與這種自我有關的科學被胡塞爾稱為“現象學的自我學(Egologie)”4。在其中,人們可以談論超越論自我的經驗。對于唯我論指責,這里要反駁的第二點在于:雖然胡塞爾現象學是主體性哲學,超越論自我在其中有獨特地位,但是我的經驗并非唯我論式的經驗,而是交互主體性的經驗或共同經驗。
唯我論式的經驗可以被理解為“私人經驗”,類似于維特根斯坦所說的“私人感覺”。在私人經驗中沒有同感的可能,因為這種經驗只能為此主體所知,而不能通過同感被其他自我經驗到5。但超越論自我的經驗顯然不能被理解為私人經驗,他人的經驗也可以通過同感間接地被給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由第一人稱“我”表達出來的共同經驗。這意味著,超越論自我的經驗盡管使用了第一人稱,由此被看作我的經驗,但它也可以是交互主體式的經驗。通過同感獲得的他人經驗并不直接就是我自己當下的經驗,而是在被我同感到的意義上被看作我的經驗,或被我經驗到的他人的經驗。而在另一些情況中,我與他人共享相同或相似的經驗,雖然這種經驗也屬于我,卻并非我所獨有,而是一種共同經驗。
在目前對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的研究中,超越論自我的經驗不是唯我論式的經驗而是交互主體性的經驗這一特征還未受到充分重視,但這一點在胡塞爾1910—1911年的《現象學基本問題》的講課稿中就已初見端倪。胡塞爾在其中提到對超越論經驗范圍的擴大,超越論經驗并非只限制在知覺經驗上,還包括回憶、期待和同感等意識活動所獲得的經驗1。與此同時,自然不只是單個自我的意識行為的相關項,而且“是關于一個無所不包的、按一定秩序進行的過程之標志,這個過程包括一切借助同感相互處于經驗聯系中的意識流”2。由作為指引的自然追溯相關意識經驗便會發現,這種意識經驗不是只屬于單個自我的經驗,而是通過同感被關聯起來的共同經驗。這類想法在之后的思考手稿中也多次被提及,如胡塞爾在《共主觀性現象學》第2卷的文稿17中指出:
但是人們現在會說,如果世界只不過就是所謂的客觀經驗之內在的意向性之極的系統,也就是對于我而言是內在的——盡管是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即處于我的內在性中,在一致的證實中可無限地視為同一的——那么我就是孤獨的自己(solus ipse)。
對此的回答是:世界是我的諸經驗之統一,但不僅是我的經驗(當然是諸現實的和可能的經驗)之統一,而且按照其固有的意義,也是交互主體性的統一。3
盡管胡塞爾也時常談及完全排除了陌生經驗的原真領域,但它與這一節的討論并不沖突。超越論自我的經驗是一種共同體經驗,“包含我的原本的經驗和被施以同感的,并作為被現實指示的陌己的經驗,而且包含對自己的經驗和被指示的陌己的經驗視為同一的綜合之諸可能性”4。也就是說,超越論自我的經驗其實可以區分出兩層:第一層是原真自我的經驗,也即原真領域,人們也可以將這個領域稱為“私人經驗”領域,這個領域具有唯我論色彩;第二層是交互主體性經驗,其復雜之處在于,它既是他人的經驗,也是我的經驗,它們借助同感被關聯起來。第一層經驗與第二層經驗一起由同一個自我所統一,被歸于“我”這個第一人稱之下。但歸根結底,超越論自我的經驗并不只是我的經驗,而是交互主體性的,故上述兩層次的區分以及原真還原都只能是一種人為的、抽象的區分和還原。同樣,盡管在這里我們只是談論自我,但實際上這種交互主體性的經驗也是他人的經驗,也可以由他人的自我所統一,形成對其而言的經驗統一、其他的自我對陌生自我和客觀世界的經驗。
至此,我們已在消極意義上表明,盡管胡塞爾側重于說明超越論自我的構造作用,但這不會導致批評者所說的唯我論。接下來,我們還應在積極意義上指明他人作為另一個超越論自我的獨立性和他的構造作用,以及在這個意義上與我的自我同等源初的可能。
四、另一個超越論自我及其構造功能
如上所述,如果人們試圖在存在論或實踐哲學的意義上尋找一個與自我同等源初的陌生自我,那么這一嘗試在胡塞爾那里無疑會落空。但從超越論角度看,自我和他人作為超越論主體,本質上是等值的。因此,這里的反駁主要針對唯我論批評的這一看法:在超越論態度中另一個自我與我的自我不具有同等源初性,故胡塞爾交互主體性現象學仍是唯我論的。下面從兩個方面展開說明:其一,他人的自我不能被我直接經驗到,其主體性不是我的直接的構造成就;其二,他人的自我作為另一個超越論自我,和我的超越論自我一樣是進行構造的主體,但無論是我對他人的構造還是他人對我的構造,既不會造成對我的自我的貶低,也不會造成對他人的自我的貶低。
(一)他人的自我不能直接被經驗到
胡塞爾在“第五沉思”中提出:他人不能像我自己那樣原本地被給予我,我對他人的經驗也無法像原真領域中的其他知覺經驗一樣得到真正的充實;相反,能夠不斷得到證實的只是一個指示出他人的線索1。
首先,從空間關系上來說,另一個自我的軀體所在的空間位置“這里”不能同時是我和我的身體所處的“這里”。“我親身存在于這里,是一個圍繞我定位的原真‘世界’的中心”2,與之相似,他人的自我和他所處的位置同樣是這樣一個“中心”。從胡塞爾所說的原真領域的意義上看,這是兩個獨立的領域,因此他人主體及其周圍世界不是我的本己領域的一部分。盡管借助結對和共現,我可以經驗到他人及其本己領域,但是這種“統覺/共現”永遠不能通過“體現”(Pr?sentation)得到完全充實3,而只能在新的共現中得到充實。因此,雖然他人常常被胡塞爾說成是另一個自我,是原真自我的變式,但其始終不能與我的原真自我相等同,也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自我。在對他人的經驗中,統覺不能以體現的方式所充實,這一點昭示著他異性的可能。此外,在對他人之經驗的經驗中,也同樣可以說明他異性沒有被抹殺。
根據胡塞爾的觀點,在同感中被我經驗到的是“另一個自我之意識”,但我不是像體驗到和知覺到我自己的意識那樣,“在內在的知覺中、在洛克式的反思中,體驗到和知覺到這種意識的”4。對這種經驗式的同感進行的現象學還原是一種“雙重現象學還原”,即一個針對的是同感行為本身,一個是被同感到的對象5。
在雙重還原中,人們可以清楚看到,被同感的材料和同感行為本身不屬于同一意識流。這表明,雖然他人及其經驗被我同感到,但屬于他的自我的意識流與我的自我的意識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統一體。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被同感到的意識所屬的另一個意識流統一體就是第二個自我。他人作為另一個自我被給予我時,我經驗到的這種統一性“不是我的諸感覺之統一和通過諸感覺而進行著透視變形(Abschattungen)之統一”,而是“第二個超越論的主體性,它是在我之中本源地顯示出來的(但原則上只對其自己本身而言才在自身反思中是可被知覺的)”1。
在原真還原的情況下,原真自然不是像內在體驗一樣作為實項內在于我之中,而是作為意向相關項在構造物的意義上內在于我。而wTITYmZ+vSIkppt2dLUsiA==另一個“我”,既不在實項意義上內在于我,也不在作為一般的空間事物的意義上內在于我,而是“在某種原真的多樣性中(在我的進行深入理解的、賦予靈魂的諸經驗中)”被構造起來,并“作為另一個自我為其自身存在”2。對另一自我的構造之所以不同于對一般的空間事物的構造,主要是因為他不是直接被我經驗到的,不像自然物一樣屬于我的原真領域,而是有其自身的獨立性。他以一種獨特的意義“為我存在”,即他也是一個超越論的主體,為其自身而存在。他人的自我超出了我的原真領域,是一種“新式的超越性”3。
他人的主體性通過他人身體的顯現被我經驗到,但不是直接被經驗到,我直接經驗到的只是一個軀體和身體行為。事實上,在“第五沉思”中人們就可以看到,我既不能像經驗自己那樣直接經驗到他人的自我,也不是借助推理得出這個自我,而只是在共現中間接地經驗到他人的自我4。這意味著,他人的主體性永遠不能直接被我把握。然而,從批評者的觀點來看,我仿佛能夠直接經驗到他人的主體性。這種誤解隨即導致這樣的認識:他人的超越論主體性是我的構造成就,和其他自然事物一樣屬于我的原真領域,因而他人只是我的原真領域的一部分。由此,就會不可避免地得出唯我論的結論。
(二)作為構造主體的他人
至此已經清楚的是,對他人的構造的確體現了我的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但這并沒有抹殺他人也是構造主體這一事實。在胡塞爾那里,“處于中心的不是構造的交互主體性,而是交互主體性的構造”5,即他更多討論的是作為被構造者的他人,而不是作為構造主體的他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人只能作為被構造者而存在。
其實,以托尼森為代表的批評者們并非沒看到他人作為超越論主體所具有的構造作用。只是托尼森認為,即便作為構造主體,他人的自我對我的構造這一行為本身也是我的同感所意指的對象。不僅如此,被他人同感到的自我成為眾多單子中的一個,這意味著,如此這般被構造的我的自我脫離了絕對性特征,這既是對我的絕對自我的貶低,也是對他人的絕對自我的貶低6。顯然,托尼森誤解了他人對我的自我的構造的含義,也沒有注意到自我與他我在被給予方式上的差別。
從胡塞爾討論交互主體性問題的初衷來看,他人作為本己自我以外的超越論主體,其構造作用首先體現在對同一個自然的構造上。胡塞爾指出,被我經驗到的這個自然也可以被還原到他人的經驗系統上1。不過,在超越論態度中,這同一個自然不是以如下這種方式被經驗到的:自我與他人首先在彼此完全孤立的狀態下經驗到這個自然,然后這些經驗借助萊布尼茲式所說的“前定和諧”相互關聯,最后形成對客觀自然的經驗,也就是一種交互主體性的經驗。實際的情況是,自然始終在自我與他人的相互同感的伴隨中以共同的經驗的形式被意指。
他人的構造作用不僅體現在對同一個自然的構造上,也體現在他人能夠將我視為其意向相關項這一點上。從認識論的立場看,就像他人的自我不能成為我的直接經驗的對象一樣,我的超越論自我也不能成為另一個超越論自我直接經驗的對象。這就是說,在對他人的經驗中,我只能經驗作為現象的他人,而他人的主體性則只是以共現的方式被間接經驗到。反之,他人對我的經驗也是如此。
絕對主體意義上的自我是因意向性和超越論懸擱而產生的,盡管許多自我可以一起實行超越論懸擱,但每個自我只能就其自身和他所經驗到的世界進行懸擱2。與之類似,對超越論自我的直接經驗只有在每個自我對其自身的反思中才是可能的3。而在對身體的經驗中,我的身體“是在主體的顯現方式中被給予我自身的”4。
在他人對我的經驗中,他人作為被我同感到的主體,“以一種外在的顯現方式擁有”5我的身體,也以外在的方式經驗我的自我。盡管他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構造作用是被我同感到的,但這只是強調了“被我意識到”這一認識特性,而不是表明這種構造作用是我賦予他人的能力。
正是在陌生經驗的基礎上,每一超越論的主體都被客體化為人,“這個人是主體,與它相對,有處于其對面的另一主體……這個主體對于其自身而言是在‘內在的’方式中(以唯我論的方式)被給予的,而在外在的方式中(在交往中)它被給予它的對面者,并且這是相互的”6。“內在的方式”指的是我對自身而言作為絕對主體被給予,胡塞爾所理解的唯我論的方式其實就是內在的方式;“外在的方式”則指我對他人而言作為其對象被給予,并且彼此處于相互交流中,這時我就是被他人構造的,是他人的意向相關項。
在這種交互主體性經驗中,第一人稱中的絕對自我才能被客體化,從而與他人一樣被經驗為眾多單子中的一個。在這個意義上,我的自我對他人(陌生自我)而言是他的構造成就,我的存在意義來源于他的意向性。由此,胡塞爾才提出:超越論自我既是相對于其現象而言的絕對的、無人稱變格的自我,也是可變格的自我、作為眾多超越論他者中的一員的自我,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只是表面的7。因此,我作為超越論的自我與作為眾多單子中的一員只是自我的兩個面向。
總而言之,每一個自我,內在地看是包含其他單子的超越論主體,外在地看則是眾多單子中的一個。每個單子自我既是獨立的,也與其他單子自我相關聯。在這種理解中,作為超越論主體的自我與作為眾多單子中的自我可以是同一個8。因此,使我成為眾多單子中的一個,這既不意味著對我的主體性的貶低,也不意味著對在構造活動中將我的主體性客體化的他人的貶低。不僅如此,每一個超越論自我都通過同感認識到他人也是一個超越論自我。而這意味著,我和他人都是超越論主體,我們具有同等的絕對性。
五、結語
胡塞爾交互主體性現象學所面臨的唯我論指責主要是從實踐哲學和倫理學立場作出的①。透過這一立場,對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的這些唯我論指責,實質上可以看作從類似列維納斯的倫理學角度出發,用他者的絕對性對胡塞爾現象學中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提出的挑戰。但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首先關注的并非倫理學中的他異性問題。假如人們能正確理解超越論自我的絕對性和優先性的意義和作用,而不是從倫理學和存在論角度曲解,或許會同意,超越論唯我論即使存在,對于胡塞爾的整個現象學體系而言也不是致命的。
不過,即便不是從倫理學角度,而是從胡塞爾的現象學體系內部提出唯我論的批評,其實也是不成立的。這不僅是因為,不能將超越論自我與交互主體性經驗相等同,由此也就不能把超越論自我的經驗看作是唯我論的或私人的經驗;也是因為,超越論自我兼具向內的統一性和向外的開放性。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不是缺少與超越論自我同源的伙伴,而是每個自我都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尋找認識的堅實基礎。這個自我在內部是統一的,但不是封閉的。與其說這是唯我論,毋寧說——如大多為胡塞爾辯護的研究者所認同的那樣——是自我學。只有在人們只看到超越論自我的內在統一性并將其誤解為自身封閉“單子”,而沒有注意到其向外的開放性的情況下,才會將其理解為唯我論。雖然胡塞爾自己也會誤導性地使用“唯我論”這個表達②,但在他的現象學中,除了賦予“唯我論”以特殊含義外(一種內在的、第一人稱的經驗方式),這始終只是一種方法上的權宜之計③。而且對他來說,自我只是起點,而非終點。
責任編輯 羅雨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