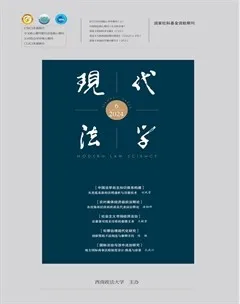刑事一體化視角下的輕罪應對
摘 要:我國現行《刑法》未對輕罪作出明文規定,但大致可以將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歸入輕罪的范疇,當然特定犯罪除外。近年來輕罪激增的原因較為復雜,既有立法層面增設輕罪這一直接原因,也有司法層面基于刑罰輕緩化的政策要求和形勢變化的時代背景而提升定罪量刑標準這一重要原因。未來,應在刑事一體化視野下妥當應對輕罪。就貫徹刑法謙抑原則而言,最為緊迫的是通過優化定罪量刑標準有效控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多發輕罪的入罪范圍;就推進綜合治理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實現行刑有序銜接,既要立足當下通過司法裁量實現“出刑轉行”,又要立足長遠謀劃對《刑法》規定的行為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允許比照適用,實現“兩法銜接”,切實發揮《治安管理處罰法》事實上的“輕罪法”作用;就貫徹程序優先理念而言,要充分發揮審前分流作用,避免輕罪案件“扎堆”進入審判程序,并在降低羈押率的前提下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就完善前科制度而言,可以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為突破口,并采取“程序修法先行,實體修法跟上”的具體策略,進一步實現犯罪的輕重有序治理。
關鍵詞:輕罪;行刑銜接;危險駕駛罪;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中圖分類號:DF61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12
隨著我國犯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而邁入輕罪時代,此前的犯罪應對模式得以相應調整。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醉駕犯罪對策的調整。①當前,亟須通過從整體層面優化思路、從操作層面強化舉措的方式推進輕罪的系統應對,特別是宜堅持實體與程序并重、立法與司法并行、綜合治理與刑事治理結合的思路,在找準原因的基礎上“對癥下藥”,妥當調適輕罪應對模式。基于此,本文基于刑事一體化的視角,在厘清輕罪范圍的基礎上,分析輕罪成因并評析當下輕罪應對策略,提出輕罪應對模式的未來改進之道,以期助益體系化治理并務求實效。
一、輕罪范圍的厘清
顧名思義,輕罪就是處罰較輕的犯罪。從域外立法來看,一些國家在刑法中明文規定了輕罪概念。例如,《德國刑法典》第12條規定,輕罪是指最高刑為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科處罰金刑的違法行為。【參見《德國刑法典》,徐久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長期以來,我國缺乏區分輕罪與重罪的傳統,而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亦未對輕罪作出明文規定。在此背景之下,確有必要對輕罪的范圍加以厘清。
(一)以刑罰輕重作為輕罪與重罪界分的基本標準
通常而言,罪之輕重取決于刑之輕重。隨著近年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將三年有期徒刑作為輕罪與重罪的分界線,把輕罪界定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的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同。本文亦原則上贊同這種劃分,但同時認為刑罰較輕是認定輕罪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有必要討論的問題是,界定輕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毫無疑問,劃分輕罪與重罪,目的在于對輕罪采取不同于重罪的刑事對策。【例如,就德國而言,“在實體法上,在法律技術上加以簡化的兩分法是為區分刑事可罰性的等級服務的。因此,重罪的未遂總是應受刑罰懲罰,輕罪的未遂僅僅在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應受刑罰懲罰(第23條第1款)。教唆未遂和其他一些處在參加犯罪之前階段的情況,在重罪時應當受到刑事懲罰,但在輕罪時一般不會受刑罰懲罰(第30條)。公職資格的喪失和選舉資格的喪失也以類似的方式與這個區分相聯系(第45條第1款)”。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頁。】這就要求納入輕罪范圍的犯罪在罪質上具有相近性,適宜采取相同的對策。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的罪質通常相近,但亦有例外。特別是在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和極端主義、軍人違反職責等犯罪中的不少罪名,法定刑配置亦包括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將上述犯罪納入輕罪的范疇,實際不利于對其采取適宜的政策。例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以下簡稱《反恐怖主義法》)的規定,對被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恐怖活動罪犯和極端主義罪犯,在刑滿釋放前經評估確有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作出責令其在刑滿釋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決定。【《反恐怖主義法》第30條第1款規定:“對恐怖活動罪犯和極端主義罪犯被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監獄、看守所應當在刑滿釋放前根據其犯罪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服刑期間的表現,釋放后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等進行社會危險性評估。進行社會危險性評估,應當聽取有關基層組織和原辦案機關的意見。經評估具有社會危險性的,監獄、看守所應當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議,并將建議書副本抄送同級人民檢察院。”】顯然,對于所涉犯罪即使刑罰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亦不應納入輕罪的范圍。
此外,還有必要提及微罪的概念。顧名思義,微罪就是輕微的犯罪。有觀點認為,微罪是與重罪、輕罪相對應的概念,微罪與輕罪的分界線應設定為一年有期徒刑。【參見梁云寶:《積極刑法觀視野下微罪擴張的后果及應對》,載《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7期,第36頁。】本文雖然原則上贊成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界定微罪的標準,但同時主張將適用緩刑的犯罪也納入微罪的范疇。從形式上看,緩刑的對象包括被判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超過了前述對微罪的刑罰以一年有期徒刑為界的主張。但是,就一般社會觀念和實際效果而言,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緩刑會輕于一年有期徒刑實刑。基于此,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或者適用緩刑的犯罪都可以納入微罪的范疇。同時,不宜將微罪作為與輕罪相區分的概念。實際上,微罪應屬于輕罪中法定刑較輕的部分,二者屬于包容關系而非排斥關系。從立法上看,妨害安全駕駛罪、危險作業罪、侵犯通信自由罪、高空拋物罪等罪名的法定刑均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均可以納入微罪的范疇;而危險駕駛罪,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代替考試罪的最高法定刑均為拘役,屬于微罪之中刑罰更輕的微罪。將微罪納入輕罪之中,可以對微罪直接適用輕罪的模式,并基于微罪的特殊性采取更為特別的對策,以促使微罪的應對更為有效。
(二)區分立法成因與司法成因細分輕罪
我國有學者將輕罪劃分為了純正的輕罪與非純正的輕罪。其中,純正的輕罪是指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非純正的輕罪,也可以稱為罪量意義上的輕罪,是指無論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否為三年有期徒刑,只要該罪的法定刑中包含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該部分犯罪就屬于輕罪。【參見陳興良:《輕罪治理的理論思考》,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3年第3期,第5-6頁。】本文雖然原則上贊同上述類型劃分,但認為應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立法成因的輕罪與司法成因的輕罪。
有效應對輕罪必須做到“對癥下藥”,這就要求厘清輕罪的成因,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區分立法成因與司法成因。唯有如此,方能對輕罪的現狀作出妥當的評價,同時對輕罪的應對提出有效建議。正如后文所述,近年來輕罪數量和占比的大幅增長,既有立法層面增設輕罪這一直接原因,也有司法層面基于刑罰輕緩化的政策要求和形勢變化的時代要求而提升定罪量刑標準這一重要原因。不討論輕罪的成因,徑直質疑當前輕罪占據主導地位的犯罪結構,無疑是不可取的。緣于具體案件的情況比較復雜和司法裁量的需要,《刑法》分則中立法者給多數犯罪設定的法定刑幅度區間跨度較大,從而使司法實踐中容易出現具體犯罪觸犯的罪名法定刑配置較高但實際判處的刑罰較輕的情況。以盜竊罪為例,法定刑涵括“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等區間。隨著相關司法解釋對升檔量刑標準的提升和對盜竊行為得手數額規定得越來越低,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盜竊案件越來越多。顯然,這類輕罪的形成,應當主要歸于司法成因,與立法增設而形成的輕罪具有明顯不同。由此可見,區分立法成因的輕罪與司法成因的輕罪具有現實意義,這是深入分析輕罪形成原因和妥當應對輕罪的前提和基礎。
基于此,借鑒純正的輕罪與非純正的輕罪的區分方法,可以將輕罪區分為立法成因的輕罪與司法成因的輕罪。所謂立法成因的輕罪,是指立法設定的輕罪,即立法規定的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此類犯罪在具體適用之中必然屬于輕罪。所謂司法成因的輕罪,是指司法形成的輕罪,即立法規定的法定刑雖然包括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但最高法定刑超過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此類犯罪在具體認定時并不必然屬于輕罪,如果具體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則該部分犯罪屬于輕罪的范疇。
二、輕罪多重成因的探究
妥當應對輕罪的前提是厘清輕罪現狀的成因。輕罪激增不能簡單歸因于立法層面增設新罪,而是立法、司法、程序等多個層面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一)立法成因:立法體系與輕罪適用
1997年《刑法》施行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基于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先后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和12部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作了13次修改。1997年《刑法》規定了413個罪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法釋〔1997〕9號)確定了413個罪名,《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見》(高檢發釋字〔1997〕3號)確定了414個罪名。】,歷經多次擴充之后形成了483個罪名的現狀。在新增罪名中,相當比例的罪名配置的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罰,且個別罪名配置的法定刑為拘役。這意味著我國進入了輕罪立法時代。輕罪立法體系的逐步成型對司法適用中輕罪的數量激增和占比攀升產生了直接影響。
1.基于社會危害考量增設輕罪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領域越來越廣,需要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規范加以規制,以有效防范風險。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八)》)增設最高法定刑為拘役的危險駕駛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九)》)增設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最高法定刑為一年有期徒刑的妨害安全駕駛罪、危險作業罪、高空拋物罪。這些輕罪的增設,緣于對新出現的社會風險防范的需要。例如,增設危險駕駛罪就是為了防范道路危險駕駛行為逐漸增多的風險。
2.基于犯罪治理方式調整增設新罪
新近《刑法》修正體現了犯罪治理方式的革新,最為明顯的當屬刑法防線的適度前移。具體而言,基于有效防治犯罪的需要,對預備行為或者幫助行為獨立入罪處罰。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對網絡犯罪預備行為和幫助行為獨立入罪,增設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正因為如此,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實際上屬于兜底罪名(堵截性罪名),即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或者幫助他人實施信息網絡犯罪,在無法構成其他犯罪的前提下,可以適用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予以懲治,以堵塞刑法規制漏洞。【正因為如此,《刑法》第287條之一和第287條之二的第3款均規定:“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作為堵截性罪名,自然不能配置過高的刑罰,否則無法體現堵截的屬性。基于此,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法定刑均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屬于典型的輕罪。
3.基于分流入刑需要增設新罪
新近《刑法》修正所增設的不少犯罪原本系受行政處罰的行為。以《刑法修正案(九)》為例,其重要使命之一即為“做好勞動教養制度廢除后法律上的銜接”。【參見李適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說明——2014年10月27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15年第5期,第827頁。】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廢止了實施50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對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但尚不構成犯罪的行為,只能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難以適應懲治、震懾所涉行為的現實需要。為了填補治安管理處罰與刑罰之間的“斷檔”,適當擴張刑法的規制范圍,對過去應予勞教的行為適度分流入罪,已是必然。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通過擴充罪狀、增設新罪等方式,將一些危害社會的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就增設新罪而言,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就是合適的例子,即對于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行政處罰后仍不改正,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確應納入刑法規制范圍,但配置的刑罰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屬于典型的輕罪。
4.基于試探性立法屬性增設新罪
新近《刑法》修正增設的不少犯罪,并非簡單的犯罪圈擴充,而是體現了犯罪規制理念的變遷。例如,與此前規制網絡犯罪的立法思路明顯不同,《刑法》第286條之一規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則是在信息網絡日益普及的時代背景下,針對犯罪與信息網絡交織的情況,基于強化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而增設的專門罪名,旨在通過有效落實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而有效防范信息網絡違法犯罪的發生。這實際上屬于“新型信息網絡犯罪”的范疇。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犯罪的增設并無先例可循,實際上屬于試探性立法,配置較低的刑罰也是務實的選擇。緣于此,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的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屬于典型的輕罪。
(二)司法成因:司法激活與輕罪適用
立法是基礎,司法是關鍵。新近刑法增設輕罪屬于客觀事實,但不能據此徑直將輕罪激增歸因于立法。毫無疑問,《刑法》分則配置的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罪名在全部罪名之中仍有相當比例,即立法層面的罪名仍然以重罪為主。由此可見,對于輕罪激增的現狀,除了立法層面的原因之外,更應當關注司法層面的原因。
1.司法對策調整激活純正的輕罪的適用
立法所增設的純正的輕罪,亦需要通過司法環節才能轉變為實際案件。特別是同一罪名面臨較大幅度的適用差異,正是說明司法對輕罪的激增作用不應被忽視。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為例,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的最初幾年,該罪名的適用并未出現案件激增的情況,甚至可以說案件較少。然而,2020年10月“斷卡”專項行動開展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被“激活”。【參見陳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相關適用問題》,載《人民司法》2021年第35期,第41頁。】在立法規定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罪名適用得以激活,原因恰恰在司法層面。具體而言,司法實務改變此前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適用主要限制在線上幫助行為的立場,逐步對提供“兩卡”(手機卡、信用卡)這一線下幫助行為適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并最終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法發〔2021〕22號)第7條所確認。這可謂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司法適用的重要轉折,即從早期的技術幫助行為擴展到線下幫助行為,對相關案件數量快速增長影響重大。
2.刑罰輕緩化激活非純正輕罪的適用
司法適用中的輕罪不限于純正的輕罪,還包括非純正的輕罪。而非純正輕罪的激增,與刑罰輕緩化直接相關。實際上,輕刑化的趨勢一直在持續,重刑率從“嚴打”時期的47.39%,到21世紀前十年的20%以上,再到2013年以后基本維持在20%以內,2014—2016年甚至在10%以內。【參見盧建平:《為什么說我國已經進入輕罪時代》,載《中國應用法學》2022年第3期,第137頁。】刑罰輕緩化的成因當然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刑法》分則罪名的法定刑幅度通常較大,司法裁量空間就較大,這就使升檔量刑標準的提升可以“將重罪變輕罪”。例如,根據《刑法》第264條的規定,盜竊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檔量刑標準為“數額巨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8號)對“數額巨大”的標準作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由此前“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提升至“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這就使相當數量此前應當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盜竊案件轉而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法定刑,從而進入輕罪的范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將詐騙罪“數額巨大”這一升檔量刑標準由“三萬元以上”提升至“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實際亦起到類似效果。可以說,升檔量刑標準提升之后,對重罪與輕罪的轉換可謂“立竿見影”,效果直接、顯著。
(三)程序成因:查證困難與輕罪適用
輕罪的增多,除了立法層面增設輕罪和司法層面刑罰輕緩化的原因之外,實際上還應當從刑事程序的視角加以考察。細究可以發現,就非純正的輕罪而言,一些情形之所以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可能原因在于偵查難以查明全部犯罪事實;而就純正的輕罪特別是堵截性罪名的適用而言,可能原因在于偵查所限未能查明全部犯罪事實,進而無法適用更重的罪名。再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為例。如前所述,該罪的定位為堵截性罪名。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絕大多數犯罪都與互聯網發生關聯。有別于傳統犯罪的幫助行為,由于互聯網的跨地域特性,網絡犯罪中的幫助行為往往沒有固定的幫助對象,即傳統幫助犯一般是“一對一”,而網絡幫助犯通常是“一對多”。這就使得對相關犯罪做到全鏈條、全環節偵查清楚越來越困難,可以查清的犯罪事實往往是碎片化的犯罪事實,得以移送的證據所能證明的也是碎片化的犯罪事實。由此,基于對碎片化犯罪事實的考量,最終的結果大概率是不能適用重罪,而只能適用輕罪。可以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成為最近幾年增長速度最快的罪名,當然可以反映對網絡犯罪的懲治力度不斷加大。但是,堵截性罪名的大幅適用,可能是由于適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省時省力”,即囿于查證現狀而將懲治重點集中于“兩卡”環節,而很難做到在全部查實被幫助的電詐犯罪組織者、實施者所涉行為的基礎上以重罪處斷。
三、輕罪應對模式的缺憾
在厘清輕罪激增成因的基礎上,本部分從罪刑均衡、綜合治理、附隨后果三個方面對輕罪現行對策展開評析,分析輕罪應對模式存在的缺憾。
(一)罪刑均衡方面
就立法層面而言,輕罪增設的整體趨勢緣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背景。可以說,通過擴張刑法的規制范圍以有效應對風險,實現對法益的有效保護,是現實所需。而就司法層面而言,輕罪激增符合刑罰輕緩化的整體趨勢,大致亦應予以肯定。當然,從新近《刑法》修正來看,也存在對部分輕罪處罰過嚴的問題。
第一,部分輕罪可以通過非刑罰的手段解決。根據罪刑均衡原則的要求,不能單純基于社會管理的需要將不應當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納入輕罪范疇加以規制,特別是對于可以通過其他手段實現有效防范的危害行為,更加應當慎用刑事手段。然而,新近《刑法》修正增設的部分輕罪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配置的法定刑為“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屬于典型的輕罪。但細究可以發現,通過完善相關管理手段,如建立健全驗證系統,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的現象可以大幅減少。因此,這類行為在犯罪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方面似可再作斟酌。
第二,部分輕罪未設置入罪門檻。罪刑均衡要求刑法秉持謙抑性,而“刑法謙抑性……關鍵是要實現妥當的處罰”【周光權:《論通過增設輕罪實現妥當的處罰——積極刑法立法觀的再闡釋》,載《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42頁。】。需要注意的是,區分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是我國法律的一貫傳統,犯罪的成立通常應當有一定的門檻。然而,為了彰顯刑事打擊,新近《刑法》修正對不少新增犯罪未設置入罪門檻,如對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的行為入罪,未設置“情節嚴重”或者“情節惡劣”的限制條件。這實際上是刑法的過度介入,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二)綜合治理方面
對刑法的過分依賴,易導致社會管理能力的弱化,不利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基于此,對于危害社會行為,應當堅持多元共治、多種手段并用,避免把所有的任務都推給刑法。
然而,新近《刑法》修正增設的輕罪,就在綜合治理方面存在進一步加強的空間。例如,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刑罰配置相對而言并不重。但必須承認,數以萬計的人被打上“罪犯”的烙印,勢必影響數以萬計的家庭。而“兩卡”案件高發,與手機卡、銀行卡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和落實不到位不無關系,實踐中不少“兩卡”人員實際就是在制度漏洞之下因貪圖小利而身陷囹圄。對此,依靠刑事懲治只能治標,必須通過完善社會治理實現治本。又如,在《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酒駕駛機動車納入危險駕駛罪的規制范圍之后,隨即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醉酒后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人“處十五日以下拘留”的規定。【參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2011年4月2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11年第4期,第433頁。】這就使得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沒有行政處罰空間,這也對此后醉駕案件的激增產生了直接影響。這一做法明顯不符合行刑銜接的要求,難以適應醉駕案件的復雜情況,不符合綜合治理的基本理念,屬于將多元措施改為單一措施。
(三)附隨后果方面
由于我國尚未建立與重罪相分立的輕罪制度,實際是將適用于重罪的相關規定直接適用于輕罪,這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在這些負面效果之中,最為突出的當屬犯罪附隨后果制度。1997年《刑法》增設了前科報告制度,第100條規定:“依法受到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以前科報告為中心的前科制度,是預防犯罪的基礎性制度,也是加強社會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的保障性制度。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法律政策調整,犯罪前科“標簽化”日益凸顯,犯罪附隨后果過于嚴苛的弊端日益突出。一方面,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地方性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都有對犯罪人員從業的限制性規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對犯罪人員有明確的從業禁止或限制,甚至許多社會性組織和單位內部管理規定,都有對犯罪人員從業的限制性規定。這說明,犯罪附隨后果的設立依據相當寬泛,存在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嫌疑。【參見張慶立:《犯罪附隨后果的規范重塑》,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4年第3期,第117頁。】另一方面,前科制度在具體執行之中“走樣”。有的地方制發規定,使犯罪人員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親屬實際遭受犯罪附隨后果的不利影響。例如,有的市轄區議事機構發布通告,對涉某類犯罪重點人員采取懲戒措施,其中對涉罪重點人員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親屬在受教育、就業、社保等方面的權利進行限制。【參見沈春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2023年備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2023年12月26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24年第1期,第33頁。】
在某種程度上,犯罪附隨后果的嚴苛程度可能超越對犯罪人員科處的刑罰。在輕罪不斷激增的趨勢下,這就愈發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例如,就危險駕駛罪來說,對被告人判處拘役,處罰的程度并不太重,但偏重的是刑罰以外的附隨后果,尤其是職業限制。因犯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的罪犯,與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犯罪附隨后果方面沒有實質區別,都會被貼上罪犯的標簽,并且在自身和子女就業、報考公務員、參軍等方面受到一系列限制。【參見吳春妹、賈曉文、李靜雯:《刑事一體化視野下輕罪治理的系統思考》,載《中國檢察官》2024年第1期,第6頁。】基于此,當下亟須對輕罪的附隨后果制度作出調整,尤其是要合理地限制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適用范圍。【參見劉炳君:《論犯罪附隨后果制度的反思與限縮》,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4年第3期,第133頁。】
四、輕罪應對模式的調適
整體而言,我國輕罪現狀符合社會發展趨勢、契合社會治理的現實需要,但也客觀存在罪刑均衡不夠、綜合治理不深、附隨后果過重等突出問題。基于此,根據實踐反映的問題作出調適,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輕罪應對體系,已是必然要求。未來,應當堅持在刑事一體化視野下研究推進,融理念與實操、實體與程序、法律與政策為一體,更好地實現輕罪應對的現代化。
(一)貫徹刑法謙抑原則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輕罪犯罪圈在做加法的同時,也應當做減法。唯有如此,才能將刑法謙抑原則貫徹落實到位,有序銜接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避免將危害社會行為動輒交由刑法規制。
1.合理劃定輕罪的規制范圍
長遠來看,對于部分社會危害不大的輕罪,應當考慮適時推進非犯罪化,在不斷健全社會管理手段的前提下,將其交由行政處罰措施加以規制。如果說立法系統推進輕罪的非犯罪化尚屬遠景目標,那么當下至少應當對輕罪妥當設置入罪門檻,避免適用的泛化。一方面,立法對輕罪要慎用無門檻入罪的模式,以情節、后果等為標準設置入罪門檻;另一方面,司法要通過妥當把握輕罪的入罪門檻,合理確定輕罪的規制范圍。
基于行刑界分的要求,無論是實害犯還是非實害犯,都應當要求一定的入罪門檻。特別是絕大多數輕罪都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即將入罪門檻交由司法裁量。對此,當然要靠司法機關在具體案件處理中切實履責,妥當把握入罪門檻。同時,對于適用頻度較高的常見輕罪,也要及時總結司法經驗,明確入罪標準。當下,最為要緊的是對輕罪適用“大戶”妥當設定入罪門檻,對輕罪數量進行適度調節。
醉駕型危險駕駛罪適用的激增,與《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該罪的入罪標準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直接相關,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3〕15號)更是直接固定這一規則。該意見第1條第1款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當時認為,“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是根據我國駕駛人員生理特點,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多方論證的結果,具有較強的科學性,且實踐操作多年,已得到社會廣泛認可,可以采用”。參見高貴君、馬巖、方文軍等:《〈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3期,第20頁。】而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高檢發辦字〔2023〕187號)(以下簡稱《2023年醉駕意見》)采用了多元化入罪標準【參見苗生明:《醉酒型危險駕駛的治罪與治理——兼論我國輕罪治理體系的完善》,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4年第1期,第5頁。】,雖然對于具有該意見第10條規定的15種從重處理情節的醉駕案件仍然堅持80毫克/100毫升的入罪標準,但實際上已將常態醉駕案件的入罪標準提升至了血液酒精含量達到150毫克/100毫升以上。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審判工作數據,2024年上半年危險駕駛罪案件一審收案同比下降12.9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上半年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網站2024年7月19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38521.html。】由于醉駕在危險駕駛刑事案件中占據絕對比例,所以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隨著入罪標準的優化和入罪門檻的適當提升,醉駕型危險駕駛案件進入審判環節的數量已有明顯下降,更加符合罪刑均衡原則的要求。
由此,可以將上述模式借鑒應用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其他輕罪。目前看來,對于入罪范圍的限制,僅在理念政策層面作倡導性規定似乎難以收到切實成效。例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法發〔2021〕22號)實際已經顧及“兩卡”案件帶來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激增的情況,在第16條強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把握,要求“區別對待,寬嚴并用,科學量刑,確保罰當其罪”,并在第3款專門強調從寬處理的情形。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上述規定未能有效控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激增的局面【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審判執行工作數據,2023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件數量位居前五,上升23.89%。參見《最高法發布2023年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主要數據》,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網2024年3月9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27532.html。】,這與上述規定過于抽象不無關系。為解決這一問題,有效緩解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激增的局面,必須改變對線下幫助行為與線上幫助行為適用統一入罪標準的模式,對前者適當提升入罪門檻。實際上,《刑法》第287條之二所列舉的“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和“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均應系網絡犯罪產業鏈之中法益侵害程度較大的環節,都可以歸屬為線上幫助的范疇。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所涉幫助類型差異較大,特別是對于法益侵害程度尚難與“技術支持”直接相當的“兩卡”案件而言,更需要借助罪量要素的考察適當限定入罪范圍。基于此,借鑒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應對的成功經驗,宜進一步優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入罪標準,特別是對于流水金額較大、獲利數額較小的“兩卡”案件,應視情況不再納入刑法規制范圍,以妥當界分刑事犯罪與行政違法。
2.融合總則與分則適用《刑法》
對于《刑法》分則罪名的適用,不能僅考慮分則條文本身,還應當顧及總則的規定,以決定是否需要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特別是要堅持綜合考量社會危害大小,準確適用《刑法》第13條但書和第37條的規定,堅決改變“構罪即罰”的觀念。
一是堅持綜合考量規則。綜合考量是近年來不少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的鮮明特點,具體司法活動中宜準確把握相關精神。例如,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也是近年來適用較多的輕罪。對此,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12號)要求,辦理涉野生動物案件,應當根據具體案情,準確認定是否構成犯罪,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妥當裁量刑罰,確保罪責刑相適應。特別是該解釋第13條第2款明確規定“根據本解釋的規定定罪量刑明顯過重的,可以根據案件的事實、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當處理”,即允許根據綜合考量不再適用該司法解釋確定的定罪量刑標準。這實際可以為其他輕罪所借鑒,對經綜合考量確實危害不大的行為作出妥當處理,合理把握其入罪范圍。
二是準確適用出罪免罰規定。《刑法》第13條劃定了犯罪的界限和范圍,其考慮到司法實踐的復雜情況,專門設置“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但書條款,交由具體辦案機關根據個案情況把握。因此,《刑法》第13條但書的規定具有司法出罪功能。【參見左智鳴:《〈刑法〉第13條但書出罪機制的反思與重構》,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4年第4期,第97頁。】同理,《刑法》第37條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行為規定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上述條文實際為司法裁量留有適當空間,可以在具體罪名特別是輕罪的適用之中妥當把握。整體而言,司法實務對但書存在不敢適用的情況,未能使但書應當具備的調節普遍剛性規則和個案復雜情況的立法目的得以實現。司法實務應當綜合全案情節考量,對于明顯不宜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要敢于適用但書規定。特別是對于一些定罪量刑標準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入罪追究明顯背離民眾感情的案件,要充分運用但書的規定,避免刑事處罰的泛化,確保案件處理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同理,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行為,也要善于依據《刑法》第37條的規定免予刑事處罰。
(二)堅持綜合治理對策
刑法只能治標,尚難治本。對輕罪應當堅持多元化的治理機制,以實現標本兼治。我國輕罪的刑事對策調適,最為重要的就是要由單純“治罪”轉變為綜合“治理”。應對輕微危害社會行為,既要靠刑事懲治開路,更要靠健全前置規定和建立長效機制,在慎用刑事手段的前提下實現防范、懲治、治理一體化,實現對輕罪的有效治理。
1.堅持實現防范為主
隨著犯罪結構的變化,實施犯罪的行為人大多不再是窮兇極惡的“罪犯”,S4ZkuCA1q09pKwUxCOjm4VIx6Y65bDc+Wp4Cc1H4g9A=而可能是具有正當職業、穩定收入、良好家庭和受過較好教育的“普通人”。可以說,不少輕罪行為實際屬于“機會型”犯罪,其之所以發生與相關預防措施不到位有一定的關系。換言之,如果強化相關預防措施,那么完全可以“防患于未然”,有效減少相關犯罪的發生。以盜竊罪為例,當前竊電犯罪下降趨勢十分明顯,就在于防范措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體使防范涉電違法犯罪的效能變得更高、更快、更準。
總而言之,輕罪應對不能止步于案件辦理,而應當高度重視源頭治理,分析犯罪滋生的原因,以治理方式的完善、治理廣度的延伸、治理效果的提升加強犯罪預防。唯有如此,方能鏟除犯罪滋生的原因,避免犯罪蔓延。
2.克服“刑法先行”現象
不少輕罪特別是純正的輕罪,屬于行政犯的范疇。就行政犯而言,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先有前置法律法規規制,后由作為“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的刑法加以規制。然而,實踐中不少卻是“刑法先行”,這既有礙相關罪名的具體適用,也影響實際效果。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設立之初就是純正的輕罪,即使增配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之后,具體適用亦主要表現為輕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系行政犯,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為前提。然而,就公民個人信息領域而言,刑法實際先于其他部門法明確了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界限。由此,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適用存在不少疑難問題。例如,對于公開的個人信息,由于信息已經處于公開狀況,獲取無須征得同意,對此應無疑義。但是,在獲取相關公開信息后進而提供的行為,是否需要取得“二次授權”(在獲取相關信息后,提供相關信息需要告知同意),則存在較大爭議。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下簡稱《網絡安全法》)未對所涉規則予以明確,所以導致實踐中對相關案件的定性不明。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施行后,相關問題才得以明確。【相關法律否定了“二次授權”的規則。例如,《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第1款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個人信息……(六)依照本法規定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第27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個人明確拒絕的除外……”】可以說,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真正有效的治理,是在相關前置法健全之后。隨著《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前置法律的健全,個人信息通過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全方位保護的體系得以構建,個人信息違法犯罪的系統治理才能真正得以推行。
鑒于此,應對輕罪要注意防止“刑法先行”局面的效仿,堅持將行政法律法規的構建“挺在前面”,真正體現刑法的“二次法”屬性。
3.實現行刑有序銜接
健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雙向發力,是應對輕罪的重要環節。應對輕罪,不是把所有危害行為都交由刑法懲處,而是要為行政處罰留有適當空間。基于此,對危害尚不明顯的行為,應當考慮優先適用行政處罰措施,慎用刑法手段。如前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刪去了對醉酒駕駛機動車行為適用行政拘留的規定,實際上擠壓了對所涉行為適用行政處罰的空間,有失妥當。基于此,《2023年醉駕意見》在優化入罪標準的基礎上,拓展了行政處罰的范圍。具體而言,其第20條第1款明確規定:“醉駕屬于嚴重的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行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公安機關應當在決定不予立案、撤銷案件或者移送審查起訴前,給予行為人吊銷機動車駕駛證行政處罰。根據本意見第十二條第一款處理的案件,公安機關還應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相應情形,給予行為人罰款、行政拘留的行政處罰。”可見,上述規定將醉駕解釋為嚴重的酒駕。這實際是囿于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條文規定的“無奈之舉”,但符合行刑有序銜接的需要,亦應予以充分肯定。
有必要特別說明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下簡稱《治安管理處罰法》)在輕罪分流方面可以充分發揮效用。我國目前尚無專門的“輕罪法”,而《治安管理處罰法》事實上發揮著“輕罪法”的作用。【參見張杰:《行刑銜接視閾下輕罪出罪路徑優化探析》,載《法學論壇》2024年第2期,第31頁。】關于我國是否需要制定專門的輕罪立法,實際上可以再斟酌。但充分發揮《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輕罪分流作用,實現行刑有序銜接,應無疑義。目前,《治安管理處罰法》正在修訂之中,修訂草案二次審議稿已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審議。圍繞《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各方都進行了較為激烈的討論,促進修訂草案不斷健全完善。在此,本文認為,就長遠而言,《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完善不應限于具體條文的“小修小補”,而應著力在輕罪分流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對此,應當在如下兩個方面實現“齊頭并進”。
一方面,立足當下,對于《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之間的重疊競合行為,通過司法妥當裁量實現“出刑轉行”。申言之,對所涉行為的社會危害進行實質判斷,將部分情節較輕的輕罪行為納入治安管理處罰范圍。實際上,對于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存在一定模糊界限,刑事懲處必要性不強的行為,通過治安管理處罰的方式加以懲戒,同樣可以收到良好效果。以自由罰為例,行政拘留最長可以到二十日,而拘役最短為一個月,二者期限差異實際不大,故對于危害尚不突出的犯罪行為適用拘留措施,在懲處效果方面不會存在明顯差異。但是,由于治安管理處罰與刑罰處罰的后果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故前者實際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部分弊端,特別是犯罪附隨后果過于嚴厲的問題。
另一方面,立足長遠,對于《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之間的缺漏空缺行為,通過比照適用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之所以認為這一主張是“立足長遠”之策,是因為本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已經二次審議,再行作出大幅調整的可能性不大。故而,對此問題的解決可能需要在后續再行推進。】《刑法》目前設有483個罪名,而這些罪名對應的犯罪行為尚難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一一對應”,還有不少缺漏。通常而言,較之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刑法》規制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更為嚴重。按照法理,對于所涉行為原則上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應當作出相應規定。否則,對相應行為,要么處以刑罰,要么難以予以治安管理處罰。這既不符合行刑銜接的要求,也容易引發不當擴大刑法適用范圍的問題。可以說,通過比照適用雖然看似擴大了治安管理處罰的適用范圍,但由于其適用前提為所涉行為在《刑法》之中已有規定,故實際上可以限定在適當范圍內。而且,通過適當擴大治安管理處罰的適用范圍,適度限制《刑法》的適用范圍,正是通過行刑有序銜接,推進有效應對輕罪的應有之義。總而言之,要立足整個行刑銜接處罰體系,而不能局限在治安管理處罰的范圍內思考問題。唯有如此,方能確保結論的周全。
4.做好反向行刑銜接
行刑銜接應當是雙向銜接而非單向銜接。2021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提出雙向移送機制,第27條第1款規定:“違法行為涉嫌犯罪的,行政機關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或者免予刑事處罰,但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司法機關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有關行政機關。”《刑法》第37條亦針對免予刑事處罰的情形明確規定可以“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這實際上強調的就是反向行刑銜接的問題,而近年來不少涉輕罪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之中更是強調反向銜接的問題。例如,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3〕7號)第12條規定:“對于實施本解釋規定的相關行為被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行為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政務處分或者其他處分的,依法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據此,對于輕罪中的出罪免罰行為,應當做好反向行刑銜接的“后半篇文章”,對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或免予刑事處罰但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避免“不刑不罰”,填補非刑事處罰和應行政處罰間的縫隙漏洞,以“出刑入行”織密法網。
(三)秉持程序優先理念
應對輕罪,必須堅持實體與程序一體推進。特別是輕罪案件的實體處理結果往往與程序運行的狀況直接相關,應當優先在程序方面加以考量,促進問題的解決。基于此,應當堅持程序優先的理念,通過優化程序促進輕罪的有效應對。
1.優化資源配置與推動輕罪快速處理
刑事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對輕罪案件與重罪案件的處理不應“平均用力”,而應當在程序處理上設置差異化的制度。相比于重罪案件,輕罪案件的社會危害較小,行為人罪責較輕,社會關系易于修復。基于此,對輕罪案件進行快速處理,實現差異化的刑事程序制度,真正做到“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是合理配置刑事訴訟資源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在實體層面更為妥當處理輕罪案件。
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刑事速裁程序,體現了對輕罪案件快速處理的追求。但是,輕罪案件的快速辦理,不應限于審判階段,而應當體現在刑事訴訟的全流程,在各階段推進刑事案件繁簡分流。無論是審前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還是審判的人民法院,都應當建立輕罪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程序上對輕罪案件作相對包容的快速處理。應當建立“輕案快立”“輕案快偵”“輕案快訴”“輕案快審”的輕罪訴訟程序【參見王淵:《刑法立法未來趨向:完善輕罪治理體系》,載《檢察日報》2017年10月31日,第3版。】,特別是慎用逮捕措施,擴大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適用,為后續實體的相對寬緩處理奠定程序基礎。
2.審前分流與檢察階段作用充分發揮
如前所述,基于刑法謙抑原則的要求,對輕罪案件應當更為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避免輕罪犯罪圈的不當擴張。這就要求更為切實地發揮審前程序分流功能,避免輕罪案件“扎堆”進入審判環節。客觀而言,寄希望于審判環節成規模對輕罪案件作出罪處理,既不現實,也不合理。
對輕罪案件的審前分流,應當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作用。總的來看,從2019年至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不起訴率逐年上升,由2019年的9.5%上升至2023年1月至9月的25.8%,約增加16個百分點。【參見張杰:《行刑銜接視閾下輕罪出罪路徑優化探析》,載《法學論壇》2024年第2期,第36頁。】但從實踐來看,檢察階段的分流功能還有進一步強化的必要。對于進入審判環節判處非監禁刑的不少案件,實際可以在檢察階段分流處理。總而言之,檢察階段適當擴大自由裁量權的適用,充分發揮不起訴制度的應有功能,是確保進入審判環節的輕罪案件規模適度的前提和關鍵。
3.擴大非監禁刑適用與降低羈押率
當前,與審前羈押率偏高直接相關聯的是對輕罪罪犯大量適用短期自由刑。以危險駕駛罪為例,有學者對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2011—2021年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裁判文書進行分層抽樣,從中選取了100萬份裁判文書為樣本進行分析。統計分析顯示,雖然對于醉酒型危險駕駛罪適用三個月以下拘役的占七成以上,但整體上實刑率偏高,適用緩刑率最高的年份,也只有略微超過一半的醉駕罪犯得以適用緩刑。【參見董玉庭、張閎詔:《醉酒型危險駕駛罪量刑實證研究》,載《時代法學》2023年第1期,第15頁。】危險駕駛罪系刑罰配置最輕、適用數量最大的罪名,對其大量適用短期自由刑,足以說明當前對輕罪的非監禁刑適用尚有改進空間。
基于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擔憂,對于確有必要予以犯罪評價的輕罪案件,也應當進一步擴充非監禁刑的適用,這既是刑罰謙抑理念的應有之義,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具體而言,對于進入審判環節的輕罪,應當盡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同時宣告緩刑。除此之外,可以通過單處罰金、免予刑事處罰來處理輕罪案件,從而大幅度減少對罪犯的監禁,在輕罪應對中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參見周光權:《短期自由刑的適用控制與輕罪治理策略》,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第137頁。】
基于實體與程序一體考量的要求,不應將目光局限在審判環節的實體處理,還應顧及審前強制措施的適用。《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的逮捕條件之一即為“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可見,審前羈押措施的采取實際與審判階段監禁刑的適用直接相關。可以說,對于審前羈押的案件,在審判階段再行適用緩刑的概率會明顯降低。而在司法實踐中,“構罪必捕”“有罪必訴”“一押到底”的觀念沒有徹底轉變,仍存在“以羈押為原則、取保候審為例外”,片面追求有罪判決率,對不捕、不訴設置過度控制程序的情況。【參見孫春雨:《因應犯罪結構變化協力推動輕罪治理》,載《人民檢察》2023年第11期,第32頁。】基于此,應當將依法少捕慎訴慎押作為辦理輕罪案件的具體工作要求,降低輕罪行為人的羈押率,為非監禁刑的適用奠定基礎。
需要提及的是,《2023年醉駕意見》對偵查環節取保候審措施的延續適用作了規定,即第24條規定:“在偵查或者審查起訴階段采取取保候審措施的,案件移送至審查起訴或者審判階段時,取保候審期限尚未屆滿且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受案機關可以不再重新作出取保候審決定,由公安機關繼續執行原取保候審措施。”這一措施的設置,實際上有利于對醉駕刑事案件取保候審措施的延續適用,避免刑事訴訟不同階段續用強制措施的繁瑣程序,對于降低羈押率和擴大非監禁刑適用均有裨益。這值得其他輕罪案件借鑒,可以考慮下一步在其他輕罪案件中加以推廣。
(四)完善前科制度
實現犯罪的輕重有序,亟須解決的是犯罪附隨后果“一刀切”的問題。輕罪與重罪可謂“輕重有別”,不僅應當在刑罰程度方面區分開來,更應當設置多元化的犯罪附隨后果制度。2024年7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參見《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1頁。】當前,應當認真貫徹落實上述要求,以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作為突破口,為系統完善輕罪前科制度積累經驗。
1.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構建
前科制度本身具有相當合理性,故在世界各國刑法中多有規定,旨在發揮風險防范和安全維護的功能。然而,對前科制度適用范圍加以適當限制,防止對有犯罪記錄的人員回歸社會進行不當限制,也是必然要求。特別是當前我國犯罪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更是要求前科制度作出適當調整。大量輕罪案件的被告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在教育和改造完畢后應當允許其及時回歸正常生活。然而,在目前的犯罪記錄制度框架下,這些輕罪罪犯因為“有前科”“有案底”,“一次犯罪,終身罪犯”,要承受由此帶來的種種不利后果,回歸社會困難重重,大大增加社會對立面。可以說,針對當前輕罪范圍不斷擴大的趨勢,為消除前科制度的弊端,有必要完善輕罪前科制度。對此,必須立足我國基本國情和司法現實,并與有犯罪記錄人員回歸社會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現實需要相適應。
對于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構建,基于穩妥推進的考慮,本文主張將適用范圍限制在輕罪之中的微罪,即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或者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同時,如前所述,應當將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和極端主義、軍人違反職責等特定犯罪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
2.立法層面的務實選擇
構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屬于立法層面的問題,無法在司法層面自行突破。就立法推進而言,最為理想的狀況當然是《刑法》cd36308455f5c44c60a311291fb9b842和《刑事訴訟法》聯動修改,構建起實體與程序相互融合的制度體系。然而,目前看來,短期之內《刑法》修改增設前科消滅制度的可能性不大。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二)》已于2023年12月29日由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其中并未涉及輕罪前科問題。本次修法之后,短期內再行修改《刑法》的可能性不大。基于此,從可操作性的角度出發,可以考慮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方式在程序法層面先行開局,邁出構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第一步,待《刑法》再次修改之時再予補充,實現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序銜接。
五、結語
輕罪應對是系統工程,涉及立法、司法及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需要共同努力推動。長遠而言,應當構建輕罪制度,實現輕罪與重罪的“立法分道”。在立法系統修改短期內難以實現的當下,應當通過立法層面的“小修小補”、司法層面的“較大作為”和綜合治理的“深入推進”,實現對輕罪的有效應對。由此,應當在刑事一體化視野下進一步貫徹刑法謙抑原則,堅持綜合治理對策,秉持程序優先理念,完善前科制度,實現對輕罪的妥當應對。ML
Addressing Misdemeanors from an Integrated Criminal Perspective
YU Haisong
(The Research Bureau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jing100745,China)
Abstract:WhileChina’scurrent criminal law does not explicitly define misdemeanors,offenses punishable by less than three years of imprisonment generally fall into this category,with some exceptions for specific crimes.The recent rise in misdemeanors is attributed to several factors:the legislative expansion of such offenses,judicial policies that elevat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in response to demands for lighter penalties,and evolving circumstances.In the future,an integrated approach is needed to effectively address misdemeanors.To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t in criminal law,it is crucial to optimiz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to control the scope of offenses,particularly for those such as aiding cybercrime,which has become more common.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seamless coordination between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should be achieved.In the short term,judicial discretion can be employed to transition certain cases from criminal procedures to administrative handling.Longterm strategies include aligning behaviors regulated by the Criminal Law with provisions in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 Law,enhancing the latter’s role as a“misdemeanor law”.Moreover,procedural justice must be prioritized by utilizing pretrial diversion mechanisms to prevent an influx of misdemeanor cases in court,while expanding the use of noncustodial sentences and lowering detention rates.To improve the criminal record system,the introduction of arecordsealing system for minor offenses could serve as abreakthrough,using astrategy where procedural reforms precede substantive legal changes,thus creating amore orderly syste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ajor and minor crimes.
Key words:misdemeanors;criminal justice integration;dangerous driving;record sealing system for misdemeanors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
青年學術編輯:張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