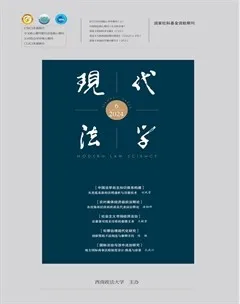論所有權讓與交易的擔保化及其限度
摘 要:具有擔保功能的所有權讓與交易泛化適用擔保規則存在弊端。擔保目的是擔保合同的構造核心,有擔保功能但無擔保目的的交易不屬于擔保。在不同擔保目的的限定下,債權人形式上取得的所有權可能屬于僅具變價功能的純粹擔保權,也可能屬于兼具變價與歸屬確認功能的擔保性所有權,后者在法律效果上與典型擔保有所區別。據此,可以將所有權讓與交易類型化為補充型、混合型和創新型三類。補充型交易具有完全的擔保功能,應與典型擔保一體適用擔保規則;混合型交易具有不完全擔保的特點,在與典型擔保進行規范統合的同時,應保留債權人通過歸屬清算等合同機制成為完全所有權人的可能;創新型交易雖有擔保功能但不屬于擔保,法官應對此種規范的限縮解釋負擔實質論證義務。
關鍵詞:民法典;功能主義;流質規則;擔保
中圖分類號:DF52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對擔保制度進行了重大變革,功能主義擔保觀的引入能夠擴張擔保合同的適用范圍,為市場交易提供更為多元的制度工具。①相較于所有權保留、融資租賃等以保留所有權形式實現擔保功能的交易已有諸多成文法關注,以讓與所有權形式實現擔保功能的交易(以下簡稱所有權讓與交易)②的規范供給相對不足。債權人通過此類合同取得的權利究竟屬于真正的所有權,還是應功能化為擔保物權,《民法典》通過后眾說紛紜。【有觀點認為具有擔保功能的所有權仍為所有權,參見王洪亮:《讓與擔保效力論——以〈民法典擔保解釋〉第68條為中心》,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5期,第145-147頁。也有觀點認為此類所有權應功能化為擔保物權,參見吳光榮:《后民法典時代的讓與擔保及其適用——兼評〈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解釋〉第28條》,載《社會科學研究》2024年第1期,第37-41頁。】對于讓與擔保交易、期前以物抵債交易等具體案型的定性,理論界與實務界亦有較大爭議。【針對讓與擔保交易如何定性的問題,理論與實務觀點未盡統一。詳細探討可參見王海峰:《讓與擔保制度中的物權法定、關系構造與私權自治》,載《法律適用》2021年第10期,第98-99頁。針對期前以物抵債協議應否定性為擔保的問題,亦見仁見智,參見劉保玉、梁遠高:《期前以物抵債協議:性質、效力與規則適用》,載《清華法學》2024年第1期,第109頁。】所有權讓與交易如何定性及適用法律,將直接影響具體交易條款的履行,并輻射到執行和破產程序的處理中。在我國語境下,此類交易的種類隨著商人源源不斷的創造力而不斷增加,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變得愈發重要。
筆者聚焦的核心問題是,所有權讓與交易應否以及如何適用擔保物權規則。該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民法典》第388條規定了“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這樣的不確定概念,所有權讓與交易應否納入該概念范疇中,這需要具體分析合同具有擔保功能與合同發生擔保效力之間的關系,并對所有權讓與交易是否構成非典型擔保進行總體區分。其二,若所有權讓與交易能夠納入其中,是否意味著擔保規則均應適用,還是應考慮所有權讓與交易的不同形態,這需要研判非典型擔保構成與擔保規則適用之間的關系,進而對交易的擔保化進行程度細分。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優先股、可轉債等特別規范已經明確排除適用擔保規則的交易類型,應按相應規定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規定了可轉換債券制度,《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則肯定了優先股交易安排。二者排除擔保規則適用的原理闡述,可參見許德風:《公司融資語境下股與債的界分》,載《法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81頁。】至于讓與擔保、期前以物抵債等司法解釋已有規定的案型,筆者對其進行討論則可以檢驗司法解釋的規定與《民法典》是否協調一致,進而在立法論和解釋論上提出相應建議。
一、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總體區分
《民法典》第388條關于擔保合同的規定過于體現原則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制度解釋》)也未明確何為“擔保功能”,何種交易安排能夠成為擔保沒有清晰明確的識別規則。將所有權讓與交易泛化認定為擔保固然簡便易行,但在具體案型中可能失之偏頗。因此,需明確所有權讓與交易何以構成擔保的問題,進而對所有權讓與交易的擔保化進行總體區分。
(一)擔保規則泛化適用模式存在弊端
所有權讓與交易的構造表現為,當事人在合同條款中約定以特定價格轉移所有權,并同時約定回購、回售、優先受償等內容而使該合同體現出擔保功能。不少觀點據此認為此類交易即屬于“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應當一體化適用擔保規則。這是因為,在功能主義擔保觀下,即便交易采用的是所有權交易而非擔保交易的名義,也應適用統一的擔保物權規則。【參見李運楊:《〈民法典〉動產擔保制度對功能主義的分散式繼受》,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第108頁。】就像所有權保留交易中出賣人的權利雖名為所有權,但因實質上發揮著擔保功能故應受擔保物權制度統一調整。【參見高圣平、葉冬影:《論民法典上所有權保留買賣交易的擔保功能》,載《法學評論》2023年第3期,第3頁。】同時,《民法典》有條件地修正了流質絕對禁止主義,流質條款雖仍受法律管制但不影響擔保法律關系的成立。【參見崔建遠:《中國民法典釋評:物權編》(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49頁;劉保玉:《民法典擔保物權制度新規釋評》,載《法商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12頁。】這其實是通過成文法認可了當事人以讓與所有權的方式進行擔保融資的交易模式。【參見陳永強:《〈民法典〉禁止流質之規定的新發展及其解釋》,載《財經法學》2020年第5期,第40-41頁。】因此,當事人無論是采取買賣、以物抵債、股權轉讓還是其他交易形式,都應將當事人的意思認定為擔保并統一適用擔保物權規則。
擔保規則的泛化適用模式看似邏輯自洽,但不可避免將產生諸多問題。實踐中所有權讓與交易存在多種樣態,部分交易中的標的物所有權讓與條款構成合同約定的核心,如初創企業作為債務人與債權人約定以轉移股權的方式進行融資,在符合特定條件時債權人享有溢價回購請求權。【參見“通某資本公司與某發銀行股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759號民事裁定書。】此種交易形態中所有權讓與的歸屬功能較強,擔保功能不過是交易的附帶效果。裁判者若怠于思考具體交易中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徑行適用擔保規則,不僅不符合當事人真意,還將阻礙多元融資安排的實現。這是因為,其一,在前述交易模式中,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是達成一種或股或債的交易安排,債權人依照合同約定保留了成為完全所有權人的可能。將交易認定為擔保意味著債權人對標的物享有的權利被限制在債的范圍內,這無疑背離了當事人的真實交易安排。【參見鄒海林:《所有權保留的制度結構與解釋》,載《法治研究》2022年第6期,第44-45頁。】其二,對于發展前景不明的初創企業而言,通過向債權人讓渡利益的方式實現融資目的,是符合雙方利益的市場化路徑。擔保是債這種信用交易模式的附屬,若將該交易定性為擔保,意味著債權人無法取得股權而只能采用事后清算的方式獲得權利保障,這無疑違背了當事人自治達成的融資保障安排的初衷。
(二)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本質
當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邏輯體系不足以掌握某種生活現象或意義脈絡的多樣表現形態時,就需要以類型思維加以補足。【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6版),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336頁。】在《民法典》頒布前,就有學者對擔保泛化的現象表達了擔憂。【參見崔建遠:《“擔保”辨——基于擔保泛化弊端嚴重的思考》,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12期,第111-112頁。】《民法典》施行后亦有學者針對增信措施【參見朱曉喆:《增信措施擔保化的反思與重構——基于我國司法裁判的實證研究》,載《現代法學》2022年第2期,第139-145頁。】、融資租賃【參見張家勇:《論融資租賃的擔保交易化及其限度》,載《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2期,第79-84頁。】過度擔保化的問題進行了反思。既然擔保規則的泛化適用模式存在弊端,就有必要先探明所有權讓與交易為何能夠成為擔保,再考慮擔保規則的具體適用問題。
1.擔保功能與擔保效力的媒介:擔保合同
在形式主義擔保觀下,擔保物權的創設需遵循物權法定原則,當事人雙方訂立的擔保合同也必須滿足從屬性、補充性和保證性等特定要件。某項交易若屬于擔保,便意味著該類交易合同可以創設擔保物權,進而產生擔保效力。
而在功能主義擔保觀下,擔保法定主義的剛性變弱,意定主義不斷“開疆拓土”。《民法典》雖繼續堅持物權法定原則,但在第388條第1款第2句將擔保合同的外延擴展至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這意味著當事人可以經由合同效果來緩和物權法定原則的僵硬性。【參見張家勇:《體系視角下所有權擔保的規范效果》,載《法學》2020年第8期,第8頁。】在非典型擔保中,當事人所訂立的合同不一定符合從屬性要件,更多時候是通過合同約定建立起擔保和主債權之間的依賴機制,非典型擔保成為擔保完全是擔保合同的功勞。【參見李運楊:《民法典時代下非典型擔保與所擔保債權的關系》,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第106頁。】可以說,擔保合同在功能主義擔保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馮潔語:《民法典視野下非典型擔保合同的教義學構造——以買賣型擔保為例》,載《法學家》2020年第6期,第16頁。】當事人正是通過擔保合同的交易安排,利用既有制度實現了擔保的法律效果。因此,功能主義擔保觀下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必須屬于擔保合同,才有可能產生擔保效力。
2.擔保合同的構造核心:擔保目的
《民法典》擴張了擔保合同的外延,但在認定擔保合同時仍應遵循必要的教義學和方法論路徑。【參見許中緣:《民法教義學視角下功能主義釋意的范式》,載《法學家》2024年第1期,第20頁。】將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歸入擔保合同本質上是對交易合同進行定性,在合同的性質認定中,合同目的處于核心地位。【參見崔建遠:《合同解釋論:規范、學說與案例的交互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頁。】分析所有權讓與交易是否構成擔保合同,關鍵在于判斷該交易是否具有擔保目的。換言之,功能主義擔保體系并未改變擔保合同的構造本質,只不過改采廣義擔保觀認定擔保目的,從而實現擴充擔保手段并消滅隱性擔保的制度初衷。
在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原《物權法》)的形式主義擔保體系下,法官需秉承狹義擔保觀對擔保目的進行判斷。若某項合同交易無法增加債務人的責任財產,也未能在債務人的部分責任財產上創設抵押權或者質押權,則不會認為該交易具有擔保目的。例如,當事人通過訂立股權轉讓合同的方式約定將財產轉移至債權人名下,同時約定符合特定條件時債務人或第三人需溢價回購,當事人轉移股權的意思可能會被認定為通謀虛偽而無效,交易也常被定性為借貸而非擔保。【參見“彤某公司與姚某明股權轉讓糾紛案”,上海金融法院(2021)滬74民終133號民事判決書。】對于當事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訂立的以物抵債協議,因欠缺設立抵押或者質押的目的,司法實踐也多不將其認定為擔保交易。【參見“澳某公司等與華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6153號民事裁定書。《民法典》頒布后,部分司法裁判仍持此種不構成擔保的判斷,具體參見湖北省黃岡市中級人民法院(2023)鄂11民終641號民事判決書。】市場中大量交易模式因此無法成為擔保,多方主體均呼吁《民法典》為非典型擔保松綁。【參見《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編寫組編:《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116頁。】
功能主義擔保變革的核心是要求裁判者以廣義擔保觀認定擔保目的。在判斷合同是否具有擔保目的時,法官無需再聚焦于交易能否創設抵押權和質押權,而只需判斷交易合同是否足以為債權人創設一項具有優先性的權利。如果交易能夠使債權人實際控制特定財產,或者將責任財產從債務人的一般財產中分離,使債權人取得清償上的優先性,此種交易也屬于擔保交易。【參見謝鴻飛:《〈民法典〉實質擔保觀的規則適用與沖突化解》,載《法學》2020年第9期,第4頁。】以此審視前述回購型約定,債權人在取得財產所有權后能夠對財產加以控制,進而避免債務人實施轉移資產或貶損資產價值的行為,在債務人逾期清償債務時掌握變價受償的主動權,故該交易具有擔保目的。期前以物抵債交易同樣如此,只要當事人完成了標的物的交付,債權人便足以獲得清償上的優先性,使交易具有擔保目的從而能夠成為擔保。【參見張家勇:《物上擔保權益的分層構造及實現保障》,載《中國法學》2024年第2期,第209-210頁。】
總而言之,在功能主義擔保觀下,合同交易的名稱雖已不再重要,但對擔保交易構成的認定不應過度泛化。應遵守教義學的基本邏輯,通過擔保目的要素對擔保合同進行限定。
(三)總體層面的區分適用模式
由于擔保功能與擔保合同之間需要通過擔保目的要素進行關聯,有擔保功能但無擔保目的的所有權讓與交易便不屬于擔保,所有權讓與交易在擔保構成上需進行總體區分。
在術語使用上,功能與目的常被視作同義詞,如法律的目的常被解讀為法律制度所需要實現的功能。【參見許中緣:《民法教義學視角下功能主義釋意的范式》,載《法學家》2024年第1期,第23頁。】但在合同解釋理論中,合同的功能與合同的目的存在區分,前者是對合同所表現出的經濟效果的外在描述,后者則注重于探尋通過何種方式和手段能夠實現此種經濟效果。【參見闕梓冰:《論合同定性中的“目的”——以名實不符合同為視角》,載《法學家》2023年第6期,第38頁。】對于具有相同經濟功能的交易,如果在合同目的上存在差異,則會被歸類為不同性質的合同。例如,借款合同和信托合同均表現出融資功能,但信托合同中信托公司參與其中并分擔融資風險,使此種融資模式有別于借款,二者在法律性質上不能簡單等同。【參見“潘某義與四川某托公司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688號民事判決書。】擔保功能與擔保目的亦是如此,擔保功能可以理解為一種保障債權實現的效果,擔保目的則指代的是當事人通過擔保的方式實現債權的保障效果,具有擔保功能的所有權讓與交易不必然具有擔保目的。
首先,如果交易只是一種純粹的債權性保障機制,沒有為債權人創設優先于第三人的權利,則該交易不屬于擔保。例如,當事人之間簽訂買賣合同約定特定財產“用于償還此借款”,此類交易是通過督促債務人如期履行的方式保障債權實現,而非為債權人創設一種優先性的權利,故此類交易不屬于擔保。【參見“陳某與胡某等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糾紛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24)新23民終670號民事判決書。】由于債務人的潛在損失是確定的,該約定可以理解為違約金條款或者利息條款。【參見汪洋、劉沖:《行為經濟學視角下擔保型以物抵債的界定》,載《云南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第18頁。】在此意義上,違約金條款、定金條款等均具有擔保功能但并非擔保。【參見李志剛:《功能主義擔保立法語境下融資租賃出租人的物權性質與救濟——“變性”抑或“增容”?》,載《經貿法律評論》2023年第5期,第57-58頁。】其次,如果交易創設的債權人保障機制已經超越了債的范圍,則同樣會被排除出擔保的范疇之外。如在前述對賭交易中,雙方約定的所有權讓與的歸屬功能較強,債權人通過交易取得了或股或債的選擇權,保留了成為公司股東的可能。對債權人的此種保障措施已經不限于對債進行優先受償,此類交易也不屬于擔保。【參見趙旭東:《第三種投資:對賭協議的立法回應與制度創新》,載《東方法學》2022年第4期,第97-98頁。】
概言之,在《民法典》的功能主義擔保體系下,交易具有擔保功能不必然就能成為擔保,還需進一步判斷交易合同是否構成擔保合同。擔保目的系擔保合同的構造核心,有擔保功能但無擔保目的的所有權讓與交易不屬于擔保。
通過前述對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內在正當性的考察,能夠回答該交易為何可以成為擔保的問題,但尚不足夠。《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第2句僅規定了擔保合同的定義,定義性規范本身不是法律適用的規范,而僅是法律適用的媒介,旨在引導裁判者在擔保規則與案件事實之間不斷往返流轉。【參見孫維飛:《定義、定性與法律適用——買賣型擔保案型的法律適用問題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第168頁。】所有權讓與交易構成擔保是否意味著應一體化適用擔保規則,還是需考慮交易的不同構造而作不同安排,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二、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程度細分
《民法典》的頒布并不意味著之前所有的爭論塵埃落定,相反,這更有可能開啟一段新的探索之旅。【參見姚輝:《當理想照進現實:從立法論邁向解釋論》,載《清華法學》2020年第3期,第46頁。】擔保制度的功能主義變革奠定了擔保規則統一適用的基礎,也提出了內部細分的要求。在擔保目的的限定下,債權人取得的所有權雖被功能化為擔保權,但因交易構造的不同,此種擔保權呈現出純粹擔保權和擔保性所有權的二元形態,二者在《民法典》體系下存在法律適用效果上的差異。
(一)從所有權讓與到擔保權益創設:功能化
所有權屬于物的歸屬權,在出賣人轉移標的物所有權時,買受人取得所有權便足以享有完整的物上權能。但在當事人基于擔保目的轉移所有權的情境下,債權人取得的便不是完全所有權而是擔保權。問題在于,擔保目的從而何來,是解釋當事人主觀意圖后形成,還是對交易進行客觀評價后得來。在不同的所有權讓與交易構造中,交易的擔保目的又是否存在差異,這將直接影響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限度問題。
1.擔保目的的功能化評價本質
在學理層面,合同目的可以分為主觀目的和客觀目的,前者指代當事人訂立合同時共同想要實現的效果;后者又稱典型的交易目的,是法院給予合同的法律效果,其可以鎖定合同性質。【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74-875頁。】做此區分的意義在于,裁判者在適用法律時不僅需要考慮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還應兼顧第三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客觀目的能夠將外部價值納入合同解釋內部,從而維護既有規范的安定性和權威性。【參見闕梓冰:《論合同定性中的“目的”——以名實不符合同為視角》,載《法學家》2023年第6期,第35-36頁。】例如,實踐中企業會通過循環買賣大宗商品的方式實現金融借貸的效果,買賣合同雖屬當事人真意但無法得到金融監管規范的認可,裁判者此時需要運用客觀目的工具否認買賣的真意并將合同定性為金融借貸,以確保管制規范的適用。【參見“日某港公司與山西焦某公司企業借貸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74號民事判決書。】擔保交易多涉及第三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擔保目的應定位為合同的客觀目的。在判斷所有權讓與交易是否具有擔保目的時,裁判者不應直接根據當事人意圖追求的法律效果進行認定,而應綜合考量強制性規范的目的,通過規范評價后形成判斷結果。《民法典》擴張擔保手段和消滅隱性擔保的立法意旨,正是通過規范評價的方式進入合同解釋中。
不過,裁判者在對合同進行功能化評價之前,必須先探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如此方可避免以裁判者的意思取代當事人的意思,從而對合同自治形成不當壓制。【參見孫維飛:《定義、定性與法律適用——買賣型擔保案型的法律適用問題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第172頁。】在所有權讓與交易中,對當事人真意進行解釋是為了厘清當事人的真實意圖,這需要綜合考察合同的內容約定、締約背景以及履行行為等要素。例如,在股權轉讓合同中,如果合同約定股權轉讓人(債務人)享有回購選擇權,受讓人不享有任何股東權利,則當事人之間轉移股權的真實意圖便更偏向于創設擔保。【參見“西藏某托公司等與北京某源公司返還原物糾紛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終9835號民事判決書。】但如果合同約定的是股權受讓人(債權人)享有回購選擇權,且回購的條件不確定,則當事人轉移股權的真意便偏離了融資擔保的范疇。【參見“時某汽車公司等與亞某投資公司等股權轉讓糾紛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21)京民終102號民事判決書。】
由于當事人轉移所有權的真實意圖不盡相同,裁判者對此進行功能化評價后形成的擔保目的亦有所差異,因此,在不同擔保目的限定下,交易為債權人所創設的擔保權益也存在區別。
2.債權人擔保權益的二元形態
(1)典型擔保目的與純粹擔保權
在抵押、質押等法定擔保合同中,當事人系以被擔保債權之外的財產創設擔保權,擔保財產的交付或變更登記行為均是出于創設擔保權的目的。在所有權讓與交易中,如果所有權的移轉只是作為融資擔保的手段,此時所有權的歸屬功能完全附屬于擔保功能,債權人取得的權利屬于純粹擔保權。
例如,當事人之間簽訂以物抵債合同并將標的物所有權轉移至債權人名下,同時約定在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債權人有權就標的物優先受償(《擔保制度解釋》第68條第1款)。或者訂立買賣合同轉移標的物所有權,同時約定債務人支付回購款后標的物所有權自動轉移回債務人,若未支付回購款則債權人有權就標的物優先受償。此時,當事人表面意思是轉移標的物所有權,但債權人僅能優先受償而無法取得所有權的約定表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在于融資擔保。在此種情境下,應根據《民法典》第146條的規定否認轉移所有權的約定,揭示當事人旨在進行擔保的真意,合同名為所有權讓與實為擔保。【參見吳光榮:《后民法典時代的讓與擔保及其適用——兼評〈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解釋〉第28條》,載《社會科學研究》2024年第1期,第40頁。】
以讓與所有權形式實現擔保功能的交易模式在《民法典》施行前便已獲得《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以下簡稱《九民紀要》)第71條的認可,《民法典》第388條的規定進一步肯定了此種交易構造的正當性。在此類交易中,債務人或第三人同樣是以被擔保債權之外的財產創設擔保權益,債權人取得的擔保權益僅具有變價屬性,故只要該交易不存在違反擔保主體資格規則、公司擔保程序規則等情況,就應受到與擔保物權相同的對待。
(2)非典型擔保目的與擔保性所有權
在部分所有權讓與交易中,當事人旨在轉移的標的物本身為其所擔保債權據以發生的內容,此時所有權轉移兼具擔保功能與歸屬功能,債權人保有成為完全所有權人的可能。此類交易并未獨立于主債權之外,為債權人創設的也非純粹擔保權,而是受擔保目的限制的所有權,即擔保性所有權。
在交易實踐中,出于滿足投融資雙方利益的需要,當事人簽訂股權轉讓合同時通常會為債務人附加一項在一定期限后回購股權的選擇權,債務人到期可以選擇回購股權,也可以放棄回購從而使債權人終局性地取得股權。部分交易還會約定清算條款,如債務人放棄回購時,債權人應按照評估機構確定的股權價值進行多退少補【參見“巨某投資與福建稀某公司等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119號民事判決書。】,或者以評估所得的市場價格的特定比例進行抵償并多退少補。【參見“深圳奕某帆公司等與深圳兆某基公司等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751號民事判決書。】此類交易中,債務人回購的選擇權條款與清算條款表明,當事人之間轉讓股權的意思是真實而非虛假的,只不過在債務人放棄回購之前,債權人并未終局性地取得股權。在《民法典》之前的形式主義擔保觀下,擔保規則只能直接適用于擔保交易而無法類推適用于具有擔保功能的所有權交易,此種交易安排要么被視為規避交易而歸于無效,要么被認定為所有權交易而賦予債權人絕對優先力。【參見馮潔語:《民法典視野下非典型擔保合同的教義學構造——以買賣型擔保為例》,載《法學家》2020年第6期,第14頁。】金融機構便經常采用票據回購、信托收益權回購等方式發放貸款,以便獲取比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甚至擔保債權人更為優越的地位,由此產生了廣泛的隱性擔保問題。【參見王樂兵:《金融創新中的隱性擔保——兼論金融危機的私法根源》,載《法學評論》2016年第5期,第50頁。】
法律規避并非一項獨立的法律制度,其本質上是法律解釋問題,法律規避行為也不一定都會歸于無效。【Stefan Andreas Stodolkowitz,Umgehung von Rechtsnormen und vertraglichen Regelungen,JuS2019,S.1144.】《民法典》擔保制度的功能主義變革,使擔保規則不會因為當事人實施了規避行為而被排除適用。【參見李運楊:《動產擔保立法中的功能主義:緣起、內涵及發展》,載《比較法研究》2023年第6期,第124頁。】對于前述約定了債務人回購選擇權和清算條款的股權轉讓交易,當事人之間的真意雖為轉移所有權,但所有權轉移實質上為債權人創設的是一種具有優先性的擔保權益,出于消滅隱性擔保的規范目的,法官需要將該交易評價為擔保。換言之,該交易的擔保目的并非通過真意解釋得出,而是功能化評價的結果,債權人雖然真實取得了標的財產的所有權,但所有權的權能受到擔保目的的限制。正是因為該交易的擔保目的是通過功能化評價形成的,故僅有在需要“消滅隱性擔保”時,該交易才需要與典型擔保一起共同適用設立、公示、順位等擔保規則。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應遵循當事人真意認定權利義務關系,債權人的法律地位介于擔保權人與所有權人之間,其仍有可能通過合同機制成為完全所有權人。
基于擔保目的的不同,債權人取得的權利可以分為純粹擔保權與擔保性所有權兩類。與純粹擔保權相比,擔保性所有權在擔保功能外還發揮著歸屬功能,這逐步觸及流質禁止規則的規制領域。鑒于此,擔保性所有權的創設只有與流質禁止規則協調一致,才能取得規范層面的正當性。
(二)擔保性所有權與純粹擔保權的法效區分
為債權人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形態因更加突出所有權的歸屬功能而面臨正當性難題。因此,需進一步澄清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與流質禁止規則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區分擔保性所有權與純粹擔保權是否具有規范意義。
1.所有權歸屬約定與流質禁止規則的沖突
流質禁止規則屬于擔保制度的重要規則,從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開始便為成文法所采納并被原《物權法》所延續。雖在《民法典》立法過程中多有解禁流質的呼聲,《民法典(草案)》相關規則亦數易其稿,但立法者最終仍選擇保留相關規定。【呼吁解禁流質條款的立法論思考,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可參見高圣平:《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編纂:問題與展望》,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2期,第91-93頁。】從《民法典》第401條和第428條的文義看,當事人約定流質條款的做法雖不再被明確禁止,但在解釋上仍應認定流質約定無效,只不過此種無效不影響擔保法律關系的成立。【參見崔建遠:《中國民法典釋評:物權編》(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49頁;劉保玉:《民法典擔保物權制度新規釋評》,載《法商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12頁。】
在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中,當事人對所有權歸屬作出了事先約定,不少觀點認為這有違流質禁止規則。有學者認為,從《民法典》關于流質的規定來看,是將作為非典型擔保的讓與擔保交易轉化為典型擔保物權,這意味著所有權歸屬約定的效力無法得到承認。【參見吳光榮:《后民法典時代的讓與擔保及其適用——兼評〈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解釋〉第28條》,載《社會科學研究》2024年第1期,第37頁。】《民法典》生效后亦有判決認定所有權歸屬約定無效。【參見“張某某與呂某某等合同糾紛案”,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2024)內02民終292號民事判決書。】從《擔保制度解釋》第68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合同編通則解釋》)第28條第2款的文義和權威解釋來看,裁判者也傾向于否認雙方事先達成的以固定價格取得標的財產的約定效力。【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研究室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編通則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332頁。】這與《九民紀要》第71條的規范邏輯一致,即否認所有權歸屬約定的效力并將當事人的意思轉化為設立擔保。【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404頁。】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涉及讓與擔保的公報案例和指導性案例中,采取的便是此種無效法律行為轉化的思路。【參見“閩某公司與西某鋼鐵等民間借貸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20年第1期;“建行某灣支行與藍某能源公司等信用證開證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11號(2019年)。】《合同編通則解釋》發布后,亦有判例援引相應規定將所有權歸屬約定認定為無效。【參見“姚某某與周某某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24)浙02民終420號民事判決書。】
出于所有權歸屬約定可能違反流質禁止規則的擔憂,雖始終有學者提出應將讓與擔保制度納入《民法典》,但終因分歧過大且實踐探索不足而作罷。【參見王海峰:《讓與擔保制度中的物權法V4ceP8Fe4LsHvFjllPr1TQ==定、關系構造與私權自治》,載《法律適用》2021年第10期,第97頁。】這也彰顯出立法者對于所有權歸屬約定效力的謹慎態度。
2.《民法典》體系下的所有權歸屬約定
“如果法律解釋的路徑及方法有所偏離,則所作解釋及所得結論難免失當,甚至誤導立法、司法和學說發展。”【崔建遠:《混合共同擔保人相互間無追償權論》,載《法學研究》2020年第1期,第83頁。】在《民法典》體系下,前述否認所有權歸屬約定效力,并將旨在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與典型擔保交易一體化處理的觀點有待商榷。
首先,在法律解釋方法論上,若立法者變更了規范的內容,那么連續性規則將不再有效,此時恰應作出相反解釋。【參見[德]托馬斯·M.J.默勒斯:《法學方法論》(第4版),杜志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39頁。】對于流質禁止規則的解釋也不例外。《民法典》第401條和第428條刪除了“不得”的表述,改變了之前絕對禁止流質的規范立場,意在緩和流質禁止規則的剛性特質。“僅能優先受償”的表達,意味著相應規則僅在于否認擔保物不經清算而直接歸屬債權人所有的交易安排。若合同約定了歸屬型清算條款,則應按照當事人的約定實現債權人的優先受償。【參見陳永強:《〈民法典〉禁止流質之規定的新發展及其解釋》,載《財經法學》2020年第5期,第43頁。】因此,若否認所有權歸屬約定,將使《民法典》緩和流質禁止規則剛性特質的立法宗旨落空。【參見謝鴻飛:《動產擔保物權的規則變革與法律適用》,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第10頁。】
其次,《民法典》及司法解釋的規定也明確認可了所有權歸屬約定的效力。在交易結構上,所有權保留、融資租賃交易的擔保功能同樣內嵌于所有權歸屬約定之中,《民法典》第642條和第752條允許保留所有權人和融資租賃中的出租人通過行使取回權的方式實現擔保權益,這實質上便認可了所有權歸屬約定的效力。【參見李志剛:《功能主義擔保立法語境下融資租賃出租人的物權性質與救濟——“變性”抑或“增容”?》,載《經貿法律評論》2023年第5期,第60-61頁。】所有權保留交易和融資租賃交易所具有的合同自治屬性,使之在法律效果上與典型擔保有所區別。【參見紀海龍:《民法典所有權保留之擔保權構成》,載《法學研究》2022年第6期,第92頁。】背后的原因在于,《民法典》采取的并非一元化的功能主義模式,而是功能性的形式主義路徑。因此,以所有權為媒介的擔保交易無需被重新定性為擔保物權,而能夠按照合同的約定發揮擔保效力。【參見高圣平:《動產擔保交易的功能主義與形式主義——中國〈民法典〉的處理模式及其影響》,載《國外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第14頁。】
最后,認可所有權歸屬約定的效力,有助于應對商事交易的復雜性,使各方主體的利益最大化。流質禁止規則的規范意旨在于避免債務人因盲目自信而遭受損害。【參見汪洋、劉沖:《行為經濟學視角下擔保型以物抵債的界定》,載《云南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第16-17頁。】在擔保交易的標的財產價值變動頻繁時,若否認所有權歸屬約定而強令當事人必須事后進行拍賣、變賣,極可能會因處分不及時而導致標的物價值降低,債務人利益因此受損。相較之下,遵循當事人合意進行歸屬清算能夠使財產價值最大化,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對各方主體均有益無害。晚近以來擔保法發展的趨勢之一便是強化私人執行擔保物權的程序,使擔保物能夠以其最大價值清償債權,進而降低執行成本,增加債權人受償機會。【參見謝鴻飛:《民法典擔保規則的再體系化——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二審稿〉為分析對象》,載《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6期,第52頁。】從典型裁判來看,對于存在經濟上困難的企業自愿以降價方式處置其資產的交易模式,最高人民法院也表達了肯定的態度。【參見“仙某公司與鈞某公司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516號民事裁定書。】
《民法典》體系下流質禁止規則的核心意旨在于保障債務人利益,規制的僅是不經清算的所有權歸屬約定,從而在私法自治與法律強制之間尋得平衡。對于當事人之間事先讓與所有權的約定,應當直接解釋為非典型擔保合同并附加強制清算義務,而非先使該約定無效,再由法官確定一個未必符合當事人真意的典型擔保意思。為債權人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能夠與流質禁止規則協調一致,進而取得規范意義上的正當性。
(三)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程度界分
所有權讓與交易即便構成擔保,亦會因具體構造的不同而在適用擔保規則時存有差異,這恰是功能主義與形式主義混合立法模式的張力所在。對于旨在創設純粹擔保權的所有權讓與交易,因所有權僅具有擔保變價功能而不具備歸屬功能,與典型擔保的法律效果相同,故應將其完全功能化為擔保,并一般性地類推適用典型擔保規則。《擔保制度解釋》第68條、第69條均是以徹底擔保化的所有權讓與交易為模板設計的。
為債權人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則兼具擔保變價功能和歸屬功能,具有不完全擔保的特點,在法律效果上與典型擔保有所區別。在法律適用時,不應將此類交易定性為典型擔保,而應尊重交易構造的特殊性,在將其定性為無名合同的基礎上,具體考量擔保成立、公示和順位等擔保規則的規范目的,對擔保規則的適用進行具體類推。《擔保制度解釋》第1條區分了司法解釋對典型擔保的普遍適用性和對非典型擔保的特別適用性,亦表明非典型擔保需依其形態具體判斷是否適用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則。例如,《擔保制度解釋》第57條規定融資租賃合同可以類推適用超級優先權規則,主要目的在于增強承租人的再融資能力。在售后回租案型中,交易產生的是承租人自有物的融資效應,不存在承租人新購資產的特殊保護問題,此時再賦予出租人的債權以超級優先權就難言正當。在售后回租的融資租賃交易中,應排除《擔保制度解釋》第57條的適用。【參見張家勇:《論融資租賃的擔保交易化及其限度》,載《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2期,第82頁。】同樣的,《擔保制度解釋》第68條和第69條的規定是否適用于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之中,亦需結合交易的具體形態進行個案判斷。
三、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具體限度
類型化是厘清復雜法律現象的有力工具。任何類型化方案均非先驗的公理,而是具有目的指向的歸類方式。如果只是對交易進行事實性、經驗性的分類,則此類型與彼類型之間可能因相互交叉或者過分疏離而缺乏規范實益。【參見賴虹宇:《隱名出資的類型重釋與規范構造——基于對契約法思維的反思》,載《現代法學》2022年第2期,第55頁。】秉承擔保規則區分適用的導向,可以將所有權讓與交易分為補充型、混合型及創新型三類,三者呈現所有權的擔保性由強到弱,歸屬性由弱到強的趨勢,在擔保規則的適用上存在差異。
(一)所有權讓與交易的類型化方案
為債權人創設純粹擔保權的交易與典型擔保具有實質評價上的一致性,此類交易由市場主體通過合同自治構建,系抵押、質押等典型擔保合同形態的補充,故可以將之命名為補充型交易。典型擔保合同是立法者通過特定的評價基準對生活事實進行抽象歸納的結果,其本質上是類型化而非概念思維的產物,故不可避免的具有滯后性。人民法院雖不斷通過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方式對新型交易的法律適用進行回應,但仍然難以涵蓋所有情況。《擔保制度解釋》第68條是從當事人約定角度對讓與擔保進行的類型劃分,并非全面的窮盡式列舉。交易當事人可以通過為法律行為附條件或者為債權人施加不得隨意行使所有權等債法性限制的方式,對交易類型推陳出新。【參見李運楊:《民法典時代下非典型擔保與所擔保債權的關系》,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第104-105頁。】例如,當事人可以在所有權轉移中附加授權委托安排內容,明確債權人在債務逾期履行時有權處理標的財產并收取交易價款。【參見“廈門信某公司與天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21)閩民終458號民事判決書。】在《民法典》功能主義擔保變革的背景下,補充型交易能夠為擔保制度提供更廣泛的外延。
為債權人創設擔保性所有權的交易形態兼具擔保功能與歸屬功能,可以將之稱為混合型交易。此種交易形態中當事人可能具有規避法律的意圖,但其通常不會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規定以及公序良俗,這使之有別于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規避行為。后者是指以法律禁止的形式發生不被法律所允許的法律效果,屬于絕對無效的行為。【Vgl.Staudinger/Fischinger/Hengstberger(2021)BGB§134Rn.168.】不過,混合型交易雖不必然歸于無效,但債權人的擔保權益終究是基于功能化評價而來,無法取得與擔保物權人相同的地位。混合型交易如何具體適用擔保規則,有待于在不同交易場景中分別進行判斷。
創新型交易指具有擔保功能但不屬于擔保的交易形態。此類交易中,所有權讓與條款屬于合同的核心條款,所有權的歸屬功能強而擔保功能弱,不符合擔保交易的構造。如在前述約定債權人選擇回購權的股權轉讓交易中,雖然所有權轉移也發揮著保障債權實現的功能,但在企業經營得當、股權價值提升的情況下,債權人出于商業理性通常不會要求企業回購股權,債務人據此無法否認債權人的完全所有權人地位。【參見“張某駒等與南京某研股權轉讓糾紛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21)京民終495號民事判決書。】在附回購條款的融資租賃交易中,當事人之間通過合同機制將第三人不履行債務的風險由回購權利人轉嫁給回購義務人,從而形成了一種超越擔保的債權保障新機制。【參見王文勝:《托底型回購合同的風險轉嫁機理》,載《法學研究》2020年第4期,第155-157頁。】前述交易模式均系雙方為解決目標公司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而設計,屬于在融資擔保交易外保障債權人利益的創新安排,故可以將其命名為創新型交易。
前述類型化方案能夠彰顯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區分,但這僅是為司法裁判指明一個方向,并不意味著法官可以直接依據該抽象模式作出法律適用的結論。補充型交易在擔保效力的取得上存在層次差異;混合型交易擔保化的限度把握,需要更為精細地考量合同構造與具體規范目的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創新型交易中排除擔保規則適用屬于對規范文義的目的性限縮,法官需負擔論證說理義務,此種說理應如何切入殊值探討。因此,在完成所有權讓與交易的類型化作業后,還需要逐一確認不同類型的交易適用擔保規則的具體模式。
(二)所有權讓與交易的區分對待
1.補充型交易擔保效力的層次性
在補充型交易中,債權人的擔保權人地位系由形式上的所有權蛻變而來,故在擔保效力的取得上呈現出層次區分。具體而言,債權人擔保權益的設立應以占有或控制為要件,登記能夠進一步產生優先力,作為所有權移轉型擔保,超級優先權規則無法類推適用。
在標的所有權完成轉移前,債權人無法取得對標的財產的占有或控制,除非標的財產由第三人提供,或者存在法定優先權的特別規定,否則該交易無法產生優先效力。【參見張家勇:《物上擔保權益的分層構造及實現保障》,載《中國法學》2024年第2期,第212-213頁。】實踐中廣泛存在的買賣型擔保交易和未轉移標的財產的期前以物抵債交易即是典型。《合同編通則解釋》第28條第3款規定期前以物抵債交易中未轉移財產時債權人不具有優先力,可茲印證。不過,在解釋論上,即便未轉移標的財產,債權人也享有擔保設定請求權和變價清償請求權。【參見楊代雄:《抵押合同作為負擔行為的雙重效果》,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3期,第778頁。】若系可歸責于該第三人的原因導致財產未能完成移轉,則債權人可以參照《擔保制度解釋》第46條請求第三人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和抵債財產自身的價值內承擔責任。【參見劉保玉、梁遠高:《期前以物抵債協議:性質、效力與規則適用》,載《清華法學》2024年第1期,第109頁。】此種變價清償請求權同樣受到清算規則的限制,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責任范圍超出主債權,則可以參照《擔保制度解釋》的規定將責任范圍限制在主債權的范圍內。
在標的財產轉移占有或控制后,擔保權益得以設立。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能夠將標的財產進行變價清算,此種變價清算需遵循實現擔保物權的程序規定,即進行處分清算。【參見“上海某業公司與金某煤炭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晉民再191號民事判決書。】關于優先力問題,《民法典》及司法解釋雖未直接進行規定,但基于補充型交易與所有權保留在交易結構上的類似性,可以參照適用《民法典》第641條關于未登記的所有權保留交易優先力的規定。交易未經公示,可以對抗惡意第三人但無法對抗善意第三人。【參見王洪亮:《讓與擔保效力論——以〈民法典擔保解釋〉第68條為中心》,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5期,第146-147頁。】例如,若債務人后續再將標的財產出賣或者設立擔保,而第三人知曉交易情況,則債權人能夠對抗第三人。若債務人將標的財產另設擔保并進行登記,由于《民法典》第414條設定了特別規則,無論第三人善意與否,債權人均無法優先于第三人受償。【參見高圣平:《民法典動產擔保權優先順位規則的解釋論》,載《清華法學》2020年第3期,第105-106頁。】
在標的財產完成轉移占有和控制并進行登記后,當與其他擔保權益發生競合時,債權人可以適用《民法典》第414條確定的順位規則,進一步取得優先力。此外,《民法典》第416條新增價金超級優先權規則,旨在防止浮動抵押權人壟斷擔保人的新增資產,從而拓寬債務人就新增財產的再融資渠道。【參見王利明:《價金超級優先權探疑——以〈民法典〉第416條為中心》,載《環球法律評論》2021年第4期,第24頁。】由于所有權讓與交易需要通過轉移占有的方式設立擔保,不符合價金超級優先權規則的規范意旨,故此類交易并無適用《民法典》第416條的空間。
2.混合型交易區分適用擔保規則
混合型交易具有不完全擔保的特點,需在不同情境下區分擔保規則適用的可能性。在外部關系上,由于涉及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等第三人利益,故有必要對交易進行功能分析以凸顯其擔保屬性,并與典型擔保一體化適用擔保設立、公示、順位規則,實現消滅隱性擔保的目的。擔保規則的具體適用與補充型交易相似,此處不再贅述。在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內部關系上,因擔保效果內嵌于所有權讓與約定中,在交易失敗時,有必要區分是債務人還是債權人違約所致,以確定是維持所有權的擔保屬性還是彰顯交易的歸屬功能。
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因債權人的所有權受到擔保目的的限制,故其不得對標的財產進行不當處置,在合同約定的清償條件滿足時,債權人負有將標的物所有權轉回給債務人的義務。在債權人違約時,若強調交易的歸屬功能,將使債權人享有標的物的升值利益,這無疑會造成債權人通過不當行為獲益的結果。相反,若強調交易的擔保功能,肯定債務人的所有權人地位,僅將債權人作為擔保權人看待,有助于充分保護無過錯的債務人的利益。在債權人陷入破產或者面臨強制執行時,債務人也得以基于其所有權人的地位主張取回權或者通過執行異議之訴阻卻強制執行。
但當債務人存在未履行回購義務、將標的財產另行處置等違約行為時,則有必要凸顯交易的歸屬功能,允許債權人通過歸屬清算等合同機制獲得完全所有權人的地位。如前所述,混合型交易中的歸屬清算機制只要不會造成債務人利益的損害,便能夠取得規范意義上的正當性,當事人應遵循相應安排。例如,若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由具備相應資質的特定資產評估機構對目標股權價值進行評估以確定股權轉讓價款,這能夠確保交易價格在形成機制上的公正性。法院也傾向于認可相應約定的效力,同時也允許債務人就損害其利益的行為另行提起訴訟。【參見“巨某投資與福建稀某公司等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119號民事判決書。】再如,若當事人事前約定以評估所得的市場價格的90%抵償債務,且整體抵債的標的股權價值低于債權的價值,對該約定的履行同樣不會對債務人的利益造成損害,法院亦支持按照當事人的約定實現擔保權益。【參見“深圳奕某帆公司等與深圳兆某基公司等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751號民事判決書。】
從《擔保制度解釋》第68條的文義來看,司法解釋的態度允許處分清算但禁止歸屬清算,債權人必須以協議折價、拍賣或者變賣所得價款優先受償,如此可能導致歸屬清算約定被司法機關一概否認。在解釋論上,應將該條規定限縮為僅適用于補充型交易而不適用于混合型交易。在立法論上,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與《民法典》保持一致,即淡化無效的表達而以優先受償的表述取而代之,歸屬型清算約定便足以獲得正當性空間。【類似觀點參見王洪亮:《讓與擔保效力論——以〈民法典擔保解釋〉第68條為中心》,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5期,第148頁。】
3.創新型交易排除擔保規則適用的實質論證
將所有權讓與交易歸入創新型交易屬于解釋的結果,意味著將具有擔保功能的交易排除在擔保交易之外,這構成對《民法典》第388條文義的限縮,而限縮解釋會加重裁判者的論證負擔。由于司法解釋對讓與擔保、期前以物抵債等案型適用擔保規則做出了具體指引,若法官需排除適用,則需承擔比“原則適用而例外排除”模式下更重的論證負擔。【參見劉征峰:《法律行為規范對身份行為的有限適用》,載《現代法學》2024年第1期,第35頁。】從法律效果看,創新型交易中債權人可以直接取得標的財產并排除清算,此種債權人保障措施超越了擔保交易的范疇,法官需進一步闡釋為何要承認此種創新。
物債二分建構了買賣、借貸等典型交易模式,合同交易的典型化雖大幅減輕了裁判者的思維負擔,但可能因過于剛性而無法有效適應財產價值變動頻繁的現實環境。以債為基礎的交易中,債權人無需承擔債務人的經營風險也只能取得固定收益,擔保交易的設立旨在確保債權獲得優先受償。【參見許德風:《公司融資語境下股與債的界分》,載《法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81頁。】但在復雜的商業環境中,擔保交易的設立并不一定能保障債權的實現,在債務人違約時,對擔保標的進行變價處分本身就蘊含諸多風險。基于此種對標的物變價風險的理性認識,商事主體會在交易中將所有權歸屬要素和資金融通要素相混合,從而實現對風險的提前分配,交易安排也據此不斷推陳出新。【參見許中緣:《論混合合同適用的問題與方法》,載《法律科學》2023年第3期,第140頁。】新型合同交易是商人自治下的規則創新產物,體現出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遵循。【參見崔建遠:《民事合同與商事合同之辨》,載《政法論壇》2022年第1期,第72頁。】面對當事人自治達成的新交易類型,若強行以擔保交易進行解釋,難免遭遇削足適履的困境,使法官在法律事實的小前提選取上為適應典型合同的要件而顧此失彼。【參見陳明:《股權融資抑或名股實債:公司融資合同的性質認定——以農發公司訴通聯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案為例》,載《法律適用》2020年第16期,第51-53頁。】相反,允許商事主體以自治交易彌補法律制度的供給不足,并為此種符合各方利益訴求的交易模式提供制度保障,正是法律尊重合同自由的應有之義,能夠有效發揮促進融資、鼓勵交易等積極功效。部分規范和典型裁判已有良好探索,金融交易規范中關于典當交易、融資融券交易、可轉化公司債券、優先股的規定,實質上便肯定了歸屬型債權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參見周林彬:《商事流質的制度困境與“入典”選擇》,載《法學》2019年第4期,第138-139頁。】
不過,此種權衡結論可能會隨著社會的情勢變遷而發生變化。創新型交易固然能夠提供更適應市場需求的交易手段,但在特定歷史時期也可能表現出強烈的負外部性,造成對制度秩序的沖擊,甚至誘發金融風險。尤其是在金融監管強度提升的大背景下,裁判者對待此類創新型交易時應秉持更為嚴格的態度,從而避免對公序良俗產生不利影響。當然,即便是采取嚴格的態度,對于此種契合市場主體需求的創新型交易,規范引導可能會比直接禁止的效果更佳。【參見王睿:《金融創新中的非典型擔保類型化探討》,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期,第173頁。】
四、結論
《民法典》通過對個別詞句的修改完成了擔保規則的體系變革,指明了擔保規范的一體化適用路徑。一體化模式的良好運行依賴于特殊的交易環境,尤其是需要通過更為細致的解釋來調和規則的抽象性和實質妥當性之間的潛在矛盾,確保優化營商環境目標的實現。以所有權形式實現擔保功能的交易是檢驗功能主義立法最好的試金石。【參見紀海龍:《民法典所有權保留之擔保權構成》,載《法學研究》2022年第6期,第72頁。】筆者以既有規范與司法裁判為素材,在對所有權讓與交易泛化適用擔保規則進行反思的基礎上,先提出應以擔保目的要素對所有權讓與交易的擔保構成進行限定,后分析了所有權讓與交易擔保化的二元形態,并據此將交易分為補充型、混合型和創新型三類。此三種形態反映了所有權的擔保性從強到弱、歸屬性由弱到強的趨勢。補充型交易徹底功能化為擔保,能夠與典型擔保一體化適用擔保規則;混合型交易具有不完全擔保化的特征,在與典型擔保進行規范統合的同時,應保留債權人通過歸屬清算等合同機制成為完全所有權人的可能;創新型交易雖有擔保功能但不構成擔保,應排除擔保規則的適用。
在功能主義擔保體系下厘清擔保功能一體化的邊界,是法律解釋工作不可忽視的一部分。筆者以所有權讓與交易為觀察點,所得出的規范區分適用結論亦對其他類型的非典型擔保交易具有參考意義。ML
Discussion on Transfer Transactions with Security Functions
Becoming Secured Transactions and its Limits
Que Zibing
(Law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re are disadvantages to the generalized application of security rules to title transfer transactions with asecurity function;the security purpose is at the co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guarantee contract,and atransaction with asecurity function but without asecurity purpose is not asecurity.Subject to different security purposes,the formal acquisition of title by acreditor may be apure security right with amere realization function or it may constitute asecurity title with acombination of realization and attribution,which is different in legal effect from atypical security.Accordingly,title transfer transactions may be typified as complementary,hybrid and innovative.Complementary transactions were fully functional as security and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me security rules as typical security;hybrid transactions,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incomplete security,should be regulated as typical security while preserving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reditor to become afull owner through contractual mechanisms,such as vesting and liquidation;and innovative transactions,which were functional as security but not security,and for which the judge had asubstantive burden of proof in the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of such aregulation.
Key words:business environment;Civil Code;functionalism;regulation of liquidity pledge;purpose of the contract
本文責任編輯:黃 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