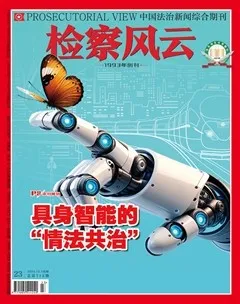唐代的詐騙犯罪與法律規制
中國古人對詐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早有深刻認知,打擊、懲治詐騙犯罪的歷史非常悠久。《唐律疏議》問世之后,中國古代打擊詐騙犯罪的立法日臻成熟,同時唐朝也發生過一些典型的詐騙案件。這些立法與案件,可以為今天詐騙犯罪的預防與懲治提供鏡鑒。
立法沿革
考察國家對某類事務的重視程度,法律文本是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唐律疏議》以前的中國歷代法典未曾完整保留下來,只能靠史籍中的零星記載窺其原貌。幸運的是,就現有史料而言,已足以把詐騙犯罪的立法史做一個較為清晰地梳理。戰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囚、捕、雜、具”六篇。漢相蕭何在此基礎上增加“擅興、廄、戶”三篇,史稱“《漢律》九章”。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漢朝“‘賊律’有欺謾、詐偽、逾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換言之,在《漢律》之中,已有大量懲治詐騙、偽造犯罪的條款,只是這些條款并未納入專篇,而是零散地分布在各篇之中。曹魏政權建立之后,魏明帝曹睿命司空陳群等人制定律法十八篇,史稱“曹魏《新律》”。這次立法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厘清法律體系,重編法律篇目,解決《漢律》法條混亂的問題。在處理詐騙犯罪問題上,合并《漢律》相關條款,專設“詐律”一篇。
立法專篇的出現,既體現了立法者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也是相關領域立法水平提升的重要體現,是中國反詐騙立法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從此以后,《晉律》《梁律》《北齊律》《北周律》《開皇律》《大業律》直至唐《唐律疏議》,全部設置“詐偽律”專篇。值得注意的是,《晉書·刑法志》中記載《魏律》中的篇名為“詐律”,非“詐偽律”,沈家本、程樹德等法學大家據《唐六典》等史籍考證,《晉書·刑法志》中的“詐律”,實際應當是“詐偽律”,可能在書籍抄刻過程中漏掉了“偽”字。《唐律疏議》每篇開始,立法者都以一段“疏議”的方式對該篇立法的源流、內容進行簡要的立法解釋。“詐偽律”開篇云,“詐偽律者,魏分賊律為之。歷代相因,迄今不改”。在篇目位次上,“詐偽律”在《唐律疏議》十二篇中緊隨“斗訟律”,位列法典第九。
從立法內容來看,《唐律疏議·詐偽律》一共二十七條,在《唐律疏議》中占據5.4%的篇幅比例。較之前代立法,每條款都附帶“疏議”立法解釋,使得其立法水平有了質的提升。在諸多條款中,“詐欺官私財物”條的內容與今日之詐騙犯罪類似,尤為值得注意。該條規定,“諸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準盜論。詐欺百端,皆是。若監主詐取者,自從盜法;未得者,減二等”。也就是說,唐代詐騙財物犯罪的量刑幅度比照盜竊罪處理。《唐律疏議》對盜竊犯罪的處罰采用“計贓論罪”原則,即盜竊不成,笞五十;盜竊一尺,杖六十;四十匹,流放三千里;五十匹以上,加役流,也就是流放三千里,并服三年苦役。不過,在本條“疏議”部分,立法者特別解釋道,本罪最高刑“罪止流三千里”,不同于盜竊的“加役流”。對因詐騙而得的贓財物,“知情而取者,坐贓論;知情而買者,減一等;知情而藏者,減二等”。所謂“坐贓”罪,《唐律疏議·雜律》“坐贓”條規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除了一般的詐騙犯罪,唐朝立法者還十分關心醫藥衛生領域的詐騙犯罪,專門設立條款予以規制,在“醫違方詐療病”條規定,“諸醫違方詐療病,而取財物者,以盜論”。
文宗尋舅
在《唐律疏議·詐偽律》中,當時常見的各種詐騙、偽造等犯罪行為,皆有法律詳細規制。如果詐騙行為影響到皇帝或軍國大事,最高可判處斬刑。然而在歷史上,仍有許多人膽大包天,為求榮華富貴而去詐騙皇帝。唐文宗李昂曾被連續詐騙三次,令人哭笑不得。唐文宗李昂(809—840)即位之時,李唐王朝已進入中后期,朝政衰敗,宦官弄權。他勵精圖治,崇儉行善,一心想要恢復盛唐的榮光,堪稱有道明君。唐文宗生母蕭氏是福建人,嫁給建安王李恒。離鄉之時,蕭氏父母雙亡,只有幼弟一人,多年音訊全無,心中非常牽掛。文宗事母至孝,即位之后,便接連降詔閩越尋找,以解母憂。
有個戶部茶綱役人蕭洪,自稱是太后弟弟。有關部門把蕭洪帶到太后的姐姐徐國夫人面前,讓她和丈夫呂璋幫忙辨認。由于年代久遠,呂氏夫婦亦無法辨別真假,只得帶著蕭洪面見太后定奪。史載蕭洪等人面見太后之時,“嗚咽不自勝”。根據種種跡象,無法斷言是假,再加上此種氛圍烘托,大家很快便認定蕭洪就是太后失散多年的弟弟。唐文宗大喜,以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舅舅,馬上封他為將軍、尚書等一系列高官,賞賜大量錢財。不久,又任命他為鄜坊節度使。宰相李訓知道蕭洪的底細,卻未立即揭穿。蕭洪了解情況后,立即巴結討好李訓,并任其兄仲京為鄜坊從事。結交李訓之后,蕭洪有恃無恐,不久便因為錢財上的問題與神策軍方面發生矛盾。官司打到宰相李訓之處,李訓支持蕭洪,從而得罪了大宦官仇士良。
就在這時,有個福建人蕭本,也自稱是太后弟弟。仇士良趁此良機,立即向皇帝揭發蕭洪。經過御史臺審問,蕭洪承認了自己的詐騙罪行,被判處流刑,不久又在途中被賜死。既然蕭洪是假,經過更為仔細的辨認,唐文宗認定眼前的這位蕭本是自己的親舅舅,賜以高官厚祿。其實據史料記載,事后證明這個蕭本也是一個詐騙犯。唐文宗真正的舅舅的確流落民間,只是他生性懦弱,怕引來殺身之禍,不敢向官府表明身份。蕭本主動與其接觸,掌握了蕭氏家族的譜系名諱等內情,從而順利通過了考核盤問,再加上仇士良保舉,贏得了唐文宗的信任。
開成二年(837),福建觀察使唐扶上奏朝廷,稱泉州晉江縣令蕭弘發來一狀,表示自己是皇太后親弟弟。唐文宗命御史臺審理此案,結果發現“事皆偽妄”,于是下令將蕭弘逐回原籍。兩年之后,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偽。請追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于一時,終取笑于千古”。劉從諫的上表使此案再掀波瀾,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唐文宗只好下令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郇對本案進行三司會審,最終確認這兩個“舅舅”也是假的。唐文宗無奈地表示,“據其罪狀,合當極法”,但最終還是“尚為含忍,投之荒裔”,將他們流放邊陲。可嘆唐文宗一片孝心,即便被騙三次,還是擔心重刑處罰這些人可能會驚嚇到真舅舅,希望未來能夠找到他。
求寶失財
受害者貪財圖利的心理弱點,是詐騙犯罪能夠屢屢得逞的重要原因。唐代筆記《唐闕史》就曾記錄這樣一樁案件,很有警示意義。河東薛氏兩兄弟,靠著祖上留下的豐厚家資,在洛陽伊闕附近隱居,過著耕田讀書的愜意生活。一天清晨,有人敲響薛氏大門。開門一看,是個道長,前來求水解渴。好客的薛氏兄弟將道長請入家中招待,道長滿腹經綸,雙方相談甚歡。這時,道長告訴薛氏兄弟,自己并非真的口渴,而是看到此處風水極佳,才愿意在此停留片刻。他進而問道:“據此處東南百步附近,是不是有塊地上種著五棵松樹?”薛氏兄弟告訴道長,的確如此,那里正是薛家的良田。道長大喜過望,悄悄告訴他們,松樹附近散發著仙氣,下有黃金百斤,寶劍兩把。挖到之后,黃金歸薛氏兄弟,其中一把龍泉劍也給薛氏兄弟,佩戴它可以位極人臣。自己只求另一把寶劍,用來降妖除魔。

薛氏兄弟又驚又喜。道長告訴他們,讓下人們準備好鐵鍬等工具,擇吉日動土,即可挖到寶物。當然在此之前,自己必須先在法壇作法,降住寶物,否則它們就會遁地而逃,無法追回。薛氏兄弟連忙詢問作法所需物品。道長讓他們準備大量繩索、彩緞、幾案、香爐、黃金祭器、墊褥等物品,同時準備豐盛的酒宴為貢品。兄弟二人信以為真,為之竭盡家產,甚至向親友借貸。道長又說:“我視金錢為糞土,時常周濟窮人。現在有一些行李放在某道觀,希望能暫存在你家。”兄弟二人連忙允諾,命人幫忙取來。只見下人們抬來四口沉重大木箱,密封得嚴嚴實實。
到了吉日夜晚,道長先帶著兩兄弟在松下法壇拜祝,后命他們先行回家,牢牢關住大門。同時再三告誡他們切不可偷窺,待作法完畢,自己會舉火為號,大家就可以出來挖寶了。薛家兄弟對道長深信不疑,在家中正襟危坐,直到天色將明,兩兄弟怕被外人發現,才不得已開門觀察,發現毫無動靜。他們連忙走到松樹下,絲綢和黃金器皿全部消失不見,地上滿是車轍和蹄印。薛氏兄弟這才明白被騙了。二人趕忙回家,打開道士遺留的四口木箱,里面裝的全是石土瓦塊。一夕之間,案件傳遍京洛。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