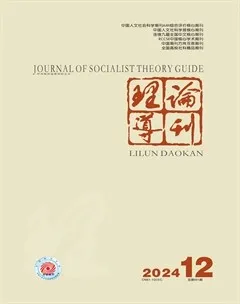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價值追求與實踐進路
摘 要:公共性既是城市基層治理的根本價值追求,也是促進社會良性運行的秩序基礎。圍繞實現數字時代的社會善治,城市基層數字治理應以賡續公共性來推動基層社會技術邏輯與治理邏輯的耦合互動。當前城市基層數字治理聚焦優化社會治理模式、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重塑社會治理規則,由此實現提升部門協同、整合治理資源、豐富服務供給、高效回應需求等技術賦能,但在數字技術賦能的過程中,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也存在忽視公共性價值問題,引發傳統社會共同體維系機制的斷裂,帶來集體意識的失落和社會認同的下降。賡續公共性,城市基層數字治理需要從公共價值創造、公共規則形成、公共空間打造、制度設施供給、治理流程優化等方面創新實踐進路。
關鍵詞:公共性;基層治理;數字治理;價值追求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4)12-0067-07
一、問題的提出
伴隨著新一代通信技術的迭代更新與飛速發展,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為城市基層治理提供了新手段、新方式與新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深入發展,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2022年5月,民政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網信辦等9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入推進智慧社區建設的意見》,強調要加大基層社會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整體推進基層社會的數字化和智慧化水平。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要推動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實現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更好滿足基層群眾的治理需求。
當前,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作為一項新的研究議題,學者們的研究旨趣主要體現為:在主體參與方面,不同群體存在差異化的利益訴求和治理傾向,需要多措并舉、統籌協調,促進不同群體對于數字技術的接受與應用[2];在治理效能提升方面,面對現代技術與傳統社會運行模式的隔閡,需要不斷創新技術應用與拓展智慧場景,更好地契合社會治理的需要[3];在實踐困境方面,當前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依然面臨著信息基礎設施落后、制度體系不完善、居民參與程度低、主體協同乏力等問題[4];在路徑創新方面,需要推動基層數字治理朝向更加開放協同、精準高效以及智能便捷等方向轉型[5]。
總之,學者們對城市基層數字治理議題展開了積極的研究,對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的現代化實踐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基于研究視角的選擇,學者們對城市基層數字治理邏輯轉向和價值追求的關注較少,忽視對基層數字治理中社會認同與情感道德等價值理性的探討。數字技術在提高社會治理效率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與改變著地方性的文化習俗、制度慣例、結構體系以及情感認同等。道斯指出,數字時代復雜、動態的社會基礎環境變化,要求數字治理必須綜合考慮社會趨勢、技術發展、信息管理、政府角色與社會目標等要素的關系互動[6]。戈德史密斯與埃格斯認為,社會信息化不是將信息技術簡單地應用于公共事務領域,它是一種融合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技術勢能的“網絡化”組織及其活動形式[7]。上述研究觀點表明,對數字治理問題的探討要聚焦更深層次的公共價值和愿景追求,關注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中的公共性賡續議題。
二、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邏輯機理與技術賦能
數字治理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源于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以及其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應用與延伸。英國學者帕特里克·鄧利維在《數字時代的治理》一文中指出,信息技術和信息系統的使用將對社會認知、組織行為、制度體系和文化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推動政府活動和公共管理作出積極的變革,由此進入數字時代的治理[8]。隨后,學者們陸續從信息化、新技術革命、后工業化等視角探討數字治理的目標、價值、特征,以及分析信息技術與社會治理創新的關系等。從互聯網時代走向大數據時代,海量數據存儲、處理與分析推動數字治理的應用領域不斷拓展、實踐內涵進一步豐富。鐘祥銘和方興東認為,數字治理是一種以信息通信技術和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的社會治理模式[9]。數字治理建立在數字技術的迭代更新與社會治理躍遷基礎上,依托現代信息技術搭建治理網絡、理順治理架構、貫通治理要素,提升公共治理活動和社會創新水平[10]。現代信息技術賦能社會治理全過程,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優化社會治理體制,以實現社會治理目標的“數字化”、流程的“清晰化”、結果的“可預見”等[11]。
(一)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邏輯機理
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依托數字技術,聚焦優化社會治理的結構樣態和行動邏輯,促進社會結構調整、社會運行方式改變和社會服務能力提升,以實現對基層治理模式、體系、能力和規則等要素的重塑。
1.建構扁平化的治理模式。現代信息技術通過推動城市基層治理的信息開放、數據共享與流程再造,打破不同性質參與主體之間的固有界限,調整基層治理中的模塊結構,持續優化資源配置,構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扁平化”治理模式[12]。數字治理扁平化使跨部門、跨層級共享數據成為可能,緩解了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信息壁壘困境,促使治理要素和治理資源科學配置與流動。數字治理扁平化通過對政府、市場與社會等參與主體結構關系的調整,吸納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促成集體治理行動的實現,化解傳統治理中資源不足和主體協同乏力的難題。
2.打造功能豐富的治理體系。光纖寬帶、移動通信網絡、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基礎信息設施的發展與應用,推動政府建立起集約高效、安全便利、智能適用的基層數字治理架構。政府通過數據、信息、技術等資源開發創新體系,實現對基層文化教育、生活服務、健康養老、環境衛生等治理場景的全過程嵌入,推動基層社會服務和環境配套設施的數字化、網絡化轉型。例如,政府依托數字技術建立的智慧社區綜合服務平臺,可以開展信息發布、政務審批、網上辦事、智慧服務等事項,使居民群眾能夠及時了解國家和地方的公共服務、勞動保障、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政策和法規,參與相關社會公共事務,獲取社會服務資源。
3.形成快速反應的治理能力。城市基層數字治理體系的搭建,有效整合人員、資金、科技、服務等要素,豐富基層群眾的參與渠道、參與方式,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共建共治水平。數字技術打破了時空界限,通過關聯治理要素,實現職能歸集重組和治理網絡構建,提高政府處理社會公共事務問題的能力。依托數字技術超強的運算能力和分析能力,政府準確預測社會治理期望或結果,及時將事件處理的要素與流程向基層群眾靠攏,作出高效、敏捷、有效的回應。同時,政府可借助技術連接和信息互通,化解科層制運作中的執行梗阻難題,提高處理棘手問題的水平,拉近與居民群眾之間的關系。
4.重塑有序運行的治理規則。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發展推動現有社會治理秩序和治理規則的改變,更好地反映參與主體的意愿和利益。數字技術加快了信息要素流通,降低了社會治理參與成本和溝通成本。不同參與主體之間通過數字技術搭建的溝通、對話和協商機制,提升了社會治理的參與層次與深度,加強了彼此的有機聯系。同時,數字技術推動傳統社會治理邊界的消解與重構,實現整體治理、跨界治理和復合治理。數字技術幫助政府更好地實現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貫通,將縱向國家權力與橫向社會參與有效鏈接,實現政府治理目標與基層群眾需求的契合。
(二)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技術賦能
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于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極大地推動了治理工具更新、治理結構變革、治理機制完善。數字技術強大的信息傳遞與網絡架構功能,有效緩解傳統科層體制下循規蹈矩所引起的溝通不暢和效率低下問題。依托數字技術所催生的“系統治理”“平臺治理”“網絡治理”等新型治理模式,賦能社會治理中的部門協同、資源利用、服務供給、信息傳遞等環節,強化政府治理與社會需求之間的互動性。
1.賦能部門協同與整合。數字技術建構起面向政府、市場、社會和居民的多層嵌套治理系統,實現對政府治理、市場服務、社會治理和居民需求之間的有效整合,形成多重界面系統融合基礎上的一體化治理。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治理情境與功能場域的創設,將深刻改變基層治理的互動方式、行為策略以及權力關系,提升彼此之間的共生性和依賴性[13]。高效快捷的數字治理運作體系的建立,能夠快速整合內外部治理資源,從而實現治理流程的優化再造,推動治理范圍的擴展和治理效能的提升。
2.賦能資源共享與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以及由參數、編碼、腳本等構成的現代數字標準體系,豐富了社會治理中的技術設計、技術開發與技術應用,推動資源要素的深度利用和新領域的探索。數字技術推動社會治理參與主體關系的調整改變,使政府、市場、社會和居民等主體共處于一個平等協商的治理時空中,更好地體現合作共治的精神。數字治理網絡和數字治理平臺的搭建加強了信息傳遞能力建設,實現數據資源深度嵌入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諸多治理領域中,以共建共治的技術賦能方式促進資源共享與利用。
3.賦能服務供給精細化。適應日益分化、復雜化的社會治理環境變化,數字技術不斷推動基層日間照料、醫療康養、文體娛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項的數字化、智能化。基層居民利用智能手機、移動平板、數字電視等終端設備,就能夠獲得相應的智能化服務信息和服務資源,獲得更多參與基層公共事務的渠道。例如,城市基層智慧醫療系統拉近了醫院專家與病人群體之間的時空距離,使社區居民足不出戶就可以獲得高水平的醫療診治。基層智慧養老通過大數據智能傳感系統加強老年人與各級養老服務機構的溝通聯系,為老年人提供各種各樣的健康服務和便捷服務。數字文化體驗平臺則為轄區內的居民群眾提供各類線上文化、教育、休閑、娛樂等服務項目,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文化娛樂需求。
4.賦能信息傳遞與回應。數字治理可以實現政府縱向層級協同與橫向功能擴展的雙重驅動,打破傳統社會治理中的信息溝通壁壘,提高信息數據的利用效率,充分發揮數字資源的增益價值。智慧政務、智慧醫療、智慧養老、智慧教育等數字治理平臺體系和智慧化場景的應用,深度整合政府、市場、社會等部門主體的信息數據,破除居民群眾在辦理相關事項和服務上的信息阻隔。治理信息及時傳遞與回應,極大幫助居民群眾提升數字社會認知水平,及時作出理性判斷,獲取更好的服務體驗。
三、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公共性價值追求及其缺失困境
數字治理依托信息技術的賦能優勢促進政府、市場、社會和居民的主體合作與資源利用,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但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發展具有兩面性,利弊并存,在為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帶來正向促進效果的同時,也會因數字技術的內在風險而產生負面的社會抑制效應。當人們將技術的客觀工具性置于絕對地位時,就可能出現技術的異化問題,導致技術反噬社會或數字治理失控[14]。[JP3]因此,在推進城市基層數字治理時,必須注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動態平衡,使數字技術契合社會環境和制度體系,服務于人民,達致數字社會的善治。
(一)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公共性價值追求
公共性內嵌于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之中,是描繪社會治理本質特征和社會發展價值屬性的概念術語,公共性也是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基本內核,用于判定數字治理與基層社會的發展契合度,展示數字治理的社會公共價值意蘊。公共性既體現為政府、市場、社會和公眾等主體之間的互動合作,又包含公共領域搭建、公共組織運作及公共規則制定等議題。公共性是現代社會生活和社會治理所蘊含的本質性內容,是數字社會和數字治理必須直面的核心命題。公共性既用來規范數字治理中的數字技術應用與模式創新,又用來防范數字治理中居民權利遭受技術利維坦的侵害,推動數字治理過程中居民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與融合。公共性在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中主要體現如下。
1.基層數字治理空間的公共性。數字治理空間呈現開放性和融通性,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技術運行系統,具有主體多元、信息共享、流程共建、評估反饋等特性。基層數字治理中無論是實體性的信息基礎設施鋪設,還是虛擬的空間網絡和智慧服務平臺打造,都會涉及關系互動、價值認同與倫理道德等要素,體現其社會化屬性。數字治理空間中的權力滲透互構、利益重塑分化和效能提升增益等模塊,也都需要一定的共同價值和行為規范來約束,從而維系治理要素間的良性互動。
2.數字治理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精神內核與文化支撐,維系著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的耦合性關聯。大數據、互聯網、區塊鏈、云計算等信息技術賦能提升城市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實現治理結構重塑、制度體系跟進、治理方式優化等目標。以公共性為牽引的文化、制度、慣例、習俗等規范性要素,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共價值導向,保障數字治理的目標不偏離,使數字治理服務于公眾意愿、追求公共目的,體現公共價值和公共精神。
3.數字治理規則的公共性。任何社會治理模式都必須基于一定的價值共識和情感認同,達成一致行動的合法性基礎,并受到社會公共性規則的約束和規范[15]。城市基層數字治理對治理效率的追求和治理方式的創新,離不開公共性社會秩序的建構與支撐。基層社會中隱形的、非正式的社會—文化脈絡要求數字技術嵌入社會治理場域時“入鄉隨俗”,使技術邏輯相洽于社會環境。公共性對數字治理中公共意識、公共規則以及公共sa6Xi8FMcSDCSEe6JquxGA==參與規范性的塑造,包含著對數字治理中公共權力、技術權力與個體權利的平衡與制約。數字治理如若缺失集體理性、公共價值、平等協商等要素,極易陷入單純追求經濟效率的誤區,產生數字形式主義、懸浮化、內卷化等問題。
(二)城市基層數字治理公共性缺失困境
當前,城市基層數字治理借助技術工具與智能算法彌補了傳統社會治理中的諸多治理缺陷,促進了城市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提升。然而,從公共性的價值視角來看,數字治理中技術邏輯對社會運行規則的調整,技術權力對治理體系的干預與滲透,并非必然推動數字技術有機嵌入基層社會治理,反而可能引發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失衡,導致傳統關系網絡、社會認同與情感道德等式微,最終影響數字治理效能的提升。
1.行政主導色彩濃厚,內生動力不足。部分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主要依賴政府單方面的行政推動,帶有較強的行政色彩和科層化思維,即在數字治理中依然延續原有的行政思路,慣用行政命令開展數據收集、平臺搭建、業務考核等工作,缺乏數字化思維使其無法對集成后的數據進行有效分析與治理轉化[16]。部分基層政府推動數字治理的初衷源于工具層面的技術創新,為了承接上級部門的信息整合任務,實現民政、社保、教育等數據信息的采集、存檔、考核測評,并未突顯向基層社會進行數字賦能與賦權等內容[17]。一些單純基于技術思維和技術工具創新所設計的數字移動終端與APP軟件,依賴算法掌握參與主體的行為偏好,但遠離居民的治理需求與治理價值。如果數字治理大多局限于數據占有、流量控制、滿意度測評、社會評價等單向度內容,必然會降低社會信任合作水平,導致數字治理的內生動力不足。數字治理缺乏一致的公共精神和價值認同,將對政府、市場、社會和居民等參與主體的合作關系產生不利影響。單純依賴數字技術連接而構建的治理集體容易因缺乏共同價值引導而陷入“機械團結”的困境[18],降低集體行動效能。
2.重績效管理,輕公共精神培育。數字治理推崇科學主義、績效管理和成本控制的理性主義,注重治理流程設計的技術化、標準化和程序化[19]的同時,也帶來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高度技術化,一定程度上抑制社會公共性的生長和發育。技術工具理性所主導的制度規則日益盛行,逐漸消解傳統社會中約定俗成的地方性規范、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致使責任道德體系和集體價值意識在數字治理網絡中失去約束力。數字治理中社會資本要素的培育與重塑,遠非治理流程的技術優化那么簡單[20],處理不當極易引發治理目標被技術追求所替代的風險。表現為基層數字治理雖然擁有完整的信息收集、數據上報、APP打卡等規則流程,但具體治理事項中出現的數據封閉性、對象壟斷性和技術閉合性等弊端,影響了溝通協調、理念融合、信任合作、道德情感等社會關系要素的培育,使社會治理跌入“數字形式主義”的泥沼,并在繁冗復雜的技術程序中沖淡或壓制價值理性[21]。
3.重治理平臺打造,忽視社會關系網絡。在新技術與社會的交互過程中,社會環境對技術系統及其構建具有重塑作用,賦予技術系統以社會屬性價值。現實中,當信息技術嵌入社會治理場域時,如果不能正確處理數字技術、社會環境和治理效能之間的關系,數字治理將面臨脫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引發數字技術懸浮化的窘境[22]。當前,數字治理平臺和網絡治理空間日益成為居民群眾進行公共交往、參與集體活動的主要場域。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網絡化和平臺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群眾辦事效率,但也減少了居民群眾線下社會性空間聚集與關系互動,間接影響不同群體之間交往接觸的水平與質量,導致社會認同感和社會歸屬感變弱。例如,對技術工具的過分依賴與應用,容易將復雜化的居民需求和社會關系技術簡單化處理,禁錮居民的個性化行為選擇[23],忽視對個體權利的保障和合理需求的滿足。
4.工具理性膨脹,減損社會資本。基層社會是一個充滿親情、道德、倫理的社會關系網絡,強調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團結友愛、和諧共融。數字治理所具有的快節奏、高流動性、利益線條化、非群體化等特性,加劇了社會治理中的原子化、異質化,表現為個體孤立、人際疏離及秩序重構等。數字治理對工具理性、經濟利益、效率至上的追求,使傳統社會治理所具有的內生互動性和文化維系力日漸衰微,引發傳統社會價值、道德與倫理等文化脈絡發生改變。弗洛里迪指出,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社會發展的進步,時常引發數字倫理和數字監管等新挑戰[24]。隨著不同形式的數字治理平臺和數字治理體系的出現,“數據”“信息”“算法”等要素逐漸嵌入公共生活之中,并成為干預和指導個體生活的重要因素。但作為客觀主體的數字技術也存在應用的閾值邊界,并非所有數字技術都能滿足或匹配基層社會治理需要,過度數字化將導致社會治理中數字工具的泛濫和數據要素的閑置[25]。技術中心主義會引發“技術利維坦”陷阱,往往致使技術標準超越社會倫理規則[26]。技術邏輯導致原有社會交換中形成的情感支持與互惠規則受到質疑和挑戰,表現為社會關系網絡的“數據化”和“算法化”,減損社會資本。
5.資源分配不均,存在數字信息鴻溝。數字治理依托技術賦能成為架構新型社會關系和推動社會發展創新的重要模式。然而,當下我國城市基層數字治理中存在著數字資源分布不均,數字治理能力迥異的現象。一方面,基層居民主動參與數字治理的意識不強,“搭便車”現象比較普遍。不同群體對數字治理公共事務的參與和熱情不同,中青年群體積極參與數字治理活動,而老年人則因為身體原因和數字技能缺失往往存在數字鴻溝障礙,日漸被邊緣化。另一方面,不同地區居民對信息基礎設施的占有與使用情況存在較大的差別,由此導致“信息鴻溝”和知識分隔等問題。居民群體數字意識和數字能力的缺失,使先進的數字治理平臺和技術運營設備優勢發揮不出來,導致數據采集困難、開發設計滯后、場景應用效果不佳、智能體驗不足等困境。部分城市刻意迎合“智慧城市”“智慧社區”建設,搭建各類集約化平臺,設計五花八門的智慧化應用場景,大大超出居民的數字認知水平,遠離居民的集體偏好,不僅未能很好地發揮其治理效能,反而增加了基層社會治理的負擔[27]。這說明強大的數字技術和海量的公共數據并非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制勝法寶,只有真正契合基層社會治理情境,聚焦居民意愿和公共利益,才會產生“1+1>2”的結果。
四、賡續公共性: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績效提升的實踐進路
正如技術的社會建構論所強調的那樣,技術嵌入社會并不是按照自有發展邏輯孤立推進的,而是在社會行動中匯合多種治理要素并與其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共同構建起具有顯著社會屬性的技術治理體系[28]。數字治理是一個包含理念更新、流程優化、能力提升、效果評價等的系統性工程,蘊含著豐富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致力于推動社會公共性的生產與創造。為更好地賡續數字治理的公共性,一方面要明確數字技術本身的優勢及局限,實現數字技術與社會環境要素的嵌入融合;另一方面要依托數字技術的社會功能建構,利用數字技術創造更多的公共利益與公共價值。
(一)創造公共價值,凝聚集體共識力量
社會治理的終極目標是走向善治。善治創造公共利益,具有主體多元、過程開放、結果公平和目標公正等特征。社會善治要求數字治理回歸人的主體性,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促進多元主體的良性互動和有序參與[29]。一是發揮集體智慧和力量,打造平等互惠的合作關系。將公共性理念嵌入數字治理的制度框架與運作機制中,規范參與主體的權、責、利關系,注重達成治理共識并最終落實到集體行動上。二是平衡“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培育公共精神、包容精神和利他意識[30]。引導數字治理從關注資源整合、技術革新、平臺建設和效率提升,轉向更加關切數字治理各系統要素間的耦合聯系,以及蘊含其中的公平、民主、協商和合作等價值。
(二)形成公共規則,構建利益共享機制
數字治理規則的形成依賴于地方性規則與習慣的融入,需要文化制度、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支撐。一是科學評估信息技術對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效能優勢與潛在風險,趨利避害。數字治理既要發揮技術規范與技術運行參數在社會治理中的優勢,也要避免技術工具性對社會治理中公平、民主、協商、參與等價值的沖擊,及時評估治理成效,回應居民群眾的需求。二是發揮地方性公共規則和利益共享機制的作用,推動數字治理從單一化、分散化向系統性、協同性擴展。技術場景的開發與應用要綜合資源稟賦、人文特色、群體特征、目標定位等要素,并將“共建”“共治”“共融”“共享”等理念貫穿數字治理的始終。
(三)打造公共空間,重塑治理關系形態
公共性構筑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文化過程,要推動數字社會關系網絡的打造,增進數字社會信任以及培育互惠規范。一是擴大數字治理的空間覆蓋面和場景應用領域,營造一種開放多元、互信互利、合作共贏的社會環境,使參與主體都能夠各盡其能、各展其長。二是加強數字治理平臺和數字治理體系中的社會關系建設,規范其中的利益、角色和行為模式等,以獲得更多系統性的社會環境支持。妥善處理傳統與現代、多樣化與公共性的關系,充分釋放數字技術紅利,激活數字治理效能。[JP3]三是基于共同的數字認知和利益關聯,打造更加開放化和扁平化的數字治理形態。分析數字虛擬空間運行規律,促進主體間的良性合作與協同行動,以便調動更多的利益相關者與資源要素參與進來。
(四)加強制度供給,彌合數字技術墮距
加大數字基礎信息設施供給和數字制度建設,不斷提升基層居民的數字生活滿意度和數字生活品質。一是推動數字技術的制度基礎再造和功能服務能力提升,規范數字治理運行中的行政尋租、資本邏輯、效率導向。促進數字技術與社會民生領域的深度融合,構建多元化的政社合作模式,引導更多的市場企業、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等參與基層數字治理,解決居民的“急難愁盼”問題。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設計,確保基層數字治理創新的可持續性。重點關注數字弱勢群體,增加他們的公共數字資源供給,避免因數字鴻溝而造成的社會分化,提升他們在數字治理中的獲得感和話語權。三是聚焦補齊社會治理短板,豐富數字治理場景設計和服務供給。借助數字技術快速準確地識別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對社會治理難題進行精準分析與研判,滿足居民差異化、個性化的治理訴求和服務需求。
(五)優化治理流程,構建社會責任體系
立足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實際,加強責任體系建設,增進基層群眾之間的“熟悉化”程度和鄰里和諧水平。一是加強數字治理中責任利益連接的結構性再造,推動政府、市場、社會與居民的主體關系由“弱連接”向“強連接”轉變,積極打造基層數字治理共同體。二是推動基層數字治理全景開放、全程監督和責任明晰。數字治理中的情境創新、要素拓展和功能延伸等,要最大程度地實現數據運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三是開展多領域、多層次、多類別的數字治理公益活動。技術類社會組織應利用其資源優勢和專業知識,幫助居民提高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能。
結語
推動城市基層數字治理的探索與創新符合新時代社會發展趨勢,是提升我國城市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必然選擇。城市基層數字治理體系的建構要體現出技術社會建構的公共性特征,更好融入城市社會文化環境與社會情感互動之中,使數字治理由單純“技術嵌入性”向“數字技術的社會適配性”轉變[31]。賡續公共性,要推動數字治理從“私”開拓“公”,從技術單邊主義發展到對公共利益和集體偏好的追尋,實現數字治理事務的集體決策管理,強化參與主體的社會歸屬感和認同感。數字治理的公共性賡續強化了數字技術與社會環境的耦合關系,有助于實現利益協調、價值共享和知識共創,推動資源整合利用,提升服務效能,最終實現技術、社會和人的和諧共生。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致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賀信[DB/OL].新華網,(2018-04-2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22/c_[KG-1.5mm]1122722225html.
[2]郝志斌.重大疫情數字治理協同機制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2020(6):92-99.
[3][JP3]鮑靜,賈開.數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原則、框架與要素[J].政治學研究,2019(3):23-32.
[4]文軍,敖淑鳳.社區數字治理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及其應對策略[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6):58-71+231.
[5]劉培功.數字治理視域下社區治理共同體的“智治”邏輯與實踐路徑[J].理論探討,2023(5):77-84.
[6]DAWES S. The evolution 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e-governance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8(12):86-102.
[7]戈德史密斯,埃格斯.網絡化治理:公共部門的新形態[M].孫迎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
[8]DNNLEAVY P. Governance and state orga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C]// MANSELL R, AVGEROU C, QUAH D, et al.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420-421.
[9]鐘祥銘,方興東.數字治理的概念辨析與內涵演進[J].未來傳播,2021(5):10-20.
[10]沈費偉,陳曉玲.保持鄉村性:實現數字鄉村治理特色的理論闡述[J].電子政務,2021(3):39-48.
[11]黃建偉,陳玲玲.國內數字治理研究進展與未來展望[J].理論與改革,2019(1):86-95.
[12]孟子龍,任丙強:地方政府數字治理何以有效提升基層治理效能?[J].中國行政管理,2023(6):15-22.
[13]譚熒,韓瑞波.基層智慧治理的運作機制與關系解構[J].探索,2021(6):137-146.
[14]卡爾·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研究[M].張旅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308.
[15]李懷,武艷楠.城市“社區社會需求”整合:一個重建社區公共性的分析[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44-53.
[16]于君博,戴鵬飛.打開中國地方政府的數字治理能力“黑箱”[J].中國行政管理,2021(1):36-41.
[17]李沫霏.基層數字治理的理論反思、現實解構與優化策略[J].經濟縱橫,2023(2):83-89.
[18]劉偉,翁俊芳.撕裂與重塑:社會治理共同體中技術治理的雙重效應[J].探索與爭鳴,2020(12):123-131.
[19]董石桃,董秀芳.技術執行的拼湊應對偏差:數字治理形式主義的發生邏輯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22(6):66-73.
[20]宋瀟,劉克,張龍鵬.統合型數字治理:基層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論邏輯與實踐機制[J].電子政務,2023(9):62-76.
[21]張現洪.技術治理與治理技術的悖論與迷思[J].浙江學刊,2019(1):160-165.
[22]何東平.基層數字治理的懸浮化及其克服之策[J].領導科學,2023(1):45-49.
[23]彭亞平.技術治理的悖論:一項民意調查的政治過程及其結果[J].社會,2018(3):46-78.
[24]FLORIDI L. Soft ethics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J].Philosophy&technology, 2018(1):1-8.
[25]范煒烽,白云騰.何以破解“數字懸浮”:基層數字治理的執行異化問題分析[J].電子政務,2023(10):59-70.
[26]胡衛衛,張迪,龔興媛.城鄉融合發展中數字治理共同體的三重邏輯與建構路徑[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112-120.
[27]趙玉林,任瑩,周悅.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壓力型體制下的基層數字治理[J].電子政務,2020(3):100-109.
[28]邢懷濱.社會建構論的技術觀[M].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5:45.
[29]樊佩佩.流動的治理:城市基層社會的公共性困境探察[J].學術研究,2016(7):69-75.
[30]ANDREWS R.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11(1):49-67.
[31]曹銀山,劉義強.技術適配性:基層數字治理“內卷化”的生發邏輯及超越之道[J].當代經濟管理,2023(6):35-40.
【責任編輯:未央】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數字賦能山東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效能提升的機制與路徑研究”(23CSDJ66)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伍玉振(1983—),男,河南臺前人,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基層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