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jiǎn)《五紀(jì)》的文本與思想特征
關(guān)鍵詞 清華簡(jiǎn) 《五紀(jì)》 《洪范》 天人關(guān)系 一治一亂
〔中圖分類(lèi)號(hào)〕B2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0447-662X(2024)11-0029-13
清華簡(jiǎn)《五紀(jì)》是近年出土戰(zhàn)國(guó)竹簡(jiǎn)中罕見(jiàn)的巨制,全文據(jù)推測(cè)在五千字以上。雖然屬于盜掘文物,但通過(guò)竹簡(jiǎn)碳14測(cè)定以及比照其他戰(zhàn)國(guó)竹簡(jiǎn),下葬年代大約可以推定是戰(zhàn)國(guó)中期。孟子和莊子都是戰(zhàn)國(guó)中期的人物,《孟子》和《莊子》二書(shū)中不乏超過(guò)萬(wàn)字的文章,但是從目前出土戰(zhàn)國(guó)簡(jiǎn)的常見(jiàn)形態(tài)來(lái)看,文章大多不長(zhǎng),尚未見(jiàn)到過(guò)一萬(wàn)字以上的,五千字左右已經(jīng)十分罕見(jiàn),因此可以想象,《孟子》和《莊子》書(shū)中那些超過(guò)萬(wàn)字的篇章很可能是后世整合起來(lái)的。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無(wú)論撰寫(xiě)還是抄寫(xiě)、收藏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僅從規(guī)模來(lái)看,已經(jīng)可以認(rèn)定《五紀(jì)》在當(dāng)時(shí)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從其內(nèi)容來(lái)看,也可以證明此言不虛。《五紀(jì)》用“后曰”的口吻來(lái)敘事,講述了后帝、黃帝等上古圣王的事跡,可見(jiàn)其氣度不凡。里面天地鬼人無(wú)所不及,按照今天的學(xué)科分類(lèi),天文、歷法、地理、物產(chǎn)、祭祀、政治、軍事、制度、倫理無(wú)所不在,宇宙觀、歷史觀、鬼神觀、天下觀、道德觀全部囊括。所以無(wú)論從架構(gòu)的完整,還是從氣魄的恢弘來(lái)看,《五紀(jì)》都稱(chēng)得上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頂層設(shè)計(jì)、宏大敘事,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認(rèn)真研究。下面,結(jié)合《五紀(jì)》問(wèn)世后學(xué)界已有研究成果,筆者試圖通過(guò)《洪范》與《五紀(jì)》的文本比較,通過(guò)從天道到人道的思維結(jié)構(gòu),通過(guò)一治一亂的歷史觀,通過(guò)“中”與“德”這兩個(gè)《五紀(jì)》最為顯著的概念,對(duì)此文的文本和思想特征作簡(jiǎn)略的概括,希望能夠引發(fā)學(xué)界各方的關(guān)切,對(duì)于此文做出更為深入更為立體的研究。
一、《五紀(jì)》可以稱(chēng)為《洪范》類(lèi)文獻(xiàn)
《五紀(jì)》問(wèn)世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可以從很多出土文獻(xiàn)和傳世文獻(xiàn)中找到與之相關(guān)之處,如《尚書(shū)》《逸周書(shū)》《春秋繁露》以及馬王堆帛書(shū)《黃帝四經(jīng)》等。然而最為接近的還是《尚書(shū)·洪范》,關(guān)于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整理者做過(guò)如下的說(shuō)明:“《五紀(jì)》在篇章結(jié)構(gòu)、內(nèi)容觀念、文句語(yǔ)詞等方面與《尚書(shū)》某些篇章有相似之處,可以認(rèn)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獻(xiàn)與思想淵源。”
因?yàn)槿罁?jù)“五紀(jì)”(“日、月、星、辰、歲”)展開(kāi),整理者據(jù)此擬定了篇名。“五紀(jì)”首出于《尚書(shū)·洪范》:“次四曰協(xié)用五紀(jì),五紀(jì):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shù)。”表達(dá)如此相近,說(shuō)明兩者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日、月、星、辰、歲”和“歲、月、日、星辰、歷數(shù)”的異同何在?目前學(xué)界有兩種說(shu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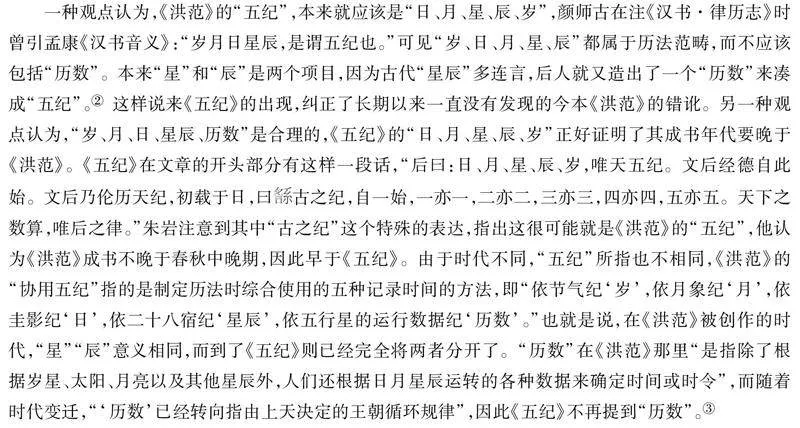
這兩種觀點(diǎn)都有其合理性,朱巖的論述更為詳盡,易于接受。因?yàn)樯婕疤煳臍v法,這個(gè)問(wèn)題可能還需要今后作更為深入的探討。但不管怎樣,說(shuō)《五紀(jì)》的“五紀(jì)”直接傳承自《洪范》,都是核心的概念,這是沒(méi)有問(wèn)題的。只不過(guò)《五紀(jì)》做出了新的調(diào)整,而且將其置于更為突出的地位。在《洪范》中,“五紀(jì)”只是九疇中的第四疇,而《五紀(jì)》中的“文后”(應(yīng)該指的是類(lèi)似“文王”的上古偉大君王),他“經(jīng)德”就是從“倫歷天紀(jì)”即排列正定“五紀(jì)”開(kāi)始的,“五紀(jì)”確立了,“天下之?dāng)?shù)算”即天地間的根本法則也確立了,《五紀(jì)》全篇也確實(shí)是圍繞以“五紀(jì)”為核心的“五”的框架展開(kāi)。這樣看來(lái),《五紀(jì)》是大大提升了《洪范》九疇中的第四疇的地位和作用。
《洪范》和《五紀(jì)》都以一種替天行道的莊重口吻,述說(shuō)了宇宙間根本法則的重要性,《洪范》假借箕子之口,向周武王敘述了“彝倫”的重要性,“彝倫”就是洪范九疇,為天帝所賜,可以授予也可以收回,《洪范》說(shuō)“鯀鱝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鉩;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即鯀本來(lái)?yè)碛小耙蛡悺保驗(yàn)樗鱽y,堵塞洪水,破壞了作為宇宙間根本秩序的五行,所以引發(fā)天帝震怒,收回了“彝倫”,接著又重新授給了禹。《五紀(jì)》雖然沒(méi)有這樣一套由上至下的程序,但同樣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先大亂后大治的歷史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后”“后帝”“文后”“黃帝”等具有神性的人物登場(chǎng),確立了天地間的根本法則,安定了天下秩序。毫無(wú)疑問(wèn),這些人物的神圣性可以比于甚至高于“禹”,在《尚書(shū)》中,“禹”也是被視為“后”的人物。因此,假托上古圣王展開(kāi)敘事,使其內(nèi)容變得神圣而高尚,是《洪范》與《五紀(jì)》的共同特點(diǎn)。
《洪范》和《五紀(jì)》都以天下大亂、洪水泛濫作為引子,引出天下大法的重要性。《洪范》首章云:“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五紀(jì)》一開(kāi)篇也說(shuō),“唯昔方有洪,奮溢于上,權(quán)其有中,戲其有德,以騰亂天紀(jì)。后帝、四干、四輔,乃聳乃懼,稱(chēng)攘以圖。”這種敘述套路的一致性,應(yīng)該不是偶然的。當(dāng)然這與一治一亂的歷史觀有關(guān),這在下文中詳述。
《洪范》與《五紀(jì)》都大量使用數(shù)字,而且兩者使用的數(shù)字以及由此體現(xiàn)的結(jié)構(gòu)明顯具有相關(guān)性。《洪范》的基本框架是“九疇”,各疇又有不同的數(shù)字加以概括,雖也使用其他數(shù)字,如“三”“六”“八”等,但使用最多的是“五”,如“五行”“五事”“五紀(jì)”“五福”。《五紀(jì)》也同樣使用大量的數(shù)字,用于描述和規(guī)范天文、歷法、鬼神、道德等宇宙間一切存在。《五紀(jì)》對(duì)數(shù)字“五”做了更為強(qiáng)化的處理,除大量出現(xiàn)的“五紀(jì)”外,還有“五算”“五章”“五建”“五谷”“五物”“五度”“五行”“五步”“五兵”“五色”“五端”“五牲”“五器”“五幣”“五享”“五常”“五時(shí)”“五正”“五親”“五德”“五刑”“五音”等。而且“五”的元素在《五紀(jì)》中無(wú)所不在,將天地間所有的事物都串聯(lián)了起來(lái),誠(chéng)如馬楠指出的那樣:
《五紀(jì)》篇?jiǎng)t是以“五紀(jì)”為中心,將五德與星辰歷象、五德與神祇司掌、神祇與六甲之旬祝宗禱祀、神祇與人體部位骨骼關(guān)節(jié)、星辰歷象與人事行用、神祇司掌與人事行用等成組系聯(lián)相配,結(jié)構(gòu)上更為縝密。
可見(jiàn),《五紀(jì)》以“五”為主的數(shù)字體系,把天文、神祇、道德、祭祀、人體、名號(hào)、職官全部組合在一起,描畫(huà)出一個(gè)數(shù)字化、格式化的世界圖景。僅次于“五”的數(shù)字是“四”,如“四干”“四輔”“四正”“四荒”“四硙”“四柱”“四維”“四極”“四方”“四位”“四時(shí)”“四度”“四禮”“四域”“四機(jī)”“四肢”“四征”,數(shù)量極多。但很多“四”還是和“五”有關(guān),例如《五紀(jì)》說(shuō)“黃帝之身,溥有天下,始有樹(shù)邦,始有王公。四荒、四硙、四柱、四維、群祇、萬(wàn)貌焉始相之。”這說(shuō)的是以“四”為組合的各種天神、“群祇”(即各種地上的神)、“萬(wàn)貌”(即萬(wàn)民),都圍繞在黃帝身邊,因此這呈現(xiàn)出“四+一”的結(jié)構(gòu),即“四”歸根結(jié)底還是為“五”服務(wù)的。當(dāng)然,“四+一”結(jié)構(gòu)又是“中”的體現(xiàn)。
如朱巖等學(xué)者指出的那樣,大量使用數(shù)字是“以數(shù)為紀(jì)”的一種表現(xiàn)。數(shù)字實(shí)際上是宇宙法則最精煉的體現(xiàn),不僅可以使得敘述井井有條,也使得天地秩序被梳理得井井有條。可以說(shuō)《洪范》開(kāi)創(chuàng)了“以數(shù)為紀(jì)”的先聲,《五紀(jì)》也是這樣,《五紀(jì)》中頻繁出現(xiàn)的“天下之?dāng)?shù)算,唯后之律”“數(shù)以為紀(jì)綱”“后閱其數(shù)”“后長(zhǎng)數(shù)稽”“后乃數(shù)稽協(xié)德”之類(lèi)的語(yǔ)句,顯示出對(duì)于“數(shù)”的格外重視。如馬楠指出的那樣,《洪范》九疇各條之間不存在橫向聯(lián)系,即九疇各條之間,還是彼此獨(dú)立,不相關(guān)聯(lián)的。而《五紀(jì)》通過(guò)“五”等數(shù)字,使天地萬(wàn)物形成了一個(gè)互動(dòng)的、有機(jī)的整體,可見(jiàn)《五紀(jì)》將“以數(shù)為紀(jì)”的思維模式推向了一個(gè)高峰,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數(shù)度、數(shù)理、數(shù)術(shù)思想的發(fā)展有著重要推動(dòng)作用。朱巖指出,《尚書(shū)大傳》和《孔叢子》都提到“《洪范》可以觀度”,“因此,《洪范》與《五紀(jì)》從文體功能角度看,都是為了展示治國(guó)安民方面的‘度’,皆可以‘觀度’。”《洪范》和《五紀(jì)》都致力于傳述或制定宇宙大法,而“數(shù)”的大量使用,正是為了建立具有法規(guī)意義和效果的“度”。這也證明兩者具有相似的理念和氣質(zhì)。
《五紀(jì)》中很多用詞、概念也來(lái)自《洪范》,除了前述“五紀(jì)”之外,還有不少例證,如馬楠指出,同樣是關(guān)于物候,《五紀(jì)》作“一風(fēng),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時(shí)”,《洪范》作“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風(fēng),曰時(shí)”。同樣是卜筮決疑,《五紀(jì)》作“天為筮,神為龜,明神相貳,人事以謀。天下之后以貞,參志上下以共神,行事不疑”,涉及筮、龜、神、人,同時(shí)需要“參志上下”;《洪范》作“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即通過(guò)王、卿士、庶人、龜、筮五者相參來(lái)判斷行事吉兇。《五紀(jì)》的“聽(tīng)唯聰,視唯明”,“視向而不明,聽(tīng)向而不聰,言向[而]不皇”,顯然可以與《洪范》五事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tīng)曰聰,思曰睿”對(duì)讀。這都充分證明了在語(yǔ)言使用和思維框架上,《五紀(jì)》有在《洪范》基礎(chǔ)上展開(kāi)與擴(kuò)充的跡象。
《五紀(jì)》有所謂“三德”,即“行之律:禮、義、愛(ài)、信、中;仁、善、祥、貞、良;明、巧、美、有力、果。文、惠、武三德以敷天下。”這里的“三德”指的是文德、惠德和武德。而《洪范》也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qiáng)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雖然同為“三德”,從表達(dá)上來(lái)看,兩者似無(wú)關(guān)系,但筆者認(rèn)為,《五紀(jì)》可能就是在《洪范》影響下形成了新的“三德”表述。所謂“行之律”即行動(dòng)的方案與法則,而《洪范》“三德”正是一種高明統(tǒng)治者的最佳行動(dòng)方法。從《孔傳》“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以及為《漢書(shū)·五行志》引用此句作注的應(yīng)劭所云“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可以看出,“三德”是統(tǒng)治者治民之德,而且是一種用“中”之道。《五紀(jì)》的“三德”從結(jié)構(gòu)上看,“文德”“武德”一左一右,“惠德”居中,正類(lèi)似《洪范》“正直”居中,而“剛?cè)帷币徽环矗虼藘烧哧P(guān)系的緊密是顯而易見(jiàn)的。
整理者的釋文以及馬楠都指出《五紀(jì)》多用韻文,以之部、職部、魚(yú)部、歌部、陽(yáng)部韻為主,《洪范》用韻則近似。朱巖更進(jìn)一步指出,《五紀(jì)》和《洪范》都具有“韻散相間”的特征,兩者“協(xié)韻四言句式,大多用以表達(dá)法則或規(guī)律,字?jǐn)?shù)不固定的散句則起敘事作用和銜接語(yǔ)篇的作用。”這都是非常有價(jià)值的發(fā)現(xiàn),充分證明了《洪范》和《五紀(jì)》具有親緣關(guān)系。
在語(yǔ)言、概念、結(jié)構(gòu)、意識(shí)等方面,《五紀(jì)》《尚書(shū)》《逸周書(shū)》的許多篇目,和馬王堆帛書(shū)《黃帝四經(jīng)》中的《十六經(jīng)》、《春秋繁露》中的《人副天數(shù)》等篇,也存在相似之處,但都是局部相似,在廣度和深度上沒(méi)有《洪范》那么顯著和強(qiáng)烈,這應(yīng)該不是偶然的。上文僅僅是論述了兩者在語(yǔ)言、概念、文體、結(jié)構(gòu)等文本特征上的相似,這還是表面的,為圣王立言、為宇宙立法的神圣意識(shí),為天地人鬼建立根本秩序的宏大敘事,從超時(shí)空、大一統(tǒng)的意識(shí)出發(fā),試圖對(duì)萬(wàn)物作出整齊化、格式化的安置,才是兩篇思想深層的共同基礎(chǔ),這還需要我們做進(jìn)一步的分析。不過(guò),僅就以上論述,我們已經(jīng)可以斷言,《五紀(jì)》是《洪范》之學(xué)在后世延續(xù)時(shí)形成的一個(gè)新的變種,從性質(zhì)上講,《五紀(jì)》屬于《洪范》類(lèi)文獻(xiàn)。過(guò)去由于文獻(xiàn)的缺乏,我們并不清楚《洪范》之學(xué)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演變,到了漢代,因?yàn)椤逗榉段逍袀鳌返任墨I(xiàn)的出現(xiàn),《洪范》才成為思想界的熱點(diǎn),其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顯得沉寂,以至于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洪范》成書(shū)很可能晚至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現(xiàn)在《五紀(jì)》的出現(xiàn),可以說(shuō)為《洪范》學(xué)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二、從天道到人道的思維框架
《五紀(jì)》通過(guò)復(fù)雜的數(shù)字系統(tǒng),搭建起了一個(gè)井井有條、無(wú)所不包的宇宙體系,但明顯可以看出,都是先講天地、鬼神,再講人事,即便人事的內(nèi)容已經(jīng)非常豐富,也絕非獨(dú)立成章,一定要和天道配合起來(lái)論述。對(duì)此,整理者在釋文的“說(shuō)明”中已有概述,馬楠在論文中說(shuō)得更清楚:
《五紀(jì)》篇以天象歷算(五紀(jì)、五算)為基礎(chǔ),構(gòu)建了宇宙體系,但更大篇幅則集中于與之對(duì)應(yīng)的人事行用方面。篇中先敘五紀(jì)、五算,后敘以歷算為綱紀(jì),樹(shù)設(shè)邦家、蕃育萬(wàn)民、敬事鬼神;先敘天地神祇,后敘神祇祭祀所呼名號(hào)及六甲之旬;先以五德與神祇司掌相配,后敘百官供事,分掌四方祝禱;先敘二十八宿,后論二十八宿所對(duì)應(yīng)禮儀、土工、農(nóng)事、兵戎等活動(dòng);先敘神祇星宿與人身骨骼關(guān)竅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繼論以身為度,以此蕃息恭祀、祛疾除祟。
《五紀(jì)》是一種典型的天人關(guān)系論,即在人類(lèi)社會(huì)與宇宙整體之間建立類(lèi)比,把天人二者看作相互匹配、相互協(xié)調(diào)的整體。這種天人關(guān)系論有著非常明確的思維框架,即從天道到人道,人道從屬于天道,人道必須符合天道,這屬于典型的“以人配天”。當(dāng)然,如黃德寬所言:“簡(jiǎn)文的主旨是通過(guò)后帝對(duì)天人系統(tǒng)的建構(gòu),理順天人關(guān)系,使天地神人按照各自應(yīng)遵循的規(guī)則運(yùn)作,以保持天地、神祇、萬(wàn)民處于‘圓裕中正’的有序狀態(tài)。”即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起一個(gè)全新的宇宙秩序,從而使天地神人各就其位,使天下得到良好的治理。從《五紀(jì)》的敘述順序來(lái)看,首先是“倫歷五紀(jì)”,即正定“日、月、星、辰、歲”這一最為根本的天文秩序,用“五”作為確定天下萬(wàn)物之基本框架,然后是正定天體的位置、星宿的數(shù)量以及相應(yīng)的神祇系統(tǒng)、祭祀系統(tǒng)。與此同時(shí),人間的道德、職官等系統(tǒng)才能建立起來(lái)。接下來(lái)我們以“五”的系統(tǒng)和神祇系統(tǒng)為例加以說(shuō)明。
《五紀(jì)》描述了極為嚴(yán)整而復(fù)雜的神祇系統(tǒng),如晏昌貴指出的那樣,“簡(jiǎn)文將神祇分為三大層次:第一層是天地、四磇、四硙、四柱、四唯組成的18群神(4×4+2=18);第二層是24群祇,‘方’是四方,每方由六祇組成,4×6=24;第三層是28宿,‘向’指四個(gè)方向,簡(jiǎn)文中又稱(chēng)‘四維’,每向七神,4×7=28,共28神;再加南門(mén)、北斗,一共是72神祇。”
那么,“五”的系統(tǒng)和神祇的系統(tǒng)究竟如何與人事對(duì)應(yīng)呢?《五紀(jì)》主要通過(guò)兩條途徑,一是通過(guò)“德”,二是通過(guò)人體。例如《五紀(jì)》云:
一風(fēng),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時(shí)。
一直,二矩,三準(zhǔn),四稱(chēng),五規(guī),圓正達(dá)常,天下之度。
直禮,矩義,準(zhǔn)愛(ài),稱(chēng)信,圓中,天下之正。
禮青,義白,愛(ài)黑,信赤,中黃,天下之章。
數(shù)算、時(shí)、度、正、章,唯神之尚、祗之司。
這里,每一條都是由五種元素構(gòu)成,而前后五條又構(gòu)成一個(gè)整體,可見(jiàn)“五”之?dāng)?shù)是天地秩序的具體體現(xiàn),這套框架導(dǎo)出了“天下之時(shí)”“天下之度”“天下之正”和“天下之章”以及“數(shù)算”,這些也都是由神祇來(lái)司掌的。時(shí)節(jié)征候、度量、顏色都是天地間的基本要素,“數(shù)算”是天地間的最高準(zhǔn)則,人間的“禮、義、愛(ài)、信、中”夾雜其中,與之緊密地匹配起來(lái),就變得天經(jīng)地義,成為人間不得不遵循的法則規(guī)范了。
《五紀(jì)》中,除了天時(shí)、度量、顏色外,“禮、義、愛(ài)、信、中”以及相應(yīng)的社會(huì)身份(賤、相如、嬪妃、友、君父母)、外表姿態(tài)(敬、恪、恭、嚴(yán)、畏)、行為標(biāo)準(zhǔn)(毋沽、毋逆、毋專(zhuān)、毋懼、稽度)、舉止規(guī)范(基、起、往、來(lái)、止)、人體部位(目、口、耳、鼻、心)還和“鬼、人、地、時(shí)、天”等宇宙存在、“東極、西極、北極、南極、中極”等宇宙方位、“日、月、北斗、南門(mén)、建星”等宇宙天體,形成一一相應(yīng)的對(duì)照,形成一個(gè)嚴(yán)密的整體,雖然這種匹配顯得有些機(jī)械和生硬,但顯然可以使得“禮、義、愛(ài)、信、中”等人的因素天然地成為天道的一部分。
《五紀(jì)》稱(chēng)“禮、義、愛(ài)、信、中”為五文德,是“后之正民之德”,因此是對(duì)百姓的要求。但是《五紀(jì)》也反復(fù)說(shuō)明,五文德同樣是天地神祇之德,或者是天地神祇司掌之德,例如三十神祇是六神一組,分為五組:以“天地”為首的一組“尚中司算律”;以“日”為首的一組“尚禮司章”;以“大山”為首的一組“尚信司時(shí)”;以“月”為首的一組“尚義司正”;以“門(mén)”為首的一組“尚愛(ài)司度”。因此人間的“德”毋寧說(shuō)就是來(lái)自神祇,或者神祇與人在“德”上是同頻共振的。
《五紀(jì)》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日之德明察,夫是故后明察。……月之德行審,夫是故后行審。……南門(mén)之德位順,夫是故后位順。……北斗之德正情稽命,夫是故后正情稽命。……建星之德數(shù)稽,夫是故后長(zhǎng)數(shù)稽。”就是說(shuō)“后”之所以能夠有“明察”“行審”“位順”“正情稽命”“數(shù)稽”五種德行,正是直接效法“日”“月”“南門(mén)”“北斗”“建星”等天體之德而來(lái)。
《五紀(jì)》中的天人關(guān)系還典型地反映在人體與天體及其神祇的關(guān)系上。如前所述,《五紀(jì)》一共記載了72個(gè)天體以及神祇的名稱(chēng),而人體的72個(gè)部位正好與之對(duì)應(yīng),很可能《五紀(jì)》本有相應(yīng)的圖,只不過(guò)未被隨葬或已經(jīng)遺失,整理者根據(jù)想象專(zhuān)門(mén)畫(huà)了一幅圖案,可以一目了然地顯示其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這“就意味著人體并非孤立的個(gè)體,而是與諸神所代表的天文氣象、地理環(huán)境、人事交往有密切的關(guān)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紀(jì)》闡述了人體生病的原因,是作為“神”之負(fù)面的“鬼”在作祟,李均明對(duì)此有清晰地概括:“將人體劃分為腰以上、腰以下、頸脊至臀、腹心肝肺、四肢五大片區(qū),并將病因與天鬼、地鬼、盟詛、人鬼、無(wú)良及不壯死作祟對(duì)應(yīng)。”黃德寬也指出:“從第79到94號(hào)簡(jiǎn),簡(jiǎn)文的視角轉(zhuǎn)向天神地癨與萬(wàn)生自體和疾祟方面,將天人關(guān)系從宏觀構(gòu)建轉(zhuǎn)向人身這一微觀系統(tǒng)。”這樣人體就被想象成一個(gè)縮小版的宇宙,這幾乎完全是一種“人副天數(shù)”的思維。
關(guān)于“人副天數(shù)”,如下所示《春秋繁露·人副天數(shù)》有非常詳細(xì)的論述:
天地之符,陰陽(yáng)之副,常設(shè)于身,身猶天也,數(shù)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dāng)?shù),成人之身,故小節(jié)三百六十六,副日數(shù)也;大節(jié)十二分,副月數(shù)也;內(nèi)有五藏,副五行數(shù)也;外有四肢,副四時(shí)數(shù)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lè),副陰陽(yáng)也;心有計(jì)慮,副度數(shù)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
此皆暗膚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合。于其可數(shù)也,副數(shù);不可數(shù)者,副類(lèi)。皆當(dāng)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wú)形者,拘其可數(shù)以著其不可數(shù)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lèi)相應(yīng),猶其形也,以數(shù)相中也。
從中可以看出,董仲舒很可能看到過(guò)類(lèi)似《五紀(jì)》的文章,對(duì)于先秦以來(lái)的“人副天數(shù)”有過(guò)精辟總結(jié),即人的身體是“天地之符,陰陽(yáng)之副”,因此“身猶天也”,與之相參的是“數(shù)”,與之相連的是“命”。但董仲舒明確地將“人副天數(shù)”分為兩類(lèi),一種是“可數(shù)”的,稱(chēng)為“副數(shù)”,一種是“不可數(shù)”的,稱(chēng)為“副類(lèi)”。《五紀(jì)》與人體相比附的是天體、鬼神和方位,并用數(shù)字貫穿起來(lái),顯然這是“副數(shù)”的方式,這種方式一般認(rèn)為是機(jī)械的,甚至是迷信的。但是如李均明指出的那樣,其實(shí)在古代醫(yī)籍中可以找到印證,如《黃帝四經(jīng)》稱(chēng)“腰以上者為陽(yáng),腰以下者為陰”,而《五紀(jì)》“腰以上的疾病稱(chēng)為‘興疾’,是天鬼作祟的緣故,或更多地歸咎于天文氣象要素。腰以下的疾病稱(chēng)為‘辟鬲’。……簡(jiǎn)文歸咎于地鬼作祟,或更多是地理環(huán)境的因素造成的。”因此,《五紀(jì)》傳承的應(yīng)該是一個(gè)流傳有序的天人感應(yīng)的知識(shí)體系,這個(gè)知識(shí)體系曾經(jīng)在現(xiàn)實(shí)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朱巖認(rèn)為,這是天事、神事和人事之間“行為—結(jié)果—征兆”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體現(xiàn),是一種極為細(xì)致的關(guān)聯(lián)性思維,可以稱(chēng)其為“征驗(yàn)”,而《洪范》由“五事”和“庶征”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則是相對(duì)簡(jiǎn)單的關(guān)聯(lián)性思維,即“相同的語(yǔ)法結(jié)構(gòu)(組合關(guān)系)串聯(lián)起五種可替換的行為、品格、氣候與吉兇(聚合關(guān)系),人們只關(guān)心它們之間的整齊排列,至于為什么如此排列(即內(nèi)在因果)卻似乎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或者說(shuō)至少不在文本中予以表述。”因此,“清華簡(jiǎn)《五紀(jì)》繼承了《洪范》中建構(gòu)‘庶征’系統(tǒng)的方法,利用‘關(guān)聯(lián)性思維’建構(gòu)起一整套‘征驗(yàn)’的系統(tǒng),這個(gè)系統(tǒng)有兩個(gè)功能:第一是警示君王與部族;第二是解釋世界構(gòu)成及事物關(guān)系。”
朱巖的解說(shuō),聚焦于從《洪范》到《五紀(jì)》天人關(guān)系的發(fā)展,非常具有啟發(fā)性。如果我們?cè)倬劢埂段寮o(jì)》之后“以人配天”類(lèi)型天人關(guān)系學(xué)說(shuō)的發(fā)展,則董仲舒“人副天數(shù)”可以給予我們很多啟發(fā)。因?yàn)椤段寮o(jì)》似乎尚未討論《人副天數(shù)》中提及的“無(wú)形者”“不可數(shù)者”,因此其天人關(guān)系即便可以稱(chēng)為“人副天數(shù)”,也尚未到“副類(lèi)”的程度。
通過(guò)與《呂氏春秋》《黃帝四經(jīng)》等文獻(xiàn)比較可以知道,天道呈現(xiàn)出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具體的、看得見(jiàn)的、可以直接效法和遵循、具有天生之可信性與權(quán)威性的禁忌和規(guī)范,既表現(xiàn)為日月運(yùn)行、四時(shí)更替等用“理”“數(shù)”“紀(jì)”來(lái)稱(chēng)呼的宇宙秩序,也表現(xiàn)為“規(guī)”“矩”“方”“圓”等天然的客觀的法度,人對(duì)此天道的把握和效法就是《人副天數(shù)》所謂的“副數(shù)”。天道又可以表現(xiàn)為陰陽(yáng)消長(zhǎng)、動(dòng)靜盈虛、剛?cè)峄?dòng)的宇宙原理,這同樣是人所需要把握和效法的規(guī)律和規(guī)范,具有天生之可信性與權(quán)威性,但卻是看不見(jiàn)摸不著,需要通過(guò)現(xiàn)象抓住本質(zhì),這就是《人副天數(shù)》所謂“陳其有形以著其無(wú)形者,拘其可數(shù)以著其不可數(shù)”的“副類(lèi)”之道。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jì)”,每一紀(jì)的第一篇都是極為嚴(yán)整的天人對(duì)應(yīng)模式,以陰陽(yáng)五行為原則,先敘述每一紀(jì)的天文、歷象、物候等自然現(xiàn)象,然后說(shuō)明天子在衣食住行上所要與之匹配的行動(dòng)原則,以及郊廟祭祀、禮樂(lè)征伐、農(nóng)事活動(dòng)等方面的施政綱領(lǐng)。顯然這是一種按照時(shí)間序列來(lái)安置的天人對(duì)應(yīng),和《五紀(jì)》主要依據(jù)空間序列形成的對(duì)應(yīng)有所不同。《呂氏春秋·圜道》也說(shuō)“天道圜,地道方,圣人法之,所以立上下。”這應(yīng)該就是體現(xiàn)為柔性原理的“副類(lèi)”之道。《黃帝四經(jīng)》也一樣,天道既指天地間那些確定不移的節(jié)律、度數(shù),也指那些進(jìn)入神明境界的圣人才可能領(lǐng)悟、把握的微妙的、適度的、難以言傳、難以量化的節(jié)奏、尺度。
顯然,《五紀(jì)》并未出現(xiàn)類(lèi)似“天子”這樣的現(xiàn)實(shí)人王,天人關(guān)系中鬼神的作用被大大強(qiáng)化,我們看不到《呂氏春秋》《黃帝四經(jīng)》中多見(jiàn)的體現(xiàn)為柔性原理的天道,“后”“后帝”“黃帝”也并沒(méi)有以“執(zhí)道者”形象出現(xiàn)。因此,“副類(lèi)”的天人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很可能是后世在繼承改造《五紀(jì)》類(lèi)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做出的新的思想發(fā)展。不管怎樣,《五紀(jì)》作者精心構(gòu)筑了天地人神一體的宏大藍(lán)圖,并對(duì)其所能產(chǎn)生的效果充滿了期待,那就是“天地、神祗、萬(wàn)貌同德,有昭明明,有洪乃彌,五紀(jì)有常。”“天道之不改,永久以長(zhǎng)。天下有德,規(guī)矩不爽。”由此形成的天人關(guān)系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因此具有了天然的神圣性和絕對(duì)性。
三、從大亂到大治的歷史觀
《五紀(jì)》作為一篇對(duì)宇宙萬(wàn)物做出整體思考的大文章,不可能不涉及歷史觀。歷史觀一般體現(xiàn)為兩個(gè)方面,一是解釋萬(wàn)物從何而來(lái),由此對(duì)于萬(wàn)物的本原本根做出探討,并同時(shí)回答萬(wàn)物的本體問(wèn)題,這也可以歸為宇宙生成論。二是解釋世界的秩序形成,回答何為美好的社會(huì),世界為什么會(huì)亂等問(wèn)題。顯然,《五紀(jì)》中沒(méi)有出現(xiàn)類(lèi)似《楚帛書(shū)》的神話生成論,也沒(méi)有出現(xiàn)類(lèi)似《老子》道生萬(wàn)物的抽象生成論。《五紀(jì)》的歷史觀可以說(shuō)是第二個(gè)方面,即治亂歷史觀的典型。這種歷史觀不重在推溯一切的起點(diǎn),而重在解釋世界動(dòng)亂的原因。因此它不是一種生成論,而是一種變化觀。
《五紀(jì)》在闡述動(dòng)亂起因的時(shí)候,用的是回溯的方式。此篇雖然大部分采用“后曰”的方式,來(lái)交代其宇宙構(gòu)想,但這種構(gòu)想的目的是為了重整山河,而不是從無(wú)到有,從零開(kāi)始。為此《五紀(jì)》穿插了兩段歷史描述,一段是關(guān)于“后帝”的,一段是關(guān)于“黃帝”的。
“后帝”的故事與洪水有關(guān),這應(yīng)該還是承自《洪范》。《洪范》一上來(lái)就提到上古洪水泛濫,“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由此引出“彝倫”(治理大法)的丟失和重現(xiàn),從而為后面“洪范九疇”的出現(xiàn)及其重要性打下了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除了《洪范》之外,《尚書(shū)》中還有很多類(lèi)似的套路,如《益稷》先以大禹的口吻說(shuō):“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接下來(lái)的“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敘述的是大禹在治水過(guò)程中對(duì)于自然地理面貌的改變。后面的大段文章,則導(dǎo)向了政治與制度的設(shè)置,如“古人之象”(服飾、音樂(lè)等)的恢復(fù),意味著禮儀典章等級(jí)的重建,“五服”“五長(zhǎng)”的劃分,意味著行政管理的重建。《禹貢》看似一部地理著作,實(shí)際上以“大禹治水”為背景,推出了山川分布、交通物產(chǎn)、貢賦等級(jí)、行政區(qū)劃、政治制度的重新安置。
《五紀(jì)》也一樣,一上來(lái)就講了一個(gè)上古洪水的故事。“唯昔方有洪,奮溢于上,權(quán)其有中,戲其有德,以騰亂天紀(jì)。后帝、四干、四輔,乃聳乃懼,稱(chēng)攘以圖。”說(shuō)的是遙遠(yuǎn)的古代,因?yàn)楹樗豢煽刂疲鳛橛钪孀罡咭?guī)范“中”和“德”被戲弄,天紀(jì)(宇宙法則)被破壞。于是后帝(上古帝王)、四干(重要諸侯)、四輔(主要輔臣)只能設(shè)法應(yīng)對(duì)這一局面,由于“五紀(jì)”的重新修整,結(jié)果天下恢復(fù)太平,“有昭明明,有洪乃彌,五紀(jì)有常”。和《洪范》一樣,雖然《五紀(jì)》后文通過(guò)“后曰”,源源不斷地闡述了宇宙秩序的設(shè)想,構(gòu)建了龐大嚴(yán)整的天人體系,但洪水的元素再也沒(méi)有出現(xiàn),因?yàn)楹樗闹卫聿⒎亲罱K的目標(biāo)。
清華簡(jiǎn)《三不韋》與《五紀(jì)》關(guān)系極為密切,此文的篇首和片尾也都提到洪災(zāi),“唯昔方有洪,不用五則,不行五行,不聽(tīng)五音,不章五色,[不]食五味,以?戲自鬎自亂,用作無(wú)刑。”“唯昔方有洪,溢戲,高其有水,權(quán)其有中,漫?,乃亂紀(jì)綱,莫申德。”這種描述方式和《五紀(jì)》《洪范》相當(dāng)接近。后面借助天帝的使者“三不韋”向“禹”授予“五刑則”,導(dǎo)出了設(shè)官建邦、祭祀祝禱、修明刑罰、敬授民時(shí)、秉德司中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行為。
在《洪水與戡亂:清華簡(jiǎn)〈五紀(jì)〉中的兩個(gè)重要元素》一文中,筆者闡述了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即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過(guò)大洪水發(fā)生,是否真的有過(guò)大禹治水,鯀是否真的因?yàn)橹嗡《溃鋵?shí)并不重要,古人是要借此引出“亂”的話題,因此《五紀(jì)》《三不韋》中的“有洪”很可能是古書(shū)中作為叛亂勢(shì)力出現(xiàn)的共工,而《洪范》中的鯀也同樣是叛亂勢(shì)力的代表。有亂就必有治,這才是這些文章論述的重點(diǎn)。因?yàn)椤皝y”象未必只有洪水,也可以是其他現(xiàn)象。例如《尚書(shū)·呂刑》說(shuō)“若古有訓(xùn),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講的是遠(yuǎn)古蚩尤作亂以及苗民自作刑罰、自建神人關(guān)系的事情,之后便有顓頊“絕地天通”的宗教控制,以及舜通過(guò)三后(伯夷、禹、后稷)重建刑律法典,開(kāi)展水土治理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等行為。
馬王堆帛書(shū)《黃帝四經(jīng)》也一樣,《十六經(jīng)·觀》說(shuō)“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順無(wú)紀(jì),德虐無(wú)刑,靜作無(wú)時(shí),先后無(wú)名,今吾欲得逆順之[紀(jì)]……以為天下正”,于是黃帝命令力黑“浸行伏匿,周流四國(guó),以觀無(wú)恒,善之法則”。這說(shuō)的是,即便物理意義上的天地已經(jīng)生成,人文制度依然沒(méi)有出現(xiàn)。最初的世界是“無(wú)紀(jì)”“無(wú)刑”“無(wú)時(shí)”“無(wú)名”“無(wú)恒”的,也就是混亂的,和《五紀(jì)》所述“有中”“有德”“天紀(jì)”遭到破壞的情況一樣,黃帝的作用就在于其是“善之法則”,結(jié)束無(wú)序、重建有序。
《五紀(jì)》中出現(xiàn)的“黃帝”,同樣是以結(jié)束混亂的王者形象出現(xiàn)。而他所要征伐的對(duì)象,正是善于打造“五兵”、能夠操縱各種妖祥的蚩尤,黃帝率領(lǐng)臣下與之大戰(zhàn),取得勝利,殺了蚩尤,百神終于安寧,萬(wàn)民終于歸屬。然后就是重建秩序的一貫套路,樹(shù)邦立公,建立官職,通過(guò)設(shè)置軍舞戰(zhàn)歌來(lái)創(chuàng)建禮樂(lè)制度。通過(guò)比較,我們推斷《五紀(jì)》和《黃帝四經(jīng)·十六經(jīng)》有著共同的知識(shí)背景和傳承系統(tǒng),甚至可以說(shuō)《黃帝四經(jīng)》歷史觀也是《五紀(jì)》的進(jìn)一步延伸。
總之,“有洪”制造洪水,破壞“有中”“有德”“天紀(jì)”,蚩尤操縱妖祥、打造五兵,使得“百神皆懼”,這都非閑筆,而是《五紀(jì)》作者有意安排的前奏曲,“后帝”“黃帝”的出現(xiàn)正是為了要結(jié)束混亂、重整山河。所以“后帝”重新排列正定“五紀(jì)”,其作用絕不僅限于整頓歷法;“黃帝”討伐“蚩尤”并解剖、毀壞其身體,也絕不僅是軍事行動(dòng)和祭祀行為,而是天下由大亂到大治的必然環(huán)節(jié),因此有著更為復(fù)雜而深刻的意義。一切政治建制的合理性理念,必須從一治一亂的歷史觀中導(dǎo)出,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們過(guò)去僅僅通過(guò)傳世文獻(xiàn)并不能得到明確的認(rèn)識(shí),現(xiàn)在通過(guò)《五紀(jì)》,再串聯(lián)起《尚書(shū)》《黃帝四經(jīng)》《三不韋》等文獻(xiàn),這種歷史觀的線索越來(lái)越清晰。這種類(lèi)型的歷史觀,不同于《楚帛書(shū)》的傳世神話說(shuō),不同于老子及其道家“大道廢”基礎(chǔ)上的文明倒退說(shuō),不同于韓非子的文明進(jìn)步說(shuō),不同于荀子人性惡基礎(chǔ)上的國(guó)家起源說(shuō),不同于鄒衍的“五德終始說(shuō)”,它建立在天地人神一體的整體宇宙觀上,認(rèn)為這個(gè)宇宙在經(jīng)歷著一治一亂的循環(huán),人類(lèi)一切問(wèn)題的產(chǎn)生以及一切制度的重建都可以由此得到回答,因此是亙古不變的原理。知識(shí)、思想、宗教、權(quán)力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得到重新配置,因此是政治變革合法性的基礎(chǔ)與保障。這種歷史觀很可能在整個(gè)先秦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但我們以前研究并不多,有待進(jìn)一步深入考察。
四、“中”與“德”是《五紀(jì)》的核心理念
“五紀(jì)”看似《五紀(jì)》中最重要的概念,但只是一種工具和途徑。《五紀(jì)》所要實(shí)現(xiàn)的核心理念是“中”與“德”。如前所述,《五紀(jì)》首章敘述了“有洪”作亂,天下失序的狀態(tài)。這個(gè)混亂狀態(tài)表現(xiàn)為兩個(gè)方面:一個(gè)是“天紀(jì)”被破壞了,需要重整;一個(gè)是“有中”“有德”被輕慢了,需要重建。如果說(shuō)“五紀(jì)”代表的是天文秩序和宇宙基本框架,那么“有中”“有德”應(yīng)該代表的是包括人間在內(nèi)的整個(gè)宇宙的最高準(zhǔn)則和最佳狀態(tài)。“有”在這里應(yīng)該是發(fā)語(yǔ)詞,沒(méi)有實(shí)際意義,如《三不韋》中有相似文句,“唯昔方有洪,溢戲,高其有水,權(quán)其有中,漫?,乃亂紀(jì)綱,莫申德。”這里雖然還繼續(xù)沿用“有中”,但后面“德”就是單獨(dú)使用的。因此,“中”與“德”是《五紀(jì)》中極為重要的兩個(gè)概念,事實(shí)也證明,“中”與“德”是《五紀(jì)》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兩個(gè)字。
“中”字,整理者大多釋讀為“忠”,筆者認(rèn)為這是沒(méi)有必要的,雖然這個(gè)字是個(gè)雙關(guān)語(yǔ),在某些場(chǎng)合確實(shí)可以假借為“忠”(如“天下禮以事賤,義以待相如,愛(ài)以事嬪妃,信以共友,中(忠)以事君父母”),但首先,這個(gè)字的構(gòu)架本來(lái)就不從“心”;其次,如果讀為“忠”,將使“中”之內(nèi)涵、意義和價(jià)值大打折扣,如果使用“忠”,其對(duì)應(yīng)的深度和廣度將完全無(wú)法體現(xiàn)。所以應(yīng)該直接讀為“中”,僅在某些特殊的場(chǎng)合可以假借為“忠”。筆者在《清華簡(jiǎn)〈五紀(jì)〉的“中”觀念研究》一文中,提出“中”的使用大約可以做如下三個(gè)方面的歸類(lèi):1.代表最高理念的“中”;2.作為具體德目的“中”;3.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的“中”。
代表最高理念的“中”,僅僅從《五紀(jì)》首章描寫(xiě)混亂狀態(tài)時(shí)所謂“權(quán)其有中,戲其有德,以騰亂天紀(jì)”已經(jīng)可以窺見(jiàn)一斑。作為具體德目的“中”,指的是“中”是“禮、義、愛(ài)、信、中”五文德中的一種,如果僅僅是一種德目,就不會(huì)有那么高的價(jià)值,但其實(shí)不然:首先,如前所述,《五紀(jì)》中五文德絕不僅僅是人間的倫理規(guī)范,五種文德和天地間幾乎所有的重要元素都構(gòu)成了匹配,因此是宇宙秩序的一環(huán),是天道的體現(xiàn);其次,“中”在五種“文德”里被排在最后一位,居于特殊的位置,與“中”相匹配者,如“天”“數(shù)算”“心”“圓裕”“黃”“君父母”“中極”等,在層級(jí)上明顯高于與其他四德相匹配者。“后帝”“黃帝”在出場(chǎng)的時(shí)候,也明顯體現(xiàn)出以“中”統(tǒng)外,以“一”統(tǒng)“四”的特點(diǎn)。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的“中”,指的是《五紀(jì)》屢屢出現(xiàn)的“心相中,中行圓裕”“我行中”“中曰行”等說(shuō)法,最后甚至以“愛(ài)中在上,民和不疑,光裕行中,唯后之臨”作為總結(jié),可見(jiàn)其明確地把“中”作為一種目標(biāo)、方向來(lái)實(shí)踐,或者說(shuō)以“中”的方式來(lái)行動(dòng)。
總之,“從地位上看,《五紀(jì)》的‘中’居于統(tǒng)攝的、主宰的位置。從內(nèi)涵上看,‘中’這種德與中正、公平、無(wú)私、寬裕相應(yīng),具有絕對(duì)的、神圣的特點(diǎn)。從行為上看,‘中’就是所要實(shí)現(xiàn)的目標(biāo),一種最佳的行動(dòng)方式。”“中”如此崇高的價(jià)值與地位,也和《五紀(jì)》非常明確的中央意識(shí)以及潛藏的大一統(tǒng)意識(shí)高度吻合。與《五紀(jì)》有類(lèi)似意涵的“中”,在傳世文獻(xiàn)中可見(jiàn)于《尚書(shū)·呂刑》和《逸周書(shū)·嘗麥》,這兩篇文獻(xiàn)都將刑律稱(chēng)為“中”,表示“中”有公平正義的意思。也可見(jiàn)于《論語(yǔ)·堯曰》的“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這里的“中”與天文歷法有關(guān),而《五紀(jì)》的“中”正好與“數(shù)算”“數(shù)稽”匹配,具有宇宙法則的特征。在出土文獻(xiàn)中,最為相近的就是清華簡(jiǎn)《保訓(xùn)》,作為周文王遺言的《保訓(xùn)》中出現(xiàn)了四個(gè)“中”,被視為治國(guó)理政的最重要法則,其意義既和歷法有關(guān),也和刑律有關(guān),但歸根結(jié)底體現(xiàn)著公平公正之意,這和《五紀(jì)》所見(jiàn)的“中”在精神實(shí)質(zhì)上高度一致。
后世儒家也推崇“中”,但主要指《論語(yǔ)》以及《禮記·中庸》所見(jiàn)之“中庸”,《中庸》說(shu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對(duì)“中”評(píng)價(jià)極高。《五紀(jì)》雖然沒(méi)有形容“中”為天下大本,但實(shí)際上對(duì)“中”的評(píng)價(jià)也不低于此。這樣說(shuō)來(lái),《五紀(jì)》的“中”和“中庸”貌似有相似處。然而從《論語(yǔ)》和《中庸》篇看,“中”一方面被理解為“喜怒哀樂(lè)之未發(fā)”,也就是與外在的“身”相對(duì)的內(nèi)在的“心”以及情感和意志,另一方面被理解為執(zhí)兩用中、不偏不倚的最佳行為方式。而且這個(gè)“中”要與“和”聯(lián)系起來(lái)才能發(fā)揮作用,即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àn)物育焉”。因此這個(gè)“中”更多指的是內(nèi)心的活動(dòng)以及外在的行動(dòng),如“君子而時(shí)中”“從容中道”所示,是可以隨時(shí)調(diào)整、靈活應(yīng)用的,和《五紀(jì)》所表達(dá)的作為宇宙間最高的秩序和準(zhǔn)則的“中”有相當(dāng)距離。
《洪范》未見(jiàn)“中”的概念,如果我們視《五紀(jì)》為《洪范》的繼承與發(fā)展,那么對(duì)“中”的樹(shù)立與高揚(yáng)可以說(shuō)是差異最大的地方。為什么會(huì)有這樣的轉(zhuǎn)變,值得深入探究。《洪范》雖未見(jiàn)“中”,但后人卻用“大中”釋“皇極”,漢代孔安國(guó)云:“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dāng)用大中之道。”孔穎達(dá)也說(shuō):“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dāng)使大得其中,無(wú)有邪僻。”如果說(shuō)孔安國(guó)和孔穎達(dá)的解釋不是空穴來(lái)風(fēng),那么《洪范》中第五疇“皇極”的概念,正是“中”的源頭之一。細(xì)察“皇極”的內(nèi)容,主要指的是人倫意義上各種最佳的行為方式,而不涉及宇宙秩序,因此即便《五紀(jì)》的“中”來(lái)自《洪范》,其內(nèi)涵和高度也顯然大大加強(qiáng)了。
“德”是《五紀(jì)》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概念,《五紀(jì)》認(rèn)為,“天下有德,規(guī)矩不爽”,最有秩序的時(shí)代是“有德”的時(shí)代,相反,混亂的時(shí)代就是“有德”被戲弄拋棄的時(shí)代。和“中”一樣,“德”在《五紀(jì)》中也有不同層次,也有廣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德首先是人之德、民之德,是德行,是行動(dòng)準(zhǔn)則,具有倫理規(guī)范的意義,這層意涵在《五紀(jì)》的五種“文德”(禮、義、愛(ài)、信、中)中表現(xiàn)得最為充分。《五紀(jì)》說(shuō)“唯德曰禮義愛(ài)信中,合德以為方”,即五種“文德”合在一起,就可以成為行為標(biāo)準(zhǔn)了。
如前文所述,這五種文德的關(guān)聯(lián)性極強(qiáng),和天時(shí)、天體、星辰、神祇、方位、度量、顏色、身分、舉止、外表、禁忌、人體部位可以對(duì)應(yīng)匹配起來(lái),這樣做的目的當(dāng)然是為了顯示人倫的天經(jīng)地義,因此是不可抗拒的天道之一。《五紀(jì)》在“天五紀(jì),地五常,神五時(shí)”之后接著說(shuō)“五親五德,天下之算”,“五親”可能指“賤、相如、嬪妃、友、君父母”這五種親近之人,“五德”就是五種相應(yīng)的德目,和“五紀(jì)”“五常”“五時(shí)”一樣,“五德”也是天下之“算”,即不可抗拒的宇宙法則。至于為何要在社會(huì)上大量流傳的各種德目中選擇這五種,為何要這樣排列,可能存在作者根據(jù)自己的設(shè)計(jì)而拉郎配的可能性。“德”又是君主之德,是德政,是政治行為方式,是作用與能力的體現(xiàn)。《五紀(jì)》中除了五種“文德”外還有“三德”,即“文德”“惠德”“五德”。“文德”就是“禮、義、愛(ài)、信、中”,可見(jiàn)五種“文德”就包含在“三德”之中。“惠德”指“仁、善、祥、貞、良”,“武德”指“明、巧、美、有力、果。”《五紀(jì)》說(shuō)“文、惠、武三德以敷天下”,可見(jiàn)有了“三德”,天下的治理就易如反掌了。
如前所言,“三德”可能承繼了《洪范》“三德”的模式。“惠德”居中,“文德”“武德”一左一右,類(lèi)似于《洪范》“正直”居中,“剛?cè)帷币徽环础F鋬?nèi)在邏輯應(yīng)該是,“禮義愛(ài)信中”為“民之德”(或統(tǒng)治者“正民之德”),是為社會(huì)大眾建立的倫理秩序,而“明、巧、美、有力、果”是政治上的最佳效果,“仁、善、祥、貞、良”作為“惠德”,是高明的統(tǒng)治者在“文”和“武”之間居中調(diào)節(jié)的正確姿態(tài),所以準(zhǔn)確地說(shuō),只有“惠德”指的是君德。和五種“文德”一樣,其德目的選擇和排列,未必有明確的邏輯關(guān)系,完全有可能是出于搭建宇宙秩序的需要,而生拉硬扯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
在有的地方,《五紀(jì)》也強(qiáng)調(diào)君主的“德”來(lái)自上天所授,如“南門(mén)授信,而北斗授愛(ài),是秉信而行愛(ài)。既膺受德,踐位有常。”從“踐位有常”來(lái)看,其主體一定是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者如果能夠從象征天體主宰之位的“北斗”“南門(mén)”中秉受“信”“愛(ài)”之德,那么他就有資格“踐位”,并保證政治的順利(有常)。這似乎是西周以來(lái)天命有德的套路,這一點(diǎn)被后世儒家大為發(fā)揮,《五紀(jì)》中也有這方面的思想資源。
《五紀(jì)》中還有很多“德”的表述,體現(xiàn)出《五紀(jì)》德思想極為復(fù)雜的面相。如《五紀(jì)》中還有一個(gè)“三德”,即“皇天之三德”,“以事父之祖,而供母之祀,化民之忒,是謂三德。”如李均明所言,這屬于諸神中“高大”這個(gè)神的職司,這個(gè)“三德”應(yīng)該是在祭祀中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德”。“高大”同時(shí)出現(xiàn)于二十四神祇與三十神祇中,司掌“信”與“時(shí)”,“信”與“時(shí)”為何與祭祀之德有關(guān),還有待分析。
《五紀(jì)》在分析疾病發(fā)生的原因時(shí)說(shuō),“雜德不純,百祟之殃”,有“雜德”也就必然有“純德”,可能《五紀(jì)》也認(rèn)為,“德”是秉受于天的、原生的、純粹的東西,接近于《老子》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因此,這個(gè)“德”已經(jīng)暗含德性的成分,當(dāng)然這個(gè)德性未必是倫理意義上的。
《五紀(jì)》又說(shuō)“天之正曰明視,人之德曰深思”,這個(gè)“德”顯然指的是認(rèn)知上的能力和作用,即不同于天能“明視”,明察秋毫,人的能力在于心智,可以深思。
《五紀(jì)》在文章最后提到“言天有信,言神有化,言地有利,言事有時(shí),言型有情,言德有則,言古有矩。”這里“德”和“則”形成對(duì)應(yīng),顯示“德”的含義可以和“則”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從前文的分析來(lái)看,《五紀(jì)》的“德”雖然在個(gè)別地方有德性(“雜德”)義,但大多是作為德行、德政來(lái)理解的,即這是一種外在的、剛性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雖然也具有倫理色彩,但屬于“儀式倫理”,而非“德性倫理”,即這種“德”更強(qiáng)調(diào)規(guī)范意義上的不得不為,而非發(fā)自?xún)?nèi)心的道德自律,而且需要配合整體的宇宙法度。在這一點(diǎn)上,《五紀(jì)》的“德”和后世儒家心性意義上的“德”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特質(zhì)。
將“德”與“則”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在《五紀(jì)》中僅此一處,然而在清華簡(jiǎn)《三不韋》篇中卻得到了更為豐富的論述。《三不韋》有“五刑則唯天之明德”,賈連翔認(rèn)為《三不韋》中的“德”每每可與“則”進(jìn)行概念替換。這一現(xiàn)象在傳世文獻(xiàn)中也可以得到印證,但過(guò)去并不重視。例如《逸周書(shū)》之《和寤》有“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zhuān)陆禐閯t,振于四方。”說(shuō)的是武王手下大臣之美德降于民間成為典范,影響遠(yuǎn)及四方。《成開(kāi)》和《本典》篇均有“顯父登德,德降為則,則信民寧。”即德高望重者舉明道德,道德降為法典,法典切實(shí)則百姓安寧。《文酌》也有:“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lè)有哀,有德有則。”《逸周書(shū)》這些“德”“則”連用的說(shuō)法值得注意,即“德”是可以轉(zhuǎn)為“則”(典范)的。
這提醒我們可能需要重新理解《詩(shī)經(jīng)·民》中這幾句話:“天生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這里也是“則”“德”對(duì)應(yīng)連用,顯然這個(gè)“懿德”應(yīng)該往天地間外在的秩序、法則去理解。《韓詩(shī)外傳》卷6引用此句后說(shuō):“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潛夫論·相列》引用此句后說(shuō):“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lèi),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這都保存了人之德必須與天之法則保持一致的基本傾向。然而,因?yàn)槊献釉谡撌鏊亩酥暮笠龃嗽?shī),后世儒家完全扭轉(zhuǎn)了《詩(shī)經(jīng)》的解釋方向,將“懿德”理解為內(nèi)在美好的德性,然后進(jìn)一步加入了德性來(lái)自天,因而是先天的、固有的等等內(nèi)容,來(lái)為孟子的性善論提供天道的依據(jù)。然而,從《五紀(jì)》以及相關(guān)的傳世文獻(xiàn)來(lái)看,這樣的解釋沒(méi)有什么根據(jù),“懿德”應(yīng)該就是天所展示的準(zhǔn)則和規(guī)范。
可見(jiàn),對(duì)于德的重視和經(jīng)營(yíng)幾乎貫穿《五紀(jì)》全文,成為《五紀(jì)》一條重要的線索,在比例上這條線索絲毫不輸于宇宙論,甚至可以說(shuō),宇宙論的部分也是為“德”的確立服務(wù)的。
在《五紀(jì)》中,“德”可以是德行,可以是德政,可以是民德,可以是君德,但都可以體現(xiàn)為作用、功能,最后轉(zhuǎn)化為標(biāo)準(zhǔn)與規(guī)范,因此可以與“則”和“中”聯(lián)系起來(lái)。《五紀(jì)》的作者將宇宙萬(wàn)物幾何化、格式化,就是要力圖創(chuàng)造一個(gè)嚴(yán)整的、有序的世界,因此“德”就是宇宙秩序的一種,是標(biāo)準(zhǔn)化的一環(huán)。這樣的德觀念,似乎介于德思想演變的早期階段,即強(qiáng)調(diào)外在規(guī)范與作用的一面更多一些。
總之,“中”與“德”是《五紀(jì)》中兩個(gè)最為核心的概念,“中”既是“五德”中最高者,也是中心、統(tǒng)攝、公正、圓融、準(zhǔn)則的象征。“中”既是“德”之一,又超出了“德”的范疇,具有方法上的作用與功能。“德”作為民德是外在倫理規(guī)范,作為君德是體現(xiàn)為方法和效果的政治藝術(shù)。兩者既有區(qū)別,又有不少地方是交叉的,如“中”和“德”都和秩序、法則、規(guī)范有關(guān),都有方法論的意義,也都是效果的體現(xiàn)。為什么既要“有中”又要“有德”,“中”和“德”是怎樣聯(lián)系與互補(bǔ)的33IFInUwgpEWK0ghwEAQwA==?限于篇幅,這個(gè)復(fù)雜的問(wèn)題留待他文展開(kāi)。
五、余論
《五紀(jì)》無(wú)疑是篇大文章,因?yàn)橐獮槿f(wàn)物立法,要為天下設(shè)序,所以《五紀(jì)》作者顯示出極大的雄心,假借“后”的口吻,利用“后帝”“黃帝”的故事,從歷法入手eLCsbgp6qc4RJ4uLlcnu7Q==,構(gòu)建了一個(gè)極為龐雜、但又井井有條的世界圖景,這個(gè)世界圖景里面有一治一亂的歷史觀,有天地人神相互對(duì)應(yīng)、同頻共振的宇宙觀,有無(wú)所不在的鬼神系統(tǒng),有以“五”為框架的數(shù)理結(jié)構(gòu),有與宇宙元素反復(fù)勾連匹配的道德規(guī)范,有中央突出、各就其位,超時(shí)空、大一統(tǒng)的政治布局,有追求最高理念、最佳狀態(tài)的思想探索。本文僅僅探討了源自《洪范》的文本系統(tǒng),從天道到人道的天人關(guān)系,一治一亂的歷史觀和作為核心概念的“中”“德”,限于篇幅,宇宙觀、五行觀、鬼神觀、名號(hào)觀都未能收入,而已經(jīng)討論的問(wèn)題也還流于表面,但本文的目的在于以簡(jiǎn)略的方式,概括《五紀(jì)》文本與思想上的基本特征,并梳理出主要線索和重要問(wèn)題,為學(xué)界進(jìn)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礎(chǔ)。
毫無(wú)疑問(wèn),《五紀(jì)》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體系有全面的消化和吸收,但又依據(jù)自身的要求將這些知識(shí)做出新的整合,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面貌。這樣的面貌在個(gè)性化強(qiáng)烈的諸子文獻(xiàn)中很難找到對(duì)應(yīng),因此,在筆者看來(lái),《五紀(jì)》很有可能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獨(dú)立于諸子之外,主要在最高統(tǒng)治階層傳播的知識(shí)和思想體系,是一種特殊的王官之學(xué)、帝道之學(xué)。這種對(duì)世界作出整體考量的學(xué)術(shù)體系為何沒(méi)有得到全面繼承、發(fā)展和延續(xù),也是個(gè)非常值得深思的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