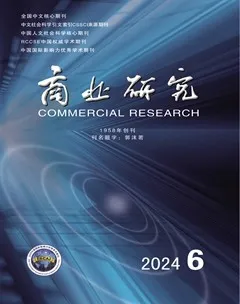數據要素集聚與實體經濟結構優化:“脫虛返實”的視角







摘"要:以數據要素集聚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發展是推動實體經濟結構優化的關鍵。本文基于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探討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程度的影響及其內在機理。研究發現:數據要素集聚顯著降低實體企業金融化程度,即促進實體經濟結構優化。機制識別發現:數據要素集聚可以減弱預防性儲備動機并增強實體獲利能力,進而抑制企業過度金融化。異質性檢驗發現: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民營企業、低金融錯配、高償債能力、地區金融科技水平較高以及法律環境較好的樣本中更為明顯。進一步分析發現,數據要素集聚也能夠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關鍵詞:數據要素集聚;企業金融化;預防性儲備動機;實體獲利能力
中圖分類號:F2734;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4)06-0010-10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20年以后,先后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明確將數據列為五個生產要素之一,指出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強調數據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乘數作用不斷凸顯,也從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四個方面對中國數據制度體系和機制的進行了頂層設計和全盤細致謀劃。為了發揮數據要素的集聚效應,國家發展改革委在2016年2月批復貴州省成為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此后又陸續批準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遼寧、河南、上海、重慶、廣東等9個省份為第二批試驗區。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構建旨在促進數據要素的流通與共享,從而有效釋放其潛在價值,成為試點地區集聚數據要素的關鍵平臺。
2008年以來,大量非金融企業不斷脫離實體經濟而涉足金融活動,呈現顯著的金融化趨勢[1]。因此,本文欲從數據要素集聚出發,探討破解實體經濟金融化困境。現有研究對數據要素的經濟效應作了豐富地探討。比如,Müller等(2018)[2]使用包含公司擁有的數據要素解決方案詳細信息的獨特面板數據集,研究表明數據要素能夠提高實體企業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創造巨大商業價值。而謝康等(2020)[3]則探討大數據從可能的生產要素成為企業現實生產要素的實現機制,研究表明數據要素能夠提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可見,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已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環節。對此,與本文相關的文獻在于探討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帶來的數據要素集聚的影響效應。在宏觀層面,研究表明數據要素集聚主要體現在提高地區全要素生產率[4]、提高試點地區科技創新水平[5]等方面。而在微觀層面,也有研究關注了數據要素集聚如何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6]。
雖然也有研究從企業內部探討利用數據要素能夠通過資源擠出、治理變革和風險分散顯著抑制企業金融化,但是該研究框架存在突出的內生性問題,且缺少關于數據要素的集聚效應如何提升企業從實體獲利能力的探討,即忽視了數據要素的外部集聚效應。對此,本文以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的準自然實驗,從預防性儲備動機和實體獲利能力視角,探討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將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設立作為數據要素集聚的外生沖擊,較好解決內生性問題,準確識別數據要素集聚與企業金融化間的因果關系。第二,基于預防性儲備動機和實體獲利能力視角,深入剖析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影響的內在機制。第三,研究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特定企業金融化行為有顯著抑制作用,可為“脫實向虛”的經濟結構優化問題提供新的治理思路。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不少研究表明,金融投資收益逐漸成為非金融企業的重要收益來源,引致金融資產的風險收益錯配,極大抑制了企業實業投資的意愿[7]。現有研究將企業金融化動機的根源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嚴重的融資約束使得具有強勁增長機會和風險較高的現金流的公司持有相對較高的現金與非現金資產總額的比率[8],更多持有金融資產以應不確定性沖擊,即預防性動機。二是在外部需求持續低迷和國內經濟經歷結構轉型的雙重壓力下,實體部門投資收益率和利潤率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同時實體經營風險亦隨之上升,即企業實體獲利的能力較弱,因而將資源配置到金融投資領域進行短期投機逐利。隨著大數據時代發展,數據要素逐漸成為企業經營決策和資產配置取向的微觀基礎與重要引擎。本文核心邏輯在于,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為實體企業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推動了數據要素集聚,可以從提高企業信貸融資便利性以抑制預防性動機,以及增強企業實體獲利能力以抑制企業短期投機逐利動機兩個途徑,減少企業金融資產配置行為,緩解企業“脫實向虛”的傾向。
第一,數據要素集聚可以提高企業信貸融資的便利性,減弱企業資源觀下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信貸融資約束是決定企業投融資政策的重要因素,融資約束限制了企業實體投資的意愿。由于銀行信貸融資是外部融資渠道的主要來源,而銀企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企業面臨嚴重融資約束,進一步加劇了企業配置金融資產的動機。現有研究指出,數據要素能夠使外部投資者識別企業利用數據要素創造價值的程度,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決策成本以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進而緩解信貸融資約束程度,最終提高企業價值[9]。具體來說,數據要素集聚緩解信貸融資約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供給端來看,數據要素的集聚為銀行提供全面且準確的企業信息,幫助銀行精準評估企業的償債能力,降低銀行對企業信用風險的擔憂;從需求端來看,數據要素集聚可幫助企業獲得更多的市場信息和機會,借此優化自身經營決策,并利用相關信息增強與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作,進而獲得有利的融資條件。因而,融資約束的緩解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成本和難度,減少企業對金融資產的依賴,同時釋放的資金可以更有效地用于實體投資,從而抑制企業過度金融化。由此可見,數據要素集聚通過優化數據要素配置和應用,緩解企業信貸融資約束,釋放實體投資的資金壓力,引導企業資源配置回流實體,減弱企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第二,數據要素集聚可以從智能化轉型和產能利用率兩個方面提升企業的實體獲利能力,進而減弱企業在金融市場的短期投機逐利動機。從企業智能化轉型來看,理論模型已證明,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智能化轉型不僅能夠促進企業勞動力技能結構調整,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企業價值[10],還能夠增強實體經濟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吸引資金從房地產流向實體經濟[11]。一般而言,推動智能化轉型有助于企業有效應對企業間的競爭困境,增強實體投資信心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具體而言,一方面,數據要素利用在推動智能技術進步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提供人工智能發展所需的訓練材料和應用場景。其根源在于,消費者生成的數據作為知識積累的關鍵因素,研發部門能夠使用此類數據進行創新,并為最終產品生產作出貢獻。劉征馳等(2023)[12]將數據要素利用與智能技術進步同時納入內生增長模型框架,發現數據要素利用通過促進智能技術進步能夠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推動資本投入到實體經濟,減少金融領域的資金流入。唐曉華等(2021)[13]在充分考慮“金融加速器”且引入共生演化機制的基礎上,構建了包含人工智能要素的多層嵌套一般均衡模型,發現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關鍵技術突破是引導經濟“脫虛向實”的有力手段。因此,數據要素集聚能夠促進企業智能化轉型,增強企業最終產品的生產效率,進而增強實體經濟獲利的能力,吸引企業資源向實體部門轉移。
從產能利用率來看,數據要素集聚能夠促進數據基礎設施完善,"降低調整成本,提升企業產能利用率,增強企業利用數據要素的外部性。一方面,從企業柔性視角出發,數據要素集聚帶來的信息化有助于企業更精確地獲得需求信息,提高企業對信息化資源的利用效率,及時有效地對需求沖擊作出反應,進而提高產能利用率[14],幫助企業釋放優質產能,降低實體部門非效率投資。另一方面,數據要素集聚能夠通過優化生產流程和資源配置,發現生產過程中的瓶頸和低效環節,進而采取針對性措施進行改進,減少資源浪費。據此,數據要素集聚能夠產生產能治理效應,抑制企業金融資產配置行為。理論邏輯在于,產能利用效率的提升通常伴隨著成本的降低和產品質量的提高,極大增強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15],進而抑制企業通過金融化手段追求快速利潤的動機。由此可見,數據要素集聚通過降低調整成本,優化信息利用流程,發揮促進金融部門向實體部門的“拉力”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兩個待檢驗的研究假說:
H1: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帶來的數據要素集聚,可以降低企業的金融化程度,幫助實體部門“脫虛返實”。
H2: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帶來的數據要素集聚,可以減弱預防性儲備動機和投機逐利動機,進而降低企業的金融化程度。
三、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21年間,且在2016年前上市的我國A股公司,作為基準回歸研究樣本。特別地,本文初始數據區間為2007—2022年,一方面,選擇"2007"年作為本文開始年份是因為2007年開始實施新的會計準則,企業金融資產持有的相關科目被重新界定并實現更為詳細的披露,同時突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的特殊背景。并且在2007年之前我國企業金融化程度總體較低,而2007年之后開始迅速攀升。因此,將樣本限定在2007年之后可以較好地排除一些混雜影響。另一方面,以2021年作為截止年份是因為本文使用未來一期的企業金融化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以緩解時間上的反向因果問題。
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Wind數據庫以及CNRDS數據庫,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設立地區和時間通過政府公開網站進行手工搜集與整理而得。樣本具體篩選過程如下:(1)剔除金融保險業、ST類以及*ST類的企業;(2)剔除主要變量缺失的樣本。此外,剔除2016年以后上市的企業,以滿足政策實施前后樣本企業均存在觀測值的要求,增強處理組和控制組企業的可比性。經過以上處理,最終得到31497個公司-年度觀測值。主要連續變量作上下1%分位數Winsorize截尾處理,已排除異常值的干擾。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為檢驗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所產生的微觀政策效應,即數據要素集聚能否有效抑制企業金融化,本文構建如下雙重差分模型:
Finaciali,t+1=γ0+γ1Treat*Posti,t+γ2Controlsi,t+∑Year+∑Firm+εi,t(1)
其中,Financial為企業金融化程度的代理變量,為緩解時間上的反向因果問題,在基準模型中使用t+1期作為被解釋變量。Treat*Post為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對數據要素集聚的外生沖擊變量。Controls表示一系列影響企業金融化的控制變量,分別從企業層面和宏觀層面加以控制;Year為年份固定效應,用以控制隨時間變化的因素;Firm為企業固定效應,用來控制企業層面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εi,t為隨機誤差項。為消除異方差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將標準誤在企業層面進行聚類調整。本文主要關注Treat*Post的回歸系數γ1,其代表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程度的凈影響,若本文理論分析無誤,其應顯著為負。主要變量的具體定義如下:
1企業金融化程度(Financial)。借鑒Demir(2009)[16]的研究,本文采用企業持有金融資產份額衡量企業金融化程度,即企業金融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其中,對于金融資產的度量,借鑒司登奎等(2023)[17]的研究,本文采用“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凈額、持有到期的投資凈額、投資性房地產凈額、貨幣資金、應收股利凈額、應收利息凈額”之和表示。基于穩健性的考慮,本文也采取兩種替代方案對其重新測度。
2數據要素集聚(Treat*Post)。本文采用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作為數據要素集聚的外生沖擊,設定處理效應變量Treat*Post。具體來說:首先,設定Treat代表受到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影響的企業的虛擬變量,若企業注冊地所在地區設立了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則Treat取值為1,否則為0。珠三角地區在建設國家級大數據試驗區時,所建設和輻射的影響范圍并不局限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還涉及廣東省內的其他城市。因此,本文將廣東的所有城市均作為處理組城市[4],并在后續實證分析中添加珠三角地區為處理組的穩健性檢驗。其次,設定Post代表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的時間虛擬變量,當樣本年度為2016年當年及以后年份時,取值為1,否則為0。貴州省于2015年9月開始建設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但直到2016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才正式批復同意,因此我們認為政策效果應于2016年才實際發揮。第二批大數據試驗區同樣于2016年陸續開始實施,因此本文選擇2016年為整個樣本期間的政策時點,并在后續實證分析中添加貴州省政策時點2015年的穩健性檢驗。
3.控制變量(Controls)。參考司登奎等(2023)[17]等已有文獻研究,從企業個體特征和地區特征兩個方面對可能影響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因素加以控制,具體包括如下: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凈利潤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經營性現金流量(CF)、股權集中度(TOP1)、股權制衡度(EB)、產權性質(SOE)、獨立董事比例(IDIR)、兩職合一(DUAL)、公司年齡(LA)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Econodev)等。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限于篇幅,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未作報告,留存備索。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本文采用模型(1)進行實證檢驗,表2報告了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程度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列(1)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代表試驗區設立對企業金融化的直接影響效果,其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266,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列(2)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213,在1%的水平上依然顯著為負。綜上可知,數據要素集聚有助于抑制企業金融化,假設H1得以驗證。
(二)平行趨勢假定與無預期效應假定
理論上使用雙重差分模型需要滿足平行趨勢假定,即在政策干預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因變量變化趨勢一致,并且保證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不能形成明顯的有效預期,即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和無預期效應假設,否則將會對政策的實施效果形成干擾。為證明政策實施的外生性,本文同時進行了平行趨勢檢驗和預期效應檢驗。
首先,以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前后五期作為解釋變量,分別設定如下虛擬變量:Pre1,試驗區設立之前的第一期取1,否則為0,Pre2至Pre5,依此類推;Current,試驗區設立當期取1,否則為0;Post1,試驗區設立之后第一期取1,否則為0,Post2至Post5,依此類推。本文以Pre1作為基期,回歸結果如表3列(1)所示。從中可以看出:試驗區設立之前,政策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但不顯著;而試驗區設立之后,政策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均至少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因而數據要素集聚與企業金融化的關系通過了平行趨勢假定。
其次,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年份前一年的虛擬變量Pre1,以考察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的前一年其政策效果是否顯現,即政策外生性需要保證該政策在實施之前并未顯現出政策效果。回歸結果如表3列(2)所示,Pre1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在政策實施之前對企業持有金融資產份額未形成預期效應,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設立具有外生性。
(三)其他穩健性測試限于篇幅,相關檢驗結果未作報告,留存備索。
為了提高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我們還分別進行了雙重機器學習法(DDML)、合成雙重差分檢驗(SDID)、安慰劑檢驗、PSM-DID檢驗、熵平衡匹配(EBM)、遺漏變量的敏感性分析、替換被解釋變量、替換解釋變量、排除混雜效應等穩健性測試。除此之外,本文也引入行業與年度的交互固定效應(Industry*Year),或者采用行業、城市和省份等三個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對模型進行重新估計。總體而言,以上穩健性檢驗在統計顯著性和系數符號上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進一步驗證了研究假設。
五、進一步分析
(一)作用機制檢驗
根據前文的分析,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設立推動了數據要素集聚,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一方面可以提高企業信貸融資便利性以抑制預防性動機;另一方面,可以增強企業實體獲利能力以抑制企業短期投機逐利動機,進而促進資本向實體部門回流,抑制企業金融資產配置。對此,為進一步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影響企業金融化的內在機制,本文借鑒劉沖等(2023)[18]的方法,構建以下兩階段模型:
Mi,t=γ0+γ1Treat*Posti,t+γ2Controlsi,t+∑Year+∑Firm+εi,t(2)
Finaciali,t+1=γ0+γ1M^i,t+γ2Controlsi,t+∑Year+∑Firm+εi,t(3)
其中,M為本文關注的機制變量,分別表示為融資約束(Constraints)、人工智能程度(LnAI)以及產能利用率(CU),其余變量定義與模型(1)一致。本文將模型(2)定義為第一階段模型,使用雙重差分方法識別數據要素集聚對機制變量M的影響。本文將模型(3)定義為第二階段模型,使用第一階段模型中機制變量M的擬合值來預測企業金融化程度,反映在數據要素集聚的沖擊下,機制變量M的變動如何傳導至企業金融化程度。
1"預防性儲備動機機制
在信貸融資受限的情況下,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成本可能較高,因此企業可能會通過增加金融資產配置來降低對外部融資的依賴,尤其是當這些金融資產能夠帶來相對較高的收益時,信貸融資約束極大激發了實體企業預防性儲備動機。隨著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設立,數據要素易形成集聚效應,增強金融機構對企業信用狀況的了解,降低企業獲取信貸融資的難度,為企業開展實體業務提供資金支持,進而較好地扭轉整體資源過度“向虛”的傾向。因此,數據要素集聚能夠通過緩解企業信貸融資約束機制,抑制企業金融化的預防性儲備動機。
對此,本文借鑒Hadlock和Pierce(2010)[19]的研究,使用SA指數來測量企業的相對信貸融資約束程度(Constraints)。具體計算公式為:SA指數=-0737×資產規模+0043×資產規模×資產規模-0040×存續年限。可知,SA指數是關于資產規模的二次函數,其對稱軸為857且開口朝上。由于本文的企業資產規模(Size)的量綱為元并取自然對數,其取值范圍在194376與261532之間,遠大于857的對稱軸。因此,SA指數越大,企業信貸融資約束程度越小。回歸結果見表4列(1)和列(2),第一階段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078,且在10%水平上顯著;第二階段中Constraints︿的系數為-27479,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數據要素集聚能夠顯著緩解企業信貸融資約束,抑制企業預防性儲備動機,進而降低企業金融化程度。
2"實體獲利能力機制
為了檢驗企業的實體獲利能力機制,本文從智能化轉型和產能利用率兩個方面具體考察。首先,新時期人工智能賦能背景下,實體經濟關鍵技術突破能否成為吸引資本回流實體,引導經濟“脫虛向實”是關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關鍵問題。一方面,數據要素為人工智能技術提供豐富的訓練材料和應用場景,推動企業在生產決策過程中采用更為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提升企業生產效率[10],進而提升企業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另一方面,數據要素集聚有助于企業更有效地配置資源,有助于推動企業將資源更多地投入到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科技創新中,進而減少企業向金融領域的資金流入。基于此,本文借鑒姚加權等(2024)[10]的研究,采用機器學習的方法生成人工智能詞典人工智能詞典的具體構建方法請參考姚加權等(2024)的研究。,通過對我國"A"股上市公司年報和專利進行文本分析,統計上市公司年報中人工智能詞語的數量,然后對其加1取自然對數(LnAI)作為企業人工智能技術的代理變量。該變量越大,說明企業的智能化轉型程度越高。回歸結果見表4列(3)和列(4),第一階段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832,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第二階段中LnAI︿的回歸系數為-02562,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數據要素集聚能夠顯著促進企業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推動企業智能化轉型,進而抑制企業配置金融資產的行為。
其次,數據要素集聚的作用還在于其對產能利用率的影響。具體來說,一方面,數據要素的集聚能夠使企業通過對大量數據的分析和挖掘,準確地識別市場需求,優化產品設計,提升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數據驅動的決策支持系統能夠幫助企業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優化生產模式,實現供需精準對接,有助于減少資源浪費和過剩產能,減少產能浪費,進而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滿足市場需求來增加利潤,能夠增強企業從實體獲利的能力,抑制企業追求金融化擴張的動機。因此,數據要素集聚能夠形成產能治理效應,提高產能利用率,且抑制企業金融化程度。基于此,本文借鑒李雪松等(2017)[20]的研究,使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法,使用實際產出與前沿產出的比值作為企業產能利用率的代理變量。該變量值越大,意味著企業產能利用率越高。回歸結果見表4列(5)和列(6),第一階段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040,且在5%水平上顯著;第二階段中CU︿的回歸系數為-53263,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數據要素集聚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產能利用率,進而減少企業金融化程度,即實體獲利能力機制得證。綜上所述,研究假設H2得以驗證。
(二)數據要素集聚影響企業金融化的期限結構差異
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是一個復雜過程,涉及更深層次的市場結構調整和金融產品創新,因而對不同期限結構的金融資產會產生異質性差異。借鑒現有研究的做法,將交易性金融資產劃分為短期金融資產,其余劃分為長期金融資產,進而計算出短期金融化(Short_Financial)和長期金融化(Long_Financial)。基于此,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對不同期限類型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從中可以發現:在列(1)企業持有短期金融資產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在列(2)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180,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以上結果說明數據要素集聚主要抑制了企業持有更多的長期金融資產,而不是短期金融資產。
(三)異質性分析
第一,基于產權性質的異質性分析。由于民營企業通常資源有限,可能缺乏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來有效利用數據要素,同時可能面臨更嚴格的市場準入門檻和融資難度,其具有更強的金融化動機。對此,本文將樣本分為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分組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結果顯示:在民營企業(SOE=0)中,Treat*Post的系數為-00224,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在國有企業(SOE=1)中,Treat*Post的系數為-00158,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由組間系數差異檢驗(Chow"Test)可知,數據要素集聚在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民營企業金融化動機的抑制作用更大。
第二,基于金融錯配程度的異質性分析。低金融錯配程度的企業通常擁有穩定和有效的金融資源配置機制,其進行金融資產配置動機和便利性更高,然而數據要素集聚可能引入額外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沖擊其已有的資源配置效率。相反地,高金融錯配程度的企業獲得金融資源的能力較差。基于此,本文借鑒邵挺(2010)[21]的研究,以企業的資金使用成本對所在行業平均資金使用成本的偏離程度來構建企業金融錯配程度的指標,并根據其年度中位數設置分組變量Mismatch,當其在樣本年中位數以上時取1,反之取0,分組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列(3)和列(4)所示。從中可以發現:在低金融錯配程度(Mismatch=0)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289,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在高金融錯配程度較(Mismatch=1)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086,僅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根據組間系數差異檢驗(Chow"Test),數據要素集聚在低金融錯配程度組和高金融錯配程度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低金融錯配程度企業的金融化動機的抑制作用更大。
第三,基于企業償債能力的異質性分析。一般而言,高償債能力的企業具有更強的財務穩定性和較低的財務風險,其可能將金融資產作為資金儲備以應對未來投資機會或風險。相比之下,低償債能力的企業可能更傾向于保守的財務管理策略,而不是追求通過金融化活動帶來的潛在收益。基于此,本文以企業流動比率的年中位數設置分組變量Flow,當其在樣本年中位數以上時取1,反之取0。進而將樣本分為低償債能力企業和高償債能力企業,分組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列(5)和列(6)所示。結果顯示:在低償債能力(Flow=0)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不具有顯著性;而在高償債能力(Flow=1)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331,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由組間系數差異檢驗(Chow"Test)可知,數據要素集聚在低償債能力組和高償債能力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高償債能力企業的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大。
第四,基于地區金融科技水平的異質性分析。金融科技的發展能夠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可達性,同時更有效地識別和管理金融投資中的風險,使得企業更容易獲得金融資源,進而可能導致企業增加對金融資產的持有和金融投資的活動。而低金融科技水平地區的企業缺乏足夠的金融科技創新和應用,導致企業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接觸有限,因而該地區企業的金融化投資動機較弱。基于此,本文借鑒李春濤等(2020)[22]的研究,以“金融科技”等48個關鍵詞百度新聞高級檢索具體指標計算和數據處理過程請參見李春濤等(2020)。,來構建地級市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并根據其年中位數設置分組變量Fintech,當其在樣本年中位數以上時取1,反之取0,分組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結果顯示:在低金融科技水平地區(Fintech=0)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在高金融科技水平地區(Fintech=1)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289,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由組間系數差異檢驗(Chow"Test)可知,數據要素集聚在低金融科技水平地區組和高金融科技水平地區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高金融科技水平地區的企業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大。
第五,基于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分析。由于法律、監管和市場基礎設施更加完善,降低了地區制度環境較好的企業的金融交易不確定性和風險,從而激發企業進行金融投資和資本運作。相比之下,制度環境較差的企業面臨更高的交易成本和風險,使其金融化動機較弱。基于此,本文以樊綱市場化指數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得分的年度中位數設置分組變量Law,當得分在樣本年中位數以上時取1,反之取0,分組檢驗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7列(3)和列(4)所示。結果顯示:在法律環境相對較差(Law=0)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在法律環境相對較好(Law=1)的樣本中,Treat*Post的回歸系數為-00300,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由組間系數差異檢驗(Chow"Test)可知,數據要素集聚在制度環境相對較差組和制度環境相對較好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地區法律環境相對較好的企業的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大。
(四)數據要素集聚下脫虛向實的經濟效應
數據要素集聚通過抑制企業金融化是否產生了經濟后果,對實體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發揮了積極作用?基于此,本文借鑒胡珺等(2023)[23]的研究,分別采用OP法、LP法以及OLS法來測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構建如下模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經濟效應進行檢驗:
TFPi,t+1=γ0+γ1Treat*Posti,t+γ2Controlsi,t+∑Year+∑Firm+εi,t(4)
其中,TFP為全要素生產率,包括TFP_OP、TFP_LP以及TFP_OLS等三個指標,其余變量與模型(1)一致。同樣考慮時滯效應,本文研究的是數據要素集聚對t+1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Treat*Post的系數γ1表示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如果數據要素集聚產生了經濟效應,促進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系數γ1顯著為正。由表8列(1)—列(3)的結果顯示:Treat*Post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均至少在10%以內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數據要素集聚能夠促進企業的生產效率轉化,表現為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可能的原因在于數據要素集聚通過緩解企業信貸融資約束,促進智能化轉型,同時更有效地處理產能過剩的問題,使企業能夠更有效地利用和管理各類資源,從而在不增加傳統生產要素投入的前提下實現產出的增長和生產效率的提升。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隨著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建立,數據要素開始在試點地區集聚,這不僅促進了數據資源的有效利用,也使得在數據要素驅動下如何治理企業金融化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為了深入理解這一現象,本文以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為研究對象,探討了數據要素集聚對企業金融化程度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現,數據要素的集聚顯著降低了實體企業的金融化水平,尤其是減少了長期金融資產的持有,這一結論在經過多重嚴格檢驗后依然穩健。作用機制檢驗發現,數據要素集聚既可以降低融資約束程度以抑制預防性動機,也可以推動智能化轉型、提升產能利用率來增強企業實體獲利能力,以抑制企業短期投機逐利動機,進而抑制企業金融資產配置。此外,異質性檢驗表明,數據要素集聚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存在差異,特別是在民營企業、低金融錯配、高償債能力、地區金融科技水平較高以及法律環境較好的企業中,其抑制作用更為顯著。最后,本文還發現數據要素集聚還能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以上結論,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啟示:第一,加強數據要素集聚區的建設與管理。政策制定者應重視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建設和發展,通過提供政策支持和財政激勵,促進數據要素的集聚和流通。同時,加強對數據要素集聚區的管理,確保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為企業提供一個穩定可靠的數據環境。第二,促進企業智能化轉型和技術創新,改善信貸融資環境。鑒于數據要素集聚能夠通過智能化轉型和技術創新增強企業實體獲利能力,政府可以推出相關政策,鼓勵企業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進行數字化升級。此外,提供研發資助、稅收減免等激勵措施,支持企業在智能化和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數據要素集聚有助于緩解企業的信貸融資約束。因此,政府和金融機構應共同努力,改善信貸融資環境,為企業提供更加寬松和多樣化的融資渠道。例如,可以通過建立風險補償機制、提供信貸擔保服務以及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來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風險。第三,差異化支持不同類型企業的健康發展,抑制不利的金融化動機。比如,對民營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支持政策,提供更多的數據資源訪問權限、降低數據使用成本,以及提供定制化的金融和技術咨詢。而對于具有較強償債能力的企業,可以提供更為靈活的信貸政策和更優惠的利率條件,鼓勵這些企業進行長期投資。
參考文獻:
[1]"彭俞超,黃志剛.經濟“脫實向虛”的成因與治理:理解十九大金融體制改革[J].世界經濟,2018,41(9):3-25.
[2]"Müller,"O.,"Fay,"M.,Vom"Brocke,"J."The"Effect"of"Big"Data"and"Analytics"on"Firm"Performance:"An"Econometric"Analysis"Considering"Industry"Characteristics[J]."Journal"of"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nbsp;2018,35(2):"488-509.
[3]"謝康,夏正豪,肖靜華.大數據成為現實生產要素的企業實現機制:產品創新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20(5):42-60.
[4]"邱子迅,周亞虹.數字經濟發展與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基于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分析[J].財經研究,2021,47(7):4-17.
[5]"劉傳明,陳梁,魏曉敏.數據要素集聚對科技創新的影響研究——基于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準自然實驗[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3,25(5):107-121.
[6]"陳文,常琦.大數據賦能了企業綠色創新嗎——基于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準自然實驗[J].財經科學,2022(8):76-92.
[7]"潘紅波,楊海霞,徐雅璐.房產限購與企業創新投資——基于信貸資源重配視角的研究[J].珞珈管理評論,2022(2)":48-66.
[8]"Opler,"T.,"Pinkowitz,"L.,"Stulz,"R.,et"al."The"Determinants"and"Implications"of"Corporate"Cash"Holding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9,52(1):"3-46.
[9]"苑澤明,于翔,李萌.數據資產信息披露、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價值[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2,42(11):32-47.
[10]姚加權,張錕澎,郭李鵬,等.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基于勞動力技能結構調整的視角[J].管理世界,2024,40(2):101-116+133+117-122.
[11]林晨,陳小亮,陳偉澤,等.人工智能、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改善:資本結構優化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20(2):61-83.
[12]劉征馳,陳文武,魏思超.數據要素利用、智能技術進步與內生增長[J].管理評論,2023,35(10):10-21.
[13]唐曉華,景文治,張英慧.人工智能賦能下關鍵技術突破、產業鏈技術共生與經濟“脫虛向實”[J].當代經濟科學,2021,43(5):44-58.
[14]王永進,匡霞,邵文波.信息化、企業柔性與產能利用率[J].世界經濟,2017,40(1):67-90.
[15]Feng,"Q.,"Hu,"X.,"Deng,"X.,et"al."Anti-corruption"Campaign"and"Capacity"Utilization"of"State-owned"Enterprises:"Evidence"from"China’s"Central"Committee"Inspection[J]."Economic"Analysis"and"Policy,"2023,80:"319-346.
[16]Demir"F."Financial"Liberalization,"Private"Investment"and"Portfolio"Choice:"Financialization"of"Real"Sectors"in"Emerging"Markets[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9,88(2):"314-324.
[17]司登奎,李小林,孔東民,等.利率市場化能降低企業營運風險嗎?——基于融資約束和企業金融化的雙重視角[J].金融研究,2023(1):113-130.
[18]劉沖,曾琪,劉莉亞.金融強監管、存貸長期化與企業短債長用[J].經濟研究,2023,58(10):75-92.
[19]Hadlock,"C."J.,Pierce,"J."R."New"Evidence"on"Measuring"Financial"Constraints:"Moving"beyond"the"KZ"Index."Th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2010,23(5):"1909-1940.
[20]李雪松,趙宸宇,聶菁.對外投資與企業異質性產能利用率[J].世界經濟,2017,40(5):73-97.
[21]邵挺.金融錯配、所有制結構與資本回報率:來自1999—2007年我國工業企業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0(9):51-68.
[22]李春濤,閆續文,宋敏,等.金融科技與企業創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20(1):81-98.
[23]胡珺,方祺,龍文濱.碳排放規制、企業減排激勵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自然實驗[J].經濟研究,2023,58(4):77-94.
Data"Elements"Agglomeration"and"Real"Economic"Structure"Optimiz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Returning"to"the"Real”
WEN"Jie1,"ZAHNG"Zhenkun2,"WU"Dinwen3
(1."School"of"Finance,"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
2."School"of"Management,"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3."Institute"for"Financial"and"Accounting"Studies,"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0,China)
Abstract:Gather"data"elements"as"the"core"of"the"real"economy"development"is"the"key"to"promote"the"real"economy"structure"optimization.Based"on"the"establishment"of"national"big"data"comprehensive"pilot"zone,"this"paper"discusses"the"impact"of"data"factor"agglomeration"on"the"degree"of"enterprise"financialization"and"its"internal"mechanism.The"results"show"that"data"factor"agglomeration"significantly"reduces"the"financialization"degree"of"real"enterprises,"that"is,"it"promotes"the"structural"optimization"of"real"economy.Mechanism"identification"finds"that"data"factor"agglomeration"can"weaken"the"motivation"of"precautionary"reserve"and"enhance"the"profitability"of"entities,"thus"inhibiting"the"excessive"financialization"of"enterprises.The"heterogeneity"test"finds"that"the"inhibitory"effect"of"data"factor"agglomeration"on"corporate"financialization"is"more"obvious"in"the"samples"with"private"enterprises,"low"financial"mismatch,"high"solvency,"high"regional"fintech"level"and"better"legal"environment.Further,"data"element"agglomeration"can"improve"enterprise’s"total"factor"productivity.
Key"words:data"element"agglomeration;"enterprise"financialization;"precautionary"reserve"motive;"physical"profitability"
(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