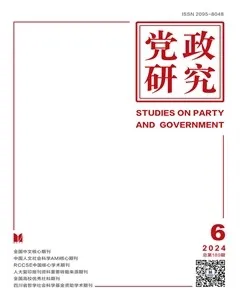生態扶貧的制度融合機制

〔摘要〕中國生態扶貧不僅解決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而且在反貧困治理中取得了重大的減貧成效。已有的研究聚焦于生態扶貧的內涵、類型、成效等方面,但對生態扶貧中的具體邏輯深入分析不足。通過個案研究發現,中國式生態扶貧突出特色在于國家整體政策與地方性的有效結合,其核心在于地方在國家扶貧強政策框架下將生態扶貧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形成了有效的扶貧治理方式。其中國家正式制度是生態扶貧實施的剛性約束和保障,并與傳統文化中自然敬畏和扶貧濟困意識主動融合,促進了生態文明理念的形成。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互動下的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形成的目標導向機制、合作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提高了我國生態扶貧治理效能。
〔關鍵詞〕生態扶貧;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融合機制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24)06-0102-11
一、問題的提出
貧困現象是阻礙人類文明前進的痼疾。工業化帶來了人口的增長和財富的累積,也使人們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和貧困問題。早期的發展理論將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對立起來思考貧困問題,并形成兩種不同的進路。一種是先發展,后治理的模式。此模式下通過資源的無限開采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最終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的惡化、資源的枯竭又進一步破壞農業生產、居住環境和基礎設施,使貧困問題進一步加劇,國家又不得不以百倍的經濟代價進行生態修復,如大規模國土綠化、濕地與河湖保護修復、防沙治沙、生態修復等工程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另一種是為了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放緩經濟發展的步伐。如羅馬俱樂部“零增長”認為經濟增長導致了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破壞,需要控制消費和生產的速度。一些學者批判零增長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充滿了道德感,對于貧困地區無疑是一種“何不食肉糜”的荒誕。傳統的發展模式未能平衡好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減少貧困之間的矛盾,能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一直是困擾著各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點。
1993年世界環境主題日呼吁關注“貧窮與環境——擺脫惡性循環”問題,指出環境惡化是第三世界貧困的根本原因。〔1〕在此會議的倡導下學者就貧窮與環境二者的關系展開了討論并形成以下結論:貧困與環境互為因果關系〔2〕〔3〕、貧困與環境正相關關系〔4〕、貧困與環境耦合關系〔5〕、貧困與環境辯證關系〔6〕。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曾經也經歷了先發展后治理的階段并付出一定的代價。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面對部分地區形成的生態貧困,從2001年起扶貧開發與可持續發展模式相結合,中國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減貧之路。2018年印發《生態扶貧工作方案》明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扶貧模式,即通過重大生態工程建設、加大生態補償力度、發展生態產業等舉措形成了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協調、脫貧致富與可持續發展相促進的發展路徑。經過近20年的發展,697a2b8d26d6267fb98dd0973fa94ad1中國式的生態扶貧累計帶動近2000萬人脫貧增收。〔7〕為什么生態扶貧能在中國取得成功,實現了既保護了生態環境,又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和解決貧困群眾增收的雙重目標。對此,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從生態扶貧的內涵、類型以及從政策制定、發展模式、效果評價等方面研究中國式生態扶貧成效在國家層面上的治理效能,較少注意地方層面上的具體執行政策機制。本文認為,自上而下的國家生態扶貧整體性政策固然是中國式生態扶貧的前提與關鍵,但是,政策的有效還有賴于地方層面以及基層的具體執行機制,因此,雙重目標的扶貧政策是如何實現的尚需從地方層面觀察其具體執行機制。本文通過西部Q縣的個案研究發現,地方在執行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國家正式制度與地方情境中的非正式制度進行有效互補融合所形成的上下聯動,是政策目標能夠有效執行的關鍵。
二、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
對反貧困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十八世紀末形成的理論認為人口增長和貧困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因此主張通過限制人口增長來解決貧困問題。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學者發現貧困問題一直與經濟的增長緊密聯系,故主張通過經濟增長增加個人和家庭收入,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成果向窮人惠及或擴散,并帶動其脫貧和致富。〔8〕〔9〕但一些研究表明,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能有效地減輕貧困問題,甚至可能導致貧富差距加大。Adelman等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更多出現在城市地區而未必是鄉村地區,說明一部分窮人并沒有從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受益。〔10〕 長期的實踐印證,在經濟比較繁榮、就業得以實現的時期貧困現象依然會存在。單靠資本投入和市場的力量的扶貧模式是無法打破貧困惡性循環的,必須通過外在力量,加大政府干預,建構反貧困制度體系。相關研究則明確認為發展中國家自身無法解決貧困,需要通過政策和制度系統的外部干預才能終結貧困。〔11〕 中國的貧困治理顯然是一種國家強力干預的模式,眾多學者認為中國扶貧的成功是制度性扶貧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貧困治理的制度基礎,〔12〕為脫貧攻堅提供合法性保障、組織保障、制度保障、資源保障,〔13〕國家制度要求的責任體系,有效解決了基層部門責任不明、動力不足的問題,〔14〕駐村制度作為一種嵌入模式有效銜接了國家與鄉村之間的聯系。〔15〕中國能消除絕對貧困主要在于中國特有的國家善治能力。〔16〕 這種自上而下的制度統籌機制被認為是中國式扶貧能夠成功的核心,即國家制度的引導作用、強制執行、資源聚集等形成的整體合力提高了治理效能。但是,制度不能自足。制度的有效還有賴于地方層面和基層的有效執行,地方與基層政府官員需要將國家制度嵌入到本地的情境之中。現有研究發現,地方非正式制度的靈活性應用是政策執行者實現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治理的有效途徑。〔17〕只有將國家正式制度與地方非正式制度實現有機融合,才能避免制度的空轉失焦,增強政策的接受度。
本文認為中國式生態扶貧的效能在于國家政策作為正式制度的合理性與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治理體系。正式制度在設計過程中會充分考慮制度內容本身的合理與外在要求。制度自上而下運作過程中微觀可操作性逐漸增強,宏觀指導性逐漸消退。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中會根據非正式制度形成地方化慣習模式,與正式制度融合成互補性的政策體系從而增強政策的接受度,形成相對完整的治理體系。
(一)正式制度:外部推動力
由于個體行為的善變無常,很可能會產生非意圖性后果,個人行為需要正式制度的引導和約束,去除個體的任意性和個人主義因素。組織的存在和延續離不開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明確了組織內各層級的權力和職責,從而避免組織跨界引起的權力濫用和職責混亂,確保組織內部的運作高效和協調。正式制度不僅形成嚴格的規訓和制約,而且通過賦權為行動者或組織提供資源支持和合法性基礎。諾斯將正式制度定義為“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一些政策法則,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這些規則從憲法到成文法與普通法,再到明確的細則,最終到單個的合約”〔18〕。正式制度在設計上一般會界定明確的責任、可為或不可為的規則以及懲罰的規則;在形式上通過正式、規范、具體的文本來確定;在實施中借助于外在的強制約束力推動政策目標的實現。正式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式制度確立在權威基礎之上,通過外部作用引導、控制和規范各種行為,并保證組織內部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在生態扶貧中正式制度通過制定政策框架指明了扶貧目標、責任分工、資源投入等,為生態扶貧提供了方向和操作規范。此外也實現了多部門、多層級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避免生態扶貧工作中的重復和資源浪費,推動生態扶貧的有效進行。
(二)非正式制度:內部驅動力
非正式制度是制度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植于地方文化和社會規范土壤中,先于正式制度自發形成的一種行為準則,包括道德、慣例、習俗等。諾斯指出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擴展、闡明和修改;是社會所認可的行為準則;是內部實施的行為標準。〔19〕中國有著濃厚的鄉土傳統,以“家”為本位的倫理觀遍及鄉村鄰里形成了“熟人社會”,行為互動邏輯與人情、面子息息相關。“在中國情理社會下人們會選擇放棄理性和制度來獲得更多社會資源和日常權威。”〔20〕中國農業社會在互動中形成了非正式制度約束的救助體系,幫助農戶的生存和延續。〔21〕有學者則發現非正式制度既影響農村社會資本提供公共品,也會影響政府在農村公共支出提供公共品的效率。〔22〕非正式制度雖然不具有正式制度的強制力,但是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著作用:一是緩沖壓力體制和現實的不確定性之間的張力,確保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有效性和靈活性;二是在正式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的情況下對其進行補充,履行正式制度的部分功能;三是憑借小團體中的互惠關系克服動員難題,為集體行動的發起提供組織基礎。〔23〕非正式制度作為一種柔性管理,不依賴于國家的外部強制力,而在于地方群眾對慣例的認同和心理的歸屬。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可被看作是一種自律方式,主要依靠人們內心的自省和自覺規制著個體的行為,個體懾于非正式制度形成的社會壓力而不得不遵守規約。生態扶貧在地方性具體情境執行中,需要結合地方的文化、社會、環境提高制度的適應性。
(三)融合機制:實現治理效能
“機制”源于工程學、物理學和生物學,后來擴展到多個學科,泛指系統內子系統或者要素之間互動及運作方式。Leonid·Hurwicz提出機制設計理論,揭示了分散資源配置下的信息交流與激勵、理性之間的關聯。〔24〕Eric·Maskin運用機制設計理論研究如何通過設計合適的機制或規則來引導復雜的社會交互和資源分配,實現特定的經濟或社會目標。〔25〕Hurwicz指出一個有效的機制或制度必須滿足三個條件:機制實現的配置結果是合意的,有效利用信息,激勵相容。機制實現的配置結果是合意的,是指配置結果與機制設計者的目標是一致的;有效利用信息,是機制實現相同配置結果所需的信息成本最小;激勵相容是指系統中個體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行動策略,與制度設計者期望目標相一致,從而減少制度執行的阻力促使參與者自愿按照制度設計者的規則采取行動。〔26〕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可以構成四種關系模式:競爭、替代、適應、互補。〔27〕中國生態扶貧制度性模式之所以有效,即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執行過程中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適應和互補,形成了政策執行的融合機制(目標導向機制、合作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從而實現既保護生態,又發展經濟、減少貧困的雙重目標,實現生態扶貧可持續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得以重視是因為它能夠對一個特定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膩的描述,是對實踐經驗的概括。羅伯特·K·殷指出案例研究的優勢在于能回答“怎么樣”和“為什么”類型的問題,他把案例研究劃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即單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單案例研究適用于如下情況:用于對現有的理論進行批駁和檢驗;異常的、獨特的現象;有代表性的或典型性的事件;啟示性事件;對同一案例進行縱向比較。〔28〕本文采用單案例研究方法,以制度理論為基礎,一方面了解生態扶貧中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設計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分析生態扶貧在資源受限的地區獲得成功的實施機制。資料來源于實地調研的訪談記錄、檔案資料、正式報道,通過資料互證確保信息準確性。
①數據來源于實地調研,下文中未注明的數據均來源于實地調研。
(二)案例選擇
本文選擇Q縣為生態扶貧的研究對象,其適用性在于以下方面。首先,Q縣坐落于中國西部青海省境內,面積1.4萬平方千米,境內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地處高寒山區,年均氣溫不足1℃,①惡劣的氣候條件嚴重制約當地農業發展。其次,Q縣內水源匯集,擁有多種珍稀野生動植物,被稱為高寒生物物種的“基因庫”,生態功能及生態價值十分重要。最后,縣域內有豐富的礦產資源40余種,是聞名遐邇的資源富集之地,但是生態環境保護的強制約束限制了資源開發。可見Q縣既有生態脆弱區的生態貧困,也有生態富集區的生態貧困。2002年青海省扶貧辦將Q縣農區的20個行政村列入參與式扶貧開發村,其中5個絕對貧困村,15個低收入貧困村。2010年Q縣被劃入四省涉藏地區連片特困區,提出片區扶貧攻堅戰略,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減貧目標的同時提升片區發展能力。2015年通過“兩線合一”Q縣確定18個貧困村,識別貧困人口4756人,貧困發生率為9.4%。2019年5月Q縣退出貧困縣序列,2020年建檔立卡貧困群眾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132.6元。
四、案例分析:資源開發限制地區何以實現生態扶貧
(一)正式制度:生態扶貧的剛性約束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反貧困就是重大任務之一,出臺的一系列條例、規劃、措施等形成了貧困治理制度體系。扶貧開發模式也從救濟式扶貧轉到開發式扶貧再轉向精準扶貧,2020年解決了千年以來的絕對貧困問題,其中生態扶貧發揮了重要減貧成效,其相關制度設計主要體現以下三方面。
1.從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并重到生態優先
環境保護與扶貧開發并重是生態扶貧的前提。中國的生態扶貧最早可以追溯至1983年“三西”農業建設計劃,不僅實現了“三西”地區農村從“救濟”向“溫飽”的歷史性轉變,也改善了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以三西建設為樣本通過政策擴散生態扶貧在全國得以實施。21世紀以來中央先后制定了兩個為期十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強調扶貧開發必須與資源保護、生態建設結合起來。十八大后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進一步提高,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中更突出生態保護優先。同時,綠色發展和產業轉型要求在地方得以實踐,提高了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脫貧攻堅中,各類專項資金向貧困地區傾斜,出臺“八個一批”“十個行業專項扶貧”等制度。諸如通過生態修復工程、設立生態公益崗為貧困人口提供就業崗位;通過易地搬遷,將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的群眾搬遷出來,從根本上解決生存發展問題;通過特色產業推進種養結合,發展循環經濟解決貧困人口生計問題等等。一系列配套制度不僅提高了貧困人口參與環境保護謀求發展的積極性,也使貧困人口從生態保護與修復中得到更多實惠。
2.生態補償制度體系構建
生態補償制度根據地區生態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等因素,明確了生態價值受益主體付費制度,實現了生態價值有償使用。1990年中央政府提出“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利用誰補償”和“開發利用與保護增值并重”的生態環境保護方針。2005年為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提出“要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盡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要求。此后每五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以及若干中共中央文件、國務院條例、政府工作報告對生態補償做出了一系列決策部署。2016年中央制定的《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繪制了生態補償橫向與縱向、分類與綜合的多元補償格局。目前已形成了森林、流域、草原、濕地、耕地、海洋等重要領域的生態補償制度體系。地方政府結合中央政府的要求陸續出臺了落實生態補償制度的具體實施方案,進一步完善了生態補償制度框架。如2011年開始青海省實施了周期為5年的草原補獎政策,對草原牧區推行草畜平衡制度和禁牧封育制度,根據草原類型、面積、草原生產力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制定適宜的補助獎勵機制,實現禁牧不禁養,減畜不減收。
3.生態責任追究的威懾力
2005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和賠償制度,遵循“誰污染誰付費、誰破壞誰賠償”的原則,對于生態破壞行為,以及未能履行生態保護義務的單位和個人,依法追究其生態責任的制度,以強制手段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為了進一步強化領導干部認真落實生態責任,2015年形成了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制度,進而壓實了政府的生態保護職責。2017年提出對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要求,并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進行終身追責。2017年印發了《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將生態空間范圍內具有特殊重要生態功能的區域加以強制性保護,“生態紅線”既是一種警示也是環境保護的底線,體現了生態保護的強制性和不可逾越性。
(二)非正式制度:生態扶貧的柔性約束
非正式制度中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倫理道德和習慣習俗等構建了整個社會的認同體系。制度設計首要目標是關心規則與文化環境的適應性。〔29〕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愛”“民本”“大同”等思想孕育了中國扶貧濟困、守望相助的慈善理念。生態扶貧是中國傳統環境保護理念與扶貧濟困理念的進一步融合。Q縣當地居民之所以能夠放棄資源開發的收益權,與當地傳統文化關系密切。神山崇拜是Q縣民間信仰,當地著名的兩座神山——牛心山、卓爾山成為當地民眾心中的神圣之地,神山崇拜的生態敬畏契合了“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自覺。當地長期的農牧文化孕育了樸素的生態倫理觀,當地游牧民族將草場稱為“窩子”,根據季節牲畜在不同窩子輪流放牧,形成草場循環利用的生存策略,展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情懷,對當地環境保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Q縣各村將生態環境保護納入《村規民約》,實行“村民道德紅黑榜”,紅黑榜涵蓋了環境保護、衛生整治、精準扶貧、移風易俗等方面,儼然成為當地的“監督崗”“曝光臺”,不僅增強鄉村自主管理,也提高了村民脫貧決心和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
(三)融合機制:生態扶貧的雙贏雙促
1.目標導向機制:精細管理,精準實施
制度是一整套嚴格、明確、有序的規章條例、規劃、措施等,為組織和個人的行為提供了依據,減少了不確定性。目標導向不僅有助于提高工作透明度和評估標準的清晰度,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執行力。生態扶貧制度的目標導向機制主要表現在定標準,定時間、定規模三個方面。通過“三定”設定可衡量的目標,便于評估生態扶貧的實際效果。
一是定標準。
在扶貧方面制定明確貧困線標準以識別貧困人口。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制定了絕對貧困線標準和低收入線標準,對貧困群眾予以補助,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歷年進行調整,2008年將絕對貧困線標準與低收入貧困線標準合二為一。Q縣脫貧標準規定: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316元以上;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532元以上;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762元以上,根據此標準精準識別貧困戶。另外對建檔立卡戶中公益崗位工資收入也做了明確標準規定:林業管護員工資每人每月1600元,草原管護員工資每人每月1200元,安置點配置衛生保潔1人,每月工資500元。在環境保護方面實施森林、草原、濕地等補償,例如2015年禁牧補助10元/畝,牧草良種補貼標準為多年生人工種草50元/畝,一年生人工種草10元/畝。所有政策性收入通過“一卡通”直接兌付給農牧民,讓農牧民在參與生態保護中直接性獲得應有的補償。
二是定時間。
根據目標設置合理的時間期限有助于督促行動和完成任務。1994年八七扶貧攻堅決定用7年左右時間基本解決八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2016年脫貧攻堅規劃決定利用5年時間使建檔立卡貧困村有序摘帽,最終實現貧困縣全部摘帽。Q縣脫貧攻堅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3年的努力消除絕對貧困,實現整體脫貧。其中2016年計劃脫貧5個村,2017年計劃脫貧7個村,2018年計劃脫貧6個村。第二階段鞏固脫貧成果。2019年脫貧摘帽后,繼續對初步脫貧的貧困村、貧困戶給予5年扶持,保持現有幫扶政策、資金支持、幫扶力量總體穩定。并制定后續幫扶計劃,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進行動態監測。
三是定規模。
確定規模、明確制度所適用的范圍、目標群體有利于制度有效執行。Q縣確定禁牧面積511.36萬畝,草畜平衡面積1225萬畝,落實草原生態保護補獎制度。按照5萬畝配置1名生態管護員的標準,從牧民中聘用310名草原生態管護員。為了確保按時脫貧,Q縣明確了脫貧規模,2016年計劃465戶1352名貧困人口脫貧;2017年計劃588戶1817名貧困人口脫貧;2018年計劃534戶1587名貧困人口脫貧。此外根據國土空間開發格局,采取差異化產業規模發展。如在農業區穩定青稞、油菜播種面積,適度發展林下經濟,開展大黃、黃菊等特色種植;農牧交錯地帶發展循環農牧業,進行藏雪雞、梅花鹿、林麝等特色養殖,構建半農半牧區舍飼飼養畜禽為主的產業區;畜牧業區,以天然的草場為依托,發展有機畜牧業,建立高原型藏羊、牦牛保種試驗示范核心片區。
2.合作機制:互聯互動,共建共享
一是部門合作,資源整合。
以往的扶貧開發是以村莊為單位進行“輸血式”貧困治理,扶貧資源分散在多個部門,部門之間缺乏合作,無法實現資源的統籌配置,縣鄉作為行政體系的末端和鄉村治理的主體缺乏對資源的控制權。為了破解以往扶貧中的碎片化管理,在脫貧攻堅戰中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賦予貧困縣資金整合的自主權,資金項目審批權,形成自下而上資金統籌整合機制,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益。例如,Q縣統籌整合各個鄉鎮中的涉農、扶貧、援建等資金發展混合經營集體經濟,通過購置賓館、租賃商鋪幫助貧困戶獲得資產收益;借助國家公園生態修復治理、退牧還草、土地沙化治理等項目資金發展牧草加工業,幫助貧困戶獲得產業增收;興建畜產品加工基地、物流園區形成采購、生產、加工、銷售融合的產業鏈,降低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幫助貧困戶獲得企業入股分紅;建立牧民專業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草場托管、牲畜托養帶動幫助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增收。地方政府通過部門合作,整合了資金和項目,形成地方特色的生態扶貧方案,提升項目的綜合效益。
二是對口支援,結對認親。
20世紀90年代國家決定采取東西扶貧協作模式,形成了“政府援助、企業合作、社會幫扶、人才支持”的東部反哺西部的制度安排。幫扶聯點單位的對口支援以政治動員形式撬動了東部的優勢資源定向配置以幫助西部脫貧,而且對口支援工作逐步細化到縣、鄉、村,同時確定了剛性目標進行考核,對口支援成為反貧困治理的一個重要的舉措。2010年中央確定山東省對口援建Q縣,援建部門與Q縣的各鄉鎮簽署了“一對一”的幫扶協作協議,在產業、生態、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方面進行幫扶援建。例如投資260萬援建綜合指揮調度中心,為生態環境監測監管、自然災害應急預警等提供技術支持。與畜牧業協會簽署“千牛萬羊”協議推動牛羊肉收購。為了落實精準扶貧,密切黨群、干群關系,Q縣黨組織中干部與轄區內的貧困群眾開展結對認親,要求干部主動為貧困群眾出謀劃策,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致富能手與困難群眾結對,通過教方法、傳經驗帶領鄰里共同發展。通過對口支援,Q縣獲得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支持。結對認親建立的信任關系,激發貧困群眾自我發展的動力。
三是優勢互補,補足短板。
牧業和農業的發展并非獨立隔絕的狀態,它們相互關聯和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存的產業。為促進農牧業的可持續發展,Q縣通過政策推動、項目扶持引導鄉鎮建立生態畜牧業專業合作社、家庭牧場、舍飼養殖基地,采取補飼、圈養、租轉、增草等措施,對草原上超載畜實行“進棚”養殖,實現超載牲畜轉移。Q縣就區域優勢而言有高原牦牛、藏羊種源示范基地,能繁殖優良畜種,但是草場資源不足限制了畜牧業發展。河西走廊有萬畝耕地、草產業發展成熟,養殖成本低、育肥周期短等優勢。Q縣政府協調當地銀行設立“飛地畜牧貸”緩解協會資金不足問題,搭建平臺幫助生態畜牧業專業合作社通過租賃、承包、聯營等方式與張掖、山丹、民樂等周邊地區形成“祁繁甘育”合作模式,實現了“農牧互補、借地增草”的發展格局。另外建立合作社、家庭牧場、托養牲畜等規模化養殖,不僅提高了牲畜的出欄率和供應量,也增強單個牧戶抵抗風險的能力。
3.激勵機制:激發動力,糾正偏差
正激勵是指一種獎勵性的刺激,用于增加個體某種行為的發生頻率或強度,既可以是物質獎勵,如錢、食物等,也可以是非物質獎勵,如贊揚、表揚等。負激勵是指一種懲罰性的刺激,用以減少某種行為的發生頻率或強度,可以是物質懲罰,如罰款、扣除工資等,也可以是非物質懲罰,如批評、降職等。
一是正激勵:及時獎勵,鼓勵參與。
2016年設立了全國脫貧攻堅獎,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對表現突出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進行表彰,加強脫貧攻堅中的榜樣力量。自2016年以來累計表彰128個先進集體和377名先進個人。〔30〕2019年Q縣上榜中國扶貧效率“百高貧困縣”,被評為“中國最美縣域”,2021年中共Q縣委被中共中央、國務院評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這些榮譽激發基層干部積極作為的實干精神。此外為了鼓勵企業和公眾參與農事體驗、牧游經濟、休閑文化等特色旅游產業,出臺了《Q縣旅游行業獎勵資金實施辦法》對新評定五星級、四星級、三星級的賓館分別獎勵10萬元、5萬元、2萬元,對新評定五星級、四星級、三星級鄉村旅游接待點分別獎勵5萬元、1萬元、0.3萬元。另外設置了“勵志愛心超市”積分制,鼓勵周邊牧戶對草場垃圾、河道垃圾等進行清理獲得愛心積分,并用積分可以換取日常生活用品。通過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提高了地方多方參與生態扶貧的力量。
二是負激勵:績效管理,責任追究。
生態環境保護和脫貧攻堅的績效考核已成為領導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之一,生態責任也實行終身追責制。這些制度有效防止了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盲目決策。2018年青海省取消了重點生態功能區GDP、工業增加值等項目考核,加大發展循環經濟、產業扶貧、生態工程治理、文化產業等方面的考核權重。青海省作為生態大省實行重大生態問題“一票否決”制,加強地方生態責任的落實。在脫貧攻堅戰中實行省級干部聯點到縣,領導干部下鄉調研,五級書記抓扶貧,貧困縣黨政正職不脫貧不調整、不摘帽不調離。壓力傳導下對第一書記和扶貧工作隊的工作職責提出了明確要求,考核細化為5個一級指標、21個二級指標、67項具體考核標準。另外在考核基礎上,制定了“召回”制度,官員任職期間表現優秀的,同等條件下優先提拔,而實際工作中出現思想不重視、能力不適應、工作不積極等“十不”情形,鄉鎮黨委和扶貧辦向縣委組織部提議申請,經調查屬實后,立即責令召回撤換。召回制度增強了基層干部對職責的認知和擔當,減少了不作為、失職等現象,有效地約束了個人行為,減少了政策執行偏差。
4.監督機制:做實做細,全程穿透
監督機制能倒逼干部履職盡責。中國的治理體系中監督機制涉及思想、道德、作風、法紀和政治生態的綜合性工作,〔31〕體現自律與他律,剛性與柔性的統一。2018年《生態扶貧工作方案》建立生態扶貧工作動態管理和監督制度,對重點工作實行臺賬管理,以監督促落實。
一是日常監督:防微杜漸,正確履職。
日常監督在扶貧領域和環境保護領域形成常態化工作模式,以防止“小病”變“重疾”。Q縣出臺了《Q縣干部監督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定期聯合相關部門召開監督聯席會議,對重點項目、重點領域進行監督。為了破解基層落實監督責任難題,實施村級紀檢委員交叉互派,隨機調配鄉鎮紀委書記的方式減少人為干擾,解決“難過人情關、熟人監督難”問題。此外成立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修復試點項目工作領導小組、河長制工作領導小組及生態績效考評考核組,形成層層抓落實的縣-鄉-村三級組織機構和監督機制。為方便群眾參與監督,形成“電、信、訪、網、微”監督舉報系統平臺,同時要求工作人員對于受理范圍外的事項要及時告知舉報渠道。為了鼓勵公眾參與生態環境監督,以鄉鎮黨委牽頭、群眾自愿的原則組建“馬背生態巡護隊”“摩托車生態巡護隊”,開展環境巡查和環境整治。常態化監督使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跟進,便于迅速采取措施予以糾正,確保責任落實不打折扣。
二是專項監督:掛牌督辦,責任壓實。
專項監督是對專項治理的監督,提高監管的針對性和實效性。Q縣對重大領域項目實行項目、責任、資金專項監督。如在扶貧工作中與州扶貧開發工作領導小組聯合成立“專項監督檢查組”,對項目實施進行檢查,列出問題清單,掛牌督辦,實行銷號臺賬,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過,問題不查清不放過,群眾不滿意不放過,問題不銷號不放過”。村兩委、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分別與貧困群眾簽訂脫貧責任書,縣脫貧攻堅辦與縣委督查室對脫貧工作進行專項督查。在生態保護方面在礦山整治、礦坑治理中實行片長、坑長責任制,加強全過程自然生態監管。在專項經費監督中實行“三公開”——“手機村(居)務通”公開、“三級”微信群公開、村(居)務公開欄公開,縣委組織部牽頭聯合民政、財政、審計等部門,定期對各鄉鎮專項經費使用情況進行專項檢查,同時將專項經費使用情況納入年度黨建目標考核。專項監督對整改不力、敷衍了事的行為進行嚴肅處理,以此增強整改的威懾力和約束力。
五、結論
中國生態扶貧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政府是生態扶貧的主體。生態環境和貧困治理的公共屬性,指明了政府是不可或缺的責任主體。在政府總體動員下,消除貧困和環境保護的行動依據自上而下、正式化的方式得以實現,通過政策、資金、技術等多方面支持,推動生態扶貧項目的實施。其次,生態優先是生態扶貧的價值取向。“美麗中國”的蘊意不僅包括共同富裕,也包括生態宜居的優美環境。生態優先在生態理性和經濟理性張力下,以生態保護為第一要義,改變了過去唯GDP論,摒棄了“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通過綠色發展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雙贏。最后,生態扶貧也呈現不足,表現為貧困主體缺乏內生性的動力。生態扶貧過多依賴于政府對資源的定向配置和輸入。尤其是精確扶貧政策在個體層面上所實施的多層次、多角度的扶持措施,強化了個體對政策的依賴心理,進而導致貧困主體主動性的缺乏。政府的扶貧舉措作為一種非市場化的干預,雖然在短期內為貧困戶和地方產業提供了必要的資源支持,但難以形成持久的長效機制。為保障生態扶貧的成果,亟需引入市場機制以增強綠色產業的競爭力,同時,個人也應通過培訓和教育不斷提升自我發展能力,增強技能,進而提高其職業競爭力。
中國生態扶貧治理之所以能夠實現扶貧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雙重目標有兩個機制。一是國家制度層面對地方扶貧政策目標、社會目標、經濟發展目標一致性的硬要求,同時為實現這一要求,中央政府進行了配套政策,如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及通過一些靈活的政策措施支持鄉村產業、生態、文化等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和可持續發展。二是地方層面面對國家扶貧政策的多目標硬性要求,將中央的強要求、配套措施和地方社會、文化等資源有機組合起來,形成自上而下責任逐級壓實的生態扶貧政策執行模式,這一模式包括幾個具體的機制——目標導向機制、合作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目標導向機制是借用中央要求和壓力體制清晰化目標,從而保證了不同層面的行動者圍繞目標一致行動,減少沖突。即通過定標準,明確政策實施的具體目標和要求,減少目標模糊性,使目標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監督性;通過定時間,制定階段性工作計劃目標,使任務按期完成,使目標具有可約束性;通過定規模,明確目標資源的投入與使用標準,確保資源的合理分配,避免浪費和重復建設,使目標具有合理性和可追溯性。合作機制是根據目標,建立國家-社會-市場三方合作機制,地方政府有意識地通過優惠政策、財政支持等方式,一方面集中優勢資源治理生態貧困,另一方面引導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生態扶貧,形成互聯互動、共建共享的格局,同時有利于政策因地制宜地加以微調,從而更有效地實現政策的多目標。激勵機制則意在激發組織成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建立有效的約束性措施規范其個人行為,減少政策執行過程的偏差性。監督機制是在生態扶貧實施過程中的全程監督,即形成穿透力,使監督規范化、日常化,而專項監督則通過整改、整治倒逼主體責任規范切實地實現政策目標。
需要說明的是,生態扶貧的治理體系中形成的這四種具體機制只是基于案例的歸納與抽象,并非實操的具體過程,但我們認為,不同地方具有相似的內在邏輯。即首先是國家制度的多目標要求及其相應的配套措施,然后是地方在強制度約束和支持性政策下,基于地方社會情境,發展出具體的執行機制。這些機制并非獨立行動而是相互密切,在不同地方反映了形式可能不同,但邏輯相似,即依據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建立清晰化目標、階段性要求、從而使目標具有可操作性、可觀察性,行為具有可約束性、可追溯性,并通過激勵與監督機制等最大化調動資源,合理化運用資源,從而實現生態扶貧的多目標。
〔參考文獻〕
〔1〕 王婭.貧窮與環境——擺脫惡性循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3,(2).
〔2〕 楊文舉.西部農村脫貧新思路——生態扶貧〔J〕.重慶社會科學,2002,(2).
〔3〕 甘庭宇.精準扶貧戰略下的生態扶貧研究——以川西高原地區為例〔J〕.農村經濟,2018,(5).
〔4〕 喬宇.生態貧困視域下民族生態脆弱地區減貧研究——以武陵山片區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15,(2).
〔5〕 郎秀云.中國生態扶貧的理論創新、精準方略與實踐經驗〔J〕.江淮論壇,2021,(4).
〔6〕 楊發庭,張亦瑄.生態扶貧的內在邏輯及實現路徑〔J〕.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1).
〔7〕 李慧.生態扶貧:在“一個戰場”打贏“兩場戰役”〔N〕.光明日報,2020-12-02.
〔8〕 Banerjee,A.et al .Six randomized evaluations of microcredit:Introduction and further steps 〔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2015,7(1).
〔9〕 Pitt,M.M,Khandker.S.R.The Impact of Group-Based Credit Programs on Poor Households in Bangladesh: Does the Gender of Participants Matte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5).
〔10〕 Adelman,I & Robinson,S.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C〕.Handbook of Deuelopment Economics. Vol II,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Publishers B.V.,1989:pp.949-1003.
〔11〕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Robinson, James A .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5).
〔12〕 張占斌.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歷史邏輯、實踐特征和貢獻影響〔J〕.理論視野,2021,(7).
〔13〕 王紅艷.中國扶貧模式核心特征研究〔J〕.理論學刊,2020,(4).
〔14〕 盧旭東,楊抒婷.中國共產黨扶貧模式沿革的進路、動力及價值〔J〕.重慶社會科學,2023,(2).
〔15〕 位杰,徐海峰.駐村制度:精準扶貧視域下嵌入式扶貧模式探析——基于河北省顧家臺村的調查研究〔J〕.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16〕徐勇,陳軍亞.國家善治能力:消除貧困的社會工程何以成功〔J〕.中國社會科學,2022,(6).
〔17〕 周雪光.論中國官僚體制中的非正式制度〔J〕.清華社會科學,2019,(1).
〔18〕 〔19〕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劉守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8:64,50-55.
〔20〕 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J〕.社會學研究,2004,(5).
〔21〕 陳軍亞.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J〕.中國社會科學,2019,(12).
〔22〕 王丹利,陸銘.農村公共品提供:社會與政府的互補機制〔J〕.經濟研究,2020,(9).
〔23〕 胡近.實證社會科學:第10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152-154.
〔24〕 陳旭東.赫維茨的經濟思想譜系及其方法論〔J〕.財經研究,2020,(2).
〔25〕 埃里克·馬斯金.機制設計與中國經濟改革〔J〕.中國經濟報告,2021,(4).
〔26〕 高煜,郭俊華.21世紀的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204.
〔27〕 鄧大才,王墨竹.非正式制度與治理:一個比較研究框架——前沿理論、中國實踐與研究前景〔J〕.理論探討,2023,(1).
〔28〕 〔美〕羅伯特·K.殷.案例研究方法的應用〔M〕.周海濤主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4:51.
〔29〕 張存達.非正式制度因素影響下的利益沖突治理制度變遷分析〔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6).
〔30〕 卓宏勇.講好中國扶貧故事 唱響鄉村振興旋律——關于我國脫貧攻堅新聞宣傳工作回顧及思考〔J〕.中國出版,2021,(1).
〔31〕 張桂林.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公權力監督思想研究〔J〕.政治學研究,2022,(5).
【責任編輯:朱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