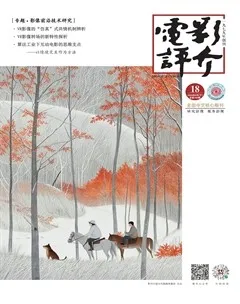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里斯本丸沉沒》:影像史學(xué)敘事下的“歷史在場”與“記憶感召”
【摘 要】" 《里斯本丸沉沒》作為一部搶救性歷史記憶紀(jì)錄片,獲得了業(yè)界和輿論的雙重口碑。從影像史學(xué)的視角出發(fā),該片讓鮮為人知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在當(dāng)代輿論場上重返并復(fù)活,以影像記憶的方式再次鐫刻在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中,也為后續(xù)研究二戰(zhàn)史的學(xué)者提供了珍貴的影像史料。本文主要聚焦并探尋《里斯本丸沉沒》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分的原因,指出《里斯本丸沉沒》運(yùn)用交叉敘事的手法講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以及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考據(jù)收集史料的全過程,并在“完全基于歷史事實(shí)”的前提下,以虛擬影像等具有想象性的現(xiàn)代影像技術(shù)呈現(xiàn)真實(shí)的歷史悲劇,形成了歷史場景與虛擬影像的互文互動,傳遞了反戰(zhàn)與和平的價值理念以及對具體的人的關(guān)愛,客觀展示戰(zhàn)爭的荒誕與無意義。此外,《里斯本丸沉沒》展現(xiàn)出的紀(jì)錄片導(dǎo)演的“歷史技藝”,也實(shí)現(xiàn)了中國話語的全球傳播,為從事對外傳播實(shí)踐的文藝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優(yōu)秀范例和行之有效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
【關(guān)鍵詞】 《里斯本丸沉沒》; 影像史學(xué); 紀(jì)錄片; “里斯本丸”沉船事件; 全球傳播
2024年9月6日,電影制片人與海洋探測工程師方勵耗時八年制作并導(dǎo)演的歷史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在國內(nèi)上映。作為一部搶救性歷史記憶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傾注了導(dǎo)演方勵的全部心血,但最終還是遭遇“叫好不叫座”的票房困境:上映兩周后,《里斯本丸沉沒》的票房僅為2000萬元,而影片需達(dá)到1.1億元的票房才可能回本①。
雖然《里斯本丸沉沒》暫未收獲一個亮眼的票房成績,但獲得了業(yè)界和輿論的雙重口碑。目前豆瓣網(wǎng)評分為9.3分,是2024年以來評分最高的國產(chǎn)院線電影②,“感動”“落淚”“人性光輝”等詞匯時常出現(xiàn)在《里斯本丸沉沒》的豆瓣影評中。在第十一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jié)上,《里斯本丸沉沒》榮獲“金絲路獎”最佳紀(jì)錄片,并將代表中國內(nèi)地競爭第97屆奧斯卡獎“最佳國際影片”。不少影迷對《里斯本丸沉沒》“沖奧”的新聞感到欣喜,認(rèn)為它實(shí)至名歸,盛贊《里斯本丸沉沒》代表中國內(nèi)地“沖奧”是“理想主義的勝利”。③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應(yīng)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優(yōu)秀的國產(chǎn)紀(jì)錄片數(shù)不勝數(shù),為何《里斯本丸沉沒》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分?講述英兵俘虜苦難遭遇故事的《里斯本丸沉沒》為何會深深感動中國觀眾?本文從影像史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剖析紀(jì)錄片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的“歷史技藝”。
一、“影像史學(xué)”敘事及其“集體記憶”感召屬性
在普羅大眾的固有印象中,歷史往往以文字的形式記載在史書上,但隨著科技水平的不斷進(jìn)步,作為新興技術(shù)的影像不僅成為人類社會的傳播媒介,更是人類歷史的重要載體,人類已經(jīng)進(jìn)入影像時代,以影像書寫歷史正在成為現(xiàn)實(shí)。[1]正如斯洛文尼亞學(xué)者阿萊斯·艾爾雅維茨(Ales Erjavec)所說:“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自身在當(dāng)今都已處于視覺(visuality)成為社會現(xiàn)實(shí)主導(dǎo)形式的社會。”[2]1988年12月,美國歷史哲學(xué)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美國歷史學(xué)專業(yè)刊物《美國史學(xué)評論》專門開設(shè)的“影視史學(xué)討論”專欄中發(fā)表了題為《書寫史學(xué)與視聽史學(xué)》(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的文章,懷特在文章中提出了“影像史學(xué)”(Historiophoty)的概念,認(rèn)為影像史學(xué)是指以影像的形式再現(xiàn)歷史和人們對歷史的理解[3],其主要意圖在于構(gòu)建電影與歷史之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這篇文章的發(fā)表標(biāo)志著“影像史學(xué)”的誕生。1996年,復(fù)旦大學(xué)張廣智教授發(fā)表論文《影視史學(xué):歷史學(xué)的新領(lǐng)域》,正式將“影像史學(xué)”等類似概念引入大陸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①。
影像史學(xué)雖然是近幾十年來新興的跨學(xué)科熱點(diǎn)話題,但是作為一種藝術(shù)形式和歷史載體,影像與歷史的結(jié)合有著源遠(yuǎn)流長的歷史。我國自古就有“左圖右史”的讀圖傳統(tǒng),“輿圖與史書對讀,可以互相參補(bǔ)印證。”[4]西方中世紀(jì)也有以圣經(jīng)故事人物為主角的圣像畫(icon),后來又從這些圣像畫的考察中發(fā)展出來所謂的“圖像學(xué)”(iconology)。[5]影像史學(xué)本質(zhì)上是在嘗試一種全民教育的大眾化歷史傳播方式。相較于文字,電影、紀(jì)錄片等影像媒介消除了人們的感官與被記錄對象之間的距離,使觀看主體不再受自身文化知識水平的限制。因此,使用影像記錄歷史、描述歷史,不僅使得單調(diào)乏味的歷史知識以及準(zhǔn)入門檻較高的史學(xué)研究得以“飛入尋常百姓家”,以生動形象的動態(tài)影像成為人民群眾生活娛樂的一部分,史學(xué)研究本身也能夠更加貼近人民群眾,更有生活氣息。[6]
不僅如此,法國歷史學(xué)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提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集體記憶又名群體記憶,哈布瓦赫認(rèn)為“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些框架內(nèi),并匯入到能夠進(jìn)行回憶的記憶中去”[7]。在此基礎(chǔ)上,電影等影像媒介不僅承擔(dān)著記錄事實(shí)、拓印歷史的保存功能,而且承擔(dān)著建構(gòu)和傳播集體記憶的功用。“二戰(zhàn)”是全世界人民重要的歷史集體記憶,但囿于敘事內(nèi)容的有限以及歷史原因,許多在“二戰(zhàn)”中爆發(fā)的中觀和微觀事件往往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曾是其中之一。根據(jù)檔案記載,“二戰(zhàn)”結(jié)束后,英國政府逐漸得知“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諸多信息,并于1948年向當(dāng)時的國民政府提出為參與救援盟軍戰(zhàn)俘的中國漁民贈與一筆捐款。但由于當(dāng)時國共兩黨正處內(nèi)戰(zhàn)焦灼之際,彼時的國民政府處理此事并不張揚(yáng),媒體也未做深度報(bào)道[8],加之戰(zhàn)爭帶來的心理創(chuàng)傷讓大部分事件各方當(dāng)事人選擇回避和遺忘,“里斯本丸”的歷史悲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鮮為人知。現(xiàn)如今,發(fā)達(dá)的電腦科技與傳播媒體為二戰(zhàn)歷史的再現(xiàn)提供了影視化、具象化的技術(shù)手段和空間。“又會拍電影,又能找到船”的方勵在舟山東極島海域?yàn)殡娪啊逗髸o期》(中國,2014)勘景時,無意中從漁民口中得知“里斯本丸”的故事,通過影像還原并講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重任壓在了方勵的肩膀上。從影像史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當(dāng)事人的口述回憶是鮮為人知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珍貴的歷史資料,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創(chuàng)意、籌備、采訪記錄以及放映傳播《里斯本丸沉沒》的全過程更是一次與時間賽跑的史料搶救行動。《里斯本丸沉沒》將零散模糊的歷史記憶轉(zhuǎn)化為直觀可感、生動在場的視聽語言,讓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悲劇在輿論場上重返與復(fù)活,并以影像記憶的方式鐫刻在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中,為后續(xù)的史學(xué)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影像史料。此外,在全球局勢緊張的大背景下,《里斯本丸沉沒》不僅令觀眾充分感受到戰(zhàn)爭的殘酷和人性的可貴,同時也給予輿論場反思戰(zhàn)爭、珍愛和平的討論空間,影片的價值得以拓展和延伸。
二、影像史學(xué)“歷史在場”式敘事:“口述”“行旅”敘事交互下的記憶復(fù)原
交叉敘事是指存在于不同時空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故事,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同時展開的敘事手法,交叉敘事既可以講述一個故事的多個視角,也可以講述一個視角的多個故事,故事線之間相對獨(dú)立,但人物故事情節(jié)有所延續(xù)。交叉敘事在我國古代章回小說中也時常出現(xiàn),例如《紅樓夢》中就有“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說法。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跨越時空的非線性交叉敘事也是感染觀眾情緒的關(guān)鍵。
《里斯本丸沉沒》大致有兩條故事線,第一條故事線是“歷史回溯線”,主要通過歷史影像、虛擬影像以及當(dāng)事人口述等方式還原“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全過程。82年前,即1942年9月25日,“二戰(zhàn)”中入侵香港的日軍將1816名駐守香港(彼時為英國殖民地)但隨后投降的英軍戰(zhàn)俘押上了“里斯本丸”(Lisbon Maru),“里斯本丸”是一艘被日本軍方征用的由日本民用客輪改裝而成的貨輪,該船計(jì)劃于兩天后啟航前往日本。由于日軍違反《日內(nèi)瓦公約》①,未在“里斯本丸”船身懸掛任何運(yùn)送戰(zhàn)俘的旗幟或標(biāo)志,導(dǎo)致“里斯本丸”于10月1日行駛至浙江舟山群島附近海域時,被美軍潛艇“鱸魚號”發(fā)射的魚雷擊中。當(dāng)天,日軍派遣艦艇悉數(shù)接走“里斯本丸”上的日軍,并將正在下沉的“里斯本丸”拖曳至中國舟山海域的東極島附近的淺水區(qū)。為了防止戰(zhàn)俘逃跑,日軍封死了所有戰(zhàn)俘艙口。為求一線生機(jī),10月2日,英軍戰(zhàn)俘奮勇自救,破艙逃生,但遭到日軍阻擊,828位戰(zhàn)俘不幸犧牲。危難之際,中國東極島附近的漁民冒著生命危險(xiǎn),立即自發(fā)駕駛小舢板救起384名盟軍戰(zhàn)俘。盡管如此,大部分生還的盟軍戰(zhàn)俘被日軍再度捕獲,僅有3名戰(zhàn)俘在漁民掩護(hù)下躲過搜捕。②戰(zhàn)爭帶來的心理創(chuàng)傷讓大部分盟軍戰(zhàn)俘在返回故鄉(xiāng)后選擇回避和遺忘此事,在宏大的二戰(zhàn)史中,“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在爆發(fā)前后的短時間內(nèi)被有限地關(guān)注后便消失在大眾視野,成為史學(xué)研究中一塊極其微小的領(lǐng)域。“里斯本丸”沉沒在中國領(lǐng)海后,也沉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第二條故事線是“搶救史料線”,這條故事線采用行旅敘事,由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擔(dān)任尋訪歷史的主角。借助行旅敘事,《里斯本丸沉沒》巧妙地將方勵以及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尋訪“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當(dāng)事人的故事串聯(lián)起來,從而建構(gòu)一個完整流暢的戲劇結(jié)構(gòu),使整部紀(jì)錄片的敘事節(jié)奏更加緊湊,紀(jì)錄片的真實(shí)感、可信度以及敘事的流動性均得以增強(qiáng),觀眾也能意識到,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攝制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的過程不僅僅是在爬梳文獻(xiàn)、還原歷史,全球化的尋人啟事、生還者的親身講述、遇難者的物件信函、后代人的追思回憶、遇難者后人的中國之行,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喚醒全人類普遍情感的攝制行動本身也是在書寫歷史。這些展現(xiàn)實(shí)際行動的行旅情節(jié)都蘊(yùn)含著《里斯本丸沉沒》的吸引力,充滿了起承轉(zhuǎn)合的節(jié)奏性,它沒有設(shè)計(jì)卻比設(shè)計(jì)更精彩,它的想象力比劇情片更具有吸引力。③在“歷史回溯線”與“搶救史料線”的交叉敘事下,盟軍戰(zhàn)俘、美軍炮手、“里斯本丸”船長等事件當(dāng)事人的故事延續(xù)至他們的后代,并最終在事件的發(fā)生地——“里斯本丸”的沉船點(diǎn)會合。如果說以林阿根為代表的中國漁民拯救了盟軍戰(zhàn)俘的生命,那么由方勵牽頭的《里斯本丸沉沒》的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打撈和搶救的歷史遺產(chǎn),則拯救了幸存戰(zhàn)俘及其家屬的精神,兩代中國人完成了拯救“里斯本丸”的歷史閉環(huán)。在某種程度上,導(dǎo)演方勵就是林阿根的當(dāng)代化身。
三、影像史學(xué)“客觀性”敘事及其超越:“零度敘事”及其“時刻想象”
紀(jì)錄片是創(chuàng)作者根據(jù)自己對生活與自然所特有的認(rèn)識和理解,以記錄真實(shí)為前提基礎(chǔ),以現(xiàn)場拍攝為主要手段,對社會和自然中實(shí)際存在著的人、事、物及其思想文化內(nèi)涵進(jìn)行藝術(shù)再現(xiàn)的影視片,客觀存在是紀(jì)錄片必須遵守的前提。[9]紀(jì)錄片以記錄不可復(fù)現(xiàn)的時間流程和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反映而顯示出特殊價值。作為歷史的“立體檔案”和“現(xiàn)實(shí)的文獻(xiàn)筆記”,紀(jì)錄片為人們留下了一份生動翔實(shí)的歷史資料。[10]大海沉船的故事永遠(yuǎn)充滿吸引力,宏大戰(zhàn)爭背景下個人命運(yùn)的走向總能調(diào)動觀眾興趣,正如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的歷史顧問、首位研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學(xué)家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在紀(jì)錄片中所說:“整個事件如此真實(shí)但又如此具有‘三幕結(jié)構(gòu)’式的戲劇性,符合人們的懸念需求和情感預(yù)期”。紀(jì)錄片也是一種敘事方式,如何在抓住“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真實(shí)性的同時,用戲劇性和藝術(shù)化的方式進(jìn)行表達(dá),成為決定《里斯本丸沉沒》成敗的關(guān)鍵。相較于其他二戰(zhàn)題材的院線影片,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并沒有簡單粗暴地控訴日軍的暴徒行徑,從而激起觀眾樸素的民族情緒或個人情緒,也沒有因?yàn)楣适轮泻兄袊蛩囟e奪主,刻意夸大中國漁民見義勇為的優(yōu)良品質(zhì),更沒有將日本軍方等所謂的加害者刻畫成臉譜化的反派并當(dāng)庭審判,而是尊重“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主線,站在第三方視角抽絲剝繭地采訪幸存戰(zhàn)俘、戰(zhàn)俘遺孤、美軍炮手等各方當(dāng)事人,包括“里斯本丸”船長后代等世俗意義上的“反面角色”,并最終將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記憶碎片”復(fù)原成一塊完整的歷史拼圖。對于一場由戰(zhàn)爭造成的人道主義災(zāi)難,這種克制情感、沉著冷靜的敘事語態(tài)既向觀眾客觀展現(xiàn)了宏大戰(zhàn)爭下個體的無奈與人性的光輝,也賦予事件各方當(dāng)事人打破沉默、敘述歷史的權(quán)力,為觀眾多維度思考戰(zhàn)爭的荒誕與無意義提供了反思的情緒空間,符合紀(jì)錄片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客觀原則。
真實(shí)雖然是紀(jì)錄片的生命,但是紀(jì)錄片并不單純是記錄史實(shí)的工具。自從“紀(jì)錄片之父”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攝制并放映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紀(jì)錄片《北方的納努克》(美國,1922)以來,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手法向來是“紀(jì)實(shí)”與“虛構(gòu)”的有機(jī)結(jié)合。英國紀(jì)錄片導(dǎo)演約翰·格里爾遜(John Grierson)認(rèn)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是“對真實(shí)事物做創(chuàng)造性處理”[11]。在《里斯本丸沉沒》中,紀(jì)錄片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充滿想象力的藝術(shù)表達(dá)也成為挑動觀眾淚點(diǎn)的關(guān)鍵。除了兩位彼時在世的幸存戰(zhàn)俘,幾乎無人知曉“里斯本丸”沉沒當(dāng)天的真實(shí)情景,所有技術(shù)手段的還原都在挑戰(zhàn)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的想象力。《里斯本丸沉沒》的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根據(jù)片段史料的發(fā)掘、僅存的幸存者回憶和一些幸存者家屬的敘述,借助動畫“復(fù)原”了當(dāng)時的沉船情景:戰(zhàn)俘們的無助絕望和堅(jiān)持,臨死前的紳士風(fēng)度、日本兵的反人道屠殺……相較于真實(shí)的歷史影像,這種基于事實(shí)又帶有想象成分的藝術(shù)化處理,更能讓觀眾產(chǎn)生視聽兼?zhèn)涞某两小"?/p>
四、影像史學(xué)式“史料敘事”:“歷史復(fù)原敘事”與“臨場感營造”
媒介的本質(zhì)就是放大,其中影像的放大作用更加顯著。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等宏大戰(zhàn)爭下的歷史悲劇的敘事層面,影像史學(xué)對歷史的書寫與傳播可以起到強(qiáng)大的情緒渲染作用,且相比文字等媒介而言更具感染力和表現(xiàn)力。當(dāng)遇到無法獲取歷史影像的場景時,數(shù)字虛擬技術(shù)為豐富紀(jì)錄片的影像內(nèi)容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相較于歷史場景與虛擬影像之間忠實(shí)性問題,二者之間的互文性問題更是關(guān)注重點(diǎn)。“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是由法國文學(xué)批評家朱莉婭·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提出的重要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的構(gòu)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zhuǎn)換。[12]互文性理論認(rèn)為,任何文本都不是獨(dú)立存在的,文本之間必然相互參照牽扯,形成一個連接時間與空間的可供延伸的符號網(wǎng)。[13]現(xiàn)實(shí)場景與虛擬影像的互文互動亦是《里斯本丸沉沒》撥動觀眾心弦的關(guān)鍵。虛擬影像不能過度虛構(gòu),它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還原。對于《里斯本丸沉沒》等歷史類紀(jì)錄片,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很難指望通過單純的真實(shí)記錄影像還原現(xiàn)實(shí)情況,因此,如何縮小影像與歷史的分野,平衡藝術(shù)表達(dá)中的歷史還原與失真,使動畫設(shè)計(jì)最大程度地貼合歷史情景,成為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設(shè)計(jì)并運(yùn)用虛擬影像補(bǔ)充紀(jì)錄片畫面的關(guān)鍵問題。當(dāng)“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諸多歷史表述接近于消亡之時,出于搶救史料的目的,制作虛擬影像也許才是接近歷史真實(shí)的解決路徑,而賦予虛擬影像以真實(shí)性的關(guān)鍵,就在于對歷史存在模式模擬的接近程度。[14]
毫無疑問,《里斯本丸沉沒》在真實(shí)性層面做到了嚴(yán)謹(jǐn)?shù)目紦?jù),開篇字幕“本故事完全基于歷史事實(shí)”足以給觀眾吃下一顆定心丸。為了多角度印證與還原“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事實(shí),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歷時8年輾轉(zhuǎn)中國、英國、加拿大、美國、日本等國多地,采訪了120多位盟軍戰(zhàn)俘的家屬,以及事件其他當(dāng)事人的后代和歷史學(xué)家,攝錄和采集了數(shù)倍《里斯本丸沉沒》的影像素材與歷史材料。時間所具有的歷史厚重感、客觀性以及歷史的公正性,必須在這種為了真實(shí)性而進(jìn)行的艱苦工作的基礎(chǔ)上才能產(chǎn)生。[15]對于歷史類紀(jì)錄片而言,真實(shí)性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其中,宏觀歷史事實(shí)的細(xì)節(jié)固然關(guān)鍵,但是隱藏在歷史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更能感動觀眾。于是,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以近乎搶救性的速度采訪了彼時仍在世的兩名英軍戰(zhàn)俘和一名參與救援的中國漁民,匯編成具有珍貴歷史意義的口述史。《里斯本丸沉沒》的創(chuàng)作固然離不開“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材料及口述史,然而,對史料的簡單編排與堆砌無法構(gòu)成有生命力的歷史,真正的歷史應(yīng)是生動而鮮活的[16],是一種深刻的歷史解讀。為此,《里斯本丸沉沒》的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在確保紀(jì)錄片內(nèi)容真實(shí)可信的前提下,建構(gòu)一系列具體清晰的人物形象,使之在內(nèi)容表現(xiàn)上飽滿豐富,情感傳遞上深刻動人。此外,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通過動畫設(shè)計(jì)等高新影像技術(shù),使得“戰(zhàn)俘用摩斯密碼傳遞信息”“第一位被困戰(zhàn)俘刺破黑暗,迎接陽光的瞬間”“盟軍戰(zhàn)俘在日軍槍口下相互幫助”以及“中國漁民與落難戰(zhàn)俘的交談”等諸多歷史細(xì)節(jié)能夠超脫口述史料以及文字材料等單一文本的桎梏,在歷史場景與虛擬影像的互文互動中以藝術(shù)化的表現(xiàn)形式“再現(xiàn)歷史”,讓觀眾身臨其境般地回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現(xiàn)場,帶給觀眾真聽、真看、真感受的視覺和情感體驗(yàn)。如此這般,歷史場景的考據(jù)與虛擬影像的呈現(xiàn)得以在《里斯本丸沉沒》中以影像互文的關(guān)系更好地表現(xiàn)出來,這些在宏大歷史敘事中往往被忽略卻又蘊(yùn)含著細(xì)膩情感的歷史細(xì)節(jié),也因?yàn)橛跋袷穼W(xué)的切入而獲得巨大的傳播空間。
五、影像史學(xué)的“人之歷史主體”敘事:情感敘事及書寫“具體的人”策略
從影像史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里斯本丸沉沒》作為主體參與并構(gòu)建的成果,其并非“里斯本丸”沉船事件鏡像化的直接反映,而是具有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主觀意愿的歷史敘述。因此,敘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視角和語態(tài)既反映了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也影響了觀眾認(rèn)知?dú)v史的思想觀念。人文社科離不開對人的關(guān)注,作為影視藝術(shù)的紀(jì)錄片始終要以表現(xiàn)人的生命活動和社會活動為中心。[17]有的歷史紀(jì)錄片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往往會忽視人的主體性地位,將微小的個體淹沒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或者將其籠統(tǒng)地概括為抽象化符號,這樣的紀(jì)錄片不僅容易讓觀眾忽視對生活中微觀個體的關(guān)注,而且容易陷入群像傳播的誤區(qū),難以讓觀眾產(chǎn)生共情。在同類災(zāi)難影片《泰坦尼克號》(美國,1997)中,總計(jì)有兩千多名無辜的旅客和船員死亡,對于大部分“無名氏”的死亡,觀眾可能會感到震撼,卻很難感到心碎,但是當(dāng)杰克的身影緩緩沉入冰冷的北大西洋后,觀眾的眼淚才唰地掉了下來。學(xué)者鄒振東指出,這是因?yàn)閺?qiáng)調(diào)集體以及“人海戰(zhàn)術(shù)”的群像傳播是最難產(chǎn)生效果的傳播類型,觀眾的淚點(diǎn)更容易被一個個具體的命運(yùn)所打動,個體的傳播往往比群像傳播更容易打動人心。①
雖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發(fā)生在宏大的二戰(zhàn)歷史背景當(dāng)中,但是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超越了傳統(tǒng)的歷史宏大敘事,沒有將英軍戰(zhàn)俘視為一個籠統(tǒng)抽象的群像,而是讓具體的事件當(dāng)事人講述具體生動的故事,擺脫群像傳播的桎梏,從而襯托出戰(zhàn)爭本身的荒誕與無意義。例如美軍炮手加菲爾德在自己生日這天向滿載同盟軍的“里斯本丸”發(fā)射魚雷,他的朋友在寄給他的生日賀卡上還寫道“祝賀你擊中敵軍艦船,生日快樂”,在得知“里斯本丸”上死去的都是盟軍后,加菲爾德因罹患精神疾病而退伍。此外,“里斯本丸”最初只是一艘貨船,“里斯本丸”的船長經(jīng)田茂也只是一個平民船長,他本人并不愿意拋下英國戰(zhàn)俘,但是在日軍的槍口面前,經(jīng)田茂只能被迫執(zhí)行命令。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經(jīng)田茂在香港軍事法庭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刑滿釋放兩年后,經(jīng)歷了一場無妄之災(zāi)的經(jīng)田茂憂郁至死。在遇到方勵之前,經(jīng)田茂的子女甚至不知道“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對于一起客觀存在的沉船事件,《里斯本丸沉沒》并沒有剝奪加害者發(fā)聲的權(quán)力,相反,這些所謂的加害者對于殘酷的歷史事實(shí)的口述會讓觀眾感覺更加客觀真實(shí)。
《里斯本丸沉沒》更為虐心的地方在于導(dǎo)演方勵在影片開頭就預(yù)先告知觀眾“結(jié)局已定”,給觀眾的思緒里植入了“命定”的潛意識。在此基礎(chǔ)上,影片以倒敘形式講述種種美好的親情和愛情時,更能強(qiáng)化這些故事帶給觀眾的沖擊力,讓觀眾意識到戰(zhàn)爭的荒謬與無意義,導(dǎo)致每一個被迫卷入其中的個體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受害者。
與這種批判荒誕戰(zhàn)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影片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對于具體的人的愛。愛是人類輿論的最高價值,也是人類輿論認(rèn)同度的最大公約數(shù)。在藝術(shù)輿論場中,愛情是電影乃至一切藝術(shù)的主流輿論,是藝術(shù)永恒的主題。[18]例如在同為船難事故的經(jīng)典電影《泰坦尼克號》中,無論是將要被淹沒的女主人公拿著斧頭解救男主人公的畫面,還是男主人公死后還緊緊支撐著女主人公的橋段,都彰顯出愛情的偉大與責(zé)任的崇高。[19]正如魯迅所說,悲劇就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20],當(dāng)災(zāi)難或戰(zhàn)爭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愛,作為苦難見證者的觀眾自然難掩淚水。《里斯本丸沉沒》也講述了一段被戰(zhàn)爭摧毀的愛情,1940年,從廈門逃難到香港的中國女性梁素琴(后修正為“梁秀金”)與英國士兵約翰·韋弗(John Weaver)相愛,韋弗在寄給母親的信中坦白了這段愛情,并決定在1941年的圣誕節(jié)舉辦婚禮,但是香港保衛(wèi)戰(zhàn)在婚期這天爆發(fā),韋弗淪為戰(zhàn)俘,隨后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葬身海底,一場戰(zhàn)爭帶來的無妄之災(zāi)讓戀愛中的男女天人永隔。被戰(zhàn)爭摧毀的愛不只是男女之間的愛戀,還包括對親人的眷戀。一位英國士兵給家里寫了一封家書,因?yàn)閼?zhàn)爭以及通信設(shè)施落后等因素,這封流露著一位士兵強(qiáng)烈的回鄉(xiāng)愿望的家書直到三年后才送到他的家人手中,但是家書的主人已經(jīng)陣亡在中國東極島海域,這封家書也成了他的遺書。一段段普通人的恩怨情仇與悲歡離合支撐起《里斯本丸沉沒》的敘事內(nèi)容與情感網(wǎng)絡(luò),足以讓觀眾代入劇中的角色,進(jìn)而萌生出感同身受的共情效應(yīng)和印象深刻的觀影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里斯本丸沉沒》的片尾滾動字幕猶如一座莊嚴(yán)肅穆的“歷史豐碑”,詳細(xì)地公布了1816名盟軍戰(zhàn)俘以及參與救援的中國漁民的名字。在中觀尺度的戰(zhàn)史事件意義上,“里斯本丸”的悲劇雖在極小的范圍內(nèi)被有限地關(guān)注到,但往往被學(xué)者和史家們作為二戰(zhàn)期間的諸多戰(zhàn)爭慘劇之一,經(jīng)歷生死劫難的1816名盟軍戰(zhàn)俘也被籠統(tǒng)地描述為一個單薄的數(shù)字。①學(xué)者鄒振東在《生命永遠(yuǎn)是個位數(shù)》中寫道:“生命永遠(yuǎn)是個位數(shù)。死一個人和死千萬人,對于當(dāng)事人和他的親人,沒有千分之一,只有百分之百。”②抽象籠統(tǒng)的數(shù)據(jù)是缺乏震撼力的,具體清晰的數(shù)據(jù)才會給人震撼。從影像史學(xué)的視角出發(fā),《里斯本丸沉沒》在院線紀(jì)錄片的片尾字幕公布名單,就是將“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罹難者以及救援者刻入歷史,這既是對逝者的最大尊重,也是將悲劇的感染力由抽象化為具體,警醒世人反思戰(zhàn)爭,珍視和平的同時,也令后人記住他們的存在。在《里斯本丸沉沒》中,觀眾足以透過一個個具體的人的人性閃光瞬間,感知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對于每個個體的重視。《里斯本丸沉沒》對于具體的人認(rèn)真和莊嚴(yán)的態(tài)度,讓觀眾為之動容。
結(jié)語
意大利史學(xué)理論家貝奈戴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21]從“文以載道”到“影以載道”,電腦技術(shù)以及傳播媒介的進(jìn)步也推動了歷史書寫方式的變革,具有真實(shí)性保證的影像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歷史證據(jù),為多元化的歷史敘述提供史料依據(jù)。導(dǎo)演方勵及其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對于史料的挖掘與梳理的目的,不僅是回溯再現(xiàn)“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歷史事實(shí),更重要的是提取其中蘊(yùn)含的當(dāng)代價值。作為一部由中國人講述的以外國人為主人公的紀(jì)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實(shí)現(xiàn)了中國話語的全球傳播,跨越國界藩籬的和平頌歌永遠(yuǎn)具有團(tuán)結(jié)各國人民的聲量。正如方勵本人所說,《里斯本丸沉沒》就是想用真實(shí)的歷史告訴大家,戰(zhàn)爭可以毀掉一切,要遠(yuǎn)離戰(zhàn)爭,珍惜和平。這也正是《里斯本丸沉沒》打動人心的地方,也是該片廣受好評的原因。①
《里斯本丸沉沒》不僅將“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刻入公眾的集體記憶,傳遞了反戰(zhàn)與和平的價值理念,為后續(xù)研究二戰(zhàn)史的學(xué)者提供了珍貴的影像史料,同時,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及有效提升中國國家形象的親和力和傳播實(shí)效等方面,《里斯本丸沉沒》展現(xiàn)出紀(jì)錄片導(dǎo)演的“歷史技藝”,也為從事對外傳播實(shí)踐的文藝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優(yōu)秀范例和行之有效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
參考文獻(xiàn):
[1]姜萌,陶賦雯,滕樂,施琪航.歷史的影像與影像中的歷史——影像史學(xué)的溯源、辨思與發(fā)展前瞻[N].光明日報(bào),2022-02-16(011).
[2][斯洛文尼亞]阿萊斯·艾爾雅維茨.圖像時代[M].胡菊蘭,張?jiān)迄i,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6.
[3]White H.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8(05):1193-1199.
[4]劉躍進(jìn),周忠強(qiáng).“左圖右史”的傳統(tǒng)及圖像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運(yùn)用[ J ].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5(03):120-128,192.
[5]王燦,魏麗蓉.影像史學(xué)視域下三線建設(shè)研究的價值邏輯與實(shí)踐路徑[ J ].寧夏社會科學(xué),2023(06):192-198.
[6]王鎮(zhèn)富.影像史學(xué)研究[D].濟(jì)南:山東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2011.
[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9.
[8]唐洪森.中英處理救助“里斯本丸”戰(zhàn)俘義舉述論[ J ].民國檔案,2009(03):112-115,111.
[9]邵雯艷.在藝術(shù)的名義下——紀(jì)錄片真實(shí)的美學(xué)含義[ J ].中國電視,2007(08):61-64.
[10]唐晨光.影視史學(xué)——?dú)v史學(xué)家如何透過影像來研究和考證歷史[ J ].電影評介,2011(03):1-3.
[11]Grierson J.FROM \"FIRST PRINCIPLES OF DOCUMENTARY\" (UK, 1932)[ J ].Film Manifestos and Global Cinema Cultures,2014:453-459.
[12]Kristeva J.Bakht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 J ].Critique,1967(33):438-465.
[13]范志忠,喻文軒.影游改編的跨媒體想象力與敘事機(jī)制[ J ].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22(03):46-56.
[14]陶濤,張德宏.虛擬真實(shí)·主觀真實(shí)·質(zhì)樸真實(shí)——論紀(jì)錄片真實(shí)的三個層面[ J ].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05):156-158.
[15]程波.《里斯本丸沉沒》:從塵封的史實(shí)到影像的史詩[N].解放日報(bào),2024-09-19(009).
[16]范高培.民族記憶的影像書寫與互文形塑:紀(jì)錄片《伊文思看中國》創(chuàng)作研究[ J ].電影評介,2024(09):86-91.
[17]邵雯艷,楊涵.歷史紀(jì)錄片:構(gòu)建現(xiàn)在與過去的“對話”[ J ].中國電視,2022(09):22-27.
[18]鄒振東.弱傳播:輿論世界的哲學(xué)[M].北京:國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18:146-147.
[19]陳旭光,張明浩.論災(zāi)難電影的奇觀美學(xué)、敘事、主題及當(dāng)下啟示[ J ].藝術(shù)評論,2020(04):62-77.
[20]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203.
[21][意]克羅齊.歷史學(xué)的理論和歷史[M].田時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5:238.
【作者簡介】" "黃浩宇,男,江西瑞金人,浙江大學(xué)傳媒與國際文化學(xué)院博士后(在站),主要從事影視文化及傳播研究;
李彥清,男,湖南長沙人,華僑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碩士生。
①潮新聞.豆瓣漲到9.3,票房過千萬!《里斯本丸沉沒》逆襲!方勵卻說:決定拍時,就知道不可能收回成本[EB/OL].(2024-09-16)[2024-09-16].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2902308.
②澎湃新聞.豆瓣9.3分的年度罕見高分!這部關(guān)于舟山的電影你看了嗎?[EB/OL].(2024-09-23)[2024-08-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835825.
③聯(lián)合早報(bào).中國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將報(bào)名競逐奧斯卡[EB/OL].(2024-09-28)[2024-09-28].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40928-4879709.
①參見:張廣智.影視史學(xué):歷史學(xué)的新生代[J].歷史教學(xué)問題,2007(05):36-41.
①參見:《日內(nèi)瓦公約》第三部第六編第二十三條規(guī)定,戰(zhàn)俘營在白天應(yīng)標(biāo)明自高空清晰可見之PW或PG字母。
②參見:于澤遠(yuǎn):《里斯本丸沉沒》為何廣受好評?[EB/OL].(2024-09-23)[2024-09-25].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40923-4804506.
③參見:李立.無法復(fù)制的創(chuàng)作——《里斯本丸沉沒》的秘密[EB/OL].(2024-09-16)[2024-09-2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744486.
①陳旭光.《里斯本丸沉沒》:沉沒的是歷史 打撈的是不該忘卻的記憶[EB/OL].(2024-09-25)[2024-09-25].https://mp.weixin.qq.com/s/qg54mDd3HzbkDNgHJmI7qQ.
①參見:鄒振東.電影里的傳播學(xué)——從電影《長津湖》講起 | 博雅茶座(第一期)[EB/OL].(2021-11-03)[2024-09-2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F411a7yA/.
①王升遠(yuǎn).《里斯本丸沉沒》:那些沒有墓碑的生命,意味著什么?[EB/OL].(2024-09-23)[2024-09-25].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27070185168019.html.
②鄒振東.生命永遠(yuǎn)是個位數(shù)[EB/OL].(2013-04-11)[2024-09-25].https://www.infzm.com/contents/89611?source=131.
①于澤遠(yuǎn).于澤遠(yuǎn):《里斯本丸沉沒》為何廣受好評?[EB/OL].(2024-09-23)[2024-09-23].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40923-4804506.